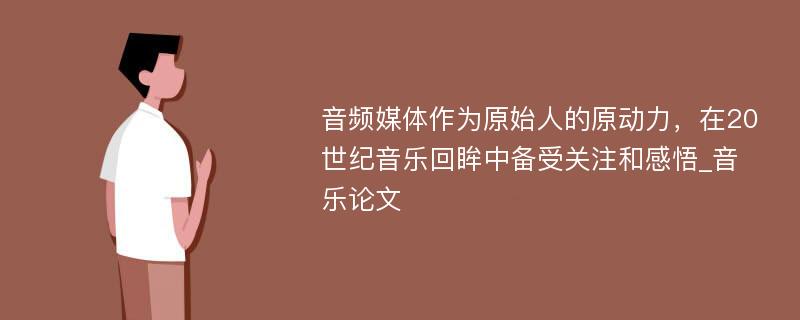
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并感性作为最初的人本驱动——通过20世纪音乐回望之后的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论文,感性论文,音响论文,最初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疑,艺术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不断地寻找一种合式的形式,即创造一个尽可能足以替代生活原型的对应物;而审美就在此发生。处在20世纪末端,如果真要对职业化分工后了的所谓“现代音乐”,有一个属于定位性质的“给出”,则就是: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
回望世纪,也许不会怀疑,文化的多元性,已然成型。与其说,这是一种属前瞻性的“真实”判断,不如说非理念使然,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海上景观”——在一片汹涌澎湃的汪洋(大众文化)之中,一个颠簸沉浮的舢舨(知识分子文化)随着海浪而起伏,它一再绕行于自言自语的孤岛(制度文化),试图守护被无尽开垦并极度消费而肢解了的大陆架资源库(民间文化),并防范着海上幽灵(神秘文化)的乘虚而入……。
设问:为什么同一文化物(音乐),有其不同的性质类别(经典,民间,流行,实验,宗教,等等)?简单的回应,因不同文化当事人所创制诠释或者传承、传播。进而,之所以不同行为姿态,则不同文化当事人自身结构使然。于是,有了不同的叙事风采,以及可持续并可垂范的人文风格——及不同风土并世俗情怀,及不同体裁并物象辞态,及不同传统并人文籍贯,及不同境界并终极关怀,等等。
然而,多分天下并非当下始端,众声喧哗亦不由此终端。无非是,因“多元文化”成型,并冠以“主潮名义”。于是,多分天下无轴心,众声喧哗无秩序。之后,宁静不见了,只有尘嚣。
而这个“之后”,尤其,针对极端专业化了的“现代音乐”。因为,在文化多元的语境当中,有一个几乎贯穿世纪的动荡,这就是“现代音乐”。作为一个个例,似乎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人类音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变革最为频繁和剧烈的一个世纪。尤其,随着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部分作品,无论在总体风格样式,还是在具体技法手段上,都有相当规模的流变与衍变。进度之快,力度之强,幅度之大,程度之深,承受度之弱,都是以往历史所不可比拟的。而所谓“不可比拟”,就在于: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
无疑,在“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之后,已然有一个隐型的潜在答案在:我们正处在传统意义上的旋律萎缩至极的状态,并且,作为一个存在,又与20世纪新音乐,及其大量实验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存在本身,至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背景。
以西方音乐为例,这一时段发生了两次重大革命(在此之前,作为历史过渡,分别呈现出音响结构愈益紧张与愈益松驰的趋向,大致可以后期浪漫派音乐和印象派音乐作为典型)——
第一次:大/小调功能体系全面瓦解,其中,十二音体系的规范成型,可视为音高元素被极度扩张的极端个例;第二次:寻找新的音响资源,并极度扩张音响的取域范围,其中,音色/音响音乐及其泛化,可视为音色元素被极度扩张的极端个例。具体而言——
十二音,依照十二个半音均匀等分的平均律原则,将十二个音作完全独立意义的处理,为避免重复并形成“引力中心”,有相应禁忌:在原型音例尚未完整呈示之前,十二个音的身份只有一次有效。于是,在绝对平等的前提下,成就一种“去中心”“平面化”的样式。然而,由于自然次第顺序的不可逆动,况且,“不协和”作为其主导关系,因此,在“均匀切割”与“平面无隙”的形态预设之后,并“音响还原”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仍然会显现出“切割不等”与“凹凸不平”的形态。
音色/音响音乐,其前提在于:一、极度扩张传统的音响结构方式,纵向上,在和弦/和声、调性/调式之后,有音簇/音块/音柱等等;横向上,在节奏/节拍、乐句/乐段之后,有点状/线状/网状等等。二、对所有音响的全面开禁,甚至冠以“全声音”的名义,不仅有非规则的乐音,有人工合成的声音,还有噪音的介入,甚至,有告别“媒体”的无声(可视为后现代音乐文化的开端)。于是,乐音沦陷:消解调式/调性中心,噪音介入:拆除乐音/噪音界限,告别媒体:贯通有声/无声障碍。
此外,乐音构成元素中的余下二者:音长与音强,除了分别对音高扩张与音色扩张有所推助之外,其本身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比如:大量汲取或者分享民间音乐的节奏/节拍资源,再比如:通过人工合成音响(电声)可将音强推至极限。
至此,通过拉动技术,不仅推动乐音构成元素及其相应方式的空前增长,而且,引发人的音响感受方式,进而,改变其先在的意义指向。
一切似乎都处在“失重”了的“真空”当中——
没有了调性体系,每个音都因为绝对的独立自主,而退出中心;
没有了乐音体系,只要可以发声,或者引发声响,都可能构筑材料;
没有了强声律动循环体系,节拍的门槛被拆卸;
没有了规则的纵横疏密层次,以及多声编织体系,一切都可能镶嵌在均匀的网底;
没有了曲式结构体系,对称与平衡不再成为唯一;
等等。
其直接结果:音响结构形态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不仅在材料,而且在样态,不仅在空间,而且在时间。其间接后果:则旋律轮廓被消解,主题通道被拆除。
于是,捅开了说,所谓“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之后,就是当下音乐正面临一个“无旋律”“无曲调”“无主题”处境,或者说,再度进入“自然声音”的“无差别”境界。
对此,有人形容为:惯性的小舟被倾覆;有人则预测:可推进一种新经验的生成。
对此,既可以说:选择的门道是最最狭窄的;也可以说:选择的路径是最最宽阔的。
依此推展: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所发生的轴心位移是取向多元——理性逻辑,比如:以调性为轴心的聚合型格局开始向边缘化、平面化格局转换,共性写作向个性写作转型,感性运作被理性操作所替换;那么,第二次革命所发生的轴心重建则似乎又开始取向单元——非理性逻辑,比如:边缘化、平面化的分离状态再度向“音色——音响”轴心聚合,“音色——音响”取代“主题——旋律”,当然,个性写作似乎更趋向于“当时写作”。
两次重大革命以及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造成的影响是大面积的,无论东西文化,还是古今文化,或者雅俗文化,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不同重心与各自内部之间的不同比重,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根本的变换或置换。
在中国,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两次重大革命、以及所造成的两度传统文化言路断裂,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专业音乐话语系统的两次“失语”,其后果就是,历史时序的断裂、文化约定的断裂、叙事对象的断裂。甚至有人这样断言,近二十年,一部分中国音乐的发展,已然有这样的显示:文化颠覆成了,“母语环链”断了。这是一种代价?还是一个过程?而根本的问题所在,即:在绞断“母语环链”之后……能否继续文化颠覆?
就现象而言,及其表层外延,这次重大革命以及所造成的两度传统断裂(古典——浪漫主义传统的断裂与部分现代主义传统的断裂),几乎都是直接由技术元素的极度分离与总体结构的主导元素位移所引发的;然而,究其深层内涵,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文化变革,则仍然与当代文化迅速进入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文化统摄圈相关。由此可见,当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现象一旦出场,便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一部分超前激进分子(集团)进行行为操作与心理宣泄的实验场所。这部分文化当事人不仅不愿忍受以机器与工厂为标记、以分工流水线为机制的主导文化的统摄,对标准化产品大批量复制的现代工业文明充满厌恶,于是,萌发焦躁心理与愤怒情绪;而且又不堪承受以集团权力意志与高度职业分工为象征的主宰型意识形态的统治,对规范化人格大面积定位的宪制政治产生厌倦,于是,施以政治抗议与文化反叛行为。就这样,大量实验音乐(例如:具体音乐、噪音音乐、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空间音乐、电子计算机音乐、简约音乐、音色——音响音乐、新浪漫主义音乐、新复杂主义音乐,等等)的出现,也许,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逆反心理、情绪与抗议、反叛行为)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了现实的辩护。
就本体而言,音乐是人的创造,音乐作为人文化的开端和终端,进而,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已然不是自然本体,但又来自自然。从而,不可排除人类对声音的无穷探索,作为一个合理存在,不仅要研究“全音乐”“全乐音”,而且,要研究“全声音”,包括“无声”。于是,在方法意义层面,必须“直接面对”。具体者——
一、作为行为策略。如同胡塞尔和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言,“面对事物本身”“在音乐中,乐音并不是事物的表现,而是事物本身”——尽可能祛除笼罩与弥漫在音响之外的精神遮蔽,包括隐蔽、蒙蔽,直接面对敞开,以真正亲历、亲近、亲和实际发生的音响——“重返音乐厅”之意义所在。
二、作为历史姿态。如同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盟主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所言,“文明最美妙的精华和最罕见的成果容易消失,但文明的老根却不顾寒冬和断裂依然存在”,一个保证:历史作为一种“长时段存在”,将通过不同方式文化/文明的有序更叠而得以接续;再一个保证:人文历史作为一种“长时段存在”,将通过人类总体文化/文明的持续不断成为“几乎永远”。其之所以“长”,不仅以时间为计量(持续不断),而且以空间为尺度(蔓延无尽)。
三、作为思维步骤。如同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悬置“乐义”之追问,而通过还原,直接面对“音位”,在计量和考量之后,再及人文含量的定位,于是,音位是乐义存在的寓所/能被感受的乐义存在是音位。
之后,别一个潜在的设问: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之后,人文是否失踪?也就是说,无论在施众结构或者在受众结构当中,音响媒体由边缘地带位移至轴心地带,并担当主体角色时,其合理性甚至合法性何以体现?进而,传统的踪迹果然迷失?
无疑,这一系列提问,都是在经历了一场由技术元素引发的人文颠覆之后。
然而,即便如此,总有一张“底牌”至今依然还在,并未翻开,这就是——
音乐是人的创造/音乐是人创造的。
于是,无论哪一品种类型的创作或者制作,即使当“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之后,仍然不会完全消解人文意向,并拆除家族印迹。也许,这就是——文化之所以“可持续发展”,历史之所以“长时段存在”——的一个底基,一种根源。
于是,(Musics),之所以冠以大写字头,之所以加缀复数形式,不仅仅在于计量或者考量的实在与精确,更在于意义的扩展:在尽可能充分显示多样化和相互接近的意义之后,以表示对人为极限的再度扩张和延伸。
还是“诗意地居住”,大约在五十年以前,海德格尔就如此忠告。
言下之意,当下缺乏“诗意”?进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球策略,是否已然覆盖,甚至弥漫?究竟是有限制的发展,还是合式合理存在?
曾经有人多次这样问我:你对生态文化抱持什么态度?不是难以回答,实在是现状令人尴尬。至少,有这么一个迹象:科学唯一/理性至上,作为当今历史文明主潮,并具世界性意义。或者说,归属于认知系统者,处于理性界域之中者,作为人的一种需要,就是以一种精确与实在的方式展示,并假借相应的语言予以表达。以当下而言,这种方式及其相应语言,占据主导,并具标示“人文化”历史进程的功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或者在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时段距离之后,则无论其方式抑或其语言,在整个人类进程中,似乎仅仅是一个阶段,或者一个环节。
如果,以扩张了的“知识型”,或者铺张着的“科学理性”,来涵括一个总体的人类进程,那么很显然,除此之外,还应有:处于感性界域之中,并与之相适应的感受方式;处于知性界域之中,并与之相适应的体验方式;处于灵性界域之中,并与之相适应的觉悟方式。而“处于理性界域之中,并与之相适应的认知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并由感受方式、体验方式转换而来,再向觉悟方式转换而去,以至形成一个人本结构系统的完形。从而,“人文化”的全面发展机制。而在我的心目当中,至少,“生态文化”理应是这样一种方式:足以引发精神灵魂空间的共振,以弥补物质功利时间的中断。
末了,作为“重返完形人本结构系统”的一个重要步骤,“知识安全”不失为一个策略。
无疑,“知识安全”由“知识经济”杜撰而来。进而,通过“知识架构”,也必然关涉其产权并安全。尤其,处在一种新人文意识形态之下:官方意志形态,大众意象形态,知识分子意义形态。
之所以提出“知识安全”问题,目的旨在——
一、坚固知识产权的归属,充分重视在人文生态中,个体性与私有化作为一种合理存在;
二、遏制知识垄断的蔓延,通过对人文资源的共同享受与共同开发;
三、防范知识霸权的威胁,祛除理性格式化的大面积覆盖;
四、加速知识结构的更新,及时剔除陈旧老化顽渍,以及排斥其他的惯性,防止重复建树并人文资源的无谓浪费;
五、推进知识整合的完形,促进人本结构系统的良性循环。
如果说,人类停止进化的一个前提,是过于封闭自己,并过度安全保险,那么,知识安全必然关涉“知识间性”及其互向关系。对传统和国际的过度依赖,则个人知识极不安全。于是,最后整合的意义何在:传统,价值,文明,文化?无理僭越或者无法僭妄,其结果,都只能是肢解主体。
于是,感性作为最初的人本驱动,同样,是知识安全的必要保障。
针对“现代音乐”,也许,处于实验时段,一切都难以甚至无需定论。可问题是,藉此惯性,是否将永远处于实验当中?经典已然消解,传统正在拆除。难道现代音乐果然没有一点可取?否则,何以自足生成,况且,在一定意义上,还真有一点愈益成熟的架势。也许,听的人会越来越少,可写的人却越来越精。大概这才是历史的正常轨迹。
就这样,之所以被称之为:现代,先锋,前卫——
途径:走向极端图解放,不然,连门都无法打开;
方式:混乱之中求纯粹,否则,就假装循规蹈矩;
目的:唯“一”的起点,反之,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人说,这路越走越窄,这门越开越小,这人越写越少。
当然,有狂涛覆盖,有起伏跌宕,有密码泄露,有震荡颠覆……,但到头来,倒是越来越趋于正常。试想,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实验创意,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实验诠释,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实验接受,如果所有的人都把多情的眼光投向一种音乐,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仅单调,而且,毫无光彩。就这么一段“险滩”,就这么一段“栈道”,无以计数的人都来参与,不仅拥挤,而且无聊,于是,要想从“实验的河道”上顺利飘流渡过,再少再少一点人……
也许,不仅对这样一种,而且,对任何一种类型的音乐而言,最最理想的“自我安全防范”,只能是——明确界限,互不干扰,异质相间,耦合互动。
由此折返,并回到“元叙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籁”理应包容于“天籁”之中。
起初,人的声音仅仅限于表达,和自然;随后,扩大成为交际,和人。至此,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消费,这些声音都只是传达一种意思,或者,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然而,随着声音功能的愈益进化和强化,其本身似乎也有了结构的意义,于是,一种纯粹的生产与消费出现了:人们需要一种只供感性愉悦的声音,音乐就算是这一需要的最后方式。
此刻,“人籁”所及,已大大越出“天籁”之界,从此,音响也有了自己的“合理界桩”:从一点声音,到一条声音,再到一片声音,一块声音,一团声音……并且,被不同的人群集取之后,又有了不同的样态。
有人说,六合之内外:生“物”由天,成“象”在人。
可见,不管是对声音的无穷探索,还是直接面对音响本身,其底线或者根本,只能是“人与人相关”。因为,音乐是人文化了的原初音响,并作为特别的叙事/抒情,是对总体人类音响所进行的“第一次命名”,因而,也是人类对声音有所需求的一种“最后方式”。
一个具体的“前提”和一系列抽象的“给出”:在人本感性需求的驱动下,拉动……,推动……,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