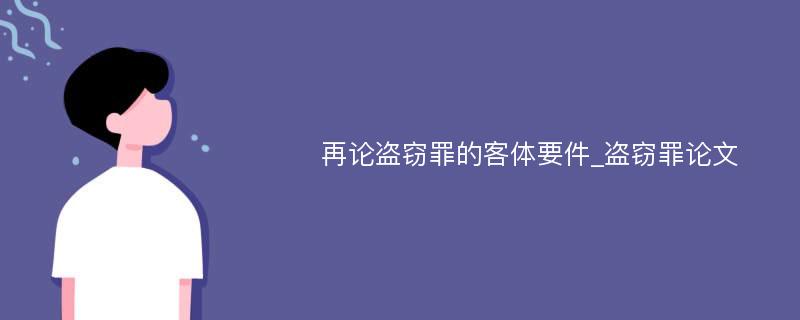
对盗窃罪客体要件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盗窃罪论文,客体论文,要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盗窃罪的客体要件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任何盗窃行为都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即便是以赃物、违禁物为对象的盗窃行为,同样也侵犯到财产所有权,因为这些物品(指赃物、违禁物)要么原来属于他人所有,要么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归国家所有,故盗窃这些物品的行为与直接从财物所有人手中窃取财物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换言之,盗窃赃物、违禁物的行为之所以构成盗窃罪,归根结底在于这类行为也侵犯到合法的财产所有权这一客体。(注: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0页; 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42页; 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1993年版,第656页以下。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都是以这种“所有权说”为依据将盗窃赃物、违禁物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而很少有人提出疑议。(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页。)但是,在我们看来, 认为这一行为侵犯到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见解是很值得商榷的(尽管我们完全赞成对将赃物、违禁物作为对象的盗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而且不仅是在盗窃赃物、违禁物的场合,即使是在行为人盗窃处于他人(非所有人)合法占有之下的财物(如留置物、抵押物等)的情况下,恐怕也不能将其侵犯的客体说成是财产所有权。种种疑问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省的刑法理论并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探讨盗窃罪的客体要件。
一
在国外刑法理论中,关于盗窃罪的保护客体(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客体要件),存在着“本权说”、“占有说”(或称“所持说”)及其他各种中间学说的争论。这里主要就在日本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即“本权说”与“占有说”作一简略介绍与分析,以资借鉴。
(一)本权说
该说认为盗窃罪的保护客体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注: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85页,第686页。)所谓本权, 是指基于一定法律上的原因而享有的占有权利。(注: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本权包括所有权在内,但并不仅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其他基于法律规定的占有,如抵押权、(注:在近现代各国民法上,抵押权之成立与存续,不以转移标的物之占有为必要。但《日本民法典》第356条则明确作出了与此相反的规定。参见梁慧星、 陈华彬主编:《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留置权等。本权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根据这一学说,如果行为人窃取的仅仅是单纯事实上的他人所持财物,(注:在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用“所持”这一用语代替刑法上的占有,以便与民法上的占有相区别。)而没有侵犯他人的所有权或其他本权,就不成立盗窃罪。在日本,关于本权说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法条上的根据。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 盗窃罪的一般对象为“他人的财物”、“他人的不动产”,这些用语意味着规定盗窃罪的宗旨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人对财物的所有权。不过,其第242 条又例外地规定自己的财物在由他人占有或因公务机关的命令由他人看守的情况下,应被视为“他人的财产”,从而表明盗窃罪的立法目的不仅仅限于保护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对其他本权的保护,但单纯事实上的占有即所持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日本刑法第242 条所规定的“占有”已不再是单纯事实上的占有或所持,而是基于权源的占有即可以对抗所有者的占有。因此,从日本刑法第235条和第242条的规定来说,盗窃罪的保护客体只能是所有权和以占有为基础的其他本权。
第二,实质性的根据。一般认为,近现代刑法属市民刑法,即反映市民社会价值观念的刑法,而市民社会是以所有权的绝对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在盗窃罪的刑事立法中应以保护所有权(以及其他因所有权而派生的本权)为目的。
但是,在我国台湾省,同样持本权说立场的学者却认为,窃取盗窃犯人持有之赃物的,仍不妨于构成盗窃罪。按他们的见解,这并非因认非法持有为独立法益而如斯解之,在此所保护法益乃原权利人之所有权或管理权。故原权利人向盗窃犯人窃回原归自己所有或持有之物,并不构成盗窃罪。对于法律上禁止持有或所有之违禁物,可成为财产犯罪的客体,是台湾实例及学者所共认的,但不能因此而认非法持有为财产犯罪上之独立法益,其保护法益在于法律秩序之维护。(注:参见吴正顺:《财产犯罪之本质、保护法益》,载《刑法分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初版,第673页。)
(二)占有说(或称所持说)
在日本,占有说现在已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通说。此说认为,盗窃罪的保护客体是财产的所持等财产上的利益本身。(注: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86页。)根据该说,当自己的所有物为他人不法所持时,如果窃取了它,只要没有特别阻却违法的事由,仍应成立盗窃罪。并且,从占有说出发,作为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只要具有“窃取他人所持财物的故意”即可,没有必要具备“非法占有的意思”。占有说的理由有:
第一,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的是“他人的财物”、 “他人的不动产”,而不是“他人的所有物”,并且,就自己的所有物而言,日本刑法第242条规定中的那些他人所持并不限于基于权源的适法场合, 所以本权说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根据该条规定,自己的所有物被他人占有时,对其窃取的仍应成立盗窃罪,这就表明盗窃罪是将侵犯所持而不是侵犯所有权作为本质的。
第二,就其实质性的理由而言,所有权制度是市民社会的基础,但所有权是抽象的权利,财物的经济效用是依财物被所持管理而实现的,因此,为了保护所有权,必须保护所持自身,更何况如果以欠缺本权为理由而允许侵犯他人所持的话,其结果就会产生无秩序的实力争斗,因此,所持本身必须作为独立的价值在刑法上得到保护。
第三,法律上承认从占有违禁品和赃物的人那里窃取这些物品成立盗窃罪,就意味着侵害的客体是占有而不是所有权。
读者从上述介绍中可能已经发现:首先,我国的所有权说与日本的本权说所持观点大体一致,但比本权说的保护范围要小,即我国的所有权说未提及对其他本权的保护问题;而且,对于窃取违禁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两说也有不同的解释。其次,日本的本权说与占有说争论的焦点与分歧在于:对于窃取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的,应否认定为盗窃罪,或者说规定盗窃罪的立法意图究竟是保护何种法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国台湾省刑法理论中的本权说与日本的占有说存在一致之处,即两说都注重对法秩序的维护。
二
下面,笔者将以作为盗窃罪行为客体(即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的财物所处的状态为研究的出发点,分别讨论窃取他人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和窃取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行为所可能侵犯的客体。
窃取他人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况:窃取赃物的行为和窃取违禁物的行为。对于窃取赃物的行为,如第三者窃取盗窃嫌疑犯盗窃所得财物的情况,按照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该财物属于他人所有,存在一个合法的所有权,因此,第三者的窃取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仍然是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我国台湾省本权说所持观点与此相同)。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分析该财物在两次盗窃行为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刑事司法实践对盗窃罪认定的具体事实要求。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和现有民法理论,所谓所有权,指所有人于法律限制范围内,对于所有物为全面支配的物权,它可以通过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各种权能形态表现出来。为维系所有权的圆满状态,法律又赋予所有人以物上请求权,即所有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所有物者,有请求返还的权利。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注:有人认为作为盗窃罪客体要件的所有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作为民事权利的所有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两者之间存在差别。对此,笔者持反对观点。参见董进宇:《盗窃犯罪再认识及延伸思考》, 《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 )我们再来分析窃取赃物的行为(仍以上述例子为证)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对于第三者窃取盗窃嫌疑犯盗窃所得财物的行为,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即第一次盗窃行为人与被窃取财物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和第三者的窃取行为与被窃财物之间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对于原所有人来讲,在经过第一次盗窃行为之后,所有人对于该财物在法律上并没有丧失所有权,但在事实上,所有人已经不可能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任何一项权能,要恢复其实质性的所有权,只有通过行使返还请求权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经过第一次盗窃行为之后,所有人的所有权已经遭到了事实上的非法剥夺(当然,这种说法在民法学界或许遭到非议),那么,第三者第二次窃取该财物时,所侵害的客体与其说是原所有人的所有权,不如说是所有人的返还请求权,虽然说返还请求权是基于所有权而生的权利,“但其终究不是所有权本身”。(注: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因此,对于第三者的窃取行为,若仍然认为其侵害客体是原权利人之所有权,似有过分牵强之嫌。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时,一般只需认定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实施了窃取他人所持财物的行为且该财物不是行为人所有即可,而不需亦不会去认定该财物之现实持有人对该物是否享有所有权。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在认定盗窃罪时,根本不会也不必去认定所有权的存在。众所周知,实体法的规定不应脱离诉讼实践的具体要求,对于盗窃罪犯罪构成的确立也应当以认定盗窃罪的诉讼实践为基础。在窃取赃物的场合,赃物的背后肯定会存在一个合法的所有人,但人们根本不必去认定该物是否赃物,只需认定行为人窃取所得财物是他人所持而非行为人所有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若仍然坚持盗窃罪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则难免脱离了客观实践的具体要求。
对于窃取违禁物的行为,根据我国法学界的通说,违禁物应当依法没收,属于国家,因此,该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仍然是财产所有权。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这种观点实际上提到了一个“国家所有权”的概念,也就是说国家对于违禁物享有所有权。这种说法本身在法律上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因为财产所有权是民事主体的一项民事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的物,首先必须能够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而违禁物是法律上禁止持有之物,其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既然如此,若说国家对违禁物享有所有权,岂不是荒谬。
第二,违禁物在其产生之后,至其因案发被没收之前,国家根本不知它的存在,也就不能对之加以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说国家对该物享有所有权呢?
第三,对于毒品等违禁物,国家在没收之后,可作医疗之用,若说国家对之享有所有权,这时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该物品此时不是作为毒品而是作为一种药用物资为国家所有。而对淫秽影碟等物品及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加以利用的违禁物,又何从去谈所有权的问题呢?
第四,至于窃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属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而不是一般的财产犯罪,因此,对于枪支、弹药、爆炸物这类违禁物品是不能从一般财产的意义上去讨论其性质的。
在笔者看来,国家没收违禁物和处分违禁物的行为,是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而不是作为民事主体的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行为,它根本不同于所有权的行使。因此,说窃取违禁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所有权的观点实不足取。
既然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对于窃取赃物、违禁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存在理论上的缺陷,那么对这类行为所侵犯的客体究竟应当如何去把握呢?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大陆法系“占有说”的有关理论,即窃取赃物、违禁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占有本身。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亦或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两类行为均可以构成盗窃罪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这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哪里呢?对于赃物、违禁物之现实持有人而言,他们对赃物、违禁物之持有实际上是一种非法占有,这种不法状态本身绝不是法律所认可和支持的。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种不法占有作为一种既存的事实状态,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规范,绝不允许公民以私力解决。当然,笔者并不同意全部引进“占有说”的观点,下面将通过实例来加以具体说明。
在日本,有过这样一个判例,即债权人已经取得了作为担保财产的运货汽车的所有权,但该货车仍然处于债务人的占有保管之下,后来债权人擅自将该货车开走,对于这一行为,日本最高裁判所认定构成盗窃罪。这一判例,实际上是否定了不法占有不构成盗窃罪保护客体的主张,可谓对占有说最有力的支持。持“占有说”的学者以这类行为为事实基础进一步提出,盗窃罪在主观上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要有“窃取他人所持财物的故意”就行了。对于这类行为,笔者认为在我国不宜认定为盗窃罪,也不应该取消“非法占有目的”之主观要件,因为:
首先,从合理性来讲,行为人只是想取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没有侵犯他人财产的主观恶意,若仅仅是因为行为方式欠妥当就将其行为认定为犯罪,恐怕于情理不合。
其次,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无故占有他人财产不及时返还或不予返还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对于这类情形,若一律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无论是对公民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讲,还是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同时,这一要求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公民个人之间以实力争斗来解决纠纷,而是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这类情形自然会逐渐减少和消失。
再次,如果取消“非法占有目的”之主观要件,就无法区分盗窃罪与通过秘密窃取方式毁坏他人财物之犯罪行为的界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窃取赃物、违禁物的行为所侵犯客体是占有本身。与大陆法系占有说不同的是,笔者主张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为“新占有说”,以此观点为出发点,对于行为人秘密取回被他人不法占有的自己财物的行为,就不应当构成盗窃罪。
三
以上是就窃取赃物、违禁物的行为所侵犯客体的分析论证,并提出“新占有说”的主张,但赃物、违禁物毕竟是特定的对象,二者都是处于非法占有状态之物,盗窃罪更多的表现为窃取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对于这类情况,“新占有说”又是否同样适用,它较之于我国通说即“所有权说”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呢?
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合法权益。盗窃罪作为一种财产犯罪,刑法对之加以规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稳定的财产关系和合法的财产利益。在此,让我们先具体分析一下作为盗窃罪行为客体的物究竟可能涉及到何种财产利益关系。
在民法上,一物之上除设定所有权外,还可以设定他物权(因为盗窃罪的行为客体限于动产,所以这里对物权的分析也以动产物权为限),涉及动产的他物权主要是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中抵押权是不需要转移占有的,即所有人自己占有所有物,他方(相对于所有权人的债权人)于所有物上享有抵押权,由此来确保自己债权的实现,而质权、留置权作为一种债的担保,则是由物之所有人以外的债权人占有该物,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所有与占有的分离。在现代民事经济活动中,由于各种风险的普遍存在,使得担保制度得以充分发展,担保物权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对于成就各种民事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他物权人来讲,担保物权更是其债权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因此,窃取财物的行为,不仅会侵犯到该物之所有人的利益,对于该物之上可能的他物权人来讲,其债权利益的实现也受到了侵害和威胁。如窃取留置物的行为,行为人的窃取行为不仅侵犯了留置物之所有权人的利益,而且对于占有该留置物的债权人而言,其债权利益的实现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在债权人占有留置物的场合,债权人债权利益的实现有赖于留置物财产价值所提供的担保,而留置物的灭失使得债权人债权利益面临着无法实现的风险,而且在债务人即留置物所有人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还可能面临着赔偿损失的问题。将债务人与债权人利益损失两者相比较,似乎债权人即留置权人才是该盗窃行为的真正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若说盗窃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恐怕与现实不相符合。
另外,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加之充分利用资源的社会要求,使得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成为一个极为普遍的事实,也就是说,所有与利用的分离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所有人基于知识、技能的欠缺或其他原因,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他人(财产利用人)经营管理,自己获取所有权收益,财产利用人则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经营管理他人财产,获取财产利用收益。在这一对利益关系中,所有权收益必须依赖财产利用收益才能实现,财产利用收益因此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这就要求法律对之加以保护,而“所有权说”只是注重了所有权人的利益,对于财产利用人的独立权益则未能加以重视。
因此,无论是对物之所有人来讲,还是对他物权人来讲(这里主要涉及到物权关系),也无论是对财产所有人来讲,还是对财产利用人来讲(从现有的民法理论来讲,这里涉及到的主要有债权关系),他们合法的财产利益都应当得到刑法的重视和保护。那么,有关盗窃罪客体要件的理论,应当如何体现刑法的这种保护,如何去适应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性要求呢?正如大陆法系持“占有说”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无论是财产所有,还是财产利用,都是以对财产的实际持有支配即占有为前提的,因此,要保护上述合法的财产利益必须保护占有本身。
当然,除了上述分析的基于物权和债权的占有外,合法占有还包括基于其他本权的占有,如受他人委托无偿保管他人财产的占有。对于这类占有而言,要保护其背后合法的所有权,保护占有自身也就已经足够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于窃取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来讲,还是对于窃取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而言,“新占有说”都是同样适用的。因此,我们主张,盗窃罪的客体应当是对财物的他人占有,同时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对于非法占有而言,承认其为盗窃罪的客体,并不是因为非法占有本身是一种合法权益,而是因为其代表了一种既存的将由法律予以规范的事实状态,任何第三人对之加以侵犯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这里,作为盗窃罪客体要件的占有是一个事实上的概念,即对物的事实上的持有支配,它与民法上的占有概念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