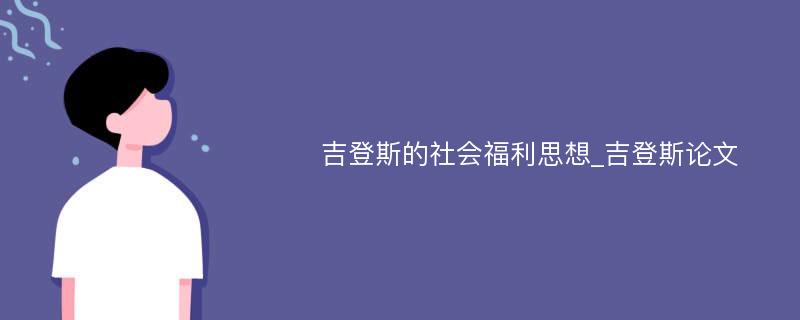
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思想论文,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福利的原则与目标
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面对的风险都是可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生育、养老,还有一些风险是自然发生的概率性事件,如工伤、失业、疾病等,这两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都能以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吉登斯把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定义为“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1](22)。吉登斯认为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人为风险,这种风险难以预料,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具体而言,人为风险(manufactured risk)指的是“我们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框架中要积极面对的风险”[2](157),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1](22)。
如何区分这两种风险?吉登斯指出了人为风险的三个不同点:“一是人为风险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的‘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1](155)人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的所作所为。
正是因为风险性质改变了,传统的福利制度出现了危机,吉登斯认为这种危机是风险管理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不可否认,从俾斯麦时期开始发展并在贝弗里奇等人的努力下逐步完善的福利制度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以事后补偿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相应的人为风险的大背景下已危机重重。“福利国家体现的是生产主义、外部风险、传统的家庭分工等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福利国家失去了原来的基础,而解决外部风险的手段无法解决风险。”[1](169)
在传统福利危机重重的背景下,吉登斯提出了他的福利改革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
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公民享有福利是一种政治权利,如威连斯基(Wilensky)给福利国家下的定义:“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所得、营养、健康、住房、教育水平,对于国民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权利而非慈善”[3]。这种制度设计中对公民责任的忽视导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依靠福利,志愿失业。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给予了很好的解释。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低。那么,高福利国家的消费和劳动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的位置将在低福利国家的上方,即高福利国家的公民的效用水平比低福利国家的公民高。因此,假设同样一个单位时间的劳动,高福利国家的雇员要求的消费补偿是C,低福利国家的雇员要求的是C′,可以肯定C>C′。若一单位时间的劳动的报酬在C与C′之间,那么高福利国家的雇员会因其效用水平低于预期而不愿工作,低福利国家的公民会因其效用水平高于预期而愿意工作。所以,高福利国家一方面是一些低报酬的工作无人做,另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吉登斯主张强调责任。他说:“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4](69)。在传统的福利制度中个人有提供保险经费的责任,如果个人失去工作后,他就有权利得到补偿而不需承担责任,可见这就出现了无工作者的责任断层。针对这种情况,吉登斯强调“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4](68)。“那些从社会产品(social goods)中收益的人应当负责任地利用两者,而且应当反过来回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作为公民权利(citizenship)的一个方面,‘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必须对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机构和个人同等适用。”[5](52)。可见,吉登斯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同时也强调集体的责任,主张个人、集体和国家一道为建设福利国家做出贡献。
在无责任即无权利原则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积极福利政策的主张。
如前所述,传统的福利政策主要是根据外部风险组织起来的,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具有被动性,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重新分配,其目标是维持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不至于因遭遇风险而陷入生存危机,因此被称为消极的福利政策。而今面对人为风险,吉登斯提出了积极的福利政策,“其目标是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autotelic self)……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不刻意回避风险或者设想‘其他人会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积极地面对风险,因为后者带来了自我实现”[2](201)。可见传统福利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人的生存,其手段是外在的物质或现金给付;而积极福利政策的目标是推动人的发展,其手段是增强人自身的生存能力。
这种目标的确定来源于对幸福的重新审视。传统的福利观局限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其实“幸福”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吉登斯引用了最出色的福利国家批评者吉尔斯·默里的研究成果来说明这个问题,默里指出:在物质需求的满足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收入的提高并不会导致更大的幸福,根据马斯洛的理论,美好生活的关键条件是自我实现。因此,一个真正关心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在传统福利国家不民主而且限制个人的自由的情况下,吉登斯认为改革后的“积极的福利就是要积极做出生活决定而不是消极地计算风险”[1](115)。与此相对应的政治转变是从解放政治(生活机会的政治)转向生活政治(生活决定的政治或生活选择的政治)。
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积极的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
此外,吉登斯还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概念,他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替代“福利国家”这一概念。社会投资型国家适用于推行积极福利政策,与传统的福利国家相比,社会投资型国家不仅关心经济福利,而且关心“心理利益的培育”,原因是人的幸福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的统一。为了提供国民自我实现的条件,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4](122)。在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居中心地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一方面可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推动福利国家的改革,总之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改革的良性互动。为什么?原因是经济问题与福利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提高了人的生存能力,经济问题和福利问题就都解决了,因此,在人力资本上投资是治本之策。另外,“保险原则和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1](101)。
二、社会福利具体改革主张
吉登斯根据他的社会福利原则与目标,相应地提出了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主张。
首先,在解决老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必须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随着寿命不断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很多学者预测负担老年系数会越来越大,老龄问题会越来越重。吉登斯认为这种老龄问题是一种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并指出:“从65岁开始算老龄纯粹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创造”[2](176),并且这种创造最早源于1889年俾斯麦第一次确定的官方退休老龄。另外,养老金也是福利国家的发明,其实质是一种储蓄形式。“老年人必须由国家照料的期望创造了一种同样有害的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5](40)。人到退休年龄便成为养老金的领取者,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具有两个弊端:首先,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被视为负担,而且也确实成为了负担。其次,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老年人。如有的老人身体状况好,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以继续工作而且愿意工作,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他只能退休。而如果有的老人身体状况不行,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
吉登斯认为解决老龄问题必须调动老年人的能动性,他说:“应该把老年人视为解决当前福利困境的推动力,而不是困境的制造者”[2](178),“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条件”。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实际上,美国已取消了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总之,老年人不能再靠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养活,而应自己养活自己。吉登斯指出:“在传统意义上的退休年龄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休假,分阶段退休以及退休预演都有可能出现”[2](191),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更加灵活的进出机制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生活质量,有利于享受更大的幸福。
其次,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从减少社会排斥着手。“平等和不平等的分界线是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5](90),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包容性’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公共空间中的参与[4](107)。排斥有两种: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根据定义,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排斥问题,以提高被排斥者的“社会能力”。相应的方法是:一、限制精英的志愿排斥;二、提高社会底层人民的抗排斥的能力。
吉登斯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有:1.重建公共领域。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无法阻挡时,重建公共空间可以增强上层与下层的对话,营造公共生活的环境。2.利用福利制度调节再分配。但这种福利制度必须能造福大多数人,并产生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3.加强教育和培训。托尼·布莱尔的“教育、教育、教育”已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4.以社区为中心开展扶贫。支持当地的项目,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
再次,在对贫困国家的援助问题上,吉登斯主张应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以往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大多是经济援助,这种财富的转移并没有解决贫困国家的贫穷问题,反而引起了对富裕国的依赖。吉登斯指出,这种依赖与福利国家内部的国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相似,引发的问题(如项目的实际受益者并不是原来设想的那些人,被援助对象的道德受到破坏)与福利国家内部的问题相似。如何解决?吉登斯提出了一个“可供替代的发展方案:从一些地方或者许多地方的既有政策中汲取营养的一种能动性政治方案。”[2](164),简单的说就是立足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培养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聪明智慧,尊重当地的传统。
三、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虽然有批评认为吉登斯的福利思想是老生常谈,毫无用处。但值得肯定的是: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大环境,吉登斯敏锐地指出了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并提出了全新的原则、目标和政策。其大致的框架是:在人为风险占主导的全球化环境下,必须采取积极的事先预防的办法,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从解放政治转向提供多种机会的生活政治,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高度参与、共担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建立一种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与福利良性发展的社会投资型国家。不足的是,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部分,他的福利改革思想并不具有系统性,也不像贝弗里奇计划一样具有可操作性。但如果说贝弗里奇计划是对当时的福利政策的定位,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吉登斯的福利改革思想是对当前福利国家改革方向的定位。
很多学者认为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撒切尔主义、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以及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等。但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道路”的深层理论动因却是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学说和现代性批判学说[6],因此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不能不对布莱尔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对布莱尔的第二代福利思想的影响。布莱尔认为:第二代福利是要给人以扶持而不仅仅是施舍,福利应是成功的跳板,而不仅仅是安全网,这体现了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第二代福利能适应妇女从家庭走向工作的趋势,强调公民身份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之上,这符合“无责任即无权利”原则;第二代福利鼓励地方决策,鼓励公共部门与私人合作,而不仅仅是政府发号施令,这体现了吉登斯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建福利国家的思想。[7]二是对布莱尔政府的福利政策的影响。布莱尔政府于1998年10月推出了全面改革福利制度的总体规划,这一规划的总体原则是“有付出才能有所得”,总体思路是“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为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提供生活保障”。[8]可以说这一规划很好地体现了吉登斯的“无责任即无权力原则”和“积极福利”的思想。
数据显示,吉登斯的福利思想在英国的实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工党减少补贴、增加教育和培训的政策以及“从福利转向工作计划(welfare-to-work schemes)”,使英国在1999年的就业率达到75%,而整个欧洲的平均就业率为61%;[9]同年英国的失业率也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英国的失业率为4.3%,而欧盟15国的平均失业率则为9.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