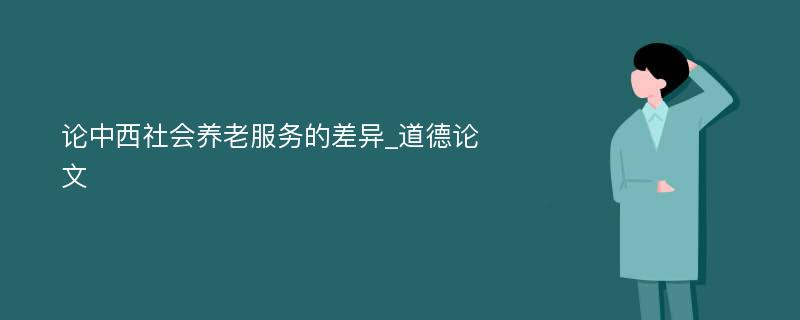
论老龄社会关怀的中西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龄论文,中西论文,差异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2)01-0125-04
老龄社会关怀是指以老龄人群为关怀对象,通过社会制度伦理建构来提升其生活质量、并使之完满地走向生命终点的社会伦理实践。老龄社会关怀的中西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崇祖尽孝与敬神博爱的文化根源差异;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实践形式差异;德行不朽与回归上帝的终极目标差异。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传统伦理差异、未富先老与先富后老的国情差异分别是造成老龄社会关怀中西差异性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人口结构老龄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共同背景决定着中西老龄社会关怀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并将趋同。
一、崇祖尽孝与敬神博爱:文化根源差异
崇祖尽孝与敬神博爱之异是造成老龄社会关怀中西差异性的文化根源。崇祖尽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特征。崇祖指祖先崇拜与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缅怀先祖恩德、承续先祖遗志、团结族人并旺续家业,同时将这份崇敬之情、感恩之意化作对现世的父母长辈的孝敬之行,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孝道是连接先祖与后人、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桥梁,也是老龄关怀伦理文化产生的道德根基。孔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纪孝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第十九章)可见,儒家讲孝道,生、死、葬、祭是不可分割的,其中孝养父母是最根本的道德要求。虽然祖先崇拜及其祭祀活动具有将“鬼”即先祖“神”化之倾向,潜具敬奉鬼神的宗教伦理属性,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神是存而不论的。从夏人“事鬼神而远之”,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以及周人所言“天不可信”(《尚书·君奭》)等典籍记载表明,随着无神论思想的萌芽,以及本土宗教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影响,古人逐渐将目光由鬼神移转至现实。周公总结夏、殷灭亡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主张,说明他认识到“民”比“神”更高、“德”比“天”为重。“德”之本乃孝道,对人子而言,孝道不仅是敬祭先祖,更重要的是孝养双亲,并移孝作忠。由此,彼岸世界的人神关系转化为此岸世界的亲子关系。
孔子“孝悌”为本的仁学思想的形成与孟子以“四心”为基础的“仁政”主张的提出,表明道德理性逐步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牵系与支持,崇祖、祭祖只不过是后人“奉先思孝”(《商书·太甲中》)、以孝侍老并实现以孝治国的一种礼制文化载体。“孝,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尊老孝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起点。“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这是孝道的具体实践路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家庭成为实施老龄道德关怀的温床,家庭养老成为承载孝道的现实伦理途径。“养耆老以致孝”(《礼记·王制》)是历代王朝以孝治国的政治伦理方略,彰显了孝道内蕴的强大政治伦理功能与道德辐射效应;同时表明以孝道为根基的老龄关怀伦理文化由家庭扩展到社会,并通过移孝作忠,成为家国同构下政治与伦理双向互动的社会发展机制。
如果说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国教,是农耕经济条件下基于孝道的老龄关怀伦理由以产生的文化根源,那么,宗教信仰则主宰着西方人的心灵与现实生活,是契约经济条件下基于博爱的老龄关怀伦理由以产生的文化根源。对上帝的爱、信、从是西方基督教伦理文化的主题,爱上帝是三德之首,为至善。然而,爱上帝与爱俗世是对立的。《约翰一书》宣称:不要爱世界与世界上的事;若要爱世界,爱上帝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要爱父母与妻儿,就不能全心全意爱上帝。[1]只有一心爱上帝才能赎洗原罪、获得来世的幸福。这种宗教观念抛开了血缘亲情,将亲子之爱变成人神之欢,将浓浓的血缘亲情淹没在与上帝的拥抱中,人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点。爱神、敬神的宗教观念与淡薄的血缘情感自然不可能产生尊老孝亲的老龄关怀伦理文化,而孕生出以爱上帝为核心的宗教关怀伦理文化。
然而,基督教又是主张博爱的,这是一种超越了血缘亲情的大爱,它不分亲疏远近、等级贵贱,在敬仰共同的神这一根本的宗教伦理原则指导下,追求爱人如己。这种大爱使孝养父母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道德价值的社会善行,而不是人子的义务与家庭的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敬神、博爱的宗教伦理文化是西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兴起的催生剂,也是其不断健全与发展的道德信仰之源。
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实践形式差异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是中西方老龄社会关怀的实践形式差异。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体现为以父权制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宗法人伦关系。“三纲五常”是维护宗法人伦关系的总纲。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生产条件下,人的生、养、老、病、死、葬都在家庭内完成,由此形成了以孝道为根本原则、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形式的老龄社会关怀模式。
古希腊城邦时期,由于契约关系解构原始血缘关系、公民身份超越人子身份、公民权侵蚀家父权、民主政治摧毁王权专制,形成了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经济,契约伦理关系成为当时城邦社会关系的主导方面。这对现代西方老龄关怀伦理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代际关系由家庭内血缘性依附关系转变为基于法权的平等关系;赡养父母并非子代的法定义务,因而没有形成家庭养老模式,而是逐步形成了以法权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要形式的老龄社会关怀模式。
家庭养老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也是目前我国法定的一种养老形式。《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养老是指主要由子女或其他亲属为老龄人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养老形式,其中,经济来源是决定养老形式的主要依据。目前,我国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老龄人口比例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退休金也在逐年提高。
家庭养老承载的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道德关怀,这份浓浓的关怀之情使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得到稳固延续,但它毕竟是传统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下多子养老的必然选择。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相继婚育,“四二一”人口结构成为一种重要的扩大家庭形式,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所特有的一种倒金字塔形赡养结构。从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是老龄化中国的必然选择。它不仅体现了多子养老向独子养老的赡养责任分担形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家庭道德关怀向社会道德关怀的实践转换,反映了家庭内血缘亲情关爱向社会制度性道德关怀的拓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老龄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并使其生活质量得到稳步提高。近几十年来,美国老龄人口的福祉状况得到较为迅速的改变,他们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经济上非弱势的人口群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老年人生活的大幅度提高是1960年来普遍性公共政策致力于减轻老年贫困的结果。……其他社会目标都得不到同样程度的政府关注或资源。”[2]社会保障是美国国家开支最大的计划,而养老保险又是社会保障中开支最大的一项。尽管美国政府在其他需求领域也有相当大的开支,但老龄人显然得到了最高的优先权,这就是社会关怀的道德优先权。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一方面保障了老龄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内代际伦理互动日趋疏松。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要吸纳中国式家庭养老的温情与爱意,在社会制度伦理建构中融入“反哺式”亲情关怀。我国则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探拓并不断完善以社会养老保障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居家养老关怀模式。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共同背景之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家庭道德关怀与社会制度性道德关怀互补,以及老幼两代互惠、共赢,是中西老龄伦理文化不断交融、老龄社会关怀模式共同发展与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德行不朽与回归上帝:终极目标差异
临终关怀是老龄社会关怀的重要环节。德行不朽与回归上帝是中西方老龄临终关怀的目标差异。
肉身化尘泥、德行永不朽,是中国传统死亡观的精义所在。将死之无奈、死之意识转化为生之创造的理念与现实的道德实践,在死亡的无限悬临中创造人生的价值,是儒家传统伦理文化关于死亡的生存伦理。儒家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来践履人生的价值,在塑造高尚人格的道德实践中超越死亡,由此缓解生死对立,而当死亡真正来临时,问心无愧、死而无憾。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反映了他追求德行不朽的死亡伦理观与终极价值关怀取向。荀子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所谓善终,就是善待生命的终了阶段,是基于对死亡的真切领悟而积极、主动地把握生命整体过程尤其是临终阶段的道德关怀实践。荀子的善终论承续了孔子向死而生的伦理精神,并将儒家的死亡伦理推向极致。
儒家向死而生的生死观以及德行不朽的终极关怀对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行不朽”成为很多中国老人化解死亡焦虑、实现人生善终的道德心理动因,也是其走向生命终点的终极价值追求。德行不朽、死而永生的道德信仰与价值追求在老龄临终关怀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与心理安抚功效,因而,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老龄临终关怀的终极价值目标。
回归上帝是西方人所追求的人生归宿,也是西方老龄临终关怀的终极价值目标。它源自西方敬神的宗教信仰。哲学家与神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眷注。”[3]对西方人而言,“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始终包围着个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的一个坚固的精神模子,它把个人的一生所有寻常的和非寻常的时刻都予以圣洁化并包含在圣餐和宗教仪式之中”[4]。基督教神学通过原罪、赎罪、回归上帝来阐释人生的痛苦、死的必然性及其超越性,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信仰层面的终极价值关怀。据《圣经》记载,上帝原本是将人造成不死的,但由于亚当和夏娃受到隐身于蛇形的魔鬼引诱,违背上帝的诫命,偷吃了分辨善恶之树的果子,犯下罪错,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使人间充满各种罪恶、灾难和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原罪。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都必须为原罪付出死的代价。当然,上帝不只是给世人安排了不可逆转的死亡终局,对那些虔诚地信奉上帝、心甘情愿地赎罪者,上帝可将其灵魂引向极乐世界,到那里任享一切。“极乐世界”虽是美妙的幻境,却给信众无限的希望。回归上帝的终极价值追求在老龄道德关怀尤其是临终关怀活动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心灵安抚功效,很多西方老人或手捧、或头枕《圣经》,或请牧师诵读《圣经》,平静离世,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上帝在美妙的天堂里等候着自己。
德行不朽是道德精神的永存,回归上帝是灵魂的再生,作为老龄临终关怀的两种不同向度,二者殊途同归。前者追求的是在俗世中德行彪炳后世,后者追求的是在彼岸世界里灵魂的复活,二者的有机结合必将在老龄临终关怀活动中产生神奇的道德心理抚慰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