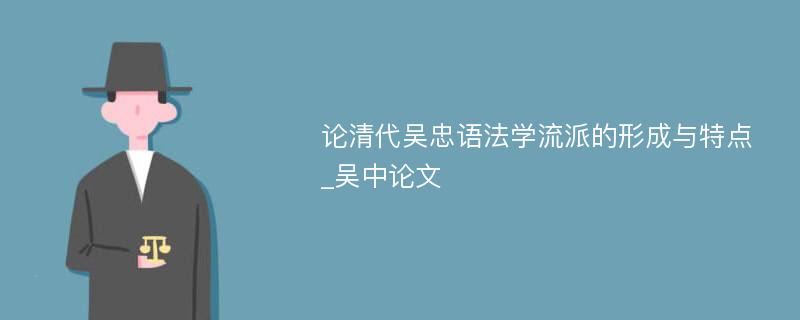
论清代吴中声律词派的形成及其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中论文,清代论文,特色论文,声律词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2-0165-05
一
乾嘉之际,朴学考据之风盛行,大批学者潜心于经学、史学、小学、音韵学的研究。这一风气也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领域,在文章方面出现了桐城派古文,标举“义理、考据、辞章”的结合,诗歌创作方面则有翁方纲所倡举的“肌理说”,反对将考订训诂与诗歌创作判为二事,提出“为学必以考正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的主张。于词学上则出现了一批学者对唐宋词乐的考察研究以及在创作中对声律的倡举重视,如戴震的弟子凌廷堪,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及《辽史·音乐志》等书,作《燕乐考原》六卷,对唐宋词乐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将对词乐的推重与声律的倡举践履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曾自谓其词云:“稿中所用四声,非于唐宋人有所本者,不敢辄为假借。所用韵,凡闭口不敢阑入抵腭、鼻音,至于抵腭与鼻音亦然。”(《梅边吹笛谱序》)时人称其词云:“不主一家,而严于律。今人之词,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伍崇曜《凌廷堪〈燕乐考原〉跋》)凌氏的词论与词之创作无疑已开吴中声律派之先河。并且康乾年间,词学研究之风甚炽,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超编成《词学全书》,至嘉庆年间,秦恩复刻《词学丛书》,一些词学理论书籍如曾慥《乐府雅词》、张炎《词源》以及《词林韵释》等(其中《词源》为戈载校点)得以刻行。《词学丛书》的刻行对当时的词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这些书籍流布甚少,不易见到。即以凌廷堪为例,他著述《燕乐考原》时,尚未及见《词源》,甚至去世前才见到。其《燕乐考原》卷一云:“廷堪尝著《燕乐考原》六卷,皆由古书今器积思悟入者,既成,不得古人之书相印证,而世又罕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久之,竟难以语人。嘉庆己巳岁春二月,在浙晤钱塘严君厚民(杰),出所藏南宋张叔夏《词源》二卷见示,取而核之,与余书若合符节,私心窃喜前此尚未误用其精神。于是录其要者,以自验其学之艰苦。且识良友之饷遗,不敢忘所自也。”由此可见秦氏刻书之重要了。
另外,在戈载之前,有关词韵、词谱的著作已有数种,如徐士麟《坦庵订正词韵》、沈谦《词韵略》、万树《词律》、吴绮《词韵简》、王一元《词家玉律》,徐釚曾刊明代沈璟《古今词谱》、楼俨《白云词韵考略》、吴烺与程名世《学宋斋词韵》、许宝善《自怡轩词谱》、许昂霄《词韵考略》、赖以邠《填词图谱》、吴宁《榕园词韵》、秦恩复《词学丛书》刻《词林韵释》、吴堂《词谱异同》等。这些词韵词谱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从宋词韵脚中归纳出来,可称复古派;一为在分韵时,更多注意当时的语音实际,甚或以某地方音为根据,可称为趋时派,如许昂霄的《词韵考略》即属此。此可视作有清一代汉学派、宋学派的不同风气在词韵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众多词谱、词律、词韵著作编纂及刊行,尤其是康熙五十四年刊行了楼俨、杜诏、陈廷敬编纂的《钦定词谱》四十卷,对清代词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强大的推动作用,对吴中声律派的产生及有关声律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亦提供了一种深厚的学术积淀。
然上述词韵著作却又层次不一,或过于简单,或曲韵、词韵不分,或滥采时语,多有谬误之处,除万树《词律》外,苦无善本。一者不便于学词者宗法,二者从词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必要对这些词韵著作作一番清理与整合,再者亦有“病夫率尔倚声者都不以此(韵律)为事,于是欲起而救正之”(顾广圻《词林正韵序》)的用意。
戈氏正是本着此种意图进行他的词学研究的。他在《词林正韵·凡例》中,梳理词韵源流,评述韵书得失。如论《词林韵释》云:“近秦敦夫先生取阮芸台先生家藏《词林韵释》,一名《词林要韵》重为开雕,题曰宋菉斐轩刊本,而跋中疑为元明之季谬托,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诚哉是言也。观其所分十九韵,且无入声,则断为曲韵无疑。”《词林韵释》于当时颇为学词者所推重,宗法者甚多,若不廓清,则遗误难除。论其他韵书云:“国初沈谦曾著《词韵略》一编,毛先舒为之括略并注……又似纷杂,且用阴氏韵目删并,既失其当,则分合之界模糊不清,字复乱次,以济不归一类,其音更不明晰,舛错之讥,实所难免。同时有赵钥、曹亮武均撰《词韵》,与去矜大同小异。”“若李渔之《词韵》四卷……以乡音妄自分析,尤为不径。”“至前此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平、上、去三声用曲韵,入声用诗韵、骑墙之见,亦无根据。近又有许昂霄辑《词韵考略》,亦以今韵分编……大旨以平声贵严,宜从古;上去较宽,可参用古今;入声更宽,不妨从今。但不知所谓古今者,何古何今而又何所谓借叶。痴人说梦,更不足道。所幸者诸书俱未风行,犹不至谬以传谬。今填词家所奉为圭皋信之不疑者,则莫如吴烺、程名世诸人所著之《学宋斋词韵》,其书以学宋为名,宜其是矣,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种种疏缪,其病百出,不知其作,贻误来兹,莫此为甚。而复有郑春波者继作《绿漪亭词韵》以附会之、羽翼之,而词韵遂因之大紊矣。”对各家韵书之得失作了切中肯綮的评述,其所著《词林正韵》“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其中明显带有乾嘉考据朴学尚实求真的风气。乾嘉朴学之风于词学实肇始于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其中对词之总集、别集、词谱、词韵、词话作了深入考察研究。当然此种学风的浸润不可能是单一的、线性的,它可能在词学研究的许多层面上同时铺展,戈载《词林正韵》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其他的层面戈氏则于《宋七家词选》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对吴文英词的整理与校定。虽然仅是从声律的角度,然其参校众多的版本、选本、韵书,从音韵的角度校理词集的学术方式,对后之晚清四家编校词集当有所助益。
二
地域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十五国风就有明显的风格差异。此种差异,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不同,而且更与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许多文学流派就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如宋代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公安派等,但这些流派在文学创作上并未呈现出能够表征该地域文化历史特征的风格来,如江西诗派创作上主张宗法杜甫、韩愈,诗歌创作须有深厚的学养,隶事用典须无一字无来处,又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方式推陈出新,并没有表现出江西地域性的人文色彩。这或许是由于其时一些地域性文化历史的积淀尚不丰厚,亦未形成迥异于其他地域而可代表本地域的人文特征;或者是作家们尚未具备以诗歌表现地域人文风致的理性自觉。明代诗文流派,前、后七子声名甚显,牢笼亦广,然不以地域称;公安、竟陵二派虽冠以地域之名,然以倡举性灵,独抒性情为长,加之其地域文化历史积淀也不甚丰厚,故而二派亦无鲜明的地域特性。至清代就不同了,清词流派都带有地域名称,其成员的聚集、创作的繁盛,往往都在其地展开,不惟创始者活动倡导于此而已,并且词坛领袖的开宗立派,亦往往受到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因而自觉地选择宗奉对象,其创作中亦潜涵着地域文化习俗、艺术传统的历史积淀。如阳羡派的风格悲慨激扬,出自苏辛;但他们同时还对一位在宋代词名不算太高的乡先辈蒋捷大加推崇,加以师法。我们在考察吴中词人群时,亦应遵循这一视角。
吴嘉洤《亡友七人传》曾云:“吴中乐部甲天下。”吴中文学向来就有推重文学的音乐体性,追求外在形式的典雅的传统。《晋书·乐志》曾云:“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吴声歌曲由一开始的徒口而歌,到后来的被之管弦,配乐而歌,即表征着对音乐体性的重视与追求。西晋陆机对文学形式、色泽美的崇尚,南朝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提出,对诗歌声律美的追寻,可谓其远响。南宋时姜夔在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创作了咏梅名篇《暗香》、《疏影》两阕歌词和乐曲,范成大将家伎小红嫁给他,姜氏曾有诗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即反映出吴中一地深厚的音乐积淀。并且戈载的依绿园别墅即在石湖附近,戈氏《凄凉犯·感题依绿园别墅·序》云:“去石湖数里,而近有范村,白石道人《玉梅令词序》所云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范村是矣。予家依绿园在焉,此地面山临流,宅幽势阻。是吾祖所经营而予弱年所游钓也。”其《石湖仙》序云:“同人举消寒雅集,议建姜白石祠于石湖上,附以吴梦窗、张玉田,以此三贤皆熟游吴中也。”可见吴中词人对姜氏的推重与仰慕。至明代沈璟于戏曲创作中重音律,倡导本色论,形成吴江派。沈璟家里,凡客人登门必言及音律,“娓娓剖析,终日不置”(王骥德《曲律》),形成良好的氛围,沈璟于曲之创作提出“宁协律而词不工”,与临川汤显祖为表意而不惜字句不协的创作主张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沈氏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显示出对戏曲艺术形式美、音乐美的追求与恪守。可以认为吴中地域人士在内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有对文学形式美、音乐美的深厚积淀,与对此种美学风格发自内心的眷恋与固守。
词的创作的衍变与行进虽然具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些固有特性,但亦非一种孤独的孑然而行。它必然要受到整个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乃至其他文体特质的浸润,从而以一种半似拒斥又半似敞开的姿态来拥抱、接受之。如元明戏曲兴盛,其时的词作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曲化的特征,这也是明代词学衰敝以及词作风格由典雅蕴藉滑向粗俗浅白的重要原因。同样戏曲创作中对外在形式、声律美的推重亦必然会影响及词学领域,吴中声律派词人群的创作与主张就是于词学领域中对其的一种应和,亦可以认为在此种强劲的地域色彩的惯性力下,吴中词人群亦必然会揭橥声律的大旗。
三
如果说地域性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力有点间接的话,那么家庭渊源与前辈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家族文化的研究视角是我们研究明清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戈载于《词林正韵·凡例》中曾云:“惟自揣音韵之学,幼承庭训,尝见家君与钱竹汀先生讲论,娓娓不倦。予于末座,时窃绪余。家君著有《韵表互考》、《并韵表》、《韵类表》、《字母汇考》、《字母会韵纪要》诸书,予皆谨谨校录,故于韵学之源流、升降、异同、得失,颇窥门径。近又承顾丈涧蘋,谈宴之余,指示不逮,更稍稍能领其大略焉。”戈载之父戈宙襄,字小莲,有隽异之才,喜读书,凡经史诸子,历代大家之文,均浸浸于胸中,袁枚曾称其“古文在诗之上,能从《庄》、《列》、《韩非》、《国策》诸家蕴酿而出,笔力又足以济之,再假以数年,如悍将开边,不知到何境界”(《答戈小莲书》)。著有《方舆志略》、《十六国地理考》、《大儒传道录》、《名儒传经录》、《小人儒录》及上述韵学著作等。钱竹汀即钱大昕,其为学淹博,通晓经术、天文、数学、历法、文学、音韵、训诂、历史、金石、典章等,亦有诗词之作,其词风格清朗疏快,颇有些情韵,而毫无学人逞露腹笱的习气,著有《潜研堂全书》。父亲的勤于著述,对音韵学的精心研究,以及父辈间学术交流的浓郁的氛围,给幼小的戈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插下了执著追求学术的种子。
顾涧蘋即顾广圻,字千里,从江声游,读惠栋书而通晓其义,于学淹通经史、训诂、天文、历算、舆地、声韵等,精于校勘旧籍,亦能为古诗文词,其词多咏物之作。张德瀛《词征》卷六评其词云:“如春水初涨,更染岚翠。”顾氏于词学创作主张严守声律,其《扁舟载酒词序》云:“盖闻填词之有宫律,譬则规矩也。其词句之美,譬则巧也,所谓能事者尽规矩之道以施夫巧者也。词家之盛,由两宋以溯唐五季而涉金元,罔有不知此旨者,更明三百年陵夷衰微,迨至国朝复起其废,善言宫律者,椎轮万氏,囊括词尘是已……特是读者知其辞句之美易,知其字字入宫律难。余往者亦尝留意于《碧鸡漫志》、《乐府指迷》等诸家之说,用求卷中,众作不啻重规叠矩,故敢首揭此者,将以待闻赏音者之击节云。”乃吴中最早倡举声律之说者,吴中七子的词论,皆缘于顾氏的影响与启发。戈载尝述顾广圻论词云:“词之所以为词者,以有律也。词之有律,与人之有五官无异。五官之位次一定不易。若移目为口,置耳于鼻,鲜不骇为怪物者。词之于律亦然。人必五官端正而后论妍媸,词必四声和协而后论工拙。否则长短句之诗耳,何云词哉?”(《翠微雅词自序》)在顾氏的启发下,嘉庆以来吴中商榷音律、研探词韵的风气愈见其盛,顾氏虽然没有成为吴中词人群体的领袖,不过,他作为乡前辈对吴中词人群体的形成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顾氏曾为《词林正韵》、《吴中七家词》撰写序言,称与吴中七子为世交,推举之心、奖掖之情甚切。
另外,吴中七子之一的王嘉禄,乃王芑孙之子。芑孙幼有异禀,年十二三即能诗文,有《渊雅堂编年诗稿》二十卷,其词作《瑶想词》一卷,被陈乃乾辑入《清名家词》。沈彦曾之父沈清瑞,号芷生,与兄沈起凤俱以诗文名,其诗宗齐梁,而出入初唐四杰之间,尤擅词,有《沈氏群峰集》五卷、《绿春词》一卷。王嘉禄《兰素词序》云:“吾友兰如,芷生丈季子也。少负殊禀,以余力精研四声二十八调,而求其离合。又性喜游历,客武林最久,烟晨月夕,迥清饮渌,辄以宋人乐府写之,顷将刻行所作削稿相质。循节揣声,动谐律吕,有空灵之气,有宕往之神,有凄缛之采,有绵邈之旨……是非原本家学而又得山水清气以为之助,乌能及是耶!”综上所论,可以推知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前辈的影响与奖掖嘉许,为戈氏等从事声律之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亦直接推动促使了吴中倡举声律词人群体的形成。
四
吴中词人群体标举声律亦有针对词之创作过于诗化的弊病而救治的意图。一方面词乐的散佚失传,曲的兴盛,使是词的音乐体性逐渐消亡。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云:“词萌于唐,而盛于宋。当时伎乐,惟以是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易于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于是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其宗宋也,亦犹诗之宗唐。”词作为一种文体应该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样式,是文本形式与音乐形式的结合。由唐宋历元明至清,词由“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成为文章之一种,即指出了词之作为综合艺术的文本形式与音乐形式由并驾齐驱、比翼并重而渐失一翼,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的流衍进程。由此来看,清词的中兴,亦不是作为综合艺术的词的复苏,而是词的文本形式的兴盛。
另一方面,清词复兴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清人推尊词体的不懈追求,是非常重要的。从清初《倚声初集》把词同诗、文、赋等传统上被认为是正统文学的文体相提并论,以重词价,推尊词体,到浙西、常州词派,竭力把格律形式的词赋予古近体诗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地位,或崇尚“醇雅”,或重视比兴寄托,以攀附儒家诗教。此种尊词的路径与李清照《词论》中推尊词体的思想可谓大相径庭。李清照所推重的是综合艺术的词,而清代之尊词走的则是苏辛以诗为词的路子。对这一问题,晚清词人王鹏运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词林正韵跋》中曾言:“夫词为古乐府歌谣变体。晚唐北宋间,特文人游戏之笔,被之伶伦,实出声而得韵。南渡后与诗并列,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当其末造,词已有不能歌者,何论今日!”“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即说明词之尊体是以牺牲“词之真”——词之音乐体性为代价的。
戈载等针对词之创作过分诗化的现象,从音乐体性的角度来推尊词体,他认为“词之所以为词者,以有律也。词之有律,与人之有五官无异。五官之位次一定不易。若移目为口,置耳于鼻,鲜不骇为怪物者。词之于律亦然。人必五官端正而后论妍媸,词必四声和协而后论工拙。否则长短句之诗耳,何云词哉?”(《翠微雅词自序》)当然要恢复宋之词乐已不再可能,沈义父《乐府指迷》已批评其时作词风气,“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其原因在于词之音律亡失,依音律填词也不再可能,就只好依照格律来写作了。格律与音律虽存有许多的差异,但于格律的恪守中却可见出吴中词派追求词之音乐体性的苦心。也正如王鹏运所言:“居今日而言,词韵实与律相辅。盖阴阳清浊,舍此更无则律,是以声亡而韵始严,此则戈氏著书之微旨也。”(《词林正韵跋》)戈载强调填词应严守格律,并对当时词之创作中存在的“恃才者不屑拘泥自守,而谫陋之士,往往前人之稍滥者利其疏漏,苟且附和,借以自文,其流荡无节,将何底止”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实虑伪误淆混之处,沿习既久,沉溺难返,韵学不明,词学亦因之而衰矣”,遂提出“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律,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词林正韵·凡例》)的主张,其中“声音之道”,“宫调之理”,即表征了他对词之音乐体性的执著与渴盼。
实际上戈氏没有对过分追求词之诗化,注重内容的比兴寄托的偏至予以过多的批驳,仅是标举声律的宗旨,客观上是一种冷默的反抗,它与浙西、常州词派的理论与创作主张形成一种制衡,对清季民初的词坛产出了深刻的影响。如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论近代词派云:“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像朱古微、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一卷三号)蔡嵩云《柯亭词论》论临桂派词人曾云:“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与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广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即指出了吴中词人群倡举声律的潜在意义。当然,吴中词人提倡声律亦存有针对浙西末派流弊起而救之的因素,金应珪曾将浙西末派的弊端归纳为三,即淫词、鄙词、游词。常州张惠言从内容上注重比兴寄托,强调词体的严肃性、崇高性,戈载等则从词的外在形式入手,强调词的音乐性,对率尔操觚、肆意为之者进行批驳。
其实戈载等倡举声律以纠正词过分诗化以及浙派流弊的做法,是效仿南宋姜派词人标尚格律以救治辛词末派流于粗豪叫嚣,词之音乐体性殆失的弊端。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悖论是文学研究中一个两难命题,二者必须统一和谐,融为一体,过分强调一方,均会产生一种偏至。而当此一偏至出现时,往往又有标举它的对立面予以救治,形成一种制衡。上述情况即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