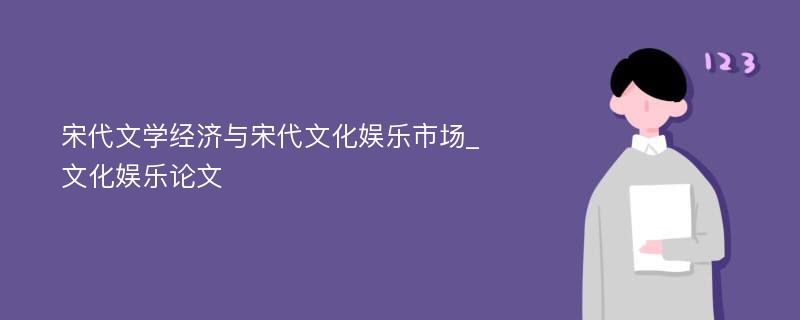
宋代文学与经济——1.宋代文人与文化娱乐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化娱乐论文,文人论文,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2-0048-17
和以往的朝代相比,宋代的城市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汴梁的人口规模超过百万,随着唐代坊市制度以及夜市禁令的取消,代之而来的是店铺林立,通夜骈阗。庞大的人口规模,相对繁盛的市场经济,在城市中催生了规模巨大的文化娱乐市场。宫廷教坊而外,《东京梦华录》提到的汴梁城内外瓦子八座,城内外妓馆娼楼十九处。这还只是专门性的文化娱乐场所,实际上,多数酒店亦兼营娱乐行业:“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向晚灯柱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宴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1]靖康之难后,宋迁都临安。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大量人口的迁入,使得临安的繁华很快便不减旧都,而文化娱乐行业更远过汴梁,如《武林旧事》提到的杭州内外的瓦子有二十三座之多;妓院娼楼、兼营娱乐的酒店茶楼更是星罗棋布,遍布全城。
在宋代的文化娱乐市场中,文人居于非常明显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约略体现在以下数端:首先,从文化市场的消费情况来看,文人士大夫占据了这个市场的高端。据南宋洪巽《旸谷漫录》记载:“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御侍。”[2]而《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也记载“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一供饮客之用……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妓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3]许多市井阶层的家庭培养女儿学得包括歌舞在内的许多才艺,其理想的目的是侍奉士大夫;而名妓(宋时名妓以歌舞才艺表演为主)在一般情况下也以士大夫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视侍奉士夫以外之人为降格。其次,从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内容来看,无论是话本、杂剧、院本、诸宫调,其内容多或出于史传、或出于前代文学作品,其对前代文史的关注态度很明显是文人化的;而故事中男性主人公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士,他们占据了文艺舞台的绝对主角位置,市井阶层在文艺作品中是不折不扣的龙套。再次,就当时文艺作品所流露的生活态度与趣味来看,品味高雅的宋词所流露的自然是士大夫的趣味和生活,这种带有非常明显的富贵气息与文人意向的作品能够获得整个社会包括市井阶层的认同,足以说明整个社会对文人情趣的趋奉;而一般通俗性的文学作品也充满了对士大夫生活方式与情调的艳羡,尽管这种艳羡出于市民的视角,和真正的士大夫情怀还有着非常明显的距离。
宋代文人在文化娱乐市场的主导地位,离不开他们所具有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处境。纵观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文人所受到的优容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优容的获得,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赵匡胤以陈桥兵变起家,而这已经是五代以来兵士拥立皇帝的第四次。为了改变这种“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建立一个文治而非武治的社会,就必须处处刻意抬高文人,以便为整个社会树立方向与榜样,而具体的措施,就是一面奖励进士,拓宽进士的出路,一面提高文官的待遇。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唐,但隋唐两代每科取进士不过数十人,并且即使考中进士也不能立即做官。进士出身,在隋唐确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然就总体而言,读书做官还不足为具有广泛号召力的理想出路。宋代与隋唐不同。宋时开科取士,进士名额多至七百人,士人一旦获得进士出身,即刻便荣登仕途。作为进士中佼佼者的状元,获得的更几乎是全社会的崇拜:“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疆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幸无以加。”[4]官员的俸禄也优厚到了让整个社会艳羡的程度,除正俸外,尚有禄粟、职钱、从人衣粮、冬春服等名目繁多的补贴项目,并且即使致仕,也仍然享有半俸,谓之“祠禄”。数量庞大的群体,崇高的社会地位,宽裕的经济处境,遂使得士大夫成为整个社会最为优越而令人艳羡的阶层,也因此成为文化娱乐市场必须迎合的消费群体。
与元明两代的对比可以将宋代文人在文化娱乐市场上的优越地位映衬得更加突出。元代文化娱乐市场中文人的卑下地位是一望而知的。这种卑下的地位,反映在娱乐消费上,是无力与官僚和富商争胜,即使与青楼名妓交好,依靠的也往往是以其才华博得的同情,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宋代文人相对与青楼阶层的巨大优越感:反映在文艺作品的内容上,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尽管由于文人仍然掌握着文艺作品的话语权力,所以在很多作品中还是文人为主角,但无论是杂剧中他们在情场上的大获全胜(如《救风尘》),在仕途上的直上青云(如《破窑记》),背后都难以抹去巨大的精神胜利意味和对现实的悲酸,更不用说散曲中的牢骚满腹;而在艺术趣味上,则不得不全面向市民趣味靠拢,不避浅俗甚至庸俗,因为文人含蓄精致的艺术追求已经随着这一阶层的沦落而受到鄙弃——而这一切都可以在元代文人卑下的社会地位和寒窘的经济处境中找到答案。和元代文人的全面沦落相比,明代文人的处境要好得多,但随着经济的发达,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时代的弄潮儿此时已是市民中的佼佼者商人。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低到靠正常的收入尚不足以维持一个规模稍大的家庭的良好运转——海瑞死时的贫穷就是对这一史实的极好说明——所以靠手中的权力寻租特别是向商人寻租乃成为明代中后期的通行做法,而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风气的败坏,斯文扫地与对商人财富的艳羡,反映在文化市场上就是市民趣味在文艺舞台上的大放光彩。相比之下,尽管和宋代的城市规模、城市经济相适应,市民此时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他们中的上层分子——商人,更在商业的经营和运作中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如《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条记载,一些大型的从事金银财帛交易的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5]但就整体的情况来看,商人这一时期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宠儿。反映在文化娱乐市场上,就是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独特声音,他们的审美趣味还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是以配角或反面的形象出现。
文化娱乐行业的高度发达,对宋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市场的刺激下,一些直接面对市场的文艺类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种情况可以举出宋杂剧、戏文、说话,也包含一些为射利的词作,比如柳永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实际上就是靠填词谋生的。如果没有发达的文化娱乐市场,它们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托。当然,文化娱乐市场的刺激并非只是这样直接和简单。发达的文化娱乐市场的存在实际上也构成了宋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背景。离开了这个大的背景与环境,一些文学现象则无法想象。以一代之文学宋词而论,除了少数作家如王安石等不涉及狭邪之游外,如欧阳修、苏东坡等绝大多数作家的词作中都有很多表现风花雪月、偎红倚翠的内容,乃至为数众多的赠妓之作。这些作品本不为射利,但如果缺少了宴游之乐,词客高会这一特定的娱乐场合,离开了歌妓红牙板上、唇吻之间这一特殊的传播媒介,离开了对于风月场上优雅扬名的追求,则是不可能被创作出来的。实际上,词在元明两代的衰落原因固然众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随着音乐的变化渐与日常娱乐的分离。尽管如此,词与娱乐行业特别是青楼的关联还是斩不断理还乱,后世文人的词作中多写风花雪月之情,男欢女爱之思,词的文体特点固然是一个原因,而词的表达内容的延续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文化娱乐市场的存在,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和以往非常不同的评价体系,这对文人的创作心态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以往对于文学创作的评价多决定于一个很小的名人文化圈子,圈子中的权威人士的褒贬,有时竟然能够瞬时确立一个人的名声,典型的例证比如贺知章对李白、顾况对白居易的揄扬。尽管从更长远的范围来看,作家的名声最终决定于艺术成就的高下,但小圈子的评价在当下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评价机制在宋代依然存在,其影响力也没有丝毫的减弱,比如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评价,使得苏轼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发达的文化娱乐市场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机制。尽管这个市场的主导力量是文人而不是市民,但毕竟面对的市场消费者的构成要复杂得多,其评价机制也要复杂得多。在这个机制内,作品的价值不决定于权威的品评褒贬,而是决定于更为广泛的市场消费者,在这个机制面前甚至皇帝也无能为力。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柳永。文人圈对柳永评价普遍不高,认为其人儇薄无行,其作词语尘下,鄙俗浅显,甚至仁宗皇帝也对其很不以为然,在柳永参加科举本来已经考上的情况下,临轩放榜,黜落其名。文坛的否定,最高统治者的打击,使得柳永称为廊庙的逐臣,但这并没有妨碍柳永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内获得的巨大成功,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就赋予了文学作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也给与了文人除获得文人圈子承认外的一种别样的追求。柳永的情况当然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典型,但文化娱乐市场的影响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许多作家的身上。特别是那些和市场联系更为紧密的、靠市场过活的下层文人如书会才人、杂剧作家等,追求市场效应就更是压倒性的考虑了。这种影响,在宋代已经渐渐明显,而在以后的社会中,发生的作用则更为积极和重大。
收稿日期:2007-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