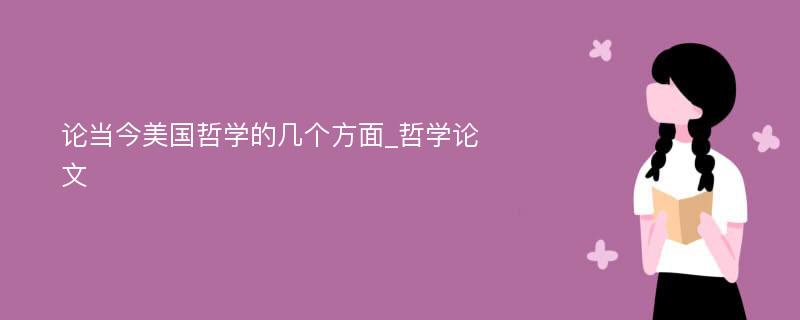
今日美国哲学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哲学论文,今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美哲学目前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错综复杂,哲学的主题分类完全打破了古代把它分为逻辑、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三分格局。
“应用哲学”——对科学、法律、商务、社会事务、计算机使用等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哲学反思——的迅速成长是北美哲学的一个显著的结构性特征。特别是过去三十年来,狭窄地专注于特别问题的哲学研究领域有了极大的扩展,扩展到对诸如经济公正、社会福利、生态环境、堕胎问题、人口政策、军事防御等领域。这种情况表明了当代英语世界的哲学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强调对特殊问题和课题进行具体的研究。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总之近年来英语世界的哲学家都倾向于摆脱那些范围广阔、包罗万象的抽象问题,即为怀特海或杜威在早期所特有的那些问题。如今,他们倾向于注意研究那些与传统哲学关心的大问题相关或由之产生的小规模的具体问题。哲学从那些总括性的一般的、大范围的问题转向了更狭窄地集中研究微观上细小的具体问题,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哲学的一个独具的特征。在哲学中,广泛地使用个案研究法,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对这种现象没有一个哲学家表示赞许,但对一个当代观察家来说,这似乎是对“时代精神”的广泛的自发的表达。
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美国哲学的性质也逐渐变得技术化了。哲学史家不断地钻研那些小的哲学的和概念上的细枝末节的问题。哲学研究日益广泛地使用语义学的形式机制、模态逻辑、编辑理论、学习理论等。越来越重的理论装备用到越来越小的目标问题上以致于使杂志的读者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技术性术语的增加绝不应当超出必要的限度。哲学的技术性不断增强无疑会牺牲哲学的更广的可接受性,甚至牺牲对本行的职业成员的可接受性。没有一个单独的思想家能精通表达今日美国哲学的知识和兴趣的全部范围。也没有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会大得使该系的教职员包罗哲学这门学科全部分支的各种专家。哲学的领域发展得不仅超出了从事哲学活动的人们的能力,而且也超出了它的机构的能力。
那么,美国哲学家是在发挥影响吗?当然在这里,关键性问题是对什么人发挥影响?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其他哲学家的影响。我们已经指出,甚至那些“领头的哲学家”力求影响别人的程度也是零零散散的:在每一场合下,只涉及整个一群人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现在转而谈论整个社会,那么我必须着重指出,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影响。美国哲学家并不是舆论制造者:他们没有接近那些力图制造舆论的媒体、政治机关、思想库等的门路。就他们毕竟还发挥一种外在影响来说,这种影响也局限于其他领域的学术界人士。行政管理学教授可能读J ·罗尔斯的书,文学教授可能读理查德·罗蒂的书, 语言学教授可能读W·V·奎因的著作。超出学术界范围以外, 如此重要的当代美国哲学家也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在本世纪初——即在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和乔治·桑塔亚那这样一些哲学家的时代——那时,情况有所不同,个别哲学家的论著至少在较为广泛的公众中搭起了某些讨论和辩论的舞台。但在今天的美国则决非如此。在美国,哲学家以及一般学术界人士在制造明达的舆论方面起不了多少作用;这种工作多半是由时势评论员、影片制作人以及谈话节目主持人来做的。今日美国社会并不反映哲学家关心的事情,反之,如果毕竟在某些地方多少还有“关系”的话,那么在那里就是哲学家的论著还反映社会所关注的事情。
许多哲学家并不热心于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哲学家大体上都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在培育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术上专长——充当观念领域中工作的专门家。这就意味着,一般说来,他们的论著是写给那些作为学术伙伴的读者来看的,而对于广大的知识性读者公众则并不怎么感兴趣(或并不存多大指望)。这是北美哲学界与大陆欧洲情况又一个明显不同之外。美国哲学是面向学术界和学者的。与之相对照,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哲学是通过关心当前争论的问题而面向更广大的由知识性读者组成的文化群众的。还有,“政治上的谁是谁非”,这是在美国各种校园里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在哲学家当中比较地说来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与诸如法律或文学领域的活动者相比)。在比较有限的美国哲学家的圈子之外,人们还是指望他们为自己的主张说出道理来,而不是用一种流行的惯于不以为然的态度去对待不赞成他们的人,更不用说采取骂人的态度了。高度专业性的职业特征趋于抵制在这个领域中的政治化。
当代美国哲学专门化倾向的突出使它(与其他时间其他地方相比)带上更多专业性和技术性特征。这就使得哲学行业被赋予某种勤奋有干劲的精神。人们相信可以用技术性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哲学对于那种悲观主义来说是没有用处的,这种悲观主义停留于用忧郁的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待人类的能力之不足。由于当代美国哲学局限于高等教育的范围内,因而不可能轻易提供青年并不打算听取的启示。
同样,日益增加的专门化倾向迫使哲学走向象牙之塔。因此,人们不可以看到最近一些年来哲学在美国文化中失宠——并不是以往向来受宠若加而失宠。多年来,不列颠百科全书每年都出一本补集名曰《年鉴》,在诸如世界政治、健康、音乐等条目下分别地谈论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直到1977年的各卷《年鉴》中,关于上一年各种发展情况的内容目录中都一直包括哲学这一条目。但是,自1977年以后,哲学条目消失了,连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在美国建国二百周年(1976年),人们似乎看到了哲学从美国人关心的领域中消失了。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美国的名人录(Who's Who)也戏剧性地去掉了哲学家和一般学人。 在同一时期,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从《时代》到《纽约时报》——都对当代哲学与人类条件问题不相关联而表示哀叹,抱怨哲学家们自我欣赏地迷恋于逻辑和语言的技巧从而使这一学科与非专业人士的问题和利益毫无关涉。显然,发出这种哀叹表明了大众对哲学的象牙之塔的疏远,同时也正好标示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这个时期,美国哲学家开始饶有兴致地转向那些摆在公共政策和人类事务日程表上的种种问题。应用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的兴盛,德性伦理学(信任、希望、邻里和睦等)、社会伦理学(分配公正、隐私权、个人权利等)的繁荣以及诸如哲学与社会、甚至哲学与农业等等哲学复合词的蓬勃出现可能也恰好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历史的篇章中出现一个非比寻常的讽刺,那就是在哲学回到当代种种问题之时恰好是在公众把哲学当作与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全然不相干的学科而放弃对其进行思考之日。
事实上,哲学在美国的(与学术性相对的)通俗文化中没有多大地位或者完全没有地位。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人们追求对宇宙的总体性理解的冲动是由宗教(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而不是由哲学来调节的。哲学问题按其本性来说是繁复的,而美国人不喜欢繁复性,他们显然喜欢答案更甚于喜欢问题。实际情况是,哲学家必须依靠细心的区分和精心挑选的规定。在这方面,美国人并不想知道在哪里隐含着复杂性,他们向往的是谚语中所说的独臂专家,他并不常说“另一方面”如何如何。我们是讲求实际,要求有效地解决问题的人。(请看在庞大的自助书市上充斥着的各种各样包含教条式灵丹妙药的图书吧!)
尽管哲学目前对广阔的北美文化并没有真正的影响,然而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却是稳固的。诚然,在美国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中,只有大约0.5%的学生专修哲学(比较一下,将近3%的人专修英语,15%以上的人专修商业和管理)。但是由于哲学在满足分布要求方面的作用,因而它在中学后教育的课程中还保持着一个显著的地位。在英国,第二次大战以后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哲学工作持有一种非常技术化的,设想得很窄的观念,结果他们有效地保持了该学科在教育系统中日趋下降的地位。与英国不同,美国不仅认为哲学要在高等教育中予以保留,而且甚至还应有所繁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了实际的和调整性的转变。美国哲学家在看风使舵方面向来是富有灵活性的。当社会上需要联系社会问题时,于是一种新的专门的“应用哲学”便应运而生。当医疗伦理问题或女权主义的远景主义问题为社会所关注时,一群有关的青年哲学家便随时准备投身于此。
因此,今天美国哲学继续富有活力地存在下去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哲学在几千个允授学士学位的机构中各有两三个够格的代表者,那么它就可以继续作为一种活跃而有成果的事业存在下去。
人们不会感到奇怪,在美国的学术舞台上哲学活动通过反映广阔的社会问题而得以繁荣。1991年在美国哲学学会的东部分会计划中的45个专题会议中,有六个会议是讨论女权主义主题的,两个讨论有关黑人问题。这样地把大约15%的计划项目内容用于讨论今日美国政治议程中的突出问题,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期刊文献的主题上,这些题目也得到比较突出的反映,正如《哲学家索引》条目所表明的,拿出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的期刊是很少的。有点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发表大量言论,他们似乎以此来抵销哲学家队伍中妇女和黑人的比例很低这个事实。
然而,有时乍看起来似乎是大规模的现象,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所投射出来的巨大的阴影。北美的女权哲学看来就属于这种情况。目前在这一领域中只有两家杂志(《女权主义研究》、《赫帕提要》),只有两个学会(分析的女权主义学会、哲学中的妇女学会)。就哲学来说,学术上的女权主义,不管在别的地方多么突出,目前在统计上不过是小小的信号而已。(诚然,从无到有总是一个大的变化。)
(李步楼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