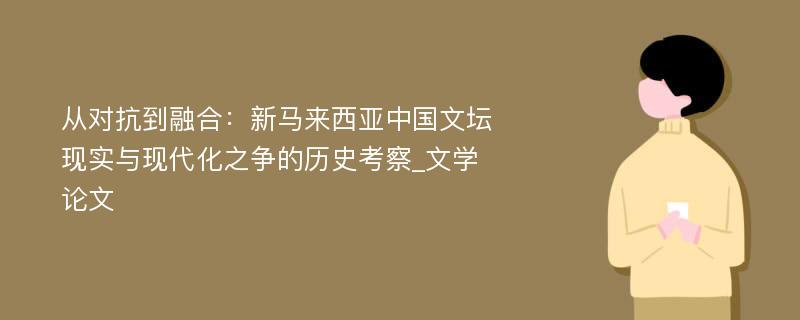
从对峙到合流——对新马华文文坛“现实与现代之争”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之争论文,现实论文,新马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0)04-0012-05
脱胎于中国新文学的新马华文文学①与她的母体一样,由于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历史使命,从一开始就与现实主义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20年代初,还处于发轫期的新马华文文学呼应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暴露黑暗”,“为人生而艺术”。方修考察梳理新马华文文学时明确指出:“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不是浪漫主义,更不是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等等。”②2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华文报纸副刊的编者如黄振彝、张金燕、陈炼青等开始提倡“南洋色彩”进入文艺,目的是改变新马华文文学浓厚的“侨民意识”,希望文学/文艺多描写南洋的现实风貌,扎根于南洋。随后,相继出现了提倡“新兴文艺”的运动(1929年)、“马来亚文艺”的论争(1934年)以及“抗战文艺口号”的论战(1938年),都表明新马华文文学想摆脱中国新文学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发展的愿望。它们仍然是在现实主义层面进行的,强调文学应该多反映马来亚的现实,不要老写“侨民题材”。1947年至1948年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是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与主体性确立的关键,焦点依然集中在现时的文学是反映马来亚地方现实还是书写中国内地题材的问题上。这一切都说明,新马华文文学在试图建构自身独成体系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增强,侨民意识淡出,逐渐脱出直接呼应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格局,但现实主义精神并没有由此减弱。50年代以后,新马社会历经一波三折的政治变动。1946年至1950年的宪制改革,将非巫族马来亚公民权益问题提到历史日程,1948年为了对付马共全国进入紧急法令状态和1957年围绕马来亚独立宪法制定前后的风波,使“政治民主”、“文化多元”问题成为新马华人最关心的问题。这一切都使新马华文作家不能不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适时提出,在思想意识上明确地向马来亚华人灌输国家观念,加强华人对马来亚的归属感,并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文学功能上则倾向于强调反映现实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充溢着为民请愿的激情。所以,新马华文文学即使在已中断了同中国文学现实形态和思潮的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现实主义轨道上运行。从以上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主流非常符合当时的史实。
现实主义作为最强盛的创作力量活跃在新马文坛上,有力地介入到社会人生的诸多层面,但这种情势到了60年代开始分化瓦解,并非现实主义对立面的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给新马文坛带来了持续近20年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如果说马来亚独立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一直存在着“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之争,那么独立之后至70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从未断歇过。这两大跨时代的论争,前者确立了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与主体性,后者则创造了“东方现代主义”,使新马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相接轨。因此,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予以关注,是我们了解六七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1961年,忠扬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学会举办的第二次马华文艺座谈会上发表《关于马华文艺的思想性》的演讲,开篇指出:“我们如果肯定马华的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是在于反映马来亚社会现实的真实,并通过对于典型环境的典型形象的创造,来达到教育广大人民的目的,进而完成其基本任务,即是在人民的爱国事业中(一)担负意识斗争的工作;(二)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要求。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马华文艺因为在客观上遭受到巨大的压力,以及自身还缺乏与劳动人民取得紧密的结合,所以被迅速发展着的社会情势,远远地抛落在后头了。”③忠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困境,但由于“当局者迷”,他一时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现实主义会在新时代举步维艰。他只是把责任归咎为马华文艺的思想倾向出了问题。他在演讲中列举了四种亟待批判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正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文艺的表现。也就是说,忠扬在此将现实主义的萎缩归因于现代主义的崛起,要求重新调整马华文艺的思想倾向。作为现实主义的忠实服膺者忠扬,对现代主义艺术展开全面批判的文章是1962年发表的《评仲达的表现主义理论——兼论现代派艺术》。在文章中,他分析了现代派艺术产生的土壤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哲学思想基础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它“背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原则”,是“较之前此的形式主义更加荒谬绝伦的新型形式主义”。对于现代派主张“艺术家内在精神才是艺术真实的基础”,“完全摒弃过去的一切艺术传统”而“出‘新’制‘奇’”颇不以为然,尤其是强烈地批判了仲达所认为的“表现主义”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质”,以“一草一木”暗示社会本质的荒诞。在他看来,“唯有狂妄的神经质者才敢大言不愧地自认‘个人的意识可以表现出人类的全意识’”。另外,忠扬认为现代派艺术所表现的“空洞的、颓废的、神秘的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唯心思想”,客观上“消解了人民群众的斗志”,而现代派片面地热烈地追求“形式的唯美、绮丽、怪诞、刺激、新奇”,则会“误导人们走上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艺术道路”④。可以看出,忠扬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对于现代主义的“打破传统”、“新奇”、“颓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虽有偏激的一面,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读者的心态。
事实上,现代主义文学(当时称为“现代文学”)在新马文坛兴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述忠扬提到的“现实主义落后于社会形势”乃是由于“客观压力”和“没有与人民紧密结合”。在这里,忠扬不敢明说“客观压力”是什么,但我们能感觉出来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压迫。1957年,马来亚独立。虽然在独立制宪前后风波不断,但新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原则和国家文化还是一边倒,完全倾向于马来族,使占马来亚全部人口近半数的华人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及边缘的地位。华人一方面变“叶落归根”思想为“落地生根”,清晰地确定了国家意识,另一方面却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排斥,不但不能享受与马来族同等的权利,而且还在语言、文化上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再加上政府打击马共,把华人视为“危险分子”,更使马华作家处处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压迫,生存环境相当压抑。因而,凡牵涉到政治、经济、宗教、种族、文化、教育等敏感问题时,马华作家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生存策略导致文学直面社会人生、反映现实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丧失,活力逐渐萎缩。另外,60年代以后,马来亚社会开始由农业为主向工业化转变,乡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方面……即马来亚社会逐渐迈向复杂化、现代化之路。而现实主义文学却没有与时俱进,依然遵循受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和俄苏写实主义影响的那一套理论,僵化的文学技巧、单纯的文学表达、粗糙的文字运用已经阻碍了文学诠释日趋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生。在这种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现代主义不失时机地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它不但可以借用暗示、寓意、象征、隐喻等手法曲折地表达复杂多变的社会现状,还可以潜入人的内心世界以心灵的骚动、压抑、困惑、失落来隐约呈现那个高度压抑的社会现实,从而超越现实主义,拓展了新马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
在文论史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不是相互对抗的文学思潮。那为什么在新马文坛上它们却以对抗的关系呈现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现实主义者出于保护现实主义在文坛的地位的目的,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新兴的现代主义作品,而是抓住现代主义采取象征、隐喻等方式造成“晦涩难懂”和潜入个人内心世界带来“脱离现实”等大作文章,有时候将之上升到“资产阶级思想”、“颓废”层面进行批判抵制。上文谈到的忠扬对现代派艺术的批判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早在忠扬的批判之前,针对《蕉风》在1959-1960年大量刊登的现代诗,1960年4月杜萨在《南方晚报》上写了两篇《新诗拉杂谈》,对现代诗首次展开批判。应该说,在新马文坛,受台湾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现代主义最早也是在诗歌方面发生的。所以,关于现代诗的批判是最早也是最多的。这里,我们以1964年钟祺发表的《论诗歌的创作目的——现代诗的批判》一文为代表,分析一下当时现实主义者面对现代主义兴起的心态和批判理由。钟祺从现代主义诗人认为“诗歌的创作是没有任何目的”和“诗歌创作本身就是目的”入手,分析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特别以台湾现代派诗人纪弦和覃子豪的作品和观点为例,批判他们是“最顽固最退化的一种诗派”。他总结说:1.现代派反对自古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承继了“西洋一切疯狂、堕落、颓废、极端个人主义的传统”,这样,会“毒害人们的纯洁的心灵,麻痹人们对生活的斗争的热情和意志”;2.现代派在作品中“散播着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悲观思想,一种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的命运充满着恶意的嘲笑”,是“对怀着炽热的希望从事于波澜壮阔的社会事业斗争的人们一个严重的打击”⑤。这是一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把现代主义者(或形式主义者)归类到“极端仇视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这一层面进行批判的,其中曲解的地方很多,和忠扬的观点可以相互佐证,反映了当时现实主义者面对现代主义的“奇异风”不知所措的情状和“上纲上线”的批判做法。
二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主义具有激进的反传统特征,面对现实主义日趋僵化的文学思维和保守姿态,现代主义的批判是摧枯拉朽式的,甚至不顾自身蹒跚学步时的幼稚,义无反顾地冲击新马文坛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不能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去谋求与现实主义的共融共存。1964年,林方为了驳斥钟祺对于现代诗的批判,发表《致钟祺先生》一文,其中引用法国诗人蓝波的话说:“一切必须现代化,因为人类既已从农业时代步人工业革命,就不应该开倒车,守旧地去写古老的东西,而应发掘身处时代的事物,方免沦为闭门造车和无病呻吟。”⑥对于现实主义的文学表达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形势的指责非常激烈,似乎现实主义消亡、现代主义兴起是必然的“更替”,毫无商量的余地。1968年,牧羚奴(陈瑞献)在诗集《巨人》⑦的《自序》中指出:“……一个诗坛之不‘混乱’,原因它已经时间的过滤。多少年来,一直有人在努力要使诗成为某种特定意识的附属品,他们喧嚣叫喊:不是这种模式制出来的,都不是诗;另一些人,一样从外地运来一些第三手的理论,鼓励所有写诗的人去依模制作。这些毫无自尊的模式主义者,给我们的诗坛带来了严重的阴悒和不自由的空气……”对现实主义主宰文坛达数十年之久,已经模式化/僵化予以抨击。接着又说:“整个诗坛像一间老旧的屋子的今天,我们,星马少壮的一群……只好把一间风来摇雨来漏的老屋拆掉……在重建的过程中,蓝图的设计,材料的采购与应用等,除本地的之外,当然可以参考或选择一些外来的东西,但没有一个诗作者可以从外地搬来一座房屋……我们必须自建、自造一座自己的有现代化通风设备的大厦。”同样主张要将现实主义这间“老旧的屋子”拆除,呼唤现代主义出来重建诗歌“大厦”。比较好的是,牧羚奴在此注意到了不能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应该适当地融入创新意识,“自造”自己的诗歌“大厦”。然而,措辞还是相当激烈的,引起现实主义拥护者的反感在所难免。
在新马文坛,现代主义之所以与现实主义形成对抗之势,更多的时候是由于双方都流于“意气之争”,缺乏平和、宽容的姿态相互打量/审视对方所造成。现代主义要想获得读者,获取市场,不能片面地靠攻击、指责现实主义的疲软、僵化来进行,它除了“苦练内功”提升自身作品的艺术质量、摆脱“呀呀学语”的幼稚之外,还必须要在沟通读者方面下功夫,因为过去读者“接触的都是比较接近古典主义的作品,他们习惯的是完整的结构,着重情节的描写和以动作和对话为中心的作品;他们对现代文学是陌生的,他们看不惯心理刻画,不能欣赏那些看来似无结构的结构,也不能捕捉作家在作品中的隐喻”⑧。为了使读者能够增强领略和欣赏现代文学的能力,实际上,从1961年起,现代文学“大本营”——《蕉风》⑨就开始大量刊发台湾及欧美现代主义作品及其评介,此举被《蕉风》的同仁们一致认为是“牵涉到马华文坛今后一个阶段的趋向”⑩。对于现实主义所指责的弊病如“晦涩”、“脱离现实”等,有些现代主义的提倡者也积极予以了回应,为读者澄清是非事实。1968年完颜籍(梁明广)先后发表《1968年第一声鸡啼的时候》(11)和《开个窗,看看窗外,如何?》(12)两篇文章,针对现实主义批评现代主义文学“晦涩”和“脱离现实”的说法,分别作了如下解释:“不习惯是晦涩的母亲”,“意境的浓缩与文学的浓缩加上现代人的特殊复杂感触”使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以往文艺的习惯”,“注定看起来要吃力”,“因此是晦涩的”;“现代诗最恼人的(古诗亦然),全是它的高度象征手法。其实象征并非邪魔外道,他仍是为了写实而来。这‘实’便是诗人心中的意境(写诗的人无法否认意境是现实——外在现实侵入诗人心灵,经过诗人心灵过滤后的现实)。许多现代诗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最高度的象征手法”。可以说,完颜籍的分析切中肯綮,能够比较冷静地寻找现代主义被指责的原因。
70年代以后,新马文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仍然时断时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渐渐为读者所接受,打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现代主义在小说领域兴起之后,现代主义的提倡者渐趋平和,开始立足于自身生命的体验,谋求与时代、传统的沟通,在不脱离华族文化、南洋乡土的基础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接轨,逐渐形成独具一格的“东方现代主义”模式。而现实主义在与现代主义的论争中,也开始反省自身,注意吸取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拓展表现空间,向方修所划分的现实主义之最高阶段“新现实主义”进化。
1978年,温任平发表的《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13)一文,不妨看作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的总结性文章。在这篇长长的论文里,温任平首先指出“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亦称“现实主义”)不是对立的两种主义,提醒人们注意“‘现代主义’也是写实的,它所着重的不仅是‘外在的写实’,更重视‘内在的心理的写实’”。接着,为马华现代文学溯源,确定白垚(刘戈)1959年3月6日发表在《学生周报》上的诗作《麻河静立》是第一首现代诗,对《蕉风》推行现代主义思潮的功绩给予了肯定,而且着重分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形成对峙之势的原因。他指出:因为现实主义盘踞文坛数十年,显得“老大疲弱”,“粗糙的文学表现形式已不能满足作者的内在要求”,“使得不少勇于尝试创新的作者感到不耐甚至厌恶”,导致现代文学兴起;而“现代文学的崛起使得写实主义”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写实主义的作者群因而“有时是以谩骂方式”、“有时是较为间接的影射”,将现代文学斥为“异端”、“崇洋”、“晦涩难懂”、“表现的只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没有道出劳苦大众的心声与愿望”等,“使得现代文学的作者一方面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则指出对方文学观点的错误或偏激处”。这样,两派便形成对峙之势。两派作者因此“发生过多次笔战”,但“逞意气的成分”较多。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温任平,身在论争圈内,能够这样辩证地分析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十分难得。
温任平还分别对新马文坛的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和现代主义理论及译介作了一番简要的回顾和总结,肯定了现代主义文学出现的意义。他说:“现代主义反对‘文学工具论’”,“现代主义要反映的不仅是社会上的某个阶层,更遍及社会的各阶层”,而且,“它企图映现的是整个社会或时代的黑暗与光明”。这里,温任平点出了现代主义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的可贵之处。最后,温任平毫不留情地指出现代文学所患的幼稚病:“文字的生涩”、“精神的颓废倾向”、“作品缺乏深度和广度”等,这些也正是现实主义阵营经常指责它们的地方。温任平希望现代文学的作者能够正视这些问题,从论争中获取经验,要有“雅量接受”,“然后另谋兴革”,把加强“社会性”作为现代文学今后发展的方向。
温任平在此纵横捭阖地论述,肯定了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却没有将现实主义“一棍子打死”,反而隐隐有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合流的架势(自始至终,他都反对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这是温任平严格而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强烈的自审意识所观照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就现代性而言,新马华文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还有各自的盲区,我们期待着后来者作进一步的探索。
收稿日期:2010-07-10
注释:
①必须指出的是,在历史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为英国殖民地,共处在一个政治实体中。因此,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当地习惯简称马来亚华文文学为“马华文学”。新马分家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仍沿用“马华文学”,而新加坡华文文学则简称“新华文学”。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不作细分,放在一起并称为“新马华文文学”。
②方修:《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见《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
③④忠扬:《新马文学论评》,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第3页,第77页。
⑤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委会:《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1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年,第582页,第578页。
⑦1968年,新加坡五月出版社成立,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出版现代文学书籍的唯一团体。它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就是牧羚奴的诗集《巨人》。
⑧《如何连接环结》,见马来西亚《蕉风》第129期。
⑨1955年《蕉风》创刊,后在编者姚拓、黄崖等主持下,不但积极引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理论,还大力扶持本地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者,发表过一系列关于“现代文学论争”的文章,由此成为了现代主义的大本营。
⑩见马来西亚《蕉风·编者的话》第128期。
(11)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68年1月1日。
(12)见新加坡《文艺季风》第5期,1968年10月。
(13)1978年12月16~17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在吉隆坡联邦大酒店举行“通过文学,发展文化”的研讨会,温任平提交了这篇文章。见温任平:《文学·教育·文化——研讨会工作论文集》,天狼星出版社,1986年,第1页。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马华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新加坡华人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