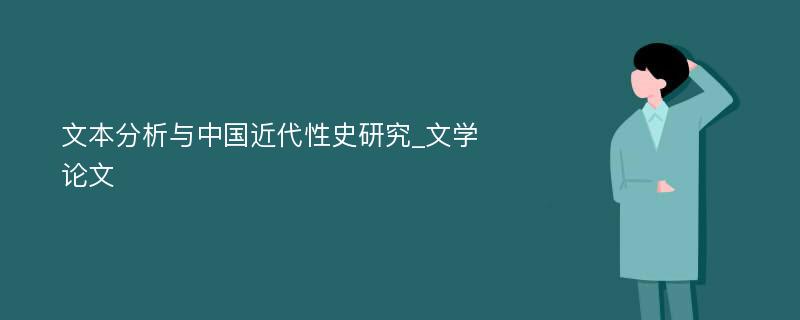
文本分析与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文本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目前在学术界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文本分析
方法,源于西方的结构主义。其中,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学者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1]一文中阐明了文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文本的概念。然而,该名词一经确立,就被赋予了某种独立的品性,从而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在海内外学者看来,文本概念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从文学性的脉络即文学作品演绎而来,故称之为文学文本;其二,源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多样性。因此,有人径直称之为非文学文本。
在美国,思想史研究者较早地关注到文学意义上的文本,因此文学的影响最早出现在思想史著述中[2]。在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者以研读文学作品的方式来“解读”劳工阶级的生活、惯用语等,思考社会与文化。在法国,福柯不仅将回忆录、日记、法院记录、医生报告、建筑蓝图、论文等视为文本,而且将监狱以及相关的刑罚制度、现象客体化为文本[3]。凡此种种,都是对于文本分析和相关研究的丰富和扩大。
人们逐渐意识到文本在生活世界中无所不在,似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文本”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于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而言,究竟哪些文本足资采用以解决研究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呢?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妇女史、性别史研究的游鉴明教授尝言:除了自传、传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之外,小说、日记或者记载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类,都反映了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让人物的撰写更加鲜活、立体[4]。显然,这些都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性别史非常重要的文本。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中,档案、地方志、报刊、碑刻、墓志铭、诗文、对联、挽联、歌词、传说、故事、民谣、戏剧、图画、雕像以及宗教经典和宣传品等也都能够作为文本加以分析、使用。当然,文本绝不仅限于此,甚至连革命政治家的种种言辞,也能被视为一种文本[2]。由此可见,透过文本及其分析,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大有可为。
2 在学者眼中,文本分析既是个方法的思考,
又是个理论性的概念。不管是在文学批评的范畴中还是在社会研究的领域中,莫不如此[3]。围绕文本分析所产生的相关理论,如文本接受、文本解读、文本生产、文本书写等,对于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价值。于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大胆尝试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近代中国性别关系的变动,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研究者们并没有拘泥于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简单分类,而是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展开各自的研究和探讨,碰触新议题。例如罗久蓉教授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再现:从一个女间谍之死看近代中国的性别与国族论述》[5]一文中,灵活运用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等概念,实现了维色尔所期待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相互流通”[6]。在作者看来,从文化传播与市场消费的角度出发,文学文本即是一种形式的史料,当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展开对话时,所反映的正是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之间的相互渗透。该文的第三部分则是从叙事文本角度,探讨郑苹如死后,她的事迹如何经过转述与再现,以及因此形成的叙事如何成为近代中国性别与国族论述的一部分[5]。不管是就文本分析而言还是从性别史研究来说,该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尝试和理论提升。
此外,我们在研究民国时期发生在天津的“双烈女事件”①时也经历了一个从以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架构全篇,到以报刊、碑刻、诗词和戏剧等不同文本为主体展开文本解读的变化过程,从而比较准确地阐释了这些文本的特质和表达方式;也为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剖析“双烈女事件”在天津所引起的反响,审视民国初年普通女性的社会地位及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性别意涵[7],建立起较为合理的论述框架、结构。
其次,透过文本书写和叙述也有助于发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意义和性别内涵。如姜海龙在研究中发觉:文本中郭隆真②的早期生命史与她个人的真实生命史存在着差距。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女革命者一般被赋予两种历史角色:革命者和妇女领袖。郭隆真反缠足、兴女学与抗婚的行为,符合“女革命者”的叙述结构,由于体现了革命者的反抗精神,也符合革命指导下的女权话语,所以才会被凸显为建构其早期生命史的典型事件。这反映了历史主流话语对文本郭隆真生命史的塑造。由此可见,在书写郭隆真的早期生命史(其实是贯穿传记始终)的研究过程中,“女革命者”的身份定位一直支配着文本的生成。他还提醒读者注意:在看到革命话语支配下的郭隆真早期生命史书写的同时,亦应该注意到所谓的“革命话语”并非完全排斥女权话语而专制性的存在,郭隆真早期生命史的革命化书写中,也同样包含着女权话语的叙述结构。
再次,从事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的研究者们还不断探寻适当的文本,深化相关研究。因为新闻报道可以帮助读者返回历史的现场,体察当时的时代氛围。在所有发布女性议题和揭示女性死亡事件的过程中,报章更是扮演了烛幽发覆、推波助澜的角色,其作为舆论空间相对独立的品格也展露无遗[8]。在以报刊媒体为主要研究资料库的学术热潮来临之际,我们长期坚持以天津、北京等地出版的报刊如《大公报》、《益世报》、《庸报》、《醒俗画报》、《人镜画报》、《北洋画报》、《晨报》、《世界日报》,特别是其中的女性专栏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女性问题是如何以“客体”的形式成为公众议题和社会事务;京津地区男权秩序、精英文化与女性主体性追寻的关系问题以及京津都市文化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大公报》副刊《家庭与妇女》的编者和作者都意识到报纸具有塑造都市文化、传播公共观念、供都市人群消费等多重功能,遂利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塑造女性形象,经由读者的阅读消费,把他们的想象投入到实际生活之中。女性则通过撰文谈论新式婚姻、女工失业、重男轻女乃至性别歧视等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传达自己的声音,参与都市文化的构造。尽管她们所选择的问题和表达的个人经验,对问题的看法或多或少经过编者过滤,参加进了丈夫、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但这更进一步说明男女共同参与了女性都市文化的创造。由于一些男性作者取了女性化的笔名,更使得该副刊的作者和读者存在着一定的性别模糊性[9]。
显然,在探讨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仅不必受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等文本类型的限制,而且完全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给予文本以适当的界定和解读,从而使中国近现代性别史得到更丰富的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撰修本身就是一种文本的书写与创造。
3 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解读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解读与文本密不可分,解读若是离开文本,就会无的放矢,但是解读并不是对文本意涵的被动接受,而是融入了解读者的理解和主观想象。至于不同解读者所表达的意涵,则往往会出现和文本的书写者、制作者的意图或十分接近、或相去甚远等情况。为此,罗歇·夏尔提埃提醒研究者注意思索文本本身、传达文本的客体以及了解文本的行为这三个极点之间紧相结合的关系网络[10]。换言之,解读者要关注作者构思的文本、出版商发行的文本以及读者阅读的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更要充分注意文本的书写者、传播者、接受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三个关系型的环节里面,文本的书写者特别值得关注。这不仅在于他们以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千变万化的内容满足读者的需要,更在于书写文本的过程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并不能真正做到尊重事实、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往往夹杂着书写者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要求及所要实现的各种目的、愿望。对此,研究者应保持高度警觉。其实,文本的建构性正是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者们应该仔细处理的问题。
在有关李超③的研究中,研究者或着力于发掘《晨报》等媒体的文本记载,将李超之死呈现出来,并借助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探讨不同文本的制作者在书写中所确立的不同的社会身份[11];或关注这一悲剧经由追悼会、媒体报道逐渐转化成一起公共事件,所引发的有关妇女命运及其解放的热烈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多种文本。而文本制造者的不同性别、身份又导致各自论述中存在某些差异[12]。
例如,胡适希望通过用白话传记的形式书写李超[13],帮助新女性塑造独立的人格,引发她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思考,最终实现对传统社会的批判。众多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参加李超的悼念活动,目的也多在于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首先强调如何运用经济手段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14],体现了校长对学生的关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指出传统社会制度才是导致李超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妇女解放必须要和社会革命相联系[15];新潮学者蒋梦鳞充分肯定李超的个人奋斗精神[16];传统学人梁漱溟大谈要根本解决妇女解放乃至人的解放的问题,必须重视情感的培育,并对陈独秀的观点提出异议[17]。研究者充分注意到,正是由于主体身份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在演讲中表达的诉求也存在某种差异。
在男性教育者之后,多位女性学生也发表了演讲。她们明确提出为追求“男女平等”,必定要人人有这种智识,有这种能力[18];汲取李超的教训,反抗旧家庭的压迫[19]。这同样也是由她们不同的身份、地位决定的。然而,所有文本在呈现李超事件时,都特别强调男权社会下的这位新女性之死的社会影响,而忽略了李超本体。
此外,关注文本书写者的主体身份,还有助于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新发现,产生新认知。
夏晓虹教授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8]一书的第八章“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中,曾系统地阐述了创办新式女子学校的惠兴④,并从满汉矛盾的角度对其自杀殉学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在研究中,则注意发掘有关惠兴自杀殉学事件本身、惠兴死后的各种纪念活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追悼、报刊媒体对该事件及其后续事件的报道、戏剧演员对惠兴之死的表演与募捐等各种文本。诸如惠兴留给学生们的遗书;《申报》、《大公报》、《顺天时报》、《东方杂志》、《惠兴女学报》等报刊媒体的报道、评论,刊登的悼词、挽联等;京剧演员田际云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惠兴女士传》的时候,采取演讲与演戏相结合的形式,使讲者、演员、观众共同参与到对惠兴自杀殉学事件的演绎中来的活动文本[20],特别是书写者的态度,进而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
报纸媒体记者在记录惠兴自杀殉学事件、书写文本的同时,也尽力向社会展出自己的形象,并将自身亦写入了历史。《顺天时报》社白话记员杨志伊,既是惠兴追悼会的参与者,又是文本的书写者,并在书写的过程中刻意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对于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的其他人,均一笔带过,但是却十分巧妙地借记述自己的演讲内容,宣扬追悼会主题,凸显自身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渲染自己的演讲取得很好的效果。
透过文本书写者的自我彰显,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文本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充斥着权力。有学者提出:“吾人采纳的书写风格,始终与吾人采纳的解读风格有关连。”[21]这似乎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吾人采纳的书写风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吾人采纳的解读风格。只有把文本书写者、传播者、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隐含其中的权力因素认识清楚,才能使文本解读更加切实、深入,进而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某些重要意涵。
4 本文所探讨的虽然是文本分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并不赞成将“历史”等同于文本,也不认同“文本之外无历史”的观点。我们始终认为,文本之外还有大量的历史存在,许多历史真实发生过,但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是没有借助某种文本得以呈现。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历史没有发生过,或者武断地断言这样的历史状况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我们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历史首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其真实性首先是表现为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而不是文本[22]。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过程中,我们尽管深知不得不从文本入手,人们似乎也越来越觉得除了文本之外,历史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但是仍必须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灵活运用文本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性别,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范畴,性别史尚属年轻。与美国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前线的状况不同,中国社会性别史的学术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和提升。在学术认知上,我们之中像法国学者那样已经认识到“性别差异,因为具有社会属性,可以使文化习俗的多重性变得有意义”[10]的人士还不够多,因而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丰富多彩的文本还有待搜集、解读,大量有价值的课题亟待深入研讨。
注释:
①1916年,两位来天津谋生的姊妹因反抗社会恶势力的压迫,双双服毒自杀,在天津乃至中国社会引起激烈反响。
②参见《革命者形象下的女权主义者:郭隆真》,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③李超,广西梧州人。父母因膝下无子,承继胞叔的儿子惟琛。民国初年,李超肄业于梧州女子师范学校,之后前往广州求学,始终遭到惟琛的极力阻挠。1918年,在姐夫欧寿松等人的资助下,她进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但惟琛仍设法阻挠,再加上姐夫欧寿松等人经济出现问题,停止资助,李超又患上肺病。1919年8月16日,李超终因贫病交加而病逝,年仅24岁。
④惠兴(1870-1905),女,满族人,镶蓝旗。满洲已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八旗学生金贤之母。19岁夫亡即守节。她提倡女学,在杭州兴办贞文女学校。后因经费不足,学校被迫停课。于1905年12月21日在家中服毒自杀,年仅35岁。
标签: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大公报论文; 李超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