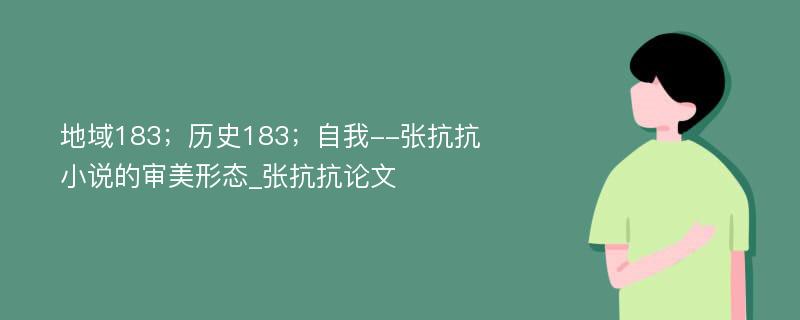
地域#183;历史#183;自我——张抗抗小说审美形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形态论文,自我论文,历史论文,张抗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爱的权利》、《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到《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乃至近期的《情爱画廊》,随着外部世界的不断改变以及作家本身对文学的不断探索,张抗抗的小说创作从题材选择、主题意蕴、作品风格到审美价值取向都一直处在某种变化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作家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她对过去生活几近固执的热切流连,使她的小说创作含纳了丰厚的人生意蕴和地域文化内涵。而且,作为一自始至终关注社会历史以及人类自身命运的女性作家,张抗抗的小说总是带着强烈的理性色彩和一种积极向上的主体张扬,当然其中也不乏困惑和矛盾,这就使得她的小说更富有意味。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张抗抗的小说创作进行简要论述。
审史与自审:张抗抗的两种创作心态
张抗抗的早期作品明显地带着启蒙主义的热情。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启蒙,是关于人性解放、科学民主、对理想和美的追求的启蒙。这种启蒙主义写作特色较集中地体现在她的早期知青题材作品里,如《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塔》、《红罂粟》、《白罂粟》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沉痛的心情描写了十年浩劫带给知识青年的苦难,并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原因。《北极光》通过女主人公陆岑岑接触的三个男性由相同的历史遭遇走向不同的人生路程,看到了历史在青年人心灵上的投影。通过岑岑不屈不挠地追寻“北极光”的执著态度,看到了一代青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闪耀着新的时代精神。这些作品因为及时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的境遇和内心思想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从创作本身来看,张抗抗这一时期的作品仍然没有脱离“伤痕”、“反思”文学的窠臼,和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品一样,她的小说显得情绪性过重,透视与反思的意境不够扩大和深邃。作者的视野往往拘囿于知青生活、知青命运自身演进轨迹的封闭性框架之中,对“文革”中的左倾路线仅作政治性的单项批判,而未能深入人本身进行自审性批判,文学的思考仅仅停留在感慨知青命运的艰难悲苦或伤悼青春的无端荒废,而没能进入具有历史感的层次。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创作时,作家曾说过,《爱的权利》就是在那个积冰消融的痛苦又痛快的时期里,听见新生活的脚步而写的。可见,由于追随“新生活的脚步”而导致创作上的粗疏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综观这一时期的创作,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由于张抗抗以她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识在作品中宣扬着有关新生活的信息,使得她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审史”意识,而不是流于一般的诉苦,因而超越了同期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同时,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理性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舒莫、李欣、荆原、郭立楠、费渊、曾储等。当然作家的“审史”意识又是与那一时代特有的启蒙意识纠结在一起的。这些带着“启蒙者姿态”的作品,在当时严寒尚未褪尽的社会,已显示出青春、热情与报春式的话语。如果说这一阶段张抗抗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凭借她强烈的“审史”意识和现实社会政治感,表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反映出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获得较大的反响,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创作中,张抗抗开始进一步关注小说艺术本身。在写作《隐形伴侣》时她如是反思:“我们强调刻画生动的人物性格,而忽略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重视人物与社会的冲突行动而轻视人自身的内部矛盾。尽管行动和性格为我们提供形象,但形象的立体性是否仅仅由此两维表层结构组成?形象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形象的内核或形而上的东西又是什么?”(注: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与此相联系,张抗抗开始“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注: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她要写一部有关灵魂的小说来“审视自身”,就张抗抗而言,这不仅是作家对早期创作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作家历史观、文学观、审美价值取向实现根本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隐形伴侣》就是这种深刻反思和转变的结晶。它以一群在北大荒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生活为题材,通过女主人公肖潇自我的两面:“显我”和“隐我”的矛盾,表现了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冲突,但是作者所要着意表现的似乎又不仅仅是这些。肖潇因不堪忍受丈夫陈旭的一再说谎而与之分道扬镳,然而当她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又对自己原先信奉的“真诚”发生了怀疑,感到自己也是虚伪的。陈旭的谎言用邹思竹的话来说是“堂堂皇皇的撒谎,比起一些人的虚伪,还是好得多……在强大的社会面前……他只有这一种反抗方式”。而肖潇那些“七分场百日大变样”、“一条河堤,两条路线”的虚假报道,用陈旭的话是“向几千几万个读者不负责任地描绘这种假象,重复这种谎言”。这里,“显我”和“隐我”的冲突、矛盾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张力。虽然我们仍然可以把这部作品归于“知青小说”,但是在主题取向和题材底蕴的发掘上,它显然不同于早期的知青文学。这里的知青生活只是一个外壳,作者所要表现的真正内核是人的自审意识,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透视,而张抗抗也正是借助于此才实现了由早期社会悲剧描述向现在对人的悲剧剖析的深刻转变。从小说的艺术描写上看,《隐形伴侣》也有根本性的突破。作家综合运用幻觉梦境、内心独白、象征隐喻等手法,细致地描摹了人物的情绪、心境、思虑、感觉及欲望等生理因素,完成了对知青题材的突破。张抗抗自己曾说:“文学形式的突破便是文学内在的突破。”(注: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里,文学形式上的因素被张抗抗高度重视,似乎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予以对待,但是我们要说,张抗抗这里所说的“形式”恰恰也是“观念的”。既要“写一部有关灵魂的小说”,就不得不潜返人的内心,因此,造成这些艺术手法上变化的首要因素还在于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是与作家从“审史”向“自审”的转变相配套的。就《隐形伴侣》而言,正是由于作家自觉放弃了传统的那种无所不知的叙事者的视角,采用现实和梦境、隐和显交替进行的手法,才更深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矛盾,突破了情节小说的窠臼。
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史”与“自审”是相统一的,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历史与人具有内在统一性,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如果说从早期知青文学到《隐形伴侣》,张抗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由“审史”向“自审”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多少还带些人为的痕迹。姑且不论早期知青文学是如何依赖于外在历史形貌的描述而忽视了人的灵魂的拷问,即使是比较成功的《隐形伴侣》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与历史的分离,这说明了张抗抗在由面对社会转向面对个体人生的解剖与自审过程中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结合点。
如何寻找这个结合点是很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文学创作终究是一种审美活动,“审史”与“自审”的结合最终还是要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而不是依赖理念去解决。张抗抗后来的小说创作也证明了这一判断。她的《残忍》和《赤彤丹朱》正是在人与人的历史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审美法则。《残忍》虽然是一个中篇,但从某种程度上却达到了写作行为与审美欲念之间的和谐。这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几个人物不同形态的“失踪”:作恶多端的傅永杰的“失踪”几乎为他赢得了“烈士”的称号;而当他的尸体被牛锛掘出后,“烈士”的封号才被撤消,但代表正义的牛锛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很久以后,十三连的人还是恍恍惚惚地觉得,深埋于地下的牛锛,只不过是一次暂时的失踪。他的灵魂已离开了这个地方。说不定哪一天,他还会在他们当年一起出发的那个城市里,再度与他们重逢”。牛锛虽然被处死了,但他却活在人们心里。而马嵘在以后的20年里,淡忘了客观上救了他命的牛锛,正义感在他身上逐渐消失,又由于李泱的失踪使他始终处于某种价值虚空状态。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显得有些飘忽不定,但正是在这种飘忽不定中,我们看到《残忍》似乎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人存在的拷问。作品沿生与死、存在与消亡、正义与罪恶的问题展开对故事的叙述,具有某种触及伟大母题的特征。长篇《赤彤丹朱》的创作稍早于《残忍》,它以一种将叙述与叙述人合为一体的特殊叙述展开对我父母、我祖辈及我自己三代人的历史描写,写出作者对那段历史的个人感受与体验。在写作方式上,作者不是凭记忆复述那段历史,而是从个人当下状况出发,反思革命,反思那个大写的“人”字。母亲和父亲曾怀着浪漫主义激情投入红色革命,但革命胜利后得到的却是无尽的磨难。张抗抗以此为切入点,把对历史的剖析和对人的剖析高度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向历史与人性内部探询的深度。
西子湖与黑土地:张抗抗的地域情缘
如果说“审史”、“自审”是张抗抗从事小说创作的两种基本心态的话,而更能显示张抗抗个案性一面的,还是她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寄寓其中的价值观念与人文理想。张抗抗的小说大多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联系,而其中联系最密切的莫过于以“西子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和以“黑土地”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她的作品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两种地域文化母体,《时间永远不变》、《火的精灵》、《塔》、《永不忏悔》、《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等无不如此。这些小说或回忆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或讲述南方的种种故事。这可能与作家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张抗抗是一位“根”的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她生于杭州,19岁时插队至黑龙江鹤立农场,之后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后又远嫁北京。每一块生存过的土地,都浸透着作家的生存艰辛和思考。而这种“根”的意识又导致她的小说创作常常以回忆的方式去表达对过去生活的理解,她的许多小说——不论是叙述南方或者北方故事——都与她的个人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因而带有一定的纪实性特点。如《隐形伴侣》是写一群在北大荒插队的杭州知青生活,其中女主人公肖潇的形象明显地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而《赤彤丹朱》则干脆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来回顾“我”的家庭史。同时,小说中处处弥散着每一块她生活或感受过的土地上浓郁的南北方文化氛围。杭州西子湖畔那烟柳画桥的浪漫图景、富庶都会的风流气派自不必说,《赤彤丹朱》中外婆家洛舍漾的水乡风情,《情爱画廊》里的江南烟雨,以及《隐形伴侣》中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的山林、荒原、冻土,《沙暴》里一马平川的宝力格牧场上空傲然飞翔的老鹰……这一切都构成了她小说中南北方文化的外部环境。当然,这里所谓的地域文化,并不仅仅是指故事的外部物质环境或者某种叙事载体。在张抗抗眼里,一块地域应该代表着一“类”生活或体现出一“类”人的精神存在。所以,在她的笔下,除了描绘江南的“杏花春雨”、塞北的“骏马秋风”,更多是揭示了这两块土地上人们不同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吴越地区优裕的自然条件不仅孕育了富庶的鱼米之乡,也孕育了以柔慧、淡泊、浪漫为主要特征的“南方”精神。《赤彤丹朱》中“我”外公、外婆处世豁达冲淡,顺应自然,面对人生的一次次大起大落,外婆总是不狂不躁,以平和的心态化解人生的种种痛苦;《情爱画廊》里的水虹、阿霓、阿秀的外秀内慧、外柔内刚;老吴、水虹情爱意识、性爱意识的开放和坦荡,表明了古老的吴越文化中既浪漫又冲淡的艺术精神在当代吴越人的血脉中流淌不息。相比较而言,北方苍凉的自然氛围和粗野的人文环境则砥砺出以热情、粗犷、坚韧为特征的“北方”精神,如《情爱画廊》里舒丽的豪侠仗义,《隐形伴侣》中肖潇生产后给她送这送那、指点她生活的那些热心的农场大娘大嫂小媳妇小姑子们……由此,张抗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可分为两大系列,即以“柔性”为代表的南方人形象和以“刚性”为代表的北方人形象,虽然其中或有变异,但总体上仍未超出以上两种范式,这使得张抗抗的小说人物形象显得明净而单纯。
从特定意义上说,文学创作和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割舍不断的联系。仅就现当代文学史而言,许多优秀作家都有这种难以割舍的“地域情缘”。地域,不仅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特定话语内涵,也成为创作主体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地。比如,沈从文就以他的湘西小说显示了特定的地域文化色彩,写出这块封闭、朴实而又神秘的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环境和他们那“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5页。)莫言笔下描绘出高密东北乡人民粗犷强悍的生命活力。而贾平凹的作品则揭示了一种雄浑、义烈、执著的“商州精神”和“秦汉遗风”。其他诸如老舍的北京市民生活,赵树理山西太行山区的文化风俗,陆文夫的苏州小巷都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就张抗抗而言,如果说她的小说创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即在于不是以唯一的某块特定区域作为自己的写作背景。她早年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不仅丰富了人生阅历,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她的地域观念。既不像一些乡土作家那样执著地表现本土上生存着的人们的生活图景,也没有把自己精神的“根”深深地扎进某块土地。她惯于以一个南方人的眼光去审度北方人的生存方式,又从一个北方人的视角去评判南方人,并一再表述,自己已不是一个南方人。作家把自己的这种心理归结为“流浪”状态,她说“曾有人说没根儿的作家不能叫作家,我便在无根之列。无根得惶惶,只好安慰自己,没准正可独创一个兼容南柔北刚的文化混合型。”(注:张抗抗:《谈谈自己》,载《北方论丛》1991年第5期。)很显然,张抗抗是需要一个“根”的,越是没“根”, 越是表现出“根”的意识之强烈。她一方面因了理性层面的批判意识而表现出对过去生活的反拨与质疑,但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和感想过去,小说《塔》中,那个曾经威风凛凛,带领几百号人马的农场分场长,回城后竟和一群大妈大嫂在一家街道企业的家禽加工厂拔鸭毛;一个满腹经纶的知青病返回城后“一直没有工作,在街道工厂糊纸盒”……这种自我价值的失落使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于是不由得感叹:“松花江——钱塘江。相距多么遥远。一个咒骂过千百遍的地方,离开了却常想念。再也不会有躺在秋天的谷草垛上,望着大雁从头顶的蓝天飞过引起的那种对未来无边无际的遐想……”在散文里,张抗抗又回忆道:“……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二十年的日月就把我这样一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磨砺得柔韧而坚实起来。”(注:张抗抗:《故乡在远方》,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这种文化上的流浪感与创作上的矛盾复杂心态,对张抗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表现地域文化而不能超越地域文化本身,那么必然导致创作的狭隘与封闭。事实上,这也正是许多作家难以突破自身创作局限,抵达人类共同精神境域而成为大家的根由。我们不能说张抗抗已然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身兼南北而最终什么也不是的“根”的困惑,才使得张抗抗能够不拘囿于某种固定的地域眼光,从而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去审视和打量生活,也为前文所述的“审史”与“自审”两种创作心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由此笔者联想到30年代的沈从文,如果他不是身处北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去回忆“边城”,他还能写出“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吗?
虚构与复制:张抗抗的人文关怀
如上所述,张抗抗对地域文化的描写超越了地域文化本身,表现出对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精神的关注。这种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就其早期作品而言,更多地还是在理性层面上以启蒙者的姿态表现出对人类正义感、崇高感、价值感的追求。如《淡淡的晨雾》中梅玫对荆原的钦慕暗示着对真理的探求;《北极光》里岑岑对“北极光”孜孜不倦的追寻衬托出爱情的崇高、纯洁和超乎世俗。此时,张抗抗的作品色调显得单一而纯净,理性沉思的成分远远大于对人的情感和形而下生存状况的关注。而从《隐形伴侣》起张抗抗的关注焦点开始从社会理性精神层面转向人类自身。无论是《隐形伴侣》还是此后的《赤彤丹朱》,它们对人的生存境域的审视和存在价值的追问,都不同程度地跳脱了早期启蒙主义式的写作成规,从而具备了更多的人本主义的意味。《情爱画廊》可以说是一个极致。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北京画家周由和苏州水巷内母女两代人的情爱故事。从故事本身来看,确是写得美仑美奂,张抗抗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至美至爱的伊甸园。水虹和周由,一个具有北方男子高大英俊健美的体魄,而一个除了具有江南女子的柔美外,还有超乎常人的无法描述的深奥含蓄的美。这一对金童玉女,一个是画家,一个是研究艺术史和美学的,他们怀着对爱和美的渴求相遇在人生轨迹的交叉路口,爱得死去活来,爱得登峰造极,共同建造了爱与美的方舟,美得让人向往,爱得使人心动。但是从小说的潜在语义结构来看,《情爱画廊》则触及到这样一个话题,即艺术创作和商业化的问题。可以说,这不是一个文学话题,但又是文学必须面对的话题。因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阅读乃至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无时无刻不被牵引在这种商业主义的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之中。商业化,不仅引发了我们的许多争执和讨论,还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诸种分化(如张承志现象,王朔、《废都》现象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布老虎丛书”本身就是一种商业操作,因为要兼顾经济效益而多少带有点迎合读者的意味,而《情爱画廊》出版至今销售状况之好也是这种操作成功的一个明证。但这并不是说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就是“商业主义”的。恰恰相反,作为一个自始至终关注社会、关注人类自身的女性作家,笔者认为《情爱画廊》是张抗抗在当前状况下借助“情爱”这一古老话题举起的反叛商业主义大旗的一种最为直率的写作和表述。小说开头,周由从北京来到苏州,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女友舒丽为挣大钱对他的背弃,实际上带有逃避商业大潮的意味。他躲进苏州水巷,躲进艺术的桃花源,遇到了水虹母女,而水虹母女又恰恰是艺术美的化身,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和冲动。周由与水虹母女两代人的情爱故事由此展开。虽然张抗抗在此前的创作中对情爱领域也有涉足,但往往偏重于理性的思考。《情爱画廊》有所不同,当“爱情”这一人类最为本真的情感方式被置放在世俗主义、商业化的对立面加以艺术描写时,作者却能尽洒笔墨。惟其如此,《情爱画廊》的“情爱”才写得至柔至美。水虹在周由心目中是美的化身,周由在阿霓眼里又是经典化的异性美的图腾,他们之间的爱的纠葛甚至没有太多情的成分,更多的是彼此间的仰慕和敬崇,这种“情爱”被唯美化了。为此,作者竟不惜让一切毁灭,甚至当水虹如愿以偿地与周由一起远在北京沉浸在“冲浪”激情中时,却让老吴的新婚妻子阿秀和尚在腹中的儿子惨死。我们很难以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真实性与否来评价这部小说。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人的婚姻危机重重,尽管我们至今仍找寻不到一条解决人类性爱的理想途径,但是像周由、水虹式的情爱也还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和虚构。作家企图借助这个美丽的梦境给生活在冰冷的功利世界中的人们以温暖、安慰和柔情,使人们暂时忘却人生的痛苦和缺憾,让未能实现的愿望在作品中获得幻想的满足。但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无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有可能真正拒绝商业主义?小说中,周由如果不选择一个像舒丽这样能干的经纪人,他的画就卖不出高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得不到世人的认可,他因此感到尴尬和迷茫。这种尴尬和迷茫也流露出作者自己在商品经济大潮面前的困惑。
许多关于《情爱画廊》的评论都注意到小说的性爱描写,其中不乏“媚俗”的指责。而笔者认为,张抗抗在性爱场面的描写上,还是颇具分寸,有意识地淡化了一些具体细节。作为一部唯美色彩浓郁的情爱小说,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含蓄地表现了沉醉在爱与美中的主人公那销魂荡魄的微妙感受,致力于将人类这一普遍而又神秘的行为艺术化、审美化,成为一种灵与肉完美交融的典范。这不用说与古代的《金瓶梅》相比,即使与同时代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与贾平凹的《废都》相比,也已是相当谨慎,更具艺术。尤其是“冲浪”这一意象的创造,除了唤起读者欣赏时的美感愉悦外,很难让人产生类似“□□□□□”的效果。它给人的感受似乎更接近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情人》,但又不像《情人》那样肆意铺张和渲染。我们能够接受《情人》中的某些描写,认为它将人的生命激情审美化,认为最后查泰莱夫人裸身在暴雨中狂舞为美的极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接受张抗抗《情爱画廊》中的性爱描写吗?说它过于世俗化,说它是在商潮冲击下的媚俗之作,而它所追求的灵与肉结合,情与性结合,欲与美结合恰恰是一种古典型的爱情观,与“五四”时期对爱与美的追求、对灵肉结合的追求的爱情观并无本质区别。文学评论家鲁枢元在一次张抗抗作品研讨会上引述一位女大学生对《情爱画廊》的看法时说:现在的情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恰恰说明了《情爱画廊》旨在恢复人本的古典精神。对“情人”这一意象的崭新创造,体现了作家自己的一种社会态度、生活态度和人文关怀,也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领域的种种新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同样是在南北方文化氛围的描写中展开的,但是小说中两种文化的铺写显然是不平衡的。尽管她设制了两个地域文化模式,以代表刚性的北方男子和代表柔性的江南女子的结合来表现生命的理想结构,但是,当我们于前半部分沉浸在苏州水巷的烟雨迷雾、小桥流水中,沉浸在苏州人宁静恬适的生活氛围里,预感着水虹到达北京后,那古老的北京城将会带给我们一些老北京的帝都风范,新北京的时代风采:那凝聚着中华民族光荣与耻辱的历史印记;那犷悍的北方地域环境时,出人意料的是水虹到了北京后就和周由在小小的两居室里爱得昏天黑地。而周由和水虹出外郊游时的外部环境,本该是展示北京地域文化的很好契机,作者也毫不惋惜地将之放弃。与浓郁的吴越文化氛围相比,北京文化氛围的描写就相对薄弱。究其根源,笔者认为还是与张抗抗创作意识中的文化价值观念有关。《情爱画廊》是作者试图借助唯美主义情爱故事的营造来抵制世俗主义和商业化的小说。与这种唯美主义情爱相对应,作者寻找到了“苏州水巷”这样颇具典型化特色的意象体和水虹母女这样的江南女子作为故事讲述的地域和人物主体,而不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很难说作者是否有意想借助江南水乡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情”、“性”观念去根治现代都市商业化的顽症,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舒丽离开周由后,治愈周由心灵之痛的确实是江南的烟雨水巷和至善至美的水虹母女,这至少表明了作家的部分文化理想。一贯擅长于描写地域情貌的张抗抗,对江南景致的描写依然是入木三分,而对北京这一现代大都市地域文化表现上的有意忘却,也许正好证明了作家价值取向上的自觉取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抗抗的这部《情爱画廊》并非所谓商业化的媚俗之作,而恰恰体现了张抗抗对世俗文化的一种反叛,体现了她对“爱情”这一话题的人本意义上的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