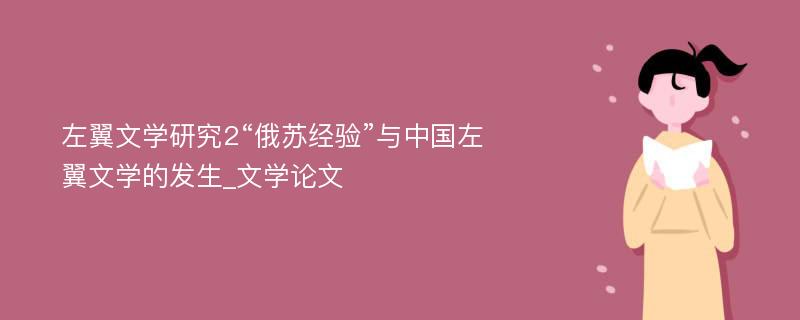
左翼文学研究——2.“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11—0116—07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外来思想和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入,对进步思想文艺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为中国左翼知识界和革命文学形态的形成与确立提供了雄厚的精神资源,并与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的驱动力——“中国体验”——一起,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一、“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俄罗斯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的源头,与“十月革命”一起,激活了中国作家的革命想象,这对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至关重要。当中国革命现代性追求的动力几乎被中国内部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消耗殆尽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不但从外部给中国输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而且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版,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等的认识,糅合了俄罗斯传统思想的精髓,比如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和人民的兄弟情谊等思想,并为人类描绘了一个阶级国家消亡、平等和谐的乌托邦世界。[1]对于中国文艺界而言,在传统文学资源和“五四”文学革命力量日趋衰竭时,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艺为五四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国翻译界对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作家、文艺理论的译介,使中国作家触摸到了俄罗斯文学与思想中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对人的独立性的思考和反奴隶主义的革命传统,这种新的文化体验、文学交流给中国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创作冲动、探索欲望和创新动力,使他们在独创性的模仿中把文学和现实尤其是革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为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或者说,中国左翼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为基石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五四作家走出“科学”、“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启蒙思维模式并从俄罗斯文学中发现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模式开始。因此,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关注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认同。
俄罗斯文学大约是在19世纪末[2](P.1)、20世纪初由中国翻译家通过德、英、美、日等语言转译过来的,如林纾翻译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社会声影录》、《路西恩》、《人鬼关头》、《恨缕情丝》、《现身说法》、《高加索之囚》等作品。不过,这些早期的译品,名为翻译实为改写,其中“谬误太多”,与原文相比可谓面目全非、精神迷失,很难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译著”。[3](P.299)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时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译介俄苏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这种情形才有所改观。早期新文化人,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茅盾、沈泽民、郑振铎等,都与俄苏文学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如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为中国读者热情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新文学作家通过译介、研究俄苏文学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和理论修养,不断促进新文学的发展,也促成了进步青年通过文学认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兴趣和爱好。这种情形正如茅盾所描绘的那样:“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和在青年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成为一种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便是:通过文学来认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4]反过来,这种运动又促进了俄苏文学更多地被译介到中国来。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的不完全统计,1917年至1927年间,我国共出版译著225种,其中俄国作品65种,占了总译作品的30%,[5]是各国中最多的,可见俄苏文学地位之重要。另外,当时出版的报刊、杂志基本上都发表过俄苏文学的译文,如《小说月报》还出版过“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贡献和影响在当时都是非常显著的,实际上,这些译文太多了,简直难以记数。到了30年代,译介俄苏文学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凶猛的潮流,无论翻译者或被翻译者,都是彼时最多的,因此,作家在创作时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换过程中,可以说到处都存有中国作家“俄苏体验”的印痕,而这些作家的俄苏体验显然有力地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生”。中国知识界俄苏体验深入扩展的契机是中国国情和俄国国情的惊人相似。关于这一点,许多思想文化界人士在20年代初就已经注意到了,例如周作人曾就此问题于1920年11月8日在北京师范学校及协和医学校做过一个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演讲的本意就是想说明有许多俄国文学的背景与中国是相似的,提醒中国文学界注意研究俄国文学发达的情形与思想内容。该演讲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先后刊载于1920年11月15日至16日的《晨报副刊》、1920年11月1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和1921年5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转载时,记者“志”云:“此篇本是周作人先生的演讲稿,在《新青年》上登过;我们因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便在这里重出也是有意思的,所以特转录了过来。”[6]这里,记者所谓的“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周作人运用了泰纳、勃兰兑斯等人的新学说、新方法分析了中俄两国文学的差别及其原因,[3](P.279)还在于他由俄国近代文学多主张“为人生”的特点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6]事后看来,周作人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他预见到了中俄之间文学交流的意义、效用;而周作人的演讲一再被转载这一事实,则反映了中国文艺界对俄苏文学求知心切的心态。等到了鲁迅以及更为年轻的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成员这里,俄苏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被广泛接受、借鉴和模仿了。于是,俄苏文学成了可以为中国思想界尤其是青年提供“切实的指示”的文学,其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导师形象越来越明显,而日本则沦为中国知识分子“俄苏体验”的一个重要“介体”。
二、“俄苏体验”的多种可能性
俄苏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深层影响在于中国作家以学生身份的“俄苏体验”上,这种“体验”并非文学译介和阅读意义上的双向文化交流。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文化交流,交流是双方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进行的是单方面的俄苏文学“输入”,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输出”,中国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当然,如是说并不等于否定中国左翼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主体性,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左翼文学发生过程中,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中国作家体验俄罗斯民众的“感受”存在多种可能性,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诸多方面。
首先,20世纪初中国作家对俄苏文学的文化体验主要是由“个体”而不是党派或组织发掘出来的,且这种发掘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紧密相关。[7]事实上,留学苏联的中国人大多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骨干,并非都是未来的左翼文学作家;而在中国左翼文学的生成过程中,留苏作家的数量很少,值得一提的恐怕仅有瞿秋白、蒋光慈等几个人,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左翼文学的基本思想维度及其文学本质、结构,仍然来自于留学日本的中国作家。前者以鲁迅对左翼文学的思想深度为代表,后者以创造社办刊、太阳社创作普罗文学的实绩为代表。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日渐成熟,后期创造社提倡“普罗文学”时张扬而又收敛的矛盾表现,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跨越“五四”新文学传统、摆脱通俗文学和国民党御用文学——“三民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包围而建构左翼文学理念的艰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家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并非如人所想的仅仅是出于偏见;反之,中国文艺界实现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合逻辑性,也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者简单抛弃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之所以被左翼文艺界批判后搁置乃至“抛弃”,根源在于“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已经无法继续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以新文学作家主动做出了个体选择,这种选择过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主体体验后来构成了群体性认识,这种选择和作家们接触俄苏文学有直接关联。比如,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的生命感受、生存际遇和新月派留学英美的作家完全不同,在日本与俄苏文学等亲密接触的文化体验使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充满了同情和认同感,他们比新月派作家更容易关注、体认底层民众的生存遭遇,于是他们纷纷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由此,中国留学生形成了基本对立的两大思想阵营,即留学日俄一派与留学英美一派的思想对抗。这种对抗与文坛的分化,再加上特定的文化、历史语景,就形成了左翼文学与其他文学形态互动互为或对抗论争的复杂关系。
其次,通过阅读上的异域感受和对自身生存境遇的透视,中国左翼文艺界形成了对俄苏革命经验、价值取向的无条件认同,但须注意的是,这种体验主要笼罩在对俄苏革命的认同下。瞿秋白认为:“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8]这种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是中国左翼文艺界的一种追求目标,也是一种“指示”。相比于瞿秋白,鲁迅的表述更为直白,他认为中国青年从俄国文学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善良的灵魂、酸辛、挣扎,明白了两件大事,就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个“大发现”,在那时“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煮食物,照暗夜”。[2](P.2)可以说,俄国文学照亮了中国青年的心灵,结果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的极度兴盛。在郑振铎看来,中国文艺界之所以研究俄国文学,除了一些直接的功利目的之外,原因更在于俄国文学昭示了未来中国的“美丽”前景,他形象地描述说:“俄国文学的研究,半世纪来,在世界各处才开始努力。他们之研究俄国文学,正如新辟一扇向海之窗,由那窗里,可以看出向来没有梦见的美丽的朝晖,蔚蓝的海天,壮阔澎湃的波涛,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大众都拥挤到这个窗口,来看这第一次发现的奇景。美国与日本也都次第的加入这个群众之中,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因素来与外界很隔膜之故,在最近的三四年间才得到这个发现的消息,才很激动的也加入去赞赏这个风光。”[9]瞿秋白则认为俄罗斯文学研究在中国之所以盛极一时是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原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10]就这样,中国左翼作家由对俄罗斯“赤色”革命道路的认同,发展成为对俄苏文学的集体认可,他们找到了一个新导师,一个拥有“马列主义”理论武器的精神导师。
再次,因为俄苏文学的关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相关的聚合、分离或论争等现象,这些现象所承载的“交往”活动更直接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思维方式和主体体验。俄罗斯文学除了展示想象中的革命精神和救国救民方法之外,还展示了平民关怀、人道主义等特异于中国传统的思想,这对中国进步文艺界同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俄罗斯文学可以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异域的生命、艺术感受和新异的文学形式,这对于迫切寻求陌生文化体验的中国文艺界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郑振铎曾经回忆说:“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出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11]“我们那时候对于俄国文学是那么热烈的向往着,崇拜着,而且是具着那么热烈的介绍翻译的热忱啊!”[12]这些话,一方面显示出这些译介者空前的热情,另一方面则暗示了一种关涉俄苏文学的人际关系链条的形成。这种“小团体”的成员不一定有同人关系那么紧密,但对于“交往”而言,却更灵活,不像后者容易受到其他同人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左翼作家的俄苏体验就是在这种“小团体”的对话中形成的,而不是在抽象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生发出来的。另外,这些热情的译介俄苏文学的“小团体”并非盲目行动,他们有着强烈的探索性、精心的选择性和明确的目的性。他们在五四时期非常注重能够反映人道主义、平民关怀、“血与泪”、“为人生”精神的翻译作品,到1928年前后,则更加注重译介充满反抗、抗争精神的作品,并由同情“被压迫与被侮辱者”转向重点宣扬、鼓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在此进程中,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形成了独立民族国家追求前提下“同中之异”的矛盾之结,一度成为真正的对立者,而左翼作家之间则形成了“异中之同”的人际关系,并不断聚合,最终形成了“左联”。同时,在“左联”这样的联合体中,“小团体”仍然存在,并继续作用于交往对象。比如太阳社等在“左联”成立前夕已然解体,可原社同人之间仍然会形成“小团体”的圈子,这个圈子对于鲁迅来说依然是隔膜的,反之亦然。这种小团体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招牌,但对他人思想的态度,有可能完全取决于这些思想的提出者对他们这一“小团体”的态度。
三、苏俄文艺论战,或作为1928年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一种根源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对中国左翼文学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机制。可以说,正是由于对俄苏革命和文学的羡慕、景仰,才使中国作家自觉地将文学与中国乃至世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提出“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口号并竭尽全力进行倡导和创作的。同样,也正是由于中国作家对1923-1925年苏俄文艺论战乃至“拉普”思潮的“体验”不同,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发生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和绵延至30年代的其他文学论争,而就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文化进程来说,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是极其重要的。
在苏俄文艺论战中,一方是曾担任过俄共人民军事委员会的托洛茨基和《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代表,另一方是以“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前身“岗位派”(以《在岗位上》杂志而得名)为代表。双方围绕着无产阶级能否建立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学的特征以及它与“同路人”文学的关系、党的文艺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是:应当把文艺当作“人类创作一个完全特殊的领域去对待”,这并非否定艺术的阶级标准,而是说,在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创作时,必须使阶级的标准适应创作的特殊特点,不能像对待政治那样对待艺术;他对革命的文学“同路人”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认为无产阶级缺乏文化的准备,无产阶级在专政时期将产生一种无阶级的全面的文化,所以“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13]。“岗位派”则宣称:“我们将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坚守明确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岗位。”[14]他们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15]他们用极端的阶级和政治“纯洁性”标准来衡量作家和文艺作品。他们排斥、否定旧的文学遗产,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化、文学都是资产阶级贵族的,在思想上是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对艺术创作问题没有提出自己的马列主义美学观点,因此应该建设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16](P.14)他们排斥、否定革命的“同路人”作家,并向苏共要求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实际上,这次论战是俄罗斯20世纪初无产阶级文化论争的一种延续,其核心仍然是对无产阶级文化本质的争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本质的理解和争论很多,不过,“虽然在争论的不同阶段提出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争论首先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中和在建设新的革命文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参与这个过程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的。”[17]这次论战最后以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政策》的决议而结束,决议涉及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各种不同的作家团体——无产阶级的、农民的以及知识分子出身的所谓“同路人”作家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阐明了苏共在艺术创作领域的作用、政策。苏共主张对“同路人”的态度要“灵活、谨慎”,促进革命文学的各派力量在统一的思想创作立场上联合起来,强调了发展苏维埃共和国文学的重要性。[18](P.63-64)这次论战虽然如此结束了,但作为一种国际文化现象,它却传播开去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比如中国和日本,其中尤以中国发生的思想论争最为激烈。1928年前后中国革命文学论争就是在这种国际文化历史场景中发生的。
1923-1925年的苏俄文艺论战,很自然地引起了留学苏联的蒋光慈的注意。1924年,他归国后不久就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他在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存在可能性的问题,这正是苏俄文艺论战的首要问题。接着,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几乎否定了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作家。1927年他和屈维它(瞿秋白)合作编写《俄罗斯文学》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情况,再次涉及到如何认识无产阶级艺术及其特质的问题。从蒋光慈的情况看来,他由论述无产阶级必然创造自己的文化、由呼吁无产阶级革命到认同无产阶级文化特点,都明显受到了“岗位派”的影响,其观点和做法与苏联岗位派是极为相似的。比如他认为:“不幼稚便不能走到成熟的时期,不鲁莽便不能打破萎靡的恶空气。”他相信要从事革命文学的建设,就要打倒“非革命文学的势力”。[19]他还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创造自己特殊的文化。蒋光慈的这些看法应该是根源于他的俄苏体验,如“莫普”领导班子成员B.普列特尼奥夫就认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由出身于该阶级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等来完成。”[16](P.26)
蒋光慈之外,太阳社其他作家主动仿效“岗位派”的观点和做法也是随处可见。他们与“岗位派”作家一样,对自己“革命作家”的身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蒋光慈甚至直接夸赞太阳社作家是“从革命的浪潮里涌出来的新作家”、“革命的儿子”、“革命的创造者”,他还说:“他们一方面是文艺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时代的创造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能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他们以革命的忧乐为忧乐,革命与他们有连带的关系。”[20]蒋光慈如此夸口并非毫无来由。太阳社是一个比较注重文学创作的社团,其中,钱杏邨比较注重新兴文学的批评,林伯修注重系统地介绍苏、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可以说,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与“岗位派”作家的年轻气盛有着相通之处,在感受中国现实生活时,获得了与“岗位派”成员类似的感受:重内容、轻形式、听不得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批评。1928年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文,批评了革命文学中“标语口号”等错误倾向。是时,太阳社虽然承认普罗文学处于幼稚阶段,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标语口号”倾向。所以钱杏邨引用柯根(Cogan)的理论观点——“关于普罗列搭利亚文学问题的大多数的误解和争论,都是起源于根据着传统的文学史的方法,而想要在形式方面决定它们的价值”——来做自己立论的依据,他强调说:“普罗列搭利亚文艺批评家的态度,是不注重于形式的批评的,这是说对于初期的创作。所谓正确的批评必然的是从作品的力量方面,影响方面,意识方面——再说简明些吧,普罗列搭利亚文艺批评家在初期所注意的,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形式,是要从作品里去观察‘社会意识的特殊的表现形式。’”[21]由此可见,钱杏邨之所以理直气壮地指责茅盾并认为自己有着“正确的批评态度”,正是因为他认同“岗位派”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和做法。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文学与阶级、革命、政治关系的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界必须解决的急务,这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文学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苏俄文艺论战引起了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注意,他们在思考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时,提出了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的要求。李初梨、彭康等人将文艺的宣传功能和阶级性统一起来,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强调文艺宣传煽动的效果越大,无产阶级艺术价值越高。创造社对艺术性质的理解,与苏联“岗位派”的观点是极为一致的,他们吸取了岗位派的优点,同时也带来了岗位派的片面性。他们机械、狭隘地理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把艺术庸俗化地理解为政治的附庸,让艺术像“留声机器”一样被动地替政治“传高调”[22]。这正如郭沫若对青年所说的那样:“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第二,要你无我,第三,要你能够活动。”[23]郭沫若的观点后来受到了李初梨等人的质疑,[24]为此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当留声机是指客观存在规定主观意识,文学家要追求马克思主义、获得唯物辩证法。这种解释固然说得过去,但他的主张显然否定了作家的自我和艺术创作上的个性。当这类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后,对艺术的独立性无疑是一种损害。更糟糕的是,片面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导致了重新划分文学队伍和对作家“全部的批判”、“理论斗争”的要求。成仿吾说:“一般地,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他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特殊地,在文艺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们的社会意识的迷药与赞扬我们的敌人的歌词清查出来,给还他们的作家,打发他们一道去。”[25]这种要求使创造社不可避免地走向对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苛评,比如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认为新文学运动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所以当他们以阶级史观来对“五四”文学革命进行评价时,“五四”新文学就失去了发展的阶级根据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法性,“五四”时代被认为已经“过去”,那么对五四作家进行批判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拉普”文艺思潮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构建
在创造社运用所谓革命文艺理论批判五四作家时,苏俄文艺论战和“拉普”文艺思潮也引起了茅盾、鲁迅等作家的注意。茅盾早在1925年5月《文学周报》上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时,就已经开始关注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范畴、内容、本质。较之蒋光慈近乎狂热的提倡,他冷静地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艺术“缺乏经验”、“供给题材的范围太小”、“观念的褊狭”,有着重内容轻形式的问题,有着内容“浅狭”、“单调”以及把“刺激和鼓动”误认为是艺术的目的的全体等“毛病”。[26]这里,茅盾与“岗位派”的文学观明显不同。1925年8月任国桢编辑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被列为“未名丛刊”第二种出版,该书介绍了论战中各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译者提醒读者注意1923年以来的苏俄文艺论战对艺术的三种不同定义:“烈夫派”(左翼未来派)“反对写实,提倡宣传。否认客观,经验,标定主观,意志。除消内容换上主张,除消形式换上目的。”“纳巴斯徒”(即“岗位派”)强调“艺术有阶级的性质,艺术是宣传某种政略的武器。无所谓内容,不过是观念罢了。”沃隆斯基认为,应该强调写实,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为作家能把高深的学说和认识生活联系起来才是“真艺术家”。[27]鲁迅非常赞赏任国桢选译这本书,并由此对苏俄文艺论战、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烈夫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有了初步的了解。鲁迅还通过译介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了解了一些托洛茨基的文艺观点。综合看来,鲁迅对托洛斯基的“无产阶级文化否定论”未必赞同,但对于托洛茨基对文艺的深刻理解和对同路人的宽容态度,他是持赞同态度的。此外,冯雪峰也在翻译苏俄文艺理论时,注意到了苏俄文艺论战,并根据自己对论战情形的理解,针对后期创造社攻击鲁迅的现象提出:智识阶级担负“无产阶级文学之提倡”和“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确立”的任务是十分正当的,对于革命也是很紧迫的。但革命是只将革命的智识阶级看作“追随者”,革命对于“追随者”“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28]这里冯雪峰所说的“追随者”就是“同路人”。
以是观之,在1925年以后,“拉普”文艺思潮已经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兴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首倡者由此意识到中国要建设的新文学不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而是属于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新兴文化。这确实是一种新体验。可惜的是,由于社会阅历、人生经验、文艺思想、创作实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加之在介入苏俄文艺论战、“拉普”文艺思潮乃至整个苏联文坛状况时每个人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这些都加重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分歧。相对而言,蒋光慈、郭沫若等人是无条件地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这与“岗位派”、“列夫派”的主张相一致,而鲁迅、茅盾等人认为应该在承认文艺自身艺术特性的基础上认可文学阶级性内涵的存在,这与沃隆斯基、托洛斯基的观点相接近。双方的分歧为1928年前后的思想交锋打下了基础。有意味的是,这种思想交锋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构建。
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全力以赴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创建革命文学理论,不过,这种建构是通过对所谓“旧作家”、“旧文学”批判的方式实现的。这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坚信无产阶级在文化上可以轻易地取得胜利的浪漫主义幻想以及“岗位派”对“同路人”的否定态度非常相似。“岗位派”认为“同路人”的文学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对应于此,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对中国“同路人”文学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并将小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视为反革命文学。这虽然存有受日本福本主义影响的因素,但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他们对“岗位派”、“拉普”思潮的认可。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以阶级性为终极性价值衡量标准,将中国作家队伍划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将文艺阶级性绝对化必然导致对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对所谓‘同路人’作家的无端挞伐。”[29](P.119)他们把文坛的大部分作家归入小资产阶级行列,认为小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后来干脆将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就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30]他们将小资产阶级视为仇敌加以批判,并发动了对鲁迅的“理论斗争”,认为鲁迅是反对革命文学的,他的作品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缺少时代精神。一些创造社成员更进一步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反封建的意义,他们将“反帝”视为比“反封建”更为紧迫的任务。这虽然也不错,但他们由此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对立起来,批判、抛弃了前者的传统。就这样,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割裂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将鲁迅、茅盾等作为“同路人”作家大加排斥、批判和嘲笑。此外,他们还把“拉普”的庸俗社会学分析方法和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引入中国。这两种方法强调文艺对政治的依附作用,以作家的世界观取代创作方法,以政治立场来规范、限制作家的艺术感受,这就抹杀了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结果使中国无产阶级文艺阵营陷入了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机械唯物主义的陷阱,具体表现为: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理论和创作方法僵化,在批判“革命浪漫蒂克”等小资产阶级情调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思想极端,把浪漫主义、自我个性等文艺特质性的东西也抛弃了。
“拉普”文艺思潮对中国左翼文艺界各派的影响都非常深远。1928年,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氛围的促动下,根据藏原惟人等的日译本转译了《文艺政策》一书,并从1928年6月开始在《奔流》上连载。该书包括1924年至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文艺政策的两个文件《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以及《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等一些对“拉普”论争的意见,鲁迅由此联想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对于这些情况,创造社、太阳社也有所了解。那么,为什么他们对“左”倾思潮中的错误缺少清醒的认识?我想,除了国际、国内“左”翼思潮的影响之外,他们自身的“俄苏体验”出现了问题。他们很难把“拉普”和“左”翼思潮的错误联系起来,他们对俄苏文学的无条件认同使他们很难改变立场和态度,因此直到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指示,他们才停止了对鲁迅、茅盾的攻击。但这并不等于错误文艺思想的立刻清除,他们很快又陷入了“拉普”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泥坑。直到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发布决定,批判了“拉普”的错误主张、做法和创作方法,开始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加上1933年“左联”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左翼文艺阵营才步入了更加健康的轨道,进而构建了相对成熟的左翼文艺理论。
考察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绝大多数作家的俄苏体验主要来自于俄罗斯革命的政治影响力和从日文等转译而来的俄苏文学,并非来自于留学苏联的亲身体验。当然,就算是亲身体验也不一定全面、正确。中国作家凭着政治热情、理想和信念,将对俄苏文学的所有认知活动都纳入到俄罗斯人民的生存发展和文化体系中,而这种完美的体系只能是一种虚构,其问题很多。中国作家完全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去体验俄罗斯人民及其知识分子的感受,这意味着他们的理解与俄罗斯人民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文化体验之间存在难以测知的差距。那么,“俄苏体验”对于中国文艺界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推动和促进中国左翼文学的生成;反之,它也会误导中国作家的理性判断,例如一些左翼作家在30年代中苏之间的中东铁路和边界领土问题上就做出了完全支持苏联的错误决断,这种教训无疑是极为深刻的。
标签:文学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中国作家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作家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