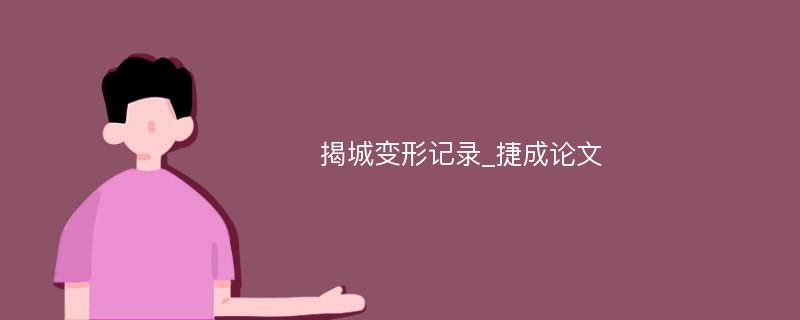
捷成变形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形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变化莫测的大海随时都可能遭遇风险。热衷航海的捷成集团董事总经理海宁(Helmuth Hennig)曾有过一次令其终生难忘的经历。 在一次比赛中,他与朋友驾驶帆船从香港开往越南,全程航行了6天。在航行期间,帆船主桅杆不幸折断,没有帆的船只有依赖马达航行。两天后,马达出现故障,油料也开始短缺,船员们只好在海上漫无目的的漂泊。 非常幸运的是一只台湾渔船恰好经过,渔民供给了一些燃油。但这些燃油并不对路,反而把船的引擎烧坏了。直至其他船只路过的时候,海宁才重新获得了一些柴油,清洗维修完马达之后,船只才得以重新起航,最终所有人成功到达目的地。虽然比预期时间长了一些,但所幸大家都安全无恙。 与航海类似,海宁所打理的生意亦曾险象环生。2003年的非典即是如此。“对捷成来讲,公司业务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产品送到销售地点,要跟人去接触,但是在非典时期都没有人愿意去上街或者跟人打交道。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突然之间就变得陌生,而公司似乎无能为力。幸好它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 好在海宁已有所准备——当公司生意出现风险时,除了会出售部分现有业务之外,捷成所拥有的现金储备通常足以支持公司一年的顺利运营。这正是其能延续百年至今的原因之一。 捷成洋行奉行的原则及主要成功因素,亦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这一制胜法则来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思想家孟子的启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895年,来自丹麦奥本罗的雅各布·捷成(Jacob Jebsen)与他的表哥海因里希·谢逊(Heinrich Jessen)在香港创建捷成洋行。当时从欧洲来华的路途险象环生,耗时长达六个月之久。在中国,两人遭遇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冲击。然而,一种纽带很快便得以建立并巩固,并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经受了考验。 如今,当你走进香港铜锣湾嘉兰中心31层的捷成集团办公室,你会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这里墙壁上挂着殖民时代的货轮帆船油画、收藏多年的19世纪中国及东亚地形图,走廊两边的红木中式家具上摆放着官窑寿桃花瓶瓷器,办公室里亦堆放着书法字画等古玩。走廊尽头则是一块边角锈迹斑驳的方形厚重铜牌,上书“捷成洋行”四个大字,它的另一边则悬挂着深蓝色的三鱼商标。 铜牌最初来自捷成所拥有的轮船上,而三鱼商标——最中间那条鲭鱼与上下两条鲭鱼方向相反——这是奥本罗(Aabenraa)的家族纹章,其独特创意源于勇敢善战的鲭鱼无时无刻的游动,亦象征着捷成的企业精神。 嘉兰中心不远处便是香港昔日繁忙的海港,那里曾是100多年前捷成、谢逊兄弟来往中国停泊船只的地方。在来华之前,雅各布·捷成的父亲曾在香港指挥货运船只多年,两人在繁忙的香港港口嗅到商机,并设立贸易公司,这即是捷成集团的雏形。在捷成总部嘉兰中心的会议室里至今仍悬挂着这两位创始人的画像。 令人诧异的是,在全球商业和互联网贸易如此发达的今天,洋行——这门古老的生意依然兴隆。捷成集团董事总经理海宁以一种在外人看来偏执且墨守成规的方式从事着这门古老的生意。这家公司从不投机,从不碰房地产和金融,甚至极少对所代理的品牌发起收购或投资。扎根于经济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捷成却以另一种独有的方式扩张。 在捷成办公室里,你甚至不太容易找到视频电话等现代高科技办公设备,但你能感受到的是整个公司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家族传承的敬意。在不经意间,抬头看到窗外的摩天大楼及熙熙攘攘的海港,你会好奇是怎样一种古老的精神和规则,令其在险象环生的商业丛林存活了一百多年,并迸发出新的活力? 在中国大陆,捷成并非明星公司,也鲜有消费者会注意到它。它更像隐藏在明星产品背后的巨人——借助市场的力量,以无形之手将其打造出来,继而令其家喻户晓。 翻开捷成当下的代理名录,超过200个明星品牌令人目不暇接。汉莎航空、西门子、沃尔沃、乐高、宾得、卡西欧等均与之颇有渊源,奔驰、保时捷、奥迪、沃尔沃、现代、雷诺等汽车品牌无一例外曾由捷成负责代理并开拓香港或内地市场。在清末,捷成从事靛蓝染料贸易,在曼彻斯特采购面纱,并建立一条航线定期往返于香港、海口和北海三地,它的生意疆界因时而变,仅1951年一年捷成洋行就售出了75万台血压仪。 汽车或许是捷成历史上最成功的部门。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捷成便已是奔驰的代理商。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捷成又获得德国大众的代理权。1954年,捷成洋行的一名高管成功争取到保时捷中国独家代理合同,之后从1955年便正式开始与保时捷进行长达近六十年的合作。这项业务在20世纪八十年代达到巅峰,奥迪、沃尔沃、现代、雷诺等均由其代理并开拓内地或香港市场。 但这项生意并不稳固,正如捷成家族第二代管理团队成员之一的Hans Schlaikier所言:“代理的矛盾之处在于,事情做得不好就会被委托人炒鱿鱼;但如果做得很好,最后结果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这便是代理业的本质所在。 直营由此开始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建立了自己的业务部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大量厂商都开始收回代理权,并自己铺设销售渠道。20世纪九十年代,捷成在汽车领域仅重点代理保时捷一家品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捷成率领保时捷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保时捷因此成为世界三大顶级跑车品牌最早进入内地的一家。它在北京建立内地首家保时捷销售中心,地点是毗邻天安门广场与王府井的长安俱乐部。之后捷成又在上海、杭州设立新的保时捷中心。截至目前,捷成已在大中华区设有8个保时捷中心,分别是北京、上海(浦西与闽行)、广州、深圳、杭州、香港、澳门。 在当年,这是一门风险极高的生意。2001年,保时捷在中国内地全年仅售出27辆汽车,2004年,这一数字增至386辆,但到了2006年它迅速增至2305辆。2011年,保时捷已累计售出24340台,2013年飙升至3.6万辆。 但即使如此,2008年的某一天,时任捷成集团董事总经理的海宁依然接到了保时捷销售总监的电话。在此之前,两人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电话里,对方说:“我觉得你们做得非常棒,长期以来对保时捷都有很好的支持。但是中国市场非常大,仅凭一家很难实现长远的愿景。” 听闻至此,海宁深知痛苦的一天终于到来——保时捷将收回捷成大中华区独家总代理权。“这给捷成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对于捷成来说,这是困难的一年,但是我们也理解,毕竟中国是如此庞大复杂的市场。对于保时捷来说,很难只让一家企业来做他们的代理,并把一切做好。这里面涉及诸多资金投入,还有运作速度。” 作为回报,保时捷仍与捷成继续以下两方面的合作:一是令捷成与保时捷成为进口合作关系,相当于合资企业共同进口:二是捷成继续代理保时捷的产品,允许捷成在中国一些大的城市不断的开设保时捷中心。 时至今日,捷成仍是保时捷在华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经销商,同时也是保时捷(中国)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捷成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2011年捷成销售保时捷6662台,占到内地销量的三分之一。到了2012年,捷成共交付保时捷新车7273辆,创造了单个保时捷经销商在华年度销量的历史新纪录。随着新经销商的加入和新店开业,捷成的销售占比虽逐渐下滑,但营收数字却仍不断攀升。 除了保时捷,捷成还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西门子中国区总代理,巴斯夫(首个代理品牌,从1897年开始)、博世、禄来、宾得、卡西欧等品牌都曾借助捷成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在合作多年后,与保时捷相似,这些品牌纷纷选择收回代理,自建渠道进行分销。 这种痛苦的分离曾在捷成内部引起激烈的讨论。1984年,时任捷成集团主席的迈克·捷成(Michael Jebsen)曾对此类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无论规模多大,捷成洋行都要坚持现有的业务,因为总能找到需要捷成帮助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 但毫无疑问,墨守成规的商业模式总有局限性,Michael Jebsen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此,他感叹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我们看似好事,但对洋行的各项代理业务却意味着‘借来的时间’。” 经历类似阵痛的不仅仅是捷成。其百年兴衰历史过程可谓整个洋行业的缩影。甲午战争结束后,外资洋行盛行,一度膨胀至全国近3000家,但能延续至今的却寥寥可数。捷成不仅在时代的变革中存活下来,而且还找到了新出路。其转型路径在于,在恪守洋行本行业务的基础上,捷成能够从一家普通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为专业化的市场营销和经销机构,这种转变备受业界瞩目。 作为集团的董事总经理,海宁是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的关键人物。他认为洋行应该从“中间人”的角色变为“增值者”。这个自1983年便加入捷成洋行货运部,2000年开始担任捷成集团董事总经理的丹麦人为其注入了新的力量。 1983年,当西门子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业务部门时,海宁便意识到类似的情况会时有发生,近一个世纪以贸易公司身份踏上历史舞台的捷成洋行应该及时转变。正如海宁所说:“旧品牌会让位于新品牌,而不是沉浸在历史中,标榜自己是一个‘曾经代理过西门子’的公司。” 于是,除了传统的销售及市场营销业务外,捷成对围绕营销业务的其它服务进行细分,并分割出其它的服务领域。例如为企业提供货品仓储、空运、海运、工程安装及售后服务,甚至是IT基础设施建设等。如此一来,捷成不仅仅是分销商,同时还提供专业的策略投资服务。 2004年,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成为捷成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平台。2006年,捷成洋行与天津环雅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合资成立捷成(中国)物流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港保税物流园区,仓库建筑面积达三万平米,是目前中国北方最大的保税仓库之一。 它甚至与上游制造商一起寻找商机,联合生产以实现产品的本地化。2007年,德国MITEC汽车系统股份公司与捷成成立了美特捷成汽车系统(大连)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主要生产专为中国国内市场设计的发动机平衡轴及提供齿轮组解决方案。 在明确企业发展战略后,2009年,海宁又着手进行新一轮改革,即成立四大策略性业务单位:消费品、工业、饮料以及奢侈品,令各部门独立预算,自负盈亏。“四大业务单位各自会有特定的收益增长目标,针对这个目标,它们会根据自己行业发展的趋势去选择怎么做。集团不会布置任务要求今年完成若干个项目,或者增加几个品牌。不同部门针对财务和经济上的目标都会有自己的商业计划,并按照自己部门拟定的商业计划执行。”捷成集团企业发展总经理蔡洁雯对记者说。 如何管理不同业务板块?关键在于数据管理。海宁表示:“公司每个产品都有不同的业务方向,总的来说所有的数据会有一个内部参照点,即关键值,高于这个关键值则表示运营的很好。如保时捷、蓝妹啤酒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个关键点在30%。现在有200多种产品关键值介于13%至30%之间,其他的都高于30%这个关键点。” 一旦某些业务的发展速度低于30%,捷成也不会轻易砍掉。“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司必须考虑平衡产品系列。有一些产品的利润率比较高,但未必持续保持下去。有些产品的利润空间不大,但很稳健,所以要考虑产品在整个成长区间所处的不同阶段。只有如此,这么多的产品才能够互相平衡地健康发展。”海宁说。 而对于亏损的产品线,捷成会慎重考虑多方面才会做出剥离的决定。“捷成真的像一条大船,因为如果你在海上轻易有突破性的行动,这条船很容易就翻了,捷成的文化一直都属于稳健型。”蒋洁雯说。 为了明确增长目标,从2005年开始,捷成还实施了“五年计划”,以实现2005年至2015年收入每五年增长翻番的目标。经历一番改革后,捷成集团2010年总收入已超过8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高达90亿港元。到了2013年,集团营业额达到115亿元人民币,约合145亿港元。 营收得以快速突破的关键在于捷成善于从大中华区庞大的中产阶层中掘金。消费品成为其代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宾得、卡西欧、戴森、博朗、Ya-Man等品牌组成了捷成的消费品业务,获益于此,捷成的网络很快得以覆盖大中华区超过860家电器商店及百货公司。 主管消费品的捷成集团董事李家祥将其消费品业务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卡西欧之类的电子消费品:二是保健及美容产品:三是戴森为主体的优质家品,包括空气净化器、抽湿机等。 每天清晨李家祥一到办公室即会打开电脑,查看他所关注的五个经营数据,这五个数据分别是捷成集团所有业务的进度、消费品业务的发展、香港与内地总体销售增长、产品市场销售数据以及员工流动情况。 这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也是消费品业务持续做大的秘密。捷成消费品业务起步之初,主要以摄影设备及产品为主。日本宾得相机就是捷成的主推产品之一,此外,还有德国品牌禄来。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摄影产品的数码化,捷成开始代理了卡西欧数码相机等产品。即使智能手机对低端数码相机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时至今日,卡西欧在香港市场占有率仍有28%,远超佳能等其他品牌,这与捷成的缜密操盘密不可分。 事实上,较之于其他品牌的广告预算,卡西欧的广告预算并不多。但捷成通过社交平台寻找人气博主,在网络上传达卡西欧的产品概念,并通过博主分享使用心得,如此拉动用户口碑,最终打开市场。之后,捷成还与整个供应链和渠道商配合,采用透明价格,拒绝价格战,与分销商配合协作,依据市场销售指数进行推广。如此最终确保每个合作方都能获利。 原本饮料业务也归属于捷成消费品部门,但随着其迅速发展与壮大,它最终独立成为捷成的一个单独部门。它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906年。其业务包括声誉卓著的蓝妹啤酒,也包括葡萄酒。 2005年,加拿大人郭路华(Michael Glover)加入捷成,成为该部门主管。彼时,其葡萄酒部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独立葡萄酒进口商与经销商,同时也是中国第三大普通酒进口商。 蓝妹啤酒的业绩也不俗。数十年来,蓝妹一直在德国酿造,但20世纪八十年代末汇率突然转向,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飙升。1988年,捷成将蓝妹酿造业务搬至位于韩国首尔的Doosan集团东方酿酒厂——如此带来供应商的快速响应,在两周内,韩国酿造的蓝妹啤酒就能抵达香港的货架。除此之外,由于酿造、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其利润也得以暴增。时至今日,在香港,它的销量一直排名第一。 对于捷成而言,如何选择合适的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这至关重要。对此,海宁有一套自我的挑选原则。“这中间有若干因素和机制用来衡量产品是否合适。”海宁说。首先考虑的是合作伙伴是否愿意对中国市场进行长期投入;第二,要考虑合作产品能够带来一些额外的价值,例如是否极度令人渴望拥有,或者大幅提升生活的质量;第三,合作方的理念、价值观是否与捷成相互一致。 来自英国的戴森电器便是海宁心目中的理想产品。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真空吸尘器的发明者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2009年,戴森推出了无叶风扇产品,这款产品亦是捷成负责在华代理销售业务。 这是一次偶然间的生意。2005年,戴森的国际销售主管前来捷成消费品部介绍戴森的产品。当时,其真空吸尘器定价高达三四千元一台,属于高端产品,即使在香港,这一价格也令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市场一度滞销,因为普通的日本吸尘器在香港售价仅为几百元到一千块。 但李家祥在第一次见到戴森的产品之后,便认为这是一项好生意——戴森的主要卖点除了原创设计之外,它的微型发动机虽小但功率很大,非常实用,而且之前它在英美日等市场的口碑甚佳。 很快,李家祥便见到了戴森的高层,之后快速敲定代理合作关系。从2008年开始,戴森在捷成的协助下进入香港市场。6年之后,戴森已在整个香港吸尘器市场占据高达25%的市场份额,而香港的成功也推动了捷成与戴森在内地的合作。 2012年,戴森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戴森对捷成提出的要求是一年之内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铺设200个销售网点,这对捷成而言挑战颇大。 “一年当中开200个销售点,意味着几乎一天半就要开一个新店。这涉及到方方面面,要去找合适的地点,协商租金、店面、人员、产品,要在一定时间内展开销售活动,其间涉及到大量资金。这是捷成目前铺设最快的一个案例,但我们最终还是做到了。”海宁说。捷成成熟产品的典型投资周期通常不会超过十年,而李家祥预计戴森在内地有望“三年能打平,五年有回报”。 除了开店速度,李家祥认为认知度是未来提振戴森销售业绩的最大挑战。因为每天接触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人,他认为管理企业最重要的是将企业的价值理念传递到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起到总领作用。戴森刚进入中国,未必消费者都能明白诸如风扇没有叶片怎么产生风诸如此类的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大量的销售人员来。”李家翔说。 海宁的父亲Hans Hennig曾在20世纪四十年代加入捷成,是捷成洋行航运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主管捷成船运业务长达30年,亦曾担任M.Jebsen航运公司董事,直至八十年代才退休,而他的祖父亦是船员,也曾为捷成效力。 年轻的时候,海宁为一家德国船运公司在澳大利亚工作,因为机缘巧合来到香港探望朋友,当时一位捷成前董事就邀请他加入捷成集团。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1983年,海宁最终加入捷成。1987年到1988年间,他从具体的贸易业务岗位转向了管理岗位。2000年,他开始担任集团董事总经理,并与现任捷成集团主席捷成汉先生(Hans Michael Jebsen)成为搭档。对于如此迅速的获得升迁,海宁认为是“贵人相助”。而他所认为的贵人,正是他刚进捷成时,坐在捷成董事总经理位置上的那位老先生。“他有非常强的洞察力。他跟捷成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要交班的时候了,老的一代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让企业传承下去,让新的一代来接过这个接力棒。”海宁说。 于是,当时的捷成家族负责人便问老先生:你认为新一代接班人是谁呢?老先生便推荐了海宁。“尽管当时捷成的老板说没有位置留给我坐,但那位老先生有慷慨大度之气,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分成两半,留一半给我,我认为他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贵人。”海宁感叹道。 海宁擅长分析和管理数据,上任董事总经理不久后,他便开展了公司史上第一次全范围的大工程,即将捷成洋行的IT和通信业务整合在同一处理平台。 “当时的汇报系统还不是特别完善,大概是1个月一次,也需要去理解大量的数据。后来我兼任的职责不得不越来越多”。在2000年后,捷成大量投入到ERP系统,将其进行落实并运行,并对产生的数据进行理解和分析。2001年,海宁最终在集团内部全面完成了ERP系统的整体实施。 “数字可以给我们带来直观的印象,当然也需要把很多因素放进去理解这些数据,比如达到这个销售额是什么因素,是什么情况导致的。我很喜欢数据,但对数字的敏感,是在后天工作中培养起来的。”海宁向记者表示。 每年当捷成集团董事会或季度会议召开时,捷成汉先生就会前往香港办公室。集团很多会议和大的决策都在香港进行。在会议上,一些普通经理会站在桌子尽头向其汇报业务。“每年捷成汉先生会过来大概10次左右,家族成员和公司管理层一起来共同运作这个家族企业,虽然在细节方面有一些不同,但总体的宏观愿景、发展方向、大的策略方面都是有共识的。”海宁说。 海宁和捷成汉堪称“最佳拍档”,海宁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两人的性格比较互补。“我是一个非常在乎数据事实、理性思考的人,而捷成汉先生则比较感性。我们讨论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正式场合,而是在私下里讨论。捷成汉先生会给出一些意见,但更多的还是由我做出业务方面的决策。” 他深知在变幻莫测的中国市场,保证捷成顺利航行的关键在于风险控制。 捷成不会把所有的资源和资金仅投入到一个领域,因为这样一旦有大的波动,损失就难以估量。说到底,它很在意整个集团业务的表现,保证公司的资产损益表质量,以稳健的方式来开展业务。 在生活中,海宁是一位帆船运动爱好者,也曾当过真正的船长。对于海宁来说,他认为在海上远航,有时候跟管理一家公司非常像。 “比赛就要考虑到什么是目标?当前的竞争环境如何?也要把取胜的心态落实到现实的准备上来,要选择合适的团队来配合。帆船每次远航出行会有10个人左右,船上的每位成员要各司其职,这一切跟打理一家公司都极为相似。”海宁说。 海宁的办公室就摆放着很多船的模型。他对航运的历史如数家珍,这是因为早年的捷成集团以船运为初始业务。一百多年前,整个世界打通欧洲到亚洲商贸交流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正是依靠在船运方面积累的早期贸易经历和经验,捷成才开始了日后的对外贸易。直到1978年,捷成仍拥有自己的船队和船运业务。20世纪70年代,船运业务进入集装箱时代。而自1961年起,中国各港口的所有船只均必须由设在北京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负责,如此一来,捷成当时设在上海、天津的办事处便毫无用武之地。它决心继续坚持,直到1962年才作为最后一个离开内地的外国企业关闭了它的办事处。终于到1978年,捷成洋行重返中国大陆时,公司被迫停掉船运业务。 但喜爱水手与远航的传统仍在新一代管理层里得以继承。如今在捷成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船舶模型或与之相关的油画,这便成为捷成文化中独特的地方。 1895年捷成洋行进入香港,自此开始了它在中国长达百年的经营历史,它堪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者。尽管在诸如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或文革动乱等时期,它被迫退出中国内地,但内地再度开放时,捷成又以首批外贸企业身份重返大陆。 1992年,改革开放在毗邻香港的广东试点,得风气之先的捷成集团主席捷成汉看到新的市场机会已经来临,他将嘉兰中心整层租下,喜爱传统木工的他亲自设计了每间办公室。 自此,捷成的办公室风格一直未变,捷成家族的传统也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保留。对于捷成汉而言,理解过去、尊重传统是治理企业的精髓和要义。 作为一个能够生存百年的家族企业,海宁从不急于扩张,谨慎、稳健的前进是捷成家族的理念。“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做到的,我们需要明白自己能力的范围。公司一直以来的风格都是小步前进,而不会大步前进。在一百多年历史当中,公司从来没有因为有大量的资金就去收购其他的企业。我们在乎的是能够控制企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让命运来左右我们企业的发展。” 李家祥认为,捷成洋行一直延续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行业和核心价值的坚持;另一个则是与整个时代发展相契合。 “人们常常说捷成是很稳健的一家百年老店,其实一点都不老,因为我们与时并进,这是最重要的。市场怎么说,客户怎么需要,我们就以此调整战略。我十年前加入捷成,那时的捷成和现在完全不同,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一直没变。”李家祥说。 海宁认为,捷成的成功在于它从不会依赖一个人,也不会把一个强人放在企业当中由他完全去掌控。“我们会把企业看成是大家的,一个业务有众多的参与者,而且会把业务分散开,不会建立在依赖一个人的基础之上,而更依赖制度化管理和团队合作。”海宁说。 但眼下,手机和互联网正逐渐侵蚀洋行这个古老的行业。越来越多的厂商选择直接和消费者接触,中间商的生存空间慢慢消失。 但主管饮料业务单位的郭路华仍坚信拥有品牌和品控能力的贸易商始终都有发展空间。“例如对葡萄酒而言,中间贸易商是把控品质很重要的一环。”贸易商要保证装箱葡萄酒无论是来自法国或是智利,送到消费者面前的最终品质是一样的。中间诸多环节如温湿度控制、运送时间、仓储等都需要专业能力,而很多葡萄酒生产厂商并没有这些能力。贸易商还能向分销商提供推广和策略等诸方面支持,这是单一酒庄或厂家所做不到的。这便是捷成作为代理商的优势所在。 而对于消费品而言,李家祥认为一些特别的产品,仍需要经由销售向客户解释产品如何运作。例如生活消费类的高端产品,往往需要销售人员去售卖、解释。另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会考虑购买所带来的满足感,所以洋行的发展空间仍有拓展的可能。“公司会把互联网看成新渠道,抑或是一种新的销售方式,采取积极的方式去应对。”李家祥对记者说。标签:捷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