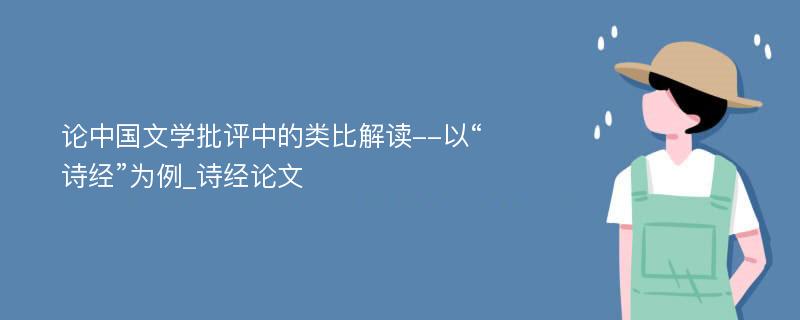
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类比性释义——以《诗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释义论文,诗经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107-07
一
先从孔颖达发现《毛诗》①释义的一个现象谈起。
孔颖达疏解《诗经》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章句分析,为此,他将“小序”、《毛传》、《郑笺》与诗歌作品的本文逐一作仔细对照,结果发现上述解释存在“于经无所当”现象。②这意思是说,“小序”、《毛传》、《郑笺》作者说明《诗经》的某些含义,核之于作品的文本,并无相当的文字可以作为印证其解释的根据。将这类情况做一个统计,它们在“小序”中出现最多,在《毛传》和《郑笺》中也有个别的例子。《毛诗》被定于一尊以后,人们对其解释义与《诗经》原义的忠实关系少有异议,在那个时代,“于经无所当”的提出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对于《毛诗》这种“于经无所当”的解释,一部分被孔颖达认为是由于各种具体原因造成的。一种情况是,有的作品因为诗人可能采取了省略、替代、兼义的手法,“小序”作者在解释作品时,将诗人可能省略、替代部分的意思,以及一词所兼的其他含义重新恢复。另一种情况是,解释者从他自己具备的古史知识出发去理解作品,或者是将多首诗歌联系起来进行互相释义,得出对作品的认识。孔颖达在这些方面为“小序”作了辩解,尽管他的辩解存在一些疑问,但毕竟还是说出了一番理由。而对于出现在“小序”中更多的“于经无所当”的例子,孔颖达仅限于指出事实,至于何以致其然的具体原因就不再涉及,也不再为之作辩护。比如:《周南·桃夭》咏唱“之子于归”(姑娘出嫁)的欣喜和幸福,“小序”将这牵扯到“国无鳏民”上面去,而从作品本身却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意思。③类似这样的“于经无所当”例子在《毛诗》中出现最多。孔颖达说:
古人说《诗》者,因其节文,比义起象,理颇溢于经意,不必全与本同,但检其大旨,不为乖异,故《传》采而用焉。④
这是他对《毛传》采用《国语·周语》解释《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话所作的评论,认为说《诗经》者有关的解释“颇溢于经意”,与作品的原意存在不少差异,然而,这一解释的“大旨”却与原作“不为乖异”,所以不妨其可以成立。宽容和接纳在解释活动中产生的某些“溢”义,这大致也是他对“小序”、《毛传》、《郑笺》“于经无所当”的解释现象所抱的态度。
孔颖达揭示《毛诗》释义存在“于经无所当”的现象,实际上触及了《诗经》解释史上诠释者自由理解和自由解释的问题,而显然,他认为只要对作品“大旨”的说明没有与原作出现“乖异”,那么这样的自由就应当是允许的。大概这也是唐以前《毛诗》一派在如何理解和解释《诗经》问题上所持的比较普遍的看法。这说明在《毛诗》释义系统内部确实存在自由释义的倾向,并不是有人将这一结论强加给了他们。孔颖达“于经无所当”之说证实了这一点,它的主要意义在此。
二
解释,最初是为了消除阅读上的障碍,使作品易于明白和被接受。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解释者并不能够保证像镜子映物一样将作品的含义按其原样、不多不少地传递出来,所以,遗漏或增添在所难免。更有甚者,人们实际的解释目的远比上述单纯的企图复杂得多,解释经常表现为对被解释文本的利用,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解释者强加于文本而使其意义变形的现象。被解释的文本与经过解释的文本,两者的含义往往很难叠合。事实上,对于两者的一般差异人们在通常情况下是予以默认的,因为这并不会影响对作品大致的阅读。而且,人们对于阅读的精确性要求一般并不高,所以可能他们原来就忽略了这些差异的存在。比如《诗经·齐风·载驱》,“小序”解释这首诗写“(齐襄公)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其妹文姜干乱伦丑事,诗人对他进行讽刺。“盛其车服”的意思,孔颖达解释说,是形容齐襄公“盛饰其所乘之车与所衣之服”。可是,他指出《载驱》只写了“车马之饰”,并没有写“盛服之事”。说明“盛其服”是“小序”作者在解说这篇诗歌时添加进去的内容。孔颖达说:“既美其车,明亦美其服,故协句言之。”⑤认为“小序”增加“美其服”的内容还是符合诗人创作此诗的初衷,因而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正是由于增添了这一笔,使《载驱》“小序”形容的齐襄公比《载驱》原诗描写的齐襄公更加突出了外表修饰,而外表修饰得越美,越显出他心灵丑秽,从而形成两者更大的反差,收到更强的讽刺效果。所以《载驱》“小序”的作者采取增添内容的方式解释作品,难说不存在某种解释企图上的故意。对于这些差别,普通的读者一般不会予以特别留意,常常视而不见,即使经慧眼道出,他们通常也会采取宽容的态度,予以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一类释义的差异没有使作品原来的意思发生太明显变形,以至产生认知的困难。似乎解释者与其他读者对这个问题在一定的“度”上自然地达成了默契。
然而,《诗经》经过解释环节使意义发生明显变形、从而导致读者难以认知的情况又比比皆是,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读者不是放弃自己阅读作品时所产生的直接感受,“强迫”自己去接受经学家的解释,那么就很难与这些解释者所得出的高深然而却难以发生自然共鸣的结论保持一致。
《诗经·召南·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诗人以草虫、阜螽这些自然界中的昆虫起兴,写相爱的男女渴望相见相遇合时的烦躁不安,既见既遇合后的平静愉快。这是此诗最单纯的含义,草虫、阜螽与君子和思念君子的女子之间,构成意义上最单纯的类比关系。然而这只是一般读者产生的阅读感受,经学家的看法则不同,于是人们就读到了他们以下的解释:“小序”说这首诗的大旨写“大夫妻能以礼自防”。《毛传》说是写“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郑玄说:“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未见君子者,谓在涂(途)时也。在涂(途)而忧,忧不当君子,无以宁父母,故心忡忡然。是其不自绝于其族之情。”“既见,谓已同牢而食也。既觏,谓已昏也。始者忧于不当,今君子待己以礼,庶自此可以宁父母,故心下也。”孔颖达综合以上诸家之说,解释更加详尽。⑥他们对这首诗的解释一个比一个具体细致,作品的含义经过他们累积式的解释则越来越落实,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将他们的解释集中起来,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将君子和思念君子的女子的身份解释为“卿大夫”及其妻子,二是将诗歌完全纳入儒家“礼”文化的系统中,用“礼”诠释诗歌中人物的行为。经过他们一番解释,原先的草虫、阜螽与君子和思念君子的女子之间单纯的类比关系,便转化成为与上层官僚家庭夫妻之间具有特指含义的类比关系,而且这种类比关系被赋予了浓郁的儒家伦理色彩,从而极其严格地突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一点在解释中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读者都无法从阅读《草虫》原诗中直接获得印象。这说明,解释者与一般读者对于这首诗歌的意义在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类似这样的解释,在《毛诗》一书中大量存在,可以说这是《毛诗》解释学最普遍的一种情况。“小序”、《毛传》、《郑笺》、《孔疏》对《诗经》的解读,有不少地方其实也是符合作品实际内容的,如《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小序”说,此诗是写男女“思不期而会焉”。《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小序”说,此诗的主意是“思君子也”。这些归纳都是恰当的。然而,“小序”、《毛传》、《郑笺》、《孔疏》的作者似乎觉得,仅仅如此读《诗经》,如此说明诗旨,太幼稚,太肤浅,离开他们对《诗经》的阅读期望太远,他们需要给诗人这类吟唱附添更多更重要的指向性含义,以显示作品的经典意义。所以他们要努力地去抠作品的微言大义,即在作品分明的显义之外,千方百计地重构一个重大的意义世界,使诗歌显得不同凡响。比如对于《野有蔓草》,“小序”又说,男女所以“思不期而会焉”,是因为“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所以这首诗歌的主旨是“思遇时”。孔颖达更是具体地概括说,此诗写男女“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陈以刺君”。“思遇时”看上去无疑比男女“思不期而会焉”意义深刻,“君政使然”、“陈以刺君”显然也大大提高了诗歌的认识深度和批判力度。经过这样的解释,男女“思不期而会焉”便下降为作品中不重要的部分,只是诗人描写的一种表面化的现象而已。又比如对于《风雨》,“小序”又说:“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玄解释“风雨凄凄”二句:“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孔颖达说:“此鸡虽逢风雨,不变其鸣,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节。今日时世无复有此人,若既得见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悦,言其必大悦也。”⑦经过这样一番解释,诗歌中的“君子”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和道德的形象,向慕“君子”也就变成了对守节度而不改的正人君子一种道德赞美。
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说明,经过经学家解释的《诗经》三百篇与未经其解释的原作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意义世界,如果不借助经学家的解释,读者虽然未必不能读懂作品,然而决然得不出经学家那样的结论。后人有放弃“序”就无法读《诗经》之说,如程颐说:“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⑧朱鹤龄说:“黜‘序’则无以为说《诗》之根柢。”⑨顾镇也说:“《诗》之有‘序’,如头面之着眉目,非是即不复省释为何人。”⑩他们所说的“序”,指《诗经》“大序”和“小序”,尤其是指说明每首诗歌写作本事和大旨的“小序”,而按照他们对《诗经》的态度,这种说法其实大致也适合于《毛传》、《郑笺》、《孔疏》。这些信“小序”派人士的话,其意思当然不是说放弃“小序”等资料以后《诗经》就真的无法被人们阅读了,而是说读者如果不从这些解释所传递的信息中接受启发,就无法体会到《毛诗》的经义。他们相信,假如不能体会出经义就意味着没有读懂《诗经》,或者就是误读了《诗经》。可见,普通读者和经学家相比,一个是在《诗经》的诗义世界徜徉,而另一个则是在《诗经》的经义世界遨游,两者差别的实质在此。
三
何以读者阅读作品时产生的直接感受与经学家对《诗经》的解释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诗经》的诗义和经义的差别是怎样造成的?这与经学解释者采用比兴的方法说《诗经》有很大关系。他们通过将诗歌描写的此物、此义与未出现在作品中的彼物、彼义进行类比,促使作品的篇内之旨向篇外之旨转换,从而实现对作品的意义极大的跳跃和扬升。这是“小序”、《毛传》、《郑笺》、《孔疏》最常见的解释《诗经》的步骤。如此解释《诗经》的意义可以称为“类比性释义”。其运动的结果,读者在解释者给出的过于膨胀的“作品”含义面前,既感到无比新鲜,又往往会陷于凄迷茫然之中。
类比,古人也称之为比类,是人们展开议论、提出判断时经常使用的比拟类推方法。它利用两种事物某一点相似的特征,引而申之,从更大的范围内对两者进行比况和互释,演绎出这两种事物其他方面更重要的相似性,以便得出推论者希望得出的结论。这种推理的方法在古代经学、史学、文学批评和研究中都有应用,而在《诗经》释义及受其影响的诗词释义等解释活动中,应用尤其广泛,可以说,这是古代最普遍的释义批评方法之一。
《诗经》的类比性释义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诗歌文本内部完成的。如《关雎》中,关雎鸟与君子、淑女之间,构成一种意义上的类比关系,关雎既是它自己,又并不是单纯作为关雎而存在于诗篇中,而是被诗人用来比拟君子和淑女。又比如《萚兮》中,以树叶(萚)因风吹动而飘落,类比兄弟(叔伯)你唱我和,同声相应,也是一种意义上的类比。这些都是单纯意义的类比,也就是前文所说《诗经》的“诗义”。解释者将这些类比的意义说明白,或者由读者通过自己阅读诗歌的前后文,大致了然比兴物与直接比兴义之间的联系,从而在文本内部完成对诗义的解释。另一种类比性释义则是通过将文本内的旨义与解释者所寻求的文本外的意义系结起来完成的。比如“大序”解释《关雎》是表现和赞颂“后妃之德”,而且详细解释道:“《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11)经学家肯定诗里出现的关雎、君子、淑女,其实都不是作为他们自己而存在于作品中,“他们”是未出现在诗里的“后妃之德”的隐喻,是“思贤才”的一种迂回说法,同样,《萚兮》中的树叶和叔伯也不是代表他们本身,而是暗示诗篇内容之外的君臣关系,即“小序”所谓“君弱而臣强,不倡而和也”(12)。这些也就是前文所说《诗经》的“经义”。无论《诗经》的“诗义”还是“经义”,都是通过读者类比性释义呈现出来,通过读者主观判断力对理解过程的参与来获得,这是两者共同的地方。可是显而易见,“诗义”与文本的关系近而实,读者一般可以通过分析文本的语言获得认识;“经义”与文本的关系远而虚,读者只有通过对文本进行特殊的、复杂的分析才可能对它加以说明。从作品获得其“诗义”,主要表现为作品意义的牵引力对阅读的作用;而从作品获得其“经义”,则主要表现为读者无限自由的理解力对作品的作用。对于经学家的这种类比性释义及其得出的结论,人们一般难以形成自然的共鸣,即使接受其解释,认同也往往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所以一旦经学背景发生变化,它们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在失去外力作用(比如强行推行经学)的情况下,普通读者对《诗经》的理解总是朝着自己的直观印象方向偏斜。
在诗内类比释义和诗外类比释义两者中,对于经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诗外类比释义。因为在他们看来,诗内类比释义只能获得诗歌的表面意思,而这并非是诗人写这首诗的根本大旨所在。这是一。其次,诗内类比释义只是对于分析用比兴手法写的诗才有必要,对于分析用赋的手法写的诗就没有必要了。如《郑风·清人》用赋的手法叙述有人在河边,举着画饰的兵器,翱翔逍遥。因为这首诗没有运用比兴,所以理解这首诗歌,只需要解释词义,不需要对诗歌内容本身进行类比分析。于是经学家就直接通过诗外类比的方法,推演这首诗歌的大旨。“小序”说:“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境),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13)在《诗经》“小序”中,这篇文字比较长,且对写诗缘起的说明甚具体。可是除了“翱翔河上”一句之外,“小序”对诗意的所有说明,在《清人》一诗中都找不到相对应的文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解释者所理解的诗外之旨。以上两点都说明,在《毛诗》释义系统中,诗外类比性释义才被经学家认为是最重要的,不可或缺,而诗内类比性释义则或有或无(视是否采用比兴手法写诗而定),即使有也只是为了满足解释经义的需要,其本身的意思无关紧要。本文所说的类比性释义,主要正是指经学家所极为重视的这种诗外类比释义。这是汉朝《毛诗》解释学最重要的特征,孔颖达所谓“于经无所当”的解释现象也主要是指这种情况。
将以上的分析概括如下:
诗内类比释义:比兴手法→直接含义。例如:关雎→君子、淑女。(《关雎》)
诗外类比释义:A.比兴手法→引申意义。例如:关雎;君子、淑女→后妃之德。(《关雎》)
B.赋(铺陈)手法→引申意义。例如:某人翱翔河上→高克陈师旅于外;刺郑文公。(《清人》)
黑格尔在分析象征艺术时指出,象征由“表现”和“意义”两部分构成,单纯的符号其“意义和它的表现的联系是一种完全任意构成的拼凑”,艺术的象征符号则不同,它的“意义与形象”是“密切吻合”的。他又指出,艺术象征符号中也存在形象与意义之间部分不协调的情况,所以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模棱两可的”,“在意义和表现意义的形象两者之间”存在着“暧昧性”。不过,这显然与单纯符号“任意”拼凑形象与意义的关系不一样。他说的单纯符号,指语言的发音、徽章或国旗的颜色,等等。(14)当艺术符号被解释者看作是一种比喻,用来喻示另一事物和道理时,它们也很可能变成单纯的符号。解释这类符号,不仅需要借助想象力以窥见其双关、模棱两可、暧昧性的含义,而且,解释者还将更多更大的变化系数添加到了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从而增加解喻的“任意”性。经学家近乎于将诗歌当作“礼”的比喻或象征符号,他们用类比释义方法(主要指诗外类比方法)解释《诗经》,恰似这种情况。郑玄认为《毛传》说的“兴”就是“比、喻”(15),这固然说明比兴体诗歌好似一个比喻或象征体,即使不是用比兴手法写的诗,在经学家看来也像是一种以叙述形式出现的比喻或象征(如前举《清人》的例子)。当他们跨过宽阔的意义空间,从诗歌作品的此义跳跃到它所比喻或象征的彼义时,随意性不仅难以避免,而且还会被充分利用,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对《诗经》的每一首作品都推演出其具体的政教和美刺的内涵,辗转得出自己所期待的结论。可见,受某种预期的想法或思想支配,让思维发生大跳跃,挣脱具体“诗义”的约束,这些都是与类比性释义始终相伴随的。这决定了类比性释义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诗歌释义的方法。然而,经学家运用类比性释义方法解释《诗经》的主要乃至唯一归结在于索求其政教和美刺的含义,从这方面说,这种执著的较为单一的释义倾向和价值判断又决定了他们解释《诗经》实际上又是不自由的。
四
然而,经学家并不承认自己将《诗经》以外的意义强加给了作品,而是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将《诗经》本来的含义明白地说出来,将诗歌原本所譬类的人事及喻指的义理指示给了世人,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利用为《诗经》作解释的机会将自己的臆见塞入其中。就是说,关雎、君子、淑女/后妃之德;有人翱翔于河上/郑文公令高克陈兵于外——这两组意义的两端相距虽远,然而将它们系结在一起的却是《关雎》、《清人》的作者,不是解释者。其他诗篇也是如此。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诗“序”的问题。诗“序”包括“大序”和“小序”,说明《诗经》大义,以及每一篇诗歌的写作缘起、本事、旨趣等等,自《毛诗》成为儒家经典以后,诗“序”在很长时期内被看作是对《诗经》三百篇最权威的说明。汉唐人普遍尊信“经”、“序”,自不待言,宋人疑“序”(尤其是疑“小序”),其影响所及,诗“序”的权威性在人们心目中降低了。(16)但即使如此,“小序”的地位总体看还依然是高的。从某种方面也可以说,一部《诗经》的影响史,主要就是诗“序”的影响史。特别是“小序”的首句,更被认为对理解《诗经》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朱鹤龄说:“大约首句为《诗》根柢,以下则推而衍者,间出于汉儒,首句则最古,不易观。”(17)直到20世纪初,随着传统经学观念淡出,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读者在前人疑诗“序”的基础上,大多相信“小序”关于诗歌写作缘起、本事、旨趣的说明是“小序”作者对《诗经》意义一次新的构建,有些内容虽然可能得之传闻,可是主要应当是反映一部分汉朝学者对《诗经》作品的理解;诗人并非真的像“小序”作者所叙述的那样写诗,“小序”也并非是对诗篇实在内涵的忠实说明。这是对信诗“序”派断然的否定,即使与历史上疑诗“序”派相比,其采取摈弃态度之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至今,怀疑和否定诗“序”所述即是《诗经》本义的理由已经累积很多,不必赘述,这里只就信诗“序”派所谓的“传承说”谈一谈。一部分经学家以诗“序”传承有自为理由,深信诗“序”对《诗经》创作缘起、本事、旨趣的说明是与作品本然相符的。然而,各人描绘的诗“序”传承“路线图”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可疑之一。(18)其次,即使按照其一般共同涉及的传承中的主要环节(孔子→子夏→荀子→大毛公→小毛公)来看,其传承事实本身也得不到有力证明,这是可疑之二。再次,即使不说以上两个疑点,而姑且承认他们描绘的诗“序”传承是真实的,然而,(一)无法否认孔子诸人都不是写《诗经》三百篇的作者,而是《诗经》的整理者和解释者,因此,即使诗“序”真是传自早期的孔子,也不能否认“序”是读者对《诗经》三百篇的理解和解释。(二)鲁、齐、韩、毛四家对同一首诗的旨义时有不同的说明,对于这种现象只有从解释者的角度去认识才比较合理,所以这也可以证明《诗经》三百篇本无诗人对其创作缘起、本事、旨趣的说明,而现存的说明文字(诗“序”)是解释者后来追加的。总之,所谓的传承说既然无法证明诗“序”出于《诗经》作者之手,就不能将解释者追溯性理解与作者的本意混为一谈。所以,将“小序”“美某某也”、“刺某某也”一类表述不是作为诗人的规定,而是作为解释者的判断来对待,对于《诗经》绝大部分作品来说是恰当的,(19)而这一类判断又是在《诗经》长期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从这方面说,“传承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当然,汉朝《诗经》学家所起的总成性作用十分突出和重要。
前面已经介绍了《诗经》类比性释义的情况,结合以上对诗“序”并非出于《诗经》作者,而是出于解释者的分析,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对《诗经》旨意的这种类比性联想也是来自于解释者而不是来自于作者。然而解释者为了让其他读者相信他们的解释是完全可靠的,便将他们的解释说成是《诗经》作者本人的主观写作意图和作品原本的含义,于是自由释义所得的结论变成了作者原有的寓意,解释变成了《诗经》的原始创作。又,解释者为了使别人信服他们这种类比性释义真确可信,便用孟子“知人论世”的方法(20),求助于历史,为每一首诗歌勾画其历史背景,找到其产生的生活土壤,说诗歌就是为他们所认定的这件事情、这个人物而作,使每一篇甚至每一句诗歌的历史内容都坐实下来。这在郑玄《诗谱》一书达到了顶点。雷克斯·马丁在《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一书中指出:“移情作用通过显示已发生事情的似乎合理性来完成重构,但一个解释似乎是合理的也不可能是适当的,除非归纳的部分是真实的。”(21)其实即使归纳部分真实,也未必可以证明重构一定合理,这还取决于归纳部分的事实与解释者重构的意义两者是否真有必然的联系。经学家对《诗经》的解释一方面倚重他们自己的“移情作用”,一方面又借助于知人论世的方法,建构历史背景,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以示他们对《诗经》的解释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然而,因为他们归纳出来的历史背景带有浓厚的阐释功利色彩,其与重构意义的联系又往往牵强附会,任意性很强,所以谈不上“适当”。类比的自由释义方法之所以需要历史,是因为历史对于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来说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满足解释的功利需要,取得增加解释可信性的效果。所以,虚拟想象出一个历史背景实际上是自由释义者一种解释的策略,以掩饰他们在解释作品时的“移情作用”。然而在《诗经》解释中,这种做法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作品含义与解释意义之间的巨大错位难以被有效弥合。面对如此窘境,为了使读者放弃自己的阅读直觉,接受经学家跳跃很大的类比性释义结论,孔颖达提出,读者在阅读《诗经》时要区别作品的假言和实意,“不可执文以害意”。(22)他视类比的此义为假言,类比的彼义为实意,强调读《诗经》要在得经义之实。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说(23),也如同他“知人论世”说一样,被经学家利用来为他们类比性自由释义作辩护。
《诗经》类比性释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对诗词批评的影响尤其深刻。从汉朝人对《楚辞》的批评,一直到近代陈沆《诗比兴笺》,都带着类比性释义批评的显著痕迹。而另一方面,这种释义和批评方法也受到了一些非议。如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一文中批评杜甫诗歌接受史上一种倾向:“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24)这虽然是针对杜诗解释而言,实际上也是针对《诗经》的释义传统,一部杜诗解释史从某种方面说,是《诗经》解释史的翻版。不过,一个基本事实是,维护《诗经》类比性释义传统的人远比批评它的人多,而且在文学批评史上他们的力量也更为强大,这恰好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什么经常被自由释义倾向占了上风。
注释:
①为统一格式,本文按学界惯称,《毛诗》即《毛诗故训传》,亦称《毛传》。《毛诗》每篇题下都有一个题解,标为“小序”,首篇《关雎》除了有“小序”,另有一篇总序,标为“大序”。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称《郑笺》,唐代孔颖达为《毛诗》作疏,即《毛诗正义》,亦称《孔疏》,以下同。
②《毛诗正义》,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③《周南·桃夭》,见《毛诗正义》,第45页。
④《毛诗正义》,第1298页。
⑤以上引文见《毛诗正义》,第352页。
⑥《毛诗正义》,第69页。
⑦以上引文分别见《毛诗正义》,第320-321、313页。
⑧《河南程氏经说》卷三,清刻本。
⑨《毛诗通义序》,见《愚庵小集》卷七,第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刻本,1979。
⑩《虞东学诗·诗说》“序说”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第37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12)《毛诗正义》,第4、21、303页。
(13)《毛诗正义》,第287页。
(14)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10-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5)如《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毛传》:“兴也。”《郑笺》:“兴者,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众妾,使得其次序,则众妾上附事之,而礼义亦俱盛。”(《毛诗正义》,第41页)虽然“兴”有领起之义,非“比”所能替代,就其主要的表达功能而言,比、兴二义接近,郑玄之说不可破。
(16)唐朝已经出现怀疑诗“序”的意见,宋人范处义《诗补传·篇目》说:“异哉!庸人之议诗‘序’也。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借之子夏。且子夏犹知不及,汉去《诗》益远,何自而知之?”怀疑诗“序”在宋朝更成为了一股风气,这是对唐人疑诗“序”一派意见的发展,并非没有先兆。
(17)《毛诗通义序》,第280页。
(18)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50页,注释8-11,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诗经》有些作品谈到作者写诗的缘故和目的,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颂,以究王讻。”但是这类作品在《诗经》中数量极少。
(20)《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焦循:《孟子正义》,第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21)[美]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第48页,王晓红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22)《郑风·有女同车》孔颖达疏,见《毛诗正义》,第297-298页。
(23)焦循:《孟子正义·万章上》,第638页。
(24)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第437-438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标签:诗经论文; 孔颖达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说明方法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读书论文; 毛诗正义论文; 清人论文; 载驱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