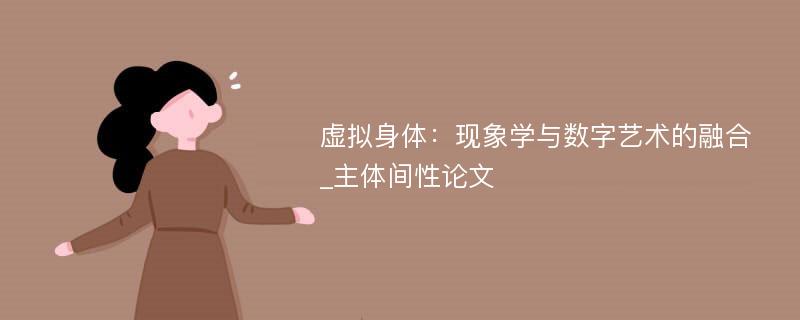
虚拟身体:现象学与数码艺术的会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身体论文,艺术论文,数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074(2004)03-0060-05
身体是主体的生理存在,是人格发展的物质依托,也是人类交往的基本条件。因此,现象学关注身体是很自然的事情,胡塞尔等人对此就多所论述。对身体的重新审视同样是数码艺术的热区。虚拟身体是现象学与数码艺术的会聚点之一。现象学对身体的思考启迪了数码艺术家的灵感,数码艺术则将对身体的思考推进到虚拟世界,丰富了相关理论。胡塞尔设想通过想象让他人的“那儿”成为我的“这儿”,数码艺术家则在数码媒体的支持下虚拟地让人们摆脱“这儿”与“那儿”的分离;胡塞尔设想通过“我”的心理作用在自己的意识中激活他人躯体,数码艺术家则依靠科技将他人躯体的影像转化为可互动的准实体。胡塞尔关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认识上的联系,海德格尔关心我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存在,数码艺术家则借助于软件实现自我与他人的融合。现象学远绍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莱布尼兹当年已经预见到比人类更为完美的单子,目前,所谓“后人”、人为进化已经成为理论界、艺术界的共同课题,以虚拟身体为主旨的作品正体现了人类对自我超越的追求。
一、虚在:摆脱“这儿”与“那儿”的分离
为了解决现象学所面临的唯我论问题,胡塞尔提出著名的统觉理论。他说:“当以反思的方式联系到其自身时,我的生命的有形的有机体(在我原初的领域里)作为其所予方式而具有中心的‘这儿’(Here);每一个其他的身体即‘他人的’身体则具有‘那儿’(There)这种方式。”[1]这表明:反思者承认自身以外的他人身体的存在,从而间接承认了我的“思我”之外他人的“思我”的存在。胡塞尔进一步指出,虽然“这儿”有别于“那儿”、反思者在现实中可能永远无法进入他人的“那儿”,但却可以用一种想象的方式在意识中使他人的“那儿”成为我的“这儿”,即设想“如果我在那儿的话,我的身体会是怎样的”。这样一来,我的身体是“首先建立的原本”,而他人的身体则是我的身体的复制形式,我可以将他人的身体领悟为和我的身体一样的那种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的身体,“类比的统觉”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实现的。这种统觉实际上是“视域互换”的“共同呈现”。他说:“在把他们作为人来经验时,我把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理解作和承认作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自我主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从这个位置上去看身边的事物,而且每个人将因此而看到不同的事物显相。……尽管如此,我们与我们的邻人相互理解并共同假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时空现实,一个我们本身也属于其中的、事实上存在着的周围世界。”[2](P92-93)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来说,肉身存在只能是特定空间中的存在,“这儿”与“那儿”因此总是分离的。媒体的作用之一正是克服上述局限。1876年3月10日,美国发明家贝尔与其助手沃森一道在波士顿法院街109号的阁楼上进行电话实验。贝尔说出了第一个通过可变阻抗话筒传输的完整的句子:“沃森先生,快来,我需要您!”当时正在隔壁房间的沃森听到了这句话,明白贝尔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在我们看来,这是利用电话媒体沟通“这儿”与“那儿”的最初尝试。现实生活中打电话的人几乎都同时使用听筒与话筒,因听筒而感知“那儿”有人存在,因话筒而得以表明“这儿”有人存在。可视电话拓展了上述联系,让人们不仅从听觉上而且从视觉上建立“这儿”与“那儿”的联系。
数码媒体由此更进一步。2001年3月25日,在旧金山艺术学院有个由迪茨策划的多媒体展览,其核心理念是“远程通信联系:虚拟拥抱”。迪茨说自己的展览“部分是历史,部分是想象,部分在现场,部分在网上,它跨越了艺术、通信与流行文化的界限。”在画廊两个彼此分离的部分摆着两张沙发,都靠着蓝色的屏幕。相互链接的视频摄像机与显示器使坐在这两张沙发上的人并排坐在屏幕上,让人们产生对于数码化主体间性的视觉体验。如果说身处异地的人原先位于“这儿”或“那儿”的存在都是“实在”的话,他们因被投射到屏幕上而实现的存在则是不同于“实在”的“虚在”,这种虚在超越了“这儿”与“那儿”的鸿沟,使二者统一起来,表现为身处异地者并排而坐。现实生活的人同样可以并坐,但坐得再近仍有“这儿”与“那儿”的分别,似乎仍然只能靠胡塞尔所说的类比的统觉来实现主体间性。对于“实在”而言,以上矛盾看来是无法克服的。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当您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无法在“那儿”,正如当我在“这儿”的时候您就无法在“这儿”一样,特定身体所占有的空间不能在同一时间内为其他身体所占有。“虚在”异于“实在”之处,恰好在于摆脱了这一困境。与“我”并坐者不是其肉身,而只是其影像。当这种影像是通过显示器呈现时,“虚在”还不够彻底,因为“我”仍然无法同时占有对方虚拟身体在显示器中所占有的空间。如果与“我”并坐者的影像是通过投影仪投射而得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虚拟身体,或者说同时占有对方虚拟身体所占有的物理空间。与此相似,如果“我”的“虚在”表现为通过投影在对方所在空间呈现出“我”的影像的话,那么,对方自然也可以同时占有“我”的虚拟身体所占有的物理空间。在这一意义上,一方的肉身与另一方的虚拟身体很自然地彼此交叠。不要忘记:数码媒体是互动性很强的媒体。依靠数码摄像机、计算机与数码投影仪的组合,很容易实现彼此交叠的肉身与虚拟身体之间的互动,而虚拟身体不过是肉身的“虚在”。因此上述互动也就是“实在”与“虚在”的互动。
当然,完全可以设计出这样一种设备,它将若干参与者的虚拟身体同时投射到同一屏幕(或沙发之类空间),由此实现“虚在”之间的互动。对此,可以另举一例加以说明。纽约一号称“浮点单位”的艺术群体关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远程表演与网络广播。1995年,由它派生出名为Fakeshop的另一群体在1999年9月奥地利林茨市举行的电子艺术节上推出一个名为“多样栖居”的作品,涉及到若干与躯体状态有关的问题。这一作品将建筑、数字视频、图象、网络广播与表演结合在一起,试图将躯体加以分懈、重组并映射入虚拟空间。表演者的躯体的若干局部被扫描为视频,然后被转化为虚拟现实世界中的对应模型,再将这些模型与原先的视频记录结合在一起,利用互联网视频软件CU-SeeMe或Webcam在网络上进行广播。作者冈珀茨试图以此表现自己对表演者躯体与其虚拟现实化身之间的互动、由三维模型在屏幕上生成的躯体与参与者在CU-SeeMe之类软件的实时投影之间的互动、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互动等现象的理解。这一项目融汇了有关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科幻小说的知识。
二、虚拟躯体:将“灵魂”赋予“化身”
如何看待作为可交互影像的虚拟躯体的意义呢?胡塞尔曾经区分两个彼此相关的概念,即“身体”(koerper)与“躯体”(leib)。大致说来,躯体是物质性的存在,而身体是兼具精神性的存在。“我之所以能够把一个自然事物理解为一个‘躯体’,即承认他人的肉体存在,并且进而把一个‘躯体’理解为一个‘身体’,即承认其他自我的存在,意识中的‘联想’能力在这里起着双重的关键的作用。”“某物引起对某物的回忆”是联想的基本形式。它使意识有可能进行双重的超越:首先,显现给我的这个陌生的躯体通过它的“举止”、它的“行为”而使我联想起我自己的躯体;其次,既然在我的躯体中包含着自我,那么在其他的躯体中必定也包含着其他的自我。这样,“他人躯体”便被赋予“他人身体”的意义。一个躯体因此被“赋予灵魂”(beseelen)、“激活”,成为一个对立于我的、具有同样灵魂本质或自我本质的他人。[3](P148-150)
他人的躯体之所以能够被激活,在胡塞尔看来是由于“我”的心理作用,在先验现象学的框架内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自然的。胡塞尔对主体间性的研究始于1905年。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aet)是作为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提出来的,指的是存在于主体之间、使得“客观的”世界先验地成为可能的共同性。对他来说,主体间性有“世间的”和“先验的”两层含义。对他来说,后者是更为根本的。哈贝马斯使用的“交互人格”(interpersonlitaet)、“交互行为”(interaktion)也是指主体间性。但是,他主张将现实生活中的交互主体而非先验的本我当成考察主体间性的出发点。如果将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用于考察躯体与身体的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与胡塞尔殊别迥异的结论:如果说他人躯体能够被“激活”的话,那么,首要原因是这种存在物能够以有灵魂的存在物所特有的方式与我们互动。我们是因为上述互动而认定这种存在物的特性的。当然,胡塞尔所说的当事人关于自身躯体的联想在上述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是根据他人躯体与自己的互动方式与自身躯体所可能采取的与他人的互动方式的一致性而认定对方作为人的特性的。
可以根据上述思路对作为可交互影像的虚拟躯体加以考察。虚拟躯体可能仅仅是静态影像,作为人物形象存在于美术作品中。此时,如果说它们可以被激活的话,那么,纯然靠的是创作者或鉴赏者的想象。因为这种想象,虚拟躯体被“赋予灵魂”,成为审美情境中的对象主体,由此建立起与艺术活动相适应的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同样包含了某种统觉或视域融合,其性质视叙述方式而异。就逼真性而言,动态影像比静态影像进了一步。然而,在传统影视作品中,人物躯体仍然只是呈现为不可交互性影像。在“远程信息处理联系:虚拟拥抱”展览中所出现的,则是可交互性影像。在这样的条件下,虚拟躯体之所以能被“赋予灵魂”,不仅是由于参与活动者的想象,而且是由于它们能够作为当事人的化身现实地与人互动。甲方对于呈现于自己身旁的乙方虚拟躯体所采取的每一行动,都被交互性设备摄取、转播、投射,转化为甲方虚拟躯体在另一空间中对乙方所采取的行动。这样,主体间性就具备了如下形式:
空间1(共在1) 空间2(共在2)
甲方身体
通道 甲方虚拟躯体
乙方虚拟躯体 乙方身体
我们还可以循着上述思路考察遥控机械人与智能体(agent)的价值。在作为艺术作品的机械人行列中,遥控机械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为遥在艺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遥在(telepresence又译“远程在场”或“远程存在”)这一术语是费希尔首先使用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属下位于加州的一个研究中心工作,主要承担虚拟环境工作站项目。他受电影放映机制造商诲利希“体验剧院”的启发,在1985年提出“遥在”一词,意为将自我投射到虚拟世界中。此后,这个术语不胫而走。遥在艺术是基于电信、机械人学、新式人机界面与计算机的交互性艺术,以遥控机械人技术为基础。它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形式或结构,而是遥控机械人所进行的远程活动。其特点是由主动一方(人)对于被动一方(机械人)进行操纵。例如,1997年,保罗斯与坎尼合作创造了《个人漫游在场》(PRoP)。作者认为,目前互联网还无法让我们进入位于接口另一端的人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换言之,我们缺乏在另一端的身体对等物,即PRoP。尽管如此,若将计算机图形图像、互联网与远程机械人技术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创造让用户得以沉浸的可航行的远程世界。这一作品就是朝这方面开拓的。
智能体不仅可供科学实验与社会服务之用,而且获得艺术家的青睐。试以网上机器人(net robot)为例来加以说明。网上机器人又称spider、web crawler、web wanderer或网络虫(netbot),主要用途是搜索在线信息。作者署名为ARN的,《攫取者》(Thegrabber)是没有商业用途的艺术网络虫。它读取人们所提供的URL之上的文件,如果发现有外部链接便加以追随,如果没有链接就停止运行。创作意图是显示上述单一过程,其次是在所访问的网站的日志中留下痕迹。界面很简洁,只要输入URL,点击“攫取”按键,就能欣赏到网络虫所经过的路径(以网页源代码的形式显示)。美国女艺术家亚历山大开发的《虫》(2000)属于智能体代理艺术作品。她很清楚网络虫访寻网页链接、替搜索引擎构建数据库的原理,认为它们因此了解网络的方方面面。她想让网络虫以异于常规的方式工作,揭示与讲述网络未为人知的故事。《虫》呈现为震波动画。当访客输入搜索词时,它就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从所返回的网页中选择一页,从中读取一段文本。从这里出发,它爬行到相链接的网页之一,再从中读取一段文本,如此前进。要是它无法从一个页面沿着链接向前推进,或者在特定服务器上待得太久而觉得累,它会倒回头沿着另一个方向运动。它力求在尽可能多的服务器之间运动,从不访问同样的页面两次(除非被骗)。这样。它提供了网络故事之一瞥,至少是网络虫的意识流之一瞥。当网络虫从每个页面读取引文时,其文本在屏幕上穿行,模仿网络信息包的流动。同时,网络虫大声读出文本,在屏幕边上显示出所访问的URL地址目录,这一目录随着网络虫所访问的地址的增加而变长,可以被看成是URL诗歌的节。在界面上,所读取的文本显示为一行行掠过的文字,或自左向右,或自右向左,亦有上下运动的。这些文字被读出声来,声音彼此交叠,难以辨识。再如,沃尔什开发的OuLiBOT就像是一个艺术个人化的搜索引擎。它拥有一台万维网服务器和许多IRC客户机,这些客户机在聊天室频道中彼此交谈。OuLiBOT的核心是个小小的过滤搜索引擎。据信这个网络虫能够对所搜索到的材料加以分析,将论题与自己的“大脑”中所保存的信息相联系,以此作为谈资。
交互性影像艺术、遥在艺术与智能代理艺术都是人的化身,代表了人的身体扩展的三种可能。交互性影像艺术并非实体性存在,无法对所处环境进行主动探索;遥在艺术所应用的遥控机器人是实体性存在(硬件),能够对所处环境进行主动探索,但它本身不具备智能;智能代理艺术比遥控机器人更胜一筹,不仅拥有智能,而且还可以在远程环境中自主完成任务。它们不同程度体现了艺术家赋“灵魂”予“化身”的理想。
三、虚拟主体间性:实现“你”与“我”的融合
胡塞尔将统觉的对象由“物”转到“他人”,由此丰富了主体间性理论的内涵。毫无疑问,身体的虚拟化可以进一步扩展我们对于主体间性的认识。就笔者所知,借助于数码媒体实现虚拟主体间性的艺术作品不乏其例。法国艺术家德劳欣利用关键词“肖像”进行网上搜索,将所得到的图像文件与原背景分离,然后在新背景中组合。由此而产生的网络艺术作品被命名为J'eux(2001)。它由15×19幅肖像组成一幅儿童头像。点击每幅小肖像,通向原肖像的链接就被激活。如果我们认定每幅肖像都代表了相应的虚拟身体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将这尸作品当成主体间性(所谓“单子共同体”)的隐喻,因为决定我们身体造型的生物基因与决定我们心理特征的文化基因都来源于某种人们共同体。这个作品并不是可变的,作为构成要素的肖像不因为人们在不同时间访问它而变化。如果将这些肖像替换为摄像头拍摄而得的15×19段人物面部表情活动(视频),由此而形成的新作品无疑将成为动态(而非静态)主体间性的隐喻。
美国亚特兰大艺术学院多媒体与网络设计系贝内特创作了《人入脸网站》(2002)。作者认为,脸部的标准图象少有交流人格完整性的能力。人格的“本质”(essence)并非某种储存在点、颗粒或象素的静态二维排列的东西。与此相反,被保存的是标志人格特性(诸如一唇的卷曲,一只眼睛的斜视,或双唇的皱起等)的微妙暗示。这些类型的人格特性可以被用来表达关于一个人的信息(当考虑到它们的结合时),或者用来使人联想到人格的复杂性。作者抓住并实时操纵面部图象,对所采集的多人面部造型加以消解、切割、重新组合,试图引导观者看穿人格完整性的幻象。居于作品中心位置的是一帧不断变动的面部肖像。它是由诸多图块(如张三的左颊、李四的右颊,男性下巴、女性秀发之类)构成的,而且不断离析,原有的图块被剥离,露出新的图块。我们可以将这一作品当成主体内部间性的隐喻。巫汉祥曾指出:“完整的主体间性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即外在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间性。”[4]根据他的分析,内在主体间性实际上就是多重自我之间的交互关系,包括理性主性和感性主体,原欲主体、自我主体和超越主体,本真主体和异化主体,此在主体与彼在主体等。《人入脸网站》所揭示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即被内化为自我的他人的交互关系。众所周知,人格发展是通过社会化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将他们当成正面楷模或反面教员,并将相应的人格特征内化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上述作品所展现的身体融合以主体生物学意义上的实性存在为依托的话,感觉的合成则看重主体生理学意义上的功能。意大利艺术家米基《大耳:想象的音景》(2002)引导人们设想自己拥有功能无比强大的耳朵,可以倾听地平线的各种音响、知觉无边无际的声音。这只独一无二的大耳朵当然是虚拟的。米基要人们用合适的形式描绘并向其网站提交自己此时此地所听见的声音,不论它们是来自室内或室外、来自城市或乡村。这类声音被汇集、合成、播放,于是访客可以从网站上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天籁、地籁与人籁,就像是真的成了“顺风耳”那样。
在西方哲学史上,莱布尼兹否认物质实体的存在,认为只有以微知觉为根本规定的单子才是实体,物质不过是无数的单子在微知觉中的一种反映。这种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首次从本体上来解决主体间性问题。胡塞尔将自己的哲学称为“现象学的单子论”,正表明了与莱布尼兹的渊源关系。进入电子时代之后,利奥塔在1988年指出:“遍布地球的电子和信息网生出了一种应被视为宇宙级的,非传统文化价值可比的记忆总体能力。这种记忆意味着的一种奇论在于,它最终将不是人的记忆。而‘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含义是:支撑这种记忆的躯体不再是一具地球人的躯体。计算机综合更多的时间段(‘次’数)的能力不断增长,所以莱布尼兹才能够说他正在孕育一个比人类本身从未能达到的更加‘完美’的单子。”[5]由人这样的单子向比人更完美的单子演变,意味着“后人”的出现。在理论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教授海勒斯出版了著作《我们如何变成后人:控制论、文学与信息论中的虚拟躯体》(1999)。在书中,她谈到三方面的问题:其一,信息如何丧失其躯体,亦即它如何被作为脱离其物质载体的实体而被观念化;其二,半机械人的文化与技术建构;其三,在控制论话语中人本主义者所说的“主体”如何被分解,引发歧见的“后人”如何出现。在创作中,美国女雕塑家维塔-莫尔与其合作者建立了元后人(2002)网站,以灵活性、柔软性和长寿性为目标设计未来躯体的原型,包括先进的大脑、增强的感觉与高效的脊柱通信系统等。她认为正在崭露头角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可使人不朽并增强创造性,基于这一观念具体解说了如何改进人的身心。诸如此类的探索已经不是科幻,而是具有某种可行性。英国里丁大学控制论教授沃里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师曼恩、澳大利亚赛伯艺术家斯特拉克等人都以自己的身体进行了大胆尝试。可以预见,在新世纪中,以躯体虚拟化为题的实验、创作与研究都将取得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