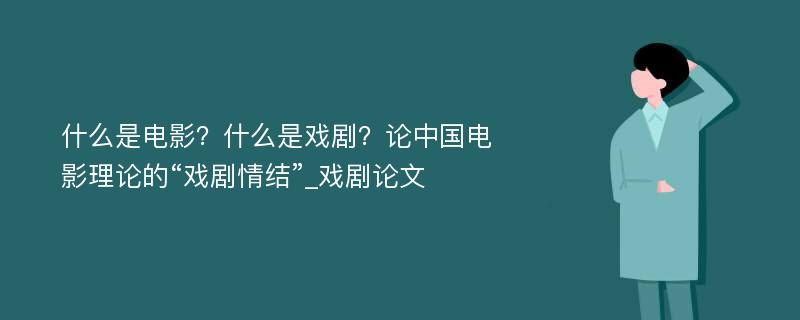
电影是什么?戏剧是什么?——试论中国电影理论的“戏剧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情结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5)01-0025-14 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影史上,中国电影与戏剧一直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影戏”作为电影的早期称谓之一,到电影与戏剧在技术、美学(表演、布景、灯光、空间构图)、从业人员及展映空间的错综交接,到电影理论上对“影戏说”的承继和反叛,戏剧长期以来既成为中国电影的丰富资源,也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戏剧与电影间的俄狄浦斯情结,或日中国电影的“戏剧情结”,在1970年代末一场关于“丢掉戏剧拐杖”的论争中达到高潮。由钟惦棐提出的“电影与戏剧离婚”成为电影“现代化”的口号和根本条件,以电影媒体特质为出发点的本体论被当之无愧地看作电影特殊审美表现形式的基础。 但是,在这些论争中,极少有人问及一个基本的问题:电影是什么?戏剧是什么?换言之,电影作为媒体的特质究竟是什么?电影的本体是否仅仅局限于电影的物质基础?随着电影技术、物质基础和电影美学的日新月异,媒体特质是否一成不变?媒体特质说到底从何而来?在电影研究日益学科专业化的今天,研究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应该以电影为中心还是将电影边缘化?如果中国电影与戏剧的历史关系值得重新研究,电影与其他媒体(文学、雕塑、绘画、建筑、音乐等)间的关系又如何对待?如何看待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因此不只牵扯到这两个媒体或与其他媒体之间的关系,更牵涉到电影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化问题。同时,研究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不仅仅是对中国电影史的叙述问题,也关涉对中国电影理论的梳理。①这些问题最终让我们走出中国电影和戏剧的个案而参与到今天对于电影及电影研究重新定位的讨论。面对新媒体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以及媒体理论与媒体史研究的日益拓宽和深入,电影研究如何在方法和研究范围上与新旧学科对话,成为本文最终关注的问题。 本文先追溯媒体特质论在西方的来龙去脉,进而反观中国电影理论史上几次对戏剧电影关系的讨论——从1920年代电影特质论的提出,到30年代“软性”与“硬性”电影之争中对戏剧和有声电影的讨论,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对戏曲电影的商榷,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影语言现代化呼声中“丢掉戏剧拐杖”的决绝。文章最终回到当代从不同学科对媒体特质论的重新探讨,继而提出电影和戏剧研究方法上新的可能。 尽管多年来在中外电影史和理论上诸多讨论中,电影的媒体特质(cinema's medium specificity)被当成不言自明的本真性,媒体特质论(medium specificity)这一话语却可以追溯到德国美学和戏剧家莱辛。莱辛在1766年的《拉奥孔》一书中将诗歌与绘画分家,将二者分为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在将两者定义为本质不同、不可混淆的艺术后,这种对媒体本质的分割便成为界定艺术成功与否的标准[1]。在电影史上,早期电影理论从1910年代便对电影媒体的特质有所述及,但要到1920年代伴随着无声电影作为公众娱乐形式和新型艺术的地位日益稳固后才逐渐成为定论。有意思的是,在1910-1920年代期间,戏剧频频作为电影特质话语中的必要反差出现以定义电影的特质。无论是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2]、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3]、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4]、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5]、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6],还是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7],都不厌其烦地将两者对照。在这些讨论中,早期电影理论家们不断围绕时空组织、表演风格和观影模式来阐发电影和戏剧两种媒体的鸿沟。如果说1910年代电影还常常被比作既定的艺术形式(雕塑、绘画、诗歌、建筑、音乐等),到20年代电影已确立它与这些艺术形式分庭抗礼的地位。电影作为现代工业产物的机械艺术,对于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而界定的表演、观察、时空组织及观影模式的约定俗成形成相当挑战。这些挑战从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上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从而赢得众多方家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艺术家和批评家发出的对电影特质的盛赞,与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形式、新的大工业制造模式,及社会组织和感受的形式的逐渐成型息息相关。因此,现代主义对于电影对后人类(posthuman)特质的热情,无形中却成为商品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中国电影史上,对于电影特质和戏剧关系的类似论述在不同历史时刻重现,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电影史与世界电影史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中国电影理论与跨国家跨地区电影理论的交接。但我更关心的不只是媒体特质这一话语在不同时段地界的重复,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具体的历史时刻,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媒体特质的话语如何与其他话语交织,并扮演何种角色。 我所关注的第一个历史时刻是1920年代的中国。有意思的是,对电影媒体特质较详尽的讨论,却是由我们公认为现代话剧之父的前辈——欧阳予倩阐发的。欧阳予倩在连载于20年代主要电影杂志《电影月报》中的长篇论文《导演论》中,对电影与戏剧从编剧、导演、演员、布景等多方考察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予倩虽是话剧史上的泰斗,同时也在早期电影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我发现,正是在他谈及实践问题时,电影与戏剧的区别不再泾渭分明。 一开始,欧阳予倩对电影媒体特质的肯定,与西方诸多讨论十分相似。文章开篇即强调电影已不再是戏剧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电影有电影的特长,有电影能够表现的,其他艺术决不能表现。而所用的方法,也完全和其他艺术不同。所以电影已经渐渐地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8:814]。② 欧阳予倩继而阐述电影媒体的诸多特征,强调它是光与影的艺术,易于传播,题材独特而与现实相关,包括风景、街市、人群、战争这些戏剧通常难以体现的影像。而早期电影在声音(无声)和色彩(黑白)上的局限,却为电影的运动性和观影的通感作用所弥补和超越。用欧阳予倩的话说,“电影是人之精力、机械力,和自然界之万象相融合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并且是近代的科学的艺术,动作的流动的艺术,概括说,就是光与影的艺术,而其中有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8:814-815]欧阳予倩由此列数电影与戏剧的诸多相异之处:戏剧出现在舞台,电影演绎于银幕;戏剧注重言语,电影注重动作:戏剧是光与色的艺术,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其中,戏剧与电影最大的区别是电影的表现空间:“戏剧的表演限于舞台,电影的表演是占了无尽的地方,譬如,天然的风景,伟大的建筑,绝不是舞台上所能有的,可是无论大海高山大瀑布大平原人类的大群集以及珍禽异兽之类,凡舞台上受限制的,电影都能收之于一片之中,在观客的面前展开来看。”[8:817]欧阳予倩的这些论述,有作者本人对电影最初直觉的认识,也与西方电影理论的输入不无关联。在徐卓呆1924年编译的《影戏学》、郑心南编译的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电影艺术》中,电影特质论已然出炉,其中戏剧与电影的对照已成为论述电影特质论的常式。③ 但是,欧阳予倩的认识,既基于他对电影戏剧的观察,更来自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话剧最早的推动者、戏曲编导和表演艺术的行家里手,他同时也参与了早期电影的创作。1926年欧阳予倩加盟民新公司后,他不但参与了3部影片《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天涯歌女》的编剧,还在后两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在谈及电影布景的一些实际考虑时,电影与戏剧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欧阳予倩谈到电影外景虽多用实景,但因各种原因,现实中的实景不尽与故事相合,仍需搭建布景。但布景并不一定以绝对写真为标准,这也是布景优于实景的地方。对欧阳予倩来说,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都应以表达情绪为中心。以戏剧为例,近代戏剧的舞台装置往往侧重光线色彩用具中的必要元素,而将影响全剧气氛或妨碍看客视线的器具或其他元素去除。电影的布景虽与戏剧不同,也应该以简为妙,将影响看客注意力或全剧情绪的因素去除[8:821]。谈到光线,欧阳予倩再次以戏剧为例,认为光是戏剧的生命,而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后者既要考虑光,还要注重影,并注重二者的搭配得当。但在谈到光影配搭时,欧阳予倩再次以戏剧为例,谈到幼稚的戏剧只图明亮和光线均匀,就像幼稚的电影一样。 在这些对电影的叙述中,欧阳予倩往往以戏剧作反衬,在具体分析时又不断以戏剧为例子,触及二者诸多相似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予倩虽以戏剧笼统而言,但他主要的例子来自西方近代戏剧和早期话剧。而在谈到电影与戏剧同为群众艺术,以情绪的组织、氛围的营造为重时,他则以戏曲为范本[8:823]。换言之,戏剧与电影不只是媒体层面的比较,而牵涉到某种戏剧形式和电影形式的比较(他特别提到未来派电影的布景应另当别论)。在这些具体的比较中,二者的交接逐渐呈现,电影虽成为独立艺术,仍常以某种戏剧形式为范本。这些交接在布景和灯光上尤其突出,不光因为早期电影和戏剧的布景灯光常常使用相同的从业人员,还让我们意识到戏剧本身的历史变化和多样性。④因此,将电影与戏剧两者在媒体层面作抽象的对照的结论,往往因为具体实践而不攻自破。值得重视的是,欧阳予倩对电影独特性的肯定,与20年代中期电影在中国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休戚相关。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电影院日渐奢华,影人和影星的地位不断上升,电影逐步由家庭转向工业化制作,电影杂志也纷纷出炉。在电影不断增加自己的放映空间和话语阵地时,对戏剧这一最接近电影的大众娱乐和艺术的形式作出挑战也就成为电影争取话语权和生存空间的必要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批评与理论中对电影特质的肯定,与电影工业和商业运作相得益彰,成为电影体制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元素。 到30年代初,也就是我考察的第二个历史时刻,电影特质的讨论再次以戏剧为反衬,而这一次则在有声电影同“软硬性”电影的争鸣中阐发。其中刘呐鸥对电影特质的讨论尤其突出。有声电影的出现,对以默片为基础的电影特质论提出了挑战。在《影片艺术论》一文中,敏感于电影技术和艺术的飞速变化,刘呐鸥开篇即对电影特质论提出了质疑:“将来在真的天然色的影片完成的时候,在立体影片成功的时候,或在电送影戏和其他电影科学所约束我们的东西完成并影遍了的当儿,谁说艺术的影片理论不会随之变更呢?”[9:105]⑤刘呐鸥对电影特质的讨论一开始即出现了悖论:影片艺术一方面因电影的发展而难以定义,另一方面又因诸多既定的讨论而有迹可循。[9:104]⑥换言之,影片艺术的定义既是暂时的又是肯定的。刘呐鸥所指的影片艺术,也就是电影特质,既包括了电影的物质技术基础,又包括了建立在这些物质条件上的艺术形式。但这种对电影特质的肯定又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在《Ecranesque》一文中,刘呐鸥将电影特质的三要素概括为“非文学的,非演剧的,非绘画的”[10:1],从而透露了这些媒体形式与电影丝丝缕缕的联系,并成为电影特质话语中的无意识(unconscious)。刘呐鸥对电影特质的讨论,大量参阅并引述西方(尤其是苏联,德国和法国的)电影理论和实践。在有关蒙太奇(montage)、电影眼(kino eye或Cine-oeil)、纯粹电影(pure cinema)、绝对电影(absolute cinema)的引介中,刘呐鸥与西方现代主义接轨,强调电影的物质技术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对人类感知、时空组织、审美成规的挑战和新的表达可能(尤其是动感、光影艺术、节奏)。 刘呐鸥的第二重悖论却与电影进化论产生矛盾,再次体现有声电影的出现对既定电影特质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光是对电影特质的内容,也是对电影特质论所暗含的前提产生了质疑。对刘和许多同时代的电影人来说,有声电影的出现似乎让电影出现了倒退,使得从作为戏剧附庸而独立出来的电影再次与戏剧合流。电影特质论本是将电影作为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它的机械基础、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联系,使得它成为机械文明时代的宠儿。但这种“现代性”光彩背后暗含的进化论基础却由于有声电影在电影表演与空间美学上有向戏剧的回潮倾向而受到冲击。早在1928年刘呐鸥便在以葛莫美为笔名的《影戏漫谈》一文中,提到“影戏的历史可以说是脱离演剧的努力的历史”[11:283],但对于电影的两大技术进步——有声和有色,既然不能否定,便面临如何解决电影再次与戏剧接近的问题。刘呐鸥提出是否可用特写、移动摄影之类电影独有的表现手段达到影戏和演剧的结合,同时对两种媒体间的前途仍持开放态度。30年代有声电影的势头渐猛,尤其是美国歌舞片盛行,对电影特质的肯定与戏剧的差别则集中在声画同步(synchronization)的讨论上。刘呐鸥将美国全部有声电影(all talkie)比作声音与动作机械同步的打字机,提出影像与声音的配合应超出只是对同步的追求而寻求“充分表达出内面的意义”[10:1]。在讨论中,刘呐鸥提出扬弃这一概念,隐隐透露了对有声和无声电影产生一种辩证而非纯粹进化论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这些看法超出了批评界对“软硬性”电影阵营的既定分野。郑伯奇作为左翼电影的重要理论家,对声画同步作出了更深刻的批评。同刘呐鸥相似,郑伯奇同样认为美国有声电影以舞台剧为模本。与之相对,他以德法的音乐片为例,提出声音的蒙太奇手法(montage du ton),并进一步提出这是对默片的承接[12:159-168];同时讨论了声画对位(contre-puncto-methode)的技巧[13][12:158]。郑伯奇更直接地挑战媒体进化论,提出话剧的出现不会取代哑剧、乐剧、木人戏、舞俑剧这些更古老的戏剧形式,而有声电影的出现也不必意味着无声电影夭折[14]。左翼电影的影人和批评家对电影声音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左翼杂志《艺术月刊》于1930年刊登的一场有声电影的讨论中,影人、影评人、剧人对有声电影是否取代戏剧多次探讨,并提出用音画或声响电影(Sound Picture)—无声电影配上器乐或音响效果,坚持字幕而不用对话——取代美国全部有声电影(talkie)的可能[15]。 在30年代初这场对电影特质与戏剧关系的讨论中,有声电影的出现对媒体特质论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媒体特质不再以不同媒体,而以媒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默片、有声电影)区别;而在同一阶段(有声电影),同一媒体又因不同的艺术处理方式(构图、表演、观影模式、剪辑、声画关系)迥异。媒体间本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因同一媒体不同的艺术取向而被超越。对刘呐鸥和郑伯奇来说,有声电影面临两种选择:或与戏剧结盟,或成为默片的延伸。这样一来,本来基于默片诸多特点而阐发的媒体特质从绝对而变成相对,媒体特质论暗含的进化论思想受挫并引起反思;同时,媒体的特质不再因电影的物质基础而形成根本差别,却因不同的艺术取向而有异。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有关媒体特质的讨论,不是在电影技术和艺术的真空中进行的。对有声电影给出定义和取向,不光牵涉到戏剧与电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针对了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形成的垄断局势。刘呐鸥、郑伯奇对苏俄及德法电影的推崇,不仅为有声电影提供了另一种美学选择,还让后者与美国有声片抗衡,并为中国电影在处于由无声到有声的过渡中制造了新的契机。这种契机不光是美学选择上的,也是技术和经济层面上的——全部有声电影在电影制作和放映上的技术要求和造价,给本来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国电影工业造成巨大压力;而采取声响电影这种以默片为基础,加以后期制作产生音响效应的电影,则可以利用现有的制片和放映设备。这些选择也不仅限于美学取向、技术和经济的考虑,同时牵涉了政治取向:对美国歌舞片的讨论往往针对它的商业化取向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说,表面上有声电影面临的选择是再次成为戏剧附庸还是承继默片从而发扬电影特质,实际则牵涉更关键的美学取向、意识形态及地理政治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刘与郑对电影特质的讨论都超出了电影的物质基础及艺术形式,而牵涉到观影、情绪、政治功能。在这里因为篇幅缘故,我不再详述。⑦这些讨论让我们意识到左右翼或软硬电影的主张者,尽管意识形态上有差别,同样存在现代主义的美学倾向和对美国电影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这些主张与苏俄和欧洲现代主义有声电影理论颇多交接。在近年来对刘呐鸥电影理论极有必要而可贵的重读和肯定中,学人们对他的肯定却往往停留在他对电影特质论的阐发,而对电影特质作为历史的话语而非天经地义的本质缺少根本的反思。放在重提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语境中,这种重读更增加了媒体进化论的色彩,与刘呐鸥本人对进化论的反思造成反讽。 如果说有声电影的出现使得电影与戏剧再次挂钩并对电影特质论提出了相当的挑战,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有关戏曲电影的讨论中,电影特质与戏剧的关系则变得更为复杂而突出。这是我考察的第三个历史时刻。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戏曲电影的繁荣,在《中国电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新剧报》等论坛上,电影和戏剧界的专家们对戏曲电影的命名和美学选择讨论激烈,引出了电影、戏剧和戏曲间诸多问题的集中讨论[16:174-189][17]。先就戏曲电影的命名上,专家们已经显现了对戏曲与电影间的不同侧重点。对于当时较普遍的“舞台艺术纪录片”这一称谓,电影导演王逸认为拍摄舞台纪录片应忠实并服务于舞台演出,不可随意更改主体、人物处理及表演形式,并要尊重戏剧演出的假定性[18:1-5]。⑧张骏祥则强调舞台艺术纪录片不必拘泥于对舞台表演原封不动的纪录,而应适应电影特有的表现形式,“从场次编排到剧情穿插,细节描绘,从唱词到动作,都允许有所更动。”[19:15]⑨张骏祥认为应克服对传统戏曲表现形式的保守心态,将其看成“不断发展着的一种独特的、卓越的民族艺术形式”,而不是“凝固了的古董”[19:17],并提出用“民族歌舞片”取代“舞台艺术纪录片”这一“意义含混的头衔”[19:16]。徐苏灵则提出用“戏曲艺术片”更为合宜,较折衷而具体地分析了拍摄中如何解决戏曲与电影表现形式的冲突[20:23-34]。⑩ 在这些讨论中,虽然各家对戏曲电影在戏曲和电影的关系上持不同态度(电影应服从于戏曲,超越戏曲,或与其调和),但对探讨的根本前提却存在共识:电影与戏曲属于两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前者写实,后者则象征写意;前者的演出强调与生活逼真,后者则风格化程式化;前者用实景,后者则通过演员虚拟化的动作、音乐和观众的想象营造戏剧环境。换言之,电影与戏曲最尖锐的冲突体现在戏曲的假定性上,而假定性最充分表现在戏曲演员身上:戏曲表演的程式性、象征性,使得电影的实景布景与演员的虚拟化动作产生冲突,镜头和剪辑又破坏了舞台演出的完整性。这些根本的差异,决定了戏曲电影面临调和二者的两难和矛盾。 在这些讨论中,电影特质论以电影特殊的表现形式现身,但与我上文考察的前两个时期比较却呈现了新的现象。电影与戏剧的二元对立,因为戏曲的出现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其一,如果说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以默片为基础的电影特质的阐发强调电影的动感和对时空的灵活组织,从而显示了其超越舞台有限时空的优越性,在50年代的讨论中,戏曲却因其假定性自然超越了舞台的时空:通过台上台下的共识、演员的虚拟性表演和观众的想象,戏曲的时空早就超出了舞台狭窄的一方天地而可以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其二,戏曲表演的虚拟动作与电影对现实的模仿产生矛盾。也就是说,电影与戏曲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和重复性。其三,以往对电影特质的叙述强调电影相对戏剧的优越性,而在戏曲电影的讨论中,面对电影特质和戏曲的特质(特殊表现形式),却出现了如何尊重后者的新命题。后者所代表的不光是一种媒体的特质,而牵涉到民族形式、大众的观赏习惯,及戏曲表演艺术家所留下的民族遗产这些举足轻重的问题。张骏祥提到大家在将戏曲搬上银幕时的畏缩心理,觉得戏曲是不能动的古董。在这些讨论中,很少有人论及戏曲独特的表现形式或电影独特的表现形式,这两个概念从何而来,为何在5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时刻使用得如此频繁,大家对戏曲与电影的共识如何形成。这一切,需要我们对20世纪戏曲假定性的界定及50年代中期60年代早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作一粗略的回顾。 王晓鹰认为假定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普及源于苏联戏剧大师奥赫洛普科夫于1959年发表的《论假定性》一文。此文翻成中文后,在中国戏剧界达成共识,原来俄文的“условностъ”的诸多译法(“虚拟的”、“程式化的”、“有条件的”)渐渐统一为假定性[21:48]。在50年代中期的戏曲电影讨论中,“虚拟的”、“程式化的”的确常常与“假定性”同时出现,但“假定性”这一词汇的使用已经相当常见,而且“虚拟的”、“程式化的”通常特指表演,而“假定性”则用于讨论戏剧尤其是戏曲的根本特征。(11)我认为对戏曲的假定性概念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1919-1925)。面对陈独秀等新文学带头人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普遍推崇和对中国戏曲的全盘否定,京剧评论家张厚载、马二先生(冯叔鸾)等人争辩戏曲的独特美学追求,强调其“假象会意”的特质及程式化的表演和唱曲相对于说白的独特表达方式。在五四时期,张等人的少数声音在1925年兴起的“国剧运动”中得到肯定。留美归来的余上沅、熊佛西、张嘉铸等人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启发,提倡戏曲的另类美学。针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特征,他们较系统地整理论述了中国戏曲的纯粹性和整体性,强调戏曲在服装、化妆、音乐上的独特夸张和唱念做打的统一。这种受现代主义影响挑战现实主义而对中国戏曲有意识的系统梳理和重塑,与中国戏曲在中西交流中日渐上升的地位平行。其中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京剧理论家齐如山合作,在戏曲理论和实践上将京戏逐渐符号化、系统化、纯粹化。由梅兰芳自1915年起对外交使节的演出到几次高调的出洋演出(1919及1924年出游日本,1930年远游美国,1935年游访苏联),将京剧提高到国剧的地位[22]。梅兰芳演出与西方电影戏剧理论的交融(爱森斯坦、梅耶荷德、布莱希特),(12)使得假定性成为京剧以至于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的标志。到1962年黄佐临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戏剧表演观具体比较,将舞台的假定性与中国的写意戏剧紧密联系[23]。 如果假定性成为中国戏曲特殊表现形式的核心话题,与中国现代性话语、传统与现代在中西语境的交汇息息相关,电影这一特殊表现形式的话题则因为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对蒙太奇和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多方译介、苏联电影和文化对中国电影的主流渗透,以及除苏联外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印度电影、日本电影)的引入变得日益普遍。自三四十年代刘呐鸥、郑伯奇、夏衍、洪深、陈鲤庭等人对蒙太奇理论的译介后,新中国建国后蒙太奇理论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电影人阮潜、史东山、张骏祥纷纷陈述电影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中重点介绍探讨蒙太奇理论和实践,同时将电影作为以反映现实为主体而拥有特殊表现技巧的媒体[24][25][26]。这些对电影特质的阐述同样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50年代初期电影制片国有化、电影发行放映检查体制化的过程中,电影理论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三大“电影建设”的目标之一;对以苏联为模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推崇导致电影人对电影理论和技巧,尤其是蒙太奇理论的深入讨论。这一切都使得电影特质论,也就是电影特殊的表现形式的讨论,逐渐成为毋庸置疑的真理。 由50年代中期升温的戏曲电影讨论,则出现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正式实施,电影和戏剧民族化的问题日益提上议事日程。这期间,话剧这一在戏曲电影讨论中隐身的戏剧形式也参与到民族化的讨论中。针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苏联专家在上海、北京等艺术院校的指导,由田汉提出的“话剧民族化”而引发的讨论促使话剧与戏曲交流。到黄佐临1962年提出梅、斯、布三种戏剧观时,已经将戏曲纳入民族性、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中。(13) 戏曲电影讨论中戏曲与电影特殊表现形式的矛盾,因此不只是媒体特征论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再书写媒体特征论的过程中,两种媒体间看似不可消解的矛盾,却展现了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电影理论实践与电影工业和政策的挂钩,而将戏曲放在了冷战时期尖锐的地理政治的中心。中国对苏联、西方在政治上的双重抵抗,在戏剧、电影、戏曲的美学选择上通过戏曲与电影特质的两难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地方主体性又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话语空间。 从这一历史长镜头反观在70年代末那一场“丢掉戏剧拐杖”、“戏剧与电影离婚”以促成“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27][28][29],则其中对电影特质论的复述已经不再让人陌生。对于电影改革的倡导者们来说,中国电影长期为戏剧,尤其是话剧的时空局限、表演风格和围绕戏剧冲突为中心的叙事结构所累。而电影在时空组织上的自由、蒙太奇手法以及声画蒙太奇,为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表达和创造方式。这些论点,如前文所述,早在默片和有声片时期已多有讨论。但与其将这些对电影特质的追求看成历史的健忘症或对电影特质的天真,同时将戏剧“化石化”的粗暴和无知,不如说这是以媒体特质为名义的政治宣言。在改革新时期,电影与戏剧工作者反思“文革”和十七年电影戏剧的实践,从而重新定位这两种最重要的公众艺术的社会意义。反抗戏剧的桎梏,更确切的说是在摒弃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影像往往与夸张的表演风格、模式化的镜语、灯光、冗长而教条的对话,以及围绕人物冲突的叙事模式,被当作戏剧的常态[30]。电影戏剧工作者为摒弃艺术的意识形态作用而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姿态——拒绝艺术的政治功能性而坚守媒体的“纯粹性”、“独立性”和“内在原则”。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讨论既坚持对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还暗含了对媒体进化论的肯定,并将这种进化论置入现代化话语中。放在今天新媒体的霸权话语中,坚持媒体特质论的观点富有反讽意味——它既迎合了新媒体之“新”,又为电影的消亡钉上棺盖。同时,在今天重读电影史,尤其对30年代电影理论的重读中,同样的二元对立和进化论的思想,为我们的重读制造了新的盲点,并回避了对我们自己话语立场的反思。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丢掉戏剧拐杖”平行的“影戏”理论的探讨所提出的另一种本体论看法。电影理论家钟大丰和陈犀禾将“影戏”看成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本土电影理论和美学。对两位学者来说,电影的“影戏”说将电影与戏剧类比,从而提升了早期电影的社会地位;同时,“影戏”说提供了一种本土的电影本体论。它以“社会功能”为核心,承袭“文以载道”的人文传统,将文艺看成道德教化和社会启蒙的工具,而与西方注重电影物质基础和艺术形态的媒体特质论大相径庭[31][32]。两位学者对“影戏”理论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一传统已成为一“超稳定系统”,阻碍了中国电影的进步和创新,从而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遥相呼应。但二者将“影戏”理论看成中国本土的电影本体学,却为我们提供了对电影特质多种界定的可能。(14) 在西方对媒体特质的理论探讨中,大家集中考虑的是媒体的物质基础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形式。早期电影理论特质的论述强调照相机的机械性及超出肉眼的观察能力(特写、广角、望远镜头等),而电影对时空的自由处理又与其成像的基本方式与剪辑和蒙太奇手法相关。电影研究之外,对媒体特质讨论较多的是艺术史。无论是Clement Greenberg强调现代主义绘画的内部和物理本质(绘画的本质是二元平面的画布)[33][34],Michael Fried提倡现代主义应建立在遵循并反叛艺术内在规律之上[35],还是Rosalind Krauss讨论媒体特质拥有物质基础(material support)和艺术形式的双重性[36],对媒体特质从社会效应层面的讨论很少有。Marie-Laure Ryan则提出将媒体从三方面定义:一是符号的,即通过不同感官(听觉视觉等)及使用编码来区分;二是物质技术的;第三是文化使用上的,即从媒体在不同文化和时刻的社会效应来定义媒体。这第三层定义往往并不与前两层的定义一致[37]。钟大丰、陈犀禾对“影戏”的再认识,可以看成是在这第三层意义上对电影特质的重新定义。尽管他们对这种本土的本体论持否定态度,回顾电影特质论在20世纪中国的历程,却让我们看到不同历史语境中,同一媒体的丰富定义与它参与社会的种种行为不可分割。 回到今天,研究电影与戏剧是否还有意义,应该怎样研究,电影与其他媒体的关系又如何?我的看法是,媒体本身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本质——媒体的技术物质基础、艺术形式和社会功用都在不断变化。强调媒体特质的理论往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充满丰富动机的前提下提出的。它参与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的功用,而不独立于这些社会功用之外。换句话说,媒体特质是一种话语而非本真本质,更不是亘古不变的东西。对媒体持开放的态度,认可新旧媒体的共存、共变化,才会让我们认识到新与旧的相对性、“新”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并深化对媒体进化论的敏感和批评。这样才能为我们拓宽电影研究提供可能。电影本身既是变化的媒体,它的变化也与其他媒体的历史交接密不可分。在本文的历史回溯中,电影是什么与戏剧是什么成为双重命题,相互界定,并与历史的大环境呼应。如果说研究戏剧与电影的关系在今天仍有意义,我们需要解决的,不光是二者的定义,而是将二者放进历史的空间中,并自问:对于电影与戏剧,我们真正想要知道什么? ①参见拙文:“Homecoming Diaries:Inhabiting and Dis-inhabiting the Theatrical in Postwar Shanghai Cinema,” in 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Ed.Zhang Yingjin.London:Blackwell,2012,pp.377-399。 ②欧阳予倩:《导演论》,原载于《电影月报》1928年第1、2、3、5、6期。 ③有关这两本书的详细讨论,参见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74-83页,第107-114页。 ④有关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对好莱坞电影灯光上的影响,参见Patrick Keating,Hollywood Lighting:From Silent Era to Film Noi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⑤刘呐鸥:《影片艺术论》,原载于《电影周报》1932年第2、3、6、7、8、9、10、15期。 ⑥“影片艺术学的定义如何……未曾确定。但是它的艺术上的特质却已经经过多数学者讨论研究过,自可知道。” ⑦关于媒体特质论、电影声音美学与软硬电影论的重新评估,可参见即将出版的拙著:Fiery Cinema:The 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 Medium in China,1915-1945,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 ⑧王逸:《谈舞台纪录电影》,原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12月18日。 ⑨张骏祥:《关于舞台纪录片向什么方向发展》,原载于《文艺报》1956年5月。 ⑩徐苏灵:《谈戏曲艺术片的一些问题》,原载于《中国电影》1956年11月号。 (11)如王逸提出:“由于舞台限制,戏剧有很强的假定性,观众来到剧场看戏,舞台上显示的一切,他们并不过分地要求真实;观众对于剧场假定性的反映生活是认可的,他们会按照戏剧的特性来感受剧场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王逸:《谈舞台纪录电影》,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12月18日,收入张骏祥、桑弧等编著:《论戏曲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第3页。 (1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融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影响关系。爱、梅、布对梅兰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用,以阐发他们在西方语境中发展的理论观念。 (13)当代戏曲专家傅瑾对黄佐临的戏剧观作了细致的重读,并对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作了极有见地的分析。见傅瑾:《三大戏剧体系的政治与文化隐喻》,《戏剧百家》,2010年第1期,第85-90页。 (14)对“影戏”理论的重新评估,参阅钟大丰:《是否有重谈“影戏”的必要性》,《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第44-46页。标签:戏剧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特质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电影理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有声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