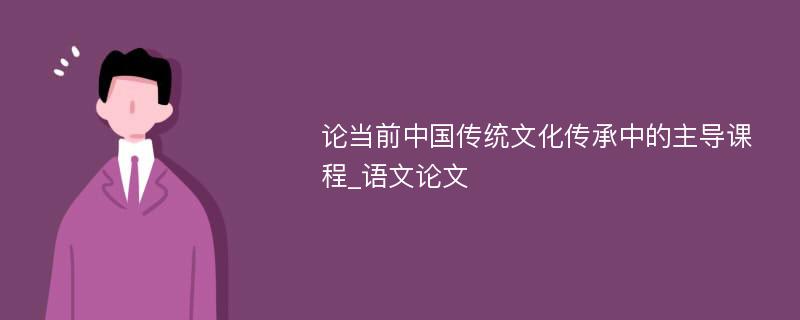
论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显性课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传统文化论文,当前我国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9)04-0058-04
学校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与课程设置不无关系,课程有显、隐之分,由于笔者已就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隐性课程因素做过详细论述,故本文仅对显性课程——“作为教师与学生教学活动之基本依据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材等”[1]——做一简要探讨。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学校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显性课程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课程计划中体现传统文化内容的科目比例、课时少;二是教材编纂中体现传统文化的篇幅、内容少。兹证如下。
一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笔者将按静态的课程计划和动态的课程实践两个维度来探讨那些能够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科目,具体包括语文、思想政治、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四科,鉴于外语学习在我国的深远影响,特将其单列予以专门讨论。
其一,静态的课程计划。从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有影响的历次全国中小学课程计划来看,① 上述四科课程设置及其课时安排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科目从原来的四科综合成三科。我国小学从1981年开始恢复中国地理课和中国历史课,1984年小学、初中坚持了这一规定,1988年开始将这两科综合成为《社会》一科,2001年将初中阶段的历史和地理综合成《历史与社会》一科。二是体现传统文化科目的课时比例偏少。20多年来,四科课时在总课时中的平均比例在小学为37.6%,初中为30.8%,高中为22.6%,并且这一比例还呈逐年下降趋势,如小学,三科全年课时从1984年的2278节次降至1994年的2074节次,所占总课时比例十年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三是具体学科占总课时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一点在作为传承传统文化主干学科的语文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该科在小学的课时总量从1984年的1938节次降至1994年的1666节次,在初中则从1981年的872节次降至1996年的280节次,分别减少了272和592个课时。四是上述四科事实上所占的学科课时比例比课程计划规定的还要低。因为,上述历史、地理的课程比例在国家课程计划中是包括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人文地理在内的,并且,除国文外,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都被安排在某一个特定年级就终止。如中国历史,在1996年以前,该科通常在被安排一学年或三学期的课时后就结束,此后学生便不再进行中国历史的学习,1996年后我国开始在高一安排中国历史,但其内容也仅限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地理则仅限于义务教育中的初二年级就结束。
其二,动态的课程实践。从笔者最近调查的各10所中小学2005—2006学年度的课表情况来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各学校在具体课程的设置上,此四科周总课时数要比国家课程计划规定的高,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家课程计划中传统文化科目、课时少这一特征;二是在高中阶段,几乎所有学校从高二第一期起就开始分文、理两科,且分科后的理科班数量要远远大于文科班。如湖北省巴东一中,高二12个班中,文科班为4个,湖南省道县二中,高二13个班中,文科班为5个,重庆市万州新田中学,高二12个班中,文科班为4个,平均比例为1/3。
其三,从课程设置中的国语、外语的比例来看。我国在国语、外语课程设置上的一个明显特征便是外语课程设置比例过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语科设置在年级上呈下移趋势。从中小学来看,1981年的《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一般学校,凡不具备合格师资条件的,不要勉强开设外语,即使具备师资条件的,也要经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在四、五年级开设”,后在1988年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二十四个学科教学大纲(初审稿)》中又明确将外语课程的设置放入初中阶段,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2001年,之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规定从小学低年级开设外语课,且作必修。二是外语科在课时上呈上升趋势。从中小学来看,我国从1981年至1992年的历次中小学课程计划所秉持的都是国语略高于外语的指导思想,之后,外语课时逐步攀升,2001年的新课改,国语、外语周课时比为4∶4,已完全持平。三是在上述两种趋势下,外语科在小、中、大学中的考核上呈从严趋势,外语作为各级各类升学的必考科目并决定是否录取的事实,已众人皆知,毋庸赘言。
二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笔者将主要探讨上述四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套教材内容的变化情况,而对建国前和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教材则存而不论。②
其一,相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传统文化内容进入到教材的篇幅总量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单位时间、空间内的文字表述总量不足。如《中国历史》,初中四套教材的文字总量分别是33.5万、32.9万、94.1万、55.7万字,若按3000年计算,描述中国历史的文字每年分别为11.7、10.6、31.7、18个字;若按5000年来计算,则每年分别为6.7、6.8、18.8、11.4个字,换言之,用来描述每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只用了不到12个汉字,显然,这是不够的。又如《中国地理》,四套教材总文字量为14.8万、17.2万、22万、29万字,按960万平方公里计算,描述每一万平方公里的文字分别只有0.15、0.17、0.2、0.3个汉字!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几个字而已,然而,文字的数量是体现内容的重要载体,没有一定数量的文字作保障,是难以充分了解方圆几百万平方公里、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基本情况的。二是单位时间内学生学习的内容总量不足。如《语文》,在初、高中6年中,四套教材给学生每年提供的学习内容分别为32.7、21、36、29.5万字,学生每天的阅读量为825字;《中国历史》四套教材给学生提供的学习内容每年分别为5.58、5.48、15.6、9.28万字,平均每年为8.98万字,每天的阅读量为249个字,如果抛去教材中日益增多的插图,学生的学习内容还远不到这个总量。
其二,相对于各科具体教材而言,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明显不足且有减少之势。如《语文》,在我国1978年以来的初、高中各四套《语文》教材中,涉及传统文化的课文平均所占比例为24%,其中最低的为19.5%(初中第四套)。在1992年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材共计12册的333课中,其中关涉传统文化内容的只有60课,占18%,除“两小儿辩日”、“刻舟求剑”、“神笔马良”等几则传统故事之外,几次小学语文教材改革都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又如《中国历史》,1980年规定“中国历史的古今比例,古代和近现代各占50%”,1986年规定“古代占3/5,近现代占2/5”,而1992年则进一步规定“古代部分为2/5,近现代部分为3/5”,至此,近现代部分超过古代。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1994年还减少了中国历史课的课时,并将部分内容进行了删除。再如《思想政治》,该科不仅在形式上没有过多变化,如1980年初一到高二的思想政治课分别为“《青少年修养》、《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1986年分别为“《公民》、《社会发展简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常识》”,1996年只是将高中三年的政治课更名为“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而且其间体现传统文化的内容也不多;自1980年明确提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知识武装学生,提高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来,在1988、1993、1997年等历次改革中均无多大变动,其教学目的和方式体现了较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以政治说教代替德性养成色彩。相对而言,《中国地理》的情形可能会好些,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在小学阶段,关于人文地理的内容过少,基本为空白,这无助于提高学生对祖国各地传统风土人情的了解;二是在中小学的《地理》教学中,我们错误的做法是先让学生学习《世界地理》,然后再学习《中国地理》,如从1988年到2001年的第二、三、四套教材中,都是将《世界地理》置于《中国地理》之前学习的,这一现象有悖于自孔子和夸美纽斯以来的“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等教育原则。
其三,就教育内容的选取而言,各教材的编写及内容体现形式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系统的掌握。其表现在:一是教材在内容设计上的结构化、逻辑性、层次性较差,不利于学生知识的系统掌握。从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教材变革来看,一个总的趋势是各科在内容上,已打破原有的“一(一)1(1)”模式,而实现了拼盘式的模块课程,这一教材设计模式在提供给学生看似简单的块状内容之后,不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框架体系,难以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同化到自身的认知结构中去。这一点,在历史教材中尤为突出,为此,有学者指责《历史课程标准》,认为“它是对历史内容的切割”、“无能恢复学校历史教育的生命力”[2]。二是教材在内容体现上的媒介化、娱乐化、连环画化,不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许多教材中的插图与彩色铜版纸交相辉映,让人打开教材便会不自觉地想起早些时候的幼儿连环画书,据笔者统计,1996年后的两套《中国历史》教材中,其插图比例在总页数中分别占到了71.5%和80.5%;而在最新的高中《思想政治》中,插图比例也占到了67.2%。笔者虽未对其他教材做类似统计,但在翻阅过程中发现,这是新课改后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几乎每页都有插图的现象,除了让学生感到新奇之外,实际上对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并无特别助益。笔者以为,文字类教材不同于其他教育内容的根本之处便在于其文字的表述性,而非媒介的娱乐性,因为单就三维生动性而言,文字教材无论如何也难望媒体项背,为考虑并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而在小学低年级采用这一形式是必要的,但到初高中后仍采用这一形式,则会适得其反。
三
以上我们对学校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不力的显性课程因素做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那么,如何通过显性课程来加强学校教育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其一,在课程目标上,应充分挖掘并体现传统文化因子。首先,在纵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逐级内化到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当中。就学校而言,关键是如何将课程目标、教学目标予以细化量化和如何挖掘非人文社会学科传统文化因子两个问题。就前者而言,课程目标的陈述不能过于宽泛笼统,教学目标的陈述则应越细越好。譬如,“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的鉴别能力”作为一般目的尚可,但作为课程目标就过于概括,而像“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的鉴别能力”作为课程目标不错,但作为教学目标则失之宽泛,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参照美国课程学专家伊劳特(M.R.Eraut)提出的“课程目标的密度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这一课程目标密度公式[3]。就后者而言,虽然我们不能像中世纪的教会学校那样,在数学教学中,将“1”解释为唯一的神,将“2”视为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两重性格等[4],但在教授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点时,却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美,在讲解宇宙万物现象的物理现象时,大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天人合一”。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如何体现,还有待我们的学科教学法专家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其次,在横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分别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的方式纳入到各具体学科领域之内。如《中国历史》一科,不仅要明确要求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所要掌握识记的基本史实,还要培养其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明的认同;《语文》一科,不仅要规定在单位时间内古典诗词美文阅读背诵的数量,还要使学生由此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丰厚博大,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科学》一科,除却基本的科学知识之外,也应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精神等有所了解。
其二,在课程结构和类型上,应调整并增加传统文化的学科和课时比例。首先,在课程结构上,应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改变当前我国人文社会学科比例偏低的状况。我们应当调整并相对增加中小学现有课程设置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学科的科目比例,确保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对半开的比例,还可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在中学增设“家政”一科为必修,并把当前我国的“思想品德”在中小学分别转换成“生活与伦理”、“公民与道德”两科[5]。其次,在课程类型上,应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灵活处理不同课程类型和教育教学模式。在小学阶段,应在学科课程和必修课程的前提下,侧重活动、隐性课程的开发和挖掘;在中学阶段,则应以必修形式的学科教学为主,同时设法结合不同地域特征新增不同学科课程科目(如在初中可设置地方历史和地理,在高中阶段可结合历史、地理课设置人类学课程等),另外还应适时安排一些活动课程以拓展教育渠道,但不宜开设过多探究课程。
其三,在课程内容和教材的编写上,应扩充并加深传统文化知识素材。首先,在课程内容上,应该扩充和加深传统文化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不仅要将那些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知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选入教材,注意课程内容的基础性,还要使所选内容与当前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注意内容的贴近社会生活性,如,思想政治科应选取那些能够部分抑制当前过分功利化、个人化的传统伦理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中国历史科要选取那些与当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史实,等等。同时还应注意学生的理解能力,在篇幅和内容上应短小精悍。其次,在教材编写上,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编制形式,确保不同阶段的不同学科在教材编制上能有所不同。如,语文一科,应遵循螺旋式、心理顺序编制原则,在小学阶段应该由简到繁、由易入难,且配以文言译文;历史一科,应采用直线式、以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顺序来组织其内容,不能因为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爱好而人为删除历史教材中的一些结构性的标题序列,另外,初中开设过的中国历史,在高中阶段也不能简单地重复,而应在内容上予以实质性的拓展;思想政治一科,应采用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理发展的特征,按自身、家庭、他人、国家、社会逐次拓展的方式来进行编制;地理一科,应该按照由近及远的拓展原则,在课程设置顺序上不能先世界后中国。
注释:
① 下文引用的相关文字及数据未作特别标明,均来自于《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历史卷》、《思想政治卷》、《语文卷》、《地理卷》(课程教材研究所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及《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通知》(教基[2001]28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全国使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和各学科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的通知》(教基函[2001]3号文件)。
② 分析的四套教材均为人教版,分别是:《中国历史》第一套指“初级中学课本”(1988-1992年版);第二套指“九年义务制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1992-1995年版);第三套指“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中学教科书(修订本)”(2001-2002年版);第四套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2001-2006年版)。《中国地理》第一套指“初级中学课本”(1988-1992年版);第二套指“九年义务制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1992-1995年版);第三套指“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中学教科书(修订本)”(2001-2002年版);第四套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2001-2006年版)。《语文》初中第一套教材是指“初级中学课本”(1981-1983年版);第二套指“初级中学课本”(1987-1988年第二版);第三套指“九年义务制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2001年版);第四套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2004-2006年版)。《语文》高中第一套教材指“高级中学课本”(1987-1988年第二版);第二套指“高级中学课本(必修)”(1990-1991年版);第三套指“全日制普通高中课本(必修)”(2003-2005年版);第四套指“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