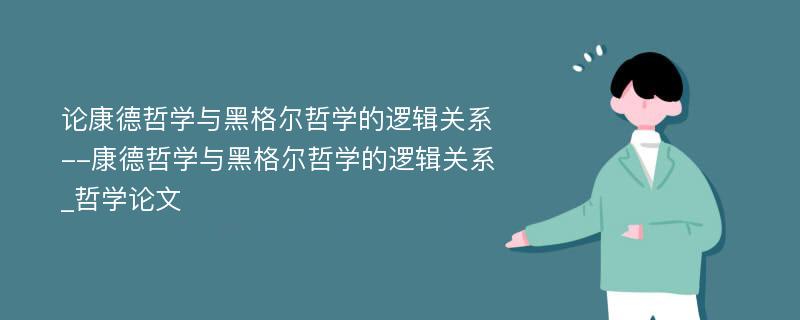
论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关系——The Logic Relation Betwee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andHegel,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康德论文,哲学论文,逻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关系象他们哲学之间的时间关系一样,黑格尔哲学是后康德哲学,表现为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本文试图在首先确立康德哲学在一般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史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探讨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应有的逻辑关系。
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所构成的哲学史,实际上就是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史。形而上学是早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立的,它指一门以超越感性事物的、比感性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形而上学(即他所谓的“第一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有的有”)或存在本身,其核心就是实体的存在;根据本体论的观点,本体论所研究的本体也是“存在”、“有”。所以,形而上学的对象和本体论的对象是相通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也是相通的。
在形而上学家看来,形而上学的对象既是最高的认识对象,又是最终的价值对象,作为最高的认识对象,它是至真的对象,把握它便可以获得绝对知识;作为最终的价值对象,它是至善的对象,把握它便可以具有最圆满的道德。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至真的对象,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便是认识这个对象,以获得绝对知识;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至善的对象,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同时又是(从道德上)追求这个对象,以达到最圆满的道德。从形而上学要认识至真的对象这个方面看,形而上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逻辑方法,在康德以前,主要表现为以直观公理为基础的、以矛盾律为主导的理性演绎法(或公理推导法);从形而上学要追求至善的对象这个方面看,形而上学的方法又应该是一种(道德上的)信念方法。因此,我们如果要从对象、任务和方法三个方面来确定古希腊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话,概括地说,形而上学的对象就是“求真”和“求善”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用逻辑和信念的方法来认识和追求真与善相统一的实体。
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学家那里,所谓善就是关于真的知识,因此善就是真,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就是知识”为形而上学家们广泛接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目的因和形式因,即真与善;而这个目的也就是表现为事物秩序或秩序的安排者的形式,因此,目的因同时也就是形式因,善同时也就是真。近代形而上学的第一位重要代表笛卡尔非常重视伦理学,但他明确肯定伦理学是一门科学,他说:伦理学“是一种最高尚、最完全的科学,它以我们关于别的科学的完备知识为其先决条件,因此它就是最高的智慧”〔1〕。 斯宾诺莎则完全承袭了笛卡尔的这种观点,他宣称哲学的目的就是追求至善的生活,但又为至善的品格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2〕因此, 虽然我们说形而上学的意义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但从实质上和从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上看,形而上学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或者干脆不如说就是“求真”;具体地(也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用理性演绎的逻辑方法去认识实体,寻求关于实体的绝对真理,其结果或目的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具有绝对确定知识的“科学之科学”,成为“科学的女王”;这种目的达到了,“求善”的目的也就自然达到了。
形而上学的意义从其确立之日起,就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就是说,形而上学要想成为具有绝对知识的“科学之科学”,必须以完成形而上学的任务即真正认识实体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外在的、无限超越的宇宙实体,从感性经验出发无论如何认识不到这个实体,而实际认识又必须从感性经验出发,因此,形而上学难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家特别是近代唯理论哲学家解决问题的典型方式正是如上所述的理性演绎法:无须凭借经验,单凭人类理性即可认识实体,并据此演绎出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实际上,这是一种独断论。所以,当西方近代哲学着重研究认识论问题时,不仅唯理论自身暴露了理论困难,而且也遭到了经验论的打击,特别是遭到了休谟的彻底批判。这一切使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时,形而上学已由“科学的女王”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妇人”(康德语)。
二
面对形而上学的危机,康德意欲通过转换形而上学的意义,来挽救形而上学这门学科。他指出:“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在它的每一部分上也都必须是科学。”〔3〕这科学不是或然的, 而是普遍必然的。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唯理论)的“独断论”就是在未预先研究理性能力的情况下假定理性是超越经验范围的,从而滥用理性。为了避免“独断论”,他发起一场思维革命,即预先研究人类理性能力,以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批判”为基础来建立新哲学,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批判哲学”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就是要寻找或判定在人类认识能力和理性能力中有什么是先天的、普遍必然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条件、范围和界限。康德称自己的批判方法为“先验的方法”,所以他的哲学又称为“先验哲学”。
康德对旧形而上学意义的转换首先表现在通过对人类理性的批判考察,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他指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超验的自在之物(宇宙、精神、上帝)的本质,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学,即它的对象是内在于人类经验自身的理性能力,是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的原理,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原理、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便是发现这些原理和规律。形而上学的任务又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实现的,由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人类理性先天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它的任务是发现这些先天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所以,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就是康德所称的“先验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批判哲学”的方法。这样,康德就基本改变了旧形而上学的意义。
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转换还表现在:他把“求真”和“求善”分开,把本体(实践)和现象(理论)分开,把旧形而上学的实体对象(加上“自由”)转换为两种信念,从而打破了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形式的绝对主义,并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落实到人的问题的研究上。
康德在把人类理性、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原理、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作为他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的同时,认为人类理性(纯粹理性)可以有理论方面的运用,也可以有实践方面的运用。从人类理性(纯粹理性)的理论方面的运用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科学知识、认识可能的先天形式,如空间、时间、范畴等先天形式及其原理,它们先于经验且仅对经验有效;因其是科学知识、认识可能的先天形式,所以自然具有真的含义。从人类理性(纯粹理性)的实践方面的运用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先天的道德规律,是内在于人心中的使先天道德规律成为可能和保证最高道德对象及理想可以成立的理念(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因其是道德规律的根据和最高道德对象及理想的条件,所以自然具有善的含义。这样,康德就在人类理性之内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对象,且保留了形而上学的真与善的意义,由于形而上学的对象划分为理论与实践,真与善两个方面,所以,形而上学的任务和方法在总的、统一的原则下也一分为二,“形而上学划分为纯粹理性思辨使用的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实践使用的形而上学。因而,要么是自然形而上学,要么是道德形而上学”〔4〕。
自然形而上学研究纯粹理性的思辨使用,从而研究经验世界的形而上学法则。经验世界是现象世界、事实世界,它受制于自然的必然性,所以自然形而上学要研究关于事实上出现某事的规律,它告诉人们“对象”是什么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因此,自然形而上学研究认识理论。康德的认识理论表现为人类理性以其先天固有的知识原理和知识形式能动地整理经验内容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知识和人类知识对象同时形成的双重过程,既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经验)知识,又产生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经验)知识的对象(现象)。它分为感性的、理智的和理性的(狭义的)三个层次。康德认为,认识不能超越现象范围,人类的最高认识能力理性如果要认识现象世界之外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那就不免产生“幻相”和谬误。在康德看来,“物自体”即“灵魂”、“宇宙”、“上帝”,它们不过是“理念”即超验的、没有任何实在对象与其相应的主观自生的概念,如果将其作“综合统一的”活动,作为“学术的信念”,它便有引导我们不断扩大现象知识,形成越来越完整的经验科学的积极作用。道德形而上学研究纯粹理性的实践使用,从而研究伦理世界。伦理世界是本体世界、价值世界,它受自由规律(自律)的支配,所以道德形而上学要研究“应当”的规律,它告诉人们行为“应当”如何。因此,道德形而上学研究实践(道德)理论。康德的实践理论要求人们的行为仅仅出于尊重先天的道德律而遵守道德律,并以“至善”即德行和幸福的统一为最高道德目标。在康德那里,“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是实现“至善”而必须“假设”的三个保证,它们是三个可以无限趋近的本体对象,实际上是三个道德信念。道德信念和认识领域的学说的信念是不同的,所谓“学术的信念”是一种类似于实践判断的纯理论的思辨判断,根据学说的信念,我们也可以相信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但学说的信念本质上并不是实践的信念,它缺乏稳定性,“我们常常会由于所碰到的种种思辨上的困难而抓不住它”〔5〕。“至于道德的信念,那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这里行为是绝对必然的,就是说我们一切都必须遵守道德律,这是绝对必须的。”〔6〕
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家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理解,即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一种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形而上学的知识是绝对知识,通过形而上学,我们可以达到至真至善,建立高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在西方近代早期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康德提出“学说的信念”和“道德的信念”,具有打破旧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的重要意义。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应该研究人,研究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在康德看来,人不仅是手段,而且自身就是目的;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首先是实践理性,所以人是精神的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它有着绝对的自由(自律),因而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不是对真理的认识论,以往形而上学所说的本体只是现象,真正的本体领域应该是关于道德的人的领域,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就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寻找真正的本体。这样,康德就通过考察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确立了新的意义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总之,尽管康德哲学存在种种缺陷,但由于康德把求真与求善分开,把形而上学的对象由外在的、超越的对象变成内在的人类理性自身,把本体论落实到对道德的人的研究上,并在某种意义上把认识真理和道德追求看成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系统(尽管其中包含了不可知论),所以在一般的形而上学(从而也一般地在哲学)的发展史上,与旧形而上学以及以往哲学相比,康德哲学不仅表现为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且标志着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就是康德哲学在西方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
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康德哲学是其源头,黑格尔哲学是其终结。如果我们从逻辑关系来考察这一首一尾的哲学,它就存在两个层面,表现为两种逻辑关系。我们先看第一种逻辑关系。
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层面看,康德哲学走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就是黑格尔把康德哲学中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系统化为唯心主义辩证法以解决近代以来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克服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走向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和可知论的逻辑过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重要特征是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他不仅把本体与现象、求真与求善、理论与实践二元化,而且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二元化。在他那里,思维和存在的最根本的对立表现在作为经验来源的物自体与作为先天的认识能力和知识形式来源的“自我”之间。认识起源于经验,而经验是物自体刺激感官的结果,所以,物自体对于人类认识而言不可缺少;认识还起源于先天的认识能力和思维形式,先天的认识能力和思维形式以人类自我意识为基础,而人类自我意识不过是人类进行认识必须先假写的主体即“自我”。“物自体”不可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由它刺激感官的结果;“自我”不可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用来作用于经验内容的先天认识形式。作为由先天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加工经验内容而形成的“现象”,实际是“观念化”的东西,正是它,既是认识对象又是认识结果。主体和客体,物自体与自我是二元对立着的不可知的东西。所以,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重要特征是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然而,这种导致了不可知论的二元论,却明确了近代认识论所讨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使它们以典型而清晰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为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解决二者的统一问题提供了前提,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正是沿着康德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条线索展开自己哲学的逻辑进程的。
(二)康德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中表述了意识的能动性思想等其他一系列辩证法观点,这又为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发挥康德哲学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的主体辩证法因素,形成系统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提供了基础。黑格尔正是借助辩证法,来克服康德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论与实践等等的二元论,以及由二元论导致的康德哲学的不可知论,以达到绝对知识,建立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的体系的。
第一,康德批判哲学在限制人类理性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理性的能动性,认为“自我”或“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不仅可以积极地形成知识,而且可以引申出自然界的规律(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的这种意识能动性的思想成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基础。因为黑格尔就是用它来形成具有能动性的实体,并通过描述实体的辩证运动来阐述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
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维的辩证法,其重要内容是“对立面的统一”、“不同诸规定的统一”的学说,亦即矛盾学说。对此,康德的形而上学也有初步的阐述,因为康德在批判哲学中重点阐述了对思维范畴的批判,并在自己的范畴表中,用三分法代替了传统逻辑的二分法,在其四组范畴的每一组中,使前两个范畴(分别构成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基础)互相对立,再用第三个范畴进到前两个范畴的统一和综合,这样,康德形而上学中的每一组范畴都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统一,形成了一个正、反、合的逻辑关系。黑格尔很赞赏康德对思维范畴采取“批判”的作法,认为一切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对自己所运用的范畴采取批判的态度,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他还认为康德对范畴的“三分法”本能地暗示了概念的运动。同时,康德的“二律背反”明确地表达了矛盾的不可避免性的思想,而且康德哲学中还存在着诸如思维与存在、本体与现象等一系列以典型而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矛盾着的对立面,这些都对黑格尔的矛盾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黑格尔说:“康德……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及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进步。”〔7〕不过, 黑格尔反对象康德那样停留在诸如本体与现象的外在对立上,也反对康德把“二律背反”看成是主观思维的矛盾,并且只举出四对矛盾。他认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世界万物的本质。黑格尔认为,只要我们不坚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是在“非此即彼”中看到“亦此亦彼”,那么我们就可能打破康德形而上学以及经验论、唯理论哲学中一对对相互对立范畴的僵硬的、外在的、静止的对立,而将它们理解为内在的对立,并达到它们的统一。这样,就既可以扬弃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片面性,也可以不象康德那样陷入物自体的不可知论,从而把形而上学变为科学。
第三,在绝对唯心主义和概念的辩证法的相互结合中,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实践“活动”的思想也为黑格尔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提供了某种启发。在近代早期哲学认识论中,唯理论哲学家和经验论哲学家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实践是被排斥在外的,或顶多当作科学认识的实验手段。康德的形而上学虽然把实践理解为纯意志活动,理解为道德活动,但他毕竟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并把它与理论(认识)理性相对立并视为比理论理性更高的东西。在一般的意义上,黑格尔肯定了康德对实践理性问题的提出,但他不满意康德对实践理性内容的规定仅停留在“应当”阶段的作法,认为“应当”和“实际”不应该是外在对立的,而应该是内在统一的。在狭义的认识论的意义上,黑格尔则认为真理性的认识(即他所谓的“理念”的认识)是在“生命”的基础上,经过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两环节来完成的,这两个环节是对立面的统一,这种统一是通过实践活动达到的,只有实践才有能力达到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继而达到绝过理念(绝对真理)。所以他指出,实践的理念比认识的理念更高,它既象认识的理念一样具有“普遍东西的资格”,又具有认识的理念所没有的“绝对现实的资格”。当然,实践在黑格尔那里,归根到底是逻辑理念运动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现实的感性活动;它所达到的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归根到底也是客观被主观所统一,而不是主观符合客观。
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唯心主义辩证法,但是,黑格尔正是依据这种唯心主义辩证法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并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以建立自己的辩证唯心主义一元论的哲学体系的。在黑格尔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中,“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8〕。 “实体就是主体”是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它既体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原则,又体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的辩证法原则。黑格尔认为,实体就是“绝对精神”,它是唯一客观独立的存在,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基础;同时,绝对精神又是主体,即它是能动的、自我辩证发展的。正因为它的辩证发展,它才真正起到实体的作用,宇宙万物正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认识自己和辩证发展过程的产物。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全部体系所表述的就是“绝对精神”能动地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由于重视实践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了辩证法的武器,确实较好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也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克服了旧形而上学的危机。因为在它那里,这种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这样,黑格尔哲学中就包含了很多发展并超过康德形而上学的地方,也为解决康德形而上学的一系列矛盾提供了可行的道路。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后康德哲学,标志着哲学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当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
四
我们已经看到,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层面看,黑格尔哲学是后康德哲学;但是,从一般的西方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史的层面看,黑格尔哲学就是前康德哲学了。康德面对旧形而上学的不可克服的危机,通过重建一种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来打破旧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以挽救形而上学这门学科;而黑格尔并没有沿着康德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在旧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继续解决认识论问题,特别是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并由此重建旧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所不同的是,他采用了辩证法的方法。所以,在他的哲学中,“求善”仍然寓于“求真”之中,旧形而上学的对象和任务仍然被坚持着,认识实体、追求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仍被视为哲学(形而上学)的目的。
(一)黑格尔批判了康德关于本体(本质)与现象的二元论,否定了康德以现象为(自然)形而上学的认识对象的做法,恢复了旧形而上学的本体对象。黑格尔的本体对象就是绝对精神,就是理念。对于绝对精神、理念,我们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规定:从“实体就是主体”这一命题中,我们首先得到关于绝对精神、理念的两个规定:⑴它是客观(绝对)唯心主义的概念。⑵它是辩证法的概念。绝对精神、理念的另外两个规定是:⑶绝对精神、理念是一种客观思想,纯粹概念,而以一种客观思想、纯粹概念作为世界的本体(本质),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对象是一种(绝对)真的对象,是一种绝对知识的对象。这一点,黑格尔说得很明确,因为他指出,哲学的对象就是真理;而且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哲学对象真理就是绝对真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说明、展示、追求这种真理的“科学”,因此,绝对精神、理念是绝对真的对象就成了绝对精神、理念的第三个规定。⑷黑格尔把伦理学、道德学说作为科学的一个领域,把善纳入真的领域,认为善属于真的知识。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绝对精神就是上帝,即上帝也正是哲学的实体对象。黑格尔说:哲学与宗教“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9〕。由于上帝“全知”、“全善”,所以黑格尔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至少有这样两层含义:其一是哲学的对象是真的对象,同时又是善的对象;其二是这种真善与统一的基础和核心是真,善就是真,因而上帝就是真理。
在黑格尔关于实体的四个规定中,后两个规定表明了旧的意义的形而上学对象的内涵;而前两个规定就其属于绝对唯心主义一元论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来说,它既反对了康德的二元论和现象主义,又反对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总之,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是绝对唯心主义辩证法条件下的真与善的统一,它是绝对真理、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这样,17世纪形而上学的主要意义即它的对象的意义便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复辟。
(二)黑格尔的哲学的任务自然地受到黑格尔的哲学的对象的规定。既然黑格尔哲学的对象是真与善的统一,那么他的哲学的任务就既有对对象的认识方面,也有对对象的追求方面。在他那里,哲学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对象的运动轨迹的考察,使对象从自在状态到自为及自在自为状态,从不自觉状态到自觉状态,认识到自己就是绝对真理,认识到自己就是通过发展过程而实现了的、把发展道路上的诸阶段都纳为自身环节的、包含了诸规定于自身之内的全面而具体的真理。但是,黑格尔并不认为哲学认识是达到“永恒的和真理的观念和确定性”的唯一道路。他在《小逻辑》中指出,那种认为哲学认识是达到“永恒的和真理的观念和确定性”的唯一道路的看法,例如认为不懂得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证明就不能信仰上帝存在,乃是混淆了哲学上的反思和其他一般思想的结果。其实,要达到“永恒的和真理的观念和确定性”,除哲学认识外,尚有其他的道路,例如宗教,宗教用表象的方式把握和信仰上帝。然而,尽管如此,黑格尔认为,由于哲学是以概念,以思维形式来认识真理、把握理念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真理的形式,绝对精神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才能以适合自己的形式认识自己,哲学是把握真理的最高形式。对于作为宗教的对象的一般真理,哲学也“必须证明从哲学自身出发,即有能力加以认识”〔10〕。
哲学的认识任务总是通过哲学的认识方法来实现的,正是方法上,黑格尔超越了他以前的形而上学。在哲学的认识方法上,黑格尔认为哲学的认识方法就是哲学的认识方法,它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方法的特殊性。对于旧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和康德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黑格尔都表示不满,作了认真的分析与批判。黑格尔说:“……真理不仅应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应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11〕正是辩证法才是解决思维与存在统一问题的关键,才能使哲学掌握绝对真理,把哲学变成“科学之科学”,所以,“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12〕。由此出发,“正确地认识辩证法是极关重要的。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13〕。而掌握辩证法的实质就在于:“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肯定中把握否定,在否定中把握肯定”。
(三)虽然在方法上黑格尔哲学超越了它以前的形而上学,但是,在运用方法的结果上黑格尔哲学又回到了康德以前的旧形而上学,回到了旧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为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提供了前提,但是他的哲学本身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因为第一,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归根到底是思维、主体内部的统一,其过程是思维、主体产生存在、客体又将其统一于自身的过程。第二,即使在黑格尔那里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不是思维、主体内部的统一,而是现实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也不可能是本体意义上的统一,黑格尔哲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即他不可能在他的哲学(形而上学)中一劳永逸地获得绝对知识。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在本性上是不相容的,所以黑格尔唯心主义最终窒息了他的辩证法。按本性说,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黑格尔“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14〕。然而,为了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强行结束了他的哲学的辩证发展,认为自己的哲学就是绝对真理。这样,他虽然用辩证法的思维框架代替了旧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最终仍象旧形而上学一样主张绝对主义,认为形而上学的知识是绝对知识,形而上学是“科学之科学”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黑格尔哲学因其辩证法而使其定位于后康德哲学,但是,由于康德在旧形而上学面临危机时转换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打破了旧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其形而上学的理论也包含了很多新的超越旧形而上学的内容,所以从一般的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史的层面上看,康德哲学处于比黑格尔哲学的更高发展阶段,因而更接近于现代西方哲学。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关系应是评价康德哲学的历史地位的重心,而我国长期以来则着重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逻辑来研究康德哲学。所以,加强研究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康德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便显得十分重要。
注释:
〔1〕笛卡儿:《哲学原理》, 见《笛卡儿哲学著作集》(英文版)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2〕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21页。
〔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8页。
〔4〕〔5〕〔6〕R·M ·哈钦斯主编:《西方世界伟人著作集》(英文版)第42卷,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1952年版,第246、242、 242页。参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680、680页。
〔7〕〔9〕〔10〕〔11〕〔12〕〔13〕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1、37、41、93、176、177页。
〔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标签:哲学论文; 康德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哲学家论文; bet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