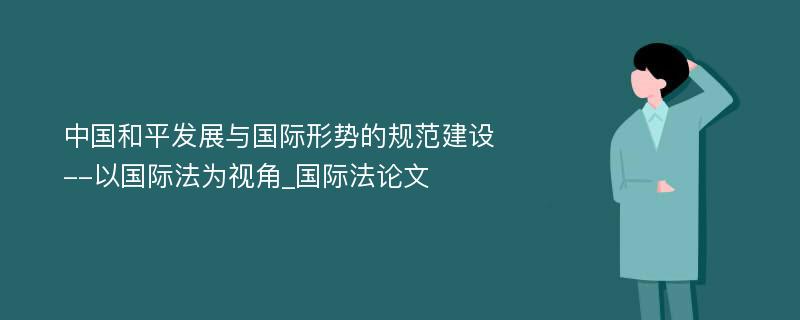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现状的规范性构建——基于国际法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规范性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和平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12-07]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8)03-0015-10
一 国际现状:一个有待澄清的概念
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时常将现状与和平划等号,①在回答中国是否是一个“现状国家”这一问题时,总是存在有意或无意的预设,往往使被讨论的客体沦为一种异类。卡尔·施密特指出,“困难的问题根本不在和平……问题只是谁来决定,和平具体讲的是什么……问题始终是:谁做决定?”②汉斯·摩根索将现状定位于战后的和约安排,主要处理战后领土及占领军安排问题,这样现状就变成了外交术语。在他看来,现状与国家政策相关,“现状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对立面,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确保权力分配有利于自己。前者在于确保某种战后的权力分配,而后者在于改变那种战后的不利安排。③奉行现状政策的国家赋予现状道义上的正当性,进而给其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如“和平”、“国际法”就是恰当的意识形态术语,它们掩盖了其真实的动机——追求权力。④摩根索对现状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施密特对现状与和平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实质: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决定现状的实质内容,但这往往是历史悲剧的前奏。鉴于目前中国也成了这种话语的客体,所以本文对现状-国际现状做以下界定,旨在不使“现状”成为因人而异的概念。
国际现状就是一种国际秩序,它通过国际法律秩序来界定。这种国际法律秩序并不是虚拟的,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际现实。⑤在本文中,国际现状的合法性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因为合法性对于国际社会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⑥合法性之于国际社会的功能在于强调规范的作用,能对国家行为进行限制。此外,国际秩序中的合法性程度直接同该秩序的稳定相关。⑦在国际社会缺乏类似国内法强制秩序的情况下,合法性给予行为者一种服从规范的义务感。⑧在本文中,国际现状的合法性通过国际法来界定,即如果国际现状的内容是符合国际法规范的,那么该国际现状就是合法的。之所以通过国际法来界定国际现状的合法性,是因为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在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同意。⑨共同同意就意味着广泛的立法参与,国际法就能广泛反映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因而赋予国际法规范合法性,就会增加服从的动机而非违反的激励。⑩在这种框架下,考察中国的和平发展同国际现状的关系问题,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国际法规范。
二 国际现状的规范性构造:以国际法为内核
在多数时候,国际现状往往以政治语言出现,模糊性正好能满足某些国家的政治目的,因而也往往不去界定国际现状到底是什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国际现状是从有利于美国力量施展的意义来解释的,尤其是军事力量格局以及它在全球的战略部署状况。美国可以频繁提及“国际现状”一词而不作解释,中国一般会困惑于国际现状这种模糊的提法。历史的教益在于,国际现状必须从其合法性来界定,对于关注国际现状的任何一方都必须如此,而不是单方面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而变化的。(11)
(一)国际现状的规范构造
“现状(status quo)”在语义上是指“事物的既存状态(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相关的衍生用法尚有“此前现状(status quo ante)”、“战前现状(status quo ante bellum)”。从法律角度来看,现状是由法律规范确立的秩序,是一种结果。现状因其规范内容才具有合法性。
合法的国际秩序是由国际社会政治力量所塑造的,“在更广、更深的意义上,法律就是政治。法律是由政治活动者通过政治程序,为了政治目的而制订的。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无不是政治力量的结果,法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也取决于政治力量”。“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规范表述……国际法反映了国家间体系的政治主张。”(12)但是,在政治力量与国际秩序合法性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政治力量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但合法性是对追求国家利益的政治力量的限制。国际法反映国家间体系的政治主张,其前提是国家间的利益协调,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所以,在近代国际法的形成阶段,“大国之间的合意是当时的国际法的基础”。(13)在当代,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大国对国际法的立法仍然具有相当的主导权,但随着联合国成员国的构成变得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国际法也就具有了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基础。如果以此来理解国际现状,那么国际体系的政治力量所决定的国际秩序就是国际现状。从合法性角度看,国际体系的政治力量如何决定国际秩序?从近代国际体系诞生到现在,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在当代,国际现状的规范性内容是国际体系成员广泛承认和同意的秩序安排,而国际条约和经过长期的国家实践所形成的习惯国际法最能反映这种广泛承认和同意的意思表达。(14)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现状就是通过国际条约及习惯国际法所构建的、能反映国际社会成员广泛同意和承认的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和效力在于共同同意。(15)国际现状的合法性就表现在具体的国际法规范上:如果一种现状是由国际法规范所决定,那么它就是合法的。
但是,同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国际现状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不同,国际法意义上的现状在各个领域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域的政治力量尚未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因而尚未构建一种国际法律秩序,因而国际法意义上的总体现状并不确定。是否存在以共同同意为特征的、国际法律秩序意义上的现状,这需要看是否存在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这种政治现状并非一成不变,其未来确实充满不确定性,但并不排除未来国际社会成员在这些领域中达成普遍性的、广为接受和同意的国际法律秩序。
(二)从战争和约到共同同意
摩根索谈到国际现状的时候,他认为所观察到的历史确实就是战争和约。广泛的承认和同意是当代国际法的要求,但在近代国际体系诞生之初和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所谓国际现状,主要是欧洲列强在战后通过一系列和会上的条约所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乌特勒支和约》、《维也纳和会》、《凡尔赛和约》都是战争结束时达成的和约,是对战争结局的安排。(16)这些战后条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战胜一方施加于战败一方的,这种战后秩序安排被战胜国单方面视为合法秩序,并没有确立一种满足普遍性承认和普遍接受的国际现状。相反,战胜一方总是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例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凡尔赛和约》实质上允许法国打压德国。(17)战胜国的这类单方面安排,造成国际政治现状其实极度不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现状的形成是在两条线上展开、发展的。其一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尊重和平、尊重人类的价值、惩罚反人类罪行的国际法规则;其二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普世性国际法律秩序的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条线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今世国际现状的基础和核心,尤其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承认的既存状态,这是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现状。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在行使“集体合法性”的政治职能,它在形式上解决了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18)
在当代,国际现状的本质在于其合法性,其来源于广泛的接受和同意,它具有一系列的法律后果。首先,国际现状不得破坏。在某些情况下,破坏国际现状会被联合国安理会视为对和平的破坏与威胁。其次,国际现状的合法性意味着破坏现状所产生的结果不具有合法性,也不会为破坏现状的国家增加任何权利,更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承认。联合国安理会第662号决议认定,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无法律效力并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这一非法情势不予承认。(19)最后,对于违反国际现状之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情势,责任国有义务恢复原状,这是国际法实践中确立的一般国际法原则。(20)
(三)当前的国际现状
国际现状的规范性内容是由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所确立的国际法律秩序,但鉴于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要在一般意义上说它们确立的国际现状是什么就可能太笼统,容易流于模糊,无助于阐释问题,所以下面从一些重要领域的国际法律秩序来理解国际现状。正如前面所述,这些领域中是否存在合法的国际现状,取决于是否存在有效的国际法规范。因此对下述领域之国际现状的分析,就是以国际法规范为核心。
1.人类生活的空间法律秩序
国际法被卡尔·施密特视为一种空间秩序,(21)而且是一种全球性的空间秩序。“地球(除极地区域外)的任何陆地几乎无不归属某国领土的一部分及在国家主权之下”。(22)主权国家的领土构成了合法的国际现状,任何武力使用、战争的行为不能改变领土现状。(2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整个海洋在法律上进行了分割,形成了不同的海洋空间:内水、群岛水域、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及海床。这些不同的海洋空间之法律地位各不相同,其中内水、群岛水域和领海属于国家主权区域,毗邻区属于非国家区域,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属于沿岸国家功能管辖区域,公海则属于国际共同体空间。(24)这些国际法规范确立的空间秩序就是一种最根本的国际现状,在当今国际社会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因为其能满足最普遍的同意和接受。(25)
2.人类生活之物质基础的法律秩序
伴随着空间法律秩序的固定,每一类型空间区域的财富归属随之固定,构成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1962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各民族及各国行使其对自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重申了此项内容。(26)一国对其领土上的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同国家的属地管辖权原则是一致的:“国家领土内一切人和物都属于国家的属地权威的支配”。(27)在20世纪末期,国家对其财富及资源的主权扩展至领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家对于开发大陆架上和专属经济区中的资源享有主权权利。
国际法上的“共有物”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出现了,后来月球和其他外太空被纳入国际空间秩序。至此,凡人类活动所能及的空间里,财富与资源归属的国际法律秩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这亦是根本性的国际现状,它同人类生活的空间秩序之确立同步进行。
3.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
国际现状的合法性还体现在国际社会成员一直强化这种合法性的意图和努力:通过国际组织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利益和义务的冲突、通过军备控制机制减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通过武装冲突的控制机制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来减少冲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此外,如果发生国际现状被取代的情况,那么应该由另一种合法的国际现状所取代,而且取代的过程也应该是合法的。国际组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军备控制条约、武装冲突法及人道主义法的功能就是规范国家行为,确保国际现状不至于被破坏,而且也确保现状的变化是合法的。
考察一国是否为所谓的现状国家,应该看其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规范,而且该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国际法规范的立法。在解释中国同国际现状关系时,笔者将这些国际现状的规范内容一般性地定位于二战后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国际法规范。
三 中国与国际法的关系——基于经验的考察
国际法反映的是集体利益,服从它有利于实现自己的利益,(28)就国际社会的总体而言,遵守国际法的历史记录良好。(29)尽管中国在接受和遵守国际法和规范方面的道路特殊,但经验表明中国之行为在符合国际法规范要求方面,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中国是自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通过战争而被迫纳入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背景成了中国制定国家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心理基础,如何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是影响中国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中的一个持久性因素。(30)国际法可以对强权政治进行限制,(31)因此,诉诸国际法规范来捍卫国家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外交政策特点,尤其是诉诸主权平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规范。在这个过程中,鉴于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中国根据自己对国际体系的理解,参与倡导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2)同时,中国通过对国际局势的评估来衡量国家利益,在投资、环境保护、争端解决、人权保护、武器销售和扩散等方面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国际法。(33)下面所涉及的三个领域是考察“中国非现状国家”这种先验判断是否成立的重要切入点,其中领土纠纷属于“空间法律秩序”的范畴,使用武力属于“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的范畴,要判断中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现状,这些都是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解决领土纠纷的模式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边界纠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弱变强,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行为是前后一贯的,即立足于当前领土实际现状、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接壤,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34)没有一起领土纠纷是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获得解决的。
中国同缅甸、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都是通过谈判达成边界协议。同越南、塔吉克斯坦、老挝、蒙古的边界协定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达成的,但中国都没有通过“改变现状”之类的手段来解决边界问题。直到最近,中国同俄罗斯通过谈判达成了边界协议,其立足点都是领土现状。关于中印边界纠纷,从事端之肇始,中国就一直强调在边界现状的基础上解决领土纠纷,主要立足点就是实际控制线,尽管现状和实际控制线对中国不利。(35)在中印边境冲突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很多时候都诉诸国际法支持自己的观点,(36)其行为符合国际法规范。(37)
当代中国在一般性观念上不但接受了近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石——领土主权不可侵犯,而且鉴于近代历史上一系列条约使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成了1949年后新中国的政治诉求,其国家政策一直谨慎、小心翼翼地维护国家主权。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关于主权与人权、人道主义干预关系的大讨论中,中国倾向于持一种更为均衡的主权观点。(38)从这一方面来看,对于既存的以国际法律秩序为核心的国际现状,中国倾向于维护而非颠覆。
(二)参与国际制度
在中国崛起和国际现状的关系上,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断:中国同大多数崛起的大国一样,最有可能寻求改变现状,即意味着打破现存国际法,主张新的国际规范。(39)中国对待国际现状的态度可以简化为对待国际法的态度,那么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况,二是中国缔结和加入的国际条约。就参与国际组织情况来看,1999年的一份研究统计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量增长很快,“中国的参与程度是美国的90%。而到90年代中期,参与程度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相对其发展程度而言参与程度已经较高。”对于中国军事力量起一定限制作用的军备控制条约,“在70年代初期,中国加入或签署的此类条约占其可参加数量的10%~20%。到9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85%~90%”。(40)
统计还表明,到2004年年底,中国缔结、加入的多边国际性条约为267件,2005年为12件,2006年为14件。(41)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对国际制度总体上呈现积极态度,这种态势一直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的时期,显著的表现是中国军费支出的绝对数量呈稳步上升的时期,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走向充满了高度关注的时期。(42)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接受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同中国发展是正相关的,这同改变和颠覆现状的判断相反。
(三)中国使用武力的历史和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使用武力的情况约为三次,分别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1年)、中印边境冲突(1962年)、中越边境冲突(1979年)。中印边境冲突是印度执行“前进政策”、单方面改变现状、其边境部队越过实际控制线导致的。(43)而且,短暂的冲突之后,中国仍然回到立足现状解决边界纠纷的一贯立场。(44)抗美援朝战争与其说是中国试图改变什么,毋宁说中国试图阻止美国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现状。中越冲突在形式上也是因为边界武装冲突而引起的,(45)这次所谓的例外不应该孤立地看,而应该放在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和越南军事联盟的行为严重挑战世界地缘政治现状以及1978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大背景来考察。这三次使用武力的结果,中国所寻求的维持和稳定边境现状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同韩国、苏联、越南、印度的关系都实现了正常化,接下来还就边界纠纷进行磋商,并达成了若干划界协议。一个可见的经验及趋势是,中国选择了立足于现状、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同他国的争端,不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纠纷,而且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同他国的总体关系,例如同中亚国家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11月4日),强调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其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46)这表明中国采取实际行动遵循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当代国际秩序中的宪法性原则。但可以预料的是,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下决定使用武力的条件,即不会放弃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量地参与、接受了国际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机制、制度,并以积极的态度利用它们维护自己的权利。
四 中国对国际法立法的参与
如前所述,国际现状之合法性来源于共同同意,是通过国际法的立法过程来表现的。国际社会的立法是高度分散性的。(47)在早期,国际法主要表现为国际习惯,如今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国际条约已经成为国际法立法的主要形式。在这方面,联合国机构以及诸多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在缔结国际条约方面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48)近年来,联合国安理会在反对恐怖主义、人道干预、核不扩散等方面的积极介入,在一片争议声中也被认为是立法的开始。(49)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法立法的程度也逐步加强。中国对国际法立法的参与是国际法发展进程重要的内容,这个过程同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力的迅猛发展是一致的,中国成为构建国际现状的重要力量。
但是,近现代国际法确实表现为欧洲国际体系规则在全球的扩展,中国真正能够以平等身份参与到这个国际体系并加入立法进程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全面参与却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1971年之后。这个参与过程开始之际,已经存在一套国际法规范,其对中国的利弊有赖于根据具体情势判断。因此具体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法的立法过程时,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中国如何对待已经存在的国际习惯和一般国际法原则?在国际法立法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同国际法规范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内立法同参与国际法立法、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涉及中国是否接受习惯国际法以及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志。第二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应对于自己不利的国际现状。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暗示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而是探究中国究竟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同意。这个问题没有一般的答案,只能依据个案分析,下面以中国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和加入WTO为例来说明中国表达其同意的可能模式。第三个问题不单纯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问题。诸多国际条约规定,为了履行条约义务,缔约国的国内法必须与条约一致,这就要求缔约国在国内采取立法行动。对中国而言,其国内的改革需求和制度建设同参与国际法立法、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要求正好契合。中国专利法的发展可以说明中国“入世”的努力、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义务同中国专利制度建设能够做到很好的协调。
(一)接受习惯国际法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力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参与国际制度呈现了积极的态势。(50)此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新的国家是否有权反对该国进入该体系之前就已成熟的规范?”(51)从新中国成立之时就面临严重的封锁,中国确实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对该体系的谴责,但其行为仍然限于国际法框架,尤其是诉诸主权、平等、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边境纠纷中,中国一再援引有关国际法来表明其立场,(52)这事实上是接受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国家的同意是国际法的基础,同意习惯国际法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些习惯国际法规范起源于欧洲,中国并没有参与其形成过程,但诸多的习惯国际法规范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石,是内生的规则。没有它,现代国际体系就会崩溃。不存在中国要颠覆它们的问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国是通过一系列西方列强强加的战争和条约体系而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守这个体系的原则,中国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和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中国自然地要借助该体系内生的基本规则维护自己在体系内的主权身份和地位,同时也维护了国际空间秩序的现状——诉诸主权独立、领土与主权完整原则是最集中的体现,所以中国加入了诸多通过条约编撰的习惯国际法,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一系列有关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
新中国成立后,其在外交关系中反复地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诸多亚非拉国家在事实上推动、实践了这些原则,中国尤其在双边关系中特别强调这些原则。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前已有的多种国际条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53)但中国特意强调它们,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在惨遭列强长达一百多年的侵略之后,当中国真正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社会中时,中国意在用此原则向国际社会表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需要真正的同意和切实的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认为是补充和发展《联合国宪章》所宣示的系列宗旨原则,并对后来的国际法律文件所宣布的原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54)
(二)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
二战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历史被视为沿海国海洋权利扩张同传统“海洋大国”、“远洋渔业国家”发生冲突的历史。(55)第三次海洋法大会中的斗争可以解读为发展中国家同现状国家(“海洋大国”)之间重新确立海洋秩序的斗争。海洋大国的海洋利益体现在维护现状中,如窄的领海宽度(3海里),更广泛的航行自由、通行自由和捕鱼自由,更为自由地开发海洋资源。海洋大国所维护的现状同沿海国扩展其海洋权利的意图发生了冲突,中国参与海洋法立法也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中国支持12海里的领海宽度,在外国军舰通过领海问题上,坚持要求军舰的通行必须事先获得沿岸国的核准和通知,1996年中国在《海洋法公约》的声明中再次重复了该主张。在大陆架概念上,中国从1974年就坚持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属性,(56)并在此后的海洋法会议上多次重申了有关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原则,1982年《海洋法公约》之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自然延伸原则。(57)此外,在毗连区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底开发、人类共有财产概念、国际海底管理局等问题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意见。(58)在海洋划界问题上,中国对中间线、等距离线规则持相当的保留意见,否认其作为有约束力规则的唯一性,主张“根据公平规则,考虑到各种因素和情况,通过平等协商,加以确定……中间线或等距离线是划界的一种方法,只有在符合公平原则的条件下才能采用。”(59)在海洋争端解决方式上,中国声明不接受《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所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这同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样。
中国在第三次海洋法大会上提出的种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的首创,在多数时候主要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张。(60)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挑战海洋制度的现状,并促成了有关部分海洋法中即时习惯法的形成和渐进发展,那么中国也参与了这种进程。这种对现状的挑战和变革通过国际法立法完成,满足了国际现状的合法性(共同同意)要求。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国际法的立法程序,表达了其在大陆架问题、海洋划界问题、争端解决程序上的意志,促成了国际海洋法新现状的形成。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情形却显示了另外一种对待现状的态度。当中国经济制度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开放的时候,其面临的国际贸易现状就是以WTO规则为中心的贸易秩序。同中国参与国际海洋法制定过程不同,中国没有参与上述WTO规则的制定,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意志和同意。中国可以选择在WTO体制之外开展国际贸易,通过双边关系来调整贸易关系。当然也可以选择加入WTO,通过多边贸易机制调整贸易关系。如果选择加入WTO,那么中国必须一揽子接受WTO规则,且必须改变国内法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地方。中国最终的选择还是加入WTO,接受世界贸易制度的现状,再修改国内相关法律以便满足WTO规则加给各个成员方的义务要求。中国加入WTO、接受国际贸易制度的现状还表现在它接受了在反倾销时对中国产品价格认定做了独特规定,这使中国企业面临外国反倾销调查和诉讼时的处境极为不利。当然,解读中国加入WTO不能局限在对现状不利或有利的二分法上,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加入者而言,肯定存在有利和不利之处,对现状的接受总体上应该对中国有利,否则无法解释中国“入世”的动机,更不能解读为中国先接受现状,等时机成熟时再伺机摧毁这种不利的现状。根据WTO中的立法机制和决策机制,单方摧毁是不可能的,除非自己愿意出局。相反,中国只能借助WTO立法中事实上的协商一致实践,在今后的贸易谈判中逐步变更不利的现状,也即通过立法参与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同意。如此一来,就同中国参与国际海洋法制定的性质一样了。
(四)完善国内制度以履行国际义务——以中国专利法的发展为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酝酿专利法是基于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61)1992年专利法的第一次修改,正值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制度启动之际,但此次修改专利法却是满足另外一个现实性目标——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创造条件,同时也为了履行中国在《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62)2000年专利法的修改面临双重目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专利法提出的标准。而加入WTO的隐含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制度,(63)如果专利法的修订能满足加入WTO的要求,那么专利法的修改也就能够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2006年,在中国知识产权局主导下,提出了2000版专利法的修订草案,纳入了若干TRIPS的规定和实践经验。
专利制度的源头并不在中国,一些相关国际条约就是在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反映了它们的知识产权利益。所以当中国在完善专利制度的时候,要面对知识产权的国际现状就意味着调整国家间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TO下的TRIPS等,但中国将专利法制度的完善和履行国际义务很好地结合起来,甚至相关国际条约都成为中国专利法知识上的来源。例如,2006年专利法修改草案纳入的TRIPS规则及其实践结果,实际上是WTO成员可以享受的权利。(64)中国在专利法立法中纳入WTO/TRIPS规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种立法路径同中国制度建设的目的一致——追求效率(鼓励发明创造、建立创新国家)和公正(保护发明创造);另一方面,这种立法路径为中国专利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知识上的来源和参照系。知识产权法律的其他部分,如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也都遵循了相似的路径。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点,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决定保护的方式和标准,但国际条约制度的制约使每个国家在建立相关制度的时候自由选择了约束。(65)这种国内立法和遵守国际义务关系的协调模式可望促进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立法。如果国际法所保护的利益同国内法所反映的利益高度一致,那么促使国内法同国际义务保持一致的激励就更强,这要求中国在国际立法进程中去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上述的论证表明,中国是一个国际现状的基本维护者。一方面,中国珍视现存的国际法律秩序所寓于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主动接受了既存的国际法律秩序,还积极参与了国际法的立法过程,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和同意,这个过程同中国崛起的过程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中国对国际法律秩序的接受、对国际法立法过程的参与行为促进了国际现状的形成。在既存的国际现状中,中国的遵守纪录良好;在国际现状尚待形成的领域,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现状立法者。如果一个新兴大国的确促成了权力的结构性变化,关键是要通过国际法的立法过程来处理这种变化,而不是通过霸权战争范式来思考和解决。(66)
五 结论
尽管中国对待国际现状的实际情况令人乐观,但本文中的这种规范框架和经验考察并不能消除某些西方学者心理上的不安情绪。例如,在讨论中国一美国力量变化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国家根据其相应的权力/力量大小,通过合作获取利益。若两个大小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为80:20,那么二者会通过国际性的合作,按照80:20的比例分配利益。海洋资源的开发就契合这种假设。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比如变成了60:40,那么弱小国家要求在现状下控制更多的海洋资源,最后收益的分配也应该为60:40。大国要么让步,要么诉诸战争解决问题。战争爆发的概率取决于对战争结局判断所依赖的信息的完备程度。(67)这个假设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权力同权利成正比例关系,但这个比例关系的假设很有问题。国际海洋法中的相关制度并不主要体现美国的海上力量,苏联解体后,美国海洋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但除了海底开发制度之外,海洋法没有因美国海洋力量的相对增长而发生相应的调整。(68)尽管如此,这个隐性的前提是世界政治学中的古典概念——心理影响力。它其实道出了另一个难题:权力同权利的比例关系不可能是固定的,因为权力是一个变量。国家力量消长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确实给现存大国带来了心理上的纷扰。尽管可能存在非零和的结果,但现存大国倾向于首先用非零和思维来看待权力结构的变化。(69)
当然,权力和权利的比例关系确实反映在某些制度性安排中,主要通过三种表决模式来体现。一是加权表决模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按照成员认缴的基金份额投票,而认缴的份额就是基于权力一力量的安排。二是平等表决模式,但制度的有效运作依赖大国的合作。如在国际海洋法立法和WTO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成员国具有平等的表决权,但如果缺少了贸易大国和海洋大国的参与和认可,这些制度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70)三是单位否决性表决模式,典型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些基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都以大国为核心,对大国的权力/权利关系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但是问题在于,仅仅强调作为现状的制度性安排,忽略产生这种现状的过程,那就很难有积极的思考结果。而这个过程就是立法,其根基在于共同同意,尤其是大国的同意。
在国际立法中,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基辛格根据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历史经验,认为大国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协调对于和平与安全必不可少。(71)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体系排除了某些大国,或某些大国没有参加,这导致了欧洲的结构性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无法在一个有效的框架内解决,从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全面参与了当前的国际制度,参与了诸多重大制度的立法过程,接受了国际体系中那些宪法性的习惯法,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存在本身也是国际现状的一部分。
注释:
①在讨论中国发展和国际现状关系的文献中,下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讨论:Alastair l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 Eric A.Posner and John Yoo,"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se of China,"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7,No.1,2006。江忆恩将国际现状同游戏规则(rules of game)做了隐性的类比,包括了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单方承诺,然后根据这些指标来考察中国行为。埃里克·A.波斯纳(Eric A.Posner)和约翰·尤(John Yoo)视国际现状为当然存在而未做界定,而且“中国非现状国家”在其文章中乃是一个先验性的判断。二者都倾向于将中国同美国发生冲突与否作为检验中国是否遵守国际现状的尺度,但得出的结论各异。
②[德]卡尔·施密特著,朱雁冰译:《现状与和平》,载《论断与概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③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 A·Knopf,1985,p.53.
④Hans J.Morgenthau,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101,pp.104-105.
⑤[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l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本文所用“合法性”的英文为“legitimacy” ,又译为“正当性”,与“legality”的意义不同。关于Legitimacy和legality的比较,参见刘毅:《“合法性”与“正当性”译词辨》,http://www.xschina.org/show.php? id=9539。“Legitimacy”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的含义是指“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型也依赖于自身在事实上的被承认”。参见[德]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本文中是在“被认可”、“被承认”这种意义上使用“Legitimacy”。出于习惯,本文仍然用“合法性”而不用“正当性”。
⑦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12.
⑧Thomas M.Franck,"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2,No.4 ,1988,pp.705-759.
⑨[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美]路易斯·亨金著,张乃根等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⑩Jonathan I.Charney,"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7,No.4,1993,pp.529-551.
(11)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13.
(12)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5页。
(13)[德]沃尔夫·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吴越等译:《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4)这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条约能够表达广泛的承认和同意。《维也纳国际条约法公约》第52条所谓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所订立的条约尽管具有形式上的要件,但不能认为是表达了当事方的同意,也是无效的。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2页。
(15)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第8页;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36~37页。
(16)参见[德]马克斯·布劳巴赫著,陆世澄、王昭仁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29页、第288~289页。
(17)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69.
(18)Inis L.Claude,Jr.,"Collective Legitimization as a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0,No.3,1966,pp.367-379.
(19)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不承认原则就是对破坏现状产生的不法情势做出反应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参见王铁崖:《论不承认主义》,载《王铁崖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461页。
(20)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国家责任法》草案第35条及其报告人评注,参见James Crawford,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Introduction,Text and Commenta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13 。
(21)Carl Schmitt,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Jus Publicum Europaeurn,New York:Telos Press,Ltd.,2003,pp.42-49, p.172;[德]卡尔·施密特著,林国基、周敏译:《陆地与海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6页。
(22)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113页。
(23)在16~17世纪,占领能导致主权的变更,到了19世纪,国际法理论逐渐承认占领不转移主权这样的理论。“战争占领中主权不转让”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参见[法]夏尔·卢梭著,张凝等译:《武装冲突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5页。
(24)这是一个海洋空间法律地位的简洁总结,参见沃尔夫·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546页。
(25)参见沃尔夫·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504~555页。从法律形式角度考察人类社会的空间秩序,该书中第五章“国际法中的空间”是很好的总结。
(26)[英]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等译:《国际公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1~592页。
(27)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328页。
(28)Jonathan I.Charney,"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7,No.4,1993,pp.529-551.
(29)“在国际法存在的四百年中,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严格遵守的”,见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295;“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候遵守所有的国际法原则和几乎所有的义务”,见Louise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47。
(30)参见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发言,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122页。
(31)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p.293.
(32)Carl Q.Christol,"Communist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Strategy and Tactic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21,No.3,pp.456-467.
(33)James V.Feinerman,"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Rogue Elephant or Team Player?" The China Quarterly,No.141,1995,pp.186-210.
(34)《2006年陆地边界工作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wjzdtyflgz/zgldbjgz/t311577.htm。
(35)参见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讲话中提及的边界问题主张,见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30页;Byron N.Tzou,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Boundary Disput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0,p.104。
(36)Arthur A.Stahnke,"The Pla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ese Strategy and Tactics:The Case of the Sino - Indian Boundary Disput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0,No.1,1970,pp.95-119.
(37)Byron N.Tzou,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Boundary Disputes,p.107.
(38)参见周忠海:《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科索沃战争与国际法》,载《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46页、第163~168页;王铁崖:《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载《王铁崖文选》,第352~353页、第358~360页。
(39)Eric A.Posner and John Yoo,"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se of China,"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Spring,2006.
(40)[美]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
(41)《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tfsckzlk/zgcjddbty/default.htm。
(42)参见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报告“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2005年,第104~105页,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5/RAND_MG260-1.pdf。
(43)参见[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189页。
(44)参见1962年10月24日、11月21日中国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之际分别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45)张爱宁编著:《国际法原理与案例解析》,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46)英文本见东盟官方网站:http://www.aseansec.org/13163.htm,中文本参见:http://www.nansha.org.cn/documents/declaration_on_the_code_of_parties_in_the_South_China_Sea_Chinese.html 。
(47)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p.296-299.
(48)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73页。
(49)Paul C.Szasz,"The Security Council Starts Legislat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6,No.4,2002,pp.901-905.
(50)Suzanne Ogden,"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Policy," Pacific Affairs,Vol.49,No.1,1976,pp.28-48.
(51)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47页。这里借用新国家这个概念,应该从政治意义上的新生力量来理解。
(52)参见Arthur A.Stahnke,"The Pla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ese Strategy and Tactics:The Case of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0,No.1,1970,pp.95-119;陈体强:《中印边境的法律问题》,载《国际法论文集》,第88页。
(53)Ian Brownlie,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18-119.
(54)王铁崖:《国际法引论》,第226~233页。
(55)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118页。
(56)周忠海:《国际海洋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315页。
(57)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464页。
(58)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第30页、第465~466页、第467~471页。
(59)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第467页。
(60)王铁崖:《中国与海洋法》,载《王铁崖文选》,第416~425页。
(61)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节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sipo/zxft/dsczlfxg/bjzl/200701/t20070116_127294.htm。
(62)参见《专利法前两次修改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sipo/zxft/dsczlfxg/bjzl/200701/t20070116_127297.htm。
(63)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9条“价格控制”规定,“中国应允许各个部门所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并应取消对这些货物和服务的多层次定价的做法”;第15条“确定补贴与倾销的价格比较”第a(2)规定被调查的产品在制造、生产和销售方面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这些规定的隐含前提就是WTO成员方的经济活动被假定是市场经济。
(64)参见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第49条和第63条,参见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sipo/zxft/dsczlfxg/bjzl/200701/t20070116_127296.htm。
(65)TRIPS就为各个WTO成员方的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确立了一个外部限制条件,成员方的立法不能违反TRIPS规则。这在“印度专利案”和“加拿大药品保护案”中可以得到证实。参见张乃根:《TRIPS协定: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79页。
(66)罗伯特·吉尔平对霸权战争范式做了一个经典解释,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207页。
(67)参见Eric A.Posner and John Yoo,"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se of China,"第二部分之“security”内容。
(68)至于后来海底开发制度的变化,并非专为适应美国海洋力量的增强,而是务实性经济观念变化的结果。参见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132页。
(69)[美]纳兹内·巴尔马等:《没有西方的世界》,载《国际利益》,2007年7/8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8月1日。
(70)美国同《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尤其是美国对国际海底开发制度方面。参见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第131页。至于在GATT和WTO框架下的多次贸易谈判,欧、美、日三方总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控制议题的能力和谈判中把玩“联系战略”的能力,其实就是规则的制订和有效实施取决于大国的参与。
(7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4页。
标签:国际法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冲突规范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