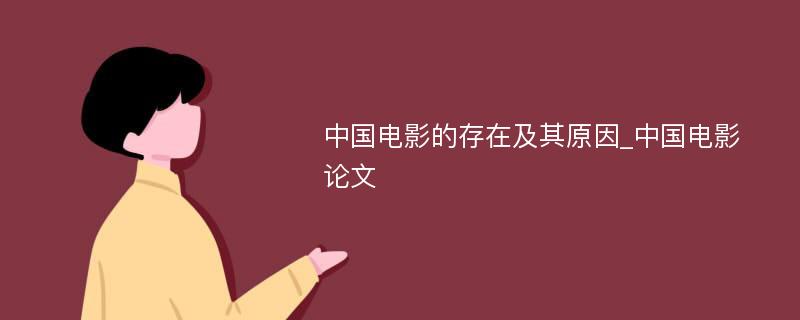
中国电影存在及其理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理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西洋影戏”到中国“电影”
在近代中国人的记忆中,电影最初是以“西洋影戏”的角色进入日常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来自异域的“影戏”虽然在外部形态上与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戏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新鲜事物。作为泊来品,它的传入,一方面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相伴而行的,另一方面无疑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这就使得外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放映活动明显地体现出“经济冒险”和“文化催生”的双重意义——从经济冒险的层面而言,它使经营者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投资风险之后,很快从中国人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从文化催生的层面而言,当观看“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种娱乐时尚的时候,中国民族电影的诞生也便因此而获得了必要的契机。
中国的民族制片业,肇始于外国电影传入9年之后的1905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老北京的著名实业家任庆泰(1850-1932),他在自己开设的“丰泰”照像馆的天庭里主持拍摄了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这是一部由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的纪录片。它的问世,一方面证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依然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整合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某种支持——指出这两点,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从《定军山》这一“文化事件”中,同样能够找到华夏文明为什么没有步巴比伦等其他古老文明之后尘的原因。
任庆泰的拍片活动由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而没能持续多久。1909年,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使得丰泰照相馆一蹶不振,而任庆泰所经营的其它实业竟也从此开始走向了下坡。电影需要文化的支持,但无疑也同样需要经济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而言,任庆泰在北京的拍片实践的终止,实际上于偶然之中体现了必然。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和近代经济的中心,上海为民族电影业同时提供了“精神气候”和物质上的必要保障。1913年,张石川(1989-1953)和郑正秋(1989-1935)利用文明戏的经验和在华外商的资本,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8年,中国当年最大的文化企业集团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活动影戏部”,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玻璃屋顶的专业摄影棚。自此开始,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集中产地,并因此而有“东方好莱坞”之誉。
从无到有的,不仅仅只是活动画面的生产,还包括一些基本术语的创设。1921年,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编辑陆洁(1894-1967),从友人信中的“教习”二字的联想中,把director翻译为“导演”。及至20年代末,中国人终于为自己确立了关于这门新兴艺术的最为基本的术语——“电影”。这些专业名词的创设,无疑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事物进行本质把握的一种东方式的智慧。
中国电影是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凭藉自己的智慧创造的关于中国的“电影”。从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就这样在经历了从短片到长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等诸种技术演变的同时,也不断以影像的方式,承载和表达着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好恶与思索、苦难与奋争、光荣与梦想。
民族身份
中国电影的早期历史,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将电影这一外来艺术形式不断加以本土化改造的历史。换言之,当中国影人一旦掌握了电影的基本语言技法之后,他们也便以越来越自觉的创作姿态,把本民族的审美意识融入到自己的银幕想象之中。在这里,我们至少应该提到郑正秋、蔡楚生和费穆的名字。
作为一位早年有着丰富的新剧(文明戏)舞台经验、深谙观众心理的爱国艺人,郑正秋的电影创作,曾经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影响。1923年底,由他编剧的《孤儿救祖记》,将提倡“平民教育”的旨意,寄寓在一个由不良的遗产制度造成的家庭风波故事之中;第一次为国产片带来了远远超过外来影片的营业效益和社会声誉。这部以热闹曲折的传奇方法和善善恶恶的道德评价见胜的影片,因商业和艺术的双重成功,成为民族电影草创阶段结束和初盛时期到来的一块界碑。10年后,郑正秋编导的又一部影片《姊妹花》,又在影坛掀起了新的狂飙。他依旧借鉴传统叙事艺术的经验,以富于对比效果的场景构思和朴拙的镜头语言,刻画了一对孪生姐妹的迥然不同的性格命运。这部“替穷苦人叫屈”的影片,创下了在首轮影院连映60余天的空前纪录。
郑正秋开创了民族电影“热闹型”的美学形态。但天不假年,竟壮年而夭。所幸其弟子蔡楚生出色地接过了接力棒。蔡楚生(1906-1968)于1934年编导的《渔光曲》,在剧作结构和控制观众的情感投入上,与4个月前首映的《姊妹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所讲述的一对贫苦的孪生姐弟的悲剧故事,再一次打动了习惯于看“苦戏”的中国普通观众,创下了比《姊妹花》还要多出20天的连映纪录。而他在40年代创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则更是将人物命运的传奇性、价值评判的伦理性,以及传统的编年历史叙述方式,与博大深刻的社会内涵统一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式的银幕史诗树立了杰出的典范。
如果说,郑正秋和蔡楚生是从平民视角来接受传统审美经验的滋养的话,那么,费穆(1906-1951)的电影创作,则更多带有传统文人的审美气息。十分可贵的是,作为一位现代儒生和电影上的“国学派”,费穆并不僵化。他在表达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同时,着意于探索“使用现代创作技巧”来“把握民族风格”。这种探索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1948年拍摄的《小城之春》。在这部以抗战结束后几位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感经历为叙事内容、充满内省精神的影片中,费穆将中国的诗、画、戏曲的美学精神与电影的时空技艺作了圆浑的嫁接,创造出一种富于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小城之春》是体现民族电影“冷隽型”美学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古典的,同时又是现代的,堪称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枚硕果。
从郑正秋、蔡楚生和费穆们的艺术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创作主体对民族身份的一种确认。而这种确认,正是电影本土化创造的关节之所以。
参与历史进步
在中国影人的主导观念中,电影从来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品;由于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巨大的动荡和变化之中,因此,在更多的时候,电影是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视听化的记录,是对于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是对基于人生经验之上的群体愿望的一种表达。在这种主导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电影从20年代的初盛期就开始形成了“参与历史进步”的主流传统。
20年代前期是五四新文化与封建旧文化激烈碰撞和角逐的时代。一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文化人,介入到电影创作的行列。他们把“为人生”、“改善社会”、“指导民众”作为理解艺术价值的首要出发点,从而不仅提高了电影的文化品位,而且也使得创作的旨趣与时代的潮流产生出积极的呼应。尽管也存在着某些不相谐调的声音,但从总体上说,揭露旧有社会体制的种种弊端、提倡个性解放、对弱者寄予人道主义同情,是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主旋律。
进入30年代,中国社会在外患内忧日益加剧的同时,面临了一种新的历史抉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兴电影运动”,凸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格调。夏衍、孙瑜、蔡楚生、沈西苓、吴永刚、袁牧之等艺术家,把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对大众生活的人文关怀以及艺术上的革新愿望结合在一起,从而相继创作出了《大路》、《神女》、《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传世佳作。此后,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中国的电影创作也进入了非常时期。相当一部分爱国影人奔赴大后方,他们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拍摄了21部故事片和近百部新闻纪录片。这些抗战影片,在主题表达上直接为战争服务,在形式选择上为图通俗化,因而无论是在前线抑或是在后方城市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宣传鼓动作用。与此同时,留在上海“孤岛”的爱国影人,也同样在“古装片”的创作中寄寓了可贵的现实讽喻精神。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不断高涨,进步影人再一次以人文知识分子的创作姿态,把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注入到对政治腐败和民生疾苦的表现之中。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有“新兴电影运动”的经验积累和八年抗战岁月的人生磨砺,中国电影在艺术上迎来了一个令人怀想的成熟和丰收的季节。在设备落后、资金匮乏、审查严厉、尤其是外国影片巨量倾销的艰难环境中,《八千里路云和月》、《天堂春梦》、《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相当数量的影片,却以厚重的思想含量和相应的视听语言运用,奇迹般地构成了民族电影史上的一个与时俱新的“经典群落”。
1949年以后的电影创作,从总体上说也依然继承了“参与历史进步”的主流传统。在新的时代氛围中,新中国初期的银幕作品,大多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普遍感受。在《白毛女》等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新旧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在《李双双》等影片中,我们又看到了对“善”与“美”的社会风尚的推崇。只是到了“文革十年”,银幕上的激情很大程度上变异成了对真实的背离。而当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到来之后,中国电影又从对人性、人情的正名开始,很快把镜头对准了前行的历史脚步。1979年出现的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从其深层来说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渴望现代化的一种折射。1980年问世的《天云山传奇》,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又以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而稍后问世的《血,总是热的》等影片,表达了对改革的强烈愿望;《黄土地》等影片,则希冀通过文化反思来汲取推动现实的力量。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越来越深刻的文化转型,中国电影也在这种转型中寻找着时代纷繁表象下的主导精神。它一方面以自身体制的改革参与着进一步走向深化的整个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在创作上不断克服浮躁,并力图以贴近百姓的银幕叙事,忠实地再现出新的历史变革中的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图景。从《焦裕禄》到《一个都不能少》,在寻寻觅觅之中,贯穿的仍然是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仍将一如既往推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
与世界对话
毫无疑问,中国并不外在于世界。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电影曾经在国际上“鲜为人知”。当改革开放为整个民族重新带来生机的时候,中国电影也在多元化的艺术探索中,真正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履。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中国电影的各种回顾展相继在数十个国家举办,中国影片也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亮相并屡屡获奖。世界在“重新发现”中国电影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新的认识。
自然,西方人士对“电影中国”也难免有某些文化误读。但中国电影毕竟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载体。应当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倒是:在由于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而使得不同的民族国家日益面临“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电影如何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民族身份?
“全球化”并非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冷静反思的问题,它或许将以牺牲文化的多样化为沉重的代价。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同的文化之间还极有可能产生更加剧烈的对抗。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平等的对话,才能保护各自的文化利益;也只有平等的对话,才能使人类免于更大的灾难并相处得更加融洽。
告别20世纪,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百年也将要走完。在未来的日子里,凝结着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经验的中国电影,有理由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产生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