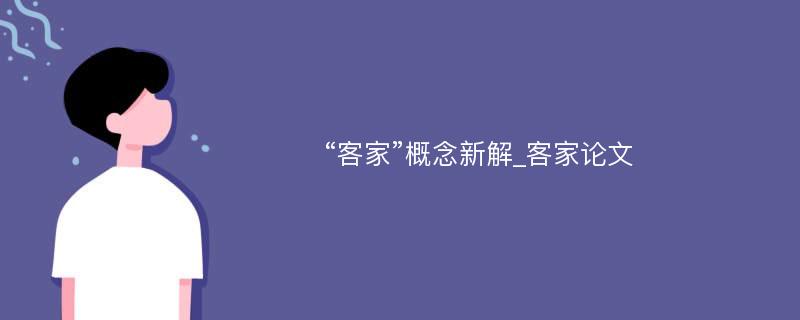
“客家”概念的新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客家”概念的诠释不宜生搬硬套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的模式。民系只是民族的地域性分支,是民族内部在民族共性覆盖下的具有相对差异的方言以及生产、生活习俗的人类群团。客家民系的形成,有一个自赣北至赣中再至赣南的“民系锻造”过程,没有江西特定的历史“温控”及“冶铸”过程,就不会有后来的客家。“客家”是与“土著”对称的名词,但在民系的称呼里却不是两个对称的概念。
关键词 客家 民族 民系 民系自觉性
一、引言
客家问题的提出已近一个多世纪,试图对“客家”作出解释的不乏其人。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的民系理论框架为客家的定义提供参照,人们遂各依自己的理解给出了形形色色、歧义丛生的表述。如国外就有一些研究者曾以“民族”和“种族”作为被定义概念的属概念。这种不具同一关系的概念表述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所抛弃。《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等辞书中的“客家”条目,内容大同小异,均以迁徙和地域作为定义概念的种差,基本上属发生定义,未能较好地揭示被定义概念的内涵和属性〔1〕。 李蓬蕊先生是当代的研究者中第一个试图用民族学的理论来定义“客家”概念的人。他说:“什么叫做客家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2〕相比之下, 李先生的表述较具科学性。其超出前人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指出了客家是民系而不是其他;二是第一次以语言、民俗及文化心态为定义概念的种差,注意揭示客家人的民系属性。严格说来,这个定义的本身还有一些瑜中之瑕。比如“历史原因”是否略嫌含混?“客家人是……的客家民系”是否失于定义循环?“客家语言”是否使用欠当?〔3〕都值得进一步商讨和完善。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民系),这一点在海内外的研究者中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往往脱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窠臼,用民族的“四个共同”来证论客家,从而混淆了民系与民族的区别,不恰当地夸大了民系的差异性,导致了一系列的误解和分歧。笔者认为,“客家”概念的科学定义,必须从民系理论的研究入手。不弄清什么是“民系”,就无法解释什么是“客家”。为此,笔者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 期发表了《民系理论的初步探索——客家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一文,就民系的属性、定义,民系生成与存在的原因,民系的区分标准,汉民族的分支,民系与民族、民系与民系的关系,以及民系的稳定性与变异性、吸收性与排他性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粗浅的探讨,试图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民系理论框架。文章对“民系”所给的定义为:“民系是民族的区域性分支,是民族内部在民族共性覆盖下的,具有相对差异的方言以及生产、生活习俗的人类群团。”这一界说及相关的全部见解,是本人诠释“客家”概念的基本理论支点。
二、“客家”的定义及内涵
通过对民系理论的初步研究,我对“客家”概念的认识开始明晰起来。如何进一步运用民系的理论来定义“客家”呢?依然是一个大伤脑筋的问题。姚公骞师曾给我提供过一条“三性”研究思路。他认为,客家概念的定义必须注意时间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即民系性)。“时间性”,就是要在历史的过程中动态地把握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变化;“地域性”指客家的分布情况,主要居地以及地理环境对民系性格的影响;“民族性”就是客家的民族共性以及作为一个民系存在的个性差异。按照这一思路,我将“客家”概念的定义表述为——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分支,其先民祖籍中原,自东晋至两宋之交,由于战乱等种种历史原因,陆续迁入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中,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比较独特的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稳定的民系。
这个定义包括了以下内涵:
1.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支系。客家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单立的民族。客家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祖先原本就是中原汉人,具有高度发展的汉族文化。南迁后与南方汉人及少数民族发生混化和变异,由于他们的迁徙属“板块转移式”,在聚居的特定区域内占有较土著相对的人口优势,并处于一个较高的文明层次,因而始终保持自己的族性不变,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他们的汉族意识反而变得更为明晰和强烈。他们的名称由一个他律的称呼转化为民系成员的自称,恰恰说明了他们对母族对祖籍的尊崇、依恋与自豪。
既然客家是一个民系,那么它便具有作为汉族成员的共同属性。它与其它民系的区别,仅仅是在历史因素、区域差异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量的差别。它在生产、生活、习俗文化上的诸多内容,必然同其他民系有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正如兄弟姐妹之间相貌难免会有若干相似之处一样,任何夸大性的描述与孤立割裂的研究都是不恰当的。因此,客家问题的研究必须纳入汉民族的历史范畴之中,结合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考察客家民系的形成与成因,并从民族共性的认识中去辨识客家民系的个性差异。
2.客家是由东晋以来历次战乱中被迫南迁的部分中原汉人演化而成的一支汉族民系。客家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的产物,并具有移民社会的种种特征,这从“客家”一词的语义中就不难看出。中原汉人的南迁,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徐人的南徙。江西境内较多徐器的出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客家的源流,从时间性的角度来说,笔者倾向于东晋至两宋之交,就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而言,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次:第一次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西晋永嘉丧乱,北方少数民族内移而导致大量的北方流民从秦雍(晋、陕、甘一带)沿汉水流域渡江至洞庭湖地区;从青徐(鲁、苏、皖)渡淮水、长江至太湖流域;从司豫(河北、河南一带)沿汝水而南,渡长江而至鄱阳湖地区,最远者达赣中和赣南山区,或沿江南下到皖南、苏南一线。第二次为唐中叶至唐末,由于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影响,再度引起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迁。罗香林先生及其后的许多研究者多注意唐末的移民运动,而对唐中叶的移民现象注意不够。《旧唐书·地理志》云:“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中唐移民进入江西的也不在少数。据《旧唐书》、《新唐书》及《元和郡县图志》的人口资料分析,隋大业至唐元和的二百年间,江西户口由8.5万余户猛增至29.3 万余户,比率为3.42倍。其中以“既完且富,行者如归”的洪州增长最快,为7.58倍,饶州次之,为4.56倍。第三次为五代至两宋之交。仅以江西为例,从元和至北宋崇宁元年近三百年内,人口由29.3万余户猛增至200万余户,为5.84倍。其中以虔州(赣南)最为突出,为9.37倍, 吉、袁、抚、信四州也增加了4~5倍以上〔4〕。毫无疑问, 这是大批北方人民进入江西的结果,不可能全是生育的因素。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徙,一步步地向纵深发展,最后推及现客家主要聚居的赣、闽、粤山区。
当然我们不能说东晋至隋唐的北方移民就是客家,但客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无疑要追溯到这一时期。笔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孕育肇始于东晋南朝,唐后期初具雏型,至北宋最终形成。这种判断与语言学界关于客家方言形成时间的推定也是基本一致的。周振鹤、游汝杰认为:“中唐以后这样大量的北方人民进入江西,使赣客语基本形成。而且随着北方移民逐步向赣南推进,使赣客语这个楔子也越打越深……两宋之际发生的由北而南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客家话最终形成。”〔5〕
此外,客家人举族而迁,武装移徙,群体特征的养成以及聚族而居、耕战结合、居室型制、习俗文化等许多人文事象也都可在魏、晋、隋、唐的北方汉族中找到渊源〔6〕。
宋以后,客家人还有过几次大迁,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客家原来的区域分布,成为当今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民系。但是宋以后的迁徙已是准客家的移动,同客家民系的形成关系不大,因而没有必要作为概念的内涵写入定义项。
3.客家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赣、闽、粤三省结合部的山区中形成、定居并由此扩散各地的一支民系。客家是北方人口迁徙的产物,但单纯的迁徙不能解释客家的成因。“客家”原本是土著的对称,举凡离开本土,寄居他乡的人户都可称为客家,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民系特称的概念,必须同那种广义的“客家”严格区别开来。确实有人曾把祖籍中原的古代名人统统称为客家,笔者对这种无视民系特殊内涵,抹杀民系差异的“泛客家论”提出过批评〔7〕。 确凿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原南迁的汉人有不少已构成或融入南方的其他民系,并没有全部演化成客家。客家还是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形成的一支民系,有必要作地域性的分析与限制。
罗香林先生所列三十余个纯客住县(有出入,但大致可信),二十九个分布于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中,因之不少研究者都称这一地区为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俗语中也有“无山不客,无客不山”,“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说法。即使在其边缘的深圳地区,广府人和客家人也有极其鲜明的区域分界。广府人多数居住于广深铁路以西的平原地区;客家人则聚居于以东的丘陵山区。江西三面环山,其北带江,江西的客家人也依山为行止,主要聚居于赣南以及赣东、赣西的丘陵山区。因此,我们可以说客家是在山区形成的民系,客家人是由北方平原居民演化而成的南方山民。
赣闽粤交界处是华南地区地势比较高阻的大片山地,南岭山脉自贵州向南盘亘,下至湘赣交界处,构成五岭山脉与九连山山脉,闽赣交界处又有连绵起伏的武夷山。“高山(相对的)大岭,触处皆是,连县的西北为萌渚岭分支,郴县南部为有名的骑田岭,南雄北境,则有号称‘岭外第一关’的梅岭(又称大庾岭),和平北境九连山,则绵亘更阔,东连龙川、河源,南连博罗、增城、龙门、从化,西连翁源、乳源,北连江西龙南,峰峦巍峻,地势高阻;寻邬东部有萧帝岩,西南入兴宁为大望山,东北出福建永定为博平岭,折西经长汀至连城为虎忙岭。”〔8〕东晋以来的北方流民大多循赣江及赣东之旴江流域逐步向这片山地移徙。
尽管在宋以前这一地区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域,但却是流民驻足生息的理想天地,也是客家民系赖以形成的特定空间。这一带山旷人稀的居民布局,使南迁北民在平原富庶区域无从立足时,易于克服阻碍,建立一个个小型的家庭“殖民地”,并逐步散布各山谷坑坳,形成压倒土著的绝对优势。丘陵山地间无数零零碎碎、大大小小的相对适于农耕的河谷盆地,为习于农作的中原人提供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起码条件,而不必痛苦地放弃世代承传的物质生存方式〔9〕。重要的是, 山区重峦叠嶂所造成的封闭性以及交通的艰阻不便,也使外力难以入侵,统治势力鞭长莫及,从而避免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大程度的居民混化变异与组合。邓迅之先生分析过南方五个民系的形成情况,他说:“越海系蕴酿的时期虽较其他四系为早,然其特征的形成,则与五代时吴越楚王马殷的建国有相当的关系。此外如湘赣系的形成,则与王审知的称王八闽有相当关系。客家民系的形成虽与五代时候各个割据政权无涉,然依其在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奥、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各个政权的融化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和习俗,而与其四周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别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对照起来,便觉二者有点不同,因而他人遂觉其为别一系统,而其人也自觉其是另一系统,这样在意识上和观念上便成了客家这个民系。”〔10〕“纯粹自体”未免言过其实,但赣闽粤山区处于诸割据政权的夹缝之中,有一个相对自在安定的时期,避免了“政权融化势力”的干预与分割,则是事实。南迁的北民正是在这片“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崇山峻岭之中,厮守着他们的故土风习与祖宗语言,在山外世情发生急剧变异的情况下处于相对静态;同时又在自然选择、民族融合以及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推力下,去调整、改变、重新整合自己的心理素质,从而发展成汉民族中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11〕。
客家民系形成于山区,但北民南迁入山的并非只此一支,为什么它们不能成为客家?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客家的形成与聚居地特指赣闽粤交界处的山区,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特定空间。其次,客家先民不是一步跃入这一地区,而是由北而南一站一站地逐步移入其间的。这些因素在客家民系属性演成的过程中必然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因此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我们不能不注意江西。笔者在《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赣南摇篮说”,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东晋南渡的北民有秦雍流人、司豫流人、青徐流人三大支流,罗香林先生独以“司豫流人”为客家的源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古代的中原,可以论证客家族源的正统性,还在于这支流民渡江而入江西,最远者已达赣中与赣南,成为第一颗播向赣南山区的孕育客家民系的种子。笔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有一个自赣北至赣中再至赣南的“民系锻造”过程,因此客家的方言与习俗同赣民系最为接近,以至赵元任、罗常培等方言学家甚至认为赣方言与客方言属于同一系统,主张合称为“客赣方言”〔12〕。就以上意义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江西特定的历史“温控”及“冶铸”过程,就不会有后来的客家。
客家人的大本营为赣闽奥三省之结合部,宋以后再由此分次播迁全国许多省区以至海外,因此,“客家”概念的外延理应包容大本营以外的一切客家人。
4.客家是具有比较独特的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民系。客家作为一个民系而独立存在,是因为它在民族共同性的覆盖之下,还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其他支系的个性差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色彩。就民系识别来说,客家人最突出的表征是他们所说的别成一系的客家话。这里我们采用“客家方言”这一术语,而不用“语言”。语言学中有语系、语族、语言、方言的分类。语言和民族属同一层级的划分,指的是民族共同语。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13〕。因此我们使用“客家方言”以体现它与汉语的子母关系及其同兄弟方言的差异。
以“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民系的识别标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由:第一,客家方言有一个有别于其他方言的特殊音韵系统,诸如浊塞音声母一律变为送气清塞音;[s-][-]不分;有[-p]、[-t]、[-k] 韵尾,有六个声调。其方言词汇中保存了为数不少的古汉语语词,有些是现行普通话口语中不常使用,仅见于书面语言或特殊词组者;有些则是不见于普通话书面语而为客家方言所特有者。这些特点,正是客家人祖籍中原的历史反映。在方言分类中,汉语的其余六大方言均以其通行的地区命名,唯客家方言却是依照居民的来源和成分命名的。第二,客家方言“是汉族中最具稳定性的方言,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言。客家人有句谚语‘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若不会说客家话,那就意味着不是客家人”〔14〕。对方言的忠诚与执着被提升到“祖宗之法”的高度,这在其他民系是不多见的。正因为如此,客家方言已成为客家人最鲜明、最易识别的民系外壳。听其言而辨其人,故方言可以作为民系鉴别的主要依据之一。当然也会有某些例外。我们说客家人一定会说客家话(变异情况除外),但说客家话的不一定都是客家人,如同我们说“天下雨则地湿”,而地湿不一定就意味着天下了雨一样,二者不是全等关系。绝对化的结论往往会出毛病。
客家人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如生产活动中妇女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有甚于其他民系;生活中不缠足的习俗;围龙屋、土楼之类的典型居室形式;受迁徙和居地环境艰恶的影响,而稍稍扬弃了农业民族安土重迁、知足常乐的心理传统,较其他民系更富有一种勇敢、冒险的开拓精神等等。总的说来,在风俗文化方面,客家人同其他民系依然同多异少,至如重视教育,以读书为万般之上品;崇拜祖先,家族观念浓厚以及婚丧嫁娶、节令时俗的许多内容,难以表现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迁徙中养成的开拓精神,随着与土地的重新结合,加之山区的封闭地理,难免会出现农业民族固有的保守传统的复归。因此,客家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方面同中之异的研究,还是一个亟待展开的重要课题。
三、客家、土著、民系自觉性的辨析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谈一谈“客家”与“土著”两概念的关系及“民系自觉性”的问题。
辞书中有关“客家”的词条大都提到“客家”是“土著”的对称。从词义的源起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客家”是与“土著”对称的名词,在民系的称呼里却不是两个对称的概念。因为“土著”不是一个民系的名称。“土著”与“客家”在普通意义上相当于逻辑学上的两分法,所有的居民不是土著就是客家(包括定居客与游客)。在作为民系的客家内部,同样可以划分土著与非民系意义的“客家”。客家是移民的产物,客家形成后还有过多次的迁徙。迁移至一地自然有相对的时间先后,先来者对于后来者当然是主,是土著;后来者在立足了若干年、若干代以后,同样会成为土著。扯远点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客家都是“土著”。尽管如此,作为民系的“客家”并不因为客家人的土著化而消亡,它依然以一个民系群体的形式存在着。“客家”同与“土著”对应的“客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加甄别地混通运用,必然导至概念的混乱,不是漫无边际地滑向“泛客家论”,便是极大地缩小了客家的外延。如有人将江西的客家同广东人、福建人简单地划上等号,认为江西客家就是明末清初从闽粤回迁的移民。先期而至的赣南老客相对于回迁新客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是“土著”,老客与新客的矛盾的确也表现为“土、客”之间的矛盾,但具体到民系的范畴来说,他们都是客家。明清民国时期的“土客斗争”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客家民系内部不同区域集团或家族集团间的争斗,不全是民系与民系之间的斗争,这是以往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没有分清的问题。
“民系自觉性”就是民系存在的自我意识,通常表现为对民系利益的自觉维护,对民系历史文化的自豪与热爱。有的研究者试图从客家的得名入手来解释客家民系自觉性的产生,进而把民系自觉性的出现看成是民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因此得出客家形成于明清时期的结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梁肇庭博士运用西方社会学中流行的种族集团概念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提出的区域系统概念,对客家所具有的“高度的种族集团的自觉性”作了考察,他认为“就客家来说,集团意识的高潮是和经济萧条、科学竞争的加剧和地方势力集团的出现等因素相应的”;“客家的自觉性,第一次是在十七世纪初的岭南出现,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纪以前”;“客家”名词大约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七世纪以前的方志是没有提到这个名词的”。由此他把“客家的酝酿期”定在十三、十四世纪〔15〕。“客家”作为对外来人户的通称是由来已久的(此与历史比附论者的“给客制度”、“客户”渊源说毫不相干),作为一个民系的名词或成为客家民系自觉性的标志,确实是较晚以后的事,但我不赞成由此推迟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无疑先于名称的出现。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经常与土著集团发生冲突。参与这种斗争的最现成的组织形式便是家族,进而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成地缘性(共同的祖居地)的联盟。土客矛盾越激烈、越频繁,这种地缘性联盟也越牢固、越长久。民系的自觉性由此萌发,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当这种“自觉”以极为强烈的程度表现出来时(如梁肇庭先生所言17、19世纪的情形),这个民系的名称可能随之应运而生。“客家”由他称变为民系的自称也许是17世纪或者更晚的19世纪的事,但客家作为一个自在的群体却已经存在了四五百年!
注释:
〔1〕《辞源》第2册:“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间,中原战乱频繁,北宋末又大批南移,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尤以粤省为多。本地区居民称之为客家。”《辞海》第2册:“客家, 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末)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为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现代汉语词典》:“客家指在西晋末和北宋末从北方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等地。”《简明社会科学辞典》:“客家,‘土著’的对称。中国古代因战乱所迫渡江南徙至赣、粤、闽等地的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
〔2〕李逢蕊《客家人界定初论》, 载《客家学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笔者在《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以及《论赣地客家文化的研究与发掘》(见江西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目标·资源·构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4月版)两篇论文中也曾使用过同类词语,深感失当,有必要作进一步修正。
〔4〕参见许怀林《江西地方史》(提要)1990年油印本。
〔5〕见《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6〕〔7〕〔11〕王东林《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1991年5月上海市首届客家学研讨会交流论文,收入《客家学研究》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8〕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据香港嘉应商会印制本影印。
〔9〕放弃传统的物质生存方式对有悠久农业文明的中原汉族来说是非常困难而又痛苦的事情。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一文中说:“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耕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国禄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10〕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天明出版社1982年版。
〔12〕关于江西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拙文《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已发其绪,本人还将另文详细申论,此处不再展开论证。
〔13〕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6月版。
〔14〕陈乃刚《岭南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
〔15〕[澳]梁肇庭《客家历史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标签:客家论文; 方言论文; 江西话论文; 福建方言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客家风俗论文; 文化论文; 移民论文; 中原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 赣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