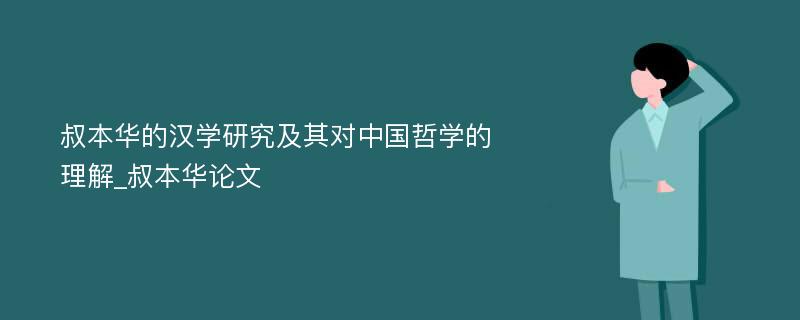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哲学思想论文,中国论文,叔本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3-0009-06
严格来说,叔本华并不是一位汉学家。因为,叔本华与他同时代的欧洲汉学家不一样,他不懂汉语,也没有造访过中国。与之相反,马礼逊等著名汉学家不仅精通当时的中国官话,还熟谙广东话、福建话,甚至他们还曾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就研究汉学的目的和角度来说,欧洲当时著名汉学家的目的非常明确,亦即传教,其研究视角仅仅是寻找汉学中有关宗教的成分[1](pp.93-100);而叔本华的研究完全是哲学目的,也纯粹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汉学中的哲学思想,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从汉学中寻找能够印证他的唯意志主义思想的证据。他认为汉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我的学说的一致性是如此的明显和惊人”[2](p.144)。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是严肃认真的。他的汉学研究的材料来源是19世纪欧洲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著作。这一点很像我国著名的西学家魏源,魏源既没有周游列国,也不懂西文,但是他凭借大量翻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和大量国人撰写的西学研究著作,撰写了巨著《海国图志》。叔本华汉学研究的成果集中在他的最重要的两本著作中:《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年初版,后分别在1844年和1859年再版)和《自然界中的意志》(1836年初版,1845年和1854年再版)。前者只提到了中国的《易经》,后者则对中国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叔本华特别推崇理学大家朱熹,认为中国的理学与他的唯意志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可惜的是《自然界中的意志》直到1998年才有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刊行,再加上国人明通西学者疏于国学,精通国学者又无意西学,所以对叔本华“汉学研究”的研究目前仍属空白。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二是中国人的儒释道三学,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叔本华极力推崇汉学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即中国诸学皆无“创世者”的概念,相反汉学却认为“天人合一”。叔本华对朱熹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和“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朱熹《朱子语类》)的观点最为欣赏,因为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也认为人和世间万物皆是由“意志”推衍的,人只是意志的“客体化”。
自然和英雄:中国人最普遍的崇拜对象
叔本华认为中国具有高度的文明,但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有其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信仰学说。
叔本华是在对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两次传教失败进行了严肃的哲学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他说:“(传教士们)都顽固地热衷于把他们自己相对较新的信仰学说传入这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还徒劳地力图在它那儿寻找这些信仰的早期踪迹,结果他们并没有彻底地了解那儿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学说。”[2](p.136)叔本华所说的耶稣会两次传教失败是指1617年明朝禁教和1717年清朝禁教。
明清两次禁教均缘起于“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的“三祭”(祭天、祭孔、祭祖),耶稣会传教士内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认同派”,认为中国典籍中的“帝”、“天”,与西方宗教的“上帝”不过是“特异以名也”,对中国“三祭”持“不争”态度。另一派是以龙华民为首的“立异派”,认为中国“三祭”与耶稣会教条相悖,持反对态度。1616年,继利玛窦之后出任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意大利籍)禁止信徒参与中国习见的三祭仪式。这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魏忠贤等人认为这是铲除耶稣教的大好时机,便上疏朝廷,以传教士劝人只奉天主,不祭祖宗,教人不孝等罪名要求朝廷严令禁止。1617年,明王朝下达禁教令,传教士悉数被押赴广州、澳门,或改名换姓,或遁迹隐形,酿成南京教案。17、18世纪之交,耶稣会再次爆发关于“三祭”的争论,甚至罗马教皇几次下谕,谴责中国礼仪风习,禁止教徒行“三祭”,并屡派特使来华主持禁谕。1717年,一直对耶稣会的在华活动持宽容、袒护态度的康熙终于被激怒,针对教皇的“禁谕”,康熙也发出“百年禁教”的“圣谕”:“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见《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这两次事件促使欧洲人潜心研究中国,撰写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书籍,叔本华就是从这些书籍中了解中国的。
叔本华从这些汉学研究书籍中很快发现,中国人的信仰与西方人的信仰完全不同。西方人的宗教有一个自有永有的“创造者”,它不仅是“创造者”,而且还是“主宰者”,因而它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只是“主宰者”,却不是“创造者”,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头脑中总是有一个“永恒的、不被创造的、唯一的神圣的存在者,他是先于任何时间的,是创造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东西的”[2](pp.141-142)。但是这种“一神教,当然就是唯一的,犹太人的学说,对于佛教徒和中国人来说都是异在的”[2](p.141),“在佛教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痕迹”[2](pp.141-142)。
对自然的崇拜 叔本华认为,“在那儿(中国)首先存在着一种全国性的对自然的崇拜。所有的人都崇拜自然”[2](p.137)。叔本华的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大规模的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表现在中国君王对天地的祭祀上。这种对自然的崇拜起源于上古时期,君王在冬至祭天和在夏至祭地。明清两代帝王设天坛地坛祭祀和祈祷丰年。建在北京的天坛地坛均始建于明朝,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地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除此之外,中国还崇拜一切自然力量,“如大海、高山、河流、风雨、雷电、火等等,每一种自然力量都归一个拥有许多庙宇的神仙管辖,此外,每一个省、城市、村庄、街道,甚至一个家族的坟地,有时甚至连一个商人的货栈都由一个神仙管辖着,这些神仙一样拥有许多庙宇”[2](p.137)。中国之所以会崇拜一切自然力量,是因为中国人相信每一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都有一个神仙负责,如风神、雷神、山神、财神等,但是这些神仙都是“主宰者”(管理者),而绝不是“创造者”。
对英雄的崇拜 叔本华认为中国还有一种公共祭礼,“是为那些伟大的先皇,王朝的奠基者,以及英雄人物,也就是所有那些由于它们的学说和行为而成为民族救星的人所举行的。他们也有庙宇,孔夫子一人就有1650所庙宇”[2](p.137)。对圣人的崇拜实质上是中国“个人崇拜”的开端,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人认为圣人实际上就是神的化身。孔庙仅仅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关帝庙、文昌庙等圣人庙。另外,在中国还有一个最大量的供奉对象,即祖先的牌位。中国人认为人的灵魂不死,祖先的魂灵将恩泽后嗣。
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在形式上与西方宗教仪式有相似之处,例如寺庙、祭司和僧侣等,但在本质上两者却有很大不同。西方宗教是一神教,它反对自然崇拜,也反对个人崇拜。如《旧约圣经》有经文曰:“除了我(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由于早期的传教士没有搞清楚中国宗教的实质,硬把他们自己相对较新的信仰学说传入这个古老的民族,最后招致失败。叔本华说:“由于欧洲人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儿有大量的寺庙、祭司和僧侣,有频繁举行的宗教习俗,于是他们就从一个固定的前提出发,那就是在这儿也一定要找到有神论。但是,他们看到的是自己期望的落空和发现对于类似的事情的不好理解。”[2](p.141)
无神论:叔本华对儒释道的判定
叔本华认为中国人普遍的崇拜对象就是自然和英雄,当然这种自然和英雄都是经过神化过的自然和英雄的象征物。叔本华还认为,“在中国,除了这种对自然和英雄的普遍的崇拜外,如果主要从教义的角度来看,就存在着三种信仰学说”[2](p.137)。这三种信仰学说就是道儒释。从语序上看,叔本华的“道儒释”的提法要比中国学者的“儒释道”更为严谨。因为叔本华是从哲学层面考察这三者关系的。就这三学的基石而言,《道德经》先于《论语》而产生,而佛学典籍更在其后。中国学者提出“儒释道”是就组织体系的建构层面而言,儒学道统的建立最早,佛教其次,道教在佛教传入之后才匆忙架构。由此可见,叔本华是从纯粹哲学的角度研究汉学的。
叔本华认为道教的基本理念在于老子的《道德经》,他说,这一学说“由比孔子早些的但仍属于同时代的老子创立。这是一种关于理性的学说,理性是宇宙的内在秩序,或万物的固有法则,是太一,即高高在上的载着所有椽子,而且是在它们之上的顶梁(叔本华自注:太极,实际上就是无所不在的世界心灵),理性是道,即路径,也就是通向福祉,即通向摆脱世界及其痛苦的路径”[2](p.137)。对道学的另一基石《易经》,叔本华认为《易经》中的中国哲学和毕达各拉斯学派一样,属于从时间即也是从数出发的哲学体系[3](p.57)。因此,叔本华认为道学世界是由“阴阳法则”统摄,因而不是一种宣扬“创世”的宗教。
关于道教典籍在欧洲的印行,较为准确和完备的是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于1842年翻译刊行的老子《道德经》,这一版本还介绍了一些道教在19世纪中国的发展状况。叔本华对此书十分推崇,他说,这一译本“使我们可以通过这第一手资料获得对这种宗教的一种解释。我们从中知道,道教学说的意义和精神与佛教是完全一致,然而现在这一学派似乎十分衰弱,它的宗师们似乎也被人们所轻视”[2](p.137)。
从19世纪至今,西方学界对“儒”一直有两种看法,或者认为是儒教,或者认为是儒学,叔本华持后一态度。叔本华认为儒学中没有形而上学作为支撑,所以不是宗教。相反,叔本华认为儒学实际上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学说。他说,孔夫子的学说,“学者和政治家们对它特别感兴趣,从翻译过来的材料看,这是一种老生常谈,主要是有关政治和伦理的哲学,而又没有形而上学作为支撑,有些地方使人感到极其空洞无聊”[2](p.136)。
叔本华还认为中国佛教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叔本华指出,因为“佛教徒普遍接受灵魂转世说”,并且“乔答摩派把对创造世界的最高存在者的信仰看作是对宗教的绝对不信”,所以“佛教徒严格地说就是无神论者”[2](p.141)。除此之外,他还研究了佛教在中国的流布。他说,“在中国的这三种宗教中,流传最广的是佛教。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在没有国家的任何扶持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了下来”[2](p.139)。这句话的前半句,叔本华是正确的,但后半句却不很符合实际。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得到政府的扶持(除了几次偶然的毁佛小插曲),甚至佛教界还有“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教训。对国主佑教的情况,叔本华也有所认识,他说,“皇帝对这三种宗教都是认可的,而许多皇帝,直至近代,都特别支持佛教”[2](p.139)。
在对中国宗教的细致研究之后,叔本华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三教一家”,二是三教都属无神论。叔本华认为道儒释三教熔融,他说,“中国的这三种宗教相互并不仇视,而是和睦相处,甚至可以说,还有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也许是由于相互影响之故,以致于出现了这样一种格言式的说法:三教一家”[2](p.139)。
的确,三教圆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早在东晋,宗炳就在《明佛论》中提出了“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的观点(《弘明集》卷八)。北周道安也在其《二教论》中认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教迹虽异,理会则同”(《弘明集》卷八)。唐代学风开明,宗密著《原人论》指出“三教皆可遵行”。他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徒,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大正藏》卷四五)。唐郭雄撰《忠教寺碑铭》分析三教宗旨后认为,“儒释道三教均以忠孝为宗”(《全唐文》卷五一一)。至宋明两代,三教圆融已成定论,“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的观点已在社会广为流行。
关于三教皆属无神论的观点,是叔本华在与西方宗教作了一番抉择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说,“欧洲人在致力于了解中国宗教状况时,就像通常一样,就像以前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同样情况下也是那样做的,首先就是想找出中国宗教和他们本国信仰的相同之点”[2](p.139),但是欧洲人失败了。“一神教,当然就是唯一的(神),犹太人的学说,对于佛教徒和中国人来说都是异在的”[2](p.139),“在佛教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痕迹”[2](pp.141-142)。叔本华这样定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认为在道儒释三学中根本没有一个“永恒的、不被创造的、唯一的神圣的存在者”[2](p.139)。三教并不把“陷入罪恶和痛苦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生灵都注定要死亡,它们的存在由于相互残杀都是短暂的)看作是神的显灵”[2](p.139)。因此,叔本华认为,“这三种宗教都既不是一神论,也不是多神论,也不是泛神论”[2](p.139)。除认为“佛教徒严格地说就是无神论者”外,叔本华还转引马礼逊的分析,认为道和儒的基本观点也属无神论思想,他说,“在博学的汉学家马礼逊那里,在他1815年起陆续出版的《中文字典》第一卷第217页上可以看到,他力图在中文典籍中找到一个上帝的痕迹,并且决心沿着这个方向作出尽可能有利的阐释,然而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确证,就在同书第268页及以下几页的解释Thung(动)和Tsing(静)这两个词,并把它们说成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时,他重新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要使这一体系不被指责为无神论也许是不可能的”[2](p.142)。
其实,最早指出中国三学属于无神论的西方人士是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龙华民,他在17世纪初(可以肯定是在1616年前,但具体年份尚无定论)就在《关于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小册子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与耶稣会同时在明朝传教的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也持相同观点。圣方济会神父萨安当亦著有《关于在中国传教的若干意见》,他对中国哲学、礼仪等的看法,与龙华民基本相同。18世纪初,一位早于叔本华一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于1708年也著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唯物”和“渎神”的[4](pp.92-94)。
的确,正如叔本华所说,汉学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创世理论。事实上,这一状况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春秋郑国子产有“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观点(参见《左传·昭公十八年》),《论语·述而》也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外,老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甚至还提出万物生成理论,亦即“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战国子思、孟子进而提出“天人合一”理论。汉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指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从而完善了这一理论。至宋程颢,又言“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最后,朱熹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朱子语类》)的理论,使任何“创世”理论都无法在中国生存。
朱熹的“万理具于一心”和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
叔本华认为,虽然汉学中没有西方宗教的“神”(创世者)的理念,但是汉学中还是有一个与“人”相对存在的概念:“天”。早期到中国的传教士根据他们一贯的思维方式,亦即找出“所有事物的最高原则,主宰世界的力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目标”,就竭力把汉学中的“天”解释成西方人的“上帝”,结果正如“苏纳特在他的《东印度和中国游记》(第四编第一章)里说:当耶稣会教士和其他传教士在争论这个词到底是意谓天空,还是意谓上帝时,中国人把这些外国人看作是不安定分子,并驱逐到了澳门[2](p.143)。
叔本华对汉学中的“天”的理解在当时的西方人中是最准确的。从他的研究资料来看,叔本华主要研究的是程朱理学。他说,“朱熹是中国学者中最有名望的人,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是当今中国教育的基础,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2](p.139)。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程朱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首先,叔本华认为汉学中“天”的首要概念是“主宰或统治者”[2](p.144),因为“天”最常见的象征是“最高权力”,如《尚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与“天”同时适用的同级概念是“上帝”,如《诗经·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汝)”;《尚书·洪范》“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但是,正如叔本华分析的,汉学中的“天”和“上帝”只有“主宰和统治者”的涵义,却没有“创世者”的概念。这一“主宰”的涵义在汉学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甚至在中国每一事都有一主宰,如关圣帝君、文昌帝君等。
第二,叔本华认为“天”有一定的法则、规律,他说,“如果天没有意愿,那末也许牛会生出马来,桃树就会开出梨花来”[2](p.144)。《易》将这一现象称为“天行健”,“天行”的规律称为“常”。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庄子提出了“物种天均”的思想,他认为“万物皆有种,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孔子对此也持赞同意见,他认为无须多言,天自行事,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程朱理学将“太极”与“天”等量齐观,认为“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朱子语类》)。在解释何以“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的问题时,程颢的观点是“天者,理也,妙万物而为言者。帝者,以主宰事而名”,“服牛乘马皆因其性而为之,胡不乘牛服马乎?理之所不可”。朱熹与程颢的观点完全一致,他认为“盖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
最后,叔本华认为程朱理学最具意义的是提出了“天的精神也许可以从人类的意志为何物中推知”[2](p.144)的观点。程朱理学的这一观点的逻辑起点是孟子的“尽心知天”理论。孟子在春秋时期郑国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基础上,认为正是由于“非所及”,故须由“迩”知“远”。孟子说“尽其心者,尽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程朱理学的先祖邵雍在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进而认为“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中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程颢承继邵雍衣钵,亦说“尝喻以心知天,……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参见程颢《遗书》)。理学大家朱熹认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最后,朱熹认为虽然人天为一,但是人欲障蔽了天理,“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是故,应“灭人欲以存天理”。
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与程朱理学如出一辙。首先,叔本华不认为有“创世者”,相反他却认为世界的真实面目是“意志”,而人与世间万物都是“意志的客体化”,这一思想类似于朱熹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他认为人的贪婪和痛苦都是因为蕴藏体内的“生命意志”推衍的结果,这一“生命意志”实是朱熹的“人欲”翻版;最后,人要回到本真,必须进行“生命意志的否定”,这又是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所以,叔本华本人在赞叹之余,也不得不说,“这最后一句话和我的学说的一致性是如此的明显和惊人,以致于如果这些话不是在我的著作出版了整整8年之后才印出来的话,人们很可能会错误地以为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2](p.144)。
收稿日期:1999-11-13
标签:叔本华论文; 朱熹论文; 耶稣会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汉学研究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哲学家论文; 宗教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