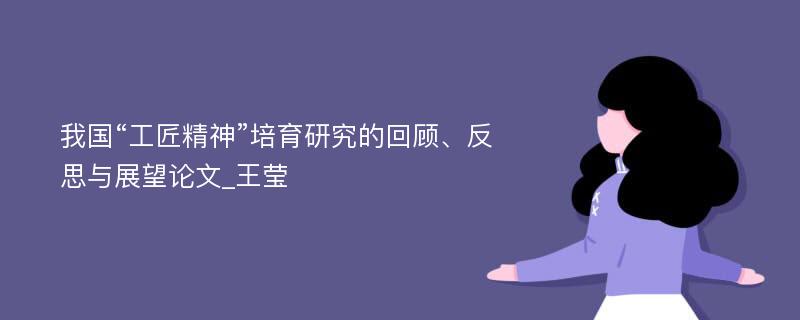
摘要: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生产和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弘扬能够有助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能够提高中国市场经济的杭风险能力,助力中国制造强国梦想的实现,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路径来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文章重点就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进行研究分析,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字:工匠精神;培育研究;回顾;反思;展望
引言
工匠精神属于职业精神的范畴,是从业人员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其核心是对自身所做成产品完美程度的追求,包括“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细节完好价值至上”“慢工出细活”等,这些研究不但明确了“工匠精神”教育属于提升学生素质的有效教育,还厘清了“工匠精神”的内在含义。
1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研究的回顾
1.1萌芽阶段
在萌芽阶段,已经出现了对“工匠精神”传承的零星介绍,但研究多集中在艺术设计、手工制作等范畴。如王迩淞的《工匠精神》介绍的是国际奢侈品香奈儿“御用”鞋匠的工匠精神;而张刃的《退休“大工匠”的技能与精神应传承下去》则是针对“工匠精神”保护和传承问题本身展开的强调性文章,蒋梅的《论先秦工匠艺人的艺术精神》亦属同类,这一时期有关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的研究还是一个较为“寂寥”的状态,相关研究只是就“工匠精神”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成果较为浅显和零散,对我国“工匠精神”培育实践的影响力也较为孱弱。
1.2发展阶段
在发展阶段,对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的相关论述和研究虽然数量仍稀疏零落,但却带有显著的经济因素驱动的“痕迹”,即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多数企业开始认真审视“工匠精神”的缺失。在这一阶段,全球经济环境因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而显得“疲软乏力”,我国制造业发展也逐渐走进了“死胡同”。而此时大众媒体眼眸中新出现的“工匠精神”则惹人瞩目,并被奉为我国在当时优化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玉圭金臬”。
1.3深化阶段
在深化阶段,有关“工匠精神”培育论述和研究数量呈增长态势。在该阶段,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从艺术设计、手工制作、通讯、制造业等领域到教育领域(如邓成的《当代职业教育如何塑造“工匠精神”》)以及文化领域(如铁永功的《“工匠精神”与文字生产的前景》)等。2015年央视新闻推出系列节目《大国工匠》,更是让“工匠精神”成为全社会所热议的话题。文献出处的多元化也佐证了“工匠精神”正在被各行各业所深刻感知、讨论,并在当前浮躁的社会氛围下认真反思自身发展“路在何方”,继而提出以“工匠精神”培育来求生存、求发展。此时,开始陆续有文献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探究“工匠精神”的培育,如王力的《呼唤工匠精神》、单士兵的《让“工匠精神”成为时代共识》等。
1.4繁荣阶段
顺应上一阶段对“工匠精神”培育研究领域拓展的趋势,本阶段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推出之后,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发展,“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践转向问题。相关研究对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原则、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此外,综观当前有关“工匠精神”培育的研讨,借鉴国外经验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如李曾婷的《德国和日本工匠精神的启示》等,由此也可佐证由于我国历史上并未形成尊重工匠的传统文化,现今各行业内的“工匠精神”更是处于“神游物外”的状态。因而,当前学界主流推介我国“工匠精神”培育做法的目光还更多地停留在参考“他山之石”的层面。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2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研究的反思
2.1“工匠精神”培育的主体之思
“工匠精神”培育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工匠精神”该由谁来培育的问题,多数研究几乎“口径一致”地指出“工匠精神”培育主体应由为社会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所承担,其逻辑即是职业教育是培育工匠的教育,因而“工匠精神”培育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职业教育的本分,这显然有简单化思维之嫌。事实上现有多数研究在逻辑展开的伊始就忽视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与孕育出工匠精神的传统学徒制之间的差异,误读了现代与传统交织下“工匠精神”培育的内涵,遗忘了应通过多元的视角来解读“工匠精神”培育问题,仅将“工匠精神”培育局限在制造业领域,也混淆了现今生产发展与传承“工匠精神”的传统手工业生产之间的不同。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国职业教育所匮乏的是“努力去发现问题并通过亲身实践来解决问题的文化”,只重视学生技能的“求精”,而忽略职业素养、人文情怀的培养,这是我国制造业“只大不强”的根源,亦是职业教育的“不为”。现有研究应理清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不能”与“不为”,才能明确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角色识别和自我定位,进而在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培养主体。
2.2“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入歧途
现有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对工匠手作叙述的缺失,二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工匠制度研究的迷失,三是对现代和传统工匠文化的比较研究弱化。研究基础的不稳固致使对“工匠精神”培育路径选择的论述多集中在政府要构建工匠制度、加大对匠人的保护、社会和企业要继承手工遗产、学校要传播工匠文化等方面。
3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研究的展望
3.1“工匠精神”培育的主体“位移”
“工匠精神”培育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育过程中的“不能”与“不为”也决定了其无法承受“工匠精神”培育的主体责任之重,这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适性的“工匠精神”成为社会稀缺的原因。至此,为突破束缚,“工匠精神”培育在各教育阶段的推行“呼之欲出”。因此,杜威的教育本质观为“工匠精神”在各教育阶段培育推行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指导,推行并不意味着在每个教育阶段都要培养出学生的工匠精神,这既不合乎现实,也与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不符。但普通教育阶段或是高等教育阶段都是“工匠精神”培育、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为整个生成过程奠定坚实基础。“工匠精神”的生成过程为其在各教育阶段的推行和培育提供了可能,而各教育阶段的综合实践活动课、实践教学等都为“工匠精神”培育提供了载体。
3.2“工匠精神”培育的“车到山前”
“工匠精神”培育的“连续性”涉及到在特定的时空内工匠从事劳作时的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促成了工匠的道德规范和职业态度,并在长时间积累过程中折射出“工匠精神”的技艺之美、创造之美、坚守之美。当前,“工匠精神”的展现已被博物馆、个人展览等空间所“包办”,所谓“工匠”的劳作时间也自带“个人化”“高端化”的色彩,这使“工匠精神”本应具有的生活化、平民化的特质渐行渐远。现今“工匠精神”的“贵族化”气质已然脱离了“工匠精神”的本质,因此,在后续相关研究中,有必要探讨如何扩大工匠劳作的公共空间、进而延展工匠劳作的时间,这将是“工匠精神”培育的可能路径之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匠精神”培育并不是要回到传统工匠劳作及其时间节点之上,后续的相关研究不能只就培育而论培育,路径选择的研究需要注意到“工匠精神”生成的连续性特征、也需要捕捉到“工匠精神”所隐含的审美境界,如此才能培育出新时代“工匠精神”和新时代的新工匠。这里的新工匠是指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所具有的匠心文化、创新思想、敬业精神、专注劳作才是新时代所需要的“工匠精神”。
参考文献
[1]董娟娟.高职生工匠精神培育路径探析[J].黑河学刊,2018(05):137-139.
论文作者:王莹
论文发表刊物:《建筑学研究前沿》2018年第2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29
标签:工匠论文; 精神论文; 我国论文; 职业教育论文; 阶段论文; 路径论文; 社会论文; 《建筑学研究前沿》2018年第29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