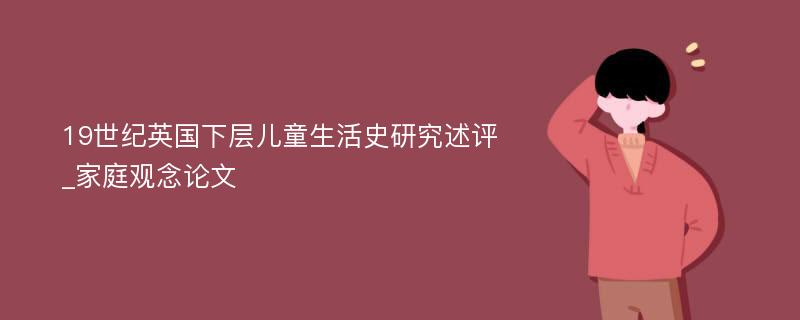
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英国论文,下层论文,史研究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4-0099-08
在历史上,儿童长期以来是一个无法表述自己的群体,他们被淹没在大众历史中而默默无闻。但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儿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儿童和童年从研究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地区,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心理学、社会政策研究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的一个中心话题。在所有关于儿童以及童年的研究中,英国19世纪的儿童生活史是一个焦点,它涉及到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这一争论很激烈的研究课题,以及这一时期童年生活模式的各个方面对其他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英国在工业革命引起剧烈社会变动时期的下层儿童生活史研究进行评述。但是,这一研究离不开童年和儿童生活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因此,笔者将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儿童史的总体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把视角拉向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的研究之中。
一
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变迁的研究首先牵涉到人们对于童年的认识问题,它为人们探讨历史上儿童的具体生活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国家儿童和童年的研究比较少。俞金尧的《儿童史研究四十年》[1] 一文,对于西方学术界关于儿童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体性的概述;施义慧的《近代以来西方童年观的历史变迁》[2],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看待儿童的观念的变迁历史。除此之外,对儿童和童年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在西方学术界,儿童史却是个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关于儿童和童年的历史研究比较少。推动历史上的儿童从研究的边缘向中心地区迈进的,是法国学者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童年的世纪》(1960年在法国出版法文版,1962年出版英文版)。阿里埃斯认为,在中世纪根本不存在童年的观念,儿童从七岁左右就正式进入成人生活世界,但他试图从中世纪寻找现代童年观念出现的轨迹。他认为,到17世纪时,在法国已经形成了两种关于童年的观念。[3](p127) 阿里埃斯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尤其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对他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与辩驳。莎哈(Shulamith Shahar)在她的《中世纪的童年》一书中就认为,“在中世纪中后期(1100~1425)存在着一种童年观”[4](p1),父母对他们的子女进行了情感和物质双方面的投资。无论人们怎么批判阿里埃斯的观点,无可否认,阿里埃斯奠定了童年研究的理论基础,即童年的观念并不是连贯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发展过程的。他的著作使得童年研究成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话题。
在70年代,许多作者更多地关注成人对待儿童的行为,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儿童和童年历史的三部曲:德·莫斯的《童年历史》[5]、爱德华·肖特的《现代家庭的形成》[6] 和劳伦斯·斯通的《1500~1800年间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7]。德·莫斯通过对历史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的研究,得出结论说:“童年的历史愰如一场我们刚刚醒来的噩梦,越往前追溯,照料儿童的水平越低,儿童越有可能被杀害、遗弃、揍打、恐吓以及性虐待。”[5](p21) 肖特从历史上母婴之间的感情等角度来阐释现代家庭的兴起。他认为,家庭形态的转变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才在大众中发生。转变的主要标志就是母乳喂养的盛行以及母乳喂养的结束。[6](p11,170) 斯通则通过研究1500~1800年间英国家庭形态的变化考察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变化。他区分了3种类型的家庭:1450~1630年间的开放世系家庭;1550~1700年间的“有限父权核心家庭”;1640~1800年间的“封闭核心家庭”。他认为,大约从1660年开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在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抚养子女的理论、标准化的抚养子女的行为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关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英国开始向“一个以儿童为导向的家庭模式”转变。[7](p405,411)
人们经常把这3部著作与《童年的世纪》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待童年的态度以及童年的待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几部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把18世纪看做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以及儿童的实际待遇与现代标准最接近的时期。在这批学者的带动之下,儿童和童年史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
但是,阿里埃斯、斯通等人的研究著作在80年代都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最先对上述研究进行反思的是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他在《1500~1914年间西方家庭史方法论》[8] 中第一次把阿里埃斯、德·莫斯、肖特及斯通的著作放在一起,名之为家庭史的“情感研究方法”,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学方法”和“家庭经济学方法”。他认为,虽然这些作者提出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困难。另外,他认为,他们没有对经济结构做密切而深入的考察,实际上鼓励了文化领域中脱离背景的研究方法。[8](p61~64) 对儿童和童年历史研究进行全面批判随着琳达·波洛克(Linda Pollock)的《被遗忘的儿童:1500~1900年间父母和孩子的关系》[9] 的出版而开始。到这时,中世纪研究者驳斥了阿里埃斯关于“中世纪社会不存在童年观念”的观点,英国史学家强烈反对斯通对17世纪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特征概括。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头,把70年代的一些代表作批判为方法论经不起推敲、技术不完善、结论完全错误。[10~12] 80年代的逆转,主要把研究重点放在考察历史中儿童的实际经历,而不是童年观念的变化。波洛克通过研究一些日记、自传和遗嘱等资料,发现“在几个世纪当中父母对丧子的悲伤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证据显示在18世纪以前父母对于年幼子女的死亡漠不关心,而18世纪以后他们却表现出深深的悲痛”[9](p141~142)。因此,她否定了阿里埃斯等人关于童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从70年代到80年代所发生的这种巨大的逆转,使得史学界一时之间处于迷茫阶段,鲜有佳作问世。
无论是阿里埃斯、德·莫斯、肖特以及斯通的著作还是他们的批评者,他们对儿童和童年的历史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情感研究方法。然而,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儿童和童年历史还存在着“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家庭经济学方法”。剑桥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小组在60年代就指出,在英国,核心家庭是主要形式,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有持续性,这种家庭也有力量承受教会、国家以及经济变化的冲击和侵袭。[13] 而且,人口学家的研究方法通常与被安德森描述为“家庭经济学”方法联系在一起,即把家庭放在某个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他们认为,家庭会对它们发现自身所处的状况作出理性的反应,如家庭所生子女数目可能会因为它们的社会一经济状况的不同存在极大的区别。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阿兰·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1300~1840年间英国的婚姻和爱》[14]。他认为,儿童在经济上能够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在情感上是父母的心灵支柱以及他们地位的证明;但另一方面,英国社会的儿童自中世纪开始就是父母的经济负担。麦克法兰认为,家庭策略会迅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反应。这也是近来许多童年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工业革命时期童工问题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
对家庭内部童年经历的研究是情感研究方法、人口学研究方法以及家庭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共同之处,这些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多年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促成了童年和儿童生活史研究的繁荣。但是,它们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导致人们忽视对童年产生影响的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更多地关注家庭以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对童年以及儿童生活的影响。在这方面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历史学家们对影响儿童生活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挖掘和研究;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学中带有后现代倾向的“新社会学童年”的出现。
80年代儿童史研究的重大转向使得历史学界在这一课题上暂时处于迷茫之中,历史学和社会学交叉综合的研究倾向一时之间暂居优势。带有后现代性的“新社会学童年”渗透进儿童史研究并对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甚至颠覆了许多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詹姆斯和普拉特(James.A.,and A.Prout)等人试图“对儿童进行理论化分析”并设置了与儿童研究有关的参数。童年在“社会性解释”(social construction)的概念中被说成是一个观念性的文化现象,具有不同的形态,每一种文化表述必须根据它自己的时期、用它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语言来加以理解。这种“新社会学童年”对于儿童和童年历史研究是一把双刃剑,既使得这种历史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促进研究工作迈向新的高度,同时也使得这一研究有走向碎化和滑入不可知论的危险。
对于“新社会学童年”甚嚣尘上的态势,拉瓦莱特进行了明确的反击。他指出,尽管童年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但是只有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其他发展联系起来才能理解。童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性’的现象,要理解它,必须把它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阶级分裂的社会中所体现出的矛盾和冲突”[15](p16)。拉瓦莱特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历史学家的回应,他们对于童年和儿童生活史研究中忽视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安娜·达文(Anna Davin)指出:“童年就像家庭或者婚姻,或者成年或老年一样,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和经济背景之中的。它的特点和意识形态是不能假想的。甚至身体的发展过程也因社会和社会团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16](p2) 换句话说,儿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地位、作用和行为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戈德森(B.Goldson)也认为,“童年必须放在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决定童年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排需要进行严格的考察”[17](p26)。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这批历史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形态的儿童的实际生活经历,英国19世纪下层儿童的生活史也因之而由边缘地带迈向了历史研究的中心舞台。
二
从历史角度来说,构成英国下层儿童生活的一个重要经历是劳动。在17、18和19世纪上半叶,下层儿童的童年生活是在贫困、为了生存而斗争、劳动以及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中度过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根本改变。“童工”几乎成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儿童的代名词,对他们的关注与研究成为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英国,较早对童工问题表示关注的是一批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有些人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们对工业革命研究的重要部分,有些人仅仅涉及一下而已。
保尔·芒图(Paul Mantoux)是提出雇佣童工劳动是工业革命早期的“必然罪恶”观的创始人。[18](p333~339) 芒图认为,在工厂制早期,儿童(主要是贫寒的教区学徒)不仅是成年男工的充足替代品,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比男工还更受欢迎。他们的生活极其悲惨,“通过这种腐败和痛苦、野蛮和卑鄙的混合,工厂就把地狱的全景摆在清教徒式的良心面前了”[18](p337)。芒图把童工看做是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在他看来,工厂主毫无约束的权力造成了这种悲惨和罪恶。
芒图的观点在哈蒙德夫妇的著作[19] 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在哈蒙德夫妇的研究中,童工成为工业革命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他们认为所有的儿童都在一种令人震惊的环境下工作,而不像芒图那样仅仅强调教区学徒。儿童在创造一支新式的工业劳工中有着最重要的地位。儿童参与劳动力队伍,使得雇主可以降低成年男工的工资,并击败工人们争取高工资的企图。当男人的工资被人为地降低到无法养家糊口的地步时,妇女和儿童被迫去工作以贴补家用。儿童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为后来的童工问题研究定下了基调。儿童在早期劳力大军中的重要性和他们的工作条件成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是,经济史学家克拉潘对哈蒙德夫妇的历史描述提出了质疑和修正。[20] 克拉潘强调工业化是缓慢演进的过程,到19世纪中期典型的英国人还是乡下人,[20](p96) 棉纺织业还不是英国工人的典型职业。但正是在纺织业中儿童对工业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工业革命并不仅仅是纺织业,那么儿童的经济地位就不像芒图和哈蒙德夫妇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他们对早期工业劳动力队伍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观点也可以因此被否决。克拉潘也试图对儿童在工厂中遭到严重虐待的观点加以修正。虽然他对童工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生活水平问题的总体观点暗示着他相信儿童生活有所改善。
继克拉潘之后,史学界形成了对垒分明的两大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争论的焦点是工业革命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是改善还是恶化了,这个时期的下层儿童被置于工人阶级的整体之中加以考察。许多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都把关于童工的部分放在广泛的立法运动中,用意就是证明童工劳动是一个严重的(正在恶化的)社会问题。[21~24] 相反,也有一些研究者利用童工法来说明19世纪童工状况的改善。[25][26] 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19世纪是对待儿童的一个分水岭。乐观派认为,工厂法和议会对童工的调查是一个正在逐步消除大部分严重暴行的社会所采取的行动。立法是消灭残余暴行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止暴行传播的手段。悲观派则认为,立法行为证明了虐待儿童的现象已经到了社会不能容忍的程度。
对于童工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工业化对童工福利的效果这两个历史课题的争论,在战后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问题的研究中又重新出现。悲观派的观点得到了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的有力支持。霍布斯鲍姆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即儿童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通过降低成年男工的工资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27](p292~293,310~312) 汤普森则认为,儿童工作的状况从工业化一开始就严重恶化了,“在1780~1840年之间,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熟悉史料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28](p381)。在汤普森看来,前工业化时代童工的重要特点是“他们是在父母的照管之下在家中从事家庭经济劳动的”[28](p384)。工厂制继承了手工工场体制的最坏的特征却没有继承它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对儿童如此规模和如此程度的剥削是我们历史上最可耻的事情之一”[28](p403)。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坚定地重申,工业革命对儿童来说是一场灾难。这种灾难观点主宰了许多关于劳工阶级的专门著作。研究工厂运动的沃德(J.T.Ward)尽管认为对早期工厂暴行的批判是建立在夸张的基础上的,但他也承认,“尽管当时人对早期工厂的反对行为可能会显得相对的无知、偏见和目光短浅,但他们的观点影响了立法行为,关于这点现代的观察家们很少能找到其中的严重错误”[29](p19)。
与汤普森等悲观派史学家相反,斯梅尔泽(Neil J.Smelser)和哈特维尔(Hartwell)却坚定不移地为工业革命时期雇佣童工的行为进行辩护。斯梅尔泽接受了童工在工厂劳动力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传统观点,却摈弃了进入工厂必然增加儿童苦难的观点。他强调儿童在工厂内外工作的相似性,认为除了贫寒学徒之外,大部分早期工厂中儿童是与他们的父母或亲戚在一起工作的,这使得“工厂工人中有一种团体的氛围”。“到了1820年,工厂生活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分离还远没有完成,尽管这时工厂制已经繁盛了40年。”[30](p193) 在斯梅尔泽看来,工厂立法并不主要是对早年虐待童工的一种明显的反应,而是技术变化和其他因素导致棉纺织工业发生结构性演变的一个组成部分。[30](p265~266) 斯梅尔泽关于家庭经济破裂的日期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家庭经济的存在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而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则尖锐地批评了他的“快乐的”童工的观点。然而,斯梅尔泽的研究标志着对童工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他是第一个把童工问题放在家庭经济范围内考察儿童地位的人。此后,人们很难仅靠那些令人恐惧的道德堕落的故事来研究童工历史。
哈特维尔是唯一与斯梅尔泽并肩作战的人,他一直是生活水平争论中的乐观派领袖。哈特维尔认为,童工状况的恶化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后果。[25](p395) 童工可能在工业革命前家庭手工业体制发展时期就达到了高峰。哈特维尔对这一场争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指出了关于童工的历史著作事实上并没有讲述童工的历史,“而是在争论一个道德问题……任何历史学家企图理解尤其是同情那些过去曾经支持童工的人将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25](p392)。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近年来出版的关于工业革命的总体历史在讨论童工问题的时候已经降低了道德愤怒的调门,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儿童在早期工厂以及工厂立法斗争中的作用。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由于从60年代开始儿童史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放在童年观念的形成以及家庭内的亲子关系等方面,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的实际生活经历往往被置于边缘地带。即便是汤普森等历史学家也是把童工问题放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问题中加以考察的。在1990年以前,除了关于教育史研究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外,关于儿童生活史研究的作品和史学家乏善可陈。① 但是,随着儿童史研究在80年代的重大转向,原有的研究主题和方法渐渐走入死胡同。在经历短暂的迷茫和沉寂之后,90年代的英国儿童生活史研究终于进入了厚积薄发的状态,涌现了大批研究佳作和有影响力的史学家。
童工问题的研究继续在1 9世纪下层儿童生活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突破了以往学术派别的窠臼。坎宁安考察了1680~1851年间的儿童就业与不充分就业状况,认为儿童的不充分就业在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存在,这就彻底摧毁了乐观派和悲观派各自的论证基础。[31] 拉瓦莱特从童工与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童工问题是一个与贫困、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关系这样更广泛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5](p14) 无论他们是否选择去工作,这种选择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处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在没有消灭贫困和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以前,童工作为一种现象不可能消灭,在现代社会它仍会以“校外劳动”的形式继续存在。[32][15] 纳尔迪内利对童工与工业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童工问题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内在罪恶,它是工人阶级家庭应对贫困的一种自然反应。童工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工厂法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革命增加了英国财富,工人阶级也从中受益,实际收入有所上升,因而不再依赖子女到工厂劳动的收入。[33] 霍普金斯在他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童年转型的研究中,对于儿童所从事的不同行业的职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到这种转型是如何发生的。[34] 除此之外,帕米拉·豪恩的《1780~1890年间的儿童工作和福利》一书也是当前研究童工历史的学者必读书。
除了童工问题这一儿童史研究的经典话题,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的童年生活全貌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进入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坎宁安、霍普金斯、豪恩、达文等人在这些方面各领风骚,皆有扛鼎之作。坎宁安偏重于较长时段里西方社会儿童(尤其是贫寒儿童)的童年生活描述;[35][36] 霍普金斯专注于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童年生活经历在19世纪所发生的转型;[34] 豪恩把自己在70年代对维多利亚乡村儿童的研究兴趣扩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儿童以及随后的爱德华时代的儿童,形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儿童生活史三部曲:《维多利亚时代的乡村儿童》[37],《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儿童》[38]、《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学校儿童》[39];达文则专注于19世纪后期伦敦贫寒儿童在家庭、学校和大街上的生活经历,更侧重于已经开始发生转型的下层儿童生活史。[16] 此外,弗莱彻编著的《值得争议的童年:儿童、父母和国家》集中了达文等儿童史名家的专题论文,对于童年的理论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阐述,虽不是个人专著,却具有理论的前沿意义。[40] 除了上述这些研究童工和19世纪童年历史的学者之外,也涌现了一些专注于儿童史某方面的专家,如亨德里克、罗斯等人对儿童福利、医疗和虐待儿童等方面的研究使人们开始从福利的角度来关注儿童的生存状态。[41~42] 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征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分析儿童的生存状态,不仅突破了60年代以来儿童史研究的狭隘范围和片面的研究方法,使得儿童史研究重新绽放出活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也有力地抵御了“新社会学童年”研究方法对历史研究的侵袭,使得儿童史研究的舞台重新回到历史学家的阵营。
三
19世纪对于英国下层儿童来说是一个重要时段,因为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几代儿童的童年生活经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19世纪末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如住房、卫生、健康等有了明显好转;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由家庭经济的支持者,变成了依赖家庭经济来抚养的消费者;他们对于父母而言所具有的情感价值使其成为家庭的中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也不再是令中上等阶层感到恐惧和忧虑的社会混乱的象征,转而成为民族未来的希望,是“有围墙的花园”中的被保护者;他们的直接生活经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不再是他们童年生活的宿命,学校教育成为他们童年生活的主宰。
这样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西方史学界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彼此之间的争论异常激烈。
纳尔迪内利认为,童工的衰落和教育的增长是工人阶级家庭策略的结果。家庭对于其子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改善(尤其是男子工资收入的增加)使得工人阶级家庭能够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因此把子女从劳动力市场中撤回;致力于拯救儿童的慈善家,或者禁止儿童工作的法律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至多是第二位的。他认为,家庭通过放弃短期的经济收益(主要是以儿童劳动收入的形式),能够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他们有可能在以后的人生中获得更好的工作和回报。更好的教育以及经济上更有保障的儿童不仅体现了一种长时段的跨代的家庭“进步”,而且更为直接的效果是,儿童在完成了教育之后,将会在抚养年老的父母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33]
对于哈钦斯(Hutchins)和哈里森(Harrison)[43] 以及平奇贝克(Pinchbeck)[44] 等研究者来讲,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国家立法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范的结果。他们认为,工厂制的恐怖导致社会活动家对政府施加压力,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有约束力的体制,它有效地禁止了“不合适的”渠道中雇佣儿童劳动。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19世纪国家的干预很不平衡,通常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机制而无法执行,立法通常是以留下许多能够让工厂主加以利用的漏洞这种形式构建起来的。资产阶级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也在某种程度上确证了立法在这个领域中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哲学仍然以自由放任为主导的时期内。然而随着19世纪的进展,日益严格的立法很显然也是某种童工劳动形式丧失合法性过程中的一部分。
也有一些研究者,如哈里斯(Harris)认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有效地把儿童从主要的工业部门中驱逐出去。[45] 也就是说,随着19世纪的进展,新的技术得到了发展,它们取代了儿童的工作,要求工人们掌握一些年幼儿童注定不能掌握的新技能,或者导致更繁重的工作任务的产生,这些工作任务需要“成年男子的体力”才能成功地完成。如19世纪八九十年代造船和电子工程等行业的发展就没有给儿童提供就业机会。
对于韦纳(Weiner)[46]和法伊夫(Fyfe)[47]来讲,义务教育的发展有效地终止了童工劳动,因为它需要儿童在工作开展的主要时间里呆在学校里。坎宁安[48] 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教育体制增长的重要性。一方面,义务教育在限制童工劳动方面产生了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与解决市中心地区儿童的失业以及不充分就业问题有着同样的关联。义务教育制的发展很显然影响了参加劳动的儿童数字。它越来越多地界定了什么是儿童在一天的主要时间里应该从事的“适当活动”。但是,它也渐渐地给工作中的儿童留下一个选择:逃学去从事雇佣劳动,要么就是去接受教育,并在课外时间劳动。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儿童们渐渐选择了一个变通办法,即从事那种能够把劳动和接受教育结合起来的边缘性工作。
近年来,拉瓦莱特[15] 通过对英国历史上的童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童工劳动在19世纪末的劳动力市场中经历了边缘化的过程,它受到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再现、工人阶级对中上等阶层童年观的接纳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政策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国家试图塑造和控制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被看做是最适合儿童的活动。然而,这并不阻止儿童去工作;它把儿童的劳动行为进行重新部署,引导到了能够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的工作中。[15](p67) 这种观点是对当今英国童工劳动所采取的形式进行的一种具有历史根据的解释,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儿童劳动行为的历史连续性和变化。
专门研究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童年生活转型的霍普金斯认为,应该通过考察中等阶级的观念与行为来理解这种转变的原因。它并不是该世纪人们对待儿童的态度上有什么深刻变化的后果,而是人们处于一个正在发生不可预知的社会变化(人口膨胀、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时代所自然激发的慈善性或同情性的动机与对社会控制的关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膨胀、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这三者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爆炸力,似乎有摧毁前工业化社会的威胁。当问题日益严重时,中等阶级往往采用一种实用主义与传统的同情心偶尔相结合的办法。改革并不总是人们善意之心的结果,动机很复杂,显然也包括了中等阶级的自我保护意识。19世纪末所获得的改革成就也不是1800年的改革家所能想象的。保护棉纺织工厂中的学徒不受虐待的希望最终以所有的童工雇佣都被置于立法的规范之中而结束;帮助教会建立学校的需要最终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世俗教育体制而告终。而19世纪末出于民族利益和维护帝国的需要,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健康和福利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工人阶级整体政治地位的抬升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儿童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开始被当做人来看待。因此,工人阶级子女生活在19世纪发生的转型事实上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生活所发生的特殊转型的一部分。[34](p6~7)
1926年,托尼(R.H.Tawney)曾说过,许多社会里“童年的待遇”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清晰地揭示“社会哲学的真正特性”[49](p239)。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吸引了大批研究者乐此不疲地致力于儿童史研究。目前儿童生活史研究继六七十年代对童年观念和亲子关系的关注以及80年代的反思之后成为儿童史研究的主流,在英国史领域,历史中的儿童的实际存在状态也成为人们研究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方面。研究的热潮虽已开始,但它需要我们不断地拓展新的领域,找寻新的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接近历史上的儿童生活,不至于过分偏重某一方面而造成挂一漏万的遗憾和对历史的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