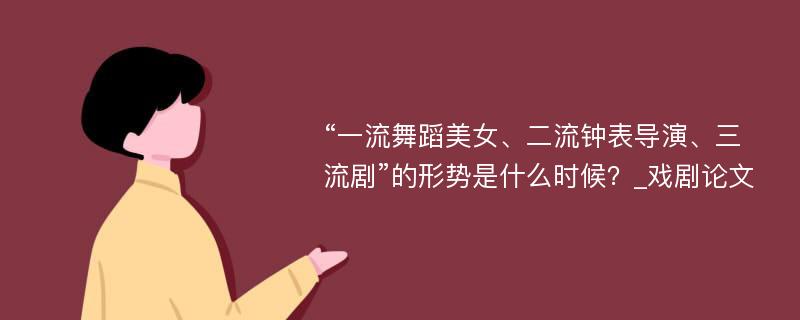
“一流舞美、二流表导、三流剧作”的局面何时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舞美论文,局面论文,二流表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导读]
独立的批评,面对——
三大剧院: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三大导演:林兆华、陈薪伊、田沁鑫
三大剧目:两版《赵氏孤儿》和新版《商鞅》
三种奖项:文华奖、曹禺剧本奖、国家舞台精品工程
三种概念:主流、非主流、主旋律
裂隙:批评的契机
春节前夕,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开会,对2003年中国话剧的创作作了回顾。会 议的议题中有一项赫然在目:当代戏剧的文本滞后现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戏剧,作 为一门融合了诸多艺术元素的综合体,其中剧本创作落后于其它艺术元素。(注:用“ 文本”一词指剧本,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但是,在现代批评(符号学)术语中,文本(
text)是指一组或多组代码(code)的集合系统。在文学中,它指文字的集合体;在戏剧 中,则是包括表演、美术、音乐等多种元素代码的复合集合体,不是剧本所能涵盖的概 念。既然自身是一个复合体,也就不存在横向滞后的问题。所以,用“编剧”这样的概 念既准确明了,也通俗近人。)
公开认可剧本创作落后的现实,并不是一件易事。就笔者所见,在戏剧创作的整体格 局的研究中,对剧作落后的批评,至少已十年有余。然而,这些声音并未引起有关方面 足够的重视;相反,与近年来越来越喧腾的剧本评奖的欢天锣鼓相比,这些微弱的批评 真如泥牛入海,渺无踪影。
2003年,对剧作落后的批评得以公开化并得到了一定的社会认同,是由一个偶然的契 机触发的。这就是由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同时改编上演了《赵氏孤儿》。这 是由中国两个最具声望的戏剧团体和两位火爆的新、老导演直接参与剧本创作的剧目。 这两出戏所共同暴露出来的剧作问题,为批评界提供了鲜明的靶环。
据我看,这两出戏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在策划阶段就犯了两个大忌,埋下隐患,使 剧目在演出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巨大的裂隙,使批评有机可寻,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么,这两个大忌是什么呢?
一曰,定位偏差:在大众艺术兴盛的当口,玩了一把精英游戏。
在中国文化中,戏曲是最大众化的艺术,虽然在观众定位上,有文人戏、宫廷戏等类 型,但基本上是通俗的大众戏剧。元曲《赵氏孤儿》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地方戏又是 最典型的大众化剧目,具有大众戏剧的所有构成要件:恩怨相报的鲜明的大众道德观, 起伏跌宕的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但是,今天话剧舞台上的两出改编剧目,却违背了 这出传统戏的基本定位,它们似乎并不在乎大众的接受。首先,两出戏不约而同地抛弃 了大众道德观,被满门抄斩、被人舍命相救的赵氏孤儿不愿复仇了,编创者企图以此在 观念上做新的诠释,标新立异;在剧情上,人艺版故事逻辑断裂,故事不支持理念;国 话版过多地沉溺于场面效果而不顾情节的混乱。人物则概念、图解,动作或是单一,或 是含混。这样改编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人看着费劲,或者干脆看不懂。把审美享受变成审 美疲劳,观众的情绪由不满而对立。于是乎,祸起萧墙,引发批评的杀心。
二曰,策略偏差:离开自己熟悉的主流位置,玩了一把“非主流”。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许多编创者都已经充分理解在政治上自我保险的重要性。譬 如《红高梁》,在商业运作上是以充满刺激的“野合”为号召的,片尾则举起了爱国主 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两者的转承虽然生硬,却是一种运作策略。在话剧舞台上,前实 验话剧院的《生死场》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运作策略,它也用爱国和民族的大旗包装了对 性场面的原始兴趣。这一策略是如此有效,保险的政治概念掩蔽了剧本创作中种种不足 (注:参见拙作《没有奇迹》,《文艺报》2001年8月6日。)。批评也在这两面大旗前偃 旗息鼓,最终它还将最高剧作奖——曹禺剧作奖揽入怀中。
而此次,春风得意的导演们不经意间偏离了《生死场》、《狂飙》等剧所遵循的政治 保险的运作策略,试图以另类主题来重新演绎古剧。不曾想作品一旦失去了政治上的保 护,就使得批评家在没有政治越轨之忧的空间中,释放出蓄积多年的所有的犀利。
赶巧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投巨资复排的《商鞅》也在2003年末公演了。三个最具 声望的话剧院团——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三位当下最 火爆的导演——林兆华、陈薪伊、田沁鑫,倾力推出的三个大制作剧目,基本上代表了 中国话剧艺术当下达到的最高水平,为较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话剧的现状,提供了一个绝 好的批评契机。
同构:主流和非主流
两个不同版本的《赵氏孤儿》和复排的《商鞅》,表现出许多相似的特质。
首先,这三个戏的舞美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水平,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艺版 《赵氏孤儿》,运用了大面积的实景,却创造了空廓而富有灵性的表演空间。高耸的山 崖挡住了全部天幕,巨石嶙峋,制造了沉重的戏剧氛围和厚实的历史感。忽而,一枝灿 烂的桃花从漆黑的崖壁前缓缓飘下、凌空而立,这虚实之间的诗意,让观众如痴如醉。 这出戏的舞美还运用了真马、喷水降雨等元素,不管人们是否赞成这种做法,它们已然 造成了极大的视觉冲击,让观众的眼球大快朵颐。国话版《赵氏孤儿》则大量借鉴了国 外现代舞美手段,以挡片形成天幕的形状变化,以灯光形成变幻的色彩,运用抽象的形 、色来直接营造戏剧氛围、展示人物心理。这一具有表现主义特征舞美手段的运用格调 颇高,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商鞅》则显示出一种对“大”的崇尚,以仰望的视 角在舞台上耸立起顶天立地的商鞅石雕头像,复制仿真的铜车铜马,悬挂起贯通舞台的 竹简、瓦当……追求大场面、大意境、大戏剧。同时,它也运用了改变天幕形体的方式 来创造不同的演区。三者相较,人艺的美,国话的巧,上话的大。整体而言,这三出戏 的舞美制作都是最耀眼的亮点,造成了视觉惊奇,显示了近年来,话剧舞美艺术在变革 中取得的巨大进步。
第二个共同点,剧作孱弱是这三出戏共同的软肋。剧作滞后已经限制了作品可能的发 展空间,拖累了其他艺术元素的创作,较为严重地损伤了作品整体的艺术性。
北京人艺版《赵氏孤儿》在情节设置上基本上沿袭了元曲的样本。只是到了结局,当 孤儿全家被杀的身世被揭开之后,孤儿却突然表示不复仇了。今天的观众并不是非要孤 儿复仇不可的木头脑筋,只是要求在剧情中揭示孤儿不采取复仇行动的因果关系,人们 并不是不能接受合理的全新诠释,但是编剧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猝然颠覆了前面所编 织的复仇情节链。难怪有人觉得编剧不讲理,好像被编导骗了(注:参见华岩《“2003 :中国话剧舞台纵论”会议综述》,即发表于《剧本月刊》2004年3月号。)。编导之所 以强行楔入“不复仇”的概念,似乎仅仅只为了要出一下“新”。至于孤儿为什么不复 仇?编导不仅没说明白,恐怕连自己都还没想明白。
国话版《赵氏孤儿》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导演视角切入来进行改编的剧本。帮助导 演实现预设的戏剧场面和舞台节奏成为这出剧本的第一任务,剧作元素已经退居二线。 剧情结构仅仅是一个为了悬挂各种好看的戏剧场景构件的支架。为了这些预设的场景和 节奏得以实现,改编者有时竟不惜牺牲剧情必要的逻辑性。为此,作品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由于剧情逻辑混乱,人们大呼看不懂,那些精心设计的导演调度成为阳春白雪,和 者寥寥。更甚者引起了一些观众情绪上的反感。
《商鞅》,制作的恢弘依然未能抹去剧作的平庸。从剧本的基本要素看,人物关系的 设置单薄而牵强,基本冲突的构成就是设置变法反对派,让人一览无余。而他与生母神 神秘秘的关系及与韩女由恋人变为君臣的关系都建立得十分勉强,编剧想藉此制造些戏 剧效果,实际上却严重地损伤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感,破坏了观众的认同感。 在剧情上,这出戏随处是杜撰,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剧。当然,今天的观众对“ 戏说”已经习以为常,并不以历史剧的眼光去挑剔它。遗憾地是,作者并未能有效地运 用这种“戏说”的自由给剧情带来些许鲜活的戏剧性。那些舌战群儒,君、臣、妃三角 恋等主要戏剧场面都似曾相识,叙事平直无光。上述这些只是技法层面的枝蔓,我感到 此剧还触及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它在我看戏的过程中一次次袭上心头,使我思绪难安 。这个问题是:把商鞅这个具有改革色彩的人物放到主角的位置,这个作品是不是就是 主旋律的、是不是就上了政治保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有点风险的问题,只是思 想之钟因此而难以停摆。
如何衡量形象的艺术性,恩格斯给出了一把极其简明的尺子,他说:看一个艺术形象 ,不仅要看他做什么,还要看他怎么做(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5页。)。稍微深入地分析一下《商鞅》,我们 就可以发现,这出戏真正落墨在变法本身的篇幅并不多,大多写的是宫廷的权力角逐。 在戏中,商鞅变法,无论是设计还是实施都很顺畅,变法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成就得到 了正反双方的承认,在这方面没有构成实质的戏剧冲突,主要的冲突是宫廷的权位之争 。商鞅最终并不因变法而死,而是为权力倾轧而亡。“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 可不除”说明这场斗争不是变法之争,而是权力之战。经历了20年改革进程的每一个中 国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因为前无古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 过河”,每一项措施都是一次探索,一次抉择。一个改革家怎么能保证自己的抉择就会 和历史的必然吻合?而每一次抉择都必须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代价又总和千千万万 的百姓的命运休戚相关,一旦失误,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改革家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常人 难以想像的。他时时刻刻经受着良心的拷问、道德的拷问、历史的拷问。剧中的商鞅不 是这样,他没有经历那些多难的选择,经受那些灵魂的煎熬。他先知先觉地带着一套完 美的变法方案来到人间,超渡众生。孩提商鞅就被作者以文人的激情戴上天才和神性的 光环,插上了天使的翅膀,商鞅虽然身为奴隶,却生来就有人权平等的思想,具有改革 家的潜质和想当君主的野心。自幼就会“天问”:“为什么有些人定为人上之人……有 些人活着却像个畜生?”等等。但作品的思想高度也就到此为止了,作者虔诚地编织着 一首献给改革家的赞美诗,却无力进一步走入改革家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现代人体 验到的改革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自然也就较少思想的启迪。剧中商鞅与其说像个改 革家,不如说更像一尊神。剧中改革作为事件被推到背景的位置,前台则上演权力的角 逐。所以,这出戏与其说是“改革戏”,不如说是宫廷权谋戏。毫无疑义,我们需要反 映改革的作品,今天中国的改革越来越深入了,我们的话剧应当跟上改革的步伐,深刻 地反映时代的精神。伟大的时代需要歌颂,更需要思考。
再次,从表导演上看,这三出戏各有成就。人艺版《赵氏孤儿》有大开大合之势,表 演上以极其简约的动作形成一种统一的程式,有气势,也大气。国话版《赵氏孤儿》是 最富有灵性的。一言一语、一行一动、一队一阵都极讲究其造型性、节奏性、整体性, 创造了许多出色的调度。但是,毋庸讳言,剧作的混乱大大限制了导演和演员艺术水平 的发挥,最终未能创造出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上话的《商鞅》,导演能把如此平平的 剧本打造成舞台精品,足见其非同一般的功力;在表演上,演员虽然努力,但由于人物 基础太差,使演员的激情表演显得夸张而空泛。比起打眼的舞台美术,表导演的逊色是 明显的。
至此我们从戏剧模式上来考察,这三出戏几乎同出一辙:第一是概念大行其道,观念 借助人物之口直接陈述,不讲究戏剧动作的支持;第二便是人物概念的直接后果——思 想内涵的空泛;第三则是剧场效果最大程度地依赖舞美手段来包装来营造。这在相当程 度上反映了话剧舞台上“一流舞美、二流表导、三流剧作”的通病。如果说《商鞅》是 直奔改革主题,可以划作是主流戏剧,那么两版《赵氏孤儿》主题则显得有些异类,但 是在戏剧模式上,不管是主流戏剧还是非主流戏剧则同出于“一流舞美、二流表导、三 流剧作”的模子,是一母所生的连体婴儿,同病相怜,同形同构。
疯狂:包装的时代
这种“一流舞美、二流表导、三流剧作”的戏剧通病,由来久矣。
早在20年前,在中国实验性戏剧兴起之初就有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批评。80年代后 期,中国话剧改革曾一度向着深度发展,出现鲜有的被人认可的剧作。然而,进入90年 代,受到政治风潮和商业大潮的影响,戏剧界也变得极其浮躁、急功近利起来。在这种 潮流中,舞美元素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毕竟是一个投钱就可以听响的领域啊!
投资天文数字的北京太庙《图兰朵》及上海和北京体育场《阿依达》的超豪华演出给 中国戏剧舞台打了兴奋剂,以大取胜,以豪华取胜,几乎成为一种共识,电视晚会、申 奥晚会及国外奥运的大型晚会中的超大型舞美装置则提供了范本和竞争对象。“视觉文 化”、“眼球经济”等零星理念的引入,则使这种大制作狂潮寻找到了理论的支柱。舞 台上的超大、超豪华之风愈演愈烈,在社会上迅速弥漫。各种演出越来越依仗舞美效果 ,靠舞美撑门面,靠舞美造惊奇,靠舞美出动静。巨大的社会需求,使一部分舞美从业 人员在供职单位的院墙外,又打开了一片新天地,率先进入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之列 。曾被誉为是“轻骑兵”的话剧,现而今已经是一个高投入的领域了。
当然,我并不一概地反对大制作的舞美。但是当它蔚然成风的时候难道不堪人忧吗?看 着越来越繁复的舞台装置,布莱希特有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频频在我脑海中闪现: 早期的布莱希特也曾是一个舞美拜物教的狂热信徒,终于有一天庞大的舞美装置压塌了 舞台,出了人命。震惊之余,布莱希特深感自责,从此他一改台风,坚定地走向简约假 定的舞台空间,成为今天你我所熟知的布莱希特。
两年前,对于这种舞台上的奢靡之风也有过批评,但这些批评之声过于微弱,早被“ 大制作”的狂潮冲刷得无影无踪。
面对这股大制作狂潮,有两种忧虑常使我自扰:
其一,在戏剧这个多种艺术元素共生的鸟巢中,如果舞美这只雏鸟抢走过多的关注和 食物,那么就有可能挤压剧作的生存空间,使原本已经孱弱的剧作进一步贬值。“一流 舞美、二流表导、三流剧作”的戏剧只可能是平庸的戏剧。反过来,“一流剧作、二流 表导、三流舞美”的戏剧则有可能是优秀的戏剧。《图兰朵》、《阿依达》的大制作是 在久经考验的剧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雕塑般的人物形象、完美整一的戏剧结构、 优美的语言和旋律深深印在世界人民的心中。演出商相信对它们投资是值得的,大投入 会赢得高回报。我们再来看看《商鞅》,假如去掉它超豪华的舞台包装,试问:它还将 剩下些什么?
看到那些内容平平的戏剧却用豪华的舞美包装起来时,我总觉得像是看见了一个涂红 抹绿却头脑空空、担心嫁不出去的傻姑娘。观众需要的是结实的舞台形象,而不是几件 漂亮的服装、几件精美的道具和几句格言式的造句。
其二,不少“大制作”剧目的投入产出比通常是巨额负数。前述《图兰朵》、《阿依 达》这样的演出是演出商的经营行为,普通百姓与它们的资本运作无关。但是,另有相 当一部分“大制作”不是市场性的投资行为,而是依靠政府财政的文化事业拨款,也就 是说纳税人是这些“大制作”经费的实际负担者。许多戏得奖之后就鲜有演出了,普通 大众看不起、看不到或不爱看,因此和这样戏剧绝缘。那么什么是这宗赔本买卖的实际 驱动力呢?
捅破了说,“一流舞美、二流表导、三流剧作”这种金玉其外的戏剧不是为大众的戏 ,有相当一部分是奔着大奖而去的。在大奖的背后,是少数人成名成家和其他种种世俗 的功利。铺就这条路的,是纳税人的钱!而获利者们却不必对纳税人负责。
红灯:回眸神坛
本文涉及的三个剧目艺术模式相同、制作实力相当,但它们的命运竟是如此的不同, 两个《赵氏孤儿》问世后,饱受批评;而《商鞅》褒扬之声不绝于耳,捧回了文华奖、 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话剧金狮奖等几乎全 部中国戏剧的最高奖项,并成为首批国家舞台精品工程的十大剧目之一。本是同根生, 相去何其远。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我看来,《商鞅》在今天的中国剧坛获奖,有它的必然性。诚然,如前所述,在这 三个实力相当的剧目中,《商鞅》在艺术上存在的问题较多。我以为,它的获奖,除了 艺术上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运作策略上的成功。这里,我将艺术创作行为与运作策 略行为分开来分析,这样做便于人们较为清晰地看到在评奖机制作用下,产生的某些应 对行为。《商鞅》是这类成功运作策略中的经典范例。
支撑着当今中国剧坛的政府奖项主要创建于90年代。那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 务,戏剧演出有义务承担起它的社会责任,这是历史使然。在这一点上,我持艺术入世 的功利态度,而不认同超凡脱俗的艺术纯粹论。与此同时,应当看到这种奖赏策略既是 历史的产物,就会有历史的动态性。如果不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时俱进及时加以调整 ,它的副作用将会伤及它的社会和艺术效应。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艺术是人类文化中一 个自足的系统,有着它相对独立的特性,是一个相当自足自律的领域。艺术是含蓄的, 是要通过形象来说话的,而政治鼓动却需要简要鲜明,所以在一部作品中,政治因素占 强势的时候,艺术创作往往会出现简单化概念化的现象。在这样的作品中,为了弥补艺 术上的缺陷,适当地强调外在包装手段,加强它的视觉观赏性,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长此以往,就会对艺术作品形成这样一个评价体系:“政治保险 + 技术包装”,即在 政治保险的前提下,以华丽的舞台效果取胜。事实上,在这样的导向下,这种潜在标准 已经转化成一个心照不宣的、普遍遵循的运作策略。正是在这样的导向下,像《生死场 》这样的剧作才需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包装。而在获奖领域的激烈竞争中,政治保 险系数也被日益抬高,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品越来越直白,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概念, 损伤了它们应有的艺术性。而舞美制作则在审美补偿机制的作用下,超常规地发展起来 。
不可否认,某些政治理念很强的演出曾经起到过较为积极的社会作用。但是,90年代 中后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不仅使中国社会空前稳定,也使人民大众对文化 艺术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人民渴求艺术,渴求精品。在这样的时候,就需要适时地调整 国家级艺术大奖的运作机制和标准,必须大幅度提高评奖的艺术含量。而《商鞅》在近 期被评为国家级的舞台精品,则反映出今天的精品评选标准依然沿袭旧制,没能根据时 代的发展作出适时的调整。《商鞅》是一个“政治保险 + 技术包装”作为运作策略的 典型案例。
如果我们把《商鞅》放到新时期戏剧创新的历史潮流中去考查,我觉得它至少丢掉了2 0年来戏剧创新的两个重要成果:
第一,80年代的戏剧创新曾一度使中国的舞台从写实的繁琐,走向了简约的多样化。 《啊,大森林》曾用积木式平台,构建了诗意的舞台环境。在《商鞅》中,这样的余韵 已荡然无存。
当然,“大制作”只是问题的表层,究其实质是对戏剧艺术大众性的态度和立场。笔 者钟爱舞台艺术,却也无力全部观赏首批出台的十个国家舞台精品。但是从发表的照片 资料上看,“大制作”已然成为主要倾向。精品非大制作不可吗?对此,我深深地怀疑 。
第二,20年来,戏剧创新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去掉了数十年来加在人物身上的 神性光环,还普通人性于角色。这一点在领袖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创作者努力去发掘 历史巨人身上的普通人的特性。但是在《商鞅》中,我看到主人翁自幼已经表现出天才 和超人的特质,年幼主人翁已经在用启蒙主义的思想在诘问历史。神性的光环已隐隐闪 现。难道好不容易走下神坛的英雄,又陡生思乡之情,翘首回望紫烟升腾的神坛?这样 一种倾向,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难道中国戏剧还要回到“远铺垫,近铺垫 ,走近看,是神仙”的时代里去吗?
如果说,《商鞅》创作和演出只是单一剧院行为,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戏剧生存 艰辛的年代,还应该适当地支持它的演出。但是,当它擢升成为一个国家的舞台精品、 戏剧范本,在近年内必将对全国戏剧发展的方向产生深刻影响的时候,那些在豪华外包 装下深入肌肤的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忧虑。
红灯频闪。警惕啊,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