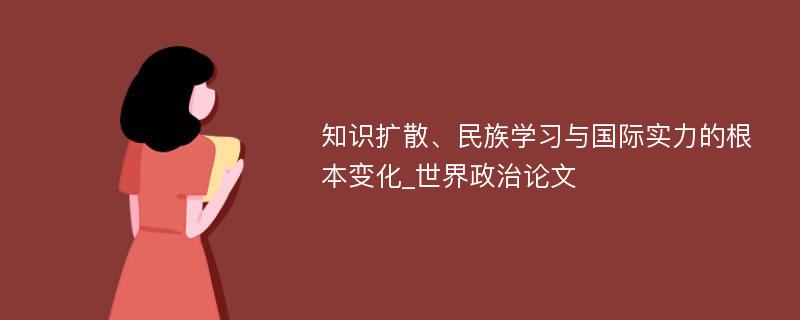
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势论文,知识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权势变迁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战略学者们醉心研究的宏大命题,权势结构的变迁不仅意味着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兴衰更替,而且影响着国际秩序的瓦解和重构,甚至关系到国际规范、交往准则的重新界定。自近代以来,国际权势结构几经变迁,经历了从欧洲强国林立与争霸制衡,到美苏侧翼大国的兴起与冷战对抗,再到美国确立一超独霸地位等发展阶段。如今,国际权势再一次处于深刻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以“无极时代”来界定当前的国际格局,法国总统萨科齐用“相对大国时代”来描述单一大国主宰全球的时代一去不返,而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则将这种权力转移称为“他者的崛起”。尽管这些话语因观察视角和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抓住了国际权势变迁的某一重要面向,并将权力和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视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国际权势何以发生变迁?大国兴衰更替的背后存不存在一般性逻辑?最新一轮的权势变迁又将带来何种国际政治经济影响?这些将是本文关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既有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由于国际权势变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谓经久日长,相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难以穷尽。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际权势何以变迁”这一命题上,并就此展开对既有各种理论的文献回顾。
(一)经济决定论
经济实力是影响国际权势变迁最具基础性的因素,争夺国际资源和财富是国家间战争不断和冲突频仍的基本动力,大国之间的兴衰更替通常也伴随着经济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才能发现大国兴衰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解释大国兴衰和文明交替领先究竟有没有必然性。①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因素是学者们思考国际权势变迁的理论起点,GDP、工业产值、城市化水平、贸易总量等指标成为他们勾勒大国兴衰图景的主要证据。
奥甘斯基在其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转移”理论,用于分析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战争行为。他以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为理论基底,着重考察大国能力分配状况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与传统的均势理论不同,他认为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发战争的最重要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尤其是当大国间权力再分配出现“持平”趋势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最高。② 奥氏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决定论式的。在他看来,国际权力之所以会出现转移,是因为大国在应对“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能力差异。③ 正是各国工业能力和政府管理效率的不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增长现象,进而造就了国际系统内持续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在奥甘斯基之后,还有很多学者对权力转移的机制和后果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④
保罗·肯尼迪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尽管《大国的兴衰》一书内容庞杂,但其核心论点却简单明了,即国际体系中的财富与力量总是相互依存的,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实力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表面上看是军队战争较量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则取决于各国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他断定:“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⑤ 因此,对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的事项就是在高额军事负担提供的短期安全与经济能力创造的长期安全中进行选择。不幸的是,在“大炮”与“黄油”的较量中,多数成熟帝国总是倾向于前者,从而难以避免地走向衰落。相反,那些原先处于弱势的国家通过专注于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拓展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进而为取代原有霸权国奠定了基础。国际权势就这样起伏不定、不断变迁。
以上两种理论观点为我们理解国际权势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启示,但都存在各自的缺陷。奥氏理论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要从现代化、工业化的宏观视野来看待国际权势的转移,特别是需要重视一国的内生能力建设。然而,他的理论逻辑是典型的宿命论,将国际权势变迁的复杂根源简单化,同时显著忽视了时代变化、技术进步等因素对权势变迁的影响。肯尼迪为我们展示了经济与军事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国间持续的兴衰起伏,但问题在于,经济实力与国际权势变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经济实力的增长能否转移成军事能力和战略影响还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认知和战略操作。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决定论没能回答“经济实力增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这一追问将引导我们去考察国际权势变迁更为广泛和深层的国内外根源。
(二)联盟作用论
如果说“经济决定论”注重一国内部的能力增长,那么“联盟作用论”则关心外部的联盟组合如何影响一国的能力状况。在国际关系史上,联盟现象无疑是最普遍和重要的国际群体行为之一,国家之间的联盟组合往往可以改变原有的国际力量对比,进而推动国际权势的显著变迁。正如丹·赖特指出的那样:“联盟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们是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首要外交政策手段,并且是战争爆发、扩散及其结果的决定性因素。”⑥
金祥宇系统分析了外部联盟对国家能力增长的影响,他首先质疑奥甘斯基仅仅注重内在要素的倾向,认为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存在两个基本弱点:第一,忽视了外部同盟关系的变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第二,难以解释前工业化时代的国际权力转移和战争行为。在质疑奥甘斯基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内部增长和外部联盟都是影响大国力量对比和权力转移的重要变量。正是内部经济增长速度和外部联盟关系的不同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再分配。⑦ 金氏的理论修正了传统权力转移理论只注重国家内部能力增长的观点,并将其理论解释的时间跨度拓展到工业革命以前,为我们理解国家能力增长的外部来源提供了理论支持。
由于战争是导致国际权势变迁最直接的因素,更多的学者主要围绕联盟政治与战争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展开分析。他们假定,在大国间实力对比没有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同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关键变量。范·埃弗拉就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即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常常是稳定的,而这时战争却又常常爆发,究其原因就是结盟或者外交所形成的“亲疏远近”的国家间关系使国家对能力状况判断发生变化。⑧ 联盟导致战争行为的更普遍解释是,一个联盟的出现经常会催生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充满相互猜疑和紧张关系的同盟,并将进一步固化军备竞赛和联盟结构,进而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⑨ 还有学者认为联盟政治的风险在于决策者倾向于将维系联盟存在视为目的本身,对盟友提供全力以赴的支持,而不管实际后果如何。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就将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危险的世界中处于外交孤立状态。⑩ 这样,联盟会鼓励一些小国的冒险主义行为,从而使得大国为顾全大局而被盟友的政策“绑架”,这也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几率和规模。
“联盟作用论”考察了外部力量组合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对联盟形成与战争行为的相关性做了深入分析。然而,学者们通过经验研究发现,联盟与战争之间的相关性是相对模糊的,在一些情况下联盟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在另一些情况下联盟却有助于维持和平。(11) 这就使得联盟理论难以对国际权势变迁提供一致性解释。此外,面对霸权的权力优势,国际体系的其他国家并不总是自动结成联盟对其进行制衡,而是选择搭便车、追随等行为,这将进一步巩固原有的力量格局而不是促进国际权势的变迁。
(三)意图支配论
不管是“经济决定论”还是“联盟作用论”都是在思考国家能力增长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图支配论”则尝试将国家的物质实力与安全观念结合起来,分析观念意图在国际权势变迁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分析了国家的成本收益考虑在国际体系变革中的作用。他假定行为体进入社会关系并创立社会结构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也就是说,新近获得权力的国家都希望建立一套国际制度以实现自身偏好的最大化,而国际制度的调整又将反映新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分布状况。因此,国际政治是否会发生变革取决于体系内的国家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一国就将力图去改变这一国际体系,相反国际体系就将继续处于稳定、均衡的状态。用吉尔平的话来说,“政治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社会制度与那些在该社会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者之中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12) 吉尔平特别强调,尽管人们把成本与收益作为可以定量分析的客观要素来谈论,可实际上它们都有很大的主观和心理上的成分。一个群体所谋求的利益以及它所愿意为之付出的成本,最终是由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和联盟所认识的那种利益来界定的。(13)
还有学者根据国家对国际秩序态度的差异区分出“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施韦勒的界定,所谓“维持现状国家”是指那些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对现存秩序心满意足的国家,而“修正主义国家”则指那些对现状极为不满,致力于打破现存秩序、改善自身在体系中的权力和尊严的国家。(14) 在早期,学者们倾向于将霸权国与现状满意、崛起国与修正意图画等号,认为霸权国往往对现状感到满意,以维护现存秩序为己任,而急剧崛起的国家则希望打破现状,以获得与其实力上升相称的权力地位。换句话说,正是崛起国的不满心理导致了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的战争,进而推动着国际权势的不断变迁。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霸权国更具修正主义意图。特别是当它感到国力日衰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压力时,霸权国倾向于发动预防性战争以阻止崛起国的权力增长。(15) 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国的心理变化更能解释霸权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权力变化。
学者们对国家意图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区分国家的客观实力与主观的政策行为,客观实力的变动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势的变迁,决策者的利益认知和风险偏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国家意图只是一个干预变量,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满意或不满很大程度上依旧取决于国家的相对实力。当实力微不足道时,一国即使心存抱怨也难以做出对抗性举措;相反,即使崛起国始终奉行维持现状政策,其实力的上升在客观上仍然会对既有国际秩序造成冲击,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四)制度决定论
上述三种理论是国际关系学者解释国际权势变迁的基本路径,而“制度决定论”则是比较政治经济学者的重要尝试,后者认为国家实力的消长和国际权势的变动,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内在的制度安排,制度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政府与社会关系、对外政策等各方面的差异。这就使得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规律,从而为国际权势的变迁提供了可能。
“制度决定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诺思,他和其合作者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做了权威解释。他们认为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对西方经济增长的解释都是错误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要素并不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增长本身。在他们看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发展出一套具有明晰产权、能够提供个人激励的制度安排,西欧发展起来的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6) 推而广之,诺思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去刺激个人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进行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诺思不无自信地得出结论:“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7)
除了诺思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制度视角回答大国兴衰这一重大历史和理论命题。比如熊彼特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最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创新者是否能够得到金融上的支持。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背后却是一整套有效的金融制度。(18) 尼尔·弗格森将英国的勃兴归功于四项具体的制度创新所结成的“权力方阵”,即培养大批文职和技术官员的税收官僚制、保护个人财产的议会制、鼓励私人领域金融创新的国债制度以及担当最终货款人重任的中央银行体系。(19) 中国学者也对制度与国际权势变迁的相关性进行了思考。张宇燕和高程认为,虽然来自美洲的金银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随机性的初始条件,但大规模货币涌入所带来的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变化最终诱发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才带来了经济绩效和西方世界的兴起。(20) 杨光斌强调了作为制度的政府治理形式的重要性,并通过考察东方帝国和西方现代强权的历史发展得出结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制度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21)
“制度决定论”强调实力增长背后的制度根源,认为制度效率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起伏,进而影响着国际权势的变迁。那么,什么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呢?在“制度决定论”看来,西方确立的以宪政主义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性制度安排无疑最具优势。然而,这既不能解释西方内部的制度差异对国际权势变迁的影响,也难以回答众多后发国家为何难以成功移植西方制度。因此,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考虑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社会环境,只有建立外来知识和内在需要相结合的制度结构才能真正推动国家实力的显著增长。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我们认为,各种既有理论从各自视角都提出了具有竞争力的解释,但它们对国际权势变迁的讨论并不充分。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知识扩散与国家学习的互动逻辑来探寻国际权势变迁的“秘密”。为了充分说明国际权势变迁的机理和影响,笔者并不局限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试图从一个极为重要和更长时段的个案人手,以期从特殊性中获得有关国际权势变迁的普遍认识。正如施普劳特夫妇所言:“尽管特殊个案经常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也有可能展示出范围更加广泛的类似现象。提出特殊个案蕴含的一般性问题,进而得出可运用于其他个案的基本性假设,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有趣和富有成效的。”(22) 具体地说,本文将研究的对象设定为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显著兴起,核心问题是西方持续近500年的国际主导地位为何会出现相对衰落?以新兴国家(23) 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何以在历经数百年的困惑和彷徨后方才找到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二、现代知识扩散:机理与进程
(一)知识扩散的概念和机理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识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24) 维基百科则将知识定义为主体获得的与客观事物存在及变化内在规定性有关的系统化、组织化的信息。知识必须具备三个特征:被证实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25) 在传统社会,知识主要依靠个体或组织的社会生产实践而获得,是经验性、无意识和偶然性的。现代知识则是自牛顿革命以来,建立在直接观察和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系统性认识。本文所讨论的现代知识超越了自然科学的狭隘范围,特指以现代性为内核、以工业化为表征的一切科学技术、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
知识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向外扩散。所谓知识扩散,是指知识通过一定的渠道从发源地向外进行传播和转移的过程。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长久独占。(26)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知识扩散的必然性。
第一,知识本身的流动性。由于不同地区知识占有的不均衡,知识存在着从高地流向低谷、由较先进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趋势。有学者借用物理学中势能和势差的概念分析了知识的传播机理。(27) 知识势能表征了某个体、某区域或某组织的知识能量的积聚以及人才、知识水平状态。由于它们之间的能力差异,知识资源在不同系统之中的分布呈现非均衡性,进而导致不同个体、区域和组织形成知识势能的差。在知识势能的作用下,知识流就像液体一样源源不断地从高知识势能的主体流向低知识势能的主体,从而导致了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举例来说,相对于封建性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高级别的知识势能。因此,当它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的亚平宁半岛诞生后就逐渐向四周蔓延开来。由于当时在东边的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的强大阻挠,资本主义呈现出向西边转移的历史路径,并最先促使西欧在近代世界的兴起。
第二,知识的社会化功能。笼统地说,知识分为形而上的抽象理念和形而下的器物技能两个层次,前者依靠直觉、灵感和思辨获得,后者则通过理性推理和观察实验得出。前者关注的是世界本原、自然与社会关系、社会规律演进等宏大问题,后者则注重社会子系统中具体的技术进步。但二者都具有现实关怀的指向,都试图通过作用于社会实践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当一项知识被确认为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进而令知识生产者获得某种竞争优势时,模仿者就会纷纷出现。红衣主教黎塞留率先抛弃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为法国霸权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进而,这一观念很快就被其他民族国家所效仿,它们根据国家利益需要随时变换联盟,目的就在于制衡任何可能在欧洲寻求霸权的国家。由此可见,知识的社会性必然导致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传播。
第三,知识的溢出效应。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由前现代向现代社会演进,国际体系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贸易兴起、军事扩张、对外殖民、宗教传播、人文交流等各种人类交往形式,在促进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互动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识的广泛扩散和传播。尽管这只是人类交往活动的副产品,但新的知识会逐渐在当地扎根,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是促使知识不断外溢的重要动力。追求霸权的帝国为了在殖民地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它会促使殖民地民族学习它的东西,还往往教给他们先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技术。(28) 而全球化则使得人类交往更加便利、频繁和常态化,进而也使得知识的溢出效应成倍增加。
(二)现代知识扩散的基本进程
既然如此,现代知识是如何扩散开来的呢?从现代化史观的视角来看,现代知识首先在欧洲生长出来,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东方文明的影响。(29) 在早期的欧洲,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经济上有多个竞争中心,不存在可以有效阻止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彼此争战的封建邦国也难以限制原始的军备竞赛。(30) 正是这种松散的政治格局和贸易体系加速了现代知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不断扩散。这就使得欧洲君主们在力量对比上不相上下,在政治影响上相互竞争,从而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国际体系。然而,相对于整个非西方世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聚集起了强大的知识力量。其结果是欧洲对非欧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入侵和支配,美洲、澳洲成为欧洲文明的外部延伸,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沦落为殖民地或附庸国,诸如奥斯曼、中国等古老帝国也未能幸免被半殖民地化的命运。(31) 随着美国的崛起,西方的地理范围和战略影响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然而,一旦西方确立起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开启新一轮的知识扩散。伴随着西方军事扩张和殖民战争,先进的技术和理念逐渐在非西方世界传播开来。首先得到扩散的是科学技术和武器系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一次科技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而后这一浪潮向东涌上了欧洲大陆,往西则扩散到南北美洲。随着西方的对外征服,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也逐渐生根发芽。科技革命带动了武器系统的升级和战争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工业化初期,长射程快发轻武器、火药填充弹重炮和蒸汽动力铁甲舰是主要的武器形态。而到19世纪中期,轻武器、火炮和战舰迅速在欧洲各国得到了普及,使得战争的方式和形态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32) 及至20世纪,航空母舰、战略导弹甚至核武器也已经得到极大发展,并成为更多国家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
其次,西方的制度结构也开始席卷全球。西方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摧毁了非西方世界落后的政治组织方式。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有效管理,西方将本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结构移植到这些地区。在中国,孙中山根据西方的宪政框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土耳其,凯末尔进行了一系列使得土耳其成为现代共和国的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改革,而这些都是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架构为蓝本的。在印度,甘地领导了一场大众民族运动,并发展出一个群众性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现代政党——国大党。如今,以定期选举、多党制、媒体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为指标的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政治选择。可见,促使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在帮助确立其优势的同时,也大大扩散到了全球。
最后,西方的现代观念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立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后来成为非西方世界反对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的有力武器。近代以来欧洲的均势外交成为后进国家处理地区关系时效仿的对象。欧洲创立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法体制是亚非拉国家争取自身权益、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依据。俄国“十月革命”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在非西方世界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亚非地区的反帝反殖运动起到了示范和激励效应。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更是成为当前世界的普世性价值,无时不影响着非西方世界的道路选择和现代化进程。
(三)新一轮的知识扩散浪潮
虽然知识扩散具有必然性,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知识扩散的速度并不迅速,而是呈现出随意性、依附性和非连续性的特点。随着人类逐渐步入当代社会,知识扩散的速度大大加快,知识的充裕和便捷正在改变世界的基本面貌以及我们对时代的理解。具体而言,知识在当代社会加速扩散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证自明。从农业时代使用铁器到工业时代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发明,再到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结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对知识扩散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技进步大大地扩展了现代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使得可供扩散的知识资源更加丰富。另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降低了知识扩散的成本,在信息时代,以前耗时费日的知识交流传递在瞬间就可以完成,从而为知识扩散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尽管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垄断和管制的种种障碍,但现代知识扩散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流向了上至政府机构、下至普通百姓的几乎每个角落。
第二,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究其实质而言,全球化是世界生活方式的逐渐同一化。从长期趋势来看,尽管遭受挫折甚至中断,但全球化无疑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方向。先是欧洲率先打破了封建式的城邦堡垒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继而挟资本主义的力量优势逐渐将亚、非、拉等地区纷纷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传统的、相互隔绝的区域相继被更大范围和更加复杂的实体所取代,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并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经历了一个高歌猛进的黄金期。正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伴随着各行为体互动的日益频繁,知识的加速扩散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三,知识经济的兴起。在前现代社会,农业是人类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土地、人口等要素展开。进入到现代社会,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国家主要的力量源泉,煤炭、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变成了大国角力的焦点。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显著兴起,知识日益成为生产要素的核心,在增强国家能力和确立竞争优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经济的兴起增加了人们对现代知识的需求,同时也凸显了知识扩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只有建立在知识广泛扩散的基础上,才能更加便捷地掌握知识,进而在未来的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国家学习与非西方世界对现代化的回应
正如许多学者观察到的一样,知识从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持续扩散乃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齐波拉认为,一个成长中的帝国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向其边界之外辐射,并对其邻国的发展作出贡献。(33) 吉尔平也直言:“军事和经济技术由较先进的社会向欠发达社会扩散,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关键因素。”(34) 现代知识在本质上代表了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潮流。由于率先开启这一潮流,西方牢固地确立起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然而,这些曾赋予西方向全世界扩张并征服巨大古老帝国的现代化潮流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即西方技术、制度和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不过,知识扩散并不必然导致剧烈的政治后果,非西方世界如何对其进行回应才是关键所在。正是非西方世界对先进知识技术和制度经验的学习,进而促使政治精英的观念变革和政治行动,才最终促成了非西方世界的觉醒。
(一)国家学习的理论来源和基本概念
学习理论是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考察个体或组织如何通过学习过程获得知识增长,进而改变行为模式、确立身份认同。对于个体来说,学习是获得知识和技能、实现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对于组织来说,学习是提高竞争水平、实现组织创新的基本路径。心理学者和组织学家对于学习的探讨为政治学家提供了重要启示。既然个体需要通过学习实现社会化,组织需要通过学习强化合作、提高效率,国家同样也需要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那么,国家的学习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国家层面的学习如何作用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个体学习能够与国家学习进行简单类比吗?这些问题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开辟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理论空间。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关系领域兴起了对学习理论的研究。罗伯特·杰维斯深入探讨了决策者如何从历史中学习以及错误学习的机理,(35) 约瑟夫·奈提出了“核学习”的重要概念,用于分析美苏在冷战期间如何通过相互学习达成关于核威慑的共识,进而建立起有限的安全合作机制。(36) 此外,学者们也检验了制度在促进学习方面的作用。通过提供信息、改变信仰系统、创设问题议程、协调合作,国际制度有效地促进了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和行为改变。(37) 在经验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冷战期间学习在帝国过度伸展、美国军事干预和美苏合作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38)
本文重点考察国家层面的学习,并将国家学习定义为一国根据既定目标,不断从历史或现实情景中习得知识经验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在主体上,主要考察国家以及体现国家意志的决策者和官僚机构,社会大众和一般组织的学习不在考察范围之内;第二,在性质上,学习应该具有战略性质,涉及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取向。简单的信息传递、短暂的行为变化并不能构成国家学习;第三,在内容上,学习包括已有和当前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包括技术工具、制度体制、价值观念等。其不仅是对他者经验的学习和模仿,也有对自身经验的反思和更新;第四,在状态上,决策者不是被动盲目地接受外来知识,而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有选择地进行学习,学习也不是一次性的简单反应,而体现为一种持续的过程。
事实上,任何政治行为都是被习得的,学习发生在国家政策的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代表国家的决策者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形势变化、改善认知结构。如果决策者不能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就会面临政策失败,甚至是个人权力的丧失。(39) 在单位层面,国家需要从历史中习得必要经验,避免以前的错误或应对当前的政策选择;同时也需要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知识经验,以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在单位互动层面,国家之间需要通过相互学习和适应,了解彼此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行为,改变零和博弈的效用结构,实现制度性合作。在体系层面,世界政治也可能在各国不断学习的基础上实现进化和超越。(40)
(二)非西方世界对现代知识的学习与回应
国家能够进行学习,并不意味着学习结果的必然优化。相反,如果国家对知识经验进行简单类比和生硬对照,往往存在着错误学习的可能性,其习得的内容只能对国家的政策选择形成误导。换言之,由于在自然禀赋、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学习能力并不一致。一国学习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态势。正如唐世平教授所言:“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竞争和兴衰,也同样基于其所拥有的学习能力。一个领先的国家可能因丧失学习能力而落后;相反,一个暂时落后的国家只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赶超比自身更发达的国家。”(41)
通过国家学习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出非西方世界对现代化的回应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而态度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学习能力的强弱以及其在近现代的道路选择和国家兴衰。第一种态度是回到过去的“复古主义”。这些国家往往在前现代社会是某一区域的中心,拥有辉煌的历史记忆和相对成熟的制度安排。尽管面临着人口与资源持续紧张、官僚机构膨胀和腐败等问题,但政治秩序基本是稳定和可控的。面对西方开启的现代化潮流,他们感到恐慌、不满,甚至仇恨。在他们看来,正是西方的野蛮屠杀和残酷征服摧毁了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传统秩序,所谓的现代化是西方殖民势力强加的结果。因此,他们学习现代化的目的不是要顺应这一潮流,而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重新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42)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即是此类态度的典型代表。
第二种态度是全盘西化的“浪漫主义”。持此种态度的政治精英往往拥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他们率先开眼看世界,对传统体制的失效有切肤之痛,对西方的现代知识推崇备至。他们认为,传统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智慧不但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潮流格格不入,而且成为阻碍其走向现代社会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想拥有美好未来,就必须彻底告别过去。相应的,他们相信西方代表了现代化的唯一正确方向,只要全盘西化就能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先进性不仅表现为有形的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更体现在无形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因此,学习西方不仅要在器物层面下工夫,更要复制西方的制度安排,甚至应该按照西方标准来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现代化”。
第三种态度可以称之为适应性调整的“改良主义”。这种态度倾向于将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43) 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工业力量、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代表了新的知识力量,只有积极向西方学习才能适应不断变迁的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反思传统体制弊病的同时,也看到其价值所在,拒绝将这些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应对现代化不力的事实归罪于历史文化,甚至是人种本身。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态度不是全盘照搬和简单移植,而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主动和有选择的学习,这不仅包括外来知识的本土化适应,而且还内含有一些重大创新,其根本指向是要建立基于外来知识与内在需要相结合的现代化。
以上三种态度代表了非西方世界对现代化回应的基本模式。(44) 第一种态度将西方扩张视为与以往一样的简单军事征服,而没有看到一种新的更高级别文明的到来。退回到传统堡垒非但没能帮助他们重建秩序、抵抗西方侵略,相反却被工业化力量彻底征服,进而滑入到国际体系的最底层。第二种态度不顾现实国情而简单移植西方知识,结果导致水土不服,出现“南橘北枳”现象。比如不少后发国家具备了民主的外在形式,却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在缺乏妥协精神和法律秩序的情况下匆忙开放大众参与,导致政府权威迅速萎缩,并不时经受着政党纷争、族群矛盾和社会撕裂之痛。第三种态度代表了一部分政治精英相对理性的看法。他们既反对盲目复古的做法,同时也排斥不顾国情全盘西化的行为,而在自主意识和开放心态下寻求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非西方世界的学习能力差异及其对国际权势的不同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当现代化潮流袭来时,非西方世界事实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对现代知识的扩散,非西方世界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由于现代化意味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宏大转型,其间必然经历复杂激烈的利益博弈、制度重组和观念碰撞。不仅如此,工业文明所代表的进步力量始终与西方野蛮的对外殖民和武力征服联系在一起,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非西方世界在抵制与接纳之间的矛盾摇摆。再加之非西方世界内部各方面的显著不同,这些国家对现代知识的学习一开始就表现出深刻的差异性,这不仅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命运,也影响着国际权势变迁的演进轨迹。
对于奉行“复古主义”的国家,其学习的结果是拒绝做出任何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决策者的认知偏好有关。如前所述,这些国家在前现代社会往往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功,这种历史记忆已经内化为决策者稳定的认知偏好。当面对新的知识体系时,他们并不是无意识地进行学习,而倾向于选择有利的信息来强化原有的认知。决策者则有意回避,甚至对那些陌生或不利的信息视而不见。(45)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并不能推动决策者的观念变化,反而维持和强化了既有的看法。在“回到过去”这一观念的推动下,决策者对现代知识采取排斥战略,整个国家仍然处在前现代社会当中。当然,由于整体力量的弱小,这些国家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败下阵来,最终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得到进一步拓展。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仍然运用各种非对称手段继续“作战”,通过战术性动作来削弱西方的外来影响。
奉行“浪漫主义”的国家在学习时则犯了简单类比的错误,以为只要全盘接纳外来知识就可以包治百病,实现自身的转型和兴盛。然而,问题是任何知识的产生都有着特殊的土壤,知识运用同样也有着相应的边界。如果仅仅看到知识的外在形式而忽视知识得以成功实践的限制条件,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换言之,许多国家在盲目崇拜的心态指引下不加辨别地拥抱西方,既没能学到外来知识的精华,又人为割裂了历史传统,造成发展进程一波三折,甚至有的沦落为“失败国家”。就其对国际权势结构的影响而言,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的学习态度有助于强化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结构,然而随着其内部治理问题的暴露,他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这种“浪漫主义”式学习,从而影响到西方世界的合法性和权威形象。
新兴国家代表了非西方世界应对现代化的第三种态度。尽管在现代化潮流到来之初,新兴国家也经历了迟疑、困惑,曾经在复古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痛苦徘徊,但最终选择了相对折中的改良主义道路。在现代知识加速扩散的背景下,新兴国家经过长期适应已经积累起了相对强大的学习能力,并将外来知识与本土经验相互对接,建立起支撑国力增长的现代国家能力结构。正是立基于此,新兴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显著提升国际地位,进而在非西方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支日益崛起的战略力量。尽管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持满意态度,但其崛起态势在客观上影响了西方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并不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出现的事态,而是一个自近代以来持续存在的历史进程。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更涉及国际力量中心转移和权力的再分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基于西方强大的实力影响和话语优势,非西方世界对现代知识学习的结果一开始都强化了原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但挑战也随即而至。奉行“复古主义”的国家对西方的统治地位充满抱怨、愤恨,通过从消极抵抗到主动出击的一系列手段来削弱西方的影响。奉行“浪漫主义”的国家则由于全盘西化的激进政策导致了内部的发展困境,从而对西方国家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挑战。奉行“改良主义”的国家尽管在姿态上相对温和,但构成的挑战却最具深刻性。伴随着这些国家群体崛起的态势,它们正逐渐从经济、安全和文明层面对西方的主导地位形成全面冲击。
四、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及其前景
知识扩散与国家学习构成了国际权势变迁的基本动力。现代知识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开始了其对外扩散的进程。不可避免的知识扩散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长久维持其对先进科学技术、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的垄断。但知识扩散的后果则取决于他者的学习努力程度。由于内部的巨大差异性,非西方世界表现出不同的学习能力和意愿。新兴国家展现出了相对强大的学习能力,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却效果不彰。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整体,非西方世界经过长期学习和不断试错后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知识基础,实现了普遍的政治觉醒,现代化的基因也逐渐在其内部扎下根来。可以说,知识扩散为国际权势的变迁提供了潜在可能,而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学习则使其变成了客观现实,二者结合共同造就了西方统治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显著兴起,带来了国际权势结构三个层面的根本性变化: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并持续500年的国际等级秩序面临瓦解,权力结构的多极化成为大势所趋。由于率先产生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西方挟工业化之威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建立起了一个西方以美国为核心、全球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双重等级体制。(46) 这种等级体制体现在物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在物理上,占世界人口10%左右的西方掌握着超过2/3的人类财富和力量,他们拥有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难以匹敌的军事力量以及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西方同样建立起了无处不在的道德优越感,不仅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国际规则和问题议程,而且其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更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
然而,在非西方世界显著兴起的背景下,这一金字塔形的国际等级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在物质领域,以经济力量对比为例,尽管西方发达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工业基础、贸易总额等方面仍然占据优势,但新兴经济体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迎头赶上,并在增长速度、经济贡献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展现出竞争优势。从2000年到2008年,新兴经济体九国(47) 占全球GDP比重从11%上升至15.7%,份额增长近40%,而西方七国的份额则从77%下降至55.8%。(48)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新兴国家追赶西方的过程。据IMF预测,危机结束后的前6年(2010—2015),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计算,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都将持续下降,到202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版图亦将出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的格局。(49)
在心理上,“凡是西方的就是美好的”这一神话正在破灭。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得人们相信美国军队并非战无不胜;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意味着西方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存在保留;非西方世界多不胜数的悲惨案例则告诉我们,依靠简单移植甚至武力强加的民主实验带来的不是鲜花和福祉,而是政局动荡、族群分裂和秩序瓦解。所有这些都加剧了西方的道德尴尬,寻求文化自主性得到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的认同。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正凭借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和道德自信,冲击着传统的国际等级秩序,推动着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国际体系不再是西方世界的简单延伸,呈现出更为异质、多元的色彩。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随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自此以后,欧洲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相继登场,上演了一幕幕争霸与制衡的斗争。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俄罗斯不仅不时进入体系中心,成为欧洲权势分布的仲裁者,而且通过持续扩张将国际体系的范围拓展至远东地区。随着美苏权势的兴起,欧洲的传统中心地位不复存在,但国际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的地理和文化背景。相对于西方大国的权力更替和国家兴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只能充当附庸和从属的角色,帝国主义力量时而对其竞相争夺,时而又共谋瓜分,甚至其命运只是西方在世界地图中随意一划的结果。正如一位新加坡学者的描述:“在过去三个世纪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是世界历史的客体。推动历史的决定是在少数西方国家的首都敲定的,如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被错误命名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在没有询问过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情况下开打的。他们本属于一场欧洲战争——至少在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之前是这样。”(50)
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西方世界开始了普遍的政治觉醒,国际体系的西方色彩随之逐渐褪去。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欧洲殖民者开始陆续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撤退,非西方世界成为主权平等、政治独立的实体。不仅如此,基于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和渴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共同诉求,非西方世界相互团结、彼此合作,组织“不结盟运动”、召开亚非会议、建立“七十七国集团”,凡此种种都意味着非西方世界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当然,由于整体实力太过弱小,他们始终被美苏冷战对抗的阴影所笼罩,并且面临着内部转型的种种难题。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非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国家开启了市场导向的内部改革,并通过和平手段加入到现行国际体系中去。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历史进程。其结果是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继政治独立之后又实现了经济崛起。随着西方国际权威因对外战略失误和内部经济问题而下降,非西方世界开始伸展独立意志和国家抱负,在解决传统安全和全球问题上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换言之,非西方世界不仅不再是被随意入侵、分割和压迫的对象,而且将自己的独立声音、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带人到世界舞台中来,国际体系呈现出更加异质、多元的色彩。
第三,世界范围内的体系性战争难以再现,但将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部冲突和大国竞争。自中世纪大一统梦想破灭以来,欧洲呈现出一种政治破碎、资源匮乏和安全脆弱的局面,内有新兴民族国家的群雄并起,外有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觊觎。正是在这种严峻环境的刺激下,欧洲发展出了一套基于人性本恶和强权有理的丛林生存法则。在其指导下,欧洲不仅在本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频繁不断的战争。当然,在近代社会早期,列强之间的战争规模和烈度相对较小,战争目标也比较有限。随着大众政治的兴起、武器系统的更新和传统道德约束的松绑,局部性冲突就逐渐演变为体系性战争。现实政治最终自食其果,不仅造成了深重的人类灾难,也葬送了欧洲的中心地位。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尽管核武器的出现抬高了战争成本,但国际社会没有一刻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阻止大国进行体系性战争的因素不断增多。从消极意义上,战略武器的持续扩散和不断升级已经使核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从积极意义上,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利益融合和合作空间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新兴国家日益崛起,它们奉行的政策取向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因而成为保障国际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竞争,国际社会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在地区层面,霸权国权威的下降增加了中小国家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局部性的冲突和战争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在体系层面,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全方位竞争不可避免,包括在经济上竞争市场份额和世界资源,安全上竞争同盟国和战略伙伴,政治上竞争国际支持和议题设置,发展模式上竞争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影响。可见,在国际权势变迁的背景下,合作空间和竞争因素同时存在,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西方和非西方尤其是新兴国家能否发展出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从双边博弈转向全球视野,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共识。
五、结语
国际权势变迁一直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常态。与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更替相比,新一轮的国际权势变迁具有根本性意义。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相对衰落的态势,非西方世界则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独立意志对现有国际体系施加影响。知识扩散与国家学习共同造就了这一宏大的政治图景。随着重新确立新的权势中心,下一轮知识扩散和国家学习又将开启,而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来源和学习对象。当然,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并没有即刻完成。一方面,西方的权势目前只是相对下降而非绝对衰落,在国际制度、定价权和话语权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如此,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也在进行自我调适和重新改革,以稳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非西方世界内部面临的转型困难异常艰巨。新兴国家需要应对经济增长、政治变革和社会治理的多重挑战;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一部分“失败国家”则还在为生存而拼命挣扎。因此,历史从来不会线性发展,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将是一个持久、漫长的转型过程。但从总体进程而言,西方统治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显著兴起将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两者共同塑造着未来世界政治的面貌和特征。
注释:
① 谢枳予:《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5页。
②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Chapter I.
③ Ibid.
④ 相关研究参见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 Charles A.Kupchan,et al.,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 Ronal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中国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评介参见李小华:《“权力转移”与国际体系的稳定——兼析“中国威胁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杨成:《对世界力量转移的系统分析——理论、历史及其区域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2期;朱锋:《“权力转移”理论评述》,《欧洲》,1998年第1期;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⑤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⑥ Dan Reiter,“Learning,Realism,and Alliances: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World Politics,Vol.46,No.4,July 1994,p.490.
⑦ Woosang Kim,“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World Politics,Vol.45,No.1,October 1992,pp.153—172.
⑧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Roots of Conflict,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Conclusion”.
⑨ See K.J.Holsti,et 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New York:John Wiley,1973,p.33; M.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John Wiley,1957,p.24; 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774.
⑩ Jack S.Levy,“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Behavior:An Analysis of the Great Powers,1495—1975”,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5,No.4,December 1981,p.582.
(11) Alastair Smith,“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No.4,December 1995,pp.405—425.
(12)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13) 同上书,第57页。
(14)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l,Summer 1994,pp.87—88.
(15) 相关研究参见 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16; Emerson M.S.Niou and Peter C.Ordeshook,“Preventive Wa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A Game-Theoretic Approach”,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1,No.3,September 1987,pp.387—419; Jack S.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World Politics,Vol.40,No.1,October 1987,pp.82—107; Randall L.Schweller,“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World Politics,Vol.44,No.2,January I992,pp.235—269;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Roots of Conflict,Chapter 4.
(16)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7)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页。
(18)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74页。
(19) Naill Ferguson,The Cash Nexus: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New York:Basic Books,2001,pp.15—16.
(20)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4—26页。
(21) 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91页。
(22)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he Dilemma of Rising Demands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World Politics,Vol.20,No.4,July 1968,p.660.
(23) 此处所指的新兴国家主要包括“金砖四国”、“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等名词涵盖的国家,它们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潜力,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显著提升。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67页。
(25) 参见维基百科网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
(26)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93—294页。
(27) 参见陈武:《知识传播机理的物理学视角探讨——从知识势差的角度来解释知识流动》,《科技和产业》,2010年第1期,第110—111页。
(28) John K.Fairbank,et al.,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p.487.
(29) 约翰·霍布森认为东方通过两个主要步骤促进了西方的崛起:传播/吸收和掠夺。首先,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缔造了一种全球经济和全球联系网,这些更为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如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通过东方全球化的途径传播到西方,然后被其吸收。其次,1492年后的西方帝国主义导致欧洲人攫取了东方各种经济资源,从而使西方崛起成为可能。参见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3页。
(30)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4—26页。
(31) 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第1页。
(32)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第76—77页。
(33) Carlo M.Cipolla,eds.,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London:Methuen,1970,p.5.
(3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80页。
(35)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六章。
(36) Joseph S.Nye,“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3,1987.
(37) 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281.
(38) See 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Janice Gross Stein,“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1,1994; Joseph S.Nye,“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Russell J.Leng,“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Coercive Bargaining in Recurrent Crisi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7,No.3,1983.
(39) George W.Breslauer and Philip E.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1,p.3.
(40) See George Modelski,“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1,Winter 1990.
(41) 唐世平:《国家学习能力与中国的赶超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42页。
(4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修订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35页。
(4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44) 这里列举的三种态度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事实上,在非西方世界,这三种态度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的国家首先尝试一种道路,经过挫败和重新学习后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同时存在着持三种态度的政治精英之间的路线斗争。
(45)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四章。
(46) 周鑫宇:《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8期,第31页。
(47) 新兴经济体九国指“金砖四国”和“展望五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
(48) 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1页。
(49)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世界大变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50) Kishore Mahbubani,The New Asian Hemisphere: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p.5.
标签: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