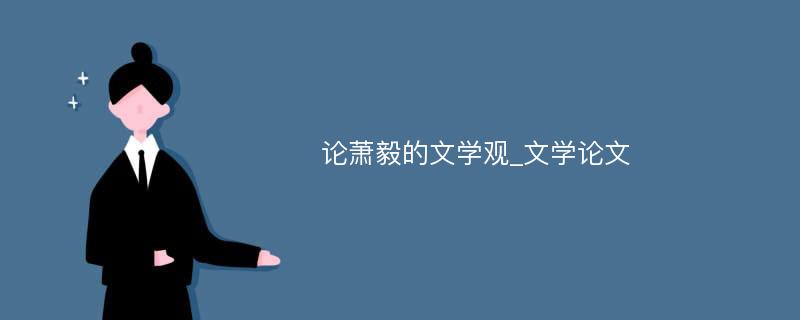
论萧绎的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论萧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武帝萧衍的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都在中国诗学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业绩。以齐梁的萧氏兄弟比汉魏的曹氏兄弟,犹贯珠联璧,堪称美谈: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已。
萧绎(508~555),字世诚,自号金楼子,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梁武帝萧衍第七子,是萧统、萧纲的弟弟。初封湘东王,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侯景作乱,他奉命在江陵举兵讨伐,大宝三年(552),平定侯景之乱,即帝位于江陵, 史称梁元帝。在位三年,西魏攻破江陵,他被杀,追尊为孝元皇帝,庙曰世祖。
萧绎幼年患眼疾,盲一目,然颖悟好学,五岁能诵《曲礼》,六岁解为诗。及长,不好声色,博览群书,平定侯景以后,似大有作为,然梁中兴的局面只是昙花一现。
作为一个人,萧绎既聪明、博学,又迷信、偏执;明明知道清谈误国(注:《金楼子·立言》篇云:“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务。中原丧乱,实为此风,何(晏)、邓(飏)诛于前,裴(頠)、王(衍)灭于后,盖为此也。),但习性不改,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仍在清谈,讲不着边际的学问;思想老在某种极端中徘徊冲突。《梁书·元帝纪》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禀性猜忌”,不肯把大本营移到金陵,致使自己过于靠近西魏前线;而且不怎么留心政道,“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既没有领导艺术,也不了解下情,在政治、军事、管理,做皇帝方面都没有才能,但是一位绝对优秀的学者和读书人。在西魏的军队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他仍于龙光殿为群臣讲解《老子》义,由“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直到魏军围襄阳,内外戒严,他才停讲。在西魏大军攻打江陵最危险的时候,他兼通的儒学、道学、文学、玄学、史学关键时刻都帮不上忙。冬十月,魏军兵临城下,他出枇杷门,亲自临阵督战,无奈梁六军败绩,魏军破门,他回天乏术,遂与太子及江陵男女百姓数万口均遭荼毒。
萧绎下笔成章,才思敏捷,为世所称。四十七岁,已留下惊人的著述,计有《金楼子》、《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注汉书》、《周易讲疏》、《内典博要》、《连山》、《洞林》、《老子讲疏》、各地地方志等四百余、文集五十卷,但多有散失,明人张溥辑有《梁元帝萧集》。
像他的人一样,萧绎的文学观向来为研究者把握不准。从他姓萧,是萧统、萧纲的弟弟,一家兄弟并称“三萧”,有的学者就以为他们的观点类似,对文学的看法也属齐鲁之政,兄弟之文,归为一派;从他《金楼子·立言》篇为文下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看,有的学者就以为萧绎和萧纲是形式主义的代表;从萧绎反复提倡“立言不朽”和《金楼子》中自比周公、孔子、太史公和其他儒学气息很重的话来看,有的学者又以为他与萧统文学观相同。
总之,对“三萧”的态度和评价,比较多的研究者是:基本肯定萧统,正面批评萧纲,完全忽略萧绎。
像刘勰撰《文心雕龙》,钟嵘撰《诗品》,刘昼撰《刘子》,萧统编纂《文选》一样,萧绎撰有《金楼子》。晋宋以来,齐梁之际学术之昌盛,文化氛围之浓厚,著书风气之盛炽,由此可见一斑。但不可理解的是,《金楼子》像它的主人一样被历史忽略了。
梁代那么重要的一部典籍,使中国文学从历史、哲学、各种非文学的母胎中分离、发展,并取得独立的标志性理论之一,以致有些日本学者以为可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鼎足而三的萧绎的《金楼子》,目前的研究者却很少,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到了即将结束的世纪末,对于《金楼子》,我们应该说一声惭愧。
因为,我们老是引它的《立言》篇以为己用,引《立言》篇又老引那么几句,对《立言》篇以外的部分,就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当前,研究《文心雕龙》已经热火朝天,拥有“龙学”、“龙刊”和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研究《诗品》也逐渐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时,《金楼子》仍少人问津,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研究专著,大陆甚至没有一本注本(注:关于《金楼子》的注本,十多年前曾由新嘉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出版过一本由台湾王梦鸥教授指导、由许德平撰写的硕士论文《金楼子校注》。荜路蓝缕,甚为难得。),论文也只有寥寥几篇,这种情况,正如它在历史中散失、湮没不彰,如今靠类书辑佚流传有着同样悲剧性的结局。
萧氏三兄弟出身同一个家庭,有相同的思想环境、读书方式,使他们都兼通儒、佛、道,和很类似的知识结构。但由于经历不同,年岁的差别,特别是他们各自形成的文学集团不同,受不同文人的影响,使他们的文学观产生差异。若仔细分析他们的理论,不偏不倚地全面考察,则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三萧”是三个圆圈,萧统在前,萧纲在后,萧绎居中;居中的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萧纲有部分重叠;与萧统重叠的部分多,与萧纲重叠的部分少;可知萧绎的文学观,虽与萧纲有相似的地方,但比较而言,更接近萧统。
如果把齐梁以来的文学观分为(一)“国史守旧派”;(二)“儒学折衷派”;(三)“审美新变派”,那么,萧统、萧绎可归于“儒学折衷派”,尽管萧绎在很重要的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方面与萧统异而与萧纲同。
在另一个文学集团里,与萧统、萧绎走着不同道路的萧纲和萧子显的文学观念,则属于“审美新变派”,代表了齐梁文学发展方向的另一种新思潮。
萧绎与萧统接近,其共同的核心在儒学思想折衷及中和美学方面,两人的文学观不仅有不兼容的地方,总体特色也不同。
萧统更多的时候体现“共性”,萧绎则体现“个性”;与萧统“兼容”的,“包罗”的,“集大成式”的编纂思想和著述态度相比,萧绎则有“个人”的、“独特”的,“私家著述”的特点;体现萧统特点的是《文选》,体现萧绎特点的是《金楼子》。
对文学的发展,萧绎、萧统有相似的观点。萧统的观点是在《文选序》里正面提出来的,他要选“文”,就必须说明“文”的发展演化问题;但萧统的论点,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说的:“时运交替,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大致相同,没有特别的新意和独特的解会,只是儒学气味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淡薄一些。划时代的《文选序》要求立论稳妥,立论稳妥就难以有新意和独特的解会。
萧绎则不同,萧绎没有正面论述文学的发展问题,但在他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涉及到“论文之理”和“属词之体”: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
由于时代的发展,时事的变化,文学,包括文学的体式也会发展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就这个结论,萧绎也与刘勰、萧统相同,但“论文之理”,即评论的理论、观念也会随时代、时事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却是萧绎个人极富创造意识的新见,是前人没有说过,后来的文论家也很少涉及,应值得我们珍视的。萧绎《金楼子》的论述,会突然有你想不到的精彩之处往往如是。
在文学思想方面,与萧统一样,萧绎也非常重视儒家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穆叔把人死后的“不朽”分为三等,第一是“立德”,第二是“立功”,第三是“立言”。“立言”的“言”,在《左传》的时代,指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政教言论,以后被人奉为圭臬,成为儒学中的经典,并深深地影响了萧绎,在萧绎的《金楼子》里,经常有关于儒家立功、修德的论述,如《立言》篇:
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汉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宝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万之众而不反,岂非儒者之贵乎?
《书》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君子之用心也,恒须以济物为本,加之以立功,重之以修德,岂不美乎?
“立言”的思想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进化,至魏晋时代曹丕给予它新的涵义。
曹丕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思想观念和现代语汇对“立言”加以阐释,使之变成“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把文章的作用上升为可以超越时空、超越贫贱、超越自我个体生命和政治生命永恒而辉煌的事业。
曹丕的这一关于“文章”和“作者”的认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划时代的意义至齐梁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一种共识。
萧统从要求极严的属于子书的《典论》中,选出《论文》一篇,就是发现了其中的意义,要不是萧统《文选》选录,《典论·论文》很可能和《典论》的其他篇目一样湮没不彰;而萧绎则正面赞同曹丕的观点,不仅是赞同,而且是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照着做,《金楼子序》说:
余以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言立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
萧绎明确说自己的“述作之志”,是受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金楼子》卷十三《杂记》篇又转述曹植《与杨德祖书》说:
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将采史官之实录,时俗之得失,为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此外徒虚言耳。
在萧绎的一生中,读书和著书立说的时间,确实比他搞政务、搞军事的时间更长。对曹丕“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的紧迫感,萧绎同样有十分敏锐的感觉,《金楼子》第六卷《自序》篇中说:
人间之世,飘忽几何;如凿石风火,窥隙观电,萤睹朝而灭,露见日而消,岂可不自序也。
七句话,六句用了四只比喻,如火、如电、如萤、如露,写时间暂短,人世袂忽,反衬应抓紧时间立言,此时不写“自序”,更待何时也?不仅如此,萧绎对自己期许颇高,自视颇高,在儒学和著述上,大有不让前贤,舍我其谁的口气,《金楼子·立言》篇说:
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
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曹植为文,有反胃之论。生也有涯,智也无涯;以有涯之身,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
把自己与周公、孔子、太史公放在同一个坐标上,并用与孔子的“获麟”比喻自己写作《金楼子》,萧绎正是在非常个性化语言中,通过对生命的失望表现自己对《金楼子》“绝笔”式的重视。
萧绎写作《金楼子》是为了立言,立言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立言”要求“言”对政治教化,对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萧绎非常重视这种作用,《立言》篇说: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
用“叙情志”与“敦风俗”两条标准,赞美由诸子发端,盛于两汉,迄于今日的私家著述的美者,表现了与萧统相类似的观点。即文学“美者”的价值,既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作用,又要能抒发情性,有娱宾遣兴的功能。兼顾社会作用和个人性情的两个方面,立论与萧统同样稳妥。
在“文”与“质”,“典”与“丽”的中和美学方面,萧绎的观点与萧统也别无二致。萧绎在《内典碑铭集林序》论述的中和美,包括“实”与“味”,“艳”与“华”,“质”与“野”,“博”与“繁”,“省”与“率”,“文”与“质”,“约”与“润”,以及这些美学范畴的对立统一与文章体制、风格的关系,甚至比萧统在《文选》和《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论述得更详尽彻底:
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裁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
文辞“繁”,文骨就“弱”,但过于“省”,又会感觉“草率”;“华丽”有余,就会失去体格,过于“质实”,文章又会淡而无味,做到中和美很难,所以要“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在诸多美学因素上保持均衡。
以上说的,除了表明萧绎与萧统同具儒家中和美的观念,还讲了如何在文中使用事类典故,典事和新意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前代和同时代文论家很少正面论述的。
钟嵘《诗品》论诗,反对在诗中用典事,但不反对在“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中运用(注:钟嵘《诗品序》云:“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但在“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中如何用典事?钟嵘没有说明;刘勰《文心雕龙》专设《事类》篇,讲事类与文章的关系;与钟嵘不同的是,他不仅赞成在文章中用事类,而且赞成在诗歌中用典事,把事类典故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注: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但是,刘勰主要强调文章用事类典故的重要性,对如何运用事类的方法仍然讲得很简单,也没有从美学范畴、对立统一的角度加以说明。
与刘勰相同的是,萧绎也认为文章中应该征引事类,否则文章的“新意”将“无所倚约”,但他对征引事类则理解得比较全面,深知引用不当引起的种种弊端。所以说明具体引用时的注意事项:譬如,引用的事类要广博,但意思不能重复雷同;引用的事类要条理清晰,安排妥帖,但不能过于拘谨,以致显得呆板木然,“事似牵课”;应该信笔挥洒、“博涉”,但不能有伤整饬,使体制变形。总之,要“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明确“事(类)”、“言(辞)”与“意”、“理”的主、从关系和具体写作时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方法。因此,萧绎关于事类的论述,对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篇无疑是一个补充。
没有证据说萧绎的立言思想来源于萧统,也没有证据说萧绎写作《金楼子》是受了萧统编纂《文选》的影响。但是,诸王之间、兄弟之间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集团和著书立说方面竞争得非常激烈却是不争的事实。
萧绎与萧统文学观不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对“文”审美特征的认识有深、浅,宽、窄的不同。这就是《立言》篇中经常为人们提及的: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风谣”,是指受民歌影响的乐府诗,也是当时文人创作的时尚。与钟嵘《诗品》评曹丕、谢惠连、吴迈远、鲍行卿使用过的“新歌”、“绮丽歌谣”、“风人答赠”,“风谣”是同一个意思。
这表明了萧绎心目中的“文”的审美特征,要像流行的吟咏情性的歌谣,有流连情思的作品才能称之谓“文”;至于“文”的标准,必须像精美的丝织品那样文采绚烂,音节要靡靡动听,语言要精练,要有动荡感人的情思性灵。这是萧绎论文的核心,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和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萧绎也指出今之士俗的浮华轻靡,《立言》篇反对“缙绅”之士和“闾巷小生”推波助澜的不良风气;“夫今之俗,缙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使人联想起钟嵘《诗品序》中“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和“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的话,但是,萧绎对“文”流连哀思的内容特性,在文采、声韵、情灵上的美学要求,不仅比萧统《文选》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向纯文学的方向发展。并且,还以此为思想基础,在实际选录作品的标准上,也表现出与萧统,同时与钟嵘《诗品》大异其趣。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说: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於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於世。衔酷茹恨,彻於心髓!操行见於《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萧绎在蕃王宅邸,曾命萧淑参与编纂诸臣僚友之文,成《西府新文》十一卷。西府,即江陵萧绎的蕃邸,江陵是萧绎奉诏讨伐侯景的起兵之处和即帝位地方,同时是当时梁代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最高军事指挥所和萧绎最后的葬身之地。
萧绎编《西府新文》事,在萧统编《文选》之前?还是编《文选》之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留待他日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府新文》中的“新文”二字,表明了萧绎选文的标准和对文的要求,当与他自己所提倡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理论有关,而与萧统编纂《文选》时的选文标准和对文的要求不同。
萧绎的《西府新文》唐代仍可以看到,《隋书·经籍志》里仍有著录,但今佚不传,这使“新文”的具体内容,究竟哪些作品被选入?称为“新文”,已难详悉。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颜之推的父亲颜协的作品一篇也没有入选。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所谓“吾家世文章”,说他家族的文学传统,一点也没有夸张,颜氏家族确实有着非常优秀的文学传统。
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曾撰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对颜协的文学活动,《梁书·文学传》曾有记载:“颜协,字子和,琅琊临沂人也。七代祖含,晋侍中、国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见远,博学有高行……协幼孤,养於舅氏。少以器局见称。博涉群书,工於草隶。释褐湘东王国常侍,又兼府记室。世祖出镇荆州,转正记室。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与协同名,才学相亚,府中称为‘二协’……大同五年,卒,时年四十有二。世祖甚叹惜之,为《怀旧诗》以伤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宾实;鸿渐殊未升,上才淹下秩’。”《北周书·颜之仪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注:《北周书·颜之仪传》曰:“父协,以见远蹈义忤时,遂不仕进,湘东王引为府记室参军,协不得已乃应命。梁元帝后著《怀旧志》及诗,并称赞其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点,一是颜协确有才学,以致萧绎《怀旧诗》也说他“上才淹下秩”,为他惋惜;二是颜协撰有诗赋铭诔书表启奏各种作品可供萧绎编《西府新文》选择;三是颜协死后萧绎叹惜、怀念,又写《怀旧志》,又写《怀旧诗》,说明与颜协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萧绎命萧淑编纂《西府新文》,对颜协的作品一篇也没有选录,好让颜之推伤心。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不可妥协的观念上的。正是颜之推说,是他的父亲颜协“亦以不偶於世”,作品“无郑、卫之音故也。”
这里的“郑、卫之音”,指当时的浮华轻靡之文,其实是一种当时流行的新时尚。
《南史·萧惠基传》说:“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钟嵘《诗品》转述从祖钟宪说的:“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美文”,其实是当时流行的“新”文,是文人学习民歌以后形成的新风格。萧绎《西府新文》选录的,也许正是这种“新文”和“美文”。
颜协的作品“讫无一篇见录”,是因为没有带郑卫之音的“新文”和“美文”,没有“新文”和“美文”,照颜之推的言外之意是“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不屑为之。
这种“新文”和“美文”的骇世“动俗”,与当时人的审美意识新变互为因果。萧绎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动俗”与“新变”所代表的新的美学内涵,并形成自己新的文学思想,这使他在对“文”的审美特征上,有比哥哥萧统更深的认识,对“文”、“笔”的解释也更纯粹,更接近当代意识;同时,像颜协,自己很欣赏的才学之士,因为坚持“典正”,“不从流俗”,所以只能“讫无一篇见录”,这些都是必然的。
有意思的是,钟嵘对大明、泰始以来的“美文”及“动俗”的风气,基本上采取了贬斥的态度,而坚持“典正”,“不从流俗”则被当作优点来赞美。《诗品》“齐黄门谢超宗”等七人条即赞美“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这是钟宪影响下钟嵘的文学观。
还有,钟嵘《诗品》对所有带民歌意味的风谣诗,及其诗人,都给予较低的评价。如评曹丕“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评谢惠连“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评吴迈远“吴善于风人答赠”;评鲍行卿“甚擅风谣之美”。这些都是对中、下品诗人给予的中、下品评语。而萧绎却把“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中的“风谣”作为“文”的标准风格,其文学观不同也如是。
《北史·文苑传序》论当时的文风说:
简文(萧纲)、湘东(萧绎),启其淫放。
把萧绎与萧纲相提并论,说他们共同开启了“淫放”之风,也许说得夸张了一点,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文学的审美特征方面,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不同,与钟嵘有别,倒与萧纲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