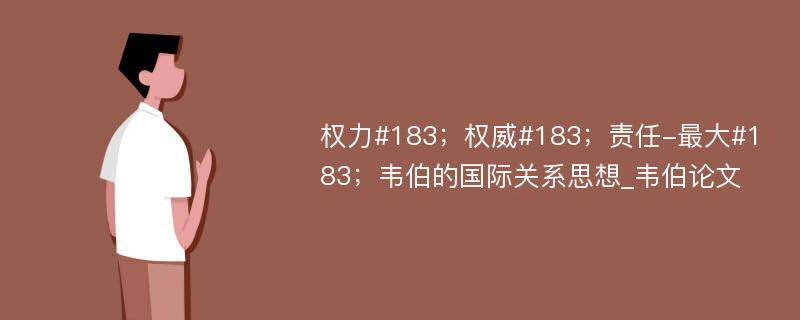
权力#183;权威#183;责任——马克斯#183;韦伯国际关系思想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国际关系论文,马克斯论文,权力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思想背景
迄今为止,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传统及众多思想大师已毫不陌生。但奇怪的是,被誉为“西方文明之子”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却意外地被众多国际政治学者所忽略。实际上,韦伯的思想轨迹跨越两个世纪,在政治现实主义的思想传承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正如著名学者迈克尔·史密斯在《从韦伯到基辛格》一书中所言,“欲了解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特有的研究途径,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理解韦伯开始。”①
韦伯的国际关系思想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德意志民族主义倾向密不可分。19世纪末叶,德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1871年才完成统一大业的德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到一战前,德国已取代昔日“世界工厂”英国的地位,成为欧洲大工业的中心。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改变了德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德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使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一度产生了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情绪,整日陶醉于经济成就之中而不愿涉足政治,同时还孕育了一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傲慢,使之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来看待其他民族。德国资产阶级既害怕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也不满容克贵族的专制统治。政治上的懦弱使他们一心希望出现一个类似于俾斯麦的政治强人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当时德国的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和平主义与扩张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的思潮都不乏大批忠实信徒。在此种政治生态中,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更加渴望在政治上与容克贵族分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德国的面貌和历史进程。他们希望德国也能像其他老牌殖民国家一样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主张进行海外扩张,以促使德国经济更快发展。
1890年是德国政局和外交政策转变的关键一年。当年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他的下台标志着德国“英雄时代”的结束,从而开始了威廉二世的半专制主义统治。威廉二世改组政府后,制定了一项争霸世界的“世界政策”,最终走向战争,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灾难。② 在世界的孤立和容克贵族的统治使德国进入大国行列的事实,使国内资产阶级对容克贵族表现出复杂的双重情绪:既怨恨又害怕,既不满又敬畏,既希望分权又不断妥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身为“资产阶级价值旗手”③ 的韦伯对容克贵族统治给德国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结晶构成了韦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韦伯在方法论上有明确的主张和鲜明的特点。首先,与“理想主义”的研究取向不同,韦伯主张从事政治研究必须“价值中立”。学者必须认清自己的角色,不能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审美倾向”或政治立场带进研究中去。④ 他认为,学者所提供的学术成果,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它不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只需指出何种做法可能造成何种后果;其次,韦伯主要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思考国际关系问题。他从政治社会学的一般概念、理论和方法出发,论述政治、国家、官僚体制以及治国伦理等一系列概念和问题。通过对权力政治、领导人的作用以及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等主题的探讨,韦伯阐明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二、权力与文化
“权力”是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同样,它也是韦伯国际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韦伯从对政治和国家的定义出发来思考权力政治问题。在他看来,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问题。所谓政治,就是指国家之间或国家各群体之间争夺对权力的享有或者试图影响权力的分配。⑤ 韦伯进而指出,国家统治的根本问题是暴力使用权的归属问题。所谓“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个既定的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⑥ 韦伯肯定拥有暴力是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前提条件。他说,如果哪个社会制度没有理解暴力的真正含义和用途,那么它将会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国家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源泉,其他机构或个人可以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前提是得到国家的授予或认可,并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⑦ 韦伯通过阐述“国家”和“政治”的内涵,揭示了政治权力的本质,强调了所有政治都离不开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在韦伯看来,权力斗争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在“权力动力”的驱使下,每个国家都极力争夺或者维持强权,以追求或捍卫大国地位,从而对他国构成挑战并导致国际冲突。
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在1890年也开始将目光转向海洋,走上了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征服之路。与德国统治阶级的军事冒险倾向不同,韦伯虽然赞同德国进行海外扩张以追求大国地位的基本目标,但他认为,德国的“天然条件”、特别是四周强邻环绕的地缘处境,决定了它应该奉行审慎的联盟政策,而非狂妄自大、一意孤行地四处征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韦伯倒向了和平主义者的行列。相反,他强调,尽管持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和平主义者”在道德上具有显著优势,但是,政治并不、也永不可能以道德为根本出发点,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他告诫那些幻想和平的人“放弃一切希望”,因为“和平”不过是冲突特征的一次变革。⑧
此外,与德国统治阶级迫切地希望以战争方式攫取更多原料和市场的目的不同,韦伯辩称,德国海外扩张的目的是出于对德意志文化、对世界历史的责任。“如果世界列强——归根结底,它们将决定未来文明的特征——不经过一场战斗而划定其实力范围”,那么作为一个大国的德国将无法承担对其他欧洲人的责任,更无颜面对自己的后代子孙。⑨ 文明来源于相关的民族文化,是“文化”存在的体现;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文化”。⑩ 从地理上说,民族与国家通常是重合的,但民族并不因此等同于国家。如果民族是个“社区”,国家便是“社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特殊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拥有民族团体的统一感才能生存。而作为现代国家重要支柱的民族统一感,则主要来自于民族文化。在讨论“民族”与“文化”之关联的基础上,韦伯进而将“文化”与“权力”联系起来。由此,韦伯希望德意志民族担负起历史使命,捍卫本民族的文化“纯洁性”,并向欧洲乃至全球传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韦伯曾对19世纪末东普鲁士农业工人人数下降问题作过调查,并因此加深了对德意志民族文化危机的忧虑。在韦伯眼里,东普鲁士发生的一些事件,表面上是德国与波兰两国的经济斗争,实质上却是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竞争。随着“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此消彼长”,德意志文化受到了代表斯拉夫文化的波兰雇工的严重侵蚀。(11) 韦伯确信,经济竞争威胁民族同一性,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威胁东部德国文化。保持东部文化就是维护民族利益,保卫德意志民族特性。德国只有以坚定的民族同一性来参与强权角逐,才不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既然身处霍布斯式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德国就不应该沉溺于“脆弱的幸福论”中,而应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可见,韦伯权力政治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观。他认为文化霸权是大国统治的一种形式,德国要统治欧洲甚至世界,就必须使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成为普世接受的行为准则,为此还必须借助权力甚至武力。韦伯的权力政治观,强调文化价值观与强权互为因果,从而修正了传统现实主义单纯依靠或追求物质力量的倾向。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这种思想往往具体化为文化扩张;而当受到异质文化的侵蚀或抵制时,则表现为动用武力来实现文化扩张的倾向。
德国东部的经济形势既造成了对德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同时也造成了容克地主经济势力的下降。韦伯认为,随着容克地主经济势力的衰退,它就不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民族领袖,在“容克地主完成了它的使命”之时,德国国内的其他阶级便应该接管政权。然而,事实却令韦伯深感失望和忧虑。由于俾斯麦的统治导致德国当时没有一个阶级在政治上足够成熟,能够充任德意志民族的领袖,带领德国人实现其“历史使命”。因此,他迫切希望德国出现一个能够捍卫德国民族利益的政治“守护神”。
三、权威、官僚与利益
韦伯给现实主义者的另一个启示,是对政治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的认识。此前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几乎都把目光聚焦在国家这样的基础性社会组织结构之上,他们虽然也重视领导人的作用,但目光仅局限在世袭制下的君王这类人身上,而非“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韦伯所推崇的是那些具有个人魅力的民选政治领导人,他相信,经过普选产生的这类领导人是促进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国际地位的首要因素。
旧制度下的容克贵族,原本是韦伯理想中的“政治贵族”。在韦伯看来,传统容克贵族在经济上靠农业工人来养活,无需过多担心物质来源,因而有充分的时间投身政治,并形成广阔的政治视野。他曾断言,这就是容克贵族政治权力和民族价值的秘密所在。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利益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体制日益盛行,官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与君主制不同,官僚体制往往被视为最有效的技术工具,官僚阶层则是超越各种党派或集团利益的中性力量。但韦伯指出,在现实中,官僚体制无法脱离阶级的漩涡,它受雇于社会阶级并加盟于社会阶级。就德国而论,普鲁士官僚体制在其合理的外表下潜伏着深层的危机。普鲁士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超越阶级的影响,它实际上是维持容克统治的工具。容克阶级通过对官僚体制和军队施加影响从而控制了整个德国政治的运转;另一方面,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商人的容克贵族,竭力利用政治权力来为本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从而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丧失自己的“民族”政治观,其内外政策总是由其所属阶级的物质利益所决定,因而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为了寻找能够取代容克阶层的新兴力量,韦伯对德国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但结果却使他越发深信,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德国各阶层不存在类似于旧制度下的容克贵族那样的角色:资产阶级由于缺乏权力政治的磨砺,在政治上胆怯而幼稚,没有资格和能力来承担民族使命;在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下诞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宣扬一种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能使民众更容易被官僚体系所操纵,因此也无法给德国提供它所需要的领袖;至于容克贵族,如前所言早已衰落,非但无力再担负国家崛起的重任,而且已逐渐成为德国的负担,阻碍着德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之,这些阶级虽然为政党和政治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但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与本阶级有关的经济因素和与之共生的经济观点的钳制,无法形成超越阶级利益的远大政治眼界。出于对超越阶级和经济因素、摆脱官僚体制束缚的政治家的迫切渴望,韦伯最终选择了具备广阔政治视野和高度政治觉悟的民选领袖。
这种民选领袖的特点是,凭借民众心理上的认可和拥护,他不仅拥有实权,而且赢得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威,因而在各个方面获得很大的独立性,能够以更广阔的政治观来制定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与“权力”的强制性特征不同的是,“权威”来自于民众发自内心的服从。韦伯认为有三种权威型的领导人:传统型、卡理斯玛型和法制型。根据韦伯的解释,“卡理斯玛”(Charisma)一词是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征的,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则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凡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它们具有神圣性或至少表率的特性”。(12) 卡理斯玛型权威便建立在这些超凡的品质之上。这种领导权威形态多存在于政治制度或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在这些时期,社会需要“救世”英雄出现来推动历史的变革;而传统型权威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是建立在传统或习俗的基础之上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封建世袭制、长老制便是典型的传统型权威统治的例子。但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人具有保守性质,往往会阻碍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发展;法制型领导权威主要存在于当代社会,它是基于人们对成文条款的信任,依靠理性化的规则界定的“职位”来实现其统治。法制型权威的统治是最具稳定性与合理性的统治形式,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13) 然而,以古今中外的史实为依据,并以其独到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体系为支撑,韦伯确信,拥有卡理斯玛型权威的领导人更具有革命性,不仅可以突破狭隘的阶级局限,还可抑制官僚体制所带来的隐患,确保国家追求国家自身的利益。因此他将德国的命运寄托在通过大众普选的方式产生的权威型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扭转德国自1918年之后的颓势。(14)
韦伯在讨论官僚体制束缚以及阶级利益左右的问题时,对卡理斯玛型权威领导人赋予了重大意义,引起了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其中所蕴含的价值的高度重视与共鸣。现实主义者们看到,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官僚机构虽然从理论上讲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命令,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是依照官僚机构利益、甚至党派利益而非国家的生存来界定国家的目标。因此,现实主义者告诫政治家们,在制定外交战略时,要采取对整个国家有利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仅仅对某个特定王朝或政党有利的对外政策。(15) 韦伯思想的服膺者们认为,在一个充满威胁的无政府环境中,必须将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政党利益置于他国及国际体系的利益之上。保护这些利益是各国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当领导人面临国内政局或所属党派的压力时,他可以借助卡理斯玛式权威(来自于他个人拥有的政治追随者的忠诚和信任)来超越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基础,与经济利益斗争保持一定距离,按照他自由选择的价值观,独立地判断国际局势,确定政策目标。历史上,卡理斯玛型权威的领导人不乏其人。比如带领美国人民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反法西斯参战道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基辛格评价道,正是由于罗斯福利用了自身吸引追随者的那种少见且令人鼓舞的特质,因此能够保持不受体制所限的作风,是政治操控者与远见者的综合体。(16)
实际上,当政府官员不再专门从贵族集团中遴选,而是从全体选民中遴选之时,经典政治现实主义者一方面为贵族统治被民主遴选和责任制所取代而哀叹,同时又幻想在当代民主社会依旧能出现类似于贵族统治者的政治家,韦伯对卡理斯玛型权威领导人的呼唤也是这种愿望的反映。此外,韦伯还认为,如果仅仅依靠议会或法律这类外在的约束来规范卡理斯玛式的领导人,将不免导致这类领导人丧失其主观能动性,挫伤其投身政治的积极性,甚至可能使之最后发展为行政官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韦伯提出了一套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以此作为对政治家的内在约束。
四、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
从外交政策实践的角度看,对于伦理原则是否适用于国际政治以及如何调和它与政治需求之间的困境,尤其是对如何处理目的与手段之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主要有三种伦理取向:非道德主义、道德完美主义和非完美主义。(17) 其中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处于光谱对立的两端。前者相信,道德问题只适用于外交政策的目的而不适用于达到此类目的之手段的选择。庸俗或极端现实主义者便属此列。后者则认为,无论道德多么崇高或美善,都无法证明有悖道德标准或者在道德上含糊不清的手段是正当的。其典型例子是和平主义者。此类伦理至善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暴力,竭力捍卫目标之纯洁性。处于两端之间的则是非完美主义者。他们倡导一种情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即认为不能以绝对的伦理标准来判断道德上可疑的手段是否正当,答案取决于具体的形势或环境,连同决策者在此形势中所追求的目标之性质。(18) 许多经典现实主义者就持这种立场,韦伯更是如此。
早在对19世纪美国牧师钱宁(19) 的思想的批判中,韦伯就对道德完美主义做过深入思考和批判。钱宁认为,国家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的伦理道德要远比国家的价值伟大和神圣,绝不允许因为国家利益而损害这些道德规范。根据他的观点,在基督教个人伦理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准则同样适用于治理国家。但韦伯认为,钱宁这种思想是危险的。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教义与国内秩序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整个中世纪的不幸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假的神圣和人类秩序的鸿沟之间的”。(20) 治国者信奉这种伦理道德将会把国家引向死亡的悬崖。
韦伯把政治伦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信念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另一种是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其区分标准是行为本身的价值和行为可预见的后果之间的不同意义。所谓信念伦理是一种目的伦理,行为者根据其信仰或目的行事,而完全不顾后果。基督教伦理便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责任伦理则是行为者完全理性地估量并且勇于承担其政策后果。那么,政治家应该恪守何种准则呢?
如果在一个“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世界中,政治家可以毫无顾虑地信奉信念伦理。你只要秉持善良的信念去行善,其结果上帝自会掌管。(21) 但是“世界脱魔”(stripped away all the veils)后的现代社会恰恰深陷在道德非理性的泥潭中,善非生善,倘若政治家想完成善的目的,他选择的手段就不能将恶的因素排除在外。如果政治家没有觉察到,在政治领域暴力是决定性的手段,没有发现任何伦理都无法回避用道德上模糊或者较为危险的手段来取得“善”的目的是一种现实的话,那么他便是“政治上的婴儿”。(22) 在没有上帝、没有先知的时代里,任何纯粹的“信念伦理”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实践中也显得荒唐可笑,唯一出路即在于“责任伦理”。通过“责任伦理”一方面可导出目标合理性行动,为经验理性的行动方式提供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与“信念伦理”相接,为抽象的道德理念奠定现实的实践基础。(23)
韦伯认为,一项行动,若是期望在责任伦理的角度上获得道德地位,就必须同时满足两项条件:首先,该行动必须产生于道德信念;其次,它必须承认世界处于非理性的环境中,赞同善可能导致恶这个观点。换言之,这种行动必须从道德信念的角度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同时还要从对可预见后果的估价方面证明自身的正当性。韦伯将第一项条件称之为“信念价值”,第二项条件称之为“效果价值”。(24) 信念伦理只符合前一种价值条件,而责任伦理则必须满足两种价值条件。这就是说,政治家按照责任伦理投身政治,除了自己对行为的道德坚信之外,他还得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他本人必须在行动之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尽量考虑到与行动相关的各种可能因素。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具体表现为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25) 对于前两者,便是信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所必需的“信念价值”,因为它们来源于对自身义务的最高信念,是他们为政治献身的动力,也使得他们有别于“暴发户似的炫耀自己的权力”的“权力政治家”。判断力则是信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所必备的品质。韦伯指出,判断力能使政治家在现实社会中保持自身头脑的冷静,保持一种与人与事的“距离”。“没有距离”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秉持以政治为业的信念,审慎地估算自己的行为与能力范围内可预见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并勇敢地为这种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责任伦理的基本要求。
五、几点评价
韦伯的思想对其后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方法论上讲,韦伯所倡导的“价值中立”为现实主义学者提供了分析国际政治的理性工具。韦伯在研究政治事务时,有意避免价值判断,而更加注重对政治问题的经验性描述和分析。这并不意味着韦伯要排除价值,相反,韦伯承认价值的重要性。他指出,“价值滋养了所有行动”,支配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内的斗争。(26) 研究者研究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他赋予了这个问题以价值。但是,价值之间的冲突不是科学研究范围内的问题,也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价值之争。因此,就其所研究的主题而言,政治研究者不可将个人价值、偏好或成见带入到资料的收集过程中,更不可受其影响而对某一问题妄加评价。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现实主义更加倾向于以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强调关注“实然”而非提出“应然”。故此往往将那些仅仅关注“应当怎样”而忽视经验事实的思想倾向称为乌托邦主义。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言,理想主义用“应然”替代“实然”,激情有余而罔顾现实。国际政治学者必须明白,“空想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源于政治现实的目标才可能实现。(27) 可见,现实主义这种追求客观和理性的精神与韦伯的“价值中立”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权力政治”虽非韦伯独创,但他对权力的研究更加突出政治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在韦伯看来,权力是政治的本质,在国际政治中,忽视政治权力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将是致命的。韦伯以及后来的卡尔、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大师从不讳言国家追求强权地位的必要性,并不遗余力地论证权力要素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意义,从而牢固确立了“权力政治学派”在国际政治学中的主流地位。韦伯权力政治观与先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对文化这一“软权力”的重视。后代的现实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衡量国家权力要素的视角,逐渐将文化影响力从军事权力等“硬权力”中剥离出来,归之于“软权力”一列。(28) “软权力”主要来自于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的影响力。一国凭借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或曰“霸权文化”,在全球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制度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来不乏其例。
问题在于,韦伯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过度放大了,从而以不平等的态度看待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普世性,视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为劣质、低等,以此种文化优越感为基础的“文化霸权”论,完全忽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价值的多元性。
再次,韦伯强调政治领导人的作用,这也是其后的大多数经典现实主义者能够认同的,在外交领域尤其如此。经典现实主义者往往认为,外交事务应该由少数政治家、外交家来处理,尽量避免受到大众政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对政治领袖的推崇,并不表明他认同纳粹主义思想。韦伯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他竭力主张在德国实施自由的社会政策,反对政治干预公民自由,反对集权统治。韦伯对卡理斯玛型权威领袖的设想,实际上是在政治自由与社会不安、阶级矛盾尖锐的两难现实处境下做出的抉择。他认为,面对社会矛盾的压力以及个人处于动荡不安的危险之中,德国民众应该牺牲自己的自由价值观,以换取一个安定的秩序和强势的政府。许多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如迈克尔·史密斯就认为,韦伯把当时普鲁士官僚盛行的状况视为一种普世的情形。为了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存活,“一种温和的国际政治观加上某种不是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致使韦伯把德国的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29) 这种认为领袖优于民众的观点,可能导致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专断,使一国的外交变得不透明,大大削弱民众对政府的制约作用。以韦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过分看重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漠视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此种带有浓厚唯心主义色彩的“英雄史观”,将不可避免地使现实主义失去最后一点理想情怀,而陷入越来越僵化的悲观主义。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韦伯的“责任伦理”观对当代国际政治思想、尤其是政治现实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雷蒙·阿隆所言,“韦伯教给我,匹夫有责,责任不在感情,而在抉择的后果。”(30) 阿隆还指出,韦伯关于“责任伦理”的定义不是对道德价值的忽视,而是对事实的接受和承认。在紧急关头必须首先拯救国家,然后才拯救个人的灵魂。摩根索也指出,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普遍公式应用于各国的行动,而是应当渗透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之中。审慎(即权衡政治行为的后果)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美德。没有考虑道德行为的政治后果便没有政治伦理可言。(31)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韦伯的“责任伦理”理解成机会主义,或者与某种被庸俗化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等同。韦伯反对政治的道德化,但他并不赞成所谓政治“不道德”论。他认为,如果责任伦理只是讲效果而不择手段,那么没有人会始终恪守这种道德观。责任伦理要求做出环境所允许的最佳道德选择,既不是恪守绝对的准则,也不是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换言之,尽管“责任伦理”强调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但并不等于“结果论”,即仅仅从结果出发来判断行为的好坏。韦伯恰恰认为,结果不可能使手段神圣化,因而也不可能用结果来判定行为的善恶。责任伦理必须是某种康德所说的“无条件命令宣示”,才有其道德意义,否则就会沦为机会主义。事实上,韦伯的“责任伦理”所要求的正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32)
然而,韦伯的伦理观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基本缺陷。他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二元划分属于伦理层面的概念区分,而伦理则是试图用理性的方式对道德上的信念进行论证。(33) 换言之,“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应该围绕何为“善”展开讨论,而不应该是围绕如何实现“善”而争论。韦伯将“责任伦理”描述为对后果的考虑,而对后果的考虑在伦理层面上属于后果伦理范畴。这样,他就掩盖了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矛盾。因为,后果伦理与义务伦理的争执就是围绕着如何能够识别善而发生的。但是,从道德角度看,政治家遵从后果伦理行事则完全错误,道德困境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者被人诟病为“非道德主义者”的一大原因。而韦伯本人应该对后人的误解负有一定的责任。
此外,后代的现实主义者在全盘照收“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二分法时,还忽视了韦伯隐藏在其中的个人价值取向。人们只注意到韦伯所标榜的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但是他本人却一直无条件地接受以促进德意志民族国家利益为己任这一信念,并将这个信念视为终身的“信念价值”。这个隐藏的矛盾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凭借韦伯制定的标尺,阿道夫·希特勒这种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名恪守“责任伦理”的领导人——他有热情(致力于一个统一欧洲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责任感(不推脱自己的民族责任)、有判断力(法国、西欧的迅速沦陷可以证明这种“品质”)。韦伯在提倡这些品质时,暗含了自己的“信念价值”。他完全凭借他对那些领导人为德国制定的政策的评估——“效果价值”——来对他们进行判断。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在道德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他们首先选择的还是国家利益。总的来说,韦伯的责任伦理观满足了现实主义“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者不仅接受了韦伯的二分法,还将“责任伦理”视为一种政治美德,一种在政治领域调和道德力量、国际行为准则与国家生存原则的“底线伦理”。
注释:
① 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ouisian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15.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1871—191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③ David Beetham,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36.
④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37页。
⑤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⑥ 同上,第196—197页。
⑦ 同上,第197页。
⑧ Sheldon S.Wolin,“Max Weber:Legitimation,Meth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ory”,Political Theory,Vol.9,No.3,August 1981,p.407.
⑨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6页。
⑩ David Beetham,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p.125.
(11) [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2页。
(1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3页。
(13) 同上,第303—305、307—322、323—351、353—361页。
(14) Steven Pfaff,“Nationalism,Charisma,and Plebiscitary Leadership: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in Max Weber's Political Sociology”,Sociological Inquiry,Vol.72,No.1,Winter 2002,p.94.
(15)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1—292页。
(16)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27页。
(17) 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77-282.
(18) Ibid.,p.280.
(19) 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780-1842),美国牧师,禁酒论者,美国三一教会联盟的创始人。
(20) J.P.Mayer,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1998,p.25.
(21) Bradley E.Starr,“The Structure of Max Weber's Ethic of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ol.27,No.3,Fall 1999,p.416.
(22) David R.Mapel,“Prudence and the Plurality of Value in International Ethic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2,No.2,May1990,p.450.
(23) 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4) [德]施路赫特:《信念与责任——马克斯·韦伯论伦理》,载李猛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314页。
(25)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783页。
(26)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94页。
(27) [英]E·H·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8)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
(29) 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pp.48-49.
(30)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刘燕青、孟鞠如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99页。
(31) 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7[th] editio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影印,pp.12,240-241.
(32) 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
(33) [德]瓦尔特·施威德:《信念与责任之间的政治家》,载单继刚、孙晶、容敏德主编:《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标签:韦伯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容克贵族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权威论文; 马克斯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