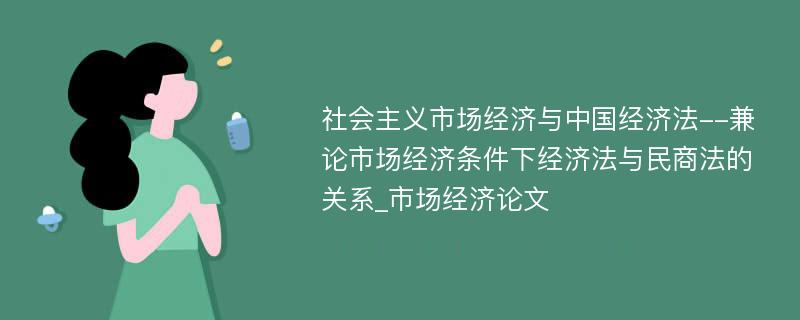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兼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法论文,条件下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社会化和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日趋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它将公法和私法的手段融为一体,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法律部门。商法与民法一样,属于私法范畴,奉行“政府不干预原则”,它不可能被改造成“经济法”,也不可能代替经济法。现实的经济制度和中国近现代民事立法的“民商台一”传统,决定了我国当前并无在民法之外另立商法部门的客观条件和法学基础。作者的结论是,民法基于其性质,是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也具有基本法的地位。这是一种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的“二元价值观”。
若干年来,我国有关民法与经济法相互关系的争论,曾一度妨碍立法和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致在法学界产生一种务实倾向,即人们只注重研究改革开放中迫切需要的具体法律制度,而把有关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理论探讨暂时搁置起来。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目前我国已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模式的情况下,进一步实事求是地探讨在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中究竟有没有经济法的一席之地、以及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已再次成为法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藉此机会发表一些意见,作为几年前一篇拙作的续篇,[1]就教于法学界的各位同志。
一、经济法与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有着内在的联系
笔者认为,民法本质上是“自由的财产流转法”。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与刑法衔接调整较轻微的侵权关系。而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精髓,就在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信号,自由、自主地开展活动,参加或与他人缔结民事法律关系,以此来达到资源的合理及优化配置。因此,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法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中都具有基本法的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制度,均由市场经济或商品关系内在的平等和自由竞争的要求所决定。任何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民法均确认其平等、平权的地位,不承认身份和权力的特权,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保证当事人在权力行使和自由活动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自愿接受的约束得以实现。
但从另一方面说,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抽象的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即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现实的经济也已经社会化,而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发达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和“公法私法化”(如金融及中央银行法、计划及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的趋势。
德国和其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遂将公法和私法结合部之法律现象或法律规范,解释为出现了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新兴的法律部门,按照一种典型的解释,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固有之法”。[2]所谓“组织经济”,“无非是指有组织的、包含着有目的的宏观管理的经济。撇开各国在所有制关系上存在的差别,“组织经济”与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管理经济”、“管理贸易”,乃至我国今天致力于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同一性质的事物或概念。
当代经济法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社会由“私—私”对立和“公—私”对立向社会化复归,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日趋社会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矛盾逐渐缓和,国家及其立法者顺应或迫于某种客观规律,日益将传统的公法和私法手段,包括民事、行政、刑事和程序法等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协调,或以社会的程序法等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协调,或以社会的代表自居、直接参与经济关系。“市民社会”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此不得不予以认可,或者说不得不在“社会契约”中对国家作这样的授权,否则它本身就无法维系下去。
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并不抱残守缺,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认可公,私法的渗透和融合,在理论上把经济法的出现解释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趋于成熟和国家与市民社会、与经济之间的藩篱逐渐消失并合为一体的结果。[3]笔者认为,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发达、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有明确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官民一致”的指导思想及相应的制度,即所谓“莱茵河模式”资本主义及其日本式变种——“法人资本主义”模式(又称“公司资本主义”)的经济及法律制度。[4]这种模式将政府的协调和参与作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经济法学说可谓不谋而合。
英美法系国家依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密切相关的“经济法”,但反垄断法、农业法等在美国也被公认是立法和法学的部门。以大陆法系的经济法观点来看,则英美法系国家无疑也存在着“经济法”现象。例如包含着声名狼藉的“超级301”和“特别301”条款的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它既规定了美国贸易代表对采取“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国家实施报复的职责、权力,又赋予美国厂商提起听证、调查或民诉程序,以“指控”外国政府的政策措施或外国厂商有关知识产权、不公正定价、不实广告、窃取商业机密等侵权行为的权利,规定的制裁措施则包括取消给予外国国家的优惠措施、限制进口、提高关税、迫使外国修改政策法律、对外国厂商发布停止销售或进口的禁令、科处罚金等,可谓一部地地道道的经济法。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法是伴随着由“人治”向“法治”过渡,在加强经济法制的呼声中应运而生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中国需要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过经济法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协调,维护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规范政府的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行为,并解决在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种种特殊问题。
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法学说已较为成熟,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排斥民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的作用的“大经济法”或民法是“公民权利保护法”的观点已被摈弃。1983年,笔者即已提出民法应调整由价值规律直接作用的(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或曰国家不直接干预或参与的)各种经济关系及有关人身关系的观点;[5]以当前有代表性的一本经济法教科书来看,它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过程中和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6]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是“具有国家计划、监督、组织等因素的经济关系”。[7]至此,应当说经济法在我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适当的位置。
二、商法与民法不可能取代经济法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是不是应该为商法所取代,由商法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弥补民法的不足呢?对这种颇为流行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就在于商法与民法一样,同属私法范畴,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
现代的民法和商法,均来源于古罗马的私法。罗马共和国后期至罗马帝国前期,罗马称霸地中海,奴隶、手工作坊制品、粮食和香料等农产品均作为商品在一个巨大的地理范围内流通,由于罗马国家的行政权力鞭长莫及,加上如恩格斯所说,“国际”(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商业交往最能体现客观规律的要求,[8]因为这种交往自发地排斥血缘关系和行政权力的干扰,于是,在各民族平等商业往来的基础上,平等要求在经济关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产生了反映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能够流传百世、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9]的罗马私法。后经西欧中世纪由注释法学派肇始的各种研究罗马法的学术流派的总结,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典的编纂;中世纪西欧沿海城市的商人自行设立裁判庭,援用罗马法处理商业纠纷,则是近现代“民商法分立”的开端。在现代民商法分立的国家,民法是私法普通法,商法是调整经营活动的私法特别法。在民商法合一的地方,如瑞士、意大利、旧中国暨现在的台湾地区,则民法是私法的同义语,商事法规是民法的特别法。所以,商法并不超越民法的范畴,二者都必须贯彻私法自治或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就是说,商法与民法一样,是与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一面相联系的,奉行的是“政府不干涉主义”。[10]
在大陆法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商法或商事法规调整的,私法的公法化,实际上就是商法的公法化。因此,在这些国家,商法的概念和范围越来越模糊,调整经济的法律正处于分化和重组之中。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商法在相当程度上被“公法化”而使之变了性;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商法(如国民党时期对民事特别法的定位,为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破产等五种)之外,新的“商事”法规或经济法规,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中央银行及银行法、证券交易及其管理法、职工参与管理法、职工股权法、国有企业法等等,层出不穷,且有不断扩张之势。这样,“商法”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相反,当代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以及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经济法现象既不可避免,在理论上亦无可否认它的存在。自从本世纪初在德国开始了关于经济法的百家争鸣以来,在欧陆国家,人们已不再否认经济法现象的客观存在,现在的争论是在经济法的性质及其与民商法的关系方面:一种观点把经济法规视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公法”,或者将其等同为经济刑法或竞争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因公、私法的界限在当代任何国家都已变得模糊不清,或因对经济法的理解过于狭窄,这种观点较少为人接受;一些商法学者希望用经济法来更新传统商法,使商法摆脱私法范畴,而这样就严重扭曲了商法作为私法的本质特征的传统形象;因此,稳健的商法学者把商法视为经济法的核心或基本法,经济法便成了商法的特别法;而认为经济法是融合传统公法和私法的新兴规范体系的观点,受到了欧洲多数法学家的赏识,并因一种新型的经济法律制度——欧共体法的发展而得以发扬。[11]
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或特点则是“就事论事”,它们将有关调整经济的法律规范分成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反垄断法、农业法等,所以不存在关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分歧或争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商法”(business law)一词,不具有部门法的意义,其商法教科书或著作,是对各种涉及商事活动的法规的综合性介绍。
或许有人会说,传统的民、商法固然不适于调整具有“公法”因素或组织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并不妨把具有组织管理性质的经济性法律规范归人民法或者商法,或者说就把公法化了的“私法”称为民法或商法,以消除传统民商法的局限性,使之能够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调整,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如上所述,在欧陆国家,已有学者作这样的理论尝试;意大利于1942年颁行、荷兰自60年代起陆续编纂民商合一的民法典,也是试图将有关经济的法律关系都规定到民法典中。前苏联民法学家为了提升民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也曾提出,“苏维埃”国家的财产关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财产关系都受计划组织因素的影响,既然民法是调整财产关系的,那么就应当把计划组织性质的法律规范大量结合到民法中去。[12]对此应作何评价?笔者的意见是:私法在历史上顺应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要求,已经形成了稳定、完善、和谐的体系,而且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来说已很复杂,如果照此办理,本来意义上的私法就不复存在,从而也就否定了民法和商法。我认为,前引恩格斯的见解是很精辟的,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自主、自由的经济交往,反映商品关系一般要求的罗马私法(现在经总结、提练为“民法”或“民商法”),就有它存在的余地,无论时代如何,哪怕是社会主义时代,都不可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而超出这种自由交往的范围,经典性的罗马法或民商法就会失去其用武之地,人们倘若既保留其名义,又对其作实质性修改,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知道,大陆法系的法学家往往把商法划分为所谓的“商私法”和“商公法”,而后者实际上并不是商法,商法学者自己也从不对其加以研究。[13]
我国在维持公有制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传统商法领域的“公法化”程度较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胜一筹,有关法律规范已被经济法所湮没;而且,1949年以前中国近现代的民事立法,已经形成了民商法合一的传统,民法中即已包括商法。所以,在我国当前,并无在民法、经济法、涉外暨国际经济法之外另立商法部门的客观条件和法学基础。当然,从一般私法的角度或在非部门法的意义上,“民商法”或“商法”的名称或提法还是可以使用的。
三、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中的作用
在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无疑是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与民商法有别的新兴法律部门。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学者把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称为“经济宪法”或“经济的基石”。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述及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三大法制支柱,[14]在此不妨再重复一遍。这三大支柱,一是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二是规范资金市场的金融和证券法制;而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则是较之传统民商法在更高层次上规范商品和劳务市场的竞争法制。后二者,主要是属于经济法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日益社会化后尚且把经济法摆到经济基本法的地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公正是公有制的内在要求,力求反映这种要求的经济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中,理应与民法一样获得基本法的地位。
民法与当事人自由、自发、自主的意志和行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固有特性,一方面决定了它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它对于遏制个别当事人追求自身利益时的消极面、对于经济的宏观协调和控制、对于有国家组织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的调整是无法胜任的。
从宏观上说,经济活动当事人自由地追求经济利益,开展经济活动,离不开计划、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手段(当然不是过去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行政强制手段)的宏观规划和调控,有关法律制度历来不属于民(商)法的范畴。
从主体制度看,凡涉及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无论是既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改革,还是依法掌握特定国有资产的机构、企业与其他主体合资经营公司企业,都离不开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依私法设立或经营的国有企业、即私有化或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或者依专门的法律或行政命令设立、经营的公法上的国有企业,以及合作企业等,虽然不是典型的企业,但也是其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由有权控制某一国有资产的机构、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或参与投资的公司、企业,却是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有关法律调整在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无疑居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主体制度——个体经营、合伙和成员为自然人的公司制度之上。
民法中法人制度的真谛,在于赋予一定的组织以参加民事流转的资格,以免其成员以各自的名义从事活动而造成不便。至于该组织是依行政法、经济法抑或民法而设立,其外部支配关系、内部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财产权的性质和行使的机制如何,法人制度并不关心,也无从进行调整。例如,国家机关也是民法上的法人,而实际上,每一个作为法人的国家机关都不是独立的,它们依法处于一定的权力支配体系之中,其经费或财产则不足以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因此,在内部组织和财产关系上千差万别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依法都可成为民法上的法人。国有或国家参与的公司企业是民法上的法人,有关的企业法律制度则是经济法的制度,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正如国家机关参加民事流转时也是民法上的法人,但其设立的依据却是国家法和行政法的道理一样。
现代的经济法,也深深地渗透到所有权或物权制度之中,在我国,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国家和集体还拥有或占有其他不动产或动产。对此,民法中源于罗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即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抽象规定,是无法进行有效调整的。所以,需要由经济法的有关管理制度和企业制度,辅以民法中保护所有权和物权的民事责任制度,来对其作有效调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中的债和合同制度对于经济主体的经营和交易活动,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我国现行的《经济合同法》,实质上就是调整经营主体间合同关系的民事合同法或“商事”合同法。但如前所述,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的规范,正常而有益的市场竞争是无法维持的,“契约自由”、“当事人间的契约就是法律”等民法原则,必须在民法本身的规范和经济法限定的范围内适用及发挥作用。民法通过债和合同制度以及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滥用权利、服从国家政策和计划等一般性条款,与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对私人所有权或个别主体的物权加以社会性限制的制度相衔接,与经济法一道,共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营和交易活动进行调整。另外,国家也直接参与招标、定货、发包、出让、投资等合同关系,有关的债和合同制度本身就是经济法的制度。
概括地说,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质来说除了不能调整组织管理性质的所谓“纵向”经济关系外,还有一些“平等主体”间的所谓“横向”经济关系或契约性的关系,也因为加进了组织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
第一,平等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所谓平等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是指在行政或财政上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它们在交往时的地位是平等的。例如,苏沪津等沿海省市分别与新疆、广西、云南、西藏、宁夏、甘肃、陕西等西部省区的政府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协作关系;[15]又如山东省政府与深圳市政府等合资兴建齐鲁钢铁基地,水电部与云南省政府等合资兴建水电站,等等。
第二,国家通过设立企业或由政府机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如进行招标、定(购)货、发包、出让、信贷、担保等活动时发生的合同关系。在实践中,这些合同有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或其他事业时订立的定(购)货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政府与国有企业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或其他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合同,在国外还有政府与国有企业或私营部门的大企业订立的贯彻国家政策的“计划合同”或“社会契约”;政府与开发商或其他厂商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订立的借贷合同,国家政策性银行与一般企业订立的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在发达国家还有议会或政府以整个国家财政提供商业担保的情形,如丹麦议会为向大贝耳特海峡工程的贷款提供担保,[16]等等。
鉴于这类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国家机关或必须执行国家政策的企业,在合同内容中需要体现国家的政策或意志,以当事人完全自主、自由的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的一般民事合同制度,是无法胜任其调整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我国的《经济合同法》及其研究,现已逐渐被纳入经济活动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或商事合同的范畴,因此,亟需在经济法的范畴内重构能够对有上述合同进行有效调整的合同制度。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教训的,如法国政府曾与主要国有企业订立“计划合同”,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国有企业和政府经营的公用事业出租或发包给私人企业经营、与其订立租赁或承包合同,但因这些合同很难适用一般民事立法,相应的法规又不健全,从而导致有关合同往往不能切实履行,发生纠纷也难以依法解决。[17]我国实行公有制,国家直接参与的经济合同较之在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常见,所以,在新形势下重构经济合同制度的问题,应当引起经济法学界的重视。
当然,这里所指的合同不包括国家机关因行政事业性消费需要而参与的一般民事合同关系,因为在所谓“集团消费”的民事合同中,并不需要把国家的政策或意志贯彻到合同的内容中去。
第三,当事人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这类关系传统上是由民法调整的,如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环保(相邻)关系、单个消费者与厂商的关系等,但现代法律基于社会的公正和协调发展,为使之达到实质的平等,便不顾法律关系形式上平等的要求,为其中弱的一方片面地规定权利,或者片面地为强势的一方规定义务,从而对民商法的主体平等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加以修正,创造出劳动、环保、消费者保护等法律制度。
凡以上超出民商法调整范畴的经济关系,就需要由经济法或“公、私法”融合的其他法律部门来调整。这种调整,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
四、简短的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经济法与民法一样,也是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真实、自主的意愿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愿能够正常地实现;经济法的根本作用,则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民法能够按照社会的需要和利益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二者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的“二元价值观”,表明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调整中的基本法地位是客观的,民法、经济法间并不存在某种主辅或主次的关系。由民法作为市场经济调整之“一元”基本法的极端后果,就是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内涵,决定了我们对“自由”、“公正和秩序”及其各自的“监护人”——民法和经济法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偏废的。
[1] 参见史际春《关于民法与商品经济一般条件的进一步探讨》,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2]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6页。
[3]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4]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请参见〔日〕冈部直明《日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制度上的摩擦》,《日本经济新闻》1992年1月27日。
[5] 参见史际春《试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客观依据》,载《法学研究》1984年第1期。
[6]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7] 〔美〕丹尼斯·特伦《商法与经济法》,《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第34页。
[8] 张宿海《经济法概念上的分歧》,《法学文集》,法学杂志社1981年版,第191页。
[9] 参见《马恩选集》第3卷第144—145页。
[10] 《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4页。
[11] 参见丹尼斯·特伦文,以及范健《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6页。
[12] 参见《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三)和E.A.苏哈诺夫《完善苏联经济立法的问题》,均载《法学译丛》1983年第3期:B.n.格里巴诺夫等《民事立法纲要和完善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载《莫斯科大学学报(法学类)》1981年第6期。
[13] 参见刘清波《商事法新论》,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版,第2页。
[14] 见《光明日报》1993年6月9日第5版。
[15] 见《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6日。
[16] 见《人民日报》1991年6月13日。
[17] 参见史际春《国有资产管理国际惯例》,《国际惯例书库③》,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599、第726页。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法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论文; 民法调整对象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合同管理论文; 民法基本原则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民法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