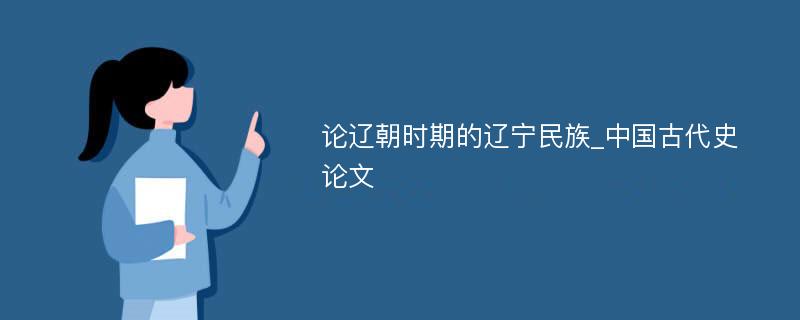
略论辽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宁论文,境内论文,时期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2006)06-0624-04
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出现了民族杂居的局面,既有汉族,又有契丹族和奚族,还有渤海族和女真族。在各民族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辽宁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同时,由于多民族长时期交错居住,在各方面互相影响,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1 汉族
辽王朝统治时期的辽宁,其汉族主要有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唐代所设州县的居民;一部分是辽初太祖从河北、河东掳掠来的俘民;另一部分是从中原地区自动来投的汉族流民,其中包括许多中原地区的士大夫、降官及其家属。关于第一部分人,我们现在虽然无法统计其具体的数量,但从一些间接的史料记载中,仍能够大致地了解一些。如东京道鹤野县,是因丁零威学道化鹤归来的神话传说而得名,此县的设置很可能沿唐代之旧,其居民1200户,应是土著的汉民[1]。海州,辽初迁渤海南海府的遗民置。辽圣宗平大延琳之叛,徙其民于上京,然后再迁泽州之民实之,这些新迁来的泽州之民也应是汉民。显州奉先县,本汉无虑县之地,辽世宗析辽东长乐县居民以为守陵(显陵)户,这些守陵户也应是汉民。还有辽西州,本汉辽西郡之地,辽世宗时置州。属民也应是当地汉人。贵德州,本唐时所设,至辽为察割的头下州,其所俘汉户当是本地人。岩州,也是唐代所设,辽代因之,其居民也无疑是当地汉人。还有银州,系太祖平渤海迁其遗民所置,但银州所辖的延津县是唐代旧治,其属民应有一部分当地的汉人。衍州,以汉户置,可能也是当地汉民。咸州,“乃招营、平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1]。这些所谓的客户,也无疑是辽西地区的汉民。中京道的神水县、金源县等,都是沿隋唐之旧,多数县民也应该是汉人。兴中府所属的安德州,还有锦州,宜州闻义县等,都是沿袭前代旧治,其属民大多数是当地汉人,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第二部分汉民,这在《辽史》中有明确的记载。仅以斡鲁朵及头下军州的辖户来看,其绝大多数都是掳掠来的中原汉民。《辽史·地理志》所记的16个头下军州中,有11个是设在今辽宁境内,其中仅秦晋国大长公主徽州就领户一万,以每户5人计,则达5万人之多。笔者粗略地统计一下11个头下军州的辖户,再加上其他几个头下州的领户,总数将达3万余户,15万多人。辽代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州县居民迁徙频繁,有的辽宁当地的汉民被迁往远地,然后再从别的地方迁来汉民实之。唐代辽东地区的汉民,在辽初时被迁往上京之地,然后又从河北虏来汉人安置于辽沈之地。如上京祖州咸宁县。“本长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2]。东京沈州所辖乐郊县,是辽太祖以所俘河北蓟州三河县汉民置,初名三河,后改乐郊;灵源县,太祖以所俘蓟州吏民置,原称渔阳县,后改灵源。另外还有中京道惠州、榆州、泽州,兴中府所辖的兴中县等,都是以掳来的中原汉民而设置的。辽代到底有多少中原汉人被掠往辽宁?其准确数字无法统计,估计至少在10万以上。
关于第三部分人,从《辽史》的相关记载和已出土的辽代汉人墓志中,即可了解概况。从中原来投汉族士大夫和降官们,他们后来都定居在辽宁,其后裔也多在辽宁境内任官,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刘承嗣、刘宇杰、刘日泳祖孙三代墓志,均出自今朝阳县西大营乡西涝村。刘氏一门在辽代比较显赫,其家族成员先后担任重要官职,墓志出土地点即其祖坟地。刘承嗣是唐卢龙节度使燕王刘仁恭之孙,其父刘守奇是刘仁恭的小儿子。刘守奇于太祖时降辽,又投河东,后奔梁,死于沧州。其子孙则流落辽地。刘承嗣曾任兴州刺史,其子刘宇杰曾任官显州、奉圣州,死后归葬祖坟。孙日泳曾官遂州刺史、来州刺史、润州刺史、宿州刺史等。刘氏一门与辽宁关系密切,其家族成员于辽金两代文献中不绝于史。刘守奇另一个儿子(承嗣之兄,墓志缺其名)的后裔刘从信的墓志也在今朝阳市西南朝阳电力修造厂院内发现[3]。刘守奇的六世孙刘宏是辽朝最后一任懿州最高长官宁昌军节度使,天庆八年(1118年),刘宏以懿州3000户降于金[4]。
再如辽西的王氏,是唐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置的后裔。王处置本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其子王郁于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年)“举室来降,太祖以为养子”[5]。其子孙长期在宜州为官,遂占籍4辽西。王郁之孙王裕、王悦,王裕曾孙王瓒等人的墓志,均出土于今喀左县境。如《王瓒墓志》记:“葬于建州柏山之先茔”[6] 82。由此可见,王氏已经把辽西地区视为自己的家乡了。青州马氏,太宗时“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7]。河北景城(今河北河间市)人陈万,辽太祖时归降国舅阿古只,为阿古只头下州豪州“豪刺军使”,太宗时任豪州刺史,陈氏一家遂定居在辽西[6] 15。还有河北玉田人韩知古的后裔,亦有占籍辽宁者。按韩氏郡望为昌黎,其地就应该在辽宁。金代之前名昌黎者只有两个地点,一为汉代的交黎县(又称昌黎县),旧址在今义县境内;二是昌黎县,治今朝阳西南木头城子镇。早在唐代,韩氏就以昌黎为郡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人称韩昌黎,可为明证。这说明韩氏一支早在汉魏或魏晋时期就在辽西地区长期居住过。韩知古的后裔韩瑜,为统军使。圣宗统和四年(986年)阵亡于涿州,归葬于霸州(今朝阳市)。其墓志出土于今朝阳市西20里朝阳沟,据其墓志记,他在霸州建有私第,说明他的家属就居住在今朝阳市。韩瑜之子,其墓志亦出土于今朝阳县境,其墓志记:“葬公于柳城之朝阳,以先夫人萧氏合葬,从祖考之宅兆,礼也”[6] 206。证明韩氏后裔已占籍今朝阳市。韩知古曾孙韩瑞墓志也在朝阳市他拉皋乡绪仗子村发现[6] 448。后汉刘崇之孙刘继文,以质子留辽七年,归国后又于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投降于辽。景宗封其为彭城郡王,居辽西,死后葬今辽宁建昌县图萨喀喇山[6] 71。平州卢龙人张建立,降辽后曾任榆州刺史,占籍榆州,死后葬今凌源市宋仗子乡二十里堡村。辽西朝阳耿氏,其祖上居上谷郡,太祖破上谷,耿氏归降,遂占籍霸州。耿延毅夫妻及其子耿知新墓志均出土于今朝阳县边仗子乡姑营子村。天祚帝时期的宰相梁援,原籍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太宗天显年间,其先祖归降辽朝,曾任宁昌军节度使之职,遂占籍辽西义县。梁援夫妻墓志均出土于今义县大榆树堡乡四道岔子村,即所谓的梁氏先茔[6] 519。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 契丹族和奚族
有了一代,契丹族与辽宁的关系比前代更为密切,因为许多契丹贵族和平民在辽代时都居住或活动在辽宁境内,其中也包括契丹皇族耶律氏成员和后族萧氏成员,特别是有几个契丹显贵的大家族,他们世代居住在今辽西地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遗物,为研究辽宁史和辽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辽代的辽东地区,其居民主要是南迁的渤海人和汉族人,但辽东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始终都是契丹人。东丹国存在期间,其国王为契丹人,大臣中也多为契丹人。东丹国废除后,设东京辽阳府,其最高长官东京留守几乎都是契丹贵族担任。如景宗初即位,封东丹王耶律倍的儿子隆先为平王,“未几,兼政事令,留守东京”[8]。耶律隆先可能是辽代第一任东京留守。还有耶律羽之的儿子和里,“终东京留守”[9]。但不知其具体任职时间。另外可查到的有:仲父房隋国王之后耶律抹只,圣宗统和初任东京留守[10]。统和十一年(993年),国舅少父房萧排押之弟萧恒德任东京留守[11]。十五年(997年),萧排押为东京留守[12]。开泰二年(1013年),以萧惠知东京留守事[13]。开泰四年(1015年),五院部人耶律八哥任东京留守[14]。太平五年(1025年),圣宗钦哀皇后弟驸马萧孝先由上京留守转为东京留守,九年(1029年),渤海人大延琳反,萧孝先“穴地而出”[15]。大延琳叛乱被平定后,由萧孝先的哥哥萧孝穆出任东京留守[16]。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驸马萧孝忠为东京留守[17]。重熙十年(1041年),萧孝穆另一个弟弟萧孝友为东京留守。清宁初,复任东京留守[18]。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年),东京渤海人高永昌叛,杀东京留守萧保先。这说明直到辽末,东京留守一职始终是由契丹贵族成员出任,多由宗室贵族和驸马担任这一职务。契丹族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长期生活在白狼水以东之地,即今阜新、彰武、北票一带。建国以后,契丹贵族所建的头下军州也多分布在这一地区。《辽史》所记的16个头下军州,其中至少有11个是建在今辽宁境内,而最集中的是今阜新地区。据考证,今阜新市境内有辽代头下军州9个,即豪、遂、渭、成、徽、懿、顺、闾等州。这些头下军州的建置,都与契丹族几个显贵的大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1年,在阜新县八家子乡果树村,出土辽圣宗时贵德州节度使萧仅墓志铭,志文中提到萧仅的五世祖萧撒刺,按其它相关石刻资料推断,应是指应天太后之弟萧阿古只。有学者认为,萧撒刺是太祖外祖父,显系误断,但他同时认为今八家子乡一带应是辽太祖之母宣简皇后家族的发祥地,则应该是正确的[19]。头下州中的豪州,是辽西地区建立比较早的一个头下军州,系萧阿古只的私人领地。豪州治所有人推定在今彰武县小南洼古城[20]。萧阿古只是应天太后之弟,为国舅拔里少父房一支的代表人物,阿古只家族与辽西阜新、彰武关系十分密切。成州是圣宗长女岩木堇(即王寂《辽东行部志》所记的粘米)的私城,岩木堇公主嫁驸马萧绍业(圣宗仁德皇后弟)、再嫁萧奉先,三嫁萧胡睹(萧孝友之子),四嫁萧惠。懿州是圣宗女槊古公主私城,公主嫁阿古只五世孙萧孝惠。渭州,驸马萧昌裔的私城。萧昌裔即阿古只五世孙萧匹敌,渭州旧址有人推定在今法库县叶茂台子乡二台子。福州,驸马萧宁(阿古只四世孙萧排押)私城,旧址在今法库县包家乡三合城。可见这些头下州的建立,都与阿古只家族成员密不可分。新中国建立前,曾在今阜新县大巴镇关山发现阿古只七世孙萧德温墓志,志文中明确记载,葬于黑山之先茔。黑山即今关山,这说明关山就是阿古只的家族墓地。萧阿古只家族是一古非常显赫的契丹人家族,据有的学者考证,这个家族在辽代先后出过6个皇后,2个皇妃,封一字王者13人,封郡王者10人,任北府宰相者17人,授北南枢密使者10人,被招为驸马者20人[21]。2001年4至11月,辽宁省考古所和阜新市的文物部门联合在关山发掘了9座大型辽墓,其中除6号墓外,都绘有壁画。出土墓志四合;萧谐领(萧和)墓志、萧德恭墓志、萧知行墓志、萧知徽墓志。萧谐领即圣宗钦哀皇后之父,萧阿古只曾孙,萧德恭是萧德温之弟,萧知行、萧知徽是萧谐领第三子萧孝诚的两个儿子。新的考古资料更进一步证实了阿古只家族与辽西阜新地区的关系[22],关山墓群所在地原来就是阿古只家族的游牧势力范围,后来成为祖坟地。另外阜新市南清河门区西山村还曾发现过萧慎微家族墓群,亦出土有墓志。但该墓成员与阿古只家族是什么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辽西的北宁市及义县,则与东丹王耶律倍家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东丹王的显陵在北宁市的医巫闾山,其子世宗、孙景宗,死后均葬医巫闾山,世宗葬显陵西山,景宗葬显陵之南,号乾陵。耶律倍的其他子孙亦多葬于此。如耶律倍第四子隆先,“与统军耶律完鲁同讨高丽有功,还薨,葬医巫闾山之道隐谷”[23]。世宗怀节皇后萧氏,本萧阿古只之女,死后亦附葬医巫闾山。景宗第二子、圣宗之弟隆庆,死后亦葬在医巫闾山。另外,在今北宁市富屯乡龙岗村,先后发现了耶律隆庆的儿子耶律宗政(查割)、耶律宗允(谢家奴)墓,并有墓志出土,隆庆的另一个儿子耶律宗教(驴粪)墓志也在今北宁市鲍家乡高起村西北山谷中发现[6] 750。有的学者认为,今北宁市一带原来就是耶律倍家族的领地,义州则应是耶律倍的私城,故其墓地选定在今医巫闾山[24]。还有,耶律元妻晋国夫人(圣宗钦哀皇后之妹)墓志发现于阜新县大板乡平顶山,志文记:“归葬于显州北平顶山,从先茔也”[25]。耶律元是耶律休哥之子,大板乡一带显然是耶律休哥的家族领地。在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村,发现了耶律仁先家族墓地,先后出土《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庆嗣墓志》(仁先之子),这些发现证明,今北票小塔子乡一带是耶律仁先的家族领地。
奚族早在唐末就已进入辽西。《辽史·地理志三》载,唐朝末年,奚人迁居利州阜俗县的瑟琶川。利州阜俗县治所在今喀左县大城子镇,有学者考证瑟琶川是今喀左北百里之虻牛河。同志还记载,“榆州,……本汉临渝县地,后隶右北平骊城县。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居”。兴中府,“后为奚人所居”。辽榆州旧治在今源原市八里堡古城,兴中府治今朝阳市。由此可见,辽代的辽西地区当有一定数量的奚人居住。
3 渤海族
渤海国的王族大氏是粟末靺鞨人,其属民有靺鞨人、高句丽,还有许多汉族人。但渤海国经过200多年的统治,各民族互相融合,到其政权灭亡之时,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渤海族。渤海族在文化方面更接近于辽东的汉族。辽代辽宁境内的渤海族,主要居住在东京道,即今辽宁东部地区和辽东半岛上各州县,而尤以辽沈一带最为集中。特别是辽阳,因为作过渤海遗民南迁后东丹国的都城,那里聚集很多渤海族的贵族家庭,如高、王、大、杨、李、张等姓。
辽东渤海族与皇族耶律氏之间有的还存在婚姻关系,主要是其王族大氏。如东丹王耶律倍有一妃姓大氏,生平王隆先。辽景宗也有一妃系渤海人,失其姓,金毓黻先生认为也是渤海大氏之女[26]。生淑哥公主,下嫁卢俊[27]。圣宗妃大氏,生女名长寿,下嫁大力秋。大力秋后坐大延琳事伏诛,公主又嫁萧萧慥古。
渤海人南迁以后,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辽宁地区。如迁到今辽西北宁市附近的渤海人主要是原中京显州和率宾府遗民,“显州之布”和“率宾之马”在唐代时就闻名于世。另外渤海人还善于制造铁兵器。他们把这一传统也带到了新居地,使医巫闾山地区成为辽代铠甲武器的制造基地和纺织业发达之地。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统和四年(986年),“铠甲缺则取于显州甲坊”[28]。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年),萧海里叛,“劫乾州武库器甲”[29]。可见辽代医巫闾山地区始终是铁兵器制造中心。
辽东渤海人,在辽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或在某些方面较突出者,亦不乏其人。如大素贤,渤海末期任司徒。东丹国建立,出任左次相。东丹国南迁,大素贤随之来到辽阳。耶律倍出逃后,大素贤佐王妃萧氏主国政,长期居宰辅之位。甘露十五年(940年),遭耶律羽之弹劾,免职。再如王继远,本汉平原王烈之后,是被渤海化的汉族人。据王氏家谱记载,王烈17代孙王文林仕高句丽,为其西部将,死于王事。又八代王乐德,始为渤海人,即继远曾祖。王继远辽初任东丹国翰林学士,居辽阳,曾撰《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其孙王咸饬,仕辽为中作使。因避大延琳之难,举家迁居渔阳。咸饬孙王叔宁,官六宅使、恩州刺使,迁居中京大定府。其子王永寿,又迁韩州(今昌图县八面城)。天祚帝天庆年间,又迁居辰州之熊岳(今盖州市熊岳镇)。王氏一门以文学显于辽、金、元三代。
另外辽初在东丹国担任重要官职的渤海人还有:大昭佐,仕于东丹,甘露元年(926年)七月奉使后唐;高正祠,国亡仕东丹,甘露四年(929年)出使后唐;文成角,仕东丹,甘露六年(931年)出使后唐;高保义,仕东丹为右录事、试大理评事,甘露六年与文成角同使后唐;列周道,为东丹国南海府(今海城市)都督,甘露十一年(936年)出使后唐;乌济显,为东丹国政堂省工部卿,甘露十年(935年)出使后唐;高徒焕,为东丹国兵器寺少令,甘露十三年(938年),与契丹使者梅里捺卢古同使南唐,并以马200匹、羊3万头与南唐交易,换回纺织品、茶叶和药材,南唐主李我昇命翰林院绘《二丹入贡图》以记其事[26]。高模翰,渤海国灭,亡命高丽(王氏高丽),高丽王妻以女,后因罪逃归,仕辽,政绩颇著,辽太宗耶律德光曾说:“朕统一天下,斯人之力也。”[30]。累官上将军,加特进检校太师,爵封我悊郡开国公,阶开府仪同三司。穆宗应历初,出任东丹国中台省右相,东京渤海遗老迎之于路,后升左相,卒于辽阳。
辽中期以后,东京渤海人之杰出者仅举两例:大仁靖,圣宗统和二年(984年)出任东京宰相府右平章政事;罗汉,官渤海帐司宰相,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九月,权东京统军使;至于大延琳、高永昌等,则更属渤海族中之佼佼者。
4 女真族
辽代辽宁境内居住的女真族主要是史料所记载的“熟女真”,亦称“曷苏馆女真”。另外在辽西地区也居住一部分女真移民。生女真部居地在辽宁境外,但行政上他们却与咸州详稳司(设在今辽宁开原市老城区)发生一定的关系。
曷苏馆女真,又称“合苏款”、“合苏馆”,关于这部分女真人的来历,南宋陈准《北风扬沙录》载:“金国本三韩辰韩之后,姓我挐氏。其地有七十二部落,阿保机恐其为患,徒豪右数千家于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三朝北盟会编》、《文献通考》皆沿袭此说。金毓黻先生认为,曷苏馆女真人可能是渤海遗族,其南迁的时间当在辽灭渤海后的天显三年[31]。台湾学者李学智先生也只主此说,认为“合苏馆”是渤海“忽汗”一词的汉字异译,其原居地在今黑龙江省依兰(三姓)[32]。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则认为“曷苏馆女真和鸭绿江北岸一带的女真可能都是从唐代开始就居住在这个地方[33]。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辽史·百官志》:“曷苏馆女真国,与渤海有别。”说明在辽代,是把曷苏馆女真人同渤海遗民严格加以区分的。曷苏馆女真人与生女真完颜部有同宗关系,故其族源无疑是黑水靺鞨,而且《辽史》中也无太祖迁女真于辽阳之南的记载,故《北风扬沙录》等宋伐史料有关曷苏馆女真的记载是不足凭信的。曷苏馆女真之名最早见诸《辽史》,为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距渤海遗民举族南迁之天显三年(928年)其间相隔84年之久。结合其名称最早出现在《辽史》上的时间和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该部女真人的迁徙应和圣宗统和初两次征讨女真有关。特别是统和三年到四年正月的那次军事行动,历时5个月,“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34]。至统和八年(990年),女真已完全被征服。曷苏馆女真很可能是内附或被俘女真生口中的一部上层人物及其家属,故其称为“豪右”。但《北风扬沙录》记女真是古三韩之后也是不准确的。
《金史》记载,曷苏馆女真人胡十门、合住,自称其始祖名阿古乃,与金皇室之祖函普是兄弟关系。“今大圣皇帝(指阿骨打)之祖入女真,吾祖留高丽,自高丽归于辽,吾与皇帝皆三祖之后”[35]。这说明曷苏馆女真的成员中还有一部分是从高丽归附辽朝的,但他们归附的时间也比较晚,大约在圣宗末到兴宗初,当与辽朝与高丽的战争有关。
辽朝对南迁的曷苏馆女真进行特殊的管理,不归州县所辖,设曷苏馆女真大王府,以女真酋豪为大王,又设惕隐、宰相等官,以统诸部。曷苏馆女真大王府被列为59个属国之一,关于辽代曷苏馆女真活动中心在哪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或以为“在今辽宁省辽阳县以南至金、复二县一带”[36]。也有人认为“以辽代的复、苏二州为中心,延伸到卢州、归州及其邻近地区”[37]。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文献记载,辽末金将撒改攻开州(今凤城市),曷苏馆人胡十门以粮饷资助。后攻保州(在今朝鲜义州和新义州之间),辽军从水路败退,胡十门半路邀击,都说明曷苏馆女真人居地离今凤城市不远。“合住,曷苏馆里海水人也”[38]。《金史》卷80《斜卯阿里传》记:“苏、复州汉民叛金,众至十万人,阿里破叛军于辟离密罕水上”。按辟离密罕水即苾里海水,指今辽东半岛上的碧流河,我认为曷苏馆人的活动中心就在今碧流河流域[39]。另外中京道的来州归德军(今绥中县前卫城),“圣宗以女真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40]。说明辽代辽西地区也有女真人居住,但所谓五部则不知具体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