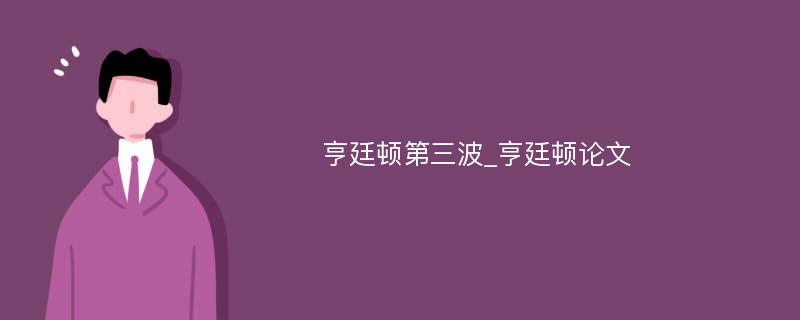
亨廷顿的《第三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不久,在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开始流行这样三大相互关系、相互支持的理论思潮,其一是“历史终结论”,其二是“民主和平论”,其三是“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主要表达了西方一些冷战人士面对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现实而产生的狂喜情绪,并骄傲地预言世界历史将从此“终结”,西方自由主民会一统天下,成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历史终结论”的主要代表作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该书是在他早先的一篇文章(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Summer,1989.)的基础上阐发而成。)。然而这种论调在现实面前很快不攻自破。冷战的突然结束并没有使西方世界摆脱种种困厄,也没有因为苏东集团的崩溃而表现得如某些西方人士想象得那样完美,而且西方民主在东方的亚洲及伊斯兰世界遇到了程度不同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在重新开始,而非什么“终结”。也因为如此,那些善于寻找矛盾焦点,习惯于“战斗”的理论家们又找到了一根“稻草”——“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挑战”(注: Samuel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亨廷顿从当代纷纭复杂的世界矛盾中,以文明作试剂,测定其本质为“文明间的冲突”,引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激烈的争论(注:亨廷顿在1993 年《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 The
Clash
of Civilzation?”一文后,旋即引起争论。《外交》和《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s)等杂志专门登载了争论文章。中国学术界也议论纷纷,主要的争鸣情况可参考(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3年10月号第4-35页,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 月出版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王缉思主编)。),并越出政治学术领域,波及到历史、哲学、人类文化学诸领域,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决策圈。如果说“历史终结论”是对现实世界形势发展阶段失之倨傲的情绪化概括,那么“文明冲突论”则是对未来世界趋势所作的悲观判断。相比之下,“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peace thery)有着更久远的思想渊源。
“民主和平”思潮与《第三波》
在解读《第三波》和“民主和平”思潮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民主和平论”的基本主张。
从“民主和平论”的中心思想(即民主国家间不会或极少相互开战)中可以析出两层意思:一是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它们之间利益冲突的适当途径,它们之间几乎从不打仗,一个民主国家从不寻求将来也不会寻求针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战争解决方式;二是民主国家间不开战并不排除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开战,相反,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开战往往是为了维护民主,总之,是正义之战。
“民主和平论”者提出的经验证据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尽管世界上发生了数不清的暴力冲突和战争,但没有一场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美、欧、日之间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打过仗,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们之间也极其不可能发生武力冲突。他们的理论论证则主要围绕“民主”与“和平”这两个概念进行。他们把“民主”作为自变项,和平作为因变项,认为民主与和平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的民主性质,即大众舆论监督和政治机构的相互制衡;另一方面,民主国家普遍奉行民主制标准和遵从民主文化,使得它们都具备相互尊重、以妥协求合作的文明共事精神;相反,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则缺少这种“精神”。非民主国家不仅缺少这样的民主精神,而且国内更缺乏有效制约战争的民主机制。
“民主和平论”在伸张自身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西方民主中心观,成为“历史终结论”者内在情绪的另一种表达。它使对民主胜利的欢呼转化为对民主政治扩展到全球的所谓“潮流”(wave)的大力推动。“民主和平论”者对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颂扬达到了高峰,以至于不仅认为民主可以保证和平、避免战争灾难,甚至认为民主是严重饥荒的“克星”,如塔尔波特所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森(A·Sen)的话:“在一个拥有民主形式的政府和言论相对自由的国家,从未发生过严重的饥荒”(注:S.Talbott,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Affairs,Nov./Dec.1996.)。
《第三波》一书的主题与“民主和平”思潮的联系
亨廷顿《第三波》一书的主题并非“民主和平论”,它本身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民主和平论”的代表作,它的研究对象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它透析了在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走向民主化的国家中,政治发展和变迁的共同原因、特征及走向等,并概括出一些带有普适性的民主化法则(或称“民主派准则”)。它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的民主化现象已经构成了新一股民主化潮流(即世界民主化潮流的“第三波”)。它直接和间接地指出,这样一股新潮流对于国际关系和人类和平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主要探讨的对象是20世纪后期,具体地说就是1974年到1990年间,世界上相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一状况。亨廷顿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或可译为“第三次浪潮”)。
亨氏把历史上的民主化过程比作一波一波起伏发展的“浪潮”,而“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并认为“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注:《第三波》,第12、14页。)。当然他也把那些“尚未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中实行的部分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包括在内。按照这个标准,他提出,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三波民主化:第一波民主化长波起始于19世纪初,大致是从1828年至1926年,约有30个国家进行了民主化,但是主要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造成了1922年至1942年的第一次回潮,这次回潮使得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降为约12个。第二波民主化短波从1943年到1962年,再次使民主国家数量上升到30个以上。但1958年至1975年又出现一次回潮,直到1974年葡萄牙发生了民主政变才掀起了迄今未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把这次浪潮看作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它在15年中“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注:《第三波》,第25页。)。到1990年时,它已经使世界上民主化国家的总数增加到了近60个之多,占世界100万以上人口国家的总数129个中的近一半。而且,到1990年止,第三波民主化“仍然没有把民主国家在世界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超过62年前的上一个波峰上”(注:《第三波》,第26页。)。同时,他还特别指出,这种波浪式前进的民主化并非没有任何障碍,相反往往表现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格局”(注:《第三波》,第25页。)。
该书在结构上分成6章。第一章回答“是什么”(What? )的问题,是对于全书研究对象的提出和说明,包括对民主含义的限定以及对民主化带来的问题的思考。第二章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 探讨了民主化呈波浪式运动的原因,重点则是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找出第三波民主化的五大肇因,即:合法性的衰落和政治的困局、经济发展和危机、宗教变革、外部势力的新政策、示范效应或滚雪球(注:详见《第三波》,第53—118页。)。在第三章回答“如何会这样”(how?)的问题,把第三波中转向民主化的威权政权分成3种,即:一党体制、 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然后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政权中执政集团与在野或反对集团的互动关系,概括出这样3类变迁过程:一是变革( transformation),即威权政权实现自我改造,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最多,有16个;二是置换(replacement), 即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这样的政权有6个;三是转移(transplacement ),即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达成妥协,采取联合行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有11个。此外,他也提到了一个例外模式,即象格林纳达和巴拿马那样由外部势力干预而带来的民主化。第四章继续回答“民主化过程的特征如何”(how?)的问题。他提出了“妥协、选举、 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注:《第三波》,第203页。)的观点。 第五章则回答新民主政体“如何持久”(how long?)的问题。既然民主化浪潮有明显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规律性,第三波民主化已出现了这个征兆,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回潮的问题呢?他为此总结出了新民主政体可能碰到和必须面对的3类问题,即:转型问题(transition problems)、情境问题(contextual problems)和体制问题(systemic problems),并且还花费大量笔墨探讨了前两类问题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处理方式及重要性。第六章回答民主化“何去何从”(whither?)的问题,展望了民主化的前景,提出了“时间属于民主一边”(注:《第三波》,第380页。)的观点。
亨氏刻意研究的主题,分明是政治民主化在世界上扩展的新趋势。本文无意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全面评价这部著作,而是想讨论该书主题与“民主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理论思潮之间的联系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亨廷顿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政治发展研究上。60年代他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注:Sammuel.P.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中译本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一书,在该书中,他更加重视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在他的研究范式中,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超过了政治民主化的迫切性。该书开篇即写道:“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治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1页。)。在此基础上, 他演绎出了著名的“强大政府论”。《第三波》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他已经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发展中政体的民主还是非民主性质问题,因为在他的新范式里,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反过来超出了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诉求。亨氏的这种范式转变,不能说不是受了冷战结束后对西方持乐观态度者的感染,尽管他不象福山那样得意洋洋,预言“历史终结”,但他经常透露出对于西方民主将遍及全球的乐观心态,以至于他在前言中情不自禁地表示,“在本书中有五处,我放弃了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而担当了政治顾问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条‘民主派准则’。如果这使我像一个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还是随它去吧”(注:《第三波》,“前言”第3 页。)。事实上,他这本书的出版在西方民主派人士中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盛赞这是一部杰出的、 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著作,并认为它的确给亨廷顿打上了“民主派马基雅维利”的烙印,尽管他拒绝这一殊荣(注: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De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一书封底文字。)。
我在这里想提出的一点看法是,在“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后,人们易于得出结论,认为亨氏放弃了对于民主遍及全球的乐观主义,转而提出未来世界将发生以文明划线的分裂与冲突的悲观预测。就连西方一些民主人士也批评他的前后矛盾(注:[美]格什曼(C.Gershman),“文明内部的冲突——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5期,第37-39页。)。 但笔者认为,《第三波》以“民主与非民主”划线,而“文明冲突论”以“西方与非西方”来划分世界,两者确有差异,但后者并非否定了对“民主”的信心。相反,在“文明冲突论”的界说过程中,他以强调民主是“西方特质”的方式强化了对西方民主优越性根深蒂固的信念,两者的逻辑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亨氏本人的著述中得到证明,他于1997年在《民主杂志》上撰文回顾《第三波》时仍疾声呐喊:“无论如何在第三波之后二十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注:美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1997年第4期,第3-12页。这里引自刘军宁译亨廷顿《第三波》一书的“序”。)。
其次,我们能分明读出来的是,“民主和平论”是《第三波》一书的逻辑起点之一。因为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就意味着和平地带(Zone of Peace)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和平与民主是无法分开的两相一致的概念。所以,他将“民主和平论”纳入自己的研究中,作为他对民主潮流合法性的支持证据之一。他曾明确论述道:“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民主国家打过的战争与威权国家打过的战争一样多。威权国家既同民主国家打过仗,相互之间也打过仗。不过,从19世纪初到1990年,民主国家(除极少几个例外)没有同其他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注:《第三波》,第29页。)。
另外,如同“民主和平论”者们强调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有推进和扩展民主的责任一样,亨廷顿的这本书也明显体现了这种观念。一方面,他把“美国的未来”与“民主的未来”等同起来,认为民主的未来对美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写道:“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和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其他国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持续它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美国却不能作出这种选择。因此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注:《第三波》,第30页。)”另一方面,他把外部力量的介入列为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五大原因之一。他声称:“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外部的行动者可以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帮助”;“第三波的开始或多或少是与欧安会及赫尔辛基最后决议相互契合的”(该决议中有一项是专门关于在东欧推进人权的)(注:《第三波》,第97、98、101页。)。 他特别乐观地评价了美国在促进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他提出美国促进别国人权和民主的政策在70年代初逐渐走向积极,199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最为活跃,里根、布什则继其衣钵。亨廷顿全面总结了美国政府在第三波中采取的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种种手段(注:详见《第三波》,第104—107页。)。最后他坦率地承认:“事实上,在卡特、里根和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个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the democratic version of Brezhnev doctrine ):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注:《第三波》,第108页。 )。
总之,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阅读亨廷顿的这部著作,显然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它完全是在为“民主和平论”夯实思想基础。不仅它本身以“民主和平”思想为假定前提之一,而且它还通过鼓吹“民主”价值的关键意义,特别是强调民主对个人自由、政治稳定、国际平等与和平及美国的未来等具有的意义,从而直接为“民主和平论”补充思想资料。如前所述,它简直就是在为“民主和平论”从观念落实到行动而摇旗呐喊。
最后的评论
“民主和平”思潮绝非空穴来风。它不仅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属于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思想的一部分,值得深入研究;而且,它作为一种流行思潮,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相比,其影响已经超出国际关系研究范围,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思想库,并影响了大众的观念,成为更难破除的“新型神话”,因此更加值得关注。
人们早已观察到,国际关系的传统内容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战争与和平不再是全部话语,主权、安全、地缘政治边界等指称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文本中被重新解读,以一些新鲜的术语和概念形式再表达出来,诸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地缘经济”、“有限主权”、“民主和平”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民主和平”本是一个国内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但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外交政策再阐释的推波助澜之下,它已经转换为国际意义上的一个语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解读亨廷顿的《第三波》一书,脱去其为“民主和平论”辩护和鼓吹的这一层“外衣”,似乎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1996年国内就有人指出,在为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出谋划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人文环境的重大变化。这位作者所指认的“人文环境”主要就是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论”,其中评述“民主和平论”时,他指出,“根据民主和平论,可以产生两个推论:其一是中国这样的非民主政体是战争可能的发源地;其二是因为民主政体能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那么在对华政策中把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则是天经地义的”(注:张勇进:“论当今中国的国际环境”,载《国际经济论》1996年第3-4期,第15-19页。)。看来,更广泛地开展对于“民主和平”思潮研究的意义已经不言而明。
亨廷顿的《第三波》一书作为政治发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除了揭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世界民主化运动的根源、过程和特征,而且初步表达了他对冷战后民主化浪潮能否持久问题的审慎乐观态度。统观该书,我们可以读出其中“民主和平”思潮给予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亨著有意无意地成了“民主和平论”的“吹鼓手”和“拉拉队员”。因此,解读该书不仅是政治学的应有之责,也是国际关系研究者之必须。
收稿日期:1999—02—03
(注:这里指的是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著的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 homa Press,1991)一书。本文除参考英文原版外,主要引文均来自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简体中文版(刘军宁译),题名为《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文简称为《第三波》。)与“民主和平”思潮
标签:亨廷顿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第三波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终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