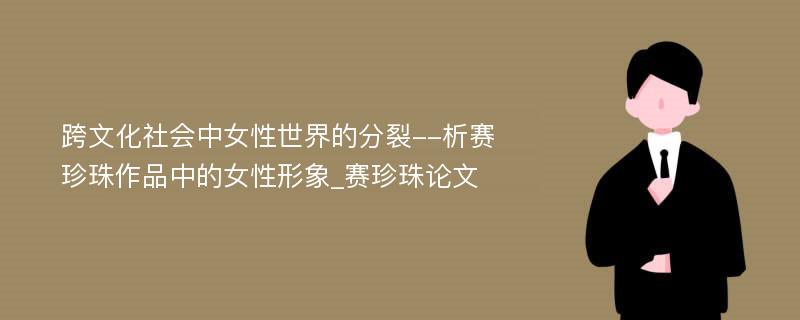
文化际会中女性世界的裂变——对赛珍珠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形象论文,作品论文,文化论文,赛珍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约主持人 姚君伟 教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4-0041-05
正如许多评论者已经关注到的,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命运,是赛珍珠创作中的两个重要母题。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作者饱含理解与同情的目光关注下,心理展现细致感人,性格刻画准确生动,情感轨迹幽微曲折,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度和力度。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主题,因作者形象的描绘、热情的阐述,不断为读者提供“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而产生了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当这两个主题风云际会时,又会发生什么故事?文化融合是美好的,但过程却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波澜不惊的,那么,它给在男权中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又带来了什么?对文化变迁中女性命运的关注,是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赛珍珠对文坛的独到贡献。
鲁迅先生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书信中有一段关于赛珍珠的评价:“……她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而1931年《大地》出版后,美国传教董事会却指责赛珍珠在写作时没有使用“传教士的视角”,“传教士身份为艺术家身份所取代”。两者观感差异很大。其实,鲁迅先生指称的是赛珍珠的社会身份,而传教董事会针对的则是赛珍珠的宗教立场。赛珍珠在写作时的确极少采用传教士视角,她习惯于把自己看作生长于中国、汲取中国文化养分长大的美国人,习惯于从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角度进行创作。她笔下的女性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她的文化立场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而逐渐定型。
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造就的第一类女性,是那些因无法适应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价值观念的全然更新、生命轨迹的急剧转折而被无情抛弃,承受极大的心灵创痛乃至最终遭到毁灭的女性。这类人物的代表有桂兰母(《东风·西风》)、结发妻(《结发妻》)、老母亲(《老母》)、凯丽(《放逐》)等。
桂兰的母亲是封建大家庭中的正室夫人,她管理家事,训导儿子,培养女儿,是全家尊敬和畏惧的对象。她自觉接受传统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她亲手把女儿塑造成三从四德的女性典范,教女儿以孝敬公婆、取悦丈夫、生儿育女为人生最高目标。当她得知留洋归来的女婿不喜欢女儿的小脚时,她虽然不能理解,但仍毫不犹豫地指示女儿放脚,“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只有一条路,……除了按他的愿望行事,你别无选择”[1]422。她叹息“时代变了”,可是她的行为准则没变,让女儿放脚,不是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思想、新观念的认同,而依然是对祖训的恪守:服从丈夫。她对于一切现代文明都拒不接受,连电线、电报都认为是野蛮人发明的亵渎神灵的东西。所以,当儿子公然提出退婚、另娶他自己选择的美国姑娘为妻时,桂兰母受到极大震撼。母与子在坚守与反叛传统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终,希望破灭、精神垮塌的母亲抱恨而终。
《结发妻》中的妻子是个柔顺的贤妻良母,“深明内则,受过良好的庭训”[2],是公婆眼里无可挑剔的好媳妇。可是在留洋归来的丈夫眼中,她只是毫无思想见解、只会唯唯诺诺的“半奴半妾之旧式妻室”。当妻子无法实现丈夫提出的让她进洋学堂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时,她惨遭丈夫无情的遗弃,连抚养子女的权利都被剥夺,最终不得不以自杀捍卫残存的尊严。
《老母》中的老母亲为供独生子留洋,卖掉了家中最后一块地,得到的回报是寄居在儿子家中战战兢兢度日。她的饮食起居习惯均不符合“卫生”标准,她因食量大而被斥为“如同下人”,连两个可爱的孙女也不许她亲近。老母亲一辈子的生活习惯遭到全盘否定,她茫然无措,欲诉无门,连寻死权都被儿子剥夺了,因为他不容母亲毁了他的名声。
赛珍珠虽是作为西方传教士之女来到中国的,但在两种文化遇合之时,她从未以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自居,她从一开始就对中西两种文化持有公正的立场和清晰的认识。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吸收各种养分,更需要异质文化的刺激,才能保持活力。文化只要在平等基础上相互交流,将会对双方都产生积极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也是为人类服务的,倘若文化的发展需要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付出牺牲幸福乃至生命的代价,这种交流的方式或价值就值得怀疑。自古至今,社会的价值标准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女人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旧时代,男人制定了一套标准要求女人恪守;新时代,他们又举起舶来的西洋镜对这些女子的言行习惯指指点点、百般挑剔,自己则永远是真理的化身。这类女子是在西方文化尺度下严重落伍的中国旧式妇女。她们深锁闺闱,因袭着千年相传、天经地义的“好女人”法则生活着,为此,她们很少真正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在旧文化中她们就是牺牲者,当时代巨变到来时,她们又因深陷于旧的传统或积习而无法迅捷适应这一变化,及时更新自己的心理结构、价值标准和行为习惯,因而首当其冲地成了传统文化不光彩的代表而遭到遗弃。她们曾经付出的自我牺牲竟成了她们耻辱的胎记,在新文化到来之时她们又一次作为牺牲者而被推上祭坛,而她们除了哀叹“命运”不济,连申诉、反诘的闪念都不曾产生。当然,赛珍珠的智慧之思并未因激荡的同情心而停止,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褊狭、封闭、保守、因循加以袒护或粉饰,相反,她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类女性对新文化缺少接纳的胸襟、学习的能力,因而难逃毁灭的命运。但是,在西方文化摧枯拉朽的横扫中,当社会普遍对新文化带来的新景象欢呼雀跃时,赛珍珠却将同情的目光转向行动的起点同时也是行动的目的——人,尤其是那个无声的群体——女性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并自觉成为她们的代言人。在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视角是独具一格的。
传记《放逐》中的凯丽与上述3位东方女性的经历不同,结局却有相似之处。凯丽是因对宗教和上帝的无限虔诚而自愿来中国拯救异教徒灵魂的美国传教士,但结果是,她非但没能拯救他人,自己反而陷入孤独、绝望的深渊:远离故国亲人,与执着于事业的丈夫无法沟通,先后失去4个幼子,难以融入她尊敬而又不能真正理解的异邦文化,看不到离乡背井的意义所在,这一切最终撼动了她的信仰,使她成为真正的精神漂泊者。她仿佛被连根拔起,与哺育自己的母体文化隔离了,又找不到新的生根的土壤,只能在绝望中逐渐毁灭。赛珍珠曾借短篇小说《天使》中女主人公——一个女传教士之口表述凯丽的心声:“我曾经设想得那么高尚的生活,当我回头看它时,只是一场与污秽和懒惰进行的战役,此外什么也不是——而且我还输了。”[3]这是从西方文化传送者的角度对文化交流的目的和价值进行的疑虑重重的思考。赛珍珠本人对海外传教的否定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其母影响的。
第一类女性尽管身份、经历不同,但都是两种文化碰撞中的飘零者和被遗弃者,个体生命被卷入时代的漩涡,激起的仅是令人悲悯的浪花。
第二类女性与之相反,她们既没有社会担当的责任感,也缺少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面对文化变革,只从个人需要出发,或贪图西方文化带来的物质享受,或把西方生活习俗奉为金科玉律,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脚下,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俭朴、奉献、孝悌、克己控欲等观念统统丢弃。这类女性有《老母》中的儿媳、《分家》中的爱兰、《同胞》中的露易丝·梁、宋罗兰等人。
《老母》中的儿媳留学归来,对乡下来的婆婆十分鄙弃,动辄呵斥她的举手投足、吃饭穿衣方面的种种“不文明”,参照标准是她后天习得的西方行为习惯。她不仅为婆婆的日常行为设置了种种规定,而且禁止婆婆亲近孙女,剥夺婆婆的天伦之乐。她以接受到的西方文化的皮毛来助长自己的傲慢习气,把本源文化中的孝悌、敬老、中和等传统美德统统抛弃,甚至丢弃了人与人之间起码的同情和理解。《分家》中的爱兰是个满脑子只有时髦的服饰、热闹的交际、逢场作戏的爱情游戏的轻浮女子,她生活在大城市里,用父亲搜刮来的钱过着奢侈享乐的阔绰生活,她未婚先孕,为保持身材,又不愿亲自哺乳。传统文化在她身上没留下任何痕迹,西方文化对于她也仅仅意味着物质享受,对两种文化的理解都极其肤浅。露易丝·梁和宋罗兰则是完全美国化的中国人,她们与母邦文化相隔千山万水,既不愿、也没有能力认识它、理解它。露易丝按美国人的习惯生活,视性爱为游戏,被父亲强令回国后,却无法扎根于此,最终还是逃回了美国。宋罗兰外表看来中国味十足,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留给她的仅限于东方女性优雅的气质,为了保住英国情人提供的物质享受,她连自己的情感都不敢面对。这类女性的精神因无根而显得十分空洞、苍白。
短篇小说《归国》是作者从另一角度审视这类女性的作品。玛蒂儿是一个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睥睨中国古老文化的法兰西人。玛蒂儿与中国留学生臻相爱结合,但当她置身于中国时,她所留意到的只是陌生的语言、喧闹的麻将、好奇的目光和随处可见的痰迹。西方人的优越感让她时时产生纡贵降尊的委屈情绪,最终与臻分手,踏上归国旅途。其实,她根本不理解、也不愿去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而在令她如此骄傲的法兰西属于她的仅仅是父亲的小杂货铺和店铺伙计——一个粗枝大叶、满脸酒刺的追求者。作者以调侃的语气,不露声色地讽刺了一些西方人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态。
第二类女性人物的共同特点是她们割裂的精神,支离破碎的价值观念,除了零星、片段的直觉外,没有完整的精神家园。更重要的是,她们或远离了母体文化,如无根的浮萍始终漂浮在海面上,或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狭小空间,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她们从未从更高的角度进行过深度思考,更没有做过任何有益的工作。赛珍珠最反对那些鄙视本土文化的“文明人”(如《结发妻》中的李渊、《老母》中的儿子和儿媳等)或用传统文化换取美元的口头爱国者(如《同胞》中的梁文华)。她认为,在文化交流中,本土文化始终应该是立身之本,只有始终坚持自身的特色,才能在文化交流中保持主人翁的姿态和主动吸纳的气度,反之,文化融合只能变成文化同化主义或文化投降主义,是鲁迅批评的“孱头”。第二类女性反映的正是文化交流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文化交汇中的杂音。文化交流在此遭遇到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羁绊和阻隔。
在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背景上,赛珍珠塑造得最具艺术感染力的形象是第三类女性。她们亲历了两种文化的强烈碰撞,对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悟,虽然也曾经有过惊惧和彷徨,但最终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了精神涅槃,获得了新生。这类女性的代表有桂兰(《东风·西风》)、吴太太(《群芳亭》)等。
桂兰从小在母亲的耳提面命中成长,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打扮都是严格按照传统标准精心设计好的。但当她带着满脑子母亲的训诫走进洞房时,听到的却是丈夫完全相反的宣言:“我将平等地待你。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你不是我的附属品,不是我的奴隶。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做朋友。”[1]405这番表白让一心准备做丈夫奴婢的桂兰晕头转向:我和他平等?为什么?我不是他妻子吗?他要是不告诉我该怎么做,谁来告诉我呢?难道他不是我名正言顺的主人吗?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让桂兰像失去舵的船,迷离、彷徨,在激流中打转。作者为夫妻关系的解冻设计了一个很具民族和时代特征的细节:放脚。桂兰的三寸金莲是母亲的得意之作,也是为未来女婿精心准备的礼物,而这恰恰成了夫妻情感沟通的最大障碍:在学西医的丈夫眼里,那是病态的、丑陋的。夫妻二人开始交流正始于桂兰同意放脚。桂兰对放脚的感受深刻反映了中西文化对撞中女性的双重不幸:“他使得这一牺牲(裹脚)毫无用处,还要我作出新的牺牲(放脚)!”[1]430所幸的是桂兰在丈夫的耐心引导下,逐渐认同了包括放脚在内的西方文化的诸多观念,对科学、育儿、男女社交等有了全新的认识,以至于对哥哥和洋嫂子的爱情也能从最初的不解和反感到逐渐接受、赞同,并最终成了哥哥的盟军,去争取母亲的理解和支持。
桂兰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渐进过程被描写得细致曲折,真实可信,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幸福的得来依然有几分侥幸:桂兰和《结发妻》中那个妻子的命运的不同,仅仅在于她遇到了一个心地善良、且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持调和态度的丈夫,他学习两种文化中的好东西,将不合适的丢弃掉;而结发妻的丈夫则是文化变革中的激进派,对于一切旧的东西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摒弃。前者获得新生而后者却遭到毁灭。这类女性依然不是自身命运的主宰。
相比之下,吴太太则是一个主动追寻个体独立价值的女性,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可算是少有的觉醒了的传统女性。她出身名门,又是南方小镇大户人家的当家太太,她知书达理、思想丰富、聪慧敏捷、多谋善断,种种繁杂家务,无一不处理得妥妥帖帖,为媳为妻为母为婆,担当各种角色都游刃有余。这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年届不惑时却突然从自己被公认的角色中挣脱出来,开始了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吴太太的独立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不离开家门的妇女解放,为丈夫纳妾,结束自己与丈夫之间无爱的性关系,给自己一份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可以称之为“精神出走”。这在男权中心社会中不失为是对男性统治权的大胆挑战。但这种反抗和寻求独立的行为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它牺牲了另一女子的自由和尊严以及家人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精神也因失去必须附丽的现实生活而显得空洞。第二阶段是接受意大利修士安德鲁的启蒙。安德鲁以睿智的目光看出在吴太太自我解放的背后是失去目标的迷乱和茫然,他以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影响她,以不受任何教规教条限制的平等精神点化她,以“世界一家”的博爱精神打动她,最终让她理清了思路,找到了定位。第三阶段是实践安德鲁的思想,以利他之心重新担当起管家的责任,并照料、培养安德鲁生前收留的孤女,把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扩大为以博爱之心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自主和独立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时,吴太太的精神已得到全面升华,并真正寻找到自由独立的价值。
与桂兰相比,吴太太这一形象的真实性有些可疑,更多地带上了作家主观想象和臆造的成分,但借助于这一形象所表达的思想却意义重大。吴太太的觉醒不同于桂兰的被动,更不同于她觉醒后的目标仍然是以丈夫首肯、悦纳为标志的家庭幸福,她的觉醒是主动寻求的,其目标是最终找到女子独立的、摆脱依附的价值和幸福感。在她觉醒的道路上,西方基督教思想起到了点醒、开悟、拨云见日的作用,在她把新与旧的美德集于一身时,两种文明的遇合也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理想的渠道。或许,这一形象的塑造足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作家的使命有别于历史学家,不仅仅以开阔的视野再现历史与现实,而且要以超越现实的勇气,以非凡的想象力,为人类提供可能成为现实的理想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涉及西方文化时较多使用了陌生化视角和漫画化手法,如桂兰打量和寻思丈夫的美国朋友,吴太太以怜悯心观察夏小姐,双方各有轻视对方的优越感,也各有误解。这种方法便于向西方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在西方国家把东方文化妖魔化的同时,东方国家同样也将西方文化怪异化。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增益彼此的价值,而相互鄙视只能显示自身的孤陋寡闻并造成可笑的误解。
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塑造的第四类女性形象,是那些既吸纳过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始终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并身体力行,自觉传播西方文化,促进两种文化互补互利、相互砥砺、共同繁荣的人。他们是作者理想主义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对未来世界的美好祝愿。这类代表有梅丽(《龙子》)、玛丽·梁(《同胞》)等。
梅丽是外交官之女,她虽长期旅居国外,接受西方教育,但在父亲的熏陶下,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国内抗战爆发后,她立即返回祖国,寻找出力报效的机会。她在教会学校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思想,与国民政府上层人物直接对话,试图改变政府的妥协立场。她后来与农民林郯的儿子相爱,相约到大后方昆明去继续抗日。梅丽这个形象出现在作品中显得十分突兀、不自然,有西方文学中常用的“机械降神”的意味。显然,这是赛珍珠为表达某种思想而创造出来的角色,她试图表达: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置身于异邦的海外华人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姿态。梅丽的行为就是作者提供的答案: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华人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应回归故里,共赴国难。
玛丽·梁是个有些男性性格的青年女子,有着严肃、认真、执着的个性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在父亲影响下,她从小就对祖国文化抱有强烈的情感。她虽生长于美国,但自始至终以中国人自居,从不贪图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时刻惦记着回归故里,用所学的育儿保健知识服务于国民。在亲眼目睹国内落后的现状后,她非但没有灰心,反而坚定了最初的信念:祖国需要她。她坚持回到最底层的民众中,去了解最真实的中国,给自己找到最准确的定位。为此,她从修建浴室、教室、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和保守、愚昧、迷信、肮脏、混乱以及顽固作斗争,积极向村里人传播科学、传播知识。她清醒地认识到这条道路很漫长,任重道远,但她和哥哥、爱人一道,把改造中国的计划一直设计到子辈,在把中国引导出封闭落后的道路上,她坚定而信心十足地走着。
如果说桂兰和吴太太在两种文化的际遇中终于找到了自我,梅丽和玛丽则超越了自我,性别观念不再是压迫她们精神的磐石,她们和男子一样,甚至比很多男子更具备行动的力量。这是赛珍珠自身不断突破自我的写照,也是她对全体女性同胞的殷殷期待。《同胞》多次写到纽约横跨宽阔的哈德逊河的华盛顿大桥,并赋予了这座桥以明显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的人物从华盛顿大桥读出了它的象征意义,最终成为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传播者,这不难令我们联想到尼克松总统对赛珍珠的评价: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玛丽这一形象多少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从桂兰母、结发妻到梅丽、玛丽,中国女子从无名到有名,从受虐到施爱,从被文化交汇的巨浪吞没到成为文化大潮中的弄潮儿,她们的精神历程虽历经坎坷、波折,但最终走出了自己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