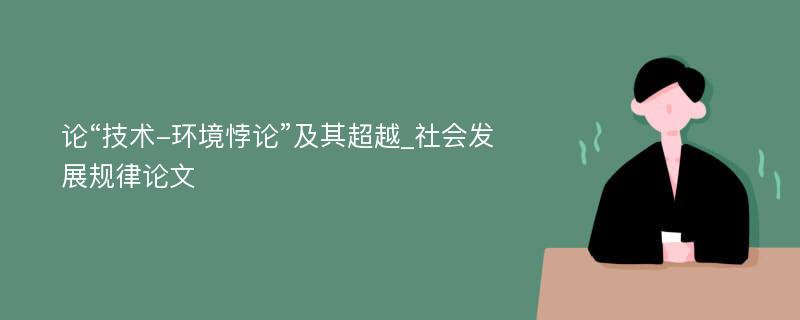
论“技术—环境悖论”及其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环境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0)07-0055-06
从技术与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强相关性来看,可以说,技术既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来源,同时又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前者如拉兹洛所言:过去二三百年的技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给人类造福,而是给人类造祸,因为它们消耗太多的能量和物质,造成的环境损害太严重[1];后者像格于布勒所讲:技术拥有巨大的力量,最终也只有技术能够使我们将自然环境从不利的人类干扰中解放出来[2]。保罗·格瑞(Paul Gray)把技术同时作为环境变化的来源和补救方法的这种特性描述成技术发展的“悖论”[3]。格于布勒在《技术与全球性变化》一书中对技术与环境的这种矛盾关系作了进一步考察,指出研究技术作为全球性环境变化的起因和补救方法这种矛盾即“技术—环境悖论”,“需要(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技术与全球性(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将环境逐渐从不利的人类干涉中解放出来”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4]。
1 从何而来:“技术—环境悖论”的生成与表现
“技术—环境悖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孕育于技术的生成中[5]。
技术生成是一种合自然规律性过程,但在技术的生成中同时也孕育了“技术—环境悖论”。这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技术生成是一个合自然规律性过程。这说明生成的技术能够具有维护环境、修复生态的功能,因为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本身就是一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过程,也就是说,生态环境与技术的生成一样,都是一个合自然规律性过程。“合自然规律性”作为技术生成的最根本的“合自然性”,表明技术是能够具有“作为全球性(环境)变化的补救方法”作用的。另一方面,技术生成中的“合自然性”同时又是建立在技术的“反自然性”基础之上的。因为技术的生成,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一定物质手段作用于物质客体的探索性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自然的“干扰”、“破坏”过程。可以说,技术的生成正是在“干扰”、“破坏”自然中实现的。这说明,技术又是能够成为环境问题来源的。以农药技术为例,农药技术是一种主要用于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消除杂草、调节植物生长的药剂技术,其技术生成是一个合自然规律性过程,譬如DDT技术就是如此——其合成工艺过程是一个合化学规律和生物学规律过程[6]。这表明,农药技术在“与自然控制因素及生物防治协调”中,是能够发挥“最大限度地减少农药在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各种弊端,使有害生物的治理做到技术上有效、经济上可行、环境上安全、生态上无害”的[7]。但农药技术生成中的“合自然性”又是建立在技术的“反自然性”基础之上的,譬如DDT技术的“合自然性”——合化学规律和生物学规律就是建立在“反自然性”——反生态学规律这一基础之上的。这说明,农药技术又是能够成为环境问题来源的。
“技术—环境悖论”一经在技术的生成中孕育,它总会以某种方式在技术应用中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技术应用作为一种技术物与自然物在技术规则支配下打破自然惯常行程、生产技术产品和产生技术副品即产生“人工物”的过程,而“人工物”具有“合自然性”的一面,这可从物质性维度来理解——从来源看,“人工物”来源于并在某种层面直接包含了自然物;从转化看,“人工物”通过人的参与产生于自然物,但“人工物”通过自然因子的参与也可向自然物转化;从受动性看,“人工物”与自然物一样,它们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与制约。可见,从物质性维度看,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人工物”具有“合自然性”的一面,它是能够发挥“作为全球性(环境)变化的……补救方法”作用的。但另一方面,“人工物”又是建立在“反自然性”基础之上的,这种“反自然性”不仅表现在技术应用中所产生的废渣、废气、废水等技术副品的“反自然性”上,而且也表现在技术产品的“反自然性”上——自然物具有自然天然性,而技术产品具有反自然天然性;自然物是自然环境的天然一员,而技术产品则是自然天然的“异己之物”,它会对自然系统产生“干扰”、“破坏”作用。也就是说,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人工物”的“反自然性”又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现实来源。
我们仍以农药技术为例。DDT作为一种具有杀虫特性的“人工物”,其“合自然性”的一面,既表现在其原子层面的自然构成性和使用后自然因子参与的转化上(尽管因其化学稳定、水溶性低、脂溶性高而难以为微生物分解而残留在环境中,但它并非不能分解和转化为“自然物”),也表现在它的“精准使用”与自然规律系统支配的整体作用中(自然规律系统的作用,使其在应用中存在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包括合乎生态学规律)相统一”的“平衡点”,该“平衡点”就存在于DDT技术的“精准使用处”)。这表明,“只要使用得当,(DDT)并不会对人和动物健康造成不良影响”[8]。当然,DDT作为天然自然的“异己之物”,“由于其设计和使用时未曾考虑到复杂的生态系统,化学控制方法被盲目地投入到了反生态系统的战斗”[9],当DDT大量进入环境要素,并通过扩散、运转、吸附、吸收、消散、富集等过程所进行的多方式、多轨迹地迁移和循环,造成了如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揭示的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可见,农药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人工物”的“反自然性”又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现实来源。
“技术—环境悖论”为什么能够在技术生成中孕育、在技术应用中表现呢?我们认为,这与技术本身的特性有关。
如上所述,技术具有合自然性,合自然性是技术的基本特性之一。但是,技术的合自然性同时又是建立在技术的反自然性基础之上的,反自然性也是技术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在技术—自然维度上,技术具有合自然性与反自然性的统一特性。技术的这一特性,提供了“技术—环境悖论”存在的客观基础。
技术还是科学知识应用的结晶。科学知识作为正确反映自然规律的认识成果,它在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世界的同时,也为技术的可靠性、稳定性提供了确定性基础。确定性也是技术的重要特性。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且这一特性在现代科学理论中更为凸现,克莱因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就是探讨这一主题的[10]。针对“确定性的终结”,普利高津还呼吁人们确立一种新科学理性,认为由科学知识概率性所表征的不确定性是内在于科学知识之中的[11]。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必将使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技术—知识维度上,技术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特性。这一特性,为“技术—环境悖论”的存在提供了知识基础。
概言之,是技术在自然维度的合自然性与反自然性统一特性和知识维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特性,提供了“技术—环境悖论”的存在根据。
2 何以可能:“技术—环境悖论”超越与技术特性的辩证运动
“技术—环境悖论”能否超越?回答是肯定的。其依据在于技术特性的辩证运动,具体地说,在于技术经历了“生态蒙昧技术”、“生态野蛮技术”发展后,其正在超越“生态野蛮技术”向“生态友好技术”发展的辩证运动。
如上所述,技术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在自然科学知识尚未建立之前,技术则以人类对自然现象的丰富认识即大量经验为其基础的,这便产生了人类技术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综合经验性技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从经验所得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12]。但是,感性的经验是“止于表面,流于肤浅,而不探求事物的究竟”的[13],以此为基础的技术在为人的活动提供“合自然性”手段时,由于其所依赖的经验知识对自然的认识不深从而对自然的“干预”也不深,其破坏自然生态的“反自然性”特性并不明显,技术的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立面尚未展开”的“朴素同一性”。在效能上,由于其之于自然生态所具有的朴素性、原始性,可以说,人类技术的第一历史形态——综合经验性技术是一种“生态蒙昧技术”、一种“原色技术”。
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建立,技术的知识基础——人类对自然本质认识的初步成果即分析科学知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的技术发展进入到第二历史形态——分析科学性技术。我们知道,分析科学是将自然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方面、因素和层次并分别加以考察的一种“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14],如物理学、化学,它所把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15],其知识往往具有“深刻的片面性”,以此为基础的技术在为人的活动提供“合自然性”强大技术支撑的同时,也因其知识基础的“深刻片面性”而在破坏自然生态方面的“反自然性”特性突出,技术的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立面的显现与分化”的“对抗性”。“技术—环境悖论”就是在此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在效能上,由于其之于自然生态所具有的破坏性,可以说,人类技术的第二历史形态——分析科学性技术是一种“生态野蛮技术”、一种“灰色技术”。
分析科学性技术的持续进步,使“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16],并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这意味着整个分析科学性技术范式面临着一种历史性转换,一种超越人类以往传统技术的新的技术形态——第三历史形态的产生!
人类技术的第三历史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综合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技术——综合科学性技术。由于综合科学是对自然系统进行深入、综合考察的一种“聆听自然、倾听自然”、“对自然亲近”的科学,如生态学、环境科学[17],它们“所揭示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多样性,不仅提供了一幅和传统的机械自然观迥然不同的世界图景,而且——孕育了一种强调相互依存、协调进化、关注未来、适度节约的价值观”[18],其知识往往具有“深刻的综合性”,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无疑是对人类以往传统技术的一种“扬弃”。这种“扬弃”既表现在它将克服以往综合经验性技术的知识基础的“经验性”和它之于自然生态的“朴素性”,克服以往分析科学性技术知识基础的“机械性”和它之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性”,保留综合经验性技术的“综合性”与分析科学性技术的“深刻性”,更是在综合科学知识这一新知识基础上的新创造,从而提升自身符合自然必然性的程度,即它既符合“征服型、力量型”分析科学所揭示的物理规律、化学规律,同时又符合“聆听自然”、“对自然亲近”的综合科学所揭示的生态规律、环境规律。这样,经过“两度否定”的辩证运动,技术的第三历史形态——综合科学性技术将成为一种“深刻的综合性”技术,技术的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的、更高层面的“对立面的协调性”。这一辩证特性告诉我们:综合科学性技术在为人的活动提供“合自然性”手段时,作为一种“深刻的综合性”技术,其“干扰”、“破坏”自然的能力或者影响将由于其遵循生态规律、环境规律而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持一种相容性,也就是说,综合科学性技术的“反自然性”是在一种更高层面上来实现其“合自然性”的。在效能上,由于其之于自然生态环境所具有的相容性,可以说,技术的第三历史形态——综合科学性技术是一种“生态友好技术”,一种“绿色(自然)技术”。
农药技术特性的辩证发展就是如此。农药技术的第一个历史形态是一种以天然物及无机化合物农药为主的“综合经验性技术”,无论是古希腊用硫磺熏蒸害虫及防病记录,还是中国用雄黄(三硫化二砷)防治园林虫害实践,都是以综合经验为其主要知识基础的该形态的典型样式。由于其“干预”自然不深,“反自然性”特性不突出,农药技术的第一历史形态主要还是一种“生态蒙昧技术”、“原色技术”。20世纪40年初,以DDT、六六六等农药技术产品为标志,农药技术发展进入到第二个历史形态——以有机合成农药为主的“分析科学性技术”。自不待言,这一形态是以分析性科学——化学科学为主要知识基础的。由于其知识基础的“深刻片面性”,该形态的技术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立面显现与分化”的“对抗性”,DDT的反生态性就是典型例子,可以说,农药技术的第二历史形态之于自然生态环境,主要表现为一种“生态野蛮技术”或“灰色技术”。20世纪70年代,鉴于有机合成农药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性,许多国家陆续禁用DDT、六六六等高残留的有机氯农药和有机汞农药,并建立环境保护机构来加强农药管理和技术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引导。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污染预防法案”,并把“杜绝污染源”作为“污染预防”这一新概念的最终目标,美国环保局还采用“绿色化学”一说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中心口号。这一切表明,农药技术正开始超越“生态野蛮”向“生态友好”发展的变化中,农药技术的第三历史形态——一种以“非杀生性”农药为主的“综合科学性技术”正艰难地向我们走来。由于该技术形态着重挖掘天然性物质,进而人工合成仿生农药及其类似物,通过对特异性生理活性物质的筛选和研究,从而达到控制或改变有害生物的生活习性、形态、生长和繁殖等,可见,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综合性科学将成为绿色农药的重要知识基础。自不待言,农药技术第三历史形态之于自然生态环境将具有极高的相容性,其辩证特性将主要表现为一种“环境友好技术”或“绿色农药(自然)技术”。
技术特性的辩证运动表明:超越“技术—环境悖论”是有其依据和可能的。
但应指出,在知识维度上,综合科学知识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综合科学性技术同样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特性。但由于综合科学知识是一种包含了生态科学知识、环境科学知识在内的知识,以此为基础的综合科学性技术尽管在本质上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作为一种生态友好技术,其应符合生态规律、环境规律则是“确定的”。这说明:“技术—环境悖论”仍然具有超越的依据和可能,但却充满风险和曲折。
3 出路何在:新绿色技术系统的构建、运行及其对“技术—环境悖论”的超越
如何超越“技术—环境悖论”?或者说,如何把“技术—环境悖论”超越的可能变为现实?我们认为:自然技术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活动和环境问题作为“世界问题复合体”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方向,这就是从“人—自然—社会”大系统的基本关系中去寻找超越的现实路径。
我们知道,“人—自然—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基本关系,且这两大关系是相互缠绕着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从单一关系的维度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技术维度来处理由双重关系——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及其缠绕所导致的问题如环境问题都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它忽视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同时以“缠绕”方式存在并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技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与社会关系及其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技术。更具体地说,在规范人与社会关系的绿色社会技术“缺位”条件下,由于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和自然技术的“求利”特性,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技术特性的辩证运动仅仅提供了“技术—环境悖论”超越的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绿色社会技术的“补位”必不可少!就像在农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仅仅只从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农药自然技术维度来处理由农药自然技术及其应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无视表征人与社会关系的绿色农药社会技术——绿色农药政策、法规以及落实绿色农药政策、法规的相关组织及其作用,而试图解决由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及其“缠绕”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技术—环境悖论”的超越难以奏效一样。在“人—自然—社会”大系统中,正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环境正义为价值取向的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包括绿色农药社会技术在内的绿色社会技术对人的自然技术活动的绿色规导以及绿色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在彼此交织、缠绕中的良性互动即新绿色技术系统的构建与运行才能使“技术—环境悖论”超越的可能变为现实。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构建的新绿色技术系统,即它是一种以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为理念、环境友好自然技术为基础以及与之契合与互动的环境友好社会技术为支撑的绿色技术系统。这一理解表明了新绿色技术系统所具有的如下“特质”:
在价值理念上,新绿色技术系统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和协调发展为价值理念的。这一理念立足于“人—自然—社会”的大系统观,从而确定了新绿色技术系统的整体性视野;这一理念厘定于大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及其缠绕的“技术线路”,从而确定了提高技术与环境相容性的思维路向;这一理念聚焦于对环境问题的别样理解——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综合体”,从而确定了超越“技术—环境悖论”的根本方略——坚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与协调发展。
在系统结构上,新绿色技术系统由两大技术系列——绿色自然技术系列和绿色社会技术系列构成。前者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系列,后者是一种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系列;在内容上,前者主要是以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科学知识为基础、以自然为作用对象的绿色自然技术系列,后者主要是基于一定环境伦理基础之上的环境政策、环境法规及其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以人的活动为规制对象的绿色社会技术系列。自不待言,两大技术系列中的有关“技术目标”的确定、“技术方案”的设计、“技术效能”的考量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和表征了“人—自然—社会”大系统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关系的缠绕。不仅如此,在这种缠绕的背后,包括官僚、学者、公共舆论、利益集团、国民情绪、乃至党派、意识形态等复杂社会因素都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交织于其中并对两大技术系列的生成和运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两大技术系列不仅缺一不可——没有绿色社会技术系列,绿色自然技术系列就失去社会的规范与支撑;没有绿色自然技术系列,绿色社会技术系列将失去现实的根据与基础,而且绿色技术系统的良好功能状态有赖于两大技术系列的契合与良性互动。
在内在特征上,绿色技术系统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视交汇”性质。这是因为:绿色技术系统中“内生”着“两只眼睛”,一只是由自然科学“母体”所“内生”的“科学之眼”,其主要功能是“视物”,另一只则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母体”所“内生”的“人文之眼”,其主要功能是“视人”。在绿色技术系统中,由于其价值理念的定向作用,它们将“双视交汇”于“人与物”的关系活动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活动中,并聚焦在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两大技术系列的共同“焦点”——“环境友好”上。绿色技术系统的科学与人文“双视交汇”特征告诉我们:该系统既有科学的强劲推动,又有人文的方向制导,这将大大降低绿色技术系统的风险。同时也说明,在知识维度上,新绿色技术系统的知识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既包含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如生态学、环境科学,也包含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如环境伦理学、环境政策学等。
新绿色技术系统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这就是“自然技术之于环境问题的生成及其衍生机理”和“绿色社会技术之于规制对象的作用及其致绿机理”的“双螺旋互动”。简要地说,由某一时期的一定自然技术水平(包括这一时期人们使用自然技术的方式)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以“问题推进”的方式“衍生”出绿色社会技术的新的设计与安排,从而使绿色社会技术水平达到另一新的高度,体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环境正义水平也将随之提高;与此相应,绿色社会技术的这种新设计、新安排及其实施又将以“制度规导”的方式使自然技术“致绿”,即促进自然技术“绿色水平”的提高(包括在绿色社会技术“规导”下的自然技术的“绿色生成”、“绿色应用”和自然技术产品的“绿色消费”等),从而使自然技术的“绿色水平”达到另一新的高度,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也随之提高……如此循环,绿色技术系统的运行便表现为一种以绿色自然技术和绿色社会技术为“双链”、以“问题推进”和“制度规导”为“配对”的“双螺旋”演进模式。正是绿色技术系统的这种“双螺旋”演进的运行方式,使绿色技术系统中的两大技术系列得以契合与互动,使绿色社会技术的供给与绿色自然技术的进步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协调”中不断发挥着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效能,从而实现“技术一环境悖论”的超越。自不待言,在超越中,由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的“绿色水平”不断提高所表征的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不断改善,我们发现,新绿色技术系统的运行将为我们“形塑”一幅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及其协调发展的文明图景。
收稿日期:2010-01-15
标签: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科学论文; 生态学论文; 科学性论文; ddt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