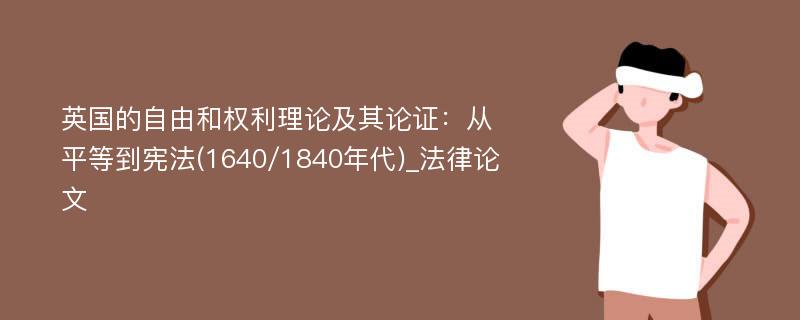
英国的自由与权利学说及其争论:从平等派到宪章派(1640—1840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章论文,英国论文,学说论文,派到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096-13
英国1640-1840年代的人权争论涉及大量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自由观念。两种不同的自由观是这一时代自始至终的辩论主题,这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关心的是设定个人——包括拥有权威的个人——干预他人活动的权力的界限。因此它确定的是个人按自己的愿望行动或生活、且不受他人干预的空间。当然,这种消极自由并非无限的,否则政府对国民便没有任何权威,造成无政府状态,弱者的自由也会受到强者的自由的压制。因此,消极自由必须有法定的界限,为此而斗争的人们坚持认为,应存在某种绝不能侵犯的最小范围的自由。为了保护这最小的自由空间,必要时可采用武力,以防止任何人的入侵。另一方面,积极自由关心的不是免于外部干预的自由,而是个人成为自己主人的权利,或至少是分享决定谁来统治他的权利。争取积极自由的斗士们涉足的争论,不是政府对国民所能拥有的合法权威的问题,而是关于国民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问题。更为激进的积极自由的支持者们主张,所有或大部分成年男子,后来还包括所有妇女,都能参与决定由谁行使国家法定权力的工作。一些为消极自由而斗争的人士继续要求积极自由,认为这是保障其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但另一些思想家则认为,这两种自由观念可能产生冲突。人民主权可能威胁个人的消极自由,因为多数可以对少数行使暴政。甚至民主选举的政府也可能作出剥夺个别国民的大多数个人自由的决定。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争论使得另一些思想家产生这样的看法:两种自由观念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个人的状况和财富千差万别。可以十分合理地认为,一个人若贫穷或受人鄙视到一定的程度,他便无法完全享用他合法拥有的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这种贫困并不必然是相关个人自己的过错。它可能是别人有意识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在这种情形下,贫困是经济压迫的牺牲品,这种压迫使得他们无法充分享有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因此,为了保证个人能够保卫其消极自由或行使其积极自由,就必须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①
人权的这三种形式——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经济自由——显然是相互交织的,在英国,它们还经常同时成为辩论的对象。不过,为了清晰起见,本文将依次探讨关于这些观念的争论。虽然本文优先考虑的是分析步骤而非年代顺序,但重大的思想发展仍首先出现在关于消极自由的争论之中,随后关于积极自由的争论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接下来是关于经济自由的争论。
一、消极自由之争
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人认为,在法律或道德方面,统治者的权威受到或应该受到法律、习惯或高级权威的限制,17世纪的英格兰无疑也是这样。不过,关于个人可以拥有的消极自由的限度、关于统治者的权威应有的界限,当时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保守派或反动派思想家们认为,统治者的权威必须是广泛的,甚至是绝对的,而臣民的自由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要避免无政府状态的话。凡臣民可使其权益高于国王意志的地方,自由就会变得无法无天,所有秩序都会退化为大混乱。尤其是在1660年以后,大量作品宣称国王的权威是绝对和随心所欲的,他的权威不受人民或人民代表的限制,亦不受议会之类的其他国家机构的限制。国王的权威如此广泛,以致它高于成文法、普通法和古老的习惯法。臣民的自由并非不可侵犯,他只能按国王的意思享有这种自由。即便国王的行为像个专断的暴君,他的臣民也不可以用武力反抗他的权威。国王唯一可能遭受的制裁是神的惩罚:就算今生没有惩罚,另一个世界里也终会有的。
从这种论点出发,可以得出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臣民没有任何形式的消极自由,他们的服从是彻底的、无条件的。但实际上,绝对权力的理论家从不打算否认臣民各种形式的消极自由。例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便认为,即使最卑微的臣民也有权使用武力挽救或保卫自己的生命。甚至最笃诚的王权主义者通常也愿意承认英国教会关于消极服从理论的说教。这种理论认为,当绝对君主发出的命令明显违背神的律法时,臣民不必服从这一命令,尽管他不可以用武力来反抗发出命令的统治者。臣民只需拒绝服从君主的命令,但也应自愿消极地承受不服从招致的惩罚。臣民必须接受尘世君主的责罚,并坚信他和君主都必定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站在最高裁决者——神的面前。大多数支持绝对君主的保守派也希望国王按照众所周知的法律和古老的习惯进行统治。虽然他们承认,国王理论上可以改变任何法律或无视任何习惯,但他们相信,国王在实践中仍会按照确定的程序实行统治,并且肯定会遵守那些他自己并未修改或撤销的法律和习惯。换言之,甚至绝对君主也可能根据法制原则行使统治权,因而臣民也可自由行事,只要行事的方式不是国王的意愿所明确禁止的。在17世纪的英国,绝对主义王权的支持者并不期望国王像个专制暴君那样进行统治。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通常应得到保障,除非他违反国王制订或认可的法律,除非国家利益要求他作出别的选择。
保守主义者在为绝对主义王权辩护,他们的对手更愿意捍卫和扩大所有臣民都应享有的消极自由的范围。更具自由色彩的思想家们认为,只有王权受到限制、全体臣民都享有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方能实现。个人的消极自由总是被描述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权利。② 从最有限的意义上说,这一诉求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得到保护以免受他人的侵害,而且只有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之后,这些权利方可交给当权者。在自由派宣传家的笔下,“正当的法律程序”指的是根据某些人为法——如成文法和习惯法——作出的决定,而非依据国王个人的专断意志作出的决定。为了限制国王对其臣民行使的合法权威,自由论者援引成文法和普通法、古老的特权和自然法。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的消极自由包括如下个人权利:未经审判不得监禁,法律面前地位平等,由同侪(即与自己身份平等之人)进行审判。不过,即便是所有人的司法平等也不被视为消极自由的充足保障措施。许多自由派思想家坚持认为,所有臣民都有不可让渡的财产权,以及广泛的良知(即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封建制度下,臣民对私人财产不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因为所有财产都由国王支配。不过到17世纪初,英国的封建主义明显消失了,臣民日益自觉地捍卫其私人财产权。例如,国王查理一世的反对者经常对国王对私人财产的具体威胁提出抗议。他们憎恶强制借款、船税、在私人家中驻扎部队,以及任何未经议会同意征收的税收。不过,直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于1690年问世之时,具有说服力的私有财产哲学辩护才提了出来。洛克详细论证私有财产起源于自然状态,那时还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府,而公民政府的设立就是因为保卫这种自然财产权的紧迫要求。神已经创造一种自然状态,那时所有人都可享有世界上的果实。然而,要想享用果实就必须占有果实。在占有果实前,人必须运用自己的劳动,而且,由于他们的劳动是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因此他们劳动的产品也成为他们的私人财产。由于人在劳动及利用劳动的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因此私人财产在自然状态下的划分也是不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私人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及保有私人财产的愿望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成为设立公民政府的主要推动力。洛克坚信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因此他认为政府不能合法占有个人财产或对其课税,除非得到个人的同意。如果有人犯下罪过,他就可以被视为默认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无罪者的财产只有在个人或其选定的代表明确同意时方可被课税。因此,个人对私人财产的消极权利也要求他拥有能影响涉及财产权的政治决策的积极权利。③
在17世纪的英国,关于信仰自由的思想辩护也取得重大进展。清教派别最初要求宗教宽容是为了避免迫害,但它们当中有些人很快就提出,宽容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收获。宗教激进派开始论证说,人不可能发现一整套令神满意的信条,也没有哪个真正的教会有合法的权利去迫害那些拒绝皈依它的人们。因此所有人都有听从自己良知召唤的自由。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比清教布道者更进一步,他歌颂个人的理智和判断力。在他看来,宗教迫害始终是多余的,因为真理将最终胜利。1660年君主制复辟后,英国教会中的一些自由派成员甚至准备承认,虽然对与错之间存在根本和永恒的区别,但应该赋予每个人选择对与错的自由。约翰·洛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并为此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哲学论证。洛克在《论宗教宽容》(1689-1692年)中认为,每个人都有坚持和表达他所选择的观点的自然权利,只要这些观点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道德。洛克并不打算容忍罗马天主教徒或无神论者,因为他认为他们的观点对社会构成威胁,他也不相信他们能实践与别人的契约;不过洛克关于信仰自由的解释比当时任何人都更宽泛。实际上,直到1859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问世,英国思想家才给出更为广泛的定义。④
在捍卫和扩展消极自由范围的过程中,绝对主义王权的反对者总是强调法治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法治确立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威与臣民自由之间的界限。但是,只有当国王对专断和绝对权威的诉求能被击败时,法治才可能有保障。国王的意志、他的特权范围,都必须有法律限定。很多激进派希望以基本宪政法律来限制国王(或议会)的权威。平等派提到的“保留”权利,如宗教自由权利,在法律上是绝不可以受任何国家权威侵犯的。辉格党人和18世纪后期的激进派还要求,个人的某些消极权利应以新的权利宣言加以阐明,以便不受国王或议会权力的侵犯。
如果国王坚持要突破其权威的法律界限,他的臣民就必须诉诸合法的抵抗形式。为了在最后时刻有所依靠,他们必须拥有保卫其消极自由不受暴政侵犯的必要力量。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威,论证抵制权威滥用的合理性,专制君主制的反对者们坚称英国拥有一种混合宪政。在这种混合宪政中,作为行政首脑的国王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威,但最高主权属于立法机构,而在立法机构中,国王的权威受到限制,因为他必须与其伙伴,即上院和下院在立法机构中合作。在这种混合宪政中,最高立法权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接受这样的限制:它必须与另两方达成一致。不幸的是,当作为行政首脑的国王以让许多臣民深为憎恶的方式行使王权时,这种混合宪政并不能解决由此造成的僵局。于是,面对把持着范围如此广大的独立权威的君主,他的对手不得不考虑如何论证抵抗这种君主的合理性。他们并不希望完全取消国王的特权,也不急于鼓励民众去造反。一个虚弱的君主制会造成政治动荡,而向普通人(他们称之为“多头怪兽”)求助则会导致彻底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640年代,查理一世的一些较为保守的反对者,特别是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和查尔斯·赫尔(Charles Herle),尝试证明人民有创建公民政府的合法权威,但同时又强调,一旦公民政府存在,最高权威便归于议会。⑤ 这些理论家论证说,在自然状态下,权力最初属于人民,唯有人民的制宪权威可以创建合法的公民政府。但政府一旦建立,立法机构便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在英国的混合制政府中,立法权威由国王和议会两院分享。如果国王滥用权力并威胁人民的消极自由,或威胁其立法合作者的权利,那么议会也唯有议会,必须运用必要的力量去捍卫宪政的平衡和臣民的自由。一旦国王权威和臣民自由之间出现争论,只有议会应充当裁决者和最后的法官。
议会作为王权与臣民自由之界限的最终裁决者的理论在1640年代初就已提出,1688-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再度被运用,此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过,但实际上,这种理论并未给上述难题提供逻辑一致的解决方案。混合宪政观念表明国王和议会是如何协同立法的,但它没有指出,立法机构中的一方,即议会,如何才能论证其抵制作为行政首脑、一个完全与之平等的立法伙伴的国王的独立权威的合理性。1640年代的激进派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坚称,人民不仅首先建立了公民政府,而且此后也一直掌握国家的最高主权。这一终极权威赋予他们抵抗国王、甚至抵抗议会的权力,如果他们的自由被侵犯的话。⑥ 按照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看法,是约翰·洛克从哲学上给了主权定位和反抗权的难题以合乎逻辑的解答。洛克反对绝对君主制,同时也否认议会在任何情况下具有最高主权。他坚持认为,最高权威从一开始就属于人民,但人民根据契约或协议将其授予最高立法机构。不过这种授予是有条件的。如果立法机构不再履行人民委托的职责,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那么它的权力就不再是合法的,整个政府制度就此瓦解。在英国,立法权威由国王和议会分享,所以当宪政被破坏时,立法机构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当最后的绝对裁决者。如果人民受到奴役的威胁、一切消极自由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他们就解除了对立法机构或其任何一方的义务。这时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最能满足其需要的新政府形式。⑦
关于如何在混合宪政中保护消极自由并反抗暴政,洛克提供了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解答,不过他的激进结论从未得到他的辉格派盟友的认同,也从未被确认为英国的法律。相反,1688-1689年革命之后,绝对而不可抵抗的主权被授予国王和议会组成的联合立法机构。[1](P189-210)从此以后,在英国,捍卫消极自由便不得不依赖于个人反抗对其自由之侵犯的意愿,甚至需要依赖保守的议会主权辩护者也承认个人的消极自由应是广泛且不可侵犯的。富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思想家,如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和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都拒绝人民主权观念,并弱化反抗最高立法机关的权利,但他们也承认人民拥有消极自由,承认最高立法机构若滥用权力、侵犯臣民的自由,则政治稳定是不可维系的。⑧ 不过在实践中,一旦人民能够对最高立法机构的决策施加有效的影响力,他们便有一个捍卫自己自由的强有力的地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应实现积极自由。
二、积极自由之争
两个世纪以来,积极自由之诉求的理论依据在于:人民是自然状态下的主权者,他们享有掌握最高权威的自然权利,即使是在他们同意创建公民政府之后。国王和议会的权力都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1640年代的平等派宣传家们最早提出,立法机构应对人民负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该在更具民主色彩的选举权、而非当时的有产者选举权的基础上经常选举议员。平等派要求的选举权究竟如何民主?现代史学家对此有过很多争论。传统见解以为,平等派是男子普选权的倡导者,但C.B.麦克弗森反对这一看法。他论证说,平等派可能否认所有仆役、工资劳动者以及领取贫困救济者的选举权。在他看来,平等派仍然赞成有产者的选举权,而且他们的改革可能排除2/3的成年男子的选举权。[2](P107-159)麦克弗森接受的显然是较为保守的平等派的观点,但他忽视了帕特尼辩论和大量的平等派小册子之中的更为激进的说法。⑨ 虽然平等派在第二和第三篇《人民协议》(Agreement of the People,1648-1649年)中并不赞成男子普选制,但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为了争取一些较为保守的军官而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即使在最为局限的情形下,平等派也主张全体男子户主享有选举权,其中将包括很多农夫和工资劳动者。这样一来,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人口比例肯定高于麦克弗森的看法。⑩
平等派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但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和其他辉格派复活了1640年代的一些激进观念。他们认为,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必须致力于保护臣民的自由,并可限制国王的权威,但他们并不质疑有限的有产者选举权,议员们正是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的。约翰·洛克是最激进的辉格派理论家,他无疑已经承认,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包括签订作为任何合法的公民社会之基础的原初契约的权利。但在实践中,他并不质疑一个由拥有殷实家财之人支配、在狭隘的选举权基础上选举出的立法机构,他从未积极地为男子普选权斗争。(11) 其他辉格派理论家,包括阿格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詹姆斯·泰雷尔(James Tyrrell)、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和约翰·特伦查德,都相当清晰地表明支持有产者选举权。他们还准备否认大多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享有投票权。(12) 除洛克外,大多数辉格派甚至想把反抗权仅限于有产者精英,因为他们担心善变而危险的暴民太容易拿起武器反对政府。(13)
这些观点造成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但是与此同时,对更为民主的选举权的要求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为了论证这些要求的合理性,人们或援引所有人都有将其在自然状态下的平等自由转换成公民社会中平等的积极自由的自然权利,或援引所有英国人都参与选举其议会代表的历史权利,或援引功利原则。第一种论证是依据对洛克的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政府权力来自人民之同意等观念的常识性的字面理解。第二种论证是基于对英国历史的一种误读: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所有英国人都拥有选举权。[3](P50-122)第三种论证是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政治制度应以它带给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总量为归依。(14) 这三种论证,特别是援引自然权利的论证,都因18世纪的思想发展而得到强化。在这些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很可能是争取宗教宽容的漫长斗争:宗教宽容日益建基于上帝眼中所有人精神上的平等,建基于每个人作为人而享有的宗教自由权利。如果对18世纪的非国教新教徒的抗争作品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关于信仰自由的诉求是如何逐步从论证其宗教仪式和教会组织模式更具正当性转变为要求不可让渡的个人判断权利的。[4](P179-192)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认为宗教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或公民权利,但他强调,为了保证这种消极自由,所有人都必须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享有积极的发言权。[5](P54-55)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甚至更明确地把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他坚持认为,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所有人都应自由地作出判断和决定。(15)
激进派思想家关于原始人的美德和未来的进步前景的乐观主义看法,同样也促进了争取积极自由的斗争。他们满怀信心地断言,自然状态是一段切实存在的历史经历,当时的原始人确曾享有平等自由。在那个黄金时代,大多数人都天性善良,他们的理智还没有被腐化,只是一小撮权势者的勃勃野心使得创立公民政府成为必须。设立公民政府的原初契约保障了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包括参与立法过程的积极权利。不幸的是,公民社会最初的民主制度被一小群自私者腐蚀和损害。为了恢复积极自由,人们必须回归原初状态下的原则,回归最初曾享有的政治平等。(16) 但令人困惑的是,很多援引原始黄金时代的激进派也相信未来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他们坚信未来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人类的理智将控制环境、将实现一种人人皆可享有平等而广泛的积极自由的政治制度。只有当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其理智的全部潜力才会完全发挥出来。因此进步取决于人的平等自决权。(17)
在18世纪的英国,这些思想发展鼓励并论证了18世纪争取广泛的政治改革的运动,不过,激发民众支持政治改革并影响了改革方案的独特性质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变迁和国外的革命。到1730和174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向人口众多的富裕地区重新分配议会席位、每年进行选举和秘密投票的要求。(18) 30年后,不列颠和美洲殖民地都可听到“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国家的所有纳税人都应有权选举征收税款的下院议员,而这样的观念又导致对男子普选权的要求。因为所有男子都缴纳了某种形式的税款。[6](P215-220)到1780年,一些激进派已经在为全面的议会改革方案而斗争,这一方案成为1830和1840年代的人民宪章的基础,即:男子普选权,每年一次大选,平等的议会选区制,秘密投票,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要求并支付薪酬。(19) 这些主张是随后几十年中议会改革运动的基础,但是,理性自然权利思想流派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并不满意这样一个仅限于对下院议员选举制度进行民主化的方案。1790年代初,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已经完全摆脱了早期激进派的思想影响,如赞美平衡的宪政、喜欢向过去寻找灵感。潘恩主张废除君主制和贵族制。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制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消极自由和完全的积极自由。每个人都应享有表达自己政治观点、选择行使国家权力之人选的平等权利。[7](P65-72,123-133)潘恩自己将这样的积极政治权利局限于成年男子,但关于自然权利平等的理性论证很快就将这样的积极权利扩展到妇女。(20)
关于成年男子的议会选举权的要求显然在18世纪末就已提出,这一要求也是1830和1840年代宪章运动的核心,但论证妇女选举权的合理性的斗争要艰难得多。在18世纪末,大多数激进派并不提倡妇女选举权,因为他们认为妇女依赖于父亲或丈夫,因而无力行使完全独立的公民的政治权利。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论证说,妇女没有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因为从自然本性上说,她们没有能力为政府工作或担任国家的军事保卫者。[8](P17)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愿意让妇女参加议会选举,但不希望她们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担任积极角色。[9](Pxiv-xv,62-63、107)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是著名的边沁主义者,他在其著名的论文《政府论》(载于1820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版增补)中明确反对授予妇女议会选举权的提议。(21) 1830和1840年代的很多宪章派曾要求改进妇女教育、增加妇女就业和工资,但这些人在提到妇女选举权的可能性时也是不冷不热。(22) 不过,早在1825年,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就为给予妇女完全的政治权利提供了最完整、最富影响力的思想辩护,虽然他的论证在英国并不被广泛认可,甚至也没有为稍后的激进宪章派完全采纳。(23)
直到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激进的自然权利理论仍然具有影响力,但是它很快就受到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来自埃德蒙·柏克这样的保守派思想家,而且来自受边沁功利主义影响的哲学激进派。杰里米·边沁争取积极自由的思想基础完全不同于潘恩政治理论的哲学根基。边沁认为:“自然权利纯粹是胡言乱语: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是修辞学上的废话,是夸张饶舌的谬论。”[10](P501)边沁拒绝所有人都享有积极自由的基本自然权利,但他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原则:对政府的判断必须依据它的功效以及它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良好程度。立法机构应是至高无上、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的,但它应始终受道德和现实的约束。任何臣民在法律上都无权对立法机构置之不理或不服从它的法律,但议会也没有制订任何它所愿意的法律的无限权力,亦无权剥夺臣民抵制它的道德权利。这种限制是必须的,因为立法机构有为公共福祉而工作的道德义务。立法机构之所以至高无上,仅仅是因为没有控制它的明确法律或惯例,不过任何臣民都可以反抗,如果他——根据自己的最佳计算——认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进行抵制的风险要小于服从的危害的话。因此,最高立法机构的权威受到臣民认可的行动范围的限制。
这些看法正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依据,这种原则即:每个人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他通常就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决者。社会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幸福和愿望像任何他人的幸福和愿望一样重要。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说在理性和智慧上并不平等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决者,那么所有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肯定应被视为公共利益的最佳裁决者。因此最佳政府就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但边沁指出,不幸的一点是,所有政府都更关心统治者的利益而非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应时刻监控统治者,应动用一切措施保证他们履行对被统治者的义务。政府应尽可能地让人民自行其是,以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因为他就是自己幸福的最佳裁决者。如果个人的消极自由必须受到侵犯,那么采取这一决策之人应对所有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不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应考虑公共利益,如果二者相互冲突的话。政府服务于其本来目的——即增进最大多数臣民的最大幸福——的唯一方式是给予所有人选择其在最高立法机构中的代表的权利,从而让每个人都担任政府的法官。在享有选举立法机构成员的积极自由后,人民将普遍挑选那些热衷于为公共利益、即个人利益的总和服务的代表。当选的代表则热心促进公共福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失去权力。因此,功利主义的原则让边沁得出这样的结论:代议制民主是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无论是在限制统治者的自私,还是在促进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利益方面都是如此。
杰里米·边沁在开始其创作生涯时并非积极自由的激进倡导者,但是,当他的《议会改革方案问答手册》(写于1810年,直到1817年才发表)问世后,他转变为一个像托马斯·潘恩那样的坚定的激进派。他开始为典型的激进改革斗争,如男子议会普选权、每年一次大选、议会选区平等、秘密投票制等,但他的要求远不止此。边沁主张废除君主制、上院和建制教会。他认为,议员只是选民委派的,而不是憎恶接受选民意见的独立代表。边沁的学生詹姆斯·密尔是1820和1830年代哲学激进派的主要理论家,他在1820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政府”一文中为代议制民主进行了辩护。不过,他更强调政府是保护个人免受他人侵犯的工具。代议制民主不仅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最佳方案,还是确保政府保护弱者免受强者侵害的最有效途径。当所有人都享有选择自己统治者的积极自由时,他们就有可能防止管理不善,也有可能对强者的行为进行控制。人的自私不可能根治,但民主制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更能在天生谋求增进个人利益的人群当中建立起利益和谐关系。(24)
三、经济自由之争
直到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时,大多数思想家仍仅仅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政治意义上探讨人权。暴政和压迫总是被诊断为政府过分且专断地干涉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当然,暴政也逐步被视为一种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当权者既不响应人民的愿望,也不受人民监控。但如果一个人因为贫困而无力保卫或增进自己的利益,那很少被视为暴政或他人压迫的结果。然而,少数思想家开始认为,很多人的贫困是强者有意识的行为造成的。因为这种贫困并不是源于贫困者的懒惰或邪恶,而是富人和强者的自私。因此,完全的政治自由只有在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或完全弥合时才能实现。
大部分致力于扩大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政治激进派,都明确反对任何旨在攻击财产私有制或以强力重新分配财富的建议。1794年谢菲尔德的一次激进派集会作出决议:“我们并不主张虚幻的财产平等,如果实践这种平等则毁灭世界,并使其重新堕入最黑暗最狂暴的野蛮主义。”[11](P738)杰里米·边沁声称:“财产平等对生存的根本原则而言是毁灭性的:它割断的是社会的根基。如果不能保障自己劳动的果实,是没有人愿意劳动的。”(25) 不过有迹象表明,一些激进派的确认识到政治暴虐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例如,平等派曾批评高额税收、什一税、专卖政策,还有导致少数富人支配众多穷人的不公正地围圈公有土地的行为。托马斯·潘恩在其十分成功的《人权论》第二部分中提出了几个减少贫困的方案,包括老人年金、家庭津贴以及母幼补贴。他在题为《农业正义》的小册子中提出,应对富人的财产课税,以便征收足够的税款,让每个男子年满2l岁时能有一笔15镑的收入、每个年满50岁的人每年能有10镑的年金。潘恩相信,压迫性的政治制度自然对穷人课征重税,而民主制度将用对富人的课税来接济穷人。他认为,仅仅进行政治改革也肯定能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因此不必利用物质手段去摧毁财产私有制。
这些方案仅仅谋求减轻贫困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而一些激进派理论家提出了进一步的主张。他们要求对财富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第一个在17世纪倡导这一做法的是杰拉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他是“掘地派”小公社的主要理论家和代言人,这些公社试图收回被权势者据为私有财产的公地。温斯坦莱声称: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为公共财产,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比他人富有从来都是依靠对他人劳动果实的强制剥夺。土地私有制是压迫的产物,由此造成的经济不平等辱没了那些被迫屈从之人的尊严。只有首先实现经济平等,完全的政治自由才有保障。温斯坦莱倡导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工资劳动、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在他的乌托邦社会里,人们过着集体生活,平等地分享耕种土地的产品。温斯坦莱并不主张用暴力革命根除私有财产,他更倾向于依靠上帝的影响力和宗教规劝的力量,但他本人鼓励掘地派小公社从个人手中收回从前的公有土地的努力。有产者的激烈反应使得这些行动很快失败。(26)
18世纪末,威廉·奥吉尔维(William Ogilvie)等少数激进派提出了将荒地和公地分配给穷人的方案。(27) 威廉·葛德文甚至希望看到私有制被彻底消灭,但他反对强制没收的做法,而是希望对富人晓之以理,劝其放弃不公正和过多的财富。[12](P423-477)真正主张在全体人民中重新分配财产的革命方案是托马斯·斯宾塞提出的。他深信,仅有政治权利——不管如何广泛——是绝不可能防止穷人受富人压迫的,因此他提出,将他认为的一切实际权力的源泉——土地置于所有公民手中。斯宾塞著名的土地方案不主张土地国有化、以便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他希望国家每个教区的居民都组成团体,这样的团体可以拥有和控制教区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可以出租给报价最高的承租者,后者亦可在缴纳规定的租金后耕种牟利,但耕种者个人绝不可拥有或出卖土地。土地租金用来支付房屋、桥梁、道路、学校、图书馆、医院、会堂等费用,这些设施均归教区全体公民使用。在这个新社会里,富人可以保有个人财产,最有能力的人可以耕作经营自然资源谋取利润,但没有私有土地所有者,而极端的贫困也将从社会中永远消除,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能够繁荣起来,因为所有公民都免于经济压迫。[9](Pxii-xiii)
托马斯·斯宾塞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地区,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大城市、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制造业造成的经济社会难题。他完全关注于自己的消灭大地主权力的计划。然而,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在思考快速工业化和无节制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和经济压迫。在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威廉·汤普森、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dgskin)、约翰·格雷(John Gray)和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Erancis Bray)等人看来,英国的新工业社会将最大部分的收益给了那些拥有财产、控制资本的懒散之人,而以劳动创造了大部分财富的多数劳动者得到的微薄报酬却不敷家用。查尔斯·霍尔称,穷人只得到了其劳动价值的1/8左右。约翰·格雷计算的比例是1/5,约翰·弗朗西斯·布雷则深信,劳动者至少被剥夺了2/3的正当工资。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非生产阶级不正当地占有,因为他们控制着资本、土地和政治权力。这个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奢靡浪费、盲目竞争,并具有压迫性。劳动者的贫困和虚弱是占有资本和财产之人的不劳而获的财富及不正当的权威造成的。因此,仅有政治改革不足以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竞争也应该被废除,经济应该受控制,劳动应该有组织,这样工业发展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福利。资本主义分裂社会,它造成的无情竞争助长了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及穷人对富人的依附。劳动必须从资本的压迫性控制之下、从政府强大的管理机器(它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持贫困、剥削和不平等)之下解放出来。(28)
这些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不公和政治压迫深为关切。在他们看来,工业社会增加了资本的权力和财富,但剥夺了穷人的经济独立和政治自由。因此需要进行改革,将穷人从经济剥削和政治虚弱中解放出来。必须运用知识和教育来改造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重塑政治和社会关系。当所有人都完全懂得自己的权利、当生产组织实现合理化时,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都会被消除。但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平等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如何才能使其成为现实?对于这些问题,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过于乐观,甚至不切实际。他们认为,理智和规劝足以终结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对穷人的压迫。正因为如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谴责这些作家是“乌托邦主义者”,不过这个指控并不完全恰当。
大多数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都不反对议会改革的建议,他们只是认为这些措施还不够。相反,他们提出了小型民主公社的劳动合作制方案。土地和财产应归地方公社集体所有,并置于劳动者自己的民主控制之下。劳动组织应有效,产品分配应公正。这里没有租金、没有货币利息、没有资本家的利润。这里没有闲散阶级,所有人都必须劳动,所有劳动者都同工同酬。这些倡议的确催生了一些合作公社和数百个合作协会,但它们通常因为经营无效而失败。这些方案本身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声称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国有工业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转可以对一个广大群体产生最大的利益。早期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最重要决策可以在这些没有官员、没有政府规章的小型合作公社内产生。他们没有意识到,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扩张已经使得英国社会大为复杂化,一个集中化的官僚机构已经在所难免并事关重大——如果要改善工人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话。这样他们就忽视了政治权力如何既受约束又能更为平等地分配的问题。
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看法同样是不切实际或乌托邦式的。他们坚信,教育和理性将教导人们懂得社会平等的好处。他们相信能说服少数特权者为了工人大众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认为,求助于推理能力和所有人都同样具有的正义感便能协调富人和穷人、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看法的批评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的批评有时走得太远了。早期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也已认识到必须依靠工人自身。他们鼓励工人组成工会,以便穷苦人之间能够自助。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忽视启发和教育受剥削的穷人的意义,他们也注意到,应鼓舞工人团结起来壮大力量,以终结不公正的制度——尽管资本家剥削者的反对力量很强大。另一方面,早期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注定是敌人,他们绝不可能被规劝去反对自己的阶级利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社会变革只能依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仍坚信,阶级和谐的目标可以实现。他们反对使用武力,即便这武力针对的是他们谴责的资本家有产阶级的压迫者和统治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产生的暴力将涤荡这些社会弊病,但早期社会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无法支持那种他们认为无望实现其目标的暴力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权力知之甚少,他们政治思想中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不过许多年来,这些不切实际的方案逐步让位于更为冷静的期望和更为有限的目标。由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斗士们取得的成就,更为关注经济压迫的人们数十年中根除了工业社会中一些贫困和不平等现象。(29)
1830和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获得的支持比此前的任何改革运动都要多,但这场运动主要关心的是实现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变革。支持人民宪章的三次全国大请愿书主要是为了实现著名的议会改革六点计划,该计划旨在实现下院选举的民主化。加雷斯·斯台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令人信服地指出,宪章派之所以提出政治改革方案,是因为他们相信,穷人的经济困窘是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造成的,在很多宪章派看来,正是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造成英国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局面。[13](P90-178)宪章运动的第一位史学家甘米奇(R.G.Gammage)在1854年写道,在一个经济窘迫的时代,“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起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治之外。”[14](P9)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敌意更多是来自后者参与了英国腐败且不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根据1832年的大改革法令,穷人并未获得多少选举权,因而这种体制更加强化——而不是因为后者作为资本家雇佣者的角色。当然,很多宪章派希望改革后的议会能通过一些改善穷人经济状况的改革法案,如土地和税收改革、取消谷物法等,[15](P113-146)但他们认为,穷人的经济困难根源于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相信政治改革才是通往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布隆泰尔·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对穷人的经济困境十分关切,但他也说:“无赖才会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财产所以你没有代表权。而我的说法相反,因为你没有代表权所以你没有财产……你的贫穷不是你没有代表权的原因。”(30) 奥布莱恩和少数其他宪章派作家,特别是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和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曾试图将宪章派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改革的要求联系起来。(31) 在他们看来,宪章运动既需要政治目标,也需要经济纲领,既应该是民主主义的,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琼斯和哈尼日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希望以土地、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来改善劳苦大众的困境。[16]不过,这些宪章派直到1848年最后一次大宪章请愿失败之后才转向社会主义。
四、结论
到19世纪中叶,为了论证本文探讨的三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很多英国政治哲学家、评论家和活动家显然已经提出了深思熟虑的理论。在为英国人民的三种自由诉求——公民自由、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提供思想和哲学论据方面,他们无疑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种自由都已成为现实。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民已经享有众多的公民自由,并且生活在法治之下。不过,享有选举下院议员的政治自南的只是统治精英和大多数成年中产阶级男子。议会改革的完成几乎还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直到1928年,全体成年男子和妇女才享有议会选举权,选举资格的民主化才告完成。削弱上院的权威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英国仍然拥有一个非选举的第二议院。另外,英国的国家元首依然是世袭的君主,且依然有一个带爵位的贵族阶层,尽管二者的权力自近代以来已经大为削弱。在20世纪,旨在更为公平地分配财产和消除贫困的福利国家形式的经济自由取得了重大进展,当然,它还没有实现任何类似于真正的经济平等的成就,因此实现本文探讨的三种自由的努力仍在继续,它们是尚未完成的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承认,没有哪位作家或斗士曾系统阐述过达致所有这三种自由的方式。即使是在宪章运动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三种自由的协调并未在英国实现,即便在理论上也是如此。的确可以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位思想家或活动家曾全面阐述过同时实现这三种自由的途径。必须承认,这三种自由之间的内在冲突也许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强调消极权利或公民自由之重要性的人,往往反对实现经济自由所必须的财富再分配方案。有些人希望维护个人持有经济力量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力量是他们靠个人努力赢得的,因此他们几乎总是反对那些强调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性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们。当人们享有积极自由或政治自由时,对于个人的公民自由应扩展到何种程度、国家为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的措施该走多远,他们总是存在分歧。人们承认,所有牵涉这三种自由的决定都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即便如此,多数人排除少数人的自由的危险也始终存在。在英国(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个人常常需要这三种相互冲突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他们认为,这三种自由可以一同达到其最完善的境界。政府和立法机构的人士当然认识到满足这些要求的巨大困难,因此他们不得不面对困难的抉择:这三种权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全体人民,它们当中谁应优先考虑——因为三者不可能得到完满的实现。
注释:
① 关于自由观念的更为详细的探讨,见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Oxford,1958)。
② 大法官科克(Coke)爵士宣称:“英格兰古老的优秀法律与生俱来,它是这个王国的臣民拥有的最悠久、最美好的遗产,因为法律不仅让他在和平与安宁中享有自己的遗产和财物,而且让他的生命和最可爱的家园得享安全。”引自克里斯托弗·希尔《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Christopher Hill,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Oxford,1963),第257-258页。平等派理查德·奥维顿(Richard Overton)在《暴君夺命箭》中说:“在财产和自由等方面,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和相似的。”(An Arrow Against All Tyrants,London,1646,第2页)亨利·埃尔顿(Henry Ireton)在1647年11月1日的帕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中宣称:“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尊重安全——我们人身的安全、我们产业的安全、我们自由的安全。”引自霍华德·埃斯金-希尔(Howard Erskine-Hill)和格拉汉姆·斯托雷(Graham Storey)编《英国内战中的革命言论》(Revolutionary Prose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Cambridge,1983),第86页。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都有“保有其财产,即生命、自由和产业”的自然权利,《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第87节。
③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第25-51、124、134、138-140、193、222节;C.B.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所有权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1962),第194-262页;J.W.高夫(J.W.Gough)《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John Locke's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1950),第64-92页。
④ 关于信仰自由的讨论,见W.K.乔丹(W.K.Jordan)《英国宗教宽容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England,4 Volumes,London,1932-1940);G.R.克莱格(G.R.Cragg)《从清教到理性时代》(From Puritanism to the Age of Reason,Cambridge,1966);约翰·普拉门那兹(John Plamenatz)《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2 Volumes,London,1963),第1卷,第二章。
⑤ 参见亨利·帕克《评陛下最近的某些答词》(Observations upon Some of His Majesty's Late Answers and Expresses,London,1642);查尔斯·赫尔《对于菲尔内博士论著的完整答复》(A Fuller Answer to Treatise Written by Dr.Ferne,London,1642)。
⑥ 如可参阅理查德·奥维顿《来自堕落的代议机构的呼吁》(An Appeal from the Degenerate Representative Body,London,1647);约翰·弥尔顿《论国王和官员的职权》(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London,1649)。
⑦ 关于主权和抵抗的整体性探讨,参阅朱利安·H.富兰克林(Julian H.Franklin)《约翰·洛克和主权理论》(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Cambridge,1978);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自然权利诸理论》(Natural Rights Theories,Cambridge,1979),第八章。
⑧ 布莱克斯通声称,人民的权利可以缩减为三个主要方面:“人身安全的权利,个人自由的权利,以及私人财产的权利”。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upon the Laws of England,4卷本,Oxford,1775),第1卷,第29页。埃德蒙·柏克即使在其最保守的阶段也承认所有臣民都享有消极权利:“人享有法治下的生存权:他们享有司法权利;……他们有享受自己产业果实的权利,并有权采取手段使其产业产生收益。他们有权获得其父母的财物,有权抚养他们的后代并改善其生活;他们有权于在生之日接受教育,在死的时候接受吊慰。无论个人自行做出什么行为,只要他不侵犯他人,他就有权按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Harmondsworth,1968),第149页。
⑨ 如可参阅雷英博罗(Rainborough)在帕特尼的演讲,见J.P.肯扬(J.P.Kenyon)主编《斯图亚特宪政》(The Stuart Constitution,Cambridge,1966),第313页;理查德·奥维顿《暴君夺命箭》;约翰·李尔本《伦敦宪章》(The Charters of London,London,1646)、《军队的真实状况》(The Case of the Army Truly Stated,London,1647);劳伦斯·克拉克森(Lawrence Clarkson)《总控诉或叛国罪之检举》(A General Charge or Impeachment of High Treason,London,1647);威廉·西奇威克(William Sedgwick)《关于军队陈情书的第二个见解》(A Second View of the Army Remonstrance,London,1648);等等。
⑩ 对于麦克弗森的有力反驳,可参阅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平等派和选举权》(“The Levellers and the Franchise”),载G.E.埃尔默(G.E.Aylmer)主编《中间期》(The Interregnum,London,1975),第57-58页。
(11) 理查德·艾什克拉夫特(Richard Ashcraft)《革命政治学和洛克“政府论上下篇”》(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rinceton,New Jersey,1986),第521-589页;A.约翰·西蒙斯(A.John Simmons)《洛克的权利理论》(The Lockean Theory of Rights,Princeton,New Jersey,1992),第68-102、336-352页;鲁斯·W.格兰特(Ruth W.Grant)《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John Locke's Liberalism,Chicago,1987),第64-98页。
(12) 阿格农·西德尼《论政府》(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London,1751);詹姆斯·泰雷尔《政治丛书》(Bibliotheca Politica,London,1694),序言部分;约翰·托兰德《民兵改革》(The Militia Reform'd,London,1698),第19页;约翰·特伦查德《论常备军与自由政府不相符》(An Argument shewing that a Standing Army is Inconsistent with a Free Government,London,1697),第4页。另见阿兰·克雷格·休斯顿(Alan Craig Houston)《阿格农·西德尼与英美的共和传统》(Algernon Sidney and the Republican Heritage in England and America,Princeton,New Jersey,1991),第68-98页;朱利亚·鲁道夫(Julia Rudolph)《渐进的革命:詹姆斯·泰雷尔和17世纪末的辉格派政治思想》(Revolution by Degrees:James Tyrrell and Whig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Basingstoke,2002)。
(13) 参阅泰雷尔《政治丛书》,第808页;本杰明·霍德利(Benjamin Hoadly)《论公民政府的本源和创立》(The Original and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Government,London,1710),第150页。
(14) 参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3[rd] edition,2 Volumes,London,1798),第2卷,第114-120页;玛丽·P.马克(Mary P.Mack)《杰里米·边沁:思想的征程,1748-1792年》(Jeremy Bentham:An Odyssey of Ideas 1748-1792,London,1962),第409-466页;菲利普·肖菲尔德(Philip Schofield)《功利和民主:杰里米·边沁的政治思想》(Utility and Democrac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eremy Bentham,Oxford,2006)。
(15) 参见理查德·普赖斯《论公民自由的性质》(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London,1776),第21-22页。另可参阅H.T.迪金森《理查德·普赖斯论理性和革命》(“Richard Price on Reason and Revolution”),载《英国的宗教身份,1660-1832年》(Religious Identities in Britain,1660-1832),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和罗伯特·G.英格拉姆(Robert G.Ingram)编(Aldershot,2005)和H.T.迪金森《18世纪英国的人民代表说》(“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载《代表的实质:近代早期欧洲和欧属美洲的国家建构》(Realities of Representation:State Build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European America),迈贾·扬森(Maija Jansson)编(Basingstoke,2007),第19-44页。
(16) 参见理查德·普赖斯《论回归的代价》(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London,1771),第275页;普赖斯《关于道德中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的评论》(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Morals,London,1769),第345页。
(17) 参见约瑟夫·普利斯特里《论政府的首要原则》,第3-8、127-191页;J.B.伯里(J.B.Bury)《进步的理念》(The Idea of Progress,London,1920),第217-237页。
(18) 可参阅《常识》,1738年4月15日、1739年10月6日和1741年1月10日号;《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7(1747),第329-331页;《雾刊》(Fog's Journal),1734年4月20日号;等等。
(19) 《威斯敏斯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1780年5月27日》(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f Westminster,27 May 1780,London,1780),第3-8页,另刊印于《约翰·杰布著作集》(The Works of John Jebb),约翰·迪斯尼(John Disney)编(London,1787),第3卷,第403-423页。
(20) 《托马斯·斯宾塞政治著作集》(The Political Works of Thomas Spence),H.T.迪金森编(Newcastle upon Tyne,1982),第xiv-xv页;《内阁》(The Cabinet),3卷本(Norwich,1793-1795),第1卷,第178-184页,第2卷,第42-48页。
(21) 重印于《功利主义逻辑和政治学》(Utilitarian Logic and Politics),杰克·李维利(Jack Lively)和约翰·里斯(John Rees)编(Oxford,1978),第53-95页。
(22) 参阅大卫·琼斯(David Jones)《妇女和宪章运动》(“Women and Chartism”),《历史》(History),68(1983),第1-21页,及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宪章派》(The Chartists,London,1984),第12-151页。
(23) 威廉·汤普森《作为人类一半的妇女的抗议书:反对作为另一半的男子使其陷于政治、民事和家庭奴役地位的企图》(Appeal of One-Half of the Human Race,Women,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Men,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and thence Civil and Domestic Slacery,London,1825)。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编辑出版了该著的现代文版(London,1983)。
(24) 关于哲学激进派,见约翰·普拉门那兹《人与社会》,第2卷,第1章;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哲学激进派》(The Philosophical Radicals,Oxford,1979),第3章;埃里·哈莱维(Elie Halévy)《哲学激进主义的发展》(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London,1972),第1部分,第3章;第2部分,第1章和第3章。
(25) 转引自玛丽·P.马克《杰里米·边沁》,第464页。
(26) H.N.布雷尔斯佛德(H.N.Brailsford)《平等派和英国革命》(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1976),第34章:克里斯托弗·希尔编《杰拉德·温斯坦莱:自由法典及其他作品》(Gerrard Winstanley,The Law of Freedom and other Writings,Harmondsworth,England,1973)。
(27) 参见《内阁》第2卷,第215-219页,第3卷,第281-295页;詹姆斯·奥斯瓦尔德(James Oswald)《大不列颠宪政评论》(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London,1783),第59页;威廉·奥吉尔维《论土地所有权》(An Essay on the Right of Property in Land,London,1782),第74、87页。
(28) 查尔斯·霍尔《文明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影响》(The Effects of Civilization on the People in European States,London,1805);罗伯特·欧文《给拉纳克郡的报告》(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London,1821);威廉·汤普森《论财富分配的原则》(An E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London,1824);威廉·汤普森《劳动报酬:劳动的诉求与资本的协调》(Labour Rewarded-The Claims of Labour and Capital Conciliated,London,1827);托马斯·霍奇斯金《保卫劳动反对资本的索取》(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London,1829);约翰·格雷《论人的幸福》(Lecture on Human Happiness,London,1825);约翰·弗朗西斯·布雷《劳动的不幸及补救》(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Leeds,1839)。
(29) 约翰·普拉门那兹《人与社会》,第2卷,第2章;J.R.丁韦迪(J.R.Dinwiddy)《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Early English Socialist”),《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1(1976),256-276页:R.K.潘克赫斯特《威廉·汤普森》;埃里·哈莱维《托马斯·霍奇斯金》(London,1956);H.L.比尔斯(H.L.Beales)《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The Early English Socialists,London,1933);G.D.H.科尔(G.D.H.Cole)《社会主义思想史》(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两卷本(London,1953),第1卷,第3、9-12章。
(30) 转引自阿尔弗雷德·普拉默(Alfred Plummer)《布隆泰尔:布隆泰尔·奥布莱恩的政治传记,1804-1864年》(Bronterre: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Bronterre O'Brien,1804-1864,London,1971),第177-178页。
(31) 《宪章派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Chartist),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编(London,1952);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欧内斯特·琼斯:宪章运动和政治传奇,1819-1869年》(Ernest Jones,Chartism and the Romance of Politics 1819-1869,Oxford,2003);A.R.绍延(A.R.Schoyen)《宪章派的挑战:乔治·朱利安·哈尼肖像》(The Chartist Challenge:A Portrait of George Julian Harney,London,1958)。
标签:法律论文; 选举权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英国议会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