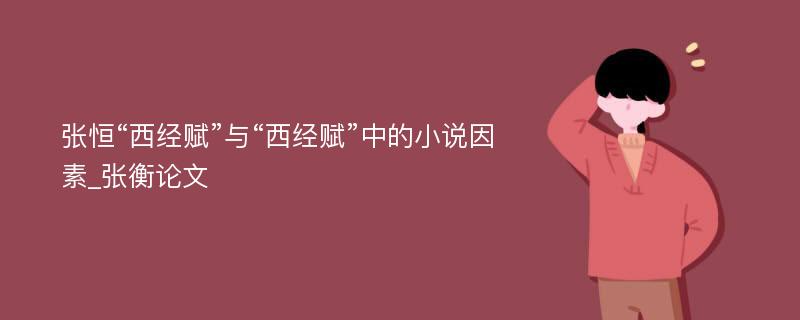
张衡《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京论文,因素论文,小说论文,思玄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赋在汉代非常繁荣,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参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七、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而小说在汉代也十分繁荣,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录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班固生活于东汉前期,其《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是此前的情况,而东汉时代的小说则缺乏充分的文献资料来考察。不过从后来魏晋时期小说的繁荣情况来看,东汉时代的小说也应该相当发达。作为同一时代都非常繁荣的两种文体,赋与小说之间有没有发生联系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东汉中期文学家张衡的赋与小说情节多有暗合之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云:“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盛衰无常,惟爱所丁。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卫后”指汉武帝皇后卫子夫,“飞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卫后兴于鬒发”之事,不见于《汉书·外戚传》,李善注引《汉武故事》曰:“子夫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飞燕宠于体轻”事,李善注引荀悦《汉纪》曰:“赵氏善舞,号日飞燕,上悦之。”并云:“事由体轻而封皇后也。”李善注所引的荀悦《汉纪》并没有讲到“飞燕体轻”的情况,高步瀛先生《文选李注义疏》则引《西京杂记》卷二云:“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赵飞燕外传》(《汉魏丛书》本):“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
此外,在《西京赋》中出现的“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等描写,李善注也引用了《西京杂记》卷三中“东海黄公”的故事来解释。而“云雾杳冥”、“画地成川”等描写与《汉武故事》中“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汉武故事》)的记载也有相通之处。以上这些线索表明,在张衡生活的时代,关于汉武帝、成帝的一些传闻、故事相当流行。
张衡赋与小说暗合的情形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云:“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李善注引《汉武故事》曰:
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尨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颜驷白首为郎、“三世不遇”的故事与《思玄赋》的赋文“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完全吻合,很能说明张衡要表达的“吉凶相仍,反仄靡所”的观点。张衡称颜驷为“尉”,大概是因为后来他被拜为会稽都尉的缘故。而李善注所引的故事中“驷尨眉皓发”一句与赋文“尉尨眉”也是相对应的。《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章怀太子李贤注也同样引用了《汉武故事》,字句略有不同:
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问:“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叶不遇也。”上感其言,擢为会稽都尉。
两则故事的情节基本相同,唯一较大的差异是前一则云“景帝好美而臣貌丑”,后一则云“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但不管是哪种原因都可以导致颜驷不遇于景帝。
关于《汉武故事》的成书时代,历来意见不一,有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建安末年、齐梁时期等不同的看法。《汉武故事》在写定之前,其中的一些故事可能长期在口头流传着,甚或已有成文的形式。卫子夫与颜驷的故事,张衡肯定是知道的,《二京赋》、《思玄赋》与《汉武故事》暗合的情形不难理解。据《汉书·艺文志》,可以确定为武帝时代的“小说”有三种:《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另外还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也可能属于武帝时代。这几种小说的内容,或与武帝时代封禅、养生、求仙之事有关,或是附会周代历史故事。前面所讲到的卫子夫与颜驷之事均难与之相合,它们应该都是东汉以来新兴的“小说”,一直流传于民间。
《思玄赋》又云:“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旧注云:
车,人名也。孕,怀子也。昔有周犨者,家甚贫,夫妇夜田。天帝见而矜之,问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当贫,有张车子财可以假之。”乃借而与之期曰:“车子生,急还之。”田者稍富,致赀巨万。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妇辇其贿以逃,与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车下宿,夜生子,问名于夫,夫曰:“生车间,名车子也。”从是所向失利,遂便贫困。
结合李善注和李贤注来看,可以知道张衡这两句赋的意思是说:“周犨夫妇为了避开张车子,卷起财物放在车上,东躲西藏,可最终还是在一个旅店里遇到了车子的降生,这成为他们由富到贫的转折点。李善注和李贤注所引故事的前半部分都明确指出车子姓张,这是《思玄赋》没有提到的信息。但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却没有交代张车子为何姓张,让人感觉意犹未惬。《搜神记》卷十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周擥啧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赀至千万。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妪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这则故事与李善注所引故事有三处大的不同:一、周姓男子名字作“周犨啧”而不是“周擥”,这一点无关宏旨,姑置不论。二、《搜神记》多出一个情节:“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这样就交待了张车子姓氏的由来——原来是张妪未婚先孕,故车子跟随母姓。在情节上前后有个照应,这是比李善注和李贤注所引故事较为精致的地方。三、《搜神记》里的故事虽然字数比李善注和李贤注增多了,但是却没有周家夫妇为躲避坏运气,“辇贿而违车”的情节,与《思玄赋》不甚相合。这三处不同说明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版本,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产生差异——一些情节可能被强调,一些段落或许被忽略,而故事人物的名字也会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篇极具戏剧性的微型小说在张衡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小说和辞赋的这种关系,在后代也仍然存在。西晋潘岳(247—300)的《西征赋》也有两处用到了《汉武故事》(参清纪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汉武故事》”条),赋云:“卫鬒发以光鉴,赵轻体之纤丽。”分别与《汉武故事》中“卫子夫事”以及《西京杂记》、《赵飞燕外传》关于赵飞燕的记载相合,这或许是受了《西京赋》“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两句的影响。赋又云:“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长傲宾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畴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缪官!”这是用《汉武故事》中的“柏谷亭事”。但相对来说,张衡辞赋作品中出现的小说因素时代较早,从而更值得我们重视。
一些叙事类赋如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扬雄的《逐贫赋》与张衡的《骷髅赋》运用虚构和拟人化手法,或虚拟客主、或虚构情节,具有一定的小说意味。这是辞赋叙事功能与小说文体功能的重合之处。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汉赋似小说”条注意到杜笃《首阳山赋》中伯夷、叔齐之鬼语,认为“玩索是篇,可想象汉人小说之仿佛焉”(钱锺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第三册,第994页)。本文讨论的是另外一种情形——辞赋与小说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表现。这也许不是简单的谁抄了谁或谁用了谁的问题,而只是他们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记载而已。
那么,《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从何而来?是来自口头传说,还是书面文学?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两篇赋创作的环境与时代。据《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二京赋》为张衡早年作品,可能在他青年时代游历三辅地区时就已经酝酿,而后“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因为三辅地区是长安旧都所在,张衡在创作之前,大概搜集了较多的长安史、地方面的资料作为素材,而小说可能也包含在内,这样,《西京赋》中的小说因素或许有地域文化影响的背景。但是这样的解释却不适用于《思玄赋》。《思玄赋》是张衡晚年担任侍中时的作品,当时张衡身在洛阳,而赋中“颜驷”一则是西京旧事,“张车子”一则却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张衡直接用这些故事入赋来看,在东汉中期,这些故事很可能已经有成文的形式了。
小说与古书里的典故在东汉中期同时进入辞赋的现象很值得玩味,它反映了民间文化因素对文人创作的渗透。关于两汉时代民间文学的发展情况,过去苦于资料奇缺,只能作一些推测。如荣肇祖先生《敦煌本〈韩朋赋〉考》云:“或者在汉魏间,贵族盛行以赋作为文学的玩意儿,民间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载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80 页)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则给我们提供了出土资料的佐证,扬之水先生说:“可否设想,骚赋、文赋、徘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行于世,且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由《神乌赋》而发现并证实了这古远的渊源。”(扬之水《〈神乌赋〉谫论》,见《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秋季号,第84页)这是民间俗赋对文人赋的影响。张衡赋中的小说因素也是民间文学对文人创作影响的一个例子。《思玄赋》所用的两则小说,“颜驷”一则与汉武帝(前156—前87)所代表的上层社会还有一定联系,同时反映了士人对于人生命运穷达、困济的思考。而“张车子”一则中的有关人物都是极为普通的民众,其故事反映的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这是民间心理和群众思想在文学中的折射。张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宛洛地区,作为帝都与帝乡,都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各种文学与艺术的形式都非常繁荣。小说本身就有世俗化和平民性的特点,它可以作为上层的娱乐与喜好,如西汉时代的“秘书小说”(《文选》卷二《西京赋》)之类,但更多的是迎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张衡作为一个上层的知识分子,以小说故事入赋,说明他在思想深处并不排斥小说——小说同样可以帮助阐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同时,这也表明东汉中期以来,官方的思想控制在逐渐削弱。《西京赋》讲到“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对西汉皇室颇有不敬之意。而赋中的另一段描写似乎更显得大胆与出轨:“阴戒期门,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怀玺藏绂。便旋闾阎,周观郊遂。若神龙之变化,章后皇之为贵。然后历掖庭,适欢馆。捐衰色,从嬿婉。”《汉书》卷十《成帝纪》“鸿嘉元年”“上始为微行出”句三国魏张晏注云:“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也有相关的记载:“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组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相对于史书记载来说,张衡明显表达了对汉成帝怠于朝政、好为冶游之事的批评态度。张衡《西京赋》所流露出的对武帝的“不敬”与对成帝的批评,在东汉前期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稍不留意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孔僖传》载:鲁国孔僖、涿郡崔駰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駰、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駰诣吏受讯。而孔僖则上书自讼,对章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免除了言语不慎带来的无妄之灾。《资治通鉴》卷四十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张衡《西京赋》的写作与章帝元和元年相差不过二十余年。政治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作家也少了许多忌讳,在文学作品里可以稍微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描写。
标签:张衡论文; 小说论文; 西京赋论文; 思玄赋论文; 文学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搜神记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西京杂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