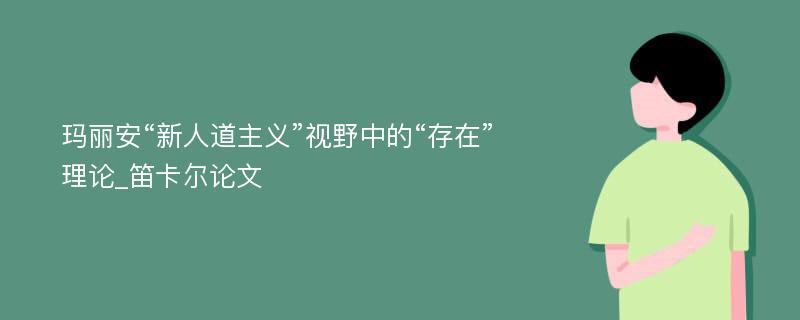
马里坦“新人道主义”视域中的“存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里论文,视域论文,人道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5-0104-06
一
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的思想立基于对现代西方世界高度“物化”、“理性化”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anthropocentric humanism)的揭示与批判。他认为,必须借助于“新人道主义”来恢复“人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追寻人早已丧失了的对“存在”的把握。在马里坦看来,“每个伟大的文明时期都受支配于一种特定的观念,即人何以塑造自己的形象。我们的行为有赖于这种关于人的形象,犹如依赖于我们的本性,这种形象……形成作为某个特定文化时代之特征的社会与政治结构。”①中世纪基督教围绕着“人是上帝的形象”(image of God)的两种解释(分别来自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刷下已是支离破碎,被分解为“彻底的基督教悲观主义”和“彻底的基督教乐观主义”:前者表现为对人之本性的彻底绝望,后者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类的努力而非“神恩”(Grace)。基督教所信仰的人之形象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世俗化(secularized)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丢失了“人的形象”。
在对现代精神的考察与批判中,马里坦将焦点集中于“铸造现代精神”、否弃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三个人的“乖谬”学说——他们的理论代表了现代文化的人类中心论辩证法。他认为,这“三个人,出于很不同的原因,支配着现代世界,且控制着折磨它的所有问题:一位宗教改革者、一位哲学改革者,以及一位道德的改革者——路德、笛卡尔和卢梭。”②精神引领时代,“任何事物都开始于精神,现代历史所有的重大事件,均成形于少数几个人的心灵深处、在无体积无质量的生命即亚里士多德所谓努斯(nous)中。路德与魔鬼辩论的那间隐修小室、陪伴笛卡尔做着他那著名的梦的火炉、卢梭在发现自然人之善时弄湿背心的范塞纳(Vincennes)森林的一角——这些就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③
由于马里坦将宗教改革视为导致现代世界罹患固疾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对路德的批判也免不了对新教教会基本神学命题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同时也是出于对天主教思想原则的维护。不过,他的批判重心最终还是凝聚于路德其人而非路德宗(Lutheran)或各新教教派(Protestants)。亦即说马里坦的思想重心是精神探源而非教派之争。④马里坦认为,路德“缺乏的乃是理智的力量”,⑤在马里坦看来,路德在经院哲学上学艺不精,只学会了一包错误的想法与模糊的神学概念,以及华而不实的论辩技巧。⑥无论是路德对当时天主教的苦修补赎之路,还是对其自身内在的精神状态都充满着怀疑,从根本上看,路德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恩典的绝望。⑦在路德看来,人的本性根本就是堕落的,任何发自这样本性的行为必定对人的得救没有帮助。由于路德不能克服自身的罪恶感和欲望,便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与其本性全然割裂的恩典的作用上;然后,又从一已之体验中推而广之,将自己的命运转化为神学的真理——只要你内心确定了你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确信你一定能获救,那么,你的意志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规定者,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上帝只是一个盟军、一个合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伙伴而已。其结果必然是自我神化(deification of self)。因此,马里坦认为,路德力图使信仰摆脱理性,把基督教福音归结为内心的体验,这种努力大大激发了现代反理性主义的个人主观主义。
而笛卡尔被视为“理性主义之父”。马里坦发现了笛卡尔思想的三个重要特征:在思想与存在的联系层面的唯心论(idealism)、在理智的等级秩序与知识的意义层面的唯理论(rationalism)以及在人观上的二元论(dualism)。⑧其核心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科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思维”。对笛卡尔来说,“我”就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理智、一个理性。我思(cogito)与我在(sum)是同一的。而“直观(intuitus)”、“天赋观念(idées innées)”、“独立于事物”恰恰是笛卡尔所理解的人类知识的特征。在笛卡尔那里,只有一种确定性的思维类型,只有一种科学的典范(普遍的科学Mathesis),任何不能被纳入其中的都会被拒斥。于是,人文学科、古代文化、希腊拉丁的伟大成就、人类的历史传统等都不值一提。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得以形成,取代以往的“人文主义时期”的是一个充满霸气的“自然科学时期”。马里坦认为这便是现代科学深刻的非人格的原则与源头。
就笛卡尔哲学的整体来看,人的认识不是从外部事物中获得最初的养料并接受外部事物的制约,而是相反,外部事物的存在恰恰是(在一个所谓上帝的概念的辅助下)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类的理智由此变成了事物的立法者。马里坦发现笛卡尔主义企图逃离往昔人类积累起来的智慧,企图使思想独立于现存的事物,而仅仅受制于“它自身内部的需要……。一个世界仅仅凭着自身,就关闭了绝对……”⑨马里坦认为,这是一种欲使人类理性的内容成为度量实在的尺度的极端企图与疯狂做法。因为,在马里坦看来,除了从外部对象获得的东西之外,人类理性是毫无内容的。而笛卡尔则认为,人类认识是与感性知觉分离的,人类认识被视为与天使的认识一般的认识,是直觉的和固有的。马里坦指出,这种“天使主义”罪过不仅割裂了理性与感觉,而且割裂了身体与思维、割裂了信仰与科学。因此,笛卡尔是现代病之根,要矫正现代的错误,首先必须摒弃笛卡尔的二元论。
卢梭则代表着人类中心的人道主义辩证发展的第三个关节点。在“范塞纳森林”的一角,卢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本善”的人性。⑩他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有罪,相反,人的原初状态(原始状态)即是善的;亦即说存在一个人性的理想状态,它处在人类历史的源头。(11)在此阶段,人处于一个完满的境地。卢梭眼里的人即从圣保罗所讲的人转变成了一种纯自然意义上的、生来就有美德的自足之人。
正如笛卡尔把理性转向了内部,卢梭也依靠心灵的内部情感来衡量意志与善。正如路德错误地宣布人性已无可救药地腐化(即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卢梭也错误地宣称人性是善的,根本无需任何救赎(即“基督教乐观主义”)。三位“改革家”所肇始的哲学革命终于在康德批判的唯心主义思想那里达到了顶峰。马里坦认为,这场革命并非是一个纯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将某些原本神圣的东西加以世俗化的过程,它将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人拉回到人自身的领域,在保留基督教外表的同时,以人的理性或善良取代了神恩,期望从人的本性那里得到上帝所能给予的东西。这场革命终于扯掉了形而上学的神圣帷幕,将时代转向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马里坦认为,从本质上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泛滥过程的必然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渐物质化与实证化。物质的丰富和技术的进步不但没有给现代人带来幸福与安慰,反而使人陷入心灵的孤寂与苦闷之中。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充分展示了人类的罪恶。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各种冲突和毁灭性的威胁。
马里坦以考察人的处境为出发点,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即“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为其历史理想。在他看来,人要求享受被爱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只能从上帝身上得到。马里坦认为,“新的人道主义”是对人的真实形象的重新发现,这种人道主义在考虑人时着眼于“人的崇高与弱点的方方面面,上帝栖居其问的、已遭伤害的人类存在的整体性,以及本性、罪恶和圣洁的完全实在性。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将认识到所有这些在人那里都是非理性的,以使其顺服于理性,使理性因超理性而充满生气,并使人开放,让神降临自身。它的主要成果将促发福音的酵母与灵感渗入世俗生活的结构,使现世的秩序神圣化。”(12)因此,马里坦认为,这种“新人道主义”是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
马里坦虽然认为,若无上帝的恩典,社会的复兴就只是一场空想,他却并不期待、希望返回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概念中去。因为,历史在变,文化也在变。“新人道主义”的前提条件正是新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以人的终极目标为基础的推动之力,这个终极目标,就是直观上帝,把握上帝。不然,“文明的发展就会失掉精神的动力、人类的压力和创造的光芒之补充,而这些东西可以激励它去取得尘世的成就……历史有一种意义,有一种方面……人类的政治和社会事业应当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创立一个博爱的国度,这不是意味着希望有朝一日一切人都将得到尘世的完善,彼此相爱如同手足,而是意味着希望人类生活的生存状态和文明结构都更接近完善,完善的标准是正义与友爱……一种真正民主的正义与友爱。”(13)
马里坦主张将人的神圣性、崇高性指向人生活的世俗结构,以使世俗生活秩序圣洁化。从这种“新人道主义”之视域中,我们所发现的是一种对于生存在现代科技“物化”环境中的现代人存在的超越性、神圣性等意义的思考。
二
“存在”意义,是马里坦“新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马里坦直觉到,在现代科技左右着的人类文明的境遇中,当代文化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能否从根本上认识“存在”,即不仅靠科学达到“现象上的”认识,而且通过哲学来达到“本体论意义上的”认识。马里坦认为这个难题对一般人来说要比科学家更需要解决。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理性只限于对“事实”、“数字”的认识,而丧失了对“存在”的把握,人因此失去了“存在”之根。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哲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科学提供给人的是一幅幅“代码图”(coded maps),表明处于可观察、可计算的相互作用中的自然与物质何为。哲学则使人从内在实在性上来把握事物是什么。哲学既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也是以理智之感觉能力为基础,即是说哲学的基本对象是“存在”。马里坦认为,一方面,人们可以透过“自然哲学”探讨经验范围内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并不只限于感官经验领域。理性的基本概念虽然首先用于经验范围,但也能借助于“类比”(analogy)用于超验的“存在”,于是就构成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所达及的是非感官经验或者非感官证实的“存在”。
因此,哲学在“理性之自然运用”上达到的是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此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层次不仅是知识而且是智慧。正是通过哲学反思,才使人的理性变得成熟、完善,而理性也在进行准确的论证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有效性。马里坦认为,正是由于人类理性具有这样的本质,人才能够借助于“原因”概念和“因果”原则超出经验范围,形成两种关于“上帝存在”或“存在的存在”的知识,即“前哲学的”和“哲学的”。就“上帝存在”或“存在的存在”而言,所谓“前哲学的知识”就是对“存在”、对“自在”、“自有存有”的纯自然的知识的直接领悟。其逻辑前提就是:有制造物必有制造者。而关于“上帝存在”或“存在的存在”的“哲学的”理解,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智慧。这种智慧依照理性的严密性展开自我论证。马里坦认为,这类论证的经典形式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的五条论证”。
在马里坦看来,“原因”的概念在阿奎那的经典论证里有其充分的本体论涵义,意指“存在”的派生性,由此推知“初始因”(Prime Cause)。“初始因”亦即绝对、无限的超越者,而“原因”和“存在”、“善”等概念一样,只有借助于“类比”才能获得——这些概念指的是上帝类似于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但上帝与事物又有本质的不同。对上帝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助于“类比”,这似乎是在说“上帝存在,因为共他存在者不存在;上帝是善的,因为其他存在者不是善的;上帝在认识、在付出爱,因为其他存在者做不到。”(14)
马里坦认为,正是由于托马斯·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个论证具有上述主旨,因而才具有真理价值。他深信,认识上帝的途径不止阿奎那提出的五种。他认为,现代科学本身提供的另一种认识上帝的途径或许更有特殊意义——他提出了证明上帝的“第六条途径”。马里坦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即关于现象的科学,虽然局限于经验领域,却能在以下双重意义上证明上帝的存在:假如自然是不可理解的,便无科学可言;假如第一理解力是不存在的,便无人类理知可言。
“存在”的意义是马里坦建构其“新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基本思想源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中的“存在论”及其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马里坦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探究,无非是想证明两个相辅相承的问题:一方面,强调上帝“存在”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揭示“作为上帝之形象”的人原本是作为“类比的存在者”而赋有超越性与神圣性,却因为人自己切断了与“存在”相联的纽带而拒绝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性,从而成了“无根的存在”。
马里坦的“存在”论即是他的“生存论”。在马里坦看来,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生存的生存主义(existential existentialism)。它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冲动和要求,是一种信仰之苦痛,是主体性向着它的上帝发出的哭号。这种生存主义的不幸在于:它在一种哲学外衣之下,发展成了一种宗教性的抗议。“生存者内部的虚无,被生存者本身的虚无取代了。”(15)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则是从“无”的痛苦经验中执着于“有”的神秘。马里坦认为,如此学院式的生存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哲学的智慧态度与宗教的祈求态度,如果将之作为一种真正关于存在(因而是关于生存)的哲学,是失败的。
因此,现代生存主义的根本难题在于其缺乏一种对于“存在”的真正的思想上的直观。马里坦认为,对于存在、对于生存着的对象的真正直观,把本质(潜能)同生存(行动)区别开来是必须的。在思想中,一个事物的本质可以客观化,而主体却是不能客观化的。每一个主体都是一个个体的实在,都是可认知性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人对主体的认识是通过将其作为人思维的客体而得,因此,我们不是把主体作为主体来认识,而是把它们作为客体来认知。人常把自身视为一切认识客体当中的主体,自视为处于世界的中心,这样一种对“作为主观性的主体性”的直观的立场是愚蠢的,它必然导致个人生存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律背反:“如果我执著于主观性的观点,我就把万物吸收到自身里面,让一切都为我的独一无二性而牺牲,我就被钉死在绝对的自私和狂妄之上了。如果我执着于客观性的观点,我就被吸收到万物里面……而我的独一无二也就是虚假的了。……这个二律背反,只能从上天得到解决。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不是我,而是他,才是中心;这一次,这个中心不是同某一特定的观察点(例如在某个观察点上看来,每个被造的主体性者是其所知宇宙的中心的那么一个观察点)相关联,而可以绝对地说,是一个超越的主体性,一切主体性都要以之作为参照。在这个时候,我才既懂得我毫无重要性,又懂得我的命运具有最高的重要性。”(16)
“自我中心”与“整体宇宙中心”常常交织而成就一个人的两重形象,作为主体的形象和作为客体的形象,既不可能协调重合,又不可能被抛弃掉。马里坦认为,只有上帝“存在”,这个矛盾才能解决。因此,无神论生存主义的悲剧部分地是在于:被他人作为一个客体来认识,永远是被不公正地认识——被与自身割裂并受到伤害。可是,被上帝所认识,是作为主体被认识。在马里坦看来,上帝要认识我,根本无需将我客体化。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是作为主体、而非客体被认识。只有对于上帝,自我才完全敞开。按照马里坦,“新人道主义”视域中的真正的生存主义,不是把自我视为无理性的感觉之流、“无用的激情”,(17)而是把自我视为有理性的灵魂——它在自我最幽深的隐秘之处,在它最充分的实现之中,为上帝所了解,在它本质的性质方面,又为人的理智所认识。
三
马里坦在神学上最大的贡献是运用“适应现代思想的需要和状况的原则”,激活700多年前的传统托马斯主义思想、构建新托马斯主义的理论,他以深刻批判现实、批判“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18)为前提,建构起以神为中心,使神道与人道互补而非互相排斥的“新人道主义”,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产生了极大影响,超越了基督教各教派宗派的圈子,最终被普遍接受。
马里坦将神圣的恩典视为崇高的同时,充分肯定人自身的价值,这是其“新人道主义”作为“完整的人道主义”或“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信仰上帝的目的在于建立慰藉人生的理智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使人类能够平安地拥有地球,征服自然。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挣脱“上帝”牵绊的生存状况中渴求恢复“人”的地位,世俗化的过程正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成长的过程,它逐渐将现代人对上帝的宗教情感转变成为对人的信仰、对物的崇拜。然而,历史的流变和残酷的现实又使人失去了这种信仰和崇拜。马里坦认为,人始终是“类比”上帝的“存在”,对人的信仰如果建立在超验的信仰之上,就会达到完满和永恒,亦即说,对人的信仰是要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这是实现其“新人道主义”的前提条件。
作为“回归基督教”过程中新托马斯主义“与现实对话”、“批判现实世界”运动的重要代表,马里坦主张二元的统一,即世俗的和精神的统一,主张人的生存“解放”,这是其“新人道主义”理论对现代人之“存在”最有价值的启示。然而,这种“统一”又何尝不是一种“悖论”式的呢?正如他自己所发现的,引导基督徒去实行基督的救赎工作的推动力,深藏于对世界的一种悖论式的理解之中:一方面,基督徒相信自然界是上帝创造并宣布为善的。(19)另一方面,就世界“自身陷于肉体贪欲、感官贪婪和精神傲慢而言,它又是基督及其门徒的敌手,并仇恨基督及其门徒”。(20)因此,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基督徒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来说,基督徒将永远是陌生人,永远是不可理解的人。这种悖论的张力所引发的后果是显著的。一方面,马里坦对于年轻一代的教士和神学家的世俗性与乐观主义不无抱怨、抨击,从而将与自己同代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同“梵二”会议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年轻神学家如汉斯·昆、爱德华·施勒贝克斯和约翰尼斯·梅茨等人分隔开来;另一方面,这些被抨击为“曲膝屈从于世界”的神学家们则又开启了以“普世性”、“世界性”和“全球性”为主旨、以“对话”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的“后现代神学”,展开了对现代世界新的批判与重构,就此意义而言,马里坦对于现代条件下西方神学的继往开来起到了先锋作用。
注释:
①Jacques Madtain:The Range of Reas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2,p.185.
②③Jacques Maritain:Three Reformers,New York,Cbarles Scribner's Sons,1955,p.4.p.14.
④马里坦承认当代路德宗有严格的清教主义倾向,而与路德其人的道德状况十分不同。Jacques Maritain:Three Reformers,New York,Chades Scribner's Sons,1955,p.185.
⑤⑥Jacques Maritain:Three Reformer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s Sons,1955,pp.4-5,pp5-6.
⑦舍勒(Max Scheler)在把握资本主义的现代人的精神脉络时认为“现代人的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恰是产生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渴望的根源和发端”。而“资本主义‘精神’在宗教改革者及其追随者背后已然作为原本的动力在推动所有宗教革新”。见舍勒:《资本主义精神三论》,罗悌伦译,载《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页。
⑧⑨Jacqaes Marhain:The Dream of Descartes,English translation by M.L.Andison,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Inc.,1944,pp.168-169.p.171.
⑩这次经历参见于卢梭著、范希衡译:《忏悔录》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3-434页。
(11)卢梭著、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3-64页。
(12)(13)Jacques Maritain:The Range of Reas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s Sons,1952,p.194.p.198.
(14)Jacques Maritain:On the Use of Philosopb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63-64.
(15)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
(16)J·马里坦:《生存与生存者》,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1页。
(17)萨特的自我描述。
(18)包括批判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限于篇幅,此问题另撰专文论述。
(19)见《旧约圣经·创世记》。
(20)J·马里坦:《加农尼的农夫》,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