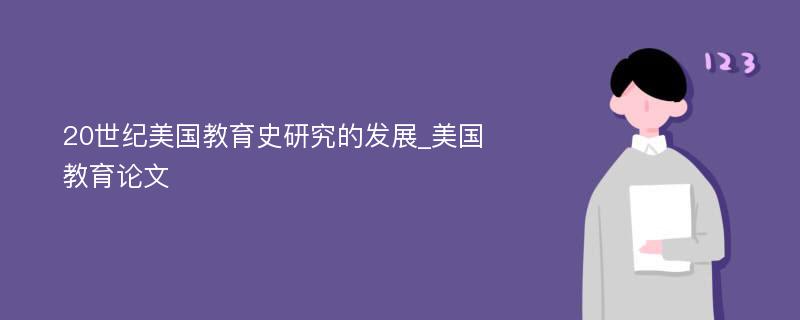
20世纪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史研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可以说是较短的,对美国这个历史不长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一般认为,美国研究教育史最早的、最杰出的先驱人物是19世纪的亨利·巴纳德。巴纳德是美国“公共教育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多年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有许多教育方面的著述。他在教育史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在《美国教育杂志》上所做的工作。从该杂志1855年创刊起,巴纳德连续担任主编达26年之久。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教育杂志》不仅刊登了许多教育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而且还重刊了一些著名的前辈教育家的著述,被称为“教育文献的大百科全书”(注:Barnard,H.C.(1970),The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in R.J.W.Selleck(ed)Melbourne Studies in Education.In P.Gordon and R.Zeter(ed),History of Education: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London:Woburn,1989,p.111.)。由巴纳德开创的美国教育史研究传统稳步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教育史开始成为美国教师培训计划内容的一部分,教育史在大学教育学科的各组成部分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凭借自己的实力确立了其学术性学科的地位。但是,教育史研究的真正发展则是在20世纪。
一、繁荣期(20世纪初)
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史研究遵循亨利·巴纳德开创的传统,主要进行教育机构史研究,关注遥远的过去甚于现在,重视研究英国教育的历史,并在历史叙述中竭力赞美教师和教学。这一时期,美国的师范学院、师范学校和教育系都广泛开设了教育史课程,教育史的研究很受重视。不过,当时教育史专业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从外部看,其它专业的学术同行对教育学的专业性表示怀疑,而教育学领域内的其它专业人员也对教育史在教师专业计划中的价值提出质疑。从内部看,由于教育史学科的过早专业化,教职人员、教材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当时教育史课程的教师都是其它专业的教师兼任的,也没有合适的教育史教材,仅有的两本书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罗列事实,大部分篇幅都是有关教育机构、教育法规和管理准则的。当时的普通教育史课程一般就是讲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教育发展状况,即使是高级课程也只是强调英国教育的发展。鉴于美国教育史方面资料匮乏的情况,斯坦福大学的屈伯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保罗·孟禄都开始着手建设美国教育史学。
随着屈伯利和孟禄开始建设美国教育史学,美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约出现在1910年左右。此时,虽然教育史的教材还不是很完备,但有许多人致力于学习和教授这些教材;教师的教学富有趣味和灵感,并善于启发灵感;学习教育史的学生数量很多,他们彬彬有礼,渴望学习;教师是各个不同学科的教授,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史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们很有信心地进行着一些研究;尊重过去的传统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当时认为,未来的教师所需要的教育史知识应是实践性强的,这种教育史需要密切关注“影响19世纪的那些政治力量和工业力量”,使未来的教师能够“通过历史演变而看到20世纪的问题。”(注:Ellwood P.Cubberley,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Boston:Hounghton Mifflin,1919,pp.Vii-x.)基于这样的考虑,教育史研究重点由欧洲转向了美国,从智力史转向了社会史,从教育理论史转向了教育机构史。体现这种转变的有屈伯利的《美国公共教育》一书、孟禄负责编撰的《教育百科全书》和孟禄的《教育史课本》等。屈伯利和孟禄成为美国教育史学的奠基人物,他们的著作成为教育史学的权威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禄培养了许多博士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第二代美国教育史学者中的杰出人物。
像许多其它黄金时期一样,美国教育史研究的这一黄金时期也是在大家还未觉察的时候就过去了。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起,很多人都对教育史的价值和地位提出质疑,教育史编纂开始受到一些新因素的影响,并形成了内容和方法论之间新的相互作用模式。
二、徘徊期(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
即使是在教育史领域的繁荣时期,也存在着对教育史的一些批评。当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认为教育史学科缺乏实用性、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等。一战后,对教育史的批评增多,教育史学科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虽然教育史仍然是教师专业学校和大学教育系中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人们对它的尊重程度下降,并且那些学习了教育史课程的教师们大多反映教育史的实际价值不大。人们对教育史的非实践性的批评加剧,对它的价值表示怀疑。
除了教育史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一因素之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也影响了教育史的研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发生,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彻底失败,需要进行“社会重建”。还有一些人则深受进步主义哲学的影响,要对历史学进行改革。这样,这一时期对教育史领域直接产生影响的就是教育领域的社会重建运动和历史领域的进步主义历史学运动。社会重建者认为必须重建新的社会秩序,这就要求教育也必须重建,学校要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此一来,教育的这一重要使命就使得教育学教授和“教师的教师”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教育者们就得放弃“正式的传统”,而认识到应该优先考虑“社会目的”。这时的进步主义历史学者致力于建立一种“有用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须直接有助于解决当代的问题。这些历史学者通过在叙述中选择和强调过去那些与现实的问题关系最为紧密的问题而力求古为今用。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开始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教育史的研究,推动教育史少些学术性,多些功用性。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教育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它成为了教育社会学基础的一部分。
教育学的社会学基础的概念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重建主义者提出来的。这个观点认为,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比较教育学是教育的社会学基础,但这些学科需要“整合”成一门学科。这一时期著名的教育史学者有赖斯纳、巴茨、康茨、拉格、埃格特森、安德森等。他们在以下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教育理论应该更宽泛、更综合,教育史要研究当前社会中的问题,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的。这样,从20年代到50年代,一方面教育史的领域趋于变窄,并专注于机构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趋向于更广泛地与其他领域发生联系。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教育史著作正在逐渐努力填补一些空白。无法避免的是,这样做又常常会带来史实的罗列,而不是深刻的阐释和分类。作为教育社会学基础的教育史,一方面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丧失了其学术性。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在撰写学校制度及其组成部分的管理史,越来越多的百年庆祝或周年庆祝活动产生了许多机构史的著作。当然,历史叙述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扩展,教育制度史涵盖了成人教育、教师培训和教师组织、大学、工业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内容。
1948年“全国大学教育学教师协会”(NSCTE)成立了“教育史处”(HES)。《教育史杂志》(HEJ)完全由NSCTE资助出版。教育史学者巴茨任HES委员会的主席,兼HEJ编委会主席。巴茨等人都认为教育是社会重建的工具,教育史必须以问题定位,必须在教育的社会学基础中发挥作用,还必须是学术性的。从实际情况来看,HEJ对于教育史应为学术研究做些什么强调得少,对于教育史在教师职业训练计划中也许能发挥的即时功效强调得多。
三、复兴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末期,进步主义教育已经衰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解散,NSCTE也奄奄一息,HEJ更是士气低落。社会学基础中的教育史丧失了独立性,面临着更多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的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开始强调,在美国社会史中要更广泛地理解教育的需要。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的“修正主义”,“新”历史登上舞台,教育史也通过加强与其母学科——历史学之间的联系而得到复兴。
美国历史学修正主义要求对传统上已经被接受的问题进行再研究。他们指出20世纪中期的历史作品的缺陷,批评这些作品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正规教育机构的教育过程这一部分”。修正主义者认为,教育过程的定义应该更宽泛、更符合人类学。这时,美国国内的平等权利运动、城市骚乱和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内深层次的紧张状况,都促使对教育进行修正。
1960年,哈佛大学历史学者贝林的《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一书出版,被看作是新历史的宣言。贝林发现:“美国历史上教育的作用是模糊的。在解决美国教育问题时,我们几乎不使用历史手段。”(注:Sol Cohen,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1900-1976:The Uses of the Past,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46 No.3 August 1976,P.300.)他批评早期教育史的权威人物屈伯利和孟禄等人不把教育史这门学科看作是美国社会史或智力史的一个方面,而是把它当作美化和激励一个新专业的手段。他们把自己的阐述限定在正规学校教育机构的范围之内,因而失去了在教育的整体背景下看待教育的能力。为了纠正这种短视的观点,贝林主张历史学者应该把教育看作“不仅是正规的教学,而且是人们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整个过程”(注:Sol Cohen,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1900-1976:The Uses of the Past,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46 No.3 August 1976,P.301.)。与此相呼应,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克雷明于1965年出版了《爱德华·帕特森·屈伯利的精彩世界》一书,对美国教育的“旧”历史编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克雷明又一次提及屈伯利的落伍、偏狭、狂热及与美国历史编纂主流相背离的过失,呼唤新的美国教育史,而这种新教育史必定是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相联系的。
新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新教育史学者尽管给教育下了不同的定义,但他们在教育的概念应该更宽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贝林认为,教育是“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整个过程”。克雷明则把教育定义为“有目的性的、体系化的和有连续性的传递、唤起或获得知识、价值、态度、技能和情感的努力,以及由这种努力所产生的任何形式的学习,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N.Ray Hiner,"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1990's and Beyond:The Case fo Academic Imperialism",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Vol.30,No.2,summer1990.pp.146-7.)。这样,教育的概念就不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了,家庭教育、黑人教育、妇女教育等都成为了教育史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了。另外,由于贝林这样一个著名哈佛历史学者确认教育是一个历史调查领域,这一点让教育史学者振奋!当教育史开始吸引大学历史系里的历史学者的时候,教育学者就有机会重获缜密的历史学术准则。教育史与历史的结盟,意味着它从社会学基础课程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
新教育史学者在恢复教育史的可信性时,采取的策略是修复教育史与它的母学科——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保持着与专业教育领域的关系。1960年,老的HES解散,新的教育史协会成立。次年HEJ也停刊了,取而代之的是《教育史季刊》。新杂志认为,“教育史应该努力发展其基础,并与社会史、文化史和智力史领域相联系;教育史还应减少其偏狭、有时甚至是狭隘的侧重点。”(注:Ryland Cray,"Editorial Commentary",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1961),1-2.)196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成立了六处,即教育史处,教育史的研究获得了新的阵地。
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史或智力史领域像教育史这样发展得如此迅速。《教育史季刊》吸引了许多国内外优秀学者的作品,参加HES、AERA六处和美国历史协会教育史部的年会的人很多。教育史协会的各部在全国兴盛发展,协会发行了一份通讯,设立了两项历史作品方面的奖项,新教育史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出现了大量的教育史著作。
60年代后期,美国教育史界出现了一种更激进的修正主义思潮,亦称激进派。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卡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1968年),《阶级、官僚政治与学校》(1971年),鲍尔斯和金蒂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1976年),卡列尔的《危机的根源》,卡诺艾的《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等等。修正派认为,传统的美国公立学校体制乃是最大的失败,是资产阶级用来控制劳苦大众、培养驯服工具、巩固其政权的手段;学校教育并不能提高劳苦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它是怀有阶级偏见,实行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当然,这些极左的观点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其势头在70年代末已经终止。人们更趋于以客观的、公正的观点研究教育史。一些历史学者又转回到公共学校,把公共学校当作历史舞台的中心。同时,教育史学者发现自己又处于新的、不确定的专业和学术位置上了。
四、低谷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对教育史的不实用性的批评,许多学校在教师教育计划中取消了教育史课程,教育史研究的队伍也在萎缩。人们批评教育史对教育承担的责任小,对教育的影响小。专业教育学者批评教育史脱离实践,与现实不相关,自以为是。专业历史学者则批评教育史狭隘、落伍、自产自销。进入80年代后,美国的教育史研究全面走入低谷。
这一时期的教育史研究者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在考虑教育史研究的范围到底是什么,是诸如学校的正规教育机构,还是构成教育的更广泛的其它成分?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争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教育史研究方向。首先,全球交流和交往方式的进展,使得学者们更进一步抛弃了原来的那种对其他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态度。现在,有了全球的教育史学者网络,这对于教育史学者看待自己和自己的作用的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近年来,在整个英语国家中都存在的研究教育史的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情况得到缓解。一般来说,专业教育学者把自己看作是“教师教育者”,他们是从教师专业目的出发来研究教育史的,而专业历史学者则更普遍的把教育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目前,这两方面的学者有相互联系、合作的趋势。
当前,在美国教育史研究中占主流的还是持教育的宽泛含义的人,如80年代末的美国教育史协会主席就把教育定义为“人类发展自己意识、形成同一性、学习社会的方式以在社会中发挥功能及确立其文化并将文化一代代传递的整个过程”(注:N.Ray Hiner,"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1990's and Beyond:The Case fo Academic Imperialism",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Vol.30,No.2,summer1990.P.149.)。教育史学者们认识到,他们所研究的学科比他们以往所认为的要更重要,教育是人类环境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它对于人类社会就和政治、经济及宗教的作用一样重要。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阶级,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史学者的工作就毫无边界了,虽然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看作具有潜在的教育性,但这也不是说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具有同样的教育性,或是说教育史学者就得研究所有的活动。从全面的层面理解教育给予教育史学者的是,从无与伦比的智力上的力量来寻求认识和理解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这样,80年代以后的美国教育史研究作品就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对于以前所忽略的教育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少数民族的教育、宗教团体的教育等等。
除了重新定义教育的概念之外,促进80年代以后的教育史研究的还有教育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教育史学者开始努力为美国的教育政策的制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特定的技能、视角和观点对制定出正确合理的教育政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关于政策研究和分析的教育史文献,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
总的来说,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史研究在美国处于低谷,但教育史学者们正在努力走出低谷,随着他们的努力,人们逐渐对教育史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美国教育史协会的人数稳定增长,《教育史季刊》上也刊登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教育史学者们认为,未来的教育史是一个广阔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极高地位的学科,它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根本性的重要作用。教育史学者们已逐渐掌握了智力方面的能力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也开始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发挥作用,未来的教育史学者将是强大的和富有智慧的。
结语
20世纪的美国教育史研究,几起几落,取得了许多成果,也留下一些经验和教训。梳理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是关于教育的概念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史就研究什么。在本世纪初,人们把教育界定为学校教育,教育史的研究也就局限在正规教育机构的历史和教育思想史方面。随着教育的概念的扩展,教育史研究也就有了新的广阔的领域,家庭教育、青少年教育、少数民族教育、黑人教育等等都成为了教育史研究的对象。现在看来,虽然对于正规教育和学校制度的发展研究仍然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教育史应该摆脱制度化的研究的限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教育的组成有更全面、更综合的理解。
其次是关于从事教育史研究的人员的问题。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到底谁应该担负起研究教育史的重任?谁的研究才是正统?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教育史的传统是由教育学者开创的,历史学者则不时对教育系中和师范学院中的教育史研究和教学提出批评,并逐渐开始从事教育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则出现了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教育史的研究和发展。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于某个研究者是在哪里工作的,是在教育系还是在历史系,关键要看他的工作是否过硬,看他的研究是否真正有价值,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在教育史研究方面各具特色,都是教育史研究的生力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史的价值问题。从教育史这一学科诞生伊始,它就一直面临着对它的价值的质疑,批评主要集中在它的非实用性上,认为它无助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对于教师的教学来讲帮助不大。其实,教育史的价值并不表现为即时效应,它能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教育问题,从而全面地分析和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它提供给教育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的是一种视角,而这对于他们制定出正确合理的教育政策和进行有效的教学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美国的许多教育史学者都已经在积极从事对教育的方针、政策进行指导的工作,新世纪的教育史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
标签:美国教育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历史学论文; history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