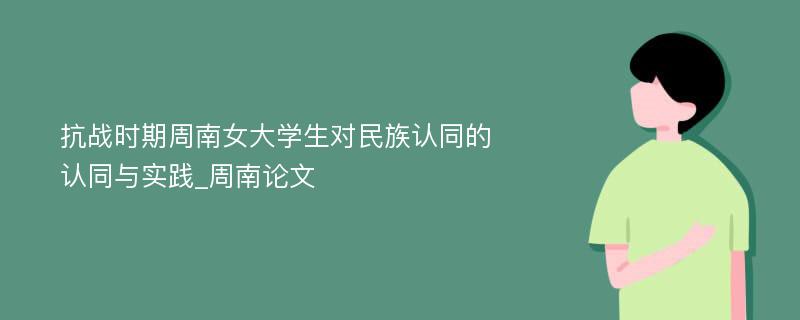
抗战时期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与践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女学生论文,国民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277/j.cnki.jcwu.2014.05.017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5-0108-06 梁启超曾在1899年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二字并称者。”[1]116至晚清十年,“制造国民”已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政治诉求[2],“国民”意指愈加明晰:“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用以重新塑造中国社会关系和国人思想人格的概念,更同时是一个新的、凝聚人心的身份认同符号。”[3]尔后,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亦被精英男性纳入“国民”范畴,立论基点为:“一国国民,必合男女而成,政治者,立于男女所合之社会基础上之物也。政治既立于男女基础上面,即不能但舍女而问男。”[4]140 1905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下文简称周南),是近代湖南著名的私立中学。其办学业绩广受社会赞誉:“群谓该校为女学之先导,此事实也……民国五年至现在以振兴人才教育为目的,小学为基石,由是湖南女生入大学者岁不乏人。”①全面抗战时期,周南更是顺应时代诉求,鼓励女学生投身抗日洪流,以履行国民之责。本文聚焦这一时期的周南女学生,意在探究知识女性尤其是女学生是怎样顺应民族救亡的召唤,认同并践行国民身份,以完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 一、周南的办学宗旨与教育管理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外省大批高等、中等学校纷纷迁往内陆省府长沙避难。随着日军犯湘,长沙成为抗战的前沿阵地,落脚不久的各校只得再迁云、贵、湘东南、湘西等偏远地区。 (一)办学宗旨 周南于1938年奉令疏散,同年8月迁往湘潭凎田,11月再迁安化蓝田,1945年4—7月迁至更僻远的樟梅乡,直至1946年2月返回长沙,才算结束流亡办学的历史。周南校史将这8年称为“蓝田时代”,被后人誉为“最为辉煌的时代”。此期,虽然战乱频仍,学校几经转徙,耗费不赀,但是在校长李士元率领下,艰苦办学,弦歌未断,师生一体,亲如一家,共济时艰,熔铸成一股“蓝田精神”。② 为规范国统区教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4月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设立教材审查、教师资格审核制度,实行“党化教育”。[5]李士元顺应战时教育方针,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青年守则十二条”③为最高原则,“朴、诚、勇”为校训。④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学生遵从国民党之主义,坚定革命意志;遵守学校纪律,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勉励学业,充实服务家庭和社会的能力;发扬博爱精神,养成高尚的情感;锻炼健全身体,养成耐劳的个性;节约金钱及时间,养成忠勇奋斗的精神,自立负责的能力,以及精诚团结的意识。 (二)教学管理 身为近代湖南教育家群体之一员,李士元恪守教育救国之职志,以“养成刻苦之习惯”、“研究高深之学问”为旨归,认为唯此“庶能以学问为济世之资,而成其报国之志也”。⑤即使在流亡蓝田时,仍强化教育管理,严抓教学质量。周南的课程设置中,除开设国文、数学、英语、史地等常规科目外,还应战时之需设有救护学、公民课、党义等课程。考试严格且频繁,包括视每科每周上课时数而定的各种月考、期终考等,由各班合场混合编排座位,严防舞弊,实行“宝塔式”淘汰制,以“去芜存菁”、“淘沙得金”。规定每日下午课余自修1小时,晚间自习至少2小时,晨起早读半小时,下午及晚间自修,由教导部监督教员值日指导,每班每周规定赴图书馆阅书1小时,另有物理、化学、生物、家事等实验室实习。 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体育教学,规定中学毕业会考体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6]周南迁至蓝田后,尽管学校体育设施简陋,但师生不畏艰难,在体育教师陈嘉钧的率领下,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建成较齐全的运动场,有排球场7处,篮球场5处,网球场3处,50公尺、100公尺跑道各一处,单双杠各2个。按校规,除正课2小时外,学生须参加上午课间操,以“振奋精神”。学校设有体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普遍运动,规定每人须在田径、球类、游泳、器械4项中至少选2项;各班体育股按班选定项目,编配队数、组数及所需时间场所表,交由校自治会体育股以整体编配,以保证学生每周3小时半的运动。⑥加之学生大都寄宿,每天下午4时至5时,每周六、周日,每个寒暑假,都可抓紧训练比赛,平时体育组除抓紧校代表队训练外,还抓紧班际球赛。[7]128因而,体育活动开展得比战前还好。据不完全统计,自1940—1945年间,周南共参加了7次较大的赛事,其中包括3届省运动会,均获佳绩。 (三)自我管理 周南素有民主办学的传统,学生的自我管理是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治会是自我管理的载体与核心。1919年,自朱剑凡推行教育改革后,学生自治会的建制基本成型,自治会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除了品德好、学习成绩好之外,还要有工作能力才算合格。因此他(她)们有号召力,有组织能力,能发动群众”。[7]40此期,周南设校自治会和班自治会二级机构,校自治会分设总务、事务、文书、学术、游艺、体育、卫生、宣传、灯油等股,班自治会相应地选出各股负责人,隶属校自治会。校自治会分对内、对外两项事务。对内事务包括:规定各班级自治会各股干事应进行的事项程序及工作场所、整个时间之编配等;出席各班自治会的有关集会;组织食事团,监督“改良伙食”;举行风纪比赛,以“整顿校内纪律”;组织演讲比赛、作文书法比赛、田径运动比赛、生产比赛、健康比赛、游艺比赛等。对外事务包括:办理民众学校;参加校外月会;“发动学生踊跃参加社会服务”,如参加抗战各种宣传及征募、慰劳、劝储、侦查,联络其他学校举行校际间的球类比赛等。总之,学生自治会作为学生的自我管理形式,与学校行政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仅减轻了后者的压力,且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培植了女生的自主能力、责任担当与团队精神,使她们的国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二、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一)“女国民”观的提出与传扬 “女国民”作为一种概念或命名,最早由1903年成立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提出,该会以“拯救二万万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同期,秋瑾在《女子歌四章》中亦唱出“我女子亦国民,亿兆同胞苦沉沦”,“社会进化权利伸,我女子亦国民”[8]等词句。在先进女性传扬“女国民”之时,精英男性亦遥相呼应。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同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以“铸造国民”[9]240为旨归。并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论述女子体育的文章指出,加强体育“不特养成今日有数之女国民,且以养成将来无数之男国民”[10],首次将女国民与男国民相提并论。1906年,上海群学社发行的《最新女子教科书》也贯穿着“女子同为女国民”的思想。1907年,《东方杂志》刊发申论:“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11]至此,“女国民”作为现代性想象进入主流话语,其社会意涵日渐清晰,即将女性与传统家庭剥离开来,不仅使女性由从属性身份转化为独立的个体身份,还使她们“通过对国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得以越过家庭,直接成为国家的构成单位,相对于国家,构造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身份”。[12]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认为,强化女性国民意识有助于动员妇女参战。1938年4月,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妇女工作旨在“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13]蒋介石在“新运”六周年广播训词中指出:“妇女同胞,占全国人口之半,也就是我们整个民族一半力量所寄,我们需要增强国力,是要使多数女同胞动员起来,在家庭、在社会一齐策动改进国民生活和加强抗战力量的工作。”[14]宋美龄更是将妇女解放与民族救亡相联系,她说:“国民对于国家的义务是不分男女的,尤其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女子解放,要看我们女子本身的努力……我们女子对国家民族和世界人类有确实的贡献,女子的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提高……只讲妇女解放还不够,还要用我们妇女的力量,来达到全民族同胞的解放,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15]148 (二)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教师的言传身教无疑是女学生认同国民身份的催化剂。李士元反复强调“秉礼、义、廉、耻之训,为立身报国之基”,号召女生“确立报国之思想,具舍己为群之志”。⑦国文教师黄厘叔叮嘱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磨炼意志,学好本领,将来要竭忠尽智,为国效力,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周敦元在讲授《正气歌》《满江红》等诗篇时,借题发挥,“纵不希望知识女子,人人为花木兰、梁红玉,亲赴前方,参加作战,然而如何宣传抗战之意义,如何慰劳受伤之士兵,如何扫除文盲,如何增加生产,皆当黽励从事,不可或疏。即今日者,又知识女子矢志报国之日也。”⑧“自家庭社会以至国家及世界之事,皆知识女青年分内之事也。”⑨由上可知,在周南教师的心目中,女生与男子同为平等的国民主体,且有义务承担同等的社会责任。 政府的规训宣传、教师的言传身教叠加影响,激发了周南女生对国民责任的思考。一名女生在习作中写道:“在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了严重的祸患,都是在苦斗里求生存,我们便是这苦斗的生力军,责任的重大,境遇的艰难,可说是空前的了。”因而“什么社会问题也谈,什么救国方法也讨论,有时我们之见解虽幼稚得可怜,但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是一片赤子之心的流露”。⑩另一女生易剑煌则对国家出路进行了探索,她通过对中、美、日三国对比,得出“惟有科学才能救中国,惟有科学才能使中国人贫困的面貌改变”(11)之结论,指出“报国之道,途径甚多,尤以科学上之贡献,需要迫急”,且以居里夫人为榜样。 与此同时,周南女学生将国民责任与妇女解放相联系。谭丽都写道:“吾人身为国民,且为具有较高知识之国民,尤宜抱定一个‘固我邦国’之大志,不问职务繁简,不论地位高低,不计薪资多少,竭吾力,行吾志。”(12)青争指出:“这次全民抗战是我们妇女表现力量的好机会,我们应当趁时加倍努力,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力量,储蓄大量的智能,准备担负起建国的工作,担负起为妇女谋彻底解放之责任。”(13)并提出妇女解放是责任担负的观点:“现今是我们表现力量的时候了,我们得奋起,利用难得的机会,求得妇女的解放。我们的解放不是权利的夺取,而是责任的担负,不是要求享受,而是勉尽义务。”(14)还有女生认为:“女子其所以在社会居于不足轻重之地位,非人为之,实以女子对于民族国家,无伟大之贡献,无惊人之表现”,提议“在此非常时期,亦即女子有所贡献于民族国家之时期”,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从事生产”等。(15)一句话,周南女学生已深刻认识到承担国民之责、尽国民之义务是确立自身国民地位的重要途径。 三、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践行 (一)刻苦向学 据校刊所载,每天清晨天未亮,高16班的王玉仙就吹起了起床号,同学们15分钟整理内务、洗漱完毕后到操场集合做早操和田间早读。校友易应南回忆道:“黎明早起,(我)就到操坪朗读或者背诵国文或英语单词,早餐后上课前学写毛笔字,有时晚自习后到老师办公室伴着油灯再学习半小时,待我回到寝室时同学们也刚上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挤时间学习。”[7]135图书馆更成为女生趋之若鹜之所,“每天开放的时间为课余短促的两小时,因为房子太狭小,迟来者每发向隅之叹,所以预先总有许多同学在焦急的等待。”(16) 刻苦学习换来了累累硕果。1940年7月高中第十班、十一班77人参加教厅的毕业会考,皆顺利通过,黎树芳荣获省数学冠军。1941年6月,高、初中升学率创新高,“即就去夏高中毕业同学之考取大学者约十之六,初中毕业之考取高中者约十之七。”(17)1942年8月5日教育厅耒字第70287号训令中写道,周南高中毕业会考(高十四、十五班)成绩优秀学生罗良莊、魏如松、陈怡佑等13人依照部颁免试升学之办法规定,保送免试升学,其中“高十五班的李光萃还是有名的‘李八百’,八门功课都是100分”。[16]因周南学生成绩优异,多所著名大学与学校签订协定,每届毕业生中的前几名免试入学。 在蓝田举办的各届各项比赛中,周南女生亦屡获佳绩。如,1940年6月,青年运动周男女共同比赛中,英语高中组第二名李曼青、第三名余泽媛,论文高中组第二名钟期荣、第三名汪树筠,理化高中组第一名胡安荣、第二名黎树芳,数学高中组第二名余泽媛、第三名胡安荣,讲演比赛高中组第一名易明西,皆是周南同学。又如,1941年5月青年运动周,国语高中组第一名王育妫,英语高中组第二名周佩铭,论文第三名王育妫等。还有,1944年3月29日举行了革命纪念日及纪念青年节的讲演、论文、壁报等比赛,讲演高中第一名为左大钰,论文高中第二名为谭丽都、第三名为谭慧等。 (二)办理民校 课余时间,周南女生利用所学知识办理民众学校,开化民智,宣传抗战救国。校自治会设社教委员会,由民校校长、事务主任、教务秘书组成。周南派学生到民众学校任教,给民众教授认字、简单算术、打借条、欠条等基本的实用知识。社教委员会还召集民校学生、家长及邻近民众,举行国民月会或家庭教育座谈会,讲演建国储蓄要义,宣讲国民公约,表演与抗战有关之戏剧和歌曲,进行抗战宣传活动。 此期周南社教办学成绩优异,1939—1945年间结业人数达2293人之多,多次获省教厅嘉奖。1940年5月教厅耒字18094号训令转教育部指令:“周南学生刘石泉办理社教工作勤奋不懈,应发奖状以资鼓励。”1943年6月,省教厅转教育部社字第14494号指令:“以周南兼办社教,成绩优异,应予嘉奖,以资鼓励。”为支持民教,省教厅多次给予补助,1940—1944年间共补助2000元。 (三)募捐劝储 周南迁校蓝田后,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令,主动参与募捐劝储活动。各班级开展“一角捐运动”。小学部“每个教室旁挂一个长竹筒做的储钱罐,每天第一堂课,大家就自动将零花钱投入桶内”。(18)学校还设立湖南省节约建国储蓄团周南支团,向邮局储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血色湘西》中有生动描写:“周南那些十几岁的女学生们,甚至老师、校长们都纷纷走上街头,演说募捐搞各样救亡活动。”[17]95报纸对周南师生积极自捐、募捐、劝储等行动也大加赞赏。报载(1940年11月21日)周南师生“对于建国储蓄赞助倡导不遗余力,在蓝田市向民众竭力宣传劝储,颇著成效,在校内更为热烈,切实倡导……堪称学校单位中劝储最特出之成绩,令人至为兴奋钦仰,富商大贾闻风兴起”。1943年1月10日,三民党湖南省直属蓝田党部公函称周南童军团、女青年分团“热心社会事业,爱护前方将士,甚为钦佩,尤以新年同众会中全体动员于冰凉之月下,不惮唇舌之劳,恶饥耐冻,发行物品义卖,以之涓滴为公,其热忱、其毅力,更属难能可贵,前线将士闻之当欢欣鼓舞”。据初步统计,1938年10月至1944年1月间,周南师生为抗战自捐、储洋金额达53607.58元;1941年5月至1943年5月间,学生为抗战募捐、劝储金额达40158余元。(19) 周南女生历来擅长文艺表演,她们利用各种节庆,如元旦、三八妇女节、国父逝世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双十节、国父诞辰日等,表演与抗战有关的戏剧、歌曲等,并将国民公约、建国储蓄等要义穿插其中,表演者情真意切,生动逼真,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以致纷纷慷慨解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39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会后陈嘉钧率领学生在蓝田市举行抗战化装宣传街头戏,吸引了全市民众近万人至火车站大坪观赏。女生们站在中央高地表演,当表演一个汉奸欺骗农妇受日兵残暴时,观众中着工人装的一个人跳入表演场地,试图抓着汉奸,口呼手舞不止,待陈嘉钧解释“这是伪装不是真的”乃止。(20) (四)农业生产 1940年10月,周南根据上级指示及颁布的《各级学校实施农业生产办法大纲》,试行农业生产,拟定了实施农业生产的办法细则,呈省教厅备案。具体办法是由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推举5人组成农业生产指导委员会,学生自治会中增设农业生产委员会,由高、初中各班出1人,共计12人组成,负责计划分配同学实施农业生产。学校计划租用邻校谭姓荒山土地两处约70方丈,开辟为四季生产工作之用,秋季借用东家禾田为冬季春初生产工作之用,租用校东侧荒地以蓄养鸡鸭,租佃邻校谭姓房屋大小四间用作养猪之用。所生产之物为春秋四季之瓜果蔬菜,以及蓄养鸡鸭等家禽家畜。将所佃之地按高初中12班分为12区,分配生产工具,实行轮流照看。收获之物均供食事工之用,另外,家事研究会还制作豆腐、豆汁、干菜等,及制作各种点心,以供消费合作社之销售。 1941年12月、1942年8月,省教厅督学两次视察周南,认为周南学生“兼习勤劳,实行扫地、种菜,且服务精神亦好”,“学生劳动兴趣颇浓,如种菜、喂猪,修运动场以及大路等,颇具成绩。”1942年秋季,生产猪14只,重2100斤,羊2只,重125斤,蔬圃共收菜计1200斤;1943年生产猪12只,重1880斤,蔬圃菜类收获计3400斤;同年4月,童军团生产中西点心、做手工菜等共收入洋1030元。(21)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学校生活物资的奇缺贫乏,使学生切身体会学校教导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尤为重要的是,使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为成为自立自强的劳动者奠定基础。 四、结语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戊戌维新时期,为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精英男性将女性纳入国民之列,冠之以“国民母”或“女国民”。五四时期,追求个性、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新女性”风行一时,“女国民”观退居幕后。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国家话语成为社会最强音,“女国民”再次凸显,上自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下至知识女性都认同这一符码。可见,“女国民”观是伴随着民族危机、女子教育的曲折发展时起时落。尽管“女国民”观为精英男性所倡导,其终极目标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却为知识女性包括女学生建构自身主体身份提供了契机。她们巧妙地利用“爱国救国,匹妇有责”[18]、“同担责任,同为国民”等主流话语,力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国民身份,大大加快了妇女解放的步伐。 注释: ①参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教职员会议记录》,湖南省档案馆,卷宗号59-07-06。 ②“蓝田精神”是指发挥团队的力量,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力量,改选环境勇于攀登的力量,意志与智慧的力量,热爱母校周南的力量。参见李士璜:《蓝田时代延续了周南百年历史》,载于《周南钟声》2008年第7期。 ③青年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载于司琦:《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史》,台北国立教育资料馆1981年版第370页。 ④“朴、诚、勇”指意志坚定,则勇之事也;生活俭薄,则朴之事也;笃行此二者而始终不渝,则诚之事也。 ⑤参见李士元:《本校三十五周年纪念词》,载于《周南女中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2期。 ⑥参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教职员会议记录》,湖南省档案馆,卷宗号59-07-06。 ⑦参见李士元:《本校三十五周年纪念词》,载于《周南女中校庆特刊》1940年第2期。 ⑧参见周世钊:《今日》,载于《周南女中三十六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第15期。 ⑨参见周世钊:《女子应有之新认识》,载于《周南女中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42年第3期。 ⑩参见黄蓂、黄友诚等:《别》,载于《周南女中三十六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第18期。 (11)参见易剑煌:《科学与中国》,载于《周南女子中学期刊》1942年第13期。 (12)参见谭丽都:《送毕业同学序》,载于《周南女子中学五一特刊》1943年第5期。 (13)参见青争:《年年此日》,载于《周南女中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4期。 (14)参见廖学道、刘湘宜等:《我们的礼物》,载于《周南女中校庆特刊》1940年第6期。 (15)参见马菊初:《解放之路》,载于《周南三十九周年纪念特刊》1943年第11期。 (16)参见杨澍:《自治会工作剪影》,载于《周南女子中学期刊》1939年第79期。 (17)参见周世钊:《今日》,载于《周南女中三十六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第3期。 (18)参见李士璜:《可敬的启蒙老师》,周南中学校友会编:《春晖芳草——百年周南纪念文集(1905—2005年)》(内部出版物),2005年。 (19)参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教职员会议记录》,湖南省档案馆,卷宗号59-07-06。 (20)同上。 (2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