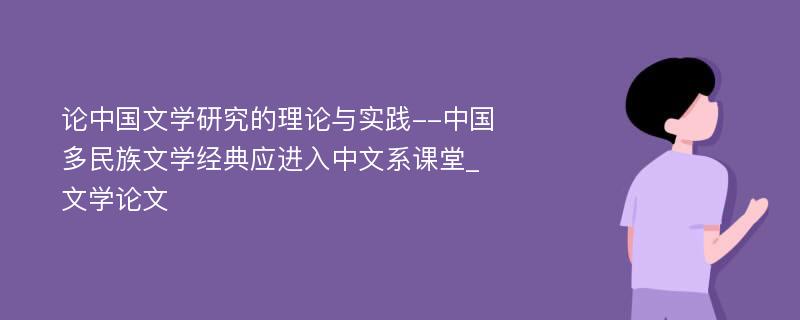
“中华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笔谈——中华多民族文学经典理应进入中文系课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笔谈论文,文学论文,中文系论文,课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框架及其二级学科的确立,应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尽管如此,百年来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证明,这种划分确实还存在着若干不合理的成分。 首先,汉语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争议。学术界已不满足于简单地以朝代划分的传统分期方法,而是希望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重新解读文学史现象。在传统观念中,文学、历史、哲学密切相关,难分彼此;而今泾渭分明,彼此悬隔。中文系又分为语言和文学,文学又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又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唐代又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的又继续分“四杰”“沈宋”,研究“四杰”的又具体分王、杨、卢、骆:总之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就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这怎么能研究得好呢?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整体观念,路越走越窄,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肢解成了毫无生命力的标本。 其次,中国文学史上的《文选》学、桐城派,一百年前被视为“妖孽”和“谬种”。从此,中国传统文学大宗文章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文学史有四大类,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其中散文只是传统文章学的很小一部分。其他三类,都有理论的借鉴,也有作品的比较。唯独中国的文章,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如何评说,面临着理论的困境。 这些问题,大家的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求同存异,努力回归中国文学的本源,则是学术界正在逐渐形成的共识。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在这里特别强调,那就是要注意中国文学空间多元发展的实际。 最近有机会到民族院校讲课,发现一个现象:民族院校文学系同学除阅读各民族文学经典外,通常还要开设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诗》《骚》、李、杜、元、白、韩、柳,都有详尽的介绍。反观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又有多少院校开设有民族文学经典课程?我没有做过统计,估计不会很多。 如果真是这样,中文系便名实不符。中文系,是中国文学系的简称。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如产生在公元11世纪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产生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以及著名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名著,已经有若干整理本,且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在文学研究界,这些文学名著早已成为显学,且成果卓著。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刘亚虎、罗汉田、邓敏文《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李炳海《民族融合和中国古典文学》就是其中的代表。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合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首次将古代、现代、当代文学以及历代多民族文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初步实现了很多学者所希望看到的文学史古今打通、多种文体打通、多民族文学打通的“三通”。从这些著作中我们知道,《福乐智慧》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成书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一部文学作品,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乃至整个亚洲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蒙古秘史》不仅是一部研究蒙古史、中国元代历史和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著作,而且是一部充满史诗气息的优美的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在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的藏族聚居区,在国外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亦有流传,反映了不同时代藏族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体育、艺术的全部知识,素有“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之称,被认为是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江格尔》是在蒙古族古老英雄传说影响下形成的一部宏大的史诗,反映了15世纪以来蒙古族封建割据时期西蒙古卫拉特地区的社会斗争场景以及人民群众要求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停止内讧、实现家乡统一、实现民族统一的良好愿望。《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宏伟的英雄史诗,讴歌了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前赴后继,率领柯尔克孜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业绩。这些英雄史诗最重要的特色,是迄今依然流传于各个民族地区,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文学。这当然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骄傲,也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好的教科书。 相对于研究界而言,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教学系统,多数没有把上述文学经典纳入教学与研究视野,绝大多数讲授只是局限于汉语文学经典,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为此,我们呼吁大学中文系开设民族文学经典课程,传播各民族文学经典,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了解这些民族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