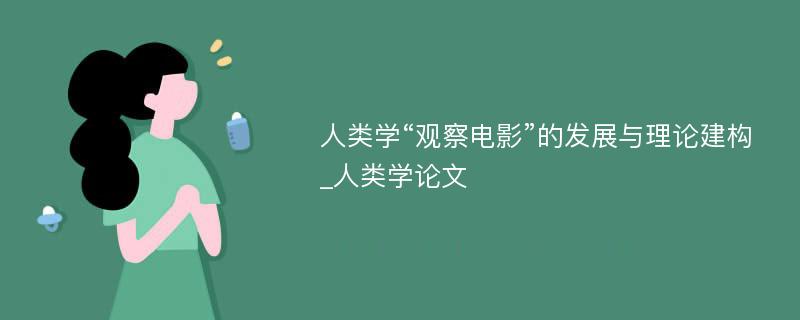
人类学“观察电影”的发展及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理论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影视人类学中,主流民族志电影一直在科学主义范式的影响下,主要以解说式纪录片为主要风格,大部分影片是作为人类学家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工具,并为文字的民族志提供辅助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影视人类学家及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希望在民族志电影的方法和理论上寻求新的突破。“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首现于1970年代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志电影,迅速推广至西方纪录片多个领域,随即被当时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制作者接纳。一时之间,以“观察”为名的纪录电影名目繁多,例如,美国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和法国让·鲁什的“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也被贴上“观察电影”的标签。①由于不同的人对“观察”有不同的理解,②其中,由科林·扬(Colin Young)提倡、大卫·麦克杜格(David MacDougall)发展的“参与式观察电影”经过四十年来的探索与发展,目前已成为欧美民族志电影的主要类型。在“观察电影”的理念与实践下,无论在认识论,还是在实践上,“人类学”与“电影”这两个不同学科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结合,对西方人类学界和纪录片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观察电影”的发展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70年代美国直接电影的影响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剧戏艺术系系主任、纪录电影理论家科林·扬及同事开始了对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的探索之路。1966年,加州大学的电影系与人类学系共同建立了一个电影培训项目,主要目标是培养非人类学专业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培养人类学专业的学者拍摄制作民族志电影。该项目提出“将民族志的调查方法作为培训的总体方法论”,③后来,此种方法论被科林·杨命名为“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80年代初,科林·杨接受英国政府聘请,回到英格兰创建英国国家电影电视学校(NFTS),担任纪录片系主任。科林·杨与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合作,再次建立相同的民族志电影培训项目,“观察电影”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得以进一步发展。 (一)早期“观察电影”(20世纪60—70年代) 60—70年代是“观察电影”的早期阶段,以科林·杨在美国加州大学进行的民族志电影制作培训为标志。这一时期,由电影导演马克·麦卡蒂(Mark McCarty)和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制作完成的影片《村庄》(The Village,1968),是“观察电影”的第一次尝试。随后,大卫·麦克杜格在东非乌干达拍摄的《与牛群一起生活》(To Live with Herds,1971)被公认是第一部人类学“观察电影”,它完全按照科林·杨提出的“观察电影”理念制作,也是大卫·麦克杜格的第一部民族志电影。之后,麦克杜格夫妇在东非肯尼亚拍摄了图尔卡纳人(the Turkana)的三部民族志电影,也被称为“图人对话”或“图人三部曲”,即《罗朗的方式》(Lorang's Way,1973)、《婚礼上的骆驼》(The Wedding Camels,1976)、《众妻之妻》(A Wife among Wives,1981)。由于东非系列影片一改传统主流的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制作方式,而是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电影”的新理念与新方法,成功地建立了“观察电影”的基本实践道路。这些影片一经问世,其新颖的创作风格和视点立即在当时西方纪录片界和人类学界带来巨大震动,大卫·麦克杜格一举成名,“观察电影”影响了新一代的西方纪录片制作者。 (二)“观察电影”的成熟期(20世纪80—90年代) 80年代中期,科林·杨来到英国创立影视人类学项目,培养民族志电影人才,也继续将“观察电影”的理念进一步付诸实践。本次项目拍摄的重要影片均以观察电影为主,包括人类学家约翰·贝利(John Baily)在阿富汗边境拍摄的《埃米尔》(Amir,1985),保罗·亨利(Paul Henley)在南美亚马孙流域拍摄的《神圣的舞者》(Devil Dancers,1986)、《双面圣人》(The Saint with Two Faces,1986)、《重返森林》(Reclaiming the Forest,1986)。从80年代起,麦克杜格夫妇在澳州拍摄反映当地土著社会情况的“观察电影”,这些影片表现出强烈的实验风格。④90年代,大卫·麦克杜格在意大利萨丁岛拍摄了《服务生的年代》(Tempus de Baristas,1993),再次成为“观察电影”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观察电影”在80—90年代得到普及和推广,很多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采用“观察电影”方式进行拍摄,包括独立电影制作者金姆·麦肯齐(Kim McKenzie)的《等待哈里》(Waiting for Harry,1982),以及加里·吉尔迪亚(Gary Kildea)的《塞尔过和柯拉》(Celso and Cora,1983)⑤等。 (三)观察电影的新发展 从第一部“观察电影”开始,大卫·麦克杜格一直是“观察电影”的核心和旗帜性人物,自2000年后,麦克杜格对“观察电影”有了新的思考,更强调“观察”的意义与价值。以“杜恩学校”电影系列为代表,包括五部影片《杜恩学校纪事》(Doon School Chronicles,2000)、《清晨之心》(With Morning Hearts,2001)、《斋蒲尔的卡姆》(Karam in Jaipur,2003),《新生》(The New Boys,2003)、《理性年代》(The Age of Reason,2003)。通过对这所印度精英学校的学生生活的描绘,这些影片不仅讲述印度中学学生的学习生活,还关注了学校的“社会美学”的构建。在《学校景观》(Schoolscapes,2007)中,“观察”的实验性更为突出和外显,麦克杜格尝试通过影像与声音的联觉,试图建立观察电影的感觉之路。三年后,麦克杜格在新德里郊区的一个儿童收容所拍摄的《甘地的孩子》(Gandhi's Children,2010),这是“观察电影”的又一力作。除大卫·麦克杜格外,2000年以来“观察电影”的重要作品还包括德国人类学家让·莱德尔(Jean Lydall)的《杜卡的困境》(Duka’s Dilemma,2002),以及澳洲纪录片制作者加里·吉尔迪亚的《克瑞马的法则》(Koriam's Law,2005)等重要影片。 二、“观察电影”的理论建构 实际上,“观察电影”一词最早出现于纪录片制作者罗杰·桑德尔(Roger Sandall)的论文。⑥受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及60—70年代美国“直接电影”的启发,科林·杨将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与电影拍摄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观察电影”的理论框架,⑦他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观察电影》正式确立了“观察电影”在西方民族志电影中的理论框架及基本特点。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在大卫·麦克杜格、保罗·亨利、安娜·格里姆肖等西方影视人类学家的持续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归纳总结“观察电影”的基本特点与方法,其基本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观察电影”的基本观点 “观察电影”的最初理念源自“直接电影”的导演李科克(Richard Leacock)的想法,“我想发现人们的一些事情”,⑧这与人类学界马凌诺夫斯基的想法不谋而合。⑨由于抛弃了早期民族志电影拍摄实践中“碎片式的民族志真实”,⑩“观察电影”主张以“影像事实”为核心,这极大地发展了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所提倡的电影美学观。尤其是,“观察电影”根植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最根本的“参与观察”方法,它强调了在田野调查中“观察”的重要性,认为拍摄过程即是“观察”过程,(11)而“观察”的过程即是以文化内部视角建立起的开放性研究过程。(12)因此,“观察电影”的核心观念以研究对象文化内部的视角为基础,以道德与人性为基本定位,由于强调并关注以下问题“电影如何制作?为何制作?为谁制作?”,(13)从而体现出明确的主体性和反思风格。由于“观察电影”以电影为媒介探索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摄影机不再是收集资料的工具而成为书写社会生活的笔,所以,“观察电影”与传统的民族志电影有本质区别。 由于“观察电影”强调的是电影作品的人类学文化内涵而非艺术性和商业性,经过长期实践与思考,大卫·麦克杜格指出“观察电影”的理论假设基础:“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值得去观察的,部分理由是因为它们自己独特的空间和世俗的形貌。‘观察电影’可以频繁地分析,但也表明了这样一种看法:电影开放的意义类型也在传递电影制作者的分析。在世界面前的这种谦卑姿态当然可以是自我欺骗和自我服务的,但这也暗示,认识到拍摄对象的故事比拍摄者自己的故事更为重要”。(14)与过去的强势态度不同,在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上,“观察电影”强调以低调和谦虚的姿态与被拍摄对象建立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关系,并且承认拍摄对象的故事比自己的故事更重要,其基本目标是发现拍摄对象的文化世界。影视人类学家保罗·亨利认为,(15)“‘观察电影’唤起拍摄对象的世界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去表明他或她是一个伟大的制作者,也不是用强烈的美学手法去操纵对世界的表征,将之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品但不再带有最初的真实经验之感”,相应地,在拍摄及后期剪辑技法上体现为十大特征:“无剧本、无定向、无脚架、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得到证词(testimony)、无旁白、无音乐、无特效、无技术性镜头拍摄、无技术性剪辑及其上述内容的统合。”由此观之,“观察电影”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电影美学观本质变化而使其具有了电影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智慧深度。 (二)“观察电影”的理论体系 不同类型的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有不同的观察方法,传统的解说式民族志电影将“观察”视为科学测量与重复分析的方法,而“直接电影”的“观察”提倡“墙上苍蝇”式、以旁观者姿态不参与也不介入的观察方法。就“观察电影”而言,它强调以“观察”为核心,提倡在观察中的“参与”,并从电影的主观性、立场、内容、叙事以及以经验情感等方面,对传统民族志电影、“直接电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卫·麦克杜格的电影制作实践和理论建树之下,“观察电影”与最近阐释的、后现代的人类学理论相契合,在电影内容、叙事、与拍摄对象间的关系、电影认识论及美学观上均呈现出与过去传统民族志电影的显著差异。 1.“观察”的存在:“主观”与“在场” 一直以来,人类学纪录片被认为是记录客观世界的最佳方式,所以,在电影中任何主观倾向的出现均被认为是对客观记录的妨碍。为保证“真实”的客观科学记录,拍摄者不能干预拍摄对象,因为摄影机的存在或多或少会对拍摄对象产生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纪录片界出现的“直接电影”于是提出了“墙上的苍蝇”的旁观式的观察方法,(16)即拍摄者最大限度地降低摄影机对拍摄对象的干预,其最突出特点表现为拍摄者“墙上的苍蝇”式的“不在场”。吊诡的是,旁观式的“观察”并不能代表拍摄对象在行动、言语和内心等方面没有受到拍摄者的干预。事实上,“直接电影”宣称的摄影机“不在场”是不存在的,只是它“视而不见”,并且在“努力地宣称自己能记录一切”。科林·杨认为这只是“一个骗局”而已,从而对“墙上苍蝇”方法提出质疑。他犀利地批评说,“所谓的‘墙上的苍蝇’并不是拍摄者不去干预被拍摄对象,恰恰相反,而是拍摄对象没有去干预拍摄者而已”,“直接电影”拍摄者只是在“天真地假装摄影机不在场”。(17) 与之不同的是,“观察电影”首先承认电影主观性的存在,“观察电影”并没有假装“不在场”,与之相反,拍摄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让观众确信到电影制作者和摄影机的“在场”,(18)并且不回避文化内部视角的呈现,这是“观察电影”与“直接电影”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长镜头的大量运用,拍摄对象日常生活的细节表达,摄影机偶尔地运动或改变机位,拍摄对象对待摄影机的亲切态度,尤其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交流对话等等,这些视觉证据让观众相信电影制作者和摄影机“存在”的真实感。此外,在“观察电影”中,当摄影机静静地拍摄时,整个拍摄过程传递着拍摄者的敏锐、细致和耐心,它不但使观众认同了拍摄者“在场”的诚实,也使观众渐渐地进入影像中的陌生文化世界。所以,“观察电影”并没有将摄影机视为“墙上苍蝇”式的冷静观察者,既不干扰也不介入到拍摄对象之中,相反,它是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为核心,拍摄者与摄影机一起进入到对象的文化事件之中,以参与的方式发现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实质,也力图挖掘文化的深层意义。虽然“观察电影”与“直接电影”貌似相同,但由于电影主观性上的差别,导致了二者在电影技术、结构、甚至是电影美学观上的差异。 2.“观察”的立场:“亲密”与“谦卑” 在传统解说式的民族志电影中,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分离,电影的权威由高高在上的、无所不知的“上帝之音”建立而起。由于同期声技术的发明,“直接电影”的新变化是出现了访谈对象的访谈声音,由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二者之间表现为“不交流”的访谈,或是太过于正式的访谈交流,尽管解说式的旁白消失,但二者之间仍是表现为沉默静止、有距离的僵硬关系。电影制作者的权威依然隐藏在电影剪辑与结构之中,同期声技术的革新只是技术上的改变。 然而,在“观察电影”中,由于承认电影的“在场”,也导致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当拍摄者参与进入拍摄对象文化事件之中,他们的讲话和交谈成为纪录电影制作的一种行为表达方式和重要的信息资源。以大卫·麦克杜格的“东非电影系列”为例,拍摄者与图西人之间的交流有三种形式:(19)其一,是拍摄对象之间的相互谈话;其二,是拍摄对象有目的地向拍摄者讲话,通常是回答拍摄者提出的问题,或是讲述拍摄者应该知道的基本常识;其三,是拍摄对象与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对话或解释。以上三种形式的谈话实为开放式的互动交流,这不仅体现了拍摄对象与拍摄者的熟悉和信任,而且最终建立起相互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在第三种谈话方式中,拍摄对象及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一览无余。双方没有隐藏,没有害怕或尴尬,有时也会有疑惑和问题。双方的亲密程度还体现在拍摄对象认真思考并回答问题,它还让拍摄对象感受到尊重,也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大家一起来讨论探索问题答案的这种方式,在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这也使得摄影机从文化外部的视角向文化内部的视角转变。 这种亲密关系还体现在拍摄对象发声的机会大大增强,他们对着摄影机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更多机会表明自己的观念和立场,不需要其他的解释者或权威的声音代替,与后现代民族志中所提倡的“多声道方法”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观察电影”中,拍摄者不再将电影拍摄视作高高在上的权威,而将其理解为对生活的尊重,以及对拍摄对象的尊敬和谦逊态度。所以,在拍摄时,由于强调“摄影机在世界面前的谦卑姿态”(a stance of humility before the world),(20)而表现为尽量地低调、远离权威的姿态,这也暗示着拍摄对象的故事比拍摄者的故事更为重要,摄影机“没有一丝自命不凡,摄影技术也没有故弄玄虚,它朴实地表达了诚实与信任”。(21)不仅仅如此,“观察电影”的这种亲密感通过电影传递给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观众感受到与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亲切与平等,因而很容易进入到对象文化知识的探索之中,进而表现为对拍摄对象的理解与尊重。摄影机的“谦卑姿态”在拍摄者、拍摄对象与观众三方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麦克杜格称之为“无特权电影风格”(unprivileged camera style)。(22) 3.“观察”的内容:“日常”与“细节” 在电影美学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提倡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对“观察电影”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此之前,很少有纪录电影关注到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例如,在“直接电影”中,虽有呈现拍摄对象的行为与活动,但其主题往往表现为政治选举、法庭、社会机构,或是流行明星的音乐演唱会,如《初选》、《莫回首》等影片。又如,在法国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所提倡的参与式电影中,大多数影片关注拍摄者的表演,未能以拍摄对象日常生活为主(23)。虽然在《北方的纳努克》便出现了大量英纽特人日常生活的场景,但为服务于戏剧化冲突的故事而被简单化和浪漫化处理。 “观察电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普通日常生活对其强大的吸引力”,它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并不是“浪漫化,也不是简单化,而是大量的生活细节化”。(24)如同马凌诺夫斯基在民族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强调的“不可触摸的生活细节一样”,在麦克杜格的《与牛群一起生活》中,观众看到的是灰尘、狂风、牛群的吼叫、嬉戏的儿童,大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是人们重复着每天单调乏味的生活。“观察电影”制作者与人类学家一样,在介绍他们的研究对象时,不仅关注他们最显见、最大众化的一面,还同时关注他们的生活琐事、闲说、易显的小事,以及马凌诺夫斯基在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中所说的“真实生活中的不值细思的事情”。(25)由于电影的独特性,使电影能够将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给观众,这是其他学科无法与电影相提并论的优势。“观察电影”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电影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来,同时,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通过细节给予呈现,“观察电影”的真实性正是“通过大量的细节性描绘给予”。(26)此外,“观察电影”对普通日常生活的关注,不是对拍摄对象奇风异俗的猎奇,也非做浪漫化或是简单化处理,而是让拍摄者以电影拍摄的方式去接近事件,并了解拍摄对象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这是让电影制作者去发现和理解拍摄对象的生活,从平凡生活中显现出生命的伟大,进而尊重生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由是观之,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是“观察电影”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魅力所在。如果说,过去的人类学家将电影视作收集和存贮资料的调查工具,那么科林·扬认为“观察电影”应该是“检验人类行为与人类关系细节的有效方法”。(27)所以,“观察电影”的摄影机不是“静止的与远距离的人类行为观察”,而是摄影机接近拍摄对象并亲密地跟随他们的发现过程,在“观察电影”中,电影的拍摄过程便是观察过程,也是发现过程,同样也是研究过程。 4.“观察”的叙述:“显之”而非“告之” 一般而言,“观察电影”之前的绝大部分纪录片以“说明”式为主,这是由英国纪录片领袖约翰·格里尔逊发明并倡导,并成为纪录片制作的主要模式。在此类纪录片中,以旁白解说为主的第三者声音对电影画面进行说明和解释,这种方式自发明以来,迅速流行于各种主流媒体和电视台,大量的电视栏目和教育影片习惯使用这种方式对观众进行教育灌疏。由于导演的操控性较强,解说式纪录片被视为“无所不知的上帝之音”而广受批评。随电影同期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直接电影”以同期声的方式直接加入拍摄对象的访谈声音,片中不再出现第三者的解说和旁白,这让观众第一次听到了电影中的人物谈话和环境声音,同时将摄影机的干预降为最小,以此呈现拍摄对象的生活与文化,让电影更具真实感,这对传统解说式纪录片产生了巨大冲击,“直接电影”因而成为纪录电影史上的重要进步和关键转折点。然而,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依然没有摆脱纪录片导演强势操控下隐藏的经典叙事结构,比如说,“直接电影”惯常使用的富有戏剧性的“危机结构”方式,科林·杨极富洞见地指出,戏剧往往是“生活的过分简单化处理,与虚构的剧情电影一样”,在“直接电影”中“人物的戏剧化处理没有改变,还是沿继冲突、危险、受到挫折的基本模式”。(28)最终,“直接电影”的叙事结构仍以导演的主观意图操纵为主。《北方的纳努克》也不例外,其叙事结构虽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事件串起,但其叙述方式是经典的戏剧冲突模式,即以封闭式来结构全片。 就电影叙述方式而言,按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观,由于电影本身呈现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电影结构上最低限度地依靠戏剧化结构,其戏剧化成分被降低,而大量地依赖日常生活化的细节来结构影片。所以,观察电影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电影从说明式的“告之”(telling)转变为表明式的“显之”(showing),(29)这也意味着影片是开放式的结构,也就是说,“观察电影”是开放式的过程与结局,或者没有结局,这也成为“观察电影”与“直接电影”区别关键之处。尤其是,麦克杜格特别强调电影是在讲述“谁的故事?”这即是说,电影的叙述方式是在“说明”制作者自己的意图?还是在“显现”拍摄对象他们的意图?是在讲述电影制作者自己设计好的故事?还是讲述拍摄对象他们本身的故事?由此可见,在电影叙事上,“观察电影”由过去受电影制作者意图的强势操纵而转变为跟随拍摄者去呈现拍摄对象的文化世界,这也使得观众进入到自己的发现旅程之中。由“告之”转为“显之”,导致“观察电影”结构方式的改变。如果说,传统纪录电影的叙事关注的是“三段式”经典结构,即包括开始、高潮、结尾组成的戏剧化冲突,那么“观察电影”更多的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而不是集中表现情节或是戏剧冲突。“观察电影”常常是以松散的结构,捕获生活化的细节,并最低限度地依赖剧情结构,从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发现并揭示文化的“真实”,而并非去创造“真实”。这个过程需要“观察电影”制作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耐心去寻找自己所观察到和体验感受到的那些文化细节,所以,“观察电影”在电影结构上坚持“以生活的细节代替戏剧性的张力,以电影的真实代替人为虚假的娱乐”,(30)如同美国人类学家吕西安·泰勒(Lucien Taylor)的精辟总结,“观察电影更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融入而不是告诉观众关于他们的生活,也更加关注表演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在摄影机前的扮演”。(31) 5.观察的感官:“经验”与“感觉” 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理论上“观察电影”均对声音效果提出了超乎以往的要求。从技术上讲,由于“观察电影”消除了背景配乐和旁白解说,使得自然音效的处理在影片中尤显重要。但如果说,传统民族志电影强调的是通过人眼的单一观看而进行观察的话,那么,“观察电影”更有意突出由视觉与听觉的结合而引发的综合的身体经验与感觉。在印度“杜恩”学校系列电影中,大卫·麦克杜格特别强调身体、经验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观察电影”中的“参与”方式不但通过“观看”将拍摄者、拍摄对象与观众结合,也将视觉与听觉相互连接而形成电影感觉与经验的交流基础。观众在电影镜头的带领下,以自己的视觉、听觉等内在的感官经验为基础进入了与电影中的陌生文化世界的交流,通过观看而引发观众自己切身的经验感受,由此产生强烈共鸣,“观察电影”因之成为三方感觉与经验交流的基础。 由是观之,“参与式观察电影”不再是科学主义范式之下所理解的“观察电影”。虽然在技术上均表现为长镜头的使用及环境声音的突显,也关注到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但“观察电影”的目的更明显地体现在强调对象文化的内部视角以及敏锐地捕捉、刻画生活细节的能力。重要的是,由于电影的方法能够特别有效地表现经验和感觉,所以观察电影“通过培育无形的感觉来唤起观众某种敏感的经验,并与人类学的情感、感觉和民族志对社会生活层面的细节产生强烈的共鸣”。(32)电影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与呈现,而更是观察者、被观察对象之间经验与感觉的回应与对话,正如斯蒂芬·泰勒提出的“唤起”而不是“表征”,(33)即是说,“观察电影”不是拍摄者简单地对文化事件的“表征”,还包括以电影的手段“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这意味着电影围绕感觉和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拍摄者、拍摄对象与观众之间的相互探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观察电影”也不仅仅是对某个文化事件的呈现和描述,而是在不同文化的电影制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以“跨文化的”方式进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协商”。(34)这是“观察电影”的摄影机以谦卑的姿态在拍摄者、拍摄对象及观众之间建立起关于“跨文化的感觉与经验的人类学知识与交流”,(35)是“关于人们可知的或是不可知的”知识的探索过程。电影传递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之感,“观察电影”因之成为“通过语境和情景发展而来的‘经验丰富’的视觉民族志”,(36)被拍摄对象、拍摄者与观众三方生产并共享人类学的知识,而最终成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所以,“观察电影”是不同文化在电影中的相遇,是“跨文化的电影”(transcultural cinema)。 总之,从“告之”到“显之”代表了“观察电影”在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电影制作方法上的重要转变,“观察电影”不但成为一种新的民族志电影拍摄方法论,而且还是关于意义、知识生产等哲学认识论的探讨。“观察电影”的意义也在于以电影为媒介生产人类学的知识,视觉以拍摄者和观看者的双重角色获得意义的理解。“观察电影”也使得主流的文字人类学开始在接受影像视觉的知识,而民族志电影也在不断地接纳人类学的视点。作为一种可行的田野工作方法,“观察电影”在电影与人类学之间也建立起良好的理解关系。(37)所以,“观察电影”不但是关于民族志电影的一种制作方式,同样也是关于以视觉为主的人类学知识的一种生产方式。 长期以来,“观察电影”这一术语的混乱局面影响了中国影视人类学及纪录片界对西方民族志电影相关新观念、新方法的认识与思考。本文梳理了“参与式观察电影”的发展阶段,认为其在诞生之初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启发和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并归纳了“观察电影”在基本方法与理论上表现出的鲜明的风格特征:在认识论上,它承认电影的主观性和拍摄者的在场;在立场上,主张拍摄者以“低调”和“谦卑”姿态与拍摄对象建立亲密关系,承认拍摄对象的故事比拍摄者的故事更重要;在拍摄内容上,以日常生活的细节为主;在电影叙事上,表现为“显之(showing)”而非“告之(telling)”;而最终的“观察电影”不仅仅是文化的“表征”,也是“唤起”。“观察电影”再次强调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观察”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以电影为手段,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以电影为媒介实践着不同文化的“相遇”。民族志电影不再仅仅只是数据资料收集和说明的工具,而应该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竞技场及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途径。 尽管很多西方人类学“观察电影”尚未被中国纪录片界及民族志电影制作者所熟知,然而,其理论建构对当代中国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及纪录片界极富启发意义。如前所述,“观察电影”质问电影的生产过程及对象,这与《写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后现代人类学论著中倡导的反思与批评精神相契合。作为某种风格化的外现形式,“观察电影”应区别于传统的“解说式”纪录片、“直接电影”的风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直接电影”理论与方法于80—90年代逐渐为中国纪录片界熟悉,在90年代中期,产生了诸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杨天乙的《老头》等社会纪实风格强烈的观察式纪录片,以及郝跃骏的《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马帮》等受电视台影响的人类学观察电影。近年来,中国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的表述方式多样化,有诸如杨蕊的《翻山》、和渊的《阿仆达的守望》等实验电影,于坚、朱晓阳的《故乡》、《滇池东岸》等人类学民族志电影,还有兰则的《牛粪》、候文涛的《苗与麻》等乡村影像作品,甚至是徐童的《算命》、范立欣的《回途列车》、周浩的《棉花》等独立纪录片制作者的最新作品。影片制作者们均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传统纪录片、民族志电影在电影主观性、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关系、电影叙事结构、作者立场等方面的不足及问题。对人类学“观察电影”的历史及理论体系的认识与借鉴,将有助于中国民族志电影及纪录片制作者,以电影为媒介探索全球化背景下异彩纷呈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及变迁。 ①参见David MacDougall,Transcultural Cinem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4;及Paul Henley,"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Methods and Media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Routledge,2004,p.109. ②不同的电影类型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观察电影”大致可以分为“解说式”、“旁观式”以及“参与式”三种类型,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观察电影”具体指的是“参与式观察电影”。 ③Paul Henley,"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Methods and Media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p.113. ④这些影片是《熟悉的地方》(Familiar Places 1980),《拍照片的人》(Photo Wallahs,1991),《开放的家》(The Opening House)。 ⑤本片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贫民窟里一对当地青年夫妇家庭生活的感人故事,荣获1984年第二届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大奖。 ⑥罗杰·桑德尔于1972年在学术期刊《视觉与声音》(Sight and Sound)上发表论文首先提出“观察电影”这一术语。在巴赞电影美学观的影响下,桑德尔关注“为得到观察的感觉而保持完整的时空”,参见Anna Grimshaw,"Rethinking Observational Cinema",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tion,2009,vol.15,pp.538-556. ⑦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Mouton de Gruyter,2003,p.99. ⑧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p.99. ⑨马凌诺夫斯基谈到初到特罗布里恩群岛之时的情况:“记得曾经多次执著然而徒劳的尝试,总是不能真正与土著人接触,也不能得到任何资料。”参见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⑩Anna Grimshaw,"From Observational Cinema to Participatory Cinema—And Back Again 7 David Macgougall and The Doon School Project",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2002,vol.18,no.1-2,p.87. (11)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p.100. (12)Judith MacDougall,"Colin Young and Running Around with a Camera",in Beate Engelbrcht(ed.)Memories of the Origins of Ethnographic Film,Peter Lang GmbH,2007,p.133. (13)Peter Loizos,Innovation in Ethnographic Film:from Innocence to Self Consciousness,1955-85,Chicago,1993,p.112. (14)David MacDougall,Transcultural Cinema,p.156. (15)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影视人类学家保罗·亨利(Paul Henley)教授的课堂讲义,2011年春。 (16)[美]罗伯特·C·艾伦《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载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17)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p.101. (18)Paul Henley,"The Origins of Observational Cinema:Conversational with Colin Young",in Beate Engelbrcht(ed.),Memories of the Origins of Ethnographic Film,Peter Lang GmbH,2007,p.154. (19)Colin Young,"MacDougall Conversations",RAIN,1982,no.50,pp.5-8. (20)Paul Henley,"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Methods and Media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p.115. (21)P.H.Gulliver,"To Live with Herds Review",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no.75,p.597. (22)David MacDougall,Transcultural Cinema,p.199. (23)让·鲁什的大部份民族志电影以宗教仪式或者具有戏剧性张力的故事为主。 (24)Paul Henley,"The Origins of Observational Cinema:Conversational with Colin Young",in Beate Engelbrcht(ed.),Memories of the Origins of Ethnographic Film,p.156. (25)Paul Henley,"Ethnographic Film:Technology,Practice and Anthropology Theory",Visual Anthropology,2000,vol.13,no.3. (26)Anna Grimshaw,The Ethnographer's Eye:Ways of Seeing on Anthropology,Cambridge,2001,p.127. (27)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p.100. (28)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p.106. (29)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in Paul Hockings(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p.103. (30)Colin Young,"MacDougall Conversations",RAIN,1982,no.50,pp.5-8. (31)David MacDougall,Transcultural Cinema,p.5. (32)Anna Grimshaw,"Teaching Visual Anthropology.Notes from the Field",Ethnos: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1,vol.66,issue 2,pp.237-258. (33)[美]史蒂芬·泰勒著、李荣荣译《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载[美]詹姆斯·克利福德、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4页。 (34)Anna Grimshaw,The Ethnographer's Eye:Ways of Seeing on Anthropology,pp.138-139. (35)Sarah Pink,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Engaging the Senses,Taylor & Francis,2006,p.17. (36)Paul Henley,"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Visu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p.110-130. (37)Sarah Pink,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Engaging the Senses.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