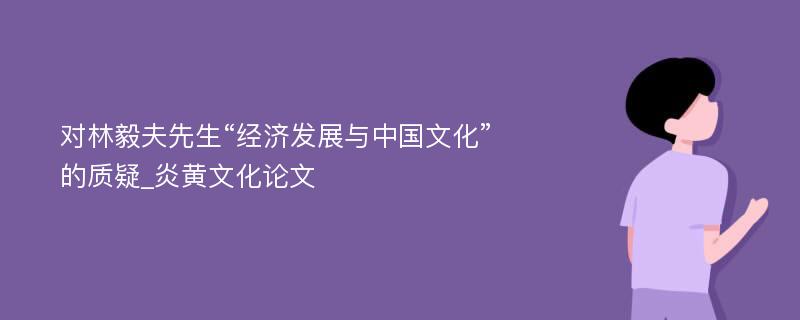
林毅夫先生“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一文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文论文,中国文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林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能说只有关系到经济活动、市场规模的地方才有“数”,而一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命运,就是一笔可以任意涂抹的烂账,可以不负历史责任地信口开河。当然,这“数”不一定是现成的数字,但却很可能是关乎中华文化的过去与未来的气数。
在信箱里发现一本新近出版的《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以下简称《走》)论文集,(注:《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第二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大论坛”论文集编委会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以下引用此书时,在行文中的括号内给出页码。)其中林毅夫先生的文章“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经》)吸引了我,因我也一直关心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的问题。阅读此文给我不少启发,比如它将文化问题与经济基础问题结合起来的讨论角度,就很不同于那些只限于思想方式和道德含义层面的文化探讨,让人有更强烈的现实感;它的一些具体的看法,比如中国文化在过去有过世界性的辉煌成就、五四反传统的不当,等,也很得我的赞同。但是,它也引起我的不少困惑,产生了不少疑问,于是信手写下,以就教于林先生与各位时贤。
为了使那些未看过林先生文章的读者对于我评议的对象有一个印象,我先简略地概括一下《经》中的观点,有不准确之处,还望林先生指正。《经》接受文化三要素的理论,即一个文化是由生产与生活的工具、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念构成的有机整体。同时,林先生主张:“但在三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组织、精神、伦理等上层建筑”。(《走》211页)所以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生产力怎么发展;上层建筑怎么演化。林先生当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首要的。在这方面,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先生有极乐观的估计:“在2030年整个中国经济规模将会赶上美国”,其后的发展势头不减,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走》214、218页)至于上层建筑演化的问题,《经》这样表述:“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随着经济基础变动,它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来看,中国的前途应该可以很乐观,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套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能不能与时俱进?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包袱、累赘?”(《走》216页)《经》在这方面的分析也是相当乐观的,因为林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么保守。“从孔子开始,其内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吸收、调整它的上层建筑。”(《走》217页)所以,这个文化也会随中国经济发展而变化调整,决不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总而言之,中国文化的前途一片光明,“到21世纪中叶,当我们的经济变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上也会变成全世界最令人羡慕的文化。”(《走》218页)
我的疑问是:首先,按照《经》,一个文化的三要素之中,经济基础或工具器物(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不就等于生产工具。)是决定性的,那么,一个文化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表明它是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应该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正在全力发展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经济基础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基础呢?从《经》看来,只能是前者,因为此文主张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策略是引进西方技术,因为这样做会比自己发明技术便宜得多。(《走》214页)其实,就是为了“国防安全”而“自己发明”的技术,比如核弹、航母,也是从西方文化的经济基础或器物中来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现在正在发展的、将来(被说成是)要领先的、“以经济基础为主导的”文化,是西方的文化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的文化呢?按《经》的基本思路,答案也只能是前者。我们正拼命跑进一个西方文化的新时代,而被认为是不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为之与时俱变、最后与之沆瀣一气的也只能是这个主宰着全球化过程的西方文化,尽管它在我们这里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带些地方色彩。林先生在文末讲他也没办法预言“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以后,中国文化到底会有哪几点特征”,(《走》218页)但他却仍然断定“到最后中国人还是会保存让国外人一接触就知道你是中国人的文化特质”,(《走》218页)这就有些一厢情愿和想当然了。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的生理基因和地理环境就保证了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了吗?这岂不违背了文化三要素的基本原则了吗?
第二,《经》面临的这个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与它实际上认定的“文化”概念有关。《经》似乎混淆了“社会发展阶段”这样一个主要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和“文化”这样一个由人群生存的诸因素所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两者当然有重要联系,但毕竟很不同。文化除了《经》说的三要素(这里面经济基础也只占一部分),还应有文化载体这一维度,尤其是文字、经典和教育传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将原始社会的打猎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商品交换相对比,认为这是文化的不同,(《走》209页)实在是过于粗糙了。从伏羲、黄帝到清朝,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化很大,我们难道就不能说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不同表现吗?再者,如果两种不同的文化,比如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印安的某种文化与澳洲土著文化,处于同样的或类似的生产与交换水准上,我们能说它们属于一个文化范畴吗?林先生在文章末的一句附带的话(“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日本人仍然各自保持其文化特质”)中,自己就否定了这种可能。但他的一大部分论述却恰恰是建立在他所否定的东西的理论前提之上的。
林先生自己也偶尔露出一些对自己理论的不安或与之不一致之处。比如上面引过的一段话(《走》216页)中,就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我们的上层建筑”等同,并因此而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注意:不是‘文化传统中的上层建筑’)会不会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包袱?”这样的问题,可见这种只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来规定和说明文化问题的方法上的困难。
另外,以美国为例来论证经济强大,自己的文化也会强大和影响增大也是不合宜的。“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在20世纪初,讲美国文化侵略其他国家的文化,会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今天连欧洲都在提防美国文化的侵略。其道理是美国经济强大,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美国社会不管在组织方式或价值取向上都出现了与其相适应的方式。比如麦当劳是为了节约时间,还有摇滚乐也是为了节约时间。”(《走》218页)但这根本无法论证作者想要说的,即“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的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走》218页)原因很简单,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所发展的是它自家的经济形态,所以(按《经》的经济决定文化的逻辑)其经济强大可以伴随文化侵略;我们这边却是在发展别人的经济形态以及组织方式,其结果(同样按照《经》文的逻辑)就是:这种经济越发展,“中国文化”就会越被削弱;如此这般,还何谈在其“基础”上的“统一”?
不管对《经》文的理论前提、“文化”概念有何异议,我还是认为它确实以一种悖谬的、反着说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作为“硬道理”的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在别的地方对它做过一些讨论,(注:张祥龙:“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改革内参》2002年第3期,15-18页。“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求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2002年9月20日出版),第1-3页。)此处不再赘述,而只想提醒一个事实,即现代化或西方化的“器物”(现代交通、市场经济、旅游设施……)发展到哪里,哪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基础和活力就受到严重威胁,如果还不是灭顶之灾的话。真正的传统文化就如同原本的自然生态,与那让麦当劳、摇滚乐大行其道的经济发展是不相配的。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正符合林先生要强调经济形态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的原意,可惜的是,《经》文并没有在应该坚持它的地方贯彻它。
此外,《经》对“儒家哲学”的解释也让我怀疑。林先生认为:“仁是一个人自己,人的行为标准其实很大程度是根据自己认为对你好的那样来行为。所以孔子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那就是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希望有成就,同时我也帮助别人有成就。仁是以自己的内心为出发来对待世界、社会。”(《走》217页)我弄不明白林先生为何要说“仁是一个人自己”,因为无论从“仁”的字形、字义和思想含义上讲,仁都要涉及两个人或更多的人。所以孔子讲“爱人”(《论语》12.22)、“克己复礼”(《论语》12.1)为仁。因此,从个人的主体好恶出发来解释孔子的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就有偏失。比如,我想去麦当劳就帮助别人也去麦当劳,我想抽烟就帮助别人也抽烟;我不喜欢听古典音乐,也就绝对不鼓励我的读中学的孩子去听古典音乐,等等,这些行为及其所依据者都说不上是仁。仁有自己的源头,这就是亲子伦常之爱,“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1.2)由此而合适、应时地扩及他人与社会,是为仁也。所以那些有损于家庭和谐,以及毫不顾及时间、地点等具体的人生处境和自然生态的普遍化、现代技术化的行为和经济形态,都不是仁道,甚至是反仁道的,不论它如何具有道德金律的外壳形式。因此,在孔子那里,仁是与“学艺”密不可分的,因为非如此就不足以将亲子之爱合适、应时地扩及他人(正名);而这“艺”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基本取向是由人伦而艺术化地达及社会,由技艺的韵律而宏大化为对天地节奏和天人合一的理解。这就决不是摇滚和那些征服、剥夺自然的技术所能比拟的了。换言之,儒家思想有自己的生命形态、成活要求和文化尊严,不是可以任人胡乱解体重装、为了某些现实的目的而加以操纵的古装偶人。《经》对“义”的理解也偏离了孟子的“义利之辨”,这里就不多加评论了。
最后,关于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因我完全不懂经济,本不该说什么,但只就《经》本身提供的信息,也还是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经》在做经济预测时,所依据的都是一些现成的条件与数字,比如引进技术的成本、技术差距的年头、人均收入的预期数字、各国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对比等等。计算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很简单和线性化,让我们这些外行人一看就懂(估计背后还有更复杂的计算和考虑,只是为了在一短文中说明问题而略去了)。但是,作者似乎只是在“生产工具”和经济规模这些“器物”层面上算账,连“劳动者”和“所有制”这样的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层面上的组织问题也未涉及,更不用说关于利益分配的公正、资源安排的合理、经济道德的效应、生态环境的制约、国际环境的变化等等方面的问题了;而这些“组织的”和“价值观念”的问题照理不应该与经济的发展无根本关联。使用同样的技术和器物,在不同的组织与价值观的体系中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后果,就如同《经》所提及的甲午海战所反映出的情况。那时中日的军事装备是中强日弱,但按日本海军武官的观察,中方一边的组织与价值精神不如日方,所以他预测日方可胜,因为“这样一个没有秩序、现代精神的军队必败无疑”。(《走》210注(注:《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第二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大论坛”论文集编委会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以下引用此书时,在行文中的括号内给出页码。))说得不错,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考虑问题方式不应该完全不适用于经济问题。中国如果不加速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的组织体制和价值取向,恐怕那些数字所计算的将不过是些丁汝昌手下的坚船利炮而已。我这里也绝没有主张中国在体制和价值观上要“照搬西方准则”的意思,但这似乎毕竟是些躲不开的问题,不能说等经济发展了再考虑,因为它们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瓶颈所在。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整个问题,即:如果高速持续地发展经济就一定导致“照搬西方准则”、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考虑不那么高速地发展经济,而是去追求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这倒很有可能是更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智慧。当然,这样一来,就要将《经》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性质的理论做某种颠倒了。(注:虽然林先生并没有完全否认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其中包含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限于是否能跟上经济发展,从而不成为其绊脚石的程度。所以我假定《经》里面没有让上层建筑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和整个文化性质的理论可能。)
我很少写评论,这次被林先生的取向高远的文章唤起了这么多的疑问与思考,实在是因为这个“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太重要了,不由人不为之萦思牵挂。对于这种与祖先遗产和子孙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不能只采取“先干了再说”的态度,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未来的文化特征“在发展过程中,由社会竞争选择出来”,(《走》218页)而是应该慎之又慎,“敬之!敬之!”(《诗·周颂·敬之》),从长计议,做到心中有数。不能说只有关系到经济活动、市场规模的地方才有“数”,而一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命运,就是一笔可以任意涂抹的烂账,可以不负历史责任地信口开河。当然,这“数”不一定是现成的数字,但却很可能是关乎中华文化的过去与未来的气数。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论文; 经济论文; 林毅夫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