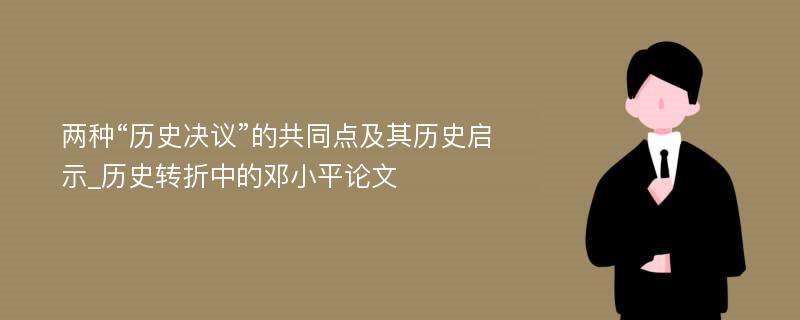
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点及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共同点论文,决议论文,启示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3—0043—04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虽各不相同,但都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重大的作用,有许多共同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 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特点
1.都是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历史地位展开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全面抗战进入新阶段,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严峻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及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思想并不统一。宗派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造活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学习与时局》等。并于1941年秋着手起草《历史草案》,总结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在他的亲自倡导下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了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之前,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要理论虽已提出,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整体上说,还不够成熟,尤其是没有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真正认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看法不一。如果这样下去,将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历史决议》的形成并通过,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1](P955)同时, 《决议》在高度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而勾画出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的理论成果。因此,《决议》的形成与通过是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先导。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总路线的确立和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全国出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可喜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与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极左思潮依然存在,一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抵触;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少数人借拨乱反正之机,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极端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闹事。在党内和理论界,也有一些人思想动摇,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历史决议》。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9次谈话, 提出了《决议》的总的写作的指导思想。他说《决议》的中心意思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要做到“争取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决议到此基本结束”[2](P292)。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六个方面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因此,《决议》的通过,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2.都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主要批判对象
两个《决议》都对中共党史上持续时间长、危害大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在分析批判中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1945年的《决议》,首先,主要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做出了详细结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着重批判王明教条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其次,深刻分析了王明以及第一、二次“左”的错误产生的根源,认为“左”倾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1981年的《决议》也是以“左”倾错误为批判对象的。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二个《决议》出台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影响。因为在粉碎“四人帮”后,尽管我们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精神枷锁没有彻底解除,拨乱反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就《决议》内容来说,则是在批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中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地位。首先,毫不隐讳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其次,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性质。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P34,30)。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3](P28)。最后,《决议》深刻分析了“文化大革命”错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尤其是指出了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3](P38~39)但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我们的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P298)。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错误。”[4](P300 )这样就把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统一起来了。
3.都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这两个《历史决议》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在主持起草的工作中,他们都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使《决议》起到了团结党心民心的作用。
第一,向前看的原则。这是《决议》能起到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作用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主持《决议》的起草时说:“弄清楚哪些政策或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1](P282)此外, 在关于《决议》是交由党代表会议还是代表大会审议的问题上,也充分反映了向前看和利于今后斗争的原则。毛泽东说:“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5](P323)
邓小平则说得更清楚: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分清是非、做出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算谁的帐,也不是为了摆平谁的恩怨,“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4](P147)。
第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在两个《决议》的起草中都贯穿着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毛泽东在主持《决议》的起草时多次强调说:“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1](P938 )如对于党的六大、上海临时中央是否合法、党内的宗派问题等当时大家争论较多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他说:“我认为(党内宗派)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1](P95)《决议》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到了原先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致拥护。博古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并表示: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5](P321 )犯错误的同志尚且能够这样看待《决议》的作用,可见它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而它的说服力则来源于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科学性和高度政治性的统一使它赢得了全党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且进一步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整套方法,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关键问题。首先,邓小平从毛泽东与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关系,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功过具体比较中,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因此,这同他晚年的错误相比较,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因为,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也并没有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况且,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积极因素;而他晚年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4](P298)。 我们纠正他晚年的错误所依据的有力武器正是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很显然,毛泽东功与过的分量和历史影响是不同的。对毛泽东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符合实际,恰如其分,在任何时候都经得起历史和人心的检验。其次,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加以严格的区别。一方面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又鲜明地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二者存在原则上的区别。邓小平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而且也坚持了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再次,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党的领导集体承担,以确保对毛泽东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指出:“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的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4](P296)并且主动承担了部分责任。 这一方面反映了邓小平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大公无私、勇于承担责任和勇于修正错误的崇高品质。最后,邓小平反对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问题上,坚持从社会历史环境的主客观条件来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4] (P299~300)因此,他强调:“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 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并说:“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5](P172)
第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入、认识能力的提高、认识手段的扩展,以及历史材料的开掘而不断深入、丰富和全面,逐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因此,人们对既往的历史,在时空上越接近,认识的局限性就越大。所以,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既本着弄清大是大非,又不过于纠缠历史的细节,它符合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当有人建议在决议草案中要具体写清楚“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损失时,毛泽东则认为“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 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5](P314~315)。这反映了宜粗不宜细的精神。
邓小平则把“宜粗不宜细”作为他主持起草决议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4](P294,148)要想在短时期内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 勉强解决还可能造成新的错案。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会成为错误”,邓小平强调“粗一点”的精神实质。
二 几点启示
1.《历史决议》为我们高举旗帜,提供了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思想武器。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全党接受,经历了一个过程,延安整风运动及其作为它的主要成果的《历史决议》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后召开的党的七大明确地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我们党就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很快取得了民族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新中国;建国后,又在这一旗帜的指引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尽管这期间我们党有过一些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这正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结果。
粉碎“四人帮”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在我们举什么旗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混乱,有人主张搞“两个凡是”,有人主张搞历史虚无主义,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亦即如何正确处理旗帜问题又摆到了人们的面前。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通过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制定《历史决议》解决了旗帜问题,为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建设扫清了思想障碍。由此可见,毛泽东邓小平是科学处理旗帜问题的典范,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2.说明通过作《历史决议》来反“左”、纠“左”,是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完成拨乱反正的关键一环。
在两个《决议》制定以前,我们党都曾对“左”倾错误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或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带来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党虽然在逐步克服“左”倾思想的束缚,但人们的思想并不统一,“左”的东西仍然以它特有的方式干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说明,一种错误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而通过《历史决议》的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来总结历史,使人们的认识达到统一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工作进而推动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团结党心民心的关键。
马克思指出:“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越就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6](P532)从实际出发, 掌握客观真实的情况,排除主观随意性是我们评价历史上大是大非的根本方法。毛泽东邓小平在主持《决议》起草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着眼于当前的奋斗目标,一切着眼于大局,不纠缠于个人的情感与恩怨的宽广眼界和可贵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也是巨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来源。
总之,两个《历史决议》无论就它的精神实质还是就它形成的方法来说,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高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乃至史学本身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1999—11—15
标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