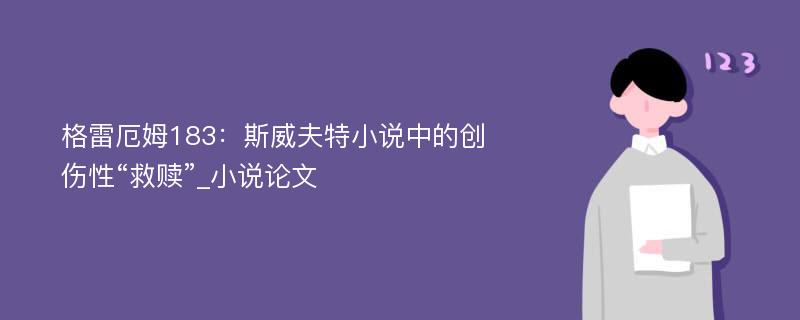
格雷厄姆#183;斯威夫特小说《从此以后》中的创伤“救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伤论文,格雷论文,斯威夫特论文,小说论文,救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此以后》是当代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于199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出版伊始评论界便针对它是否抄袭了1990年英国“布克奖”得主拜厄特的《占有》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莱文森暗示《从此以后》多处借鉴了《占有》的情节:“情节的相似……十分突出:对于新发现的维多利亚时代手稿的争夺,对学术秃鹰的抗争,对美国金钱政治的讽刺”。①事实上,无论是叙事手法的使用,还是主题的讨论,《从此以后》与当代英国文学的很多作品都有类似之处,许多评论家都指出了小说中明显引用、暗示或模仿的文本。②该作品与英国同时代小说创作之间的联系也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从此以后》与《法国中尉的女人》都描写了19世纪中期莱姆·里吉斯的场景,而且两部小说都直接地提到了莱尔、达尔文和玛丽·安妮这些在多赛特镇上空悬崖间发现史前遗骨的历史人物。哈里斯认为“斯威夫特在文体上超越了福尔斯。斯威夫特更加有才智、多变和高度的文学性”,③而斯坦博格认为此部作品是“一部约翰·福尔斯式的关于爱与信仰的叙事……只是缺少了福尔斯那强烈的叙事意识和情感共鸣”。④《从此以后》与英国文学的这种互文关系并不是小说抄袭的证据,它体现了斯威夫特小说讨论的是英国文学中人们普遍和迫切关注的一些问题。
在《从此以后》中,作家思考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尤其是与创伤历史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传统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纷纷指出历史的“叙事性”和“虚构性”本质,如“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⑤“仅仅通过观察其结构而不必探求其内容的本质,我们就可以知道,历史话语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阐述的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虚构的阐述”。⑥然而,将历史视为一种建构的观点在面对历史中的创伤时,面临着掩盖真实的创伤经验并使创伤在历史叙事中消失的危险。拉凯布拉在《再现大屠杀》中即指出了回避或否认创伤历史时常常使用的叙事方式:回避或否认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在心理学意义上的“复杂和微妙的回避[创伤]的模式”,尤其体现在那些“基于某种目的而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从而建构一种‘救赎’式的或拜物式(fetishistic)的叙事,并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些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⑦《从此以后》的叙述者比尔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面对历史的创伤时,就曾多次借助文学叙事、浪漫传奇叙事和历史叙事以期获得创伤的“救赎”。
《从此以后》在叙事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比尔在展开叙述之时的境况:他描述了近期家庭中发生的变故——在不到18个月内,母亲、妻子和继父相继过世;对于目前生活现状的思考——他依靠继父山姆的捐资而获得了大学研究员之席位,对当前的学术环境他有颇多议论。对现在的叙述引发了比尔的第二层叙事——过去生活的片段式回忆,他希望在自己的叙述中探究使他的生活走向崩溃的根源。在小说开篇比尔对读者说:“重要的、到死(原谅我用这个词)都要知道的首先是什么让我上演了自己死亡的一幕。……也许下述记录能最终解释一切,也许他们能给我一个解释”。⑧比尔的追述涉及了父亲的自杀、母亲的背叛、自己与继父的关系以及自己与妻子鲁丝的爱情婚姻生活。第三层叙事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整章整段地插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祖先马修·皮尔斯的日记,他企图通过对历史的重新编纂解释自己现在遇到的困境。在比尔的叙事中,读者可以发现构成其整个叙事的根源是他九岁时父亲的突然自杀。父亲的死对比尔来说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比尔一直感到自己在父亲的自杀中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父亲在世时比尔已经发现了母亲与山姆的通奸行为,当时比尔既没有制止母亲,也没有告知父亲。他推测父亲的自杀是因为无法接受妻子的背叛,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把父亲的死归咎为自己未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阻止悲剧的发生。
比尔对父亲之死的片面解释实际上是在把创伤经验简化为一次过失行为,从而假定了创伤“救赎”的可能。救赎原本是一个宗教词汇,在圣经旧约中先知和使徒们使用赎罪法解释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极度贫穷,因此出卖了我们的产业,从而成为了罪的奴隶,但神已通过他儿子的死亡为我们赎回了罪,当耶稣基督来临时他会恢复我们的产业,并给我们天国里的位置。救赎中隐含的意义是人的原罪和苦难得以最终解脱的希望。创伤研究基于基督教中的救赎涵义指出了创伤历史的叙事中一种“救赎”的叙事,它“通过编织目的论的故事,尤其是通过渐进发展的过程,突出地展示在叙事中可以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⑨创伤研究在分析“救赎”叙事时曾指出,“基督教和俄狄浦斯的故事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堕落和原罪)……它们把失落或者死亡归咎于一些罪过或错误,认为这些罪过和错误可以在救赎或拯救中被偿还”。⑩但是,在创伤经验中,创伤者真正感受到的是“迷惑、焦虑”,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悲伤绝境中”,创伤事件的强迫重复使受创者割断了与现实或未来的联系,使他们走不出创伤事件所带来的阴影。(11)在《从此以后》中,父亲的自杀身亡对幼年的比尔来说是一次创伤性的经历。比尔回忆他九岁的那一天,母亲以委婉的方式告诉他,父亲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吞枪自尽了,这突如其来的悲惨事件对于少年比尔来说是“太出乎意料……无法完整察知,因此无法为意识所掌握”的事情,(12)他回忆那时对于母亲的话他“好像只是听到了字面上的几个字,而几乎不知其意”,因为“一些言论需要时间进入大脑”(20),而创伤研究也证实了创伤“一开始无法察知”、“无法同化”(13)的性质。比尔在叙述中坦陈:“我是指随着父亲的死,我的世界从此分崩离析”。(114)为了拒绝创伤的实际影响,比尔在叙述中把创伤理解为一次行为的过失、把创伤的影响简化为关爱和父亲形象的失落,因此比尔在自己的历史叙事中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的“救赎”叙事,希望在叙事中弥补自己的罪责,寻回失落的一切。
一 文学叙事的“救赎”
比尔在自己人生历史的叙事中通过援引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对死亡等相关创伤事件的描述,把自己的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情节相比照,认为文学中隐含的救赎希望等同于自己创伤经验救赎的可能。比尔11岁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在书本中寻找安慰”(64),文学为他打开了“另一个可以依靠的世界”(69)。文学最触动他的是作品在最表层流露的意义,是作品“最简单、最老套的语言”但却触动人的心灵,即使是“最陈旧的过时的(和最难以忍受的)的思想——那些我们都有的想法”,当它们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时,都“像是救赎的良药(redeeming balm)”(71)。比尔引用了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一段诗以做例证:
甚至这就是时间,它带走了
我们的青春、欢乐和所有一切,
留下的只是老去的岁月和尘埃;
等我们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他就把我们一生的掌故
埋入了黑暗寂静的坟墓。
在比尔看来,虽然诗中表达的死亡主题是人们早已熟悉的,但是他却被诗歌在字句间传达的“冷静”、 “庄重”和“平衡”深深吸引,他认为诗歌向他传达了“黑暗与光明,生与死和谐共存”的平衡世界观,在诗歌中他似乎寻回了在父亲死后自己的世界已失去的平衡:“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I rest my case)。(71)
简单比较比尔的引文和诗歌的原文就可以发现比尔对原文的刻意省略和改动。从比尔的引文可以看出,他希望自己的叙事也能具有诗歌中传达的平衡,并以此抹去父亲的死在自己心中留下的伤痕。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比较比尔的叙事与原诗作却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比尔的叙事包括他所引用的诗章作为原文本,雷利的原诗作为潜文本,读者可以发现在比尔所引用的六行诗后有两行被比尔省略了,而且在第六行诗的结尾处前文本使用的是分号,而比尔的文本使用的是句号。被省略的两行是:“但是从这块土地、这个墓穴、这片尘土中/我相信上帝会将我扶起”。比尔以句号的形式省略了最后两行,显示了他拒绝或者不相信上帝的救赎,而只依赖文学的救赎作用。
比尔利用文学建构自己的人生叙事突出体现在他对《哈姆雷特》情节的依赖。比尔称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他着迷的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比尔把自己比作哈姆雷特,把母亲塞尔维亚和继父山姆视作葛忒露德和克劳迪斯,他们在父亲死后不久随即结合,因此比尔心里笃定是母亲和继父间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在比尔看来,父亲死后为他伸张正义可以减少自己心中的负罪感,从而抚平内心的创伤,《哈姆雷特》剧中隐含的救赎希望是比尔叙事依赖的模版。
比尔在叙事中以《哈姆雷特》的情节结构作为自己的原型,以此赋予创伤新的意义。《哈姆雷特》为比尔的叙事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在比尔的叙事与哈姆雷特剧本的相互影射之间,比尔设定了人生的意义,看到了完成复仇,生活回复平静的希望。《哈姆雷特》是比尔叙事的潜文本,(14)其中的人物、情节结构和主题等都在比尔的叙事中发生了“凝缩与位移”。比尔在叙事中引用《哈姆雷特》剧中的人物和情节结构是因为该剧中隐含的救赎主题。在《哈姆雷特》的诸多评论中,评论者已经点出了此剧中暗含救赎的希望。(15)哈姆雷特复仇的成功,使邪恶被清剿,在父王死后陷入混乱的世界被赋予了新的秩序和意义:在第一幕第四场结尾处,“玛塞勒斯:丹麦的国家里怕有点乌七八糟。霍拉旭:天会照顾的”(1.4.90-91)。在剧中,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成为上天指引的象征,引领着哈姆雷特最终斩除了罪恶的克劳迪斯,虽然哈姆雷特也献身了,但霍拉旭赞颂道:“夜安,可爱的王子!成群的天使们唱歌来送你安息吧!”(5.2.333)。在哈剧的暗示下,比尔也计划着对继父山姆的复仇行动,虽然像哈姆雷特一样比尔对如何实施自己的计划一直踌躇不定,但这个计划本身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意义所在:“正是这个复仇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攫住了我”,而山姆的突然死亡“剥夺了我人生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划去了我人生的一段情节”(6)。比尔对哈剧复仇情节的依赖暗示了他想要在叙事中使创伤边缘化,把自己创伤后的生活简化成一出复仇剧,并为自己实际上破碎的生活赋予悲剧的意义。
在现在时态的叙事中,比尔坦言自己过去依赖《哈姆雷特》的情节寻求人生“救赎”的失败,而他的失败使他依赖哈剧而建构的叙事更加具有讽刺效果。使比尔的哈姆雷特情节失去立足点的是比尔发现并非母亲与山姆的行为导致了父亲的自杀,而且自己的父亲有可能根本不是亲生父亲。比尔在现在的叙事中嘲讽了过去的自己:在母亲去世不久,山姆曾单独前往比尔在大学中的住所,比尔在窗前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山姆,心理仍然勾画着《哈姆雷特》中的剧情:
看看,我心里琢磨着,多么令人惊讶啊,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他来道歉了;来个全盘托出:不是要求我到他那去,而是他来卑微地敲我的门。我母亲去世了。他有时间好好考虑考虑了。他在这(克劳迪斯在祈祷)为我父亲的死做出补偿。(154)
事实上,山姆的此次拜访只是为了告诉比尔其父亲的真实身份,而且将父亲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可能是母亲告诉了父亲比尔不是他的儿子。突如其来的真相在事实上粉碎了比尔赋予自己的哈姆雷特身份,但是他仍然坚称:“我就是比尔·昂文(那么,我自己为自己断言),我就是丹麦人哈姆雷特”。(160)比尔的这句话使人联想到艾略特的名篇《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普鲁弗洛克的宣言:“不!我并非哈姆雷特王子,当也当不成”。评论者大都指出了比尔与普鲁弗洛克的相似性,(16)普鲁弗洛克宣称自己不是哈姆雷特的那一章节恰恰是比尔形象的写照:
不!我并非哈姆雷特王子,当也当不成;
我只是个侍从爵士,为王家出行,
铺排显赫的场面,或为王子出主意,
就够好的了;无非是顺手的工具,
服服帖帖,巴不得有点用途,
细致,周详,处处小心翼翼;
满口高谈阔论,但有点愚鲁;
有时候,老实说,显得近乎可笑,
有时候,几乎是个丑角。
(查良铮译)
比尔一生也没有实施他所谓的复仇计划,在年届50之时,他又被告知自己意欲为之复仇的父亲与自己可能毫无血缘关系,而且父亲自杀的原因也变得扑朔迷离。比尔已经认识到文学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象”,他的文学“救赎”之路最终也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二 浪漫传奇叙事的“救赎”
为叙事渲染童话的色彩以规避创伤的伤害在斯威夫特的《洼地》中也曾有明显的展现,在《从此以后》中比尔更加有意识地建构浪漫传奇叙事,希望以浪漫的爱情故事弥补自己幼年爱的缺失,并为自己的人生渲染传奇色彩,从而粉饰历史创伤事件、规避创伤的影响,并反思了此种“救赎”叙事的意义。
浪漫传奇(romance)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广义上是指“一种虚构作品,它的内容涉及冒险、夸张的人物(extravagant characters)、陌生或奇异的场所、神秘或超自然的事件,英雄的或不可思议的功绩、或者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它与小说的不同在于它强调“纯粹的想象”。(17)一般认为浪漫传奇文学起源于中世纪:从11世纪早期到12世纪晚期,西欧似乎已经在生活的各个部门都经历了一场改造,……武士们开始以骑士的面目出现,……在显贵云集的宫廷里,贵妇人们要求得到温文尔雅的新礼遇,尤其是从爱慕者那儿得到“优雅爱情”(courtly love)。所有的艺术都发展了各自的新形式来满足该时期的优雅精致的奢侈趣味。哥特式建筑取代了笨重的罗马式建筑,骑士的浪漫传奇取代了旧的英雄史诗……(18)
从那时起浪漫传奇文学经历了各个时期的发展,关于浪漫传奇的界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代浪漫传奇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冒险故事(侦探小说和间谍惊险读物)和爱情故事或称之为大众传奇”。(19)《从此以后》中比尔反复使用“浪漫传奇”一词形容一些事件和经历,既是指涉了中世纪“浪漫传奇”中隐含的骑士精神和优雅爱情,也意指通俗爱情故事中常常编织的童话般的爱情传奇。“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传奇是最接近如愿以偿的梦幻的”,(20)无论是在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中还是当代的爱情传奇故事中,创伤与苦难都仅仅以一种考验的形式展现出来,都只是实现完美结局所必经的一个过程。“传奇模式展现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传奇中,男人勇武豪侠,女人花容月貌,歹徒十恶不赦,而人们平常生活中遭受的挫折、窘迫和凶吉难卜则都成了小事一桩”。(21)比尔以浪漫传奇的叙事再现自己的历史是希望在这样的叙事中淡化创伤的意义,为自己的人生寻求完满的结局。
比尔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从出生那一刻起即与浪漫传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比尔认为自己生来就具备“某种童话般的气质”,他生于1936年12月,在他出生的那一周,爱美人胜于江山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为了迎娶自己的爱人而逊位了,这个在当时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逊位危机”在比尔看来“与其说是一场危机,不如说是欢迎浪漫传奇的闯入,它使人们很高兴地暂时忘掉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一切为了爱” (57)。比尔以自己的特殊生辰解释自己对浪漫爱情的倾向,他以一幕幕浪漫叙事建构自己的人生历史。
巴黎是比尔父亲去世的地方,作为创伤的发源地,他在叙述中承认在离开巴黎40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13),为了规避那时发生的创伤事件,对于那一段时间的叙事比尔尽可能地赋予巴黎和那时的生活浪漫童话的色彩,创伤在他的叙事中再次被边缘化。他承认“我们只看到我们选择去看的,我们只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13),比尔看到的巴黎是“童话之城”,有着“令人着魔的街道和永恒的受到恩准的幸福气息(eternal air of licensed felicity)”(57),母亲带他在巴黎看的第一部歌剧是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在幼小的比尔眼中,歌剧“第一幕中鲁道夫身居的阁楼窗户,还有在第四幕中,当可怜的咪咪在悦耳的旋律中奄奄一息,舞台上所绘制的巴黎屋顶的景色在现实中的巴黎都可以看到”,他感到“现实和浪漫传奇是如此紧密得联系在一起”(13)。使比尔分不清现实与传奇之间差别的不仅仅是歌剧中的舞台布景,剧中浪漫忧伤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他叙事的原型。歌剧呈现了1830年的巴黎,几个年青的流浪艺术家生活窘迫却怀着同样的希望,歌颂爱情、追求自由,他们生活在拉丁区幽暗的小巷陋室中,其中诗人鲁道夫与绣花女咪咪的爱情是剧中的主要情节,然而理想的爱情却敌不过现实的残酷,穷困的艺术家们最终未能拯救咪咪的生命,歌剧在咪咪的阖然长逝中结束,但咪咪对爱情的执着却令人难忘。这种波希米亚式的爱情被比尔融入了自己的叙事中,歌剧情节成为比尔叙述中的潜文本。在比尔对巴黎生活的回忆中,他特别追述了自己与一群芭蕾舞演员间的浪漫遭遇,“如果《波希米亚人》中的巴黎只是以幻象的形式出现,那么我徒步从公寓到学校,其间我闲庭信步并非无所事事,……现在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证明那不是个幻象,歌剧中的巴黎在现实中被真实地活生生地再现”。(19)比尔认为他自己在巴黎上演的浪漫爱情不会以悲剧收场,他在巴黎人行道上,透过高高明亮的橱窗看到的是“一幅真实的景象”——三五位芭蕾舞演员沿着靠墙的肋木伸展着各种芭蕾动作,比尔被这幅景象“迷住了”(19)。比尔接着叙述了自己无数次地在这个窗边驻足,直到有一天他在巴黎街头露天的咖啡吧邂逅了这些芭蕾舞演员。巴黎、露天咖啡吧、芭蕾舞演员这些细节都透露了叙述者比尔在营造一种浪漫的气息,他在无形中赋予了自己波希米亚人的气质。(22)巴黎在他心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文明的最高目的就是在无用的事情上钟情完美,如芭蕾舞女、咖啡厅的闲谈、普契尼的歌剧、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真丝内衣、香水、法式蛋糕、枝形吊灯、音乐厅内当灯光淡去时魔力般的安静……还有浪漫的爱情”。(20)比尔在叙事中模仿了爱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见钟情、浪漫邂逅等情节,引用了《波希米亚人》的剧本并在叙述中质疑剧中的一些场景,这种有意识的引用或暗示是在利用互文间的逻辑预设,在潜文本的基础上引导读者预设自己的叙事,读者遵循比尔的叙事会期待着比尔与芭蕾舞演员之间的浪漫故事。在这种叙事模式中,比尔在自己倾心于芭蕾舞女的那段时间内,插入父亲自尽的事件。父亲去世后,比尔和母亲离开了巴黎,他在叙事中感慨道,如果父亲没有出事,当时的他可能已经成为塞纳河畔“伟大的艺术家”、“花花公子”,“过着赖利(23)一样的生活”(57-58)。比尔认为当他返回英国时,他“不是因为父亲的死而悲伤”,而是为了“他倾慕的芭蕾舞女孩”,为自己没有开始的爱情哀伤。因为不愿去想起吞枪自尽的父亲,比尔用浪漫传奇的叙事方式粉饰了难以面对的创伤事件。
创伤对比尔的影响持续了他的一生,即使离开了巴黎回到了英国,比尔仍需要浪漫的爱情故事支撑“自己已经坍塌的世界”(114)。比尔在伦敦继续着波希米亚式的浪漫爱情,他在文学中读到的一些浪漫传奇故事也为他的叙事提供了话语空间。比尔把青年时代的自己描述成一个热爱文学的穷学生,他离开了母亲和继父的家,“住在卡姆登一所公寓的阁楼内,仅仅依靠诗歌的滋养和母亲不定期偷偷寄来的支票”,(72)以及夜间在苏霍区(Soho)一家“蓝月亮酒吧”做些杂工而生活,在这家酒吧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鲁丝。作为回顾性叙事,比尔为他与鲁丝的相遇相爱都蒙上了浪漫的色彩。他坚持认为,一切结果的发生都源于他对文学诗歌的热爱,对那段往事的叙述中,比尔从第一人称突然转入第三人称叙事,在时态上从过去时转换成现在时,在叙述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距离:“我现在看到了他,那个从前的未成形的我。那个幽灵式的、史前的人”。(72)这种叙事视角和时态的转换使比尔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叙述自己的过去,赋予自己叙事以虚构的权威,刻意使自己的叙事更接近浪漫传奇故事。他以浪漫叙事的模式首先描述了男主人公的特质:
他是自由的,他是骄傲的。他具有哈姆雷特式的自负。……他是勤奋的,他是青涩的。……但是诗歌即将成为现实的日子正在走来。那些相思的游吟诗人的叹息、狂喜、恳求都不再看似痴心妄想。所有那些可疑的、杜撰的情人、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和令人着迷的月亮女神、朱丽叶和牧羊女都不再好像是月光下的幻影、纸本间的美梦。(72)
比尔以这种方式开始他与鲁丝爱情的叙事,他在叙述中强调了青年比尔具有的浪漫秉性,使读者预设了一个浪漫爱情的发生。他刻意使自己的叙事陷入浪漫传奇叙事的成规中。虽然对于什么是浪漫传奇的叙事成规就像什么是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很难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实主义’指某种阅读经验”,读者阅读浪漫小说的经验同样也帮助读者辨别浪漫传奇叙事,具有一些“固定的类型”,如“用烂了的场景或老一套的角色”,不注重“事出有因”,经常表现“机遇、命运和天命”对情节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经常成为浪漫传奇叙事“最容易界定”的特点。(24)比尔在叙事中借用了浪漫叙事的这些特点,他首先强调了他的爱情故事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发生的”(72),他用大幅的笔墨渲染了他与鲁丝之间的机缘巧合:鲁丝第一次作为女主角在酒吧登台是由于原先的主角突然生病,面对在台上的鲁丝,比尔感到自己像“中了魔法”一样(75),一见钟情的情节由此上演。比尔与鲁丝爱情的开始是在一个仲夏的夜晚(比尔在叙述中暗指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一次突然袭来的暴雨,使他有机会和鲁丝同坐一辆出租车,而就是在这辆车上他亲吻了身边的鲁丝,在故事叙述的结尾,比尔还特意总结道:“事情注定要发生,有情人终成眷属”。(78)在自己的浪漫传奇叙事中,比尔觉得“魔杖挥动,我忘记了自己是哈姆雷特。……世界不再是疲倦、腐朽、单调和无意义的了”(78),他认为是浪漫传奇安抚了他受创伤的心灵。
比尔在自己的浪漫传奇叙事中套用童话故事常有的结尾“从此以后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78)。小说的题目《从此以后》即是摘自童话故事的结尾,这句话在比尔叙事中的频繁引用体现了卡勒所说的一种类型的互文运作——修辞或文学性预设(rhetorical or literary presupposition)。卡勒举例简析何为修辞或文学性预设:“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生了个女儿。”这句话几乎没有逻辑预设,但却有丰富的文学预设。它从语用角度把将要讲的故事与一系列其它故事联系起来,与一种文类的写作手法联系起来,因此也要求读者对它采取某种态度(期待或理解)。(25)“从此以后快乐地生活……”这句话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它使读者在阅读中期待比尔的人生叙事也如同一出浪漫的爱情剧一般,但是比尔对当下生活的叙事构成了对浪漫传奇叙事的反讽。在鲁丝成名之后,比尔生活在鲁丝的阴影下,他试图模仿传奇中的骑士“作为一名后台管理者始终等待着女主角的亲吻;……一个眩目娱乐业中卑微的奴役”(75)享受与女主角之间的优雅爱情。比尔在叙述中反观了自己建构的浪漫传奇人生,他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他只不过是“舞台上的鳏夫”、“一个舞台上带绿帽子的丈夫”(111),尽管他不愿意面对,尽管他坚持“你不知道就不会受伤害”的信条,但是妻子不忠的事实还是会呈现在他眼前。浪漫的爱情叙事无法面对残酷现实的检验,在现实中这些成规化的传奇世界就崩溃了,比尔最终认识到浪漫的爱情叙事并不能拯救他心中的创伤,幻象的破灭只是让他越来越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他在叙述中坦陈,“浪漫的爱情,都是捏造出来的,都是诗人杜撰的”。(111)
三 历史叙事的“救赎”
历史叙事是比尔寻求的第三条“救赎”之路。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历史以叙事的方式粉饰规避创伤在《洼地》中也有着清晰的呈现,评论者对《洼地》的讨论也大都涉及了这一点,但是对《从此以后》中比尔以历史叙事规避创伤的问题却鲜有论述。
父亲的死是比尔不愿触及的创伤事件,所有与父亲有关的事件都在比尔的记忆中被有意识地抑制了,“我无法轻易地唤起我的父亲,我没有依据,也许是因为曾经发生的那件事吧”,(14)“我开始呼唤一个我从不认识的父亲形象:高贵、善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63)比尔幼年时在心中构建的父亲形象与他以哈姆雷特的情节建构自己的人生息息相关,但是在他的母亲死后,继父山姆又向他揭示了亲生父亲的身份,比尔自己召唤的“先王鬼魂”也随之破碎了。比尔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祖先马修·皮尔斯,在母亲死后他得到了马修生前的日记和他死前给前妻伊丽莎白的一封信。面对这些历史资料,比尔拒绝将其交给大学里的历史学者,而是决定自己编辑出书,不是作为“学术研究”,而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他要在自己的叙事中再现马修曾经的生活, “这是一项巨大的自以为是的工程:从一个人留下的简要碎片里试图找出他过去实实在在的生活”,“就让马修成为我的创造吧”。(90)比尔希望建构虚构的历史叙事规避自己的创伤。
有关马修的日记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评论界大都认为,比尔在以19世纪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再现马修的历史时,希望在这种传统的历史再现中寻求稳定的意义,或以此建构自己的主体性,而其在叙事中逐渐感知的叙事主观性,使其对真实、稳定、意义和主体性的追寻都变得问题化。(26)然而,比尔的叙述却明确地告知读者,他在建构马修的历史时就知道自己“不是在编纂历史”,而是在“创造”,他依靠的不是传统历史叙事中隐含的“总体性”(totalization)和“统一”,比尔事实上是在利用历史叙事的主观性粉饰历史中的创伤。马修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如果比尔在马修的历史叙事中可以规避创伤,那么他也可以在自己的历史叙事中逃避创伤的影响。
比尔在马修的日记中看到与自己相似的经历,马修也曾为亲人的死而陷入了自我的危机中,也曾竭力为创伤寻求救赎之路。马修的日记跨越了1854到1860的六年时间,即从他的儿子菲力克斯夭折到他婚姻破碎的一段历程,其间也回忆了他在1844年偶遇鱼龙化石并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但是儿子的夭折使他的信仰彻底地崩溃。他选择了六年伪信仰(make-belief)的生活,希望与妻子和家人的幸福生活成为创伤救赎的良药,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向牧师岳父坦白了自己的宗教怀疑而结束了自己的婚姻。
比尔在自己的叙事中试图重新建构马修的生活,尤其是马修的浪漫爱情和幸福婚姻是如何帮助马修摆脱内心的苦痛。他以文学叙事的手法(27)虚构了马修的形象和气质,他一边告诉读者他的描述是“没有根据的”,他“丝毫不清楚马修长得什么样子”,同时又声称“我看到他是一个精力充沛、面容冷静的年轻人”,他以这种元小说的叙事手法(28)使读者也参与到他对历史的虚构中,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形象:尤其突出了其“成熟”(maturity)和“稳重”(stability),“在本质上对幸福、至少是满足的强烈的包容力”;(98)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是19世纪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淑女形象。(29)而且,在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情况下,比尔细致地叙述了马修与伊丽莎白相识之前和如何相识的过程,并不时地告诉读者“这些都是我编的”(109)。比尔的叙事既唤起读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注意,又使读者想起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及同时代类似的叙事作品,尤其是小说也涉及了莱姆·里吉斯和当地的化石。福尔斯的小说叙述者在小说中也曾向读者宣称:“我讲的故事都是想象的。我所创造的人物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30)比尔在叙事中的这种互文运作“唤起人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他的叙事“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31)他以维多利亚小说的典型情节开始自己的叙事,想象他们的相识到最后马修和伊丽莎白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婚礼当天马修的父亲送给他们一座自己亲自制作的钟,钟上的题词“爱战胜一切”(Amor Vincit Omnia,Love Conquers All)由伊丽莎白的父亲摘自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他希望他叙述的马修的故事能像小说的情节发展一样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马修和伊丽莎白“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夭折的儿子菲力克斯之前,他们有约翰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孩子,在菲力克斯之后他们还有露茜,幸福的生活使马修忘却自己信仰的危机和丧子之痛,比尔希望马修的创伤在他的叙事中得到救赎。
比尔所使用的元小说叙事又在提醒读者关注他虚构故事的意义。比尔在叙述马修的历史时常常反观自己的生活,被虚构的马修和伊丽莎白成为另一个比尔和鲁丝,(32)比尔在马修的虚构历史中找寻自己的救赎之路。比尔强调自己历史叙述的虚构性时,他已经把读者的关注从被叙述的马修转向了虚构叙事的创造者——他自己,读者从关注马修的创伤经历转而注意比尔的创伤叙事。当代理论界和史学界也指出,当历史表现为一种叙事的时候它本身已经蕴含了三层含义:历史叙事不仅仅只提到事实,历史叙事来源于对历史或更多文献的解读,或者是对一系列研究对象的分析,它首先是有所指的;其次,当被选择和被解读的历史事件置入一个能赋予其意义的框架内的时候,历史叙事就不仅是引证而是在生产意义;最后,历史叙事中隐含的象征性涵义,使其与一系列的价值系统、符号、不同民族的情感类型、伦理、宗教、文化或者社会联系在一起。(33)比尔叙事的主观性使读者注意到他对马修日记的摘选也不是客观和随意的,他摘录的日记内容大都记述了马修对自己幸福生活的依恋,自己对妻子深深的爱。比尔所选摘的日记一方面为了印证他在虚构叙事中对马修婚姻幸福的猜测,另一方面也在指涉自己的婚姻生活,意欲强调自己与鲁丝之间真诚的爱情。和马修一样,创伤已经被幸福的生活所掩盖。因此,比尔的虚构叙事暗指了自己历史建构的主观性,他使创伤在马修历史的建构中远离了或边缘化了。哈钦在讨论史学元小说时曾指出,历史的创伤成为语言的建构时,它“已经不再如当初那般刺痛——它们既在时间上不可挽回地远离了我们,而且我们决意要为别人的(或我们自己的)真实伤痛赋予一定的意义”。(34)
比尔在马修的历史建构中一直无法释怀的是,为什么在六年之后他要坦白自己的宗教怀疑,一手粉碎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不能理解他”,(132)“信仰和伪信仰有什么分别吗”。(143)比尔和马修的不同恰恰在于马修拒绝了对创伤的救赎,而选择直接面对生活的残酷。马修的日记中曾回忆了他在认识伊丽莎白的十年前,在一个“繁花盛开的仲夏”(比尔与鲁丝的爱情也发生是在一个仲夏的夜晚),他和朋友们到莱姆郊游,在大家听到少女的呼救声时,其余的人都赶到了事发现场,而只有马修没有前去,而此时他发现了鱼龙的化石,他的信仰从那时起开始动摇。在日记中马修曾感叹道:“为什么我那时没有冲过去?去帮助受难的少女。只需要一点普通的殷勤也许就拯救了我。”那时的马修没有选择一段浪漫爱情的发生,因为他知道“即使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动摇这样的认识:那一刻带给他的不是无缘由的恐慌和困惑,而是敏锐的洞察力”(100)。事实上,浪漫的爱情和宗教的救赎都没有减轻创伤对马修的影响,马修最终的选择是面对真实的创伤,即使那样的面对是痛苦的。马修直面创伤的态度也决定了比尔在为其建构的历史叙事中寻求救赎注定是失败的。
四 结语
虽然比尔企图建构各种“救赎”的叙事以减轻创伤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然而他在叙事中也意识到他不是“哈姆雷特”、不是浪漫传奇中的主人公,也不是当代的马修·皮尔斯,创伤的影响没有在“救赎”的叙事中消亡,相反比尔发现自己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我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些人,那么“我是谁”呢?这一问题成为比尔自杀后回顾自己历史的“要旨”所在。《从此以后》通过叙述者比尔对自己曾经求助的各种“救赎”叙事的反思,揭示了创伤的“救赎”叙事只是对创伤历史的规避。虽然创伤的存在对于建构一个可资利用的过去来说是个极大的障碍,因为它往往突如其来,打乱了连续的历史和平静的生活,同时给人们带来痛苦。但回避创伤或不承认它带来的持久影响只能使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加无能,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斯威夫特在小说中虽然揭示了主观叙事对历史认知带来的危机,但是他也指出,当人们都在关注历史的客观性,历史事件真实与否的时候,人们是否忽略了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呢,尤其是创伤事件在人类生存中的价值。与其过分地关注事件的真与假,不如汲取历史的经验更好地面对现在和将来的生活。
注释:
①Michael Levenson,"Sons and Fathers," in New Republic,22 June,1992,40.
②具体可参见David Malcolm,Understanding Graham Swift (Columbia: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2003) 144-146; Hannah Jacobmeyer,"Graham Swift,Ever After:A Study in intertextuality" (Erfurt Electronic Studies in English,1998); Michael Levenson,"Sons and Fathers" (New Republic,22 June,1992) 38-40; Stephen Wall,"solf-Slaughters" (London Review of Books,12 March,1992) 26; and John Lloyd Marsden,After Modernism: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Ohio University,1996) 174-206.
③McDonald Harris,"Love Among the Ichthyosaurs,"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9 March,1992,21.
④Sybil Steinberg,"Untitled Review of Ever After," in Publisher's Weekly,20 January,1992,48.
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京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8页。
⑥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选自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6-17页。
⑦Dominick LaCapra,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 Theory,Trauma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48n6,192.
⑧Graham Swift,Ever After (London:Picador,1992) 4.小说文本引用在此文中将直接在括号中标出页码。
⑨Dominick LaCapra,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 Theory,Trauma (Ithaca:Cornell UP,1994) 48n6,192,
⑩Dominick LaCapra,Writing Trauma,Writing Histor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2001) 51,44.
(11)Dominick LaCapra,Writing Trauma,Writing Histor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2001) 51,46.
(12)Cathy Caruth,ed.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4.
(13)Cathy Caruth,4.
(14)热奈特用“显文本”(hypertext)和“潜文本”(hypotext)指称互文本和互文关系,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荷马的《奥德修纪》,就是“显文本”和“潜文本”的实例。
(15)《哈姆雷特》的评论者在讨论该剧是否是一部悲剧时,涉及了剧中受难、毁灭和救赎的主题。特里亚德从三个角度界定悲剧的内涵:受苦、牺牲和再生。第三类“再生类型的悲剧”是指“在毁灭基础上产生的新生。它伴随着启蒙的生,并且由此肯定了新的生存状态。这一类悲剧深深地浸透在人的本质中,因为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超乎寻常的苦难,而是所有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悲剧事实:也就是说如果想产生接连一种美好的状态不可能始终如此,而是会发生改变的,甚至是部分的损毁”(E.M.W.Tillyard,Shakespeare's Problem Plays,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8,14)。亚历山大也认为《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因为它通过英雄人物赞美了人类通过可怕的痛苦而实现的杰出品格;通过歌颂这一过程和结果,它在我们心中产生感情净化的效果——对于痛苦的积极掌控(Peter Alexander,Hamlet:Father and S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55)。其他的评论者如凯托(Kitto)也指出剧中哈姆雷特在刺死克劳迪斯之后为丹麦国重新建立了良好的秩序(H.D.F.Kitto,Form and Meaning in Drama:A Study of Six Greek Plays and of Hamlet,2nd ed.London:Methuen,1964)。
(16)参见Jakob Winnberg,An Aesthetics of Vulnerability:The Sentimentum and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Goteborg:Goteborg University Press,2003) 158-159。
(17)Kathleen Morner and Ralph Rausch,NTC's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NTC Publishing Group,1991) 191.
(18)J.A.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沈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9)Kathleen Morner and Ralph Rausch,191.
(20)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186.
(21)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187.
(22)虽然波希米亚人是指捷克波希米亚省的当地人,波西米亚人的第二个涵意却是出现在19世纪的法国。波西米亚人这个词被用来指称那些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抱持幻想的人。在《美国大学辞典》中将bohemian定义为“一个具有艺术思维倾向的人,他们生活和行动都不受传统行为准则的影响”。比尔的叙述虽然不完全具有波希米亚人的特点,但是他在叙述中刻意表达了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和把生活艺术化的倾向。
(23)James Whitcomb Riley,美国诗人,以怀旧的方言诗闻名,常被称作“平民诗人”。少年时曾画过广告、当过小丑演员以及药贩子的助手。
(2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58,62页。
(25)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 (Ithaca:Cornell UP,1983) 128-129.
(26)参见Step Craps,Trauma and Ethics in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Brighton:Sussex Academic Press,2005) 136; Daniel Lea,Graham Swift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152。
(27)一些评论者指出比尔在建构马修的故事时使用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规范,参见John Lloyd Marsden,After Modernism: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Ohio,1996) 199.
(28)关于何为元小说的叙事手法,此处指琳达·哈钦、埃里森·李所讨论的史学元小说的叙事方法,即套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的同时又质疑了此种叙事的权威性。参见Linda Hutcheon,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 (London:Routledge,1988); Alison Lee,Realism and Power:Postmodern British Fiction (New York:Routledge,1990)。
(29)霍莫斯(Frederick Holmes)指出比尔在叙事中把马修的妻子伊丽莎白塑造成“维多利亚小说中典型的具有良好教养的女主人公”,参见Frederick Holmes,"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s Plastic:The Search for the Real Thing in Graham Swift's Ever After," in ARIEL 27.3 (1996) 25-43。
(30)Jahn Fowles,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1969) 92.
(31)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 (Ithaca:Cornell UP,1983) 103.
(32)马斯登(John Marsden)认为比尔在通过马修·皮尔斯书写自己的历史,参见John Lloyd Marsden,After Modernism: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Ohio,1996)195。
(33)Jos Carlos Bermejo Barrera,"Making History,Talking about History," trans.Yang Xiaohui,in Writing History,ed.Chen Qineng (Shangha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3)52-53.
(34)Linda Hutcheon,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Routledge,1989)82.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从此以后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哈姆雷特论文; 巴黎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