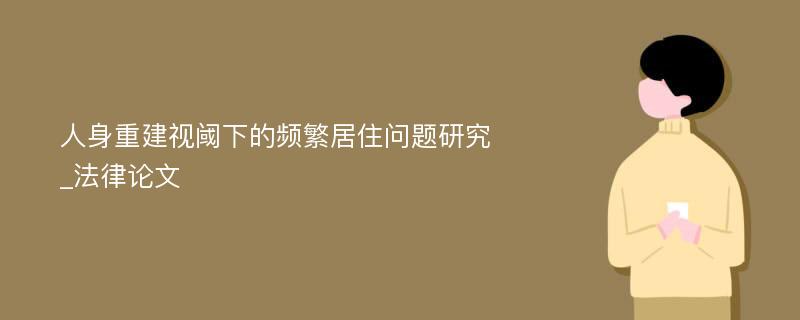
我国属人法重构视阈下的经常居所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所论文,重构论文,我国论文,属人法论文,视阈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私法中,属人法一般是指用来解决人的身份、能力、婚姻家庭和继承关系等方面民事法律冲突的法律,①其主要通过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经常居所②作为连结点,建立起自然人与某一地域法律之间的联系。③在传统上,属人法主要是指大陆法系国家的本国法即国籍国法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住所地法。④在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属人法的确定规则呈多样化,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也呈多元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采用经常居所取代国籍和住所成为属人法最主要的连结点,使得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的属人法得以重构。近年来,随着我国跨国劳务派遣、出国求学和境外旅游活动的日益频繁,我国自然人在境外期间在身份领域发生的争议应该适用哪国法律,便成为我国当事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例如,一个中国工人受派工作于外国,他的身份、能力、亲属和继承关系等问题是适用中国法还是外国法?如果他前往的是法制发达国家,其属人法上的权利应该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而如果他工作在一个法制不发达国家,其属人法上权利的保护便不无忧虑。同样,如果一个已成年的外国学生在中国留学,其相关属人法上的权利是适用其本国法还是中国法?哪一种法律更能够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同时又能兼顾当地的社会秩序?这些问题无论对中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当事人本人,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那么,以经常居所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何优势呢?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的背景下,经常居所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其在适用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经常居所的界定又应如何呢?以下笔者试在我国属人法重构这一视阈之下,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我国属人法连结点的新发展:从多元到单一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以前,我国有关属人法的规定虽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自然人行为能力、涉外动产的法定继承和扶养等领域,但属人法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包括定居国法、国籍国法、住所地法、行为地法、财产所在地法以及最密切联系地法等。例如,对确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属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43条采用定居国法,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79条、第180条、第181条则进一步规定采用定居国法、行为地法以及住所地法;而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则规定采用国籍国法,并以行为地法加以限制。关于扶养关系的属人法,《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采用最密切联系地法;《民法通则意见》第189条则扩展至国籍国法、住所地法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法。另外,对涉外动产的继承关系、⑤ 涉外监护关系⑥等的属人法,相关法律则规定采用住所地法或者国籍国法,或者二者并用。通过上述规定,我们不难发现经常居所地法并没有上升到属人法的地位。不仅如此,经常居所甚至不是确定属人法的众多连结点中的一个,它只是在确定属人法时用来判定住所的一个因素,根本无法与作为主要连结点的住所和国籍相提并论。例如,《民法通则》第15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一改以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属人法多样化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常居所地法完全取代了住所地法,并部分地取代国籍国法,逐步简化了属人法。例如,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共52条的规定中,经常居所地法出现42次,分布在25条的规定之中。在此25条中,关于经常居所的规定有以下6种情形。(1)唯一连结点。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1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在该条规定中,经常居所是唯一连结点,没有其他连结点进行补充。此类规定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有6条,即第11条、第13条、第15条、第31条、第46条以及第28条第1款和第2款。(2)首要连结点。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在该条规定中,经常居所是确定属人法的首选连结点,在经常居所不存在的情况下,或者案件存在特殊情形下,由其他类型的连结点进行补充。此类规定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有6条,即第12条、第21条、第23条、第25第、第42条及第45条。(3)替代连结点。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4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在该条规定中,首先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确定属人法;当事人没有选择的,经常居所作为连结点才能指引案件所应适用的法律。此类规定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也有6条,即第14条、第24条、第26条、第44条、第47条以及第28条第3款。(4)任选连结点。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在该条规定中,经常居所只是三个可选择性连接因素之一。此类规定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也有6条,即第22条、第29条、第30条、第32条、第33条及第41条。(5)确定多重国籍下国籍国法的连结点。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9条规定:“依照本法适用国籍国法律,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国籍的,适用有经常居所的国籍国法律;在所有国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自然人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的,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律”。(6)确定自然人经常居所不明时经常居所地法的连结点。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0条规定:“依照该法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自然人经常居所地不明的,适用其现在居所地法律”。不仅如此,在适用范围上,经常居所地法也有很大程度的扩张,其不仅适用于先前住所和国籍作为连结点的属人法领域,如自然人行为能力领域、抚养、监护和继承;也适用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人的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人格权、婚姻、收养等传统法律没有规定的领域。此外,经常居所除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外,其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还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渗透,如消费者合同(第42条),侵权责任(第44条),产品责任(第45条),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第46条),以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
由此可见,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住所作为连结点被完全抛弃,国籍的功能被弱化,仅作为替补性或者选择性的连结点出现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10个条文中,即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26条、第29条、第30条、第32条及第33条;经常居所地法已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属人法,经常居所已上升到最重要的连结点的地位。可见,《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不仅改变了我国属人法多元化的立法状况,而且使经常居所成为我国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最主要的连结点。
二、经常居所作为连结点的优势:与国籍和住所连结点相比较
经常居所通常是指自然人出于临时定居的目的,自愿并经常居住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⑦ 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经常居所在我国并非一个经常使用的法律概念,但与国籍和住所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相比较,其具有相对优势。这也许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其作为确定属人法的最重要的连结点的主要原因。
住所和国籍分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确定属人法的最主要的连结点。但晚近二者受到了强烈的批判,经常居所则成为国际和国内立法确定属人法的首选连结点。就住所而言,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概念并不统一。对大陆法系国家而言,住所可能意味着经常居所;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住所则等同于一个人永久的家。⑧在美国,住所是自然人因特定的法律目的而有稳定联系的地方(该自然人的家在该地方或法律指定该地方)。⑨住所可分为原始住所和选择住所。⑩自然人要想获得选择住所,他不仅需要居住于此,(11)而且还要有在该地安家的意图。(12)在英国,“住所就意味着家,永久的家”,(13)没有人能够没有住所而存在,也没有人为同样的目的同时拥有两个住所。(14)英国有关住所的规则非常复杂,常常难以明确判断,因此,容易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15)传统住所的概念在英格兰已受到法律改革机构严厉的批判。(16)而在新西兰、(17)澳大利亚(18)和加拿大,(19)同样复杂的概念则已经被修改。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住所是确定属人法最基本的规则,但时至今日亦大不如前般稳固而安全。“法院,尤其是立法机关,正在使用各种形式的居所或者国籍作为连结点,以替代住所。”(20)住所已是一个渐趋废弃的概念。(21)而就国籍而言,大多数民法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国籍是确定属人法最重要的连结因素。(22)相较于住所,国籍至少有如下优势:稳定且容易确定。国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连接因素,任何人国籍的变化都需要新国籍国正式的同意,而且包括一个正式的归化程序。由于自然人国籍的变化不依靠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因此,它比较容易确定。(23)然而,国籍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实践中,法院经常会遇到自然人有两个以上国籍或无国籍的情况。在此情形下,法院需要借助其他连结因素,如经常居所来确定属人法。(24)其次,国籍虽然具有稳定性,但完全以国籍来确定属人法也可能牺牲个人选择法律制度的自由。“一个人可能要面对适用违背其本身意愿的国家的法律,而这个国家或许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要逃离的国家。”(25)国籍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已经受到广泛的批判,(26)并逐渐为近来的立法所抛弃。在替代国籍作为连结点上,通常认为,经常居所至少比住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27)
在国籍和住所均不能成为确定属人法的令人满意的连结点的情况下,(28)代之以其他的连结点便成为自然的选择。(29)而采用经常居所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优势。(1)相对于住所而言,经常居所更容易确定。住所是自然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处所。住所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当事人的意图。(30)住所的确定不仅需要当事人的行为,更需要当事人的意图。(31)已有的国际实践充分表明,不论是永久居住还是当事人的意图,在确定上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32)在我国,通常住所地法无异于经常居所地法。例如,《民法通则》第15条的规定。《民法通则意见》第9条进一步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可见,在通常情况下,公民的经常居所与他的住所是重合的;如果二者不一致,则经常居所可视为住所。在涉外案件中,这也就意味着要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因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适用住所地法最终还要适用经常居所地法。(2)随着当代国际社会人员流动的日渐频繁,经常居所地通常就是自然人的生活中心和利益中心。例如,一个自然人在其经常居所地国收养一个婴儿,与之密切联系的当然是该经常居所地国的法律,而且出于当地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角度考虑,经常居所地法也应该适用于这一法律行为,而不是与经常居所地不同的住所地国法或者国籍国法。(33)(3)经常居所是解决多重国籍或者多个住所冲突的主要方案。(34)由于大陆法系国籍法与英美法系住所地法长期冲突,在1955年《解决本国法和住所地法冲突的公约》的谈判中,缔约者为解决这一冲突,将住所解释为“经常居住的处所”即经常居所,以此来化解两大法系的冲突。最后,在《解决本国法和住所地法冲突的公约》第1条、第2条和第5条中,经常居所成为解决大陆法系国家的国籍国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住所地法冲突的唯一解决方案。在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182条规定:“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第183条规定:“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所”。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用经常居所来解决国籍和住所各自的积极冲突,不如直接使用经常居所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35)
在国际立法上,自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1902年在《关于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公约》第9条中首次采用经常居所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以来,越来越多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缔结的条约以经常居所为连结点确定属人法。例如,1955年《解决本国法和住所地法冲突的公约》第5条,1961年《婴儿保护方面主管机关的权力以及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和第5条,1980年《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第4条和第8条,1996年《关于父母责任和儿童保护措施方面的管辖权、法律适用、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以及合作的公约》第5条、第6条、第7条和第10条,以及2007年《抚养义务的法律适用协定》第3条、第4条、第5条、第6条和第8条。如今,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缔结的条约中,经常居所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
除了前述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缔约的公约普遍采用经常居所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外,在晚近欧盟的相关立法中,经常居所也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连结因素。例如,《关于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第864/2007号条例》第4条、第5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和第23条规定,《关于在离婚和分居法律适用领域中执行加强型合作的第1259/2010号条例》第5条、第6条、第7条和第8条的规定,《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第593/2008号条例》第4条、第5条、第6条和第7条的规定,《关于继承的管辖权、法律适用、决定的承认与执行、相关真实文书的接受和执行以及欧洲继承证书创立的第650/2012号条例》第21条、第27条、第28条和第36条的规定。
三、经常居所作为连结点存在的问题:基于司法实践的考察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欧盟的立法将经常居所作为属人法连结点的采用,充分说明晚近经常居所在法律适用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尽管如此,经常居所作为确定涉外法律适用法特别是属人法的连结点也会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有人可能会说,采取经常居所作为连结点不利于我国公民权利的保护。近年来,每年都有上亿次的中国公民出国旅行,临时居住或移民到外国,而来华的外国人人数则小于中国公民出境的人数。(36)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而并不是移民输入国。目前,大多数移民输入国,如美国、加拿大、瑞士和比利时等国主张采用住所地法和经常居住地法为属人法,以使本国的法律能有更多的机会适用于在本国境内的外国人。而移民输出国则往往出于保护本国国民的考虑,更多地主张以国籍法为属人法。如此一来,即使本国国民旅行或移居到外国,本国法也能得到适用,从而更好地保护本国国民。(37)由于目前我国主要是移民输出国,从理论上来说,采用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将更有利于我国法的适用;而采用住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则等于将更多适用我国法的机会让位于外国法。但笔者认为,我国居民出入境的现实情况表明,采取经常居所作为确定我国属人法的连结点并不会对我国当事人产生绝对的负面影响。以2010年为例,我国内地居民出境前往国家(地区)居前十位的依次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美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38)从移民的角度来看,中国公民前往的大都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与适用中国法相比,适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并不一定不利于我国公民权利的保护。相反,有可能使我国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且我国公民一旦移民,通常会居住在外国,对发生在外国境内的争议,一般不会到中国法院起诉。如果当事人在外国法院起诉,外国法院会根据其本国法(包括冲突法)来确定法律适用,中国法并不必然得到适用。在移民的情况下,经常居所地是当事人的生活中心,其国籍国——中国——可能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任何的联系。在此情况下,中国法的适用并不具有合理性。而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外国人来华人数逐年增长。例如,2010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5211.2万人次;(39)2011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5412万人次;(40)2012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5435.15万人次。(41)对来中国的外国人而言,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将会使中国法得到更多的适用机会。立法通常会通过比较优势择善而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采取经常居所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有可能使我国公民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对中国境内涉及外国人的争议,中国法将会得到较多地适用,从而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秩序的维护。
不过经常居所作为连结点,确实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那就是经常居所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42)经常居所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经常居所评估期间的不确定性。经常居所评估期间往往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有时即使是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法院亦会对确定经常居所评估期间有不同的认定。(43)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起案件(44)中,3个月的时间就能满足经常居所评估期间的要求;而在澳大利亚的另一起案件(45)中,7周的时间则不足以满足经常居所评估期间的要求。在英国1998年的一起案件(46)中,1个月的居住期间就能满足经常居所评估期间的要求;在英国2001年的一起案件(47)中,161天也能满足经常居所评估期间的要求;但在英国2003年的一起案件(48)中,71天则不满足经常居所评估期间的要求。虽然经常居所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运用了多年且存在大量的案件,但经常居所评估期间往往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并非一个固定的期间。而在我国,经常居所评估期间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期限,即为1年以上。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民法通则意见》第9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4条和第5条亦有类似的规定。(2)相对于评估期间,定居意图则更具模糊性。定居意图通常是指自然人打算暂时并且规律地在某地生活的意愿。(49)它意味着当事人至少以生活在某一个具体地方为目的。一般而言,居住的时间越长,定居的意图越容易判断。因为是对当事人主观意思的推断,所以实践中的不确定性也愈加明显。(50)
尽管我国民事关系法律和民事诉讼关系法律均对经常居所的问题进行了关注和规定,但关于经常居所问题的可查阅的相关案件屈指可数,(51)而从那些有关住所的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经常居所的界定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1)经常居所不同于住所。在我国,公民通常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方能为经常居所。当事人必须规律性地出现在该地且时间在1年以上,临时性的出差并不导致评估时间的中断。实践中,人民法院对“连续”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俞卿诉柴勇离婚案”(52)中,慈溪市人民法院认为,尽管被告因工作原因经常出差,仅阶段性地与原告生活在一起,但被告在法院所在地已连续居住1年以上,因此,慈溪市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从该案可以看出,“连续”居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临时的出差或离开经常居所地,并不构成对“连续”的中断;如果一个人只是偶尔在一个地方居住1年或1年以上,该地不应该被考虑为该人的住所。又如,在浙江省余姚人民法院审理的“石某诉傅某债务纠纷案”(53)中,被告傅某住所地在浙江省慈溪市,自1984年起一直住在余姚市,但傅某的居住地经常在余姚市的不同乡镇之间迁移并有间断的出差行为,而且在案件审理时的居住处所居住时间尚不满1年。尽管余姚市人民法院在判断经常居所地上有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傅某一直居住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的辖区且在1年以上,余姚市人民法院最终还是行使了管辖权。在此案中,余姚市人民法院对连续居住的判断是以法院的辖区来进行判断的,而不是以某一个固定的处所来进行判断的。可见,当事人的居所也并非固定在某一个处所,如果当事人变更居所,但只要这些居所均在某一法院的辖区之内且居住满1年以上,则该法院的辖区所在地即可以构成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但问题是,固定的“1年以上”的居住期限是否具有合理性。例如,在“谢明治诉王水生继承在大陆探亲期间死亡的台湾居民的遗产纠纷案”(54)中,我国台湾地区居民王清福于1992年10月到祖国大陆探亲,将随身携带的钱财主要交给大陆居民王水生保管。1993年2月,王清福在王水生家中病逝。王清福胞妹之子谢明治起诉要求继承遗产。而人民法院最终以被继承人王清福的法定住所在我国台湾地区且在祖国大陆居住的时间少于5个月,其经常居所地不在祖国大陆为由,继而根据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的规定,即继承遗产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行使了管辖权。而事实上,王清福在生病期间,有充足的时间返回台湾地区且其在台湾地区有一养女,但他在死亡的前后,未曾联系台湾地区的养女。从案情来推断,王清福已经不再打算返回台湾地区;从法律角度来说,其已经抛弃了在台湾地区的住所。此案表明,在某些案件中,“1年以上”的经常居所评估期间太长了,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2)缺乏对当事人居住意图的考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界定经常居所时,通常缺乏对当事人居住意图的考虑。例如,在“边某诉边某某离婚纠纷上诉案”(55)中,2005年4月,原告日本公民边某被派到北京工作2年。被告日本公民边某某亦随原告居住于北京。二人的签证有效期截至2007年3月14日。2006年年底,原告边某起诉要求离婚,被告则提出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认为,由于二人在中国的居留有效期及工作期限均即将届满,在原、被告均存在近期内不能在中国继续居留的情况下,中国不是当事人的经常居所。最终,人民法院在确定管辖权时,既没有分析当事人在中国是否具有经常居所,也没有分析是否因当事人即将回国而在中国丧失经常居所,就作出了没有管辖权的裁定。而实际上,当时双方当事人在中国已连续居住近2年,并且《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意见》第5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如果不考虑当事人居住意图而仅仅根据当事人的居住事实和法律规定,该案中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应该在中国,我国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行使管辖权。而如果考虑当事人定居意图的话,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将不可能在中国居住,而且也不打算在中国居住,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将很难在中国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民法院可以没有管辖权。从该案可以看出,在经常居所的界定中,仅仅判断居住的期限这种客观的标准是不够的,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居住意图,综合判断经常居所的存在与否。
四、经常居所的界定: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5条
对经常居所的界定标准,其他国家的立法很少有明确规定,德国法(56)与瑞士法(57)对此仅有抽象规定且均强调其应当是“生活中心”,国际条约也没有对认定经常居所地的标准作出规定。经常居所作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主要的连结点,2013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对经常居所进行了规定,其第15条规定:“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1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而言,经常居所地将会与住所地重合。在国外就医治疗、被劳务派遣在国外务工、因公务在国外工作、培训学习等都不应属于在国外经常居住,因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针对这种情形作了“但书”规定。(58)
可以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传统法律中对经常居所“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评估期限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又使该规则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又将就医、留学和劳务派遣排除在外。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该方案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排除了“就医、劳务派遣和公务等情形”,那么,在此三类情形下,该如何界定经常居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针对此三类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明确是适用当事人的住所地法,还是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抑或直接适用中国法,以真正达到指导司法的效果。其次,1年的经常居所评估期限要求可能太长,而且仅仅判断当事人居住的期限而不考虑当事人的居住意图是不合理的。以“谢明治诉王水生继承案”为例,如果此案发生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行之后,根据该法第31条的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如此一来,祖国大陆的法律将很难得以适用,而不得不针对王清福在祖国大陆的财产去查询台湾地区的“法律”,并适用台湾地区的“法律”。这种结果无疑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将评估经常居所地的时间固定为1年而不考虑当事人的居住意图,在涉外案件的审理中很有可能给我国法院适用法律带来诸多的不便,也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需求。
与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国际立法和外国立法中,经常居所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事实问题应由法官判定。因此,在经常居所的界定上,法官通过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形,并主要通过分析当事人的居住事实和居住意图,进行自由的权衡。很少国家制定严格而又僵化的规则来界定经常居所。例如,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缔结的条约中,尽管经常居所作为连结点多有运用并成为最受欢迎的连结点之一,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直拒绝用规则对经常居所进行明确的界定。(59)其目的就在于要让经常居所的界定远离技术性的规则,从而避免在不同法律体系之间产生不一致性,并最终避免僵化地适用这一概念。经常居所并非一个难以理解的技术性术语,实际上只要根据这个术语普通的和自然的含义来确定即可。(60)从一开始使用这一术语,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就强调:与住所的法律概念相反,经常居所是一个事实问题。(61)而根据《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关于“住所”和“居所”法律概念规范化的第72(1)号决议》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在确定一个人的经常居所上,居住的期限和连续性、与该人及其居所有关的人身和职业联系等均应被考虑。而当事人的居住意图更是权衡的重要因素。《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整体看来,目前在国外确定经常居所上,没有固定的评估时间。(62)居住的长度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大多是依靠案件的具体情形,诸如,自然人的家庭情况、职业状况、居住的意图、在经常居所地的财产状况、搬迁的原因等,由法官们自由考量。(63)经常居所本身就是一个事实,而作为案件中存在的事实,不能用固定的思维或规则来将其固化,充分考虑案情以及当事人的居住意图等因素来灵活确定经常居所更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可以说,在经常居所的确定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沿袭旧制而采用一个固定僵化的标准,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将很难达到成功指导司法的效果。笔者认为,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将经常居所评估期限固化为1年的期限,至少这个期限是太长了。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做法,在确定经常居所时,结合具体案情来确定形成经常居所的评估时间,并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活动中心、居住意图、家庭情况、职业状况、在经常居所地的财产状况、搬迁的原因等,以使最终确定的经常居所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确定案件属人法的连结点,使得最终的法律适用结果能达到最佳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效果。
注释:
①④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②经常居所在国际上又称惯常居所。在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通过时,考虑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经常居住地”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采纳了“经常居所”的表述。本文为方便起见,统一表述为“经常居所”。
③See David F.Cavers,Habitual Residence:A Useful Concept?,Am.U.L.Rev.,Vol.21,1972.在全球的范围内,属人法的概念尽管各有差异,但下列事项通常属于其调整范畴: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宣告失踪与死亡、人格权、婚姻的实质有效性、夫妻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收养、扶养、监护、动产遗嘱和法定继承等。See James Fawcett and Janeen M.Carruthers,Cheshire,North & Fawcett: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54.
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条。
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0条。
⑦See Shah v.Barnet LBC [1983] 2AC 309.
⑧(13)See Whicker v.Hume [1858] 7HL Cas 124.
⑨(11)(12)See Restatement(First)of Conflict of Laws,(1934),Section 9; Section 16; Section 18,19,20.
⑩原始住所是指自然人出生时取得的住所,通常以父母之住所为原始住所;选择住所则是指自然人出生后依久住意思和居住事实选择取得的住所。See Restatement(First)of Conflict of Laws,(1934),Section 14,15.
(14)(15)(16)(32)(33)(35)(43)(49)(50)(61)(62)See James Fawcett and Janeen M.Carruthers,Cheshire,North & Fawcett: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5-156,p.154,p.182,p.154,p.154,p.182,pp.187-189,p.189,pp.189-190,p.89,pp.189-190.
(17)See Domicile Act 1976.
(18)See Domicile Act 1982(Cth); Domicile Act 1979(NSW); Domicile Act(NT); Domicile Act 1981 (Qld) ; Domicile Act 1980 (SA); Domicile Act 1980 (Tas); Domicile Act 1978(Vic); Domicile Act 1981(WA).
(19)See The Domicile and Habitual Residence Act 1983 of Manitoba.
(20)(22)(23)(24)(27)(60)See Lawrence Collins,et al.,Dicey &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Vol.I) ,Sweet & Maxwell,2000,p.152,p.154,p.168,p.153,p.153,p.153
(21)See Kahn-Freund,The Wills Act 1963,M.L.R.,Vol.27,1964.
(25)A.E.Anton,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ots Law,2nd ed.,Green &Son,1990,p.123.
(26)(28)See David F.Cavers,Habitual Residence:A Useful Concept?,Am.U.L.Rev.,Vol.21,1972.
(29)See Peter Stone,The Concept of Habitual Residenc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nglo-American Law Review,Vol.29,2000.
(30)(34)参见杜新丽:《从住所、国籍到经常居所地——我国属人法立法变革研究》,《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
(31)See Munro v.Munro [1840] 7Cl & Fin 842.
(36)(4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11年出入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同比稳步增长》,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96/3100875.html,2012-12-12。
(37)参见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国际私法改革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0页。
(38)(3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10年出入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同比稳步增长》,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96/2666368.html,2013-05-01。
(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12年出入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同比稳步增长》,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96/3612366.html,2013-05-01。
(42)参见黄栋梁:《我国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属人法问题》,《时代法学》2011年第4期。
(44)See V v.B(A Minor)(Abduction) [1991] FCR 451, [1991] 1FLR 266.
(45)(46)See Re A(Abduction:Habitual Residence) [1998] 1FLR 497.
(47)See Ikimi v.Ikimi [2001] EWCA Civ 873.
(48)See Armstrong v.Armstrong [2003] EWHC 777(Fam).
(51)笔者于2013年3月22日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尚未发现案件适用经常居所地法。
(52)参见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6)慈民一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书。
(53)参见张宏伟:《认定被告经常居住地的几个问题》,《人民司法》1992年第11期。
(54)参见杨洪逵:《谢明治诉王水生继承在大陆探亲期间死亡的台湾居民的遗产纠纷案》,《中国法律》1996年第1期。
(55)参见《边某与边某某离婚纠纷上诉案》,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 Db=pfnl&Gid=117681552&keyword=&EncodingName=&Search_Mode=accurate,2013-04-12。
(56)参见2009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5条。
(57)参见2010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20条。
(5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答记者问》,http://WWW.court.gov.cn/xwzx/jdjd/sdjd/201301/t20130106_181593.htm,2013-01-09。
(59)See L.I.De Winter,Domicile or Nationality?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Recueil des Cours (1969-II),Vol.128,1969.
(63)See Swaddling v.Adjudication Officer,Case C-90/97,[1999] ECR I-1075; Di Paolo v.Office National de l'Emploi,Case 76/76,[1977] ECR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