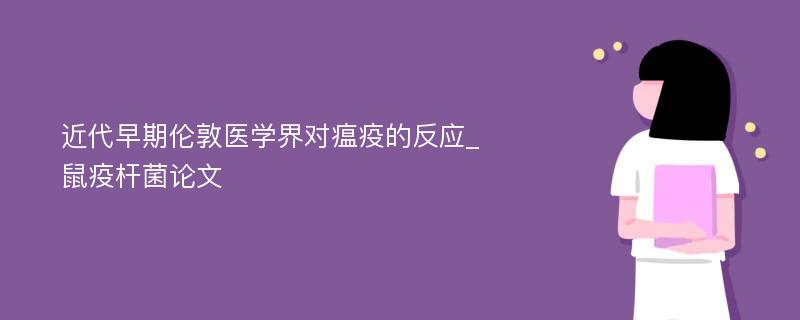
近代早期伦敦医疗界对鼠疫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鼠疫论文,伦敦论文,近代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6-0077-07
在近代早期的伦敦,以鼠疫为主的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也在社会秩序、经济生产诸方面造成了极大的破坏。① 在西方学术界的已有研究中,医疗界② 对鼠疫的应对大都是以结论的形式被转述的,即认为近代早期医疗在防治鼠疫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对医生、鼠疫防治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动态关系鲜有系统而深入的揭示。本文拟从鼠疫的临床治疗与鼠疫的预防保健着手,揭示当时医疗界的活动及其意义,并对医疗与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
16~17世纪,伦敦医生的数量较少。从1518年开始,英国创立皇家医学院,规定正式的行医者原则上必须有行医许可证,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半期,医生资格的认定与许可证的颁发一直就是皇家医学院的事情。据统计,在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150年的历史中,官方每年颁发的行医许可证固定在30人,这个数额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1518年,伦敦皇家医学院为自己的12名医生颁发了行医许可证,而伦敦人口是6万人;1589年,伦敦皇家医学院给38名医生颁发了许可证,伦敦人口是12万人。③ 医学社会史家玛格丽特·佩林与韦伯斯特对伦敦的医生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1600年伦敦共有50位拥有行医许可证的皇家医学院内科医生、100名外科医生、100名药剂师以及250名无证行医者,而此时伦敦的人口为20万人,在1600年左右这一比例为1∶400。④ 到了17世纪上半期,虽然人口不断增长,但是医生的数量仍旧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据罗伊·波特的记载,17世纪上半期,伦敦大约有500名行医者,其中有许可证的包括72名外科医生,150名药剂师,其他的为有学问的医生(the learned physician)以及民间行医者,而当时伦敦人口是60多万人。⑤ 这说明,在16~17世纪,人口急剧膨胀,而医生数量保持在基本不变的水平上,医生严重缺乏。
这些“稀有”的医生在鼠疫来临的时候,往往临阵脱逃。即便是托马斯·西登哈姆(1624~1689,英国皇家医学院学士,近代西方临床医学之父)这样享有盛名的医生,在伦敦大鼠疫来临时也逃离了伦敦。他在研究鼠疫的疗法时说过,他没有第一手的病人资料,因为那时他离开了伦敦。⑥ 一个名叫西蒙·弗曼的医生,他为自己的高尚而自豪,他说:“鼠疫到来了,所有的医生都离开了这座城市,我没有离开,我留下来拯救那些生病的人,即便我为此而死亡。”⑦ 后来,弗曼和家人都染上了鼠疫,但是只有一人没有能够逃脱,其余的人都痊愈了。一个比弗曼更加著名的内科医生——托马斯·洛奇(1558~1625,英国“大学才子派”诗人和剧作家,1603年牛津大学医学学士,皇家医学院成员),在1603年8月19日为《瘟疫手册》写序言⑧,这本书不及作者的其他作品有名,但它是为了指导人们如何应对鼠疫而写的,书中表达了作者的真诚与同情心,当洛奇将这本书呈于伦敦出版商时,当时伦敦城每周鼠疫死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之多。当然,像弗曼和洛奇这样的具有皇家行医许可证的医生留下来的还是少数,大多数医生还是远离了做医生的操守,成为鼠疫来临之前的望风而遁者。当时的诗人德克尔在他的诗作中大大鞭笞了医生的逃跑行为。在这些皇家医生逃跑之后,冒牌的庸医和江湖郎中就乘虚而入。他们耻笑皇家医生的无能、伪善和懦弱,称虽然皇家医学院的医生们学习了哲学、医学知识,懂得所谓的四体液学说,也有过严格的医疗实践训练,实际上这些都是好听不受用的。⑨
为弥补从医人员的匮乏,1542年,亨利八世颁布了他在位期间的最后一个医疗条例,名为《江湖郎中条例》,它免除了无证行医者的死刑,称从上帝那里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无证者,无论是男是女,只要诚实行医就不会受到惩罚。实际上,它是对1512年排斥江湖郎中的《江湖郎中条例》的一个修正。⑩ 1542年条例鼓励民间游医、药剂师等通医术者直接参与到鼠疫的治疗中。但是,这一条例的作用在当时也是有限的。鼠疫爆发时,这些江湖郎中往往只顾敛财,囤积居奇,高价兜售并不一定有效的药物。他们将香料、石粉以及珍珠粉搅拌在一起,称这有着神奇的功效,可以使人起死回生(11),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用。一旦疫情严重,他们同样不会为此甘冒生命的危险,同样会拒绝出诊或者干脆逃离。据记载,1665年伦敦爆发大鼠疫,当时伦敦有医生500人,其中江湖医生250人,最后的情况是他们大都逃跑了。(12)
医生的逃跑加重了患者就医的困难和本已存在的社会混乱,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由于医生匮乏,一方面是江湖游医昧着良心大发鼠疫财,另一方面是大量患者无人看管,死者枕藉。据1665年伦敦大鼠疫时留守的医生威廉·博赫斯特记载,“在伦敦城每周死亡四五百人时,由两三个年轻医生来医治四五千病人,相比较而言,医生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当一周死亡人数超过两三千人时,这两三个人还有何用呢?由于没有医生,胃病患者甚至去找牙医。在鼠疫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看病,但是有学问的医生却很少”(13)。除了医生,护理人员也很缺乏。那时雇佣一名女护士需要很高的费用,而她们面对被感染的威胁,也尽量保持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很难真正照顾病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病投医很困难,特别是穷人,普通的七口之家一周只要6先令就可以维持生活,而医生造访一次就需要花费10先令。(14) 伦敦的律师、查理一世时期的保守派官员约翰·库克对于医生收取高昂的出诊费很愤慨,他说,医生出诊一次收取10先令太多了,医生就像疾病一样在吞噬病人。(15) 因此,除非迫不得已,穷人们是不敢找医生看病的。医生的这些做法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正统医学的反对者抓住医生逃跑的把柄,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海尔蒙特医学化学学派就攻击正统医学是失败的。一些医生中的开明之士也对医生逃离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如前文提到的医生威廉·博赫斯特。另有一些医生则从纯粹的医学角度批评医生们的逃跑行为。医生托马斯·威利斯(1621~1675,皇家医学院医生,著名解剖学家)指出,鼠疫时医生因抛弃病人而无法得到第一手的疫病知识和诊疗经验,也就更加容易拘泥于成说而无所创新。(16)
二
医生人数少且经常是临阵脱逃,这是当时的实情,但是毕竟也有部分医生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留下来医治病人。事实上,病人投医难并不是导致鼠疫难以控制的关键,关键在于即便有医生,他们也难以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当时鼠疫的治疗之中,可以看到有不同专业类型的医生参与其中,如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以及民间的江湖郎中等。各种《鼠疫手册》或《瘟疫手册》是他们宣传疗法,互相竞争,以便确立自己地位的工具。内科医生主要是帮助病人从体内驱除鼠疫造成的发烧,增强身体抵御鼠疫的能力。外科医生主要是祛除鼠疫患者皮肤表面的脓疮和肿块。药剂师负责开药,如外抹膏、药片、干药糖剂等。在实际的治疗中,往往很难将内科、外科医生区分开来,很多外科医生的手术是由内科医生决定、而由外科医生负责施行的。
皇家医学院是传统医学的代表,以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医学与盖伦医学作为医学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人感染鼠疫是体液失衡所致,人体自身本来有能力将毒素排出体外,但是患病的人失去了这种自然本能,已经没有能力将毒素排出体外,因而应该通过催吐、通便、发汗、拔罐、放血等方法来祛除体内的毒素。医生一般根据患者染疫的时间长短和病情轻重来决定治疗方法,染疫时间短、病情轻的采用催吐、通便等方法。一般用芸香作为催吐剂,帮助病人将毒素从体内排出;病情较轻的病人,则服用由无花果、核桃和盐配制成的药,助其解毒通便。(17) 在这些药物短缺的情况下,也有一些江湖游医采用其他冒险的方法以达到催吐通便的效果。当时的医生威廉·博赫斯特记载,1665年,一个江湖郎中兜售自制的药丸,宣称可以将鼠疫带来的内热排出,但实际上他的药丸就是罂粟和常见的藜芦根的混合物。威廉·博赫斯特说,这确实能够起到催吐的作用,但是病人在呕吐之后,接着便可能会窒息乃至死亡。(18) 当然,即使采用了正常的催吐通便的方法,按照现代医学的研究来看,也不能阻止疫情的发展。鼠疫的临床治疗需要的是抗菌药物,那时显然还没有发明出有效的抗菌药物。
当病人的病情较重时,则采用放血、除痈等办法,这一般由内科医生决定,而由外科医生来实施。放血是鼠疫临床治疗中经常使用的办法,同样也是为了清除患者体内的毒素。至于放血的时机和量的多少,则由患者的症状决定,一般在患者皮肤表面出现黑斑之后而没有溃烂之前采用。(19) 有的时候通过放血病人奇迹般地好起来,因而看似放血起了作用。但是,按照现代医学对鼠疫的治疗手段判断,放血并没有什么实际疗效,毕竟腺鼠疫的死亡率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此外,如果在对疾病类型判断错误的情况下,病人也许并不是得了鼠疫,可能患有体表症状与鼠疫体表症状相似的其他疾病而被误当成鼠疫。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病人本来就可以自愈。放血只是在没有疗法的时候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在更多的时候它加速了患者的死亡,因此放血遭到患者及其家属的反对。当时的医生托马斯·西登哈姆就曾表示:“我不能自由地为病人放血,因为病人的亲属在旁边监视着我,他们不允许我抽取适量的血,因此我多次失败。”(20) 因为鼠疫并非体液失衡所致,所以传统的催吐、放血等治疗方法并不对症;现代医学的研究也证明,这些方法对于治疗任何一种类型的鼠疫都不合适。(21)
在身体出痈之后便不再适用于放血了,此时,内科医生和药剂师会为病人提供膏药,让炎症继续发展,直至痈疮成熟,然后进行手术。对于刚成熟的肿块,要先将脓液挤出,然后予以切除。炎症和成熟后的痈疮肿块本来就使病人疼痛难忍,而手术又无麻醉药,有的病人往往因此而疼痛致死。按照现代医学中的鼠疫疗法,患有腺鼠疫的病人,在肿大的淋巴结软化之后,可以将其切开排除脓液。从这一点上看,施用外部手术在治疗原理上是对症的,但是现代医学强调在手术前24小时必须应用足量的抗菌药物,以防病人感染细菌。(22) 由此可见,手术疗法仍然有局限性,而且实行外科的切除手术并不为当时的医生所推崇;更何况,当时外科医生地位本来就低下,人们也不认同外科医生,而且一次手术需要花费太多钱。外科手术只对肺鼠疫患者有效,病人选择进行外科手术的又很少,成功的则更少。按照当时的惯例,医生进行外科手术,还必须对手术的结果进行跟踪观察,一个医生一年只能施行两三次手术。这样看来,这种手术疗法在当时鼠疫爆发时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正统医学拿不出有效的疗法时,一些反对正统医学的新医学流派便试着探索以新的药物和方法来治疗鼠疫,在这方面医学化学学派的成绩比较突出,其代表人物是皇家医学院医生、牛津大学著名医学家托马斯·威利斯。对于当时频发的鼠疫,托马斯·威利斯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论证,并提出用汞、锑、硫、砷以及硫酸盐来配制药物,用以杀灭鼠疫病菌。(23) 这种治疗方法符合现代医学的抗菌原理,但汞、砷这些物质毒性较高,难以直接服食,临床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总之,由于认识水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新医学,面对肆意横行的鼠疫,他们的种种努力的效果都极为有限。
由此可见,面对鼠疫的肆虐和频发,伦敦的医疗界亦曾进行了各种应对活动,采取了一些治疗手段,以图解除病人的痛苦,挽救民众的生命。由专业的医生来做这些,比之中世纪的牧师医生们以拯救灵魂为第一要旨显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从伦敦医疗界的医疗活动可以看出,16~17世纪的鼠疫医学始终没能在临床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因医治而痊愈的病人寥若晨星。
三
医学的水平不足以提供有效的临床治疗时,卫生保健就显得越为重要和流行。提供卫生保健的指导可免于与病人直接接触,防止被传染,因而是应对手段中医生最为推崇的。在伦敦发生鼠疫的时候,医生们就不断地为个人和公众提供各种预防保健的建议,当时关于卫生保健的各种小册子成百上千。
从这些小册子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正统医学与新医学的理论混杂在一起。以皇家医学院为代表的正统医学秉持着四体液说(24),认为体液失衡使人感染了鼠疫,体液失衡的原因就是外界的肮脏之气。医学化学学派(25) 则认为瘴气进入体内发生了化学反应,因而发病。不论是正统医学还是新医学,都将环境卫生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疾病的病因说直接产生出疾病的应对方法。对于鼠疫的应对来讲,各派预防建议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是要清理、祛除各种脏物与瘴气,保持环境卫生和身体的清洁。这些预防的方法有传统的方法,也有新的方法,在鼠疫爆发的年份,它们都曾被应用过,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立竿见影和尽如人意。
1.清除污秽
在伦敦,每逢发生鼠疫时,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医生们都会向政府提供建议,社会上的普通医生也会编制各种手册宣传防疫措施。在他们提出的建议和防疫措施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清除城市中的污秽,包括各种垃圾、污物以及瘴气。
1603年伦敦发生大鼠疫时,医生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在他的《瘟疫手册》中就建议城市的官员们尤其要关注城市的卫生,远离那些可能滋生鼠疫的垃圾与恶臭,因为不干净的气味会影响空气,因此要彻底清扫城市卫生。(26) 托马斯·塞耶在《瘟疫手册》中也称:“要尽量保持街道、小巷的清洁……尤其是在郊区,如果街道不清洁的话,会有恶臭发出,这就会污染空气,加重鼠疫。”(27) 牧师医生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尽管在解释上与世俗的医生不同,但是同样指出了环境与疾病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一个名为尼古拉斯·邦德的牧师医生这样表达了他对鼠疫的看法:上帝会通过一定的中介让人生病,这些中介包括不洁净的水、肮脏的空气以及没有埋葬的尸体等。
祛除瘴气也很重要,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瘴气会传染鼠疫,因此需要净化空气和换气。用火熏呛空气是当时普遍认同的方法。在1578年枢密院颁布的鼠疫法的末尾,印制了皇家医学院的建议(28),其中指出了应该如何使用这种方法:将姜、迷迭香以及玫瑰花捣碎,放到盆中,然后置于火上烧,使得它们发出气味,来熏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另外要经常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
鼠疫时期火被大规模使用。弗朗西斯·赫林称,在发生鼠疫时,“要在晚上净化空气,在低地和有水的地方架上木材,并将芳香植物投入其中”(29)。在发生鼠疫的1563年,伦敦每周要点火三次,时间是晚上7点。1603年发生鼠疫时,在夜里用树脂点燃篝火,每周两次。1625年,圣·克里斯托福堂区买了土龛、焦炭、松脂,以备点火之用。皇家医学院的医生也说,经常在大街上点火,尤其是在有疫情的地方,就可以免受污染。但是,对于某些堂区来讲,点火也是昂贵的,特别是在杜松和其他芳香植物短缺的时候。史蒂文·布雷德维尔是当时的一个医生,他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他说:“希波克拉底所说的净化空气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讲却是太昂贵了,因此我建议使用火枪,每一天的早晚在城市每一条街道、小巷都放一次。这虽然不像点火那样可以产生持久的热量使得空气流动,但是火枪的突然一击也可以使空气流动,同样能够起到净化空气的效果,因为火枪中的硫散发到空气中,可以达到杀菌的效果,这对我们的健康有利。”(30)
对于点火或者是向空中放枪的做法在当时就有着争议。1665年,著名的医生纳萨尼尔·豪奇斯认为,医学院的医生们夸大了火的作用,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伦敦点火的那三天,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4000人。(31) 威廉·博赫斯特则认为,空气的污染来自于地球内部发出的气体,而不是空气自身。他说:“我并没有在家中为改换空气做些什么,但是我想我家的空气与邻居家的一样的健康,邻居家每天都在熏香、换空气,我没有做这些,但是我也健康地活着。”(32) 威廉·博赫斯特受到了新科学的影响,他既怀疑传统的点火、熏香等预防方法,又不相信新出现的一些做法,如医学化学学派所认为的通过放枪可以使火药中的硫与空气发生化学反应,以此净化空气。但是,医生托马斯·威利斯却是一个对新旧观念和方法都接受的人,他既赞同传统的点火、熏香的方法,也接受枪击空气的方法。
对于当时祛除瘴气所用的种种方法是否有效,现代研究者也有自己的观点。英国医史学家安德鲁·韦尔认为:“点火或者放枪只具有象征意义,这样的方法不可能吓跑鼠疫或者杀死病菌,就像声称放鞭炮和制造很大的声响就会带来新年和开始新的生活一样,那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33) 安德鲁·韦尔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从科学上讲,这些预防方法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由于鼠疫杆菌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生存繁殖,那么点火可以起到干燥杀菌的作用,也会驱逐、甚至杀死老鼠、跳蚤等传播媒介。用松香等香料来熏呛空气也有作用,因为松香也有燥湿杀菌除臭的作用。枪击空气也同样,弹药爆炸产生的硫化物也可以杀菌。当然,所有这些方法由于量的限制等因素而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在精神安慰方面还是有帮助的,因为鼠疫造成的混乱可能会比鼠疫本身更为可怕。
2.卫生保健
除了清除污秽与净化空气这些有关环境卫生的措施之外,医生的建议也包括个人日常起居、卫生保健方面的内容。例如,秉持四体液说的正统医学派的医生托马斯·科克指出了合理饮食对于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饮食要有节度,避免过量食用肉类,避免喝太多的酒,食物忌过凉和过热,否则会导致体液失衡从而引发疾病。(34)《瘟疫防治指南》一书是在1655年伦敦大鼠疫发生时由政府组织皇家医学院医生编写的,在书的封面写有“为穷人而作”的字样,书中指出了早餐、晚餐吃少,午餐吃好,早晚适量饮酒以及保持室内外卫生等,以此来预防感染鼠疫。(35) 著名的占星术士、优秀的内科医生尼古拉斯·卡尔佩珀所著的《通过饮食而不是医生来获得健康——致富人与穷人》是当时卫生保健的代表作,共有13章,指出恰当的饮食是健康的关键,要在质和量上把握好。在第6章中,作者写到了传染病与饮食的关系:
迄今为止,内科医生所知道的所有的传染性疾病都是受命运星辰的影响,命运星辰的恶不是来自于星辰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的身体……通过适量的饮食让身体保持健康,不受外界玷污,那么任何疾病都不会作用到你的身上。(36)
怎样做到适当饮食呢?作者在第1~4章讲,要根据不同的人和年龄来确定摄入的食物的质、量,普通人不可以食用太多的肉,因为那样会加重胃的负担,必须通过锻炼来消耗多余的摄入量;而体力劳动者则相反,他们应该摄入充足的肉类食物。
除了饮食要有节有度之外,医生们也强调食物的清洁与卫生。那些未成熟的蔬果,散发着异味的变质的肉类食物,以及时间过长的饮品等,都不可食用,因为吃了这样的食物会导致四体液的失衡,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些建议虽然是从传统的四体液学说出发的,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提高抗病能力。
总之,不论是作为正统医学的皇家医学院派,还是新医学的代表医学化学学派,抑或是民间的医生,他们关于预防鼠疫的建议,有一部分是积极的和具有科学性的,但是民众接受这些卫生保健与预防观念与切实地实施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医生们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建议,而且这些建议林林总总,有时互相之间还存在着矛盾,有一些建议甚至是有害的,而一般的民众则难以辨别利害。即使是好的建议,也不一定就会在社会和民众中普及,因为当时医生的话缺乏约束力,在鼠疫造成的混乱面前,很难说服人们按照建议的原则行事。
综上所述,在16~17世纪,医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鼠疫的临床治疗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在鼠疫到来时,医生又大量逃离,这无疑加重了社会的恐惧和混乱。临床治疗的落后恰恰说明鼠疫的预防在当时更为重要。对于鼠疫的预防,医生们提出了种种建议,按照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部分医疗保健建议是有效且可行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合理的建议也不可能完全得以贯彻。医疗界应对鼠疫未见明显的效果,这也说明应对传染病的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需要社会的集体行动以及有效的国家管制,但这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直到19世纪前期,公共卫生,包括鼠疫的应对,才取得了长足进步,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收稿日期 2009—10—09
注释:
① 关于鼠疫的危害,可参见:邹翔:《16~17世纪英国的鼠疫及其应对》,《中华医史杂志》2008年第2期。
② 在当时,医学正处在向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过渡之中。医疗界指的是所有行医者群体,不仅包括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医生,也包括民间的行医者。
③ 基思·托马斯:《宗教与魔法的衰落:16~17世纪英国大众信仰研究》(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伦敦:威登费德—尼克森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10页。
④ 南希·G希瑞丝:《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早期的医学:知识与实践介绍》(Nancy G.Siraisi,Medieval & Early Renaissance Medicine:An Introduction to Knowledge and Practic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⑤ 罗伊·波特:《伦敦:一部社会史》(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⑥ 安德鲁·韦尔:《英国医学的知识与实践(1550~1680)》(Andrew Wear,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English medicine,1550~168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⑦ F.P.威尔森:《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瘟疫》(Wilson,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⑧ 托马斯·洛奇:《瘟疫手册》(Thomas Lodge,A Treatise of the Plague),伦敦:利昂·里奇菲尔德1603年版,第1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0—18。
⑨ 托马斯·鲍威尔:《所有生意的手段》(Thomas Powell,Tom of all Trades),伦敦:托马斯·哈珀1631年版,第29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1—01。
⑩ 《王国法令》(Statutes of the Realm)第8卷,纽约:威廉·S.海因公司1993年出版,第906页。
(11) 约翰·科塔:《对英国几类无知、无怜悯心医生行医所隐含危险的一点觉察》(John Cotta,A Short Discoverie of the Unobserved Dangers of Several Sorts of Ignorant and Unconsiderate Practisers of Physicke in England),伦敦:R.菲尔德1612年版,第34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0—11。
(12) A.立奥德、多罗西·穆特《大瘟疫——伦敦最致命一年的经历》(Lloyd Moote and Dorothy C.Moote,The Great Plague: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Deadly Year),伦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3) 威廉·博赫斯特:《疫病论:1665年伦敦瘟疫的说明》(William Boghurst,Loimographia,An Account of 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 in the Year 1665),伦敦:[出版者不详]1665年版,第60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8—11—11。
(14) 约翰·库克:《唯一的必需》(John Cook,Unum Necessarium),伦敦:马修·沃尔班克1648年版,第61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7—06—11。可以通过当时的佣工工资水平来比较医生所要的出诊费之昂贵。在伊丽莎白时代,泥水匠的日薪为7便士,牧童日薪为2.5便士,田间零工日薪为2~3便士,农夫周薪为1先令(包吃),牧羊人周薪6便士(包吃),女佣年薪17先令(包吃包住)。以上工资水平参见:王春元:《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台湾: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15) 哈罗德·J.库克:《斯图亚特时期伦敦旧医疗体制的衰落》(Harold J.Cook,The Decline of the Ole Medical Regime in Stuart London),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16) 托马斯·威利斯:《威利斯医生医疗活动中的“热症”》(Thomas Willis,‘Of Fevers’in Dr Willis's Practice of Physick),伦敦:T.德林、C.哈珀1684年版,第111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7—03—12。
(17) 《陛下及其枢密院同意的命令》(Orders,thought meete by her Maiestie,and her priuie Councell),伦敦:克里斯托弗1578年印发,第11~12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7—04—11。
(18) 伦纳德·W.考伊:《瘟疫与大火》(Leonard W.Cowie,Plague and Fire),伦敦:维兰有限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22页。
(19) 威廉·布林:《应对热症的对话》(William Bullein,A Dialogue Against the Fever Pestilence),伦敦:约翰·金士顿1564年版,第41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2—11。
(20) 托马斯·西登哈姆:《著作》(Thomas Sydenham,Works),伦敦:理查德·威灵顿1687年版,第115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7—01—28。
(21) 鼠疫也分为不同类型,有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
(22) 参见网页:http://news.sina.com.cn/health/disease/20070420/1027.html,2007—04—20/2007—05—20。
(23) 托马斯·威利斯:《威利斯医生医疗活动中的“热症”》,第108页。
(24) 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体液平衡说,后经古罗马的盖伦进一步发展。它也是一套哲学与医学体系。四体液指的是干、冷、热、湿,其中,干+热=火,热+湿=空气,冷+干=土,冷+湿=水。相对于医学来说,热+湿=血液,指的是乐观,与春天相对应;冷+湿=黏液,指的是冷淡、冷静,与冬天相对应;热+干=黄胆液,指的是暴怒,与夏天相对应;冷+干=黑胆液,指的是忧郁,与秋天相对应。在医学上,四体液说在古代和中世纪一直是主流的医学学说。直到1570年的伊丽莎白法令,还规定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教条仍被作为官方教学内容在剑桥大学中传授。
(25) 医学化学学派的创始人是比利时的帕拉塞尔苏斯,帕氏对盖伦的医学进行了全盘否定。在他眼中,疾病不再是体液失衡的结果,不再可以通过相反物质的补充修正,而是因为体内发生了化学反应,只有用化学的方法才可以治疗,这样的结论就使临床诊断成为可能。既然疾病是身体局部的症状,那就必须进行局部治疗,这反过来也促使对人体进行正确的检查。帕氏抛弃了盖伦的“相逆疗法”而采用“相似疗法”。在英国,医学化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有托马斯·威利斯、托马斯·奥多德、乔治·汤普森等。
(26) 托马斯·洛奇:《瘟疫手册》,第1页。
(27) 托马斯·塞耶:《瘟疫手册》(Thomas Thayer,A Treatise of the Pestilence),伦敦:E.肖特1603年版,第8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2—01。
(28) 《陛下及其枢密院同意的命令》,第8~9页。
(29) 弗朗西斯·赫林:《瘟疫流行期的一些规则、指导与宣传》(Francis Herring,Certaine Rules,Dierections,or Advertisements for This Time of Pestilentiall Contagion),伦敦:托马斯·佩因1625年版,第A4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0—17。
(30) 史蒂文·布雷德韦尔:《瘟疫的看守人》(Steven Bradwell,A Watch- man for the Pest),伦敦:本杰明·费舍尔1625年版,第12~13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0—13。
(31) 纳萨尼尔·豪奇斯:《疫病论》(Nathaniel Hodges,Loimologia),伦敦:[出版者不详]1672年版,第20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1—11。
(32) 威廉·博赫斯特:《疫病论:1665年伦敦瘟疫的说明》,第61~63页。
(33) 安德鲁·韦尔:《英国医学的知识与实践(1550~1680)》,第323页。
(34) 托马斯·科克:《厨房医学:或是给穷人的建议》(Thomas Cocke,Kitchen- Physick:Or Advice to the Poor),伦敦:多尔曼·纽曼1675年版,第2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1—12。
(35) 托马斯·沃顿:《瘟疫防治指南》(Thomas Wharton,Direc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Plague),伦敦:F.格里夫蒙德1665年版,第1~2页。http://eebo.chadwyck.com,[发布日期不详]/2006—10—23。
(36) 尼古拉斯·卡尔佩珀:《通过饮食而不是医生来获得健康——致富人与穷人》(Nicholas Culpeper,Health for the Rich and Poor,by Dyet without Physick),伦敦:皮特·科尔1656年版,第18页。http://eebo.chadwyck.com/search,[发布日期不详]/2006—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