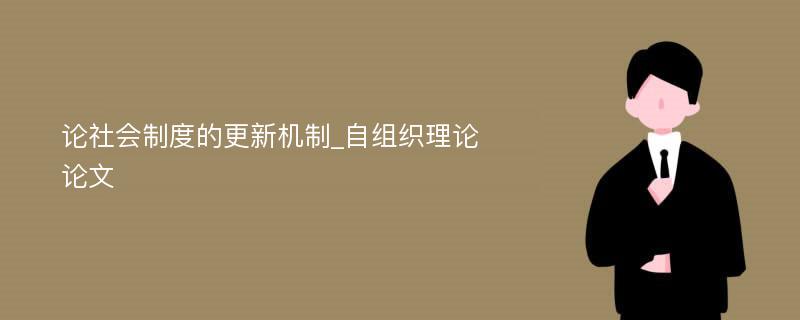
论社会系统的更新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社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40年代产生的系统论在70年代有了巨大的发展,化学家普里戈金、物理学家哈肯和生物学家艾根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同时发现了物质的自组织现象,创立了自组织理论。系统论的这一新的成果为我们认识社会特别是社会系统的更新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试图以这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为基础,从社会哲学的角度,谈谈对社会系统更新问题的一些认识。
一、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系统的序变能力
任何系统都是由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这些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存在着种种有规则的联系,这些联系被称之为系统的秩序或有序。系统在发展、衰亡的演化过程中,系统的秩序或有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要素之间和要素与系统之间表现出的无规则的随机的组合,被称之为失稳和无序。一般来说,系统的稳定与系统的秩序是联在一起的,系统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无序,无序可以看作是系统的否定因素。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恩格斯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任何系统都是过程的集合体,它在肯定自身的同时,也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和机制。这就涉及到系统的序变能力问题。
序变能力是一个系统所具有的重要素质,它是衡量系统发展能力的标志。系统的序变能力是指这个系统所具有的改变自己秩序的能力,即它所有的活力和发展的内在潜力,即系统的自维生能力。有的系统尽管有序程度很高,组织严密而且宏大,但序变能力很低,此系统就很难有发展前途。相反,有些系统的有序度并不很高,但具有很高的序变能力,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在这一点上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是一样的。熊猫处于物种寿期的晚年,虽然它的有序程度很高,但是由于它的序变能力很低而濒于绝种。而处于物种壮年的老鼠却有着很高的序变能力,繁殖力强,应变和适应能力惊人,能在核试验后的孤岛上率先大量繁殖。在社会系统中,如我国有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组织庞大、制度完善、纪律严格、有序度很高,可是它层次多、反应慢、序变能力低,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发展缓慢。而许多小型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虽然它们的有序度并不高,甚至有的制度还处于探索性的试验期,但是它们却有着很强的序变能力,能够及时地更新生产设备、改善经营品种,以非常灵活的方式适应市场的需求,有着很强的活力,因此迅速地发展起来。
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在序变能力上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序变能力的大小是和系统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序变能力的枯竭意味着系统结构的老化,只有改变旧的结构才能带来新的强大的序变能力。古代计时系统水漏装置搞得再复杂也难于提高它的计时精度,当通过钟摆定律授时达到此结构的最高水平时就再难精确了。现在的重力摆钟和铯原子钟达到很高的精度,但它们必然会像以往的计时装置一样达到精度极限,那时,无论怎样改善装置也都很难再提高它的精度,因为它的序变能力已经枯竭。这就必须通过改变旧的结构,建立新的秩序,提高序变能力,才能使系统进一步发展。同样,一个社会系统有序度很高,结构稳定而老化,其序变能力也必然随之降低。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两千年不变,社会结构稳定,从皇帝到百姓行为皆有章可循,行规言矩比比皆是,系统有序度很高;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方式的因循复制,催化循环,历久不衰。正因如此,它的序变能力很低,惰性巨大,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才步履维艰。唯有打破旧的社会结构,中断它的自催化循环链,建立起新的结构,才能使这个社会系统获得新的序变能力,跟上历史的步伐。
在序变能力上,社会系统不同于自然系统的地方在于,社会系统的序变能力是人们活动的能力,是人们对新结构的自觉选择。当人们认识到已有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无助于摄取新的社会能量(注:社会能量是能量的社会形式,是纳入了社会系统并使社会系统得以生存、运作和发展的一切能量。)之时,人们就会确定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型,并沿着这个方向改变旧的结构,设置新的联结方式,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由此可见,在社会系统中,从对社会结构老化的认识、新结构方向的确定一直到新结构目标的实现,这种序变能力无一不是人们自觉活动的表现。社会系统在序变能力上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特征,既是社会系统自维生能力的特殊性,又是社会系统超自组织性的具体表现。
二、社会系统内部偶然性的作用
社会系统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渐变发展阶段必然要达到一个序变点,在序变点以后的序变区域内系统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有很强的序变倾向,极易由原来的旧秩序跳跃式地转变为新秩序。一般说来,未进入序变区的系统是一个稳定的系统,进入序变区的系统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进入序变区的系统之所以是不稳定的,是因为它的无序。正如哈肯所说的:“无序是和大量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注:哈肯:《协同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未进入序变区的系统之所以是稳定的,是因为系统内部发生歧变的可能性很少。如果系统变化的方向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必然性。正是因为它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一特征,哈肯把它称之为“混沌”,伊·普里戈金把它称之为“分叉”,湛垦华等人把这称之为“分歧点”,等等。哈肯认为。“混沌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不寻常的个别事件,今天看来,它是很多系统的典型行为”。(注:哈肯:《协同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这种状态是系统发生序变的内在根据,也是影响序变的其他因素对系统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
系统内的涨落是影响序变的随机因素。“涨落”是源于物理学而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的概念,它指的是系统在一定时间内运动变化的平均值与这段时间内任一时刻运动变化的差异,即系统宏观状态各种随机的起伏波动。社会系统同其他系统一样,在其运行中必然伴随着涨落,当系统未进入序变区时,所有的涨落都是衰减的,对系统的结构、功能的稳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表现为微涨落。但是,当系统进入序变区后,涨落的作用会日渐增大,可能会形成改变原有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巨涨落。巨涨落形成以后,系统结构会通过其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促使某一特定的涨落获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支持,使之成为系统新序形成的主导因素,这个主导因素被哈肯称之为“吸引子”“序参量”,它的出现会对众多的涨落形成的其他可能性具有一定的支配作用,使自身成为一种最大的可能性。例如,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选择使自身受到社会重视的职业,以便获得社会对自身成长的帮助和支持。此时,社会如果通过某项改革(涨落)对教育事业加大投入,无论是收入还是名望都高于其他职业,使之成为一个吸引子,那么,教育职业就会因众多人员的追求而吸引力愈来愈大,从而改变原来的职业结构,形成一种新的职业秩序。
在从微涨落、巨涨落到新序的过程中,偶然性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系统未进入序变区之前,偶然出现的涨落不断考验着系统的稳定性;当系统进入序变区后,偶然性的涨落则提供着系统进化、演变的多种可能性,系统在尝试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寻找适合自身需要的目标。伊·普里戈金通过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证明:“系统可被描述成有组织的,并非因为它实现了一个和基本活动不同或超越它们的计划,而相反是因为某个微观的涨落在‘恰当时刻’被放大的结果使得一种反应路径优于其他许多同样可能的路径。因此,在一定的环境中,个别行为所起的作用可以是决定性的”。(注:伊·普兰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在某个分叉点附近,涨落或随机因素将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分叉与分叉之间,决定论的方面将处于支配地位。”(注:伊·普兰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生物进化树状演化趋势,在某个分叉点上,由于遗传、环境选择等各种因素的作用,生物进化的方向、速度和方式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被选择,在当时是由偶然随机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由偶然随机因素促成的这一进化方向、方式在其今后的进化中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得生物的进化必须沿着选定的方向和道路演化下去。同样,民族国家在社会形态变革关头或者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处于社会系统的序变区即分叉阶段时的不稳定阶段,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偶然性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日益增强,某一事件可能促使社会系统加速发展,也可能导致它的退化选择。中国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西安事变”,就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1920年的意大利,几乎全部工厂一度都被武装的工人占领,列宁也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熟”(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7页。),但由于劳工联盟和社会党的软弱,失去了改变旧系统建立新秩序的机会,葬送了唾手可得的革命成果。正因为在社会系统序变区中偶然性特别重要的作用,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的杰出人物大都产生在社会系统的序变阶段。所谓时势造英雄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系统进入序变区以后偶然性的作用增大了,才使得个人对整个社会系统的选择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自组织理论认为,“涨落本身也许是随机产生的,但是他们的结果却不再是纯粹随机的”。(注: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这就是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伊·普里戈金的著名论断:“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注:伊·普兰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224页。)他认为,从系统的涨落达到一个新的秩序有一个机制问题。“当一个新的结构出自某个有限的扰动时,从一个状态引向另一个状态的涨落大概不会在一步之内把初始状压倒。它首先必须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把自己建立起来,然后再侵入整个空间:这里有一个成核机制。”(注:伊·普兰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235页。)这种基核会逐渐地把自己的状态放大到整个系统,这叫做涨落放大。涨落放大是系统走向有序的自组织性的突出表现,正如埃里克·詹奇所说的,“没有这种内部的自放大,就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自组织。”(注: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哈肯从协同学的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在解释城市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时说,当一个居民区具有一定规模时,社会服务设施如学校、教师、医院、剧场、商店就会相继出现,这些设施又使得人们“增强了在足够大的居民区内定居的愿望”。不断扩大的规模,“由于人际交往的频繁和生活要求的逐渐提高”(注:哈肯:《协同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121页。),又对社会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自催化的作用下,原来居民的“基核”不断地自我放大,自行组织,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有序结构,建成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新的有序结构会通过自身的机制继续自行组织,从而保证这个结构的稳定。美国的纽约市1000万人口,所需各式各样的食品来自50个州及世界上遥远的角落,有的要耗时数日甚至数月才能达到。“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是在没有任何人的强制或统一指挥下进行的!”萨缪尔森把它归功于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注:萨缪尔森、诺德蒙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我们从非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由一个小镇(基核)通过自放大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自组织系统。
三、外部环境对社会系统序变方向的影响
当系统进入序变区以后,它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但是系统不能同时发生多种序变,而只能选择其一种序变的方向和方式。在系统实现这一序变的同时也就排除了其他的序变。然而,系统到底沿什么方向采取哪种方式发生序变,系统所处的环境将起重要的作用。例如,一只带有胚胎的鸡蛋,当处于37.8℃恒温的空气中,按自组织方式发生序变,最后孵化出小鸡;当置身于100℃水中,其蛋白质由球状折叠向纤维折叠方式发生序变,使蛋白质凝固而成为熟鸡蛋;当置身于γ射线辐射环境中,其染色体联结方式发生序变,从而改变了鸡的品种;而鸡蛋置身于污染的炎热环境中,蛋白质则向无序方向发生序变使鸡蛋腐败。同样一只有胚胎的鸡蛋,仅仅由于不同环境的作用,就导致了这个系统以不同的方式沿不同的方向发生序变。自然系统是这样,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也是这样。
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系统要同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特别是进行社会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如果说这些交流在这个社会系统稳定的条件下还只能引起微涨落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会系统进入序变区后就会引起巨涨落,环境对系统的作用就会由一般的影响而转变为对序变方式和序变方向的选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时曾说到,“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667页。)可见,中国社会系统序变的性质和方向是由当时环境所决定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影响中国革命性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与当时的世界环境是怎样的呢?斯大林是这样分析的:当时帝国主义存在着三个最重要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金融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同时它还具有“能够用革命方法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因此,俄国革命“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3-7页。)。由此可见,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这种矛盾对俄国的影响和在俄国的集中,俄国这一社会系统的序变就不会发生,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宏观系统(环境)对微观系统,机制先进的系统对机制落后的系统,那么环境对社会系统序变方向的引导和选择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就民族国家层次而言,我国近百年对环境序变的探索都体现着国际环境的引导作用。戊戌变法追随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五四”之后学习苏联(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最后按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新型的有序结构。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其国际环境对民族国家系统序变的选择就更为明显了。由欧洲经贸圈、北美经贸圈、亚太经贸圈等大区域经济引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加入亚太经济联合组织并努力进入关贸总协定,变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沟通和接轨,也体现了环境对社会系统序变方向和方式的选择作用。就更小的社会系统而言,譬如一个社区、一个民族,其环境对此系统序变方向和方式的选择作用就更为突出。我国解放前,鄂伦春人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西藏尚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这些系统存在的多种可能的序变方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环境的选择作用,使他们分别从落后机制的社会系统序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这些国家、民族、社区等社会系统的序变方向会“甘心”受系统环境的选择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使这些社会系统保持与环境的一致性,这正是社会系统自维生特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这样一种分析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呢?当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元哲学的角度,考察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论证了与自然系统相对立的社会大系统结构序变的内在机制。他们认为,人们对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物质生产活动解释人们的交往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32页。)。这个理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系统来说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上面的分析依然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所不同的是,我们是从社会哲学的角度,考察的是民族国家。这样的社会系统,不仅有向自然环境开放的第一维度,而且还有与其他国家交流的第二维度,因此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受到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其他国家社会能量输入的影响。这样一来,民族国家的社会系统就具有了不同于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的特殊性。它自己获得社会能量的方式比较落后,但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别人已经具有的文化创造方式(如现代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能量;它自己的社会能量没有与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冲突,但社会大系统中存在的社会能量由于交流和输入可能很快与之发生冲突(如俄国),使之成为诸多矛盾的集中点;它自己可能会因文化创造方式的落后而不能积蓄起足够改变社会结构的能量,但它可以通过输入其他国家的社会能量(如我国引入外资等)而完成变革社会结构的重任。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才构成了民族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过程、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之间“离异”的现象。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民族国家的这一特点,例如亨廷顿说:“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注:塞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阿尔蒙德也说:“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并不是一回事。”(注: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这些论述仅就民族国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实反映了当代一些国家的实际。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们关于民族国家社会系统的序变方向和方式由国际环境选择的结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第二,民族国家社会系统的序变确有不同于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大系统自组织过程的具体机制,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说明了民族国家社会系统的自维生特性;第三,在我国进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要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既要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并与世界惯例接轨,又应发挥我们的超自组织能力,根据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