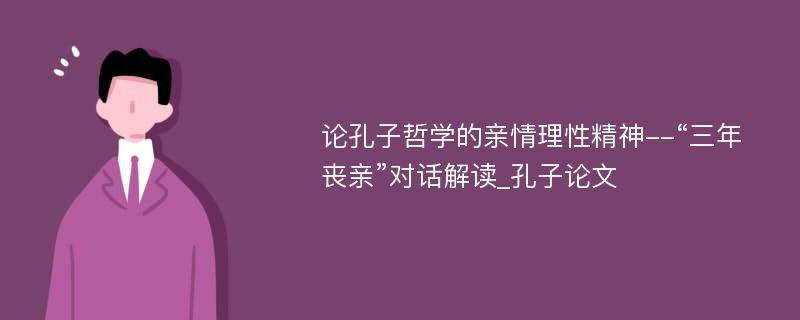
论孔子哲学的血亲情理精神——解读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血亲论文,情理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2-0033-07
一、导言
众所周知,孔子与宰我曾经围绕“三年之丧”的问题展开过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1](PP180-181)
一般来说,《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大都属于“短平快”的类型,总是弟子简要地问、孔子简要地答,如《颜渊》篇樊迟向孔子请教“仁”、“知”的对话;即便那些较长的对话,如《先进》篇“吾与点也”的交谈,也缺少严格意义上的阐发论证,不如说是扩展了的一问一答。从这个角度看,上述对话就相当独特了,因为它不仅篇幅长,而且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讨论。首先,宰我虽然对三年之丧心存疑虑,却没有以提问的口吻向孔子请教,而是通过论证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其次,孔子没有简要地解答宰我的疑问,而是向宰我提出了一个反问;在宰我答复后,他也没有用简单的断言回应,而是围绕自己的立场展开论证;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论证还延续到对话的另一方(宰我)已不在场的时候。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次对话不仅涉及到人们“有为”的动机理据问题,而且涉及到子女为什么应当“尽孝”这个对儒家来说意义重大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就使这段对话对于我们特别富于启迪意义,因为它可以由此显示孔子的论说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本文将通过对这段文本的解读,说明在孔子哲学乃至整个儒家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情理精神,尤其是一种血亲情理的精神。
二、直指人心与心安理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包括从儒家的角度看,宰我对三年之丧的质疑都是言之成理的。首先,他并没有否定守丧的必要性,而只是认为三年的时间太久。换言之,他的意图不是取消守丧的行为,而是缩短守丧的期限。其次,他认为守丧三年太久,不是因为觉得这样做难以忍受或有损健康,而是担心这样做会使君子长期远离职守、危及礼乐制度,也就是朱熹指出的“恐居丧不习而崩坏也”[1](P181)。所以,鉴于孔子不仅一贯强调维护礼乐制度的重要意义,而且对当时的“礼崩乐坏”现象深恶痛绝,甚至大力提倡“克己复礼”,我们几乎有一切理由期望:他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宰我的短丧之说。
出人意料的是,孔子根本不赞同宰我的见解(原因详后);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反驳宰我的论据。本来,他可以通过理性的计算告诉宰我:由于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君子守三年之丧、大多数君子则会恪尽职守,所以三年之丧不会构成维护礼乐制度的严重障碍。或者,他也可以从注重长远实效的角度强调:如果君子坚持三年之丧,就能在慎终追远中确保民德淳厚,从而最终有助于巩固礼乐制度。然而,孔子却没有诉诸这些有说服力的论据,而是反过来向宰我提出了一个只涉及他个人的内心感受、与维护礼乐制度毫不相干的问题:倘若守丧一年后就锦衣美食,你心里安不安?在宰我给出肯定性回答后,孔子又围绕这一点继续论证,一方面两次以反讽的口吻宣布“女安则为之”;另一方面认为:君子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感到“不甘”、“不乐”、“不安”,所以不应当去“为”——“故不为也”。
从这里看,在基于什么理据从事行为的问题上,孔子最关注的既不是理性的可行性,也不是实践的成效性,而首先是人的内心状态尤其是情感状态。借用后来禅宗的术语说,“于女安乎”的反问其实是“直指人心”;而孔子紧接着将“甘”、“乐”、“安”并提,则进一步显示:他最看重的又是人们心中安适和乐的情感体验。换言之,在孔子看来,人们是不是应当从事一年之丧,在根本上取决于它能不能使人们的内心处于安适和乐的状态:如果一年之丧可以使人们感到安适和乐,就可以去做,反之则不应当去做。这样,他便从一个“直指人心”的问题出发,提出了一条“心安理得”的准则:只要内心安适和乐,人们就拥有了从事行为的理由根据——或者说:一旦心中安适和乐,行为自然合情合理。
进一步看,这条“安则为之”的准则也不是孔子为了说服宰我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他坚持的一贯之道。在《论语》中,他经常提到“安”和“乐”,把这些情感心态说成是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首要动机和根本理由,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乐以忘忧”(《述而》)等。孔子当然不否认知识、意志、实效等因素在人类行为中的积极意义,如他反对“不知而作”(《述而》)、强调“志于道”(《述而》)等;但在他看来,构成人类行为的终极理据的,既不是理性的知识,又不是意志的选择,也不是实际的效果,而首先是情感的安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的名言就是强调:对于人们从事道德行为来说,单纯的认知不如喜好的志向,喜好的志向又不如乐在其中的身体力行。我们还可以由此品味“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的微妙差异。正如朱熹所说,这二者间存在着“深浅之不同”[1](P69):仁者是在内心之“安”中坚守仁,智者是出于“利”的考虑实行仁。至于孔子自己常常体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倾向,也是由于他在确立行为的理据时把“安”置于“知”之上,因此虽然明知某些行为在现实中不具有可行性,却为了内心安适的缘故依然去“为”。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哲学的主导精神其实是一种情理精神,一种把安适和乐的情感心态当作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哲理精神。
三、自然欲情与道德感情
作为人的一种内心状态,“安”可以发生在情感体验的不同维度上。上述对话便涉及到其中的两个维度:食稻衣锦的本能欲情与尽孝守丧的伦理感情。那么,被孔子视为终极理据的又是哪个维度上的“安”呢?自然是道德感情之“安”。
表面上看,孔子声称“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似乎是自相矛盾。一般来说,人们食稻衣锦的时候总是会感到甘甜安乐,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满足生理的需要。孔子不是禁欲主义者,当然不会否认这一点;相反,《乡党》篇还记载了他对衣食住行标准的种种严格要求。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宣布“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呢?难道这是出于他的虚伪矫饰吗?
当然不是。这其实是孔子面对自然欲望与道德情感的冲突做出的真诚选择。在二者没有冲突的时候,孔子总是充分肯定本能欲情的积极意义,并且要求把它们与伦理感情内在地统一起来,希望人们“好德如好色”(《子罕》)。然而,一旦二者出现冲突,孔子就毫不犹豫地主张“舍欲以取德”。他强调“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便清晰地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肉体生命固然重要,但在不能得兼的情况下,君子为了实现仁义理想应该勇于放弃肉体生命。同样,虽然食稻衣锦可以更好地满足生理欲望而使人们感到安适和乐,但在为父母守丧的情况下,这种安适和乐却会与道德感情(促使君子守丧的血缘亲情)发生冲突,导致君子陷入“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因此,这里说的不甘、不乐、不安,不是就自然欲望的满足而言,而是就道德情感的满足而言;至于君子之所以不应该在一年丧期后就食稻衣锦,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满足肉身需要的方面感到“心安理得”,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实现伦理感情的方面感到“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在孔子看来,如果一种行为只能使人在自然欲情的维度上感到安适,却不能使人在道德感情的维度上感到安适,君子就不应当从事它。这条以道德感情的安适和乐作为人类行为终极理据的准则,应该说也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因为他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都是旨在强调伦理情感的安适和乐高于自然欲望的安适和乐。
表面上看,既然孔子主张伦理道德可以超越感性欲望,他的哲学就应当属于“道德理性”了。这其实是把西方主流哲学的理论架构套在孔子哲学之上。问题在于,从苏格拉底起,西方理性哲学总是在道德层面上突显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要求凭借善的理性知识压抑恶的感性欲情,由此确立了道德理性精神。休谟正是针对这种道德理性精神主张:道德不是以理性知识为基础,而是以“同情”为基础。在这方面,孔子哲学与西方主流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却与休谟较为接近。首先,他不认为理性知识构成了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相反更强调道德情感在伦理生活中的决定性意义。其次,他也没有突显理性认知与感性欲望的张力冲突,相反总是力图把自然欲望与道德行为统一起来。最后,孔子认同的应当超越感性欲望的道德,也不是理性化的伦理规范,而首先是一种具有浓郁感性内涵的道德情感,如忠、孝、仁、义等。例如,在这段对话中,他要求君子用来克制食旨、闻乐、居处等感性欲望的关键因素,就不是理性的知识智慧,而是感性的血亲情感——“孝子之心”。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断言休谟哲学是“道德理性”的话,我们也没有理由断言孔子哲学是“道德理性”。归根结底,孔子哲学的主导精神是一种道德情理的精神,一种把道德情感当作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哲理精神,一种主张“合情”就是“合理”的道德精神。
四、作为本根的血缘亲情
在《论语》中,孔子讨论了许多可以超越自然欲望的道德情感,如对父母的孝、对君主的忠、对普通人的仁等。由于上述对话围绕三年之丧的问题展开,它涉及的人伦情感主要是孝。但奇怪的是,孔子在指责宰我的时候不是说他“不孝”,而是说他“不仁”。本来,宰我即便缺少对父母的三年居丧之爱,也只能说是不孝,不见得他就一定缺少其他道德情感(比方说,他至少就不缺乏维护礼乐制度的道德热情)。那么,孔子为什么批评宰我“不仁”呢?这不是以偏概全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有若的一段话中找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这里说的“仁”,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感情(“爱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包括知、勇等其他德性在内的综合性德性(“仁者必有勇”等),甚至还可以理解为“人”理应具有的道德本质(“仁者,人也”)。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理解,孝可以说都构成了实现仁的本原根据。孔子显然赞同有若的这一见解,因为他也反复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在各种道德感情中,作为血缘亲情的孝占据着本根基础的独特地位。也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才能解释孔子为什么指责宰我“不仁”:虽然宰我似乎只是缺少对父母的三年之爱,但在孔子看来,他缺少的恰恰是一切道德感情的终极本根。
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要赋予血缘亲情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他接下来就给出了答案:“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本来,父母生育抚养子女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生理现象,在其他动物那里也能发现类似的活动。不过,孔子在此提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关注这种现象的生理意义。毋宁说,他的目的是从伦理高度强调:既然父母通过生养活动给予了子女以生命,他们就构成了子女存在的源始本根。一旦确立了这一前提,结论也就清楚了:子女应当通过孝的行为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并由此确立自己在道德上为人(“仁”)的根本。所以,孔子紧接着又谈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因为后者正是当时的礼制明文规定的一种孝行,要求君子在父母死后以守丧三年的方式继续对父母尽孝。
孔子随后又问:“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在宰我缺席的情况下,这一质问似乎有点无的放矢,但它其实是孔子全部论证的画龙点睛。当然,这句话在字面上可以理解成“宰我你没有得到过父母的三年之爱吗”[2](P189),也就是以宰我为例再次申述了“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事实。不过,如果换一种角度把它理解成“宰我你没有对父母的三年之爱吗”,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孔子哲学的精神实质:他不仅要求子女在三年之丧中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而且要求子女充满血亲之爱地为父母守孝三年。换句话说,子女不能只把三年之丧当作一种出于礼制规范不得不遵守的外在义务,而应该在内心深处的真挚亲情中,心甘情愿地履行“天下通丧”的既定制度。事实上,孔子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父母不仅应当“养”、更要“敬”的关键恰恰在于:父母与犬马截然不同,犬马只是人们豢养的实用工具,父母却是子女存在的源始本根。对自己的工具只需“养”、不必“敬”;但对自己的本根不仅要“养”,而且更要“敬”,不“敬”就不足以突显父母作为本根的终极价值,就是忘“本”。所以,如果缺失内心的真诚敬意,即便有“养”父母的举动,也不能视为“孝”。进一步看,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也是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强调:倘若缺失“仁”的真诚情感,从事礼乐活动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孔子便从“直指人心”和“心安理得”的根本精神出发,将周朝确立的一系列外在礼制规范建立在人们内心道德情感尤其是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以情释礼”(依据内心情感尤其是血缘亲情说明各种礼制规范的理由根据)这一意义重大的文化精神转型。①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在“宰我出”后发表的这段言论,表面上似乎是独白式的自言自语,实际上却是围绕“孝”的核心价值发布的一份儒家宣言:人们安身立命的源始本根就是自己的父母;与此相应,人们道德存在的深度基础、乃至人之为“仁”的本质所在,也就是人们对生身父母发自内心的血亲之爱。所以,如果一种行为(比如说一年之丧)不能使人们的孝子之心感到安适,它就是不道德的(“不仁”),人们也不应当从事(“不为”);甚至,如果人们在从事某种道德行为(比如说三年之丧)的时候内心缺乏真诚的血亲情感,这种行为也会丧失它本应具有的伦理价值变得没有意义。一言以蔽之:对人来说,任何缺失血缘亲情的观念举动,都等于是忘记了父母生养自己的终极事实,都等于是忘记了自己人之为人的源始本根,因此也就等于是终极性的“忘本”和“不仁”。
现在我们也许就能理解,孔子开始时为什么要反问宰我“于女安乎”,却没有采取那些似乎更有说服力的论据了。道理很简单:在他看来,那些论据只触及到问题的枝叶,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宰我没有从“子生三年”的经历中体验到血缘亲情对于自己道德存在的本原意义,体验到指向父母的“三年之爱”对于自己立身为人的终极价值。因此,只有凭借“直指人心”的手法对宰我当头棒喝一句“于女安乎”,才能使他真正领悟三年之丧的重要意义:如果守丧一年后便食稻衣锦,他就没有充分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他对父母的血缘亲情就没有真正实现,他的孝子之心就会陷入不安不忍。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反问的“于女安乎”,也不是随便泛指哪一种道德情感之“安”,而是首先指血缘亲情这种最本根的道德情感之安。朱熹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指出:“夫子惧其真以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使之闻之,或能反求而终得其本心也。”[1](P181)这里说的“本心”,正是指人们在血缘亲情层面具有的“本原之心”。就此而言,孔子哲学的主导精神其实是一种血亲情理的精神,一种把血缘亲情这种特定的道德情感当作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哲理精神。
五、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
不过,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即便血缘亲情构成了礼乐之本、道德之本、为人之本,即便不守三年之丧会使君子的孝子之心陷入不安不忍,但在恪守三年之丧的过程中,君子还是不得不为了履行这种私德的义务,放弃他们在维护礼乐制度方面理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从而不利于实现仁政的理想。孔子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张力。首先,他并没有断言三年之丧不会对礼乐制度造成任何损害;其次,当他指出君子在守丧期间应当“闻乐”不乐的时候,他所说的“乐”恰恰是君子理应维护的“礼乐”之“乐”。但从上述对话看,如果说孔子在道德感情与自然欲情出现冲突的时候宁愿“舍欲以取德”的话,那么在血缘亲情与礼乐仁政出现冲突的时候,他却似乎宁愿“舍礼以取孝”。
孔子的这种选择好像很难理解。一般来说,既然血缘亲情主要限于家庭内部,礼乐仁政却广延到社稷国家,那么,后者就理应具有超越前者的更重大意义。因此,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人们自然也不应该凭借“舍礼以取孝”的选择,为了固守指向父母的“孝”,不惜放弃维护社稷的“礼”。这可以说正是宰我的思路:君子应当在守丧一年后便投身于维护礼乐仁政的公共职责,否则就会因为有可能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在涉及社稷国家的道德情感方面陷入“不安不忍”。
然而,孔子的思路明显不同。他当然不否认礼乐仁政的重要意义,但在他看来,既然血缘亲情构成了礼乐仁政的“本”,那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到任何伤害;甚至在与礼乐仁政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也只能放弃这些更远大的目标,以维护作为本根的血缘亲情。否则,一旦这个本根受到伤害,建立在它之上的一切(包括礼乐仁政的远大目标)最终都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沦为无本之木。这才是孔子不赞同宰我的最根本原因。在宰我看来,血缘亲情固然重要,但其意义无法超越礼乐仁政的崇高价值;因此,哪怕放弃三年之丧会使君子在血缘亲情的层面感到不安,也应该为了礼乐仁政付出这个必要的代价。而在孔子看来,礼乐仁政固然重要,但其意义却无法超越血缘亲情的终极价值;因此,哪怕三年之丧会对礼乐仁政造成损害,君子也应该为了血缘亲情的内心安适付出这个必要的代价。结果,孔子在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基础的地位之后,又赋予了它以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其实,这二者间本来就存在内在的关联,因为只要人们赋予一个东西以终极本根的地位,就必然会相应地赋予它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价值。
进一步看,上述观念同样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论语》这部经典中,他虽然十分强调血缘亲情与其他道德规范的统一,但在出现冲突时却从没有主张“舍孝以取其他道德规范”,而总是要求“舍其他道德规范以取孝”。《论语》中一些令人困惑的论述大都与此相关。例如,在“其父攘羊”的情况下,孔子要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认为血缘亲情的价值高于诚实正直的价值,因此人们可以为了父慈子孝不惜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再如,他还宣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宋儒在解释这一命题时指出:“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1](P51)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哪怕“父之道”属于不仁不义的“非道”,出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忍”的缘故,人们也应该在三年内坚守这种不仁不义的“非道”,以免父子间的血缘亲情受到伤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哲学的血亲情理精神,其实是一种不仅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地位,而且赋予它以至上意义的哲理精神。
然而,孔子的这种一贯之道却包含着内在的悖论:一方面,他强调血缘亲情构成了礼乐仁政之本,君子应该由此出发实现礼乐仁政;另一方面,他又赋予血缘亲情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价值,认为在出现冲突时,君子应该为了维护作为本根基础的血缘亲情,不惜牺牲礼乐仁政的远大理想。换句话说,他把血缘亲情确立为本原根据,本来是为了实现礼乐仁政的远大理想;但在出现冲突时,他却允许君子为了避免血缘亲情陷入不安的缘故,放弃礼乐仁政的远大理想。或许,这个悖论就是他的“直指人心”的一番论证没能说服宰我的主要原因。
六、结语
虽然孔子的论证当时没能说服宰我,但他确立的血亲情理精神却打动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儒者,构成了儒家的主导精神,并通过儒家在古代社会的独特地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构成了炎黄子孙文化精神构造的基准范型。
孟子首先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哲学的上述精神。一方面,他发扬了孔子首倡的“心安理得”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观念,并由此把恻隐羞恶等道德情感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要素,视为能够成功地实现“治天下”的内在动机(《孟子·公孙丑上》)。另一方面,他又发扬了孔子首倡的“血亲情理”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的观念,不仅把血缘亲情视为惟一的本原根据(“一本”),而且明确肯定了血缘亲情的至上意义(“为大”),并由此把“孝父忠君”的道德情感说成是人兽之辨的本质因素,宣布“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在与墨家夷子围绕“掩亲之道”展开辩论时,孟子更是特别指出:“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此,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孟子·滕文公上》)这段辩论可以说是“三年之丧”对话的精妙再现:同样涉及父母死后如何尽孝的问题,同样依据作为“一本”的血缘亲情,同样诉诸“中心达于面目”的不忍之心。差异或许在于:第一,孔子与宰我的对话面对面进行,孟子与夷子的辩论背靠背展开;第二,孔子没能说服自己的弟子,孟子却感化了自己的论敌(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难怪儒家的道统没有选择孔子的亲炙弟子,而是选择了相隔两百年的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惟一正统。
宋明儒学和当代儒学同样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哲学的上述精神。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个例证予以说明。在为孔子的“父子相隐”观念辩护时,朱熹等人反复强调:“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也,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1](P146)这些辩护可以表明:宋明儒学提倡的“天理”同样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道德理性”,而是与“人情”首先是血缘亲情密不可分的“道德情理”,以致可以说合乎“人情”就是合乎“天理”;所以,只要“爱亲之心”没有陷入不安,人们就不必计较诚实正直、公正守法等行为准则,因为这种爱亲之心本身就是最高的“天理人情”。再如,牟宗三在反驳“理智主义者”对儒家孝道的质疑时也指出:“依中国人的老观念,父母去世时不能戴金框眼镜,也不能穿绸缎,只能穿麻布。但是胡适之说:我为什么不能戴金框眼镜呢?……金框和银框都是金属,有什么分别呢?绸缎和麻布又有什么分别呢?这样一来,就把孝道否定了……你一问为什么,你就不是人,而是禽兽”[4](P447)。这段论述可以说是孔子“三年之丧”对话和孟子“掩亲之道”对话的现代演绎,它再次从一个角度清晰地表明:儒家思潮的主导精神并不是“道德理性”的精神,(难道“理性”精神会宣布“你一问为什么,你就不是人,而是禽兽”?)而是一种主张血缘亲情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本根至上价值的“道德情理”精神。
孔子哲学的这种血亲情理精神,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国人文化精神构造的深度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从下面这些至今还在流行的短语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种影响的深刻痕迹:“心安理得”、“于心不安”、“于心不忍”、“何乐而不为”、“合情合理”、“天理人情”、“情有可原”……。一方面,这种血亲情理精神包含的深度悖论,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一系列负面的效应(包括国人行为中的种种劣根性),如不讲公德、一盘散沙、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孔子哲学的这种血亲情理精神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因为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其他哲学家能够像孔子这样,在一段不超过两百字的对话中,如此精辟地揭示血缘亲情的重要意义,说明道德情感的安适和乐对于人类行为的内在价值,强调“人心”中包含的不同于“理性”之理的独特“情理”,并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对于如此众多的人们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孔子与宰我的这段几乎包含着儒家血亲情理精神的所有基本内涵的对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2010-10-20
注释:
①李泽厚将这种文化精神转型称之为“以仁释礼”,《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