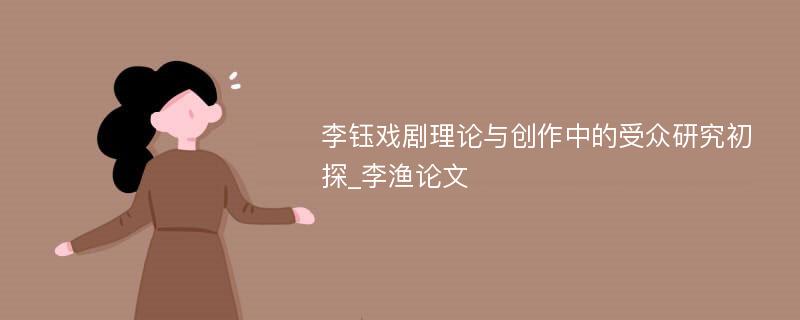
李渔的戏曲理论与创作中的观众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戏曲论文,观众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2-0028-06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戏曲艺术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演出场地从城市逐步向地域辽阔的广大农村发展,作为观众队伍的主体,封建士大夫阶层逐渐被人数众多的亿万农民和市民阶层所取代,戏曲艺术也展开了“俗唱”与昆曲的激烈竞争。如明代张岱这样记述天台某村的演剧活动:“土人于其外搭棚演戏四五台,婆娑乐神。”[1]晚明苏州创作集团的创作也使昆曲更加贴近群众。在理论方面,李渔则是其代表人物。李渔对观众问题的重视以及他在观众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既和戏曲“雅俗共赏”的新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使这新的观念有了更加完备和具体的理论形态。李渔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较多,对于民间戏曲活动相当熟悉。他曾挥笔描绘虎丘“千人石”上赛曲的盛况:“一曲清讴石上,到处箜篌齐放。思喝彩,虑喧哗,默默低头相向。早听莫唱,十万歌魂齐丧。”[2]
李渔反对只把戏曲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的观念,主张戏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李渔主张,研究戏曲要考虑戏曲向观众演出这一特点,要从观众的角度而不是作者的角度观察分析问题。从“雅俗共赏”出发,从剧场效果、观众方面提出问题,评判是非,也就成了李渔戏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以自己对戏曲观众的广泛了解为基础总结戏曲艺术,同时又在自己创作实践中表明了他明确的观众意识和对观众学方面的许多见解。因此,李渔的戏曲理论成果既具有理论色彩,又具有实践意义。
一、观众的作用
李渔十分重视观众的作用。在他看来,戏曲离不开观众,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曲,观众是戏曲服务的对象,也是戏曲的主人。李渔认识到,戏曲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具有教育功能、认知功能和娱乐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都不是单靠戏曲艺术本身可以完成的,而必须以观众为对象,在观众的参与下才能达到。所以,他在谈到戏曲艺术功能时,总是和观众并提。他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国。”[2]把戏曲比做“木铎”,说明戏曲是为观众而设的:“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3]指明戏曲是以观众为对象的,是为了让观众“知所趋避”而存在的。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发挥戏曲“木铎”的作用,就必须“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
李渔还根据戏曲艺术和文学作品之间被接受方式的差异指出“传奇不比文章”,说明了观众对于戏曲艺术的特殊意义,提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李渔认为剧本创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搬上舞台,为观众演出,而不能存有“一毫书本气也”。因为明代中叶以来,一些文人重文轻艺,创作脱离舞台和观众,热衷于“案头”之作。对这种错误倾向李渔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批评汤显祖《牡丹亭》的一些语言不大“明爽”,观众难以理解,“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他还指出,金圣叹离开舞台和观众对《西厢记》的批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为了不脱离舞台和观众,李渔对选剧和改剧分别作了论述。他说:“吾论演习之工而首重选剧者,诚恐剧本不佳,则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无用之地;使观者口虽赞叹,心实咨嗟。何如择术务精,使人心口皆羡之为得也。”而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的欣赏趣味与习气严重影响了艺术鉴赏能力,以致“牛鬼蛇神塞满氍毹之上”而“锦篇绣帙沉埋瓿瓮之间”,“瓦缶雷鸣”而“金石绝响”。李渔认为造成这种后果“非歌者投胎之误、优师指路之迷,皆顾曲周郎之过也”[3],如果“观者求精,则演者不敢浪习”。他首先从“观者”这一面找寻形成剧场现象的社会原因,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观众把各种社会问题带进了剧场,观众事实上代表着社会的时代思潮、审美心理影响并制约着剧场艺术。李渔又把教演者看作是可以左右剧场效果的第一批观众。这种左右力量首先就体现在选剧上。
为了适应演出和观众需要,就必须对所选剧本作些必要的处理,“增减出入”,使之增添“天然生动之趣”。对古剧尤其必须如此。李渔所谓的“变调”,主要就是指“变古调为新调”。李渔认为,文学艺术“无不随时更变。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犹如自然界之“桃陈则李代,月满则哉生”[3]。戏曲如果年复一年,雷同合掌,即使章节不乖,也会使人生厌,因为观众对剧中“情事太熟,眼角如悬赘疣”[3]。因而,演出旧剧,非“稍变其音”不可。根据观众实际情况和需要,李渔提出对剧本“缩长为短”。这是针对传奇剧本动辄三四十出这一现象而提出的。另外从演出艺术的特征来看,“观场之事,宜晦不宜明”,戏剧追求“幻巧”的效果,即所谓“优孟衣冠,原非实事,妙在隐隐跃跃之间”[3],因而以夜间演出为宜。从观众的需要看,日间各有当行之事,也以夜间演出为宜。而夜间演出又不宜通宵达旦。因而,一本戏的合适演出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剧本过长,必受“腰斩”之刑。鉴于此,李渔提出“与其长而不终,无宁短而有尾”[3],于是就需要“缩长为短”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李渔看到了观众在艺术审美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到观众也参与了戏曲的创造,离开了观众在剧场的积极创造活动,戏曲创作并不算真正完成。他特别强调克服观众在观场时的被动接受状况,重视研究如何调动观众的积极性。他指出戏曲符合观众的要求,才能被接受,否则就会受到观众冷淡和拒绝。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观众不能接受是戏曲创作的最大失败。他谈到科诨时就指出,观众“只消三两个瞌睡”,就会“隔断一部神情”。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戏曲审美活动就被完全破坏了,再好的演出,也会因为观众的瞌睡,“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正因为李渔认清了观众在完成戏曲创作全过程的独特作用,所以他才对调动观众在观剧时的积极心理活动特别重视。观曲中插科打诨,一般人认为是“填词末技”。李渔则因它对于观众能起到“养精益神,使人不倦”的作用,所以特别看重它,把它视作“看戏之人参汤”,告诫人们不“可作小道观”。
李渔对观众作用的认识,还表现在他重视观众的评价和选择对于戏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上。当时一些文人因过分重视案头,写出来的剧本不能上演,也从不演出,根本不重视观众的意见,看不到观众在戏曲发展中的作用。李渔和他们不同,他特别看重观众对戏曲的反应和评价,并认识到观众的爱恶对剧目的流传和剧种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关系。他对当时观众喜爱的剧目《荆》(《荆钗记》)、《刘》(《刘知远》)、《拜》(《拜月记》)、《杀》(《杀狗记》)等,十分重视,他也看到观众欣赏水平低劣会使好剧目被埋没,而质量低劣的剧目则会到处泛溢。他对观众的作用有清醒而辩证的认识,反对一味迁就和迎合,在他看来,剧目能否流传,不仅取决于戏曲艺术本身,也受到观众欣赏水平的制约,其中的关键在于戏曲和观众的供求关系,关系一致时则存,关系失调时则废。如果能够按照观众形象化、个性化的要求,戏曲词语做到“语求肖似”、“说一人,肖一人”,就一定会受到观众欢迎。他特别强调,戏曲的发展离不开观众水平的提高。他说:“观者求精,则演者不敢浪习,‘黄绢色丝’之曲,‘外孙齑臼’之词,不求而自至矣。”[3]
二、观众的组成
李渔根据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的差别,把观众分为雅、俗两部分,又根据文化程度的不同,把观众分为“读书人”和“不读书人”;他还根据年龄、性别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剧种等对观众也有明确的区分。李渔对观众队伍组成具有的这种差别感,是观众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更为难得的是李渔对观众组成具有层次感。比如,他曾把观众分为四个层次,读书人、不读书人、不读书之妇女、不读书之儿童。李渔认识到,不读书之儿童在这几种人中理解能力最低,只要这个层次观众能够理解,其他层次观众自然也可以理解。所以在解决戏曲被观众理解的工作中,对不读书的儿童应比其他层次的观众更为重视。李渔曾指出,《荆钗记》、《刘知远》、《拜月记》、《杀狗记》之所以能得传于后,就在于头绪清楚,“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3]。在这里,李渔就是以“三尺童子”作为观众能否理解的衡量坐标。
李渔看到当时昆曲面临着弋阳、四平等腔的挑战,竞争的焦点就在于对“凡夫俗子”(即所谓的“俗”)的态度上。本来他对《南西厢》极为反感,认为它把名作《西厢》改得问题百出。但当他看到若无此本弋阳、四平就会大演《西厢》时,态度就有了变化,立即肯定这个变本的功劳就在于补了缺陷,使昆曲也能演这个名剧,避免了“俗优竞演、雅调无闻”[3]的局面。李渔认识到,昆曲要发展,就要改变旧的观众结构,必须重视对“不读书”人的争取,通过扩大昆曲在观众中的适应面,更大地扩大观众圈和观众数量,为此他提出了“雅俗共赏”的主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总结了“意深词浅”、“俗而不俗”、“浅处见才”等许多宝贵经验。“浅”则能使更多人,包括那些识字不多或理解能力极低的“三尺童子”理解;“见才”,则能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吸引雅俗两部分观众。
三、观众心理
观众有哪些心理现象,对观众的心理怎样进行调控,怎样的创作才能符合观众的心理,这些问题也曾引起李渔的注意。
(一)对观众心理的认识
李渔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握,是建立在对审美心理诸元素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1.李渔关于审美感知的认识
李渔认为戏曲艺术是形象艺术,观众对戏曲的观赏首先是以对艺术形象的体验和感受开始的。他说:“至于传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与玩花赏月,同一致也。”[3]“新人耳目”,就是李渔对戏曲观众审美感知因素的发现。为了充分调动观众的审美感知因素,李渔指出戏曲要做到“饰听美观”,以达到观众“观听咸宜”的效果,使观众审美感知得到满足。李渔还注意到观众在审美活动中情感因素的发挥,把能否调动观众看做衡量戏曲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予谓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致,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即使鼓板不动、场上寂然,而观者叫绝之声,反能震天动地。”[3]他还认识到,要使观众动情,先要戏中有情。他要求戏曲表达“人情物理”,反对“无情之曲”。对剧中的感情要调剂和控制,提出了“剂冷热”的主张。他还要求戏中感情的丰富性、起伏性,“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七情俱备”[3]。
2.李渔关于审美理解的认识
李渔认为审美理解对于发挥戏剧功能的作用很大,提出“凡阅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3]。他指出要根据当时观众中审美能力差别很大的情况,少用方言,使各种观众都能理解。他要求戏曲立主脑、减头绪、多用宾白等,也都是为了观众理解的方便。但另一方面,不要“一味显浅”,“借浅以文其不深”。他说:“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猜破而后出之,则观众索然,作者赧然。”[3]
3.李渔关于审美想像的认识
李渔认为审美想像也是观众在剧场里不可缺少的心理活动方式之一。他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2]为了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像机会,他指出词曲“意则期多,字惟求少”,戏场关目,要“出奇变相”,“令人不能悬拟”,布局要有悬念,引人思索,“令人揣摸下文”。他很重视观众想像能力的发挥,把妨碍观众想像力的窠臼、俗套视为“眼中钉”,要求拔除干净。他对观众具有的想像力也十分相信,指出对于不便于直接说出的事情,可以“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或借他事喻之”,“令人自思”。他还根据当时的演出条件,认为夜间演戏有利于启发观众的想像活动。“观场之事,宜晦不宜明”,“优孟衣冠,原非实事,妙在隐隐跃跃之间。若于日间搬弄,则太觉分明,演者难施巧幻,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观听,以耳目声音散而不聚故也”[3]。
(二)对观众心理的调控
舞台艺术可以视为启动人们心灵的开关。戏剧家就靠舞台艺术来调节和控制剧场心理。在这方面李渔提供了许多经验。
1.调动观众看戏兴趣的结构
为提高戏剧性效果,李渔首先提出结构的问题,对其最为重视。从他的感觉上来看,这可以说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把虚构的情节用心地进行组装,精致地构架起来才能调动观者兴趣。李渔曾经把这种组装方法比喻为木匠盖房子的方法,或者比喻为把切碎了的布缝成衣服的缝纫法。以下择其要者而述之。
(1)戒讽刺。李渔把戏剧看做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3],而反对把戏曲作为个人报仇泄怨的工具。基于这种认识,李渔就把如何实现“劝惩”人心作为戏剧创作构思的首要问题提出来,主张剧作者“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以之报恩则可,以之报怨则不可;以之劝善惩恶则可,以之欺善作恶则不可”[3],这样才能对观众起到教化作用。
(2)立主脑。李渔借文章主脑一词说明戏曲要求情节结构的单一。就戏曲这一具体品种的创作而言,这往往只有一人和一事,这是剧作家倾注全力要表现好的一人一事。提出“止为一人而设”、“止为一事而设”这一创作的“初心”,他认为这才是戏曲创作的主脑。这种引起创作“初心”的一人一事,理所当然是作家感受最深的、能引起作家创作激情的、自然酝蓄而成一触即发之势的人和事。因而,这一个人或这一件事,当然是有特色的和引人注意的。又因为全剧的其余枝节都是从这一事实生发而出,因而,这一人一事又必然纽结着全剧的诸人诸事,是全剧结构布局中的一个经穴所在,一个扣住全局间架的结。李渔把立主脑作为戏曲创作总体构思的最重要一环,认为剧本若无主脑,则只有“零出”精神,有了主脑,才有了“全本”力量;若无主脑,则只能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有了主脑,则是串珠有线,架屋有梁。而戏曲的艺术力量是由“全本”所决定的,因而,李渔就鲜明地提出,戏曲创作,务必立主脑!立主脑就是为了观众理解的方便。
(3)脱窠臼。李渔认为,虽然“物惟求新”是一种普遍性要求,但戏剧尤其需要求新。因为戏剧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舞台动作,观众不可能任意选择片断或随意改变演出速度,因而如果不能以新的因素引起他们的兴趣,将使人难受而生厌。又因戏场是个千万人共见的公众世界,戏剧给人以兴趣或难受都是千万人共同的事,因而不可等闲视之。李渔说,名为“传奇”,即“非奇不传”的意思:“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3]李渔批评了当时一些剧作家“彼割一段,此割一段”的做法,讥讽地称之为“老僧碎补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于是,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窠臼不脱,难语填词”。李渔认为,高明的作家善于从平淡的事情中开拓出动人的奇情新态。李渔还以说人情、关物理的经、史、古文至今家传户颂,而齐谐志怪之书不传于世为证,说明这样一个至理:“平易可久,怪诞不传。”于平易处见新奇,这样才能调动观众的积极性。
(4)审虚实。他把审虚实作为作家构思剧本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提出来。他一方面明确主张“传奇无实”,另一方面又提请作家注意,对于“观者烂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的“其人其事”,则不可任意做翻案文章而与众情相违。这种题材的创作需注意从俗,因为那些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实则是历代作家和群众的共同创作,在这些形象中反映了一代代群众的爱憎之情,也能调动观众在观剧时的积极心理活动。
(5)减头绪。李渔从演剧效果出发,提出“一线到底”的主张。李渔认为,《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之所以得传于后,就是因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3]。而明代的许多传奇作家,喜欢事多关目多,头绪繁多,李渔认为这是“传奇之大病”。因为关目一多,观众就会应接不暇,无法真正理解作品的意思。只有减头绪,才能使各种观众都易于理解[4]。
(6)巧布局。李渔要求作家在下笔之前,首先要对全剧结构酝酿成熟,做到胸有成竹,一经下笔,就可以做到“一本戏文之节目全于此处理根”,“一本戏文之好歹亦即于此时定价”。所谓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在戏剧写完一个段落后,则要注意余下悬念,“使人想不到,猜不着”,引起观众揣摩下文的兴趣。而在全本收场时,要努力做到“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李渔还要求戏剧于结尾处给观众留下特别难忘的美好印象。他说:“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亏此出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3]李渔认为,只有这种“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3],才能构成一部完整而又完美的戏曲作品。
2.符合观众要求的语言
李渔认为,从戏剧艺术的特色出发,从剧场效果和观众要求出发,是戏曲语言应具备的特色。
(1)贵显浅。李渔主张戏曲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他说:“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3]“本之街谈巷议”,说明戏曲语言的大众化;“取其直说明言”说明戏曲语言的通俗化。因为戏曲是要当众表演“与大众齐听”,不能有费解之处,而且表演艺术是流动的艺术,其欣赏过程系一次性完成,因而要一听即明,不可能再思后解。李渔指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3]李渔从舞台演出的效果进行思考,认为演戏为“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之事,因而反复强调曲词“不妨直说”,而对《牡丹亭》中某些名曲则提出了批评。李渔认为只有戏曲语言通俗化,观众才不难以理解。
(2)重机趣。李渔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不仅曲词需要机趣,其他方面如宾白等也应有机趣。李渔在论宾白时提出的“意取尖新”,即与此有关。他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3]李渔在论科诨时则提出“雅俗同欢,智愚共赏”,认为插科打诨犹如看戏之人参汤,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在论格局的冲场时,李渔又提出“养机使动”之法,他说:“有养机使动之法在。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烦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数四,未有不勿撞天机者。若因好句不来,遂以俚词塞责,则走入荒芜一路,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3]这些见解,其精神如一,都是为了使创作获得灵性,使剧本增加生机。戏曲语言的生动性是调动观众积极性的源泉。
(3)求肖似。李渔认为,“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而要“肖”人“切”事,则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而性格化的关键在于“中生”之情。“景乃众人之景”,而“情乃一人之情”,因而即使写景咏物,也应落在“即景生情”上。李渔进而提出“欲代此一个立言,先宜代此一个立心”,认为剧作家不只是抒自己之情,而且要抒剧中人之情,即代剧中人立心立言,而且立心在先,立言在后。只要剧作家设身处地,体察剧中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特色,那么,就可以达到“心曲隐微,随口唾出”的境界。这种由角色心中自然吐出的话,就最符合角色的性格,并符合角色在特定情境中的内心活动。如果说戏剧艺术的特征是化身当众表演,那么剧本创作的特征是化身描写,因而剧本创作时作家必须全身心对象化。于是,“设身处地”、“幻境纵横”便成了剧作家创作心理的特征。李渔这段话非常生动而透彻地复现了剧作家的创作心象,表现了他们的思维特征,而且只有语言性格化,才会感动观众。
(4)正音律。语言的音乐性是观众乐听的一个重要因素[5]。李渔是个特别注重剧本的可演性的戏剧理论家,因而必然特别注重戏曲语言的音乐性。他曾说,“填词一道,则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并明确提出:“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如莲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橘中,始为盘根错节之才,八面玲珑之笔。”李渔不仅以正音律要求曲词,而且以此要求宾白。“宾白之学,首务铿锵。一句聱牙,俾听者耳中生棘;数言清亮,使观者倦处生神。世人但以‘音韵’二字用之曲中,不知宾白之文,更宜调声协律。”他认为:“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于宾白之中,则字字铿锵,人人乐听,有‘金声掷地’之评矣。”[3]李渔还列出许多“调声协律”的要求和方法,试图引起对宾白语言的音乐美的重视,以期获得“遍地金声”的效果。
3.使观众达到娱乐效果的创作
(1)情节新奇。李渔重视情节的新奇,在理论上,他提出“脱窠臼”的主张,在创作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对情节的设置力求新奇,避免雷同。他曾自称在创作中,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他在剧作中所描写的情节大都为前人所未写过的或写而未尽的,有些则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些反常事情。《凰求凤》一剧,写了三个女子争求一个男子的事,在封建社会里,通常只能是男子求女子,即所谓的“凤求凰”,而李渔却写了女子主动争求男子,这就出乎常情之外,这样的情节也确实十分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同时,这一情节虽出乎常情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李渔写出了封建社会女子长期被封建礼教压抑和扭曲的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之情,故这一情节既新奇,又十分可信,即如李渔所说的那样,“新而妥,奇而确”。
(2)结构严谨。这方面的成就,首先得力于他的立主脑的结构原则。不仅每一剧的立意十分明确(如《蜃中楼》、《比目鱼》歌颂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风筝误》讽刺假冒欺诈的丑恶行为,《怜香伴》表彰妻妾和睦),而且作为主脑的另一个方面,即剧作的一人一事也都十分清楚。如《蜃中楼》中的一人即是柳毅,一事即是“蜃楼双订”,由这一事引出了舜华抗婚、牧羊、张羽传书、煮海等情节。由于剧作的主题明确,故剧作虽都有多组矛盾冲突,情节也曲折复杂,但都线索分明,主线突出,情节安排井然有序,“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在具体安排情节时,李渔又十分注重“密针线”,保持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联系。如《巧团圆》剧中,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婚姻由一把玉尺相联系,姚克承初将玉尺赠给曹小姐,后曹小姐被掳去装在袋中出卖,姚克承又以曹所持玉尺而买之,最后又终因玉尺结成夫妇。而这把玉尺在剧本一开始就已经作了交待:姚克承梦中登一小楼,遇见一老人,老人谓玉尺与姚克承的婚姻有关,后来果然应验。由于注重前后照应,前后情节之间联系紧密,故也保证了全剧的结构紧凑和严谨。
(3)重视科诨。李渔善于安排科诨,很重视科诨的作用,认为科诨“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在他的剧作中,几乎每一本戏都安插了一些精彩滑稽的科诨,以调剂舞台气氛,增强喜剧效果。李渔是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来设置科诨的,故既妙趣横生,又十分自然。如在《风筝误·惊丑》这场戏中,爱娟冒充淑娟与韩世勋相会,见面后,韩世勋问爱娟对他所题的诗是否有酬和之作,爱娟不知此事,只好说已赐和过了。韩世勋便要她把和诗念给他听,爱娟先是推说已经忘掉,后实在推不掉了,只好以人人皆知的一首《千家诗》来搪塞,就闹出大笑语。这一科诨是按照爱娟这一人物特有的性格设置的,因为爱娟冒充才女,而肚中又毫无学问,故出丑弄乖,闹出这样的笑话。安插一些滑稽的科诨对调动观众的积极心理活动有重要作用。
明末清初,观众的审美经验有了极大丰富和变化,在李渔之前,我国的戏剧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作家、作品,而对于审美主体即观众的探讨还相当欠缺。李渔观众学的出现,则打破了我国戏剧理论研究传统视野的束缚,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使我国戏剧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李渔的观众学研究,是和编剧学、导演学、表演学结合在一起的,避免了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观众问题。这种从“案头”至“场上”然后又联系“台下”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使生活和艺术、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收稿日期:2004-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