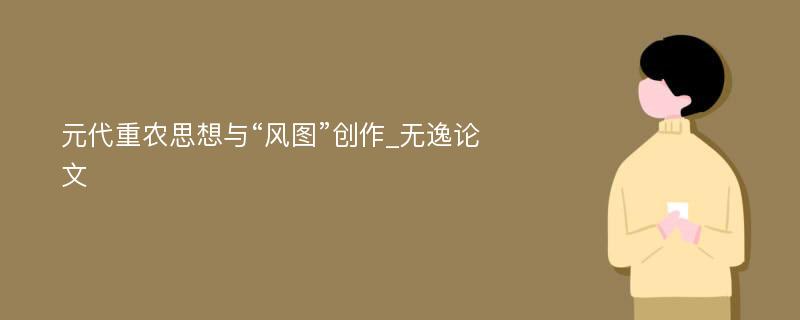
元代重农思想与《豳风图》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思想论文,重农论文,豳风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5)04-0062-07 《豳风·七月》以时令为序叙述了农人一年间的耕织劳作情况。《诗序》言此诗乃周公遭变,故陈王业之艰难,朱熹《诗集传》亦言周公因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后刘化之所由,使瞽聣朝夕讽诵以教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历代统治者视农业为王业之始,无不重视农事,因《豳风·七月》的这种解读早已深入人心,统治者借以传达重农、劝农、恤农的意志,此诗也因此成为建设王业的典型教材。 古代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政教风化,《七月》因其政教意义,成为历代宫廷画家热衷的题材,绘制了多幅《豳风七月图》或《豳风图》,挂于宫室,日夕相对,以之为鉴戒。由宋入元后,在元代重农的背景之下,元代画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创作了多幅《豳风图》。据文献记载,绘写过《豳风图》的画家就有赵孟頫、塔失不花、陈琳、盛懋、王振鹏、陈子奂等人,但存世至今的只有王振鹏和林子奂的作品,其余均已佚亡。 一、元代重农政策的宣教 蒙古族征战中原时,杀人毁屋,以致“里社为空”。人口的严重减耗,导致中原土地大量荒芜。蒙古族本是游牧民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不熟悉农业,亦不感兴趣,中使别迭等人甚至提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1](P832)而且蒙古人把这种游牧的生产方式带进中原,把耕地变为牧场,还纵牛马啃食百姓田内的禾稼桑枣,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全面推行汉法,不但学汉代统治者祭神农后稷,行“籍田”之仪,并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2](P2354)忽必烈抛弃了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场的做法,雷厉风行地制订了一系列“重农”、“劝农”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首先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由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管理系统,充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以农业立国的指导思想。其次是退牧还耕,限制抑良为奴。再次是兴修水利,军民屯田。元朝采取的这些重农政策,使全国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3](P559) 元朝廷还通过多种途径来宣传重农、劝农政策,使百姓广为了解接受,亦令帝王接受重农思想的教育。首先是编撰农书,至元十年(1273),司农司奉敕编纂《农桑辑要》并颁布天下,此书也成为司农司派员到各地巡察,督促农桑,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依据。除官撰农书外,还有私撰的农书,如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苗好谦《栽桑图说》等等。在每年春耕开始时,地方官员下乡劝农,往往也会发布劝农诗文告以劝课农桑,元人马臻《田父词》有记:“龙钟田父住深村,桑柘冈头石路分。犹领儿孙到城市,向人听读劝农文。”[4](P276)像王恽、陆文圭、黄溍、唐元、郭应木、叶岘、王毅、朱子范等人,均有劝农诗文传世。 除农书、劝农诗文之外,还有耕织图。耕织图,实际上是一种以图阐文的劝农文,把农业生产中的关键环节用图像的形式,并配以诗文歌谣,生动地描述出来。早在五代时就已出现耕织图,后周世宗留心稼穑,命画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召近臣观之。宋仁宗宝元年间,也令画工将农家耕织情况绘于延春阁壁上。南宋初年,於潜县令楼璹绘制《耕织图》,深为高宗赏识,并宣示后宫,一时朝野传诵。在元代,耕织图亦是一个重要宣教途径,程棨曾临摹楼璹《耕织图》,还被清朝皇室石刻,置于圆明园内。此外,杨叔谦也画过《农桑图》,赵孟頫据图作耕织诗。据赵孟頫《农桑图序》:“此图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5](P201)可知此图由大司徒源建议,杨叔谦据大都(今北京)风俗,依《豳风·七月》之十二月纪事,分别绘农耕、蚕织十二图,共廿四图,又由赵孟頫奉懿旨据图作诗廿四首,按十二月分咏农、桑之事,并由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儿文翻译于左方。延祐五年(1318)四月廿七日,《农桑图》由集贤大学士臣邦宁、大司徒臣源进呈,获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嘉赏,人赐文绮一段、绢一段,又再命赵孟頫撰序叙其端。元帝嘉赏《农桑图》的创作者,正因为此图可表现出元朝廷的以农为本的思想,此乃自古帝王为治之道也。 元代虽然是一个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但在当时,蒙古族本来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只是自元太祖忽必烈以来,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即使大臣中习汉文的也很少,所以杨叔谦绘《农桑图》进献,赵孟頫奉懿旨撰诗,还需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儿文翻译于农桑图左方,赵孟頫的《耕织图诗》则另卷装裱。图画形象直观,不但能代替抽象的说教,还能消除文字的隔阂,有利于士大夫向帝王表达其政治意愿及思想。在元代重农、劝农的历史背景下,《豳风·七月》因其“陈稼穑之艰难,叙农桑之节序”的诗义,也就成为元代画家所热衷的题材。 二、赵孟頫《豳风图》 赵孟頫文学艺术造诣极高,是当时书坛画坛的领袖,陶宗仪称其“公之翰墨,为国朝第一”。赵孟頫在元仁宗为太子时即常伴其左右,太子登基后又升为正奉大夫,到延祐三年,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赵孟頫在仁宗朝时供职于翰林兼国史院和集贤院,作为御用文人之外,有时也会奉旨参与宫廷的书画艺术活动,如《秘书监志》卷六记:延祐三年(1316)三月二十一日,“奉圣旨,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者么道。”[6](P104)赵孟頫《农桑图序》也记其受皇命绘《豳风七月图》一事:“钦惟皇上以至仁之资,躬无为之治,异宝珠玉锦绣之物,不至于前,维以贤士丰年为上瑞,尝命作《七月图》以赐东宫,又屡降旨,设劝农之官居。其于王业之艰难,盖以深知所本矣,何待远引《诗》、《书》以裨圣明!”[5](P201)《豳风·七月》及其诗意图,其意旨在前面已介绍清楚,而元仁宗授命赵孟頫作图以赐东宫,是为教育其继承人英宗,即延祐三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的硕德八剌,令其早知王业之艰难。 赵孟頫《豳风图》已经佚亡,已无法确知其面目,不过很有可能模仿自马和之《豳风图》卷中的《七月》诗意图。据画史记载,马和之《豳风图》在流传中被割裂,其中《破斧》一篇单独装裱,因有赵孟頫图记,被董其昌误以为赵孟頫所作。高士奇经过鉴定,确认为马和之原作,后来此画入清内府,又与原卷合装成一卷。高士奇在指出董其昌的谬误之后,又言:“赵画亦学和之,鉴藏当别之。”那么赵孟頫的《豳风图》很可能是模仿自马和之的《豳风图》了。 赵孟頫《豳风图》虽已佚亡,但在明代尚存于世。洪武九年(1376)冬十一月,宋濂跋赵孟頫《豳风图》:“臣濂侍经于青宫者十有余年,凡所藏图书颇获见之,中有赵魏公孟頫所画《豳风》,前书《七月》之诗,而以图继其后。皇太子览而善之,谓图乃方帙,恐其开阖之繁,当中折处,丹青易致损坏,命工装褫作卷轴,以传悠久,屡下令俾臣题其末。”[7](P681)宋濂跋中的“皇太子”应指未及即位就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病逝的朱标。从跋中可见皇太子对赵孟頫《豳风图》的珍惜,同时也说明了此画前诗后图,初为方帙,因担心经常打开翻阅,当中折处丹青易被损坏,所以改装为卷轴。对此,明代陈继儒及清代吴荣光均有提及,陈继儒言:“宋濂侍经于青宫十余年,凡所藏图书颇获见之。中有赵魏公孟頫画《豳风》,前书《七月》之诗,图继其后。皇太子览而善之,谓图乃古帙,恐其开阖之繁,当中折处丹青易损坏,命工装褫作卷轴以传悠久。”[8](P1034)吴荣光言:“明洪武中御府藏文敏《豳风图》方帙,特命工装作卷轴,以防损坏,见宋文宪集中跋语。文敏画在明初珍重若此,况今又四百余年,不益可宝贵耶。”[9](P882) 及至宣德七年(1432)秋七月,明宣宗朱瞻基“阅内库书画,得元赵孟頫所绘《豳风图》,赋诗一章。命侍臣书于图右,而揭诸便殿之壁。尝夏日午朝退,语侍臣曰:‘天气向炎,正农夫耕耘时也。’因咏聂夷中‘锄禾日当午’句,曰:‘吾每诵此,未尝不念农人。’”[10](P6347)可见直到此时,此图仍藏于明内府。同时,这则材料颇能反映《豳风图》对帝皇的教化作用,令皇宫之内的皇帝在炎夏之日想及农人耕种,心生悯恤之意。 另据朝鲜《中宗实录》卷一○三,即中宗三十九年(1544)五月条,赵孟頫《豳风七月图》在明嘉靖年间又流传到朝鲜,为户曹参议李名珪所得,后又献给中宗: 己亥,户曹参议李名珪以《豳风七月图》进,曰:“此臣赴京时所得,其时即欲献之,以近于书画,故未敢尔。退而见之,果非寻常书画之例,乃《豳风七月图》也。农桑艰苦之态,尽在于是。故元朝学士赵孟頫奉敕所画,并出其诗,乃人君所宜观省。况其笔法之妙,尤为奇绝。如此至宝,留在私家未安,故敢进。”传曰:“《豳风·七月》篇,乃周公欲使成王知稼穑艰难而作也。是故,古之人君或作屏,置诸左右,常观省,备悉民间艰苦也。”特赐弓箭,且赐酒。[11](P606) 从这则记录看,《豳风·七月》诗旨及《豳风七月图》的教化功能,也为朝鲜所熟知。这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赵孟頫《豳风七月图》的最后记录。 三、塔失不花《豳风图》 英宗硕德八剌还是皇太子时,大司农塔失不花也曾画《豳风图》进献。塔失不花,辽阳人,为高谅之子,高天锡之孙,历任奉议大夫、章佩监臣、纳锦府达鲁花赤、同知崇祥院事、资德大夫、院使等职。塔失不花,为其蒙古名,因元初有赐名之例,此后汉人皆以蒙古为名,即使非御赐,也多仿效。高天锡因向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建言:“农桑者,衣食之本,不务本,则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兴,古之王政,莫先于此,愿留意焉。”[2](P3614)孛罗以闻于忽必烈,忽必烈大悦,命立司农司,以高天锡为中都北山道巡行劝农使,兼司农丞。延祐四年(1317),仁宗因其祖父曾任司农一职,授塔失不花为荣禄大夫、大司农。 在英宗还是皇太子居于东宫的时候,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华事略》,并画《豳风图》以进。帝览之,奖谕曰:‘汝能辅太子以正,朕甚嘉之。’命置图书东宫,俾太子时时观省。”[2](P3615)“东宫”、“青宫”均为太子居所特称,而“承华”是太子宫门名,故后世又用“承华”代称太子宫或太子。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王恽辑集整理自广孝至审官之事理共二十篇,为六卷,成《承华事略》一书,献于尚为太子的仁宗。今塔失不花的《承华事略》大概与王恽之书相类似。元代大司农掌劝课农桑、水利、救荒等事,塔失不花任大司农之职,画《豳风图》以进,无疑是切合他的职务和身份的。塔失不花进献《承华事略》和《豳风图》的目的很明显,所以仁宗命置于东宫,俾太子时时观省,也正欲教皇位继承者知晓事理和稼穑之难,以习王道。 清代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中记“塔失不花《豳风图》,皇庆二年进”[12](P4),不知金门诏有何根据?但皇庆二年(1313),正是元仁宗即位第二年,次年改年号为延祐,而硕德八剌于延祐三年(1316)才立为皇太子,显然金门诏所言“皇庆二年进”是不可能的。塔失不花卒于延祐六年(1319),据此推测,《豳风图》应作于延祐三年至六年之间。赵孟頫记《农桑图》作于延祐五年,但《豳风图》只记作于此前,那么这两幅《豳风图》的创作时间相差应该不会太远,而且最后都置于东宫,供皇太子习知稼穑之艰难。 四、陈琳《豳风图》及盛懋《豳风图》 陈琳,字仲美,杭州人,生卒年不可考。是元代画工,师法赵孟頫,也曾画《豳风图》和《尔雅草木虫鱼图》进谒。陈琳一家世代以绘画为业,其父陈珏是南宋末年画院待诏。除继承家学外,陈琳还得到了赵孟頫的指点:“江南画工陈琳,字仲美。其先本画院待诏。琳能师古,凡山水、花竹、禽鸟,皆称其妙。见画临摹,仿佛古人。子昂相与讲明,多所资益,故其画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无此手也。”[13](P901) 作为以绘画为职业的画家,作画的题材和风格,往往受到当时文人画家尤其是官僚画家的影响,因为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品味和爱好。在元代重农、劝农的历史背景下,元仁宗不但敕命赵孟頫绘《豳风七月图》以赐太子,塔失不花进献《豳风图》也得到了他的嘉赏,复置东宫,令太子时时观省,可见元仁宗的重农思想,以及对《豳风七月》这一题材的偏好。陈琳是赵孟頫的弟子,也供职于当时宫廷绘画机构,他献画《豳风图》及《尔雅草木虫鱼图》,无疑是投元仁宗所好。王绂《书画传习录》辛集下《荣遇门》记: 陈琳……尝画《豳风》、《尔雅草木虫鱼图》,诣阙进表。其略曰:“臣闻《豳风》为周室肇基之始,《尔雅》乃元公格物之书。陈稼穑之艰难,叙农桑之节序,实有裨于君德,更念切夫民依。其中所列草木虫鱼,纷繁琐屑,或耳目所共睹,或士夫所未谙,类皆关系天时人事之宜,岂徒铺张园廛漆林之胜?顾风诗三百,笺释者不止毛、郑数家,而《尔雅》一书,纂辑者仅有景纯一解。至若布诸丹青、垂诸绢素,前人未发,后学不闻。臣早岁过庭,即承严训,壮年习艺,未敢师心。谨不揣冒眛,恭写《豳风》、《尔雅草木虫鱼图》全帙,幸毕一生之愿,宁辞十载之勤……敢麈乙夜之观,仰冀重瞳之照,庶田家物候,得备陈黼座之前,而下士怨咨,愿常廑宸衷之虑。”仁宗览奏,深用嘉悦,命赐钞五百锭,衣二袭。其所进画册,命藏麟德殿左厢,俾时时观览。[14](P281) 陈琳在奏表里解释绘《豳风图》和《尔雅草木虫鱼图》的原因:《豳风》乃周室肇基之始,陈稼穑之艰难,叙农桑之节序,有裨于君德,切夫民依;《尔雅》为格物之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其中卷八为“释草”,卷九为“释木”、“释虫”、“释鱼”,书中所列草木虫鱼,有的虽耳目共睹,有的却为士大夫所未谙,皆关系天时人事,所以绘书中草木虫鱼,令观者格物致知。在中国农史上,辨识草木虫鱼鸟兽,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甚至有《救荒本草》一书,教民众认识可以食用的野菜,以备荒灾时以济灾解饥。《尔雅》成书上限不会早于战国,东晋郭璞曾费十八年的时间来研究注解《尔雅》,并为之注音、作图。《尔雅图》现存有元人写本,题为《影宋钞绘图尔雅》,或言为郭璞所撰,书中郭璞《尔雅序》道:“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15](P455),故“别为音图,用祛未寤”[15](P456)。陈琳称《尔雅》“至若布诸丹青、垂诸绢素,前人未发,后学不闻”,显然忽略了郭璞曾为之作图,但图写书中草木虫鱼以祛未寤,却袭承自郭璞。 陈琳进献《豳风图》和《尔雅草木虫鱼图》之后,元仁宗览奏后深为嘉悦,赏赐陈琳,并将其所进画册,藏于麟德殿左厢,以便时时观览。显然,陈琳的画及奏表所表达的重农恤农思想,深得其心。元明更替后,二图皆被明朝廷接收,王绂簪笔禁林时,曾得赐观:“元社既屋,大将军率师北征,收其图籍,此册遂入内府。余时簪笔禁林,幸蒙赐观。顾其卷帙颇多,不胜悉纪,本朝又无借临之例,故外臣不可得见。杨铁崖为总裁修《元史》,亦未载此事。余恐仲美之名久而湮没也,故备志之。”[14](P281)王绂在明皇府里睹阅后,因恐其湮没于历史,特记载于《书画传习录》,是为前面所录之文。 现在,《豳风图》和《尔雅草木虫鱼图》早已佚世,不过陈琳奏表中言其早岁过庭即承严训,壮年习艺,未敢师心,现绘写《豳风》、《尔雅草木草鱼图》全帙,乃毕一生之愿,辞十载之勤,仍可凭此设想其况。陈琳身为画工,称未敢师心自诣,那绘写《豳风七月》中的耕织、《尔雅》里的草木虫鱼,想必是力求逼真,是写实而非写意的了。陈琳费十年之功图写《豳风》、《尔雅草木草鱼图》全帙,后王绂也记“卷帙颇多”,显然是一次长时间、大规模的创作,《尔雅草木草鱼图》是绘写书中之草木虫鱼,但《豳风图》是如何图写一年十二月之耕织的就无法得知了。 此外,《石渠宝笈》还著录了盛懋《豳风图》一册,但记之甚略:“素绢本,著色画。每幅小楷节书本诗。首幅款署‘子昭’,末幅又款云:钱塘盛懋制。册计三十幅。”[16](P98)盛懋,字子昭,嘉兴魏塘镇人,与吴镇是同乡。盛懋是陈琳的学生,身世跟陈琳也很像,同是世有家学的画工:“盛懋,字子昭,嘉兴魏塘镇人。父洪甫,善画。懋世其家学而过之。善画山水、人物、花鸟。始学陈仲美,略变其法,精致有余,特过于巧。”[17](P887)《豳风图》册共三十幅,为绢本著色画,也已佚亡。不过盛懋为浙江嘉兴魏塘镇人,末款署“钱塘盛懋”,疑为伪作。 五、王振鹏《豳风图》和林子奂《豳风图》 赵孟頫、塔失不花、陈琳、盛懋等人的《豳风图》均已佚亡,流藏至今的只有署名王振鹏的《豳风图》和林子奂的《豳风图》。王振鹏《豳风图》,绢本设色画,共八段,画《豳风·七月》诗意,每段左侧皆有柯九思隶书《七月》诗文及楷书注释。林子奂《豳风图》,绘《豳风》七首诗歌的诗意图,现仅存五幅,其规模形制与马和之《豳风图》相仿,一图一诗,每图后系小篆书《豳风》诗篇,篆书诗文后,又有解缙行草朱熹《诗集传》的传疏。 王振鹏《豳风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八段,分绘耕种、冶制农器、田官巡田、采桑、刈草、绩麻、染布、晒布、获稻、田猎、修理房屋、食瓜、打枣、采薪、凿冰等农事活动。但是,王振鹏《豳风图》画风更近于明清绘画面而非元画,而且柯九思款识书于“至正癸巳”,即1353年,而柯九思卒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显然书法部分为造伪,难以断为真迹。黄宾虹认为柯九思题书为伪迹,但此画应是从临摹真迹而来:“王振鹏画柯九思写豳风图……摹本,柯九思题,皇甫汸、王守、俞允文跋均伪。王孤云画工细人物著名元代,同时柯九思题,皆浙东人,此虽摹本,当从真迹而来。摹。”[18](PP12-125)虽然黄宾虹的鉴定未能视为断言,但亦可备为一说。 王振鹏是元代著名画家,元仁宗尚为太子时,因其画艺超群而赐号孤云处士。据虞集《王知州墓志铭》,元仁宗为皇太子时,赵孟頫、王振鹏、元明善、商琦等文人艺家,在东宫与皇太子朝夕相处,侍从于皇太子左右,谈论儒学文艺,颇为相得。当时,王振鹏不但得到仁宗赏识,还得以遍观内府古书绘画。在与赵孟頫等人侍从于皇太子左右时,推测王振鹏应与赵孟頫有过交流。如此,若王振鹏确实绘写过《豳风图》,很可能也缘于元仁宗的偏好以及当时的风尚。 元仁宗执政,先命赵孟頫画《豳风七月图》以赐东宫,后大司农塔失不花和宫廷画师陈琳也先后画《豳风图》以进,皆受到嘉赏。王振鹏以画艺受到仁宗赏识,与赵孟頫等人侍从于其左右,不但赐号“孤云处士”,还得以遍观内府古书画,选择《豳风·七月》绘《豳风图》,也是在情理之中。这一系列的《豳风图》反映了元代的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也反映了元仁宗对《豳风图》的偏爱。事实上,《豳风·七月》的“陈稼穑之艰难,叙农桑之节序”诗义,早已深入人心,执政者偏爱固因如此,观画者释读绘画也是如此,如王守跋道:“所谓豳风者,周公以成王年幼,未知稼穑之艰难,故举先世发迹于豳,忧勤农事,渐磨成习者,著为诗篇,使瞽聣朝夕讽诵以教之。不惟描写田野风景宛然,而且大有利于国家重农困苦之意,勿视游戏之图画耳。”[19](P316) 林子奂《豳风图》,乃绘《豳风》七诗诗意图,其中第一幅《七月流火》,绘《七月》诗意,打破了时空界限,不同时空的人事皆集中于同一画面上。自右至左,有观星象者,有春耕者,有采桑、修剪桑枝者,有凿冰藏冰者,有畯官巡田,妇子送馌者,有塞窗熏鼠者,有捕猎者,最后画众人集于公堂,祭祀宴飨的场面。图后系小篆《七月》诗,诗后有解缙行草书录《诗集传》传疏:“《周礼·籥章》:‘仲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诗也。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宴享也节。此《七月》之义也。” 因《豳风·七月》的政教诗旨,《豳风图》也每每被赋予政教的色彩。虽然因史料的缺失,林卷阿的创作动机已无法探究,但是画者未必然,观者却想当然,观画者对其《豳风图》的释读,同样着眼于圣道王化、重农勤政上。不过,在元代重农的历史背景下,林卷阿也很可能受到当时绘《豳风图》风潮的影响,况且《豳风》诗旨早已深入人心,选择《豳风》为绘画题材,想也并非无缘无故。所以,世人的释读,也是成立的,如卷后张肯题跋:“虞邵庵云:‘文章不关世教,则为空言。’余以为作画亦然。苟但游戏笔墨,惟资人之嬉玩者,则亦不足取也。若林君所画《豳风》之诗,得无意于世教耶?……噫!诵其诗,观其图,则周公之德为何如哉?蓄者宜宝之。”[20](P364)刘九庵跋林卷阿《豳风图》亦道:“历观古人之图画,必有所劝戒而作。此元人林子奂写《豳风·七月》诗并图卷。昔之序《诗》者云:‘周公陈王业,以告成王。谓民之至苦者,莫甚于农,有国有家者,宜思悯之、安之。故作是诗,备述其艰难。’今观子奂此图,使诗之意形于画,画之意原于诗,亦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矣!”[21](P186) 古代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向来被视为国家之本,历来就有重农的思想传统。因故,历代帝皇学治国之术,必习《尚书·无逸》及《豳风·七月》,令知稼穑之艰难而重农、劝农、悯农。赵孟頫《农桑图序》对此有所阐述:“臣闻《诗》、《书》所纪,皆自古帝王为治之法,历代传之以为大训,故《诗》有《七月》之陈,《书》有《无逸》之作。《七月》之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获稻’,又曰‘十月涤场’,皆农之事也。其曰‘女执懿筐’、‘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八月载绩。载玄载黄’,皆妇工之事也。《无逸》之书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成王,盖欲成王知稼穑之艰难也。”[5](P200-201) 正因如此,《无逸》、《七月》,为历代文臣名相所青睐,常作书画图进献以劝谏,又或为帝皇所重,命御用文人或宫廷画工书写绘图,以表圣意。像《无逸》,唐代名相宋璟曾书《尚书·无逸》,为图以献唐玄宗,唐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宋代,翰林学士孙奭曾也画《无逸图》以进,宋仁宗命悬挂于讲读阁内。到元代,翰林待制孙忠恕亦献所著《无逸图》。至于《七月》,因诗中描绘了农夫蚕妇一年十二个月的耕织劳作,形象生动,更主要的是,《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22](P169)《七月》成为《诗经》中最受宫廷画院内外的画家所热衷的题材,是“‘诗三百’中唯一发展出独立插图传统的。”[23](P204)后世不少《豳风图》实则上只选绘《七月》一诗的诗意,又或取《豳风》七诗作诗意图,但世人所重依然是《七月》一诗的政教意旨,如宋代马和之等院画家画《豳风图》,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唐岱、沈源、周鲲及清高宗弘历画《豳风图》,莫不是如此。在元代重农的背景之下,《豳风·七月》成为元代画家所热衷的题材,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元代《豳风图》的创作情况来看,无论是敕命创作还是绘图进献,都反映了元代统治者的重农思想,而元代统治者通过《豳风图》传达重农、劝农、恤农的思想和意志,并用以教育皇位继承人,也反映了古人对《豳风·七月》的解读和接受,即通过农人的耕织劳作,使以农业为本的国家统治者明晓王业之艰难,从而重视农业,劝导农事,体恤农民。所以,《豳风图》不但是了解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思想政策的图像文献,也为《豳风·七月》诗学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