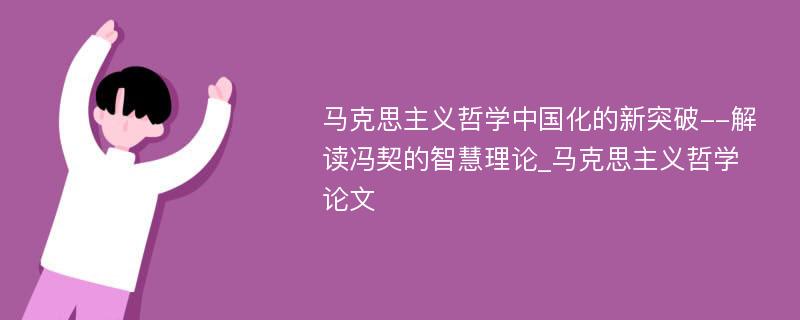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的“智慧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突破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智慧论文,读冯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如何解决时代的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与试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和失败,经过反复的比较,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但马克思主义要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即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冯契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那时,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冯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心悦诚服。他为《论持久战》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所折服,认为它“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对一百多年来的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做了历史性的总结”,其中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一词,“集中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1] (P14,P15)。他从毛泽东著作中感到,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不迷信、不盲从,“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他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读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哲学著作。他好学深思,喜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上世纪40年代,他在向老师金岳霖学习、切磋中提出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智慧,“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2]。在此之后,他进一步深化此问题的研究,把认识的过程看成是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过程。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智慧说”。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各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固然有其共性、普遍性,但更有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殊性。冯契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同中国哲学智慧相结合,以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哲学史研究中体会到,哲学家所要探索的根本问题可以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按中国传统哲学的提法,概括为人与天、性与天道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争论。他把中国哲学史上的表现形态和争论概括为: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形神之辩、力命之辩、性习之辩、有无(动静)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等等。他认为:“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1] (P23)他借用佛教“转识成智”的概念,认为“智慧说”就是要研究和回答如下的问题:“在实践基础上之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如何转识成智,获得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1] (P42)他把“智慧说”展开为各具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成一体的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其主干,《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与《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两翼。智慧说三篇,每篇一卷,共计70余万言。与智慧说三篇密切相联的是他的100多万字的四卷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一卷),这既是智慧说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准备,也是它的历史展开。智慧说贯通古今,熔铸中外,博大精深,堪称煌煌大著,是作者经过半个多世纪深思求索和精心结撰的哲学体系。
冯契把“智慧说”界定为广义的认识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篇的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在他看来,哲学讲的智慧,即是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有关性与天道的理论。冯契从中外哲学史的研究中概括出认识论的四个问题:“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1] (P46,P47)《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篇就是结合哲学史(主要是中国哲学史)回答这四个问题。冯契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它与人的自由发展有内在的联系,所以认识论要讲自由。”[1] (P72)这一篇的最后一章“智慧和自由”,讲知识向智慧的转化,讲哲学智慧的目标——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统一。可以认为,这一章是这篇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
依据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冯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始终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勉励同学。他进而把这两句话上升为建构智慧说的两个基本原则。
“化理论为方法”,就个人而言,就是把哲学理论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科学研究;就哲学而言,就是把哲学基本理论化方法论,化为思维方法,化为辩证逻辑。冯契坚持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与时下流行的否认客观辩证法不同,他坚持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3] (P2)《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篇的主旨在于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冯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辩证逻辑提供了基本原理,并出色地运用于科学研究和革命工作,但他们都没有写出辩证逻辑的专著。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逻辑研究不多,中国近代哲学对辩证逻辑同样研究不多。这一弱点造成了不良影响。他特别强调了研究辩证逻辑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他认为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注:冯契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与毛泽东有不谋而合之处。毛泽东认识论的优点是强调实践的意义,从宏观上揭示了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毛泽东的不足是未能深入思维领域,对辩证逻辑无有论述。这是导致他晚年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之一。他本人似乎也感到这一点。1961年8月,他在庐山同李达谈话时曾说,他想研究辩证逻辑,但苦于没有时间。)他还指出,在《墨经》之后,中国在形式逻辑方面不如欧洲、印度,但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丰富,要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合流,就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十分注重中国古代朴素辩证逻辑的发掘、梳理和阐释,这是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之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篇注重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和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相结合,这是该篇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该篇可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逻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想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达到世界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争自由的哲学。但在很长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哲学被遮蔽了,马克思主义者讳言自由,自由似乎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这导致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发生严重失误。基于国内外深刻的历史教训,冯契高调自由,关注和追求自由。这一点最初表现在他著的中国哲学史中。他在“绪论”中专门列了一个目,从中西比较中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在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他提出,中国哲学偏重自觉而忽视自愿,西方哲学则偏重自愿而忽视自觉。他注重中国哲学史上有关自由思想的发掘、梳理和阐释,注重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束缚、摧残个性自由的批判。他力图把自觉和自愿统一起来,达到自觉自愿。对自由思想的发掘、梳理和阐释是冯契著的中国哲学史的又一显著特点和优点。他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篇是从哲学基本理论上探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主旨在讲化理论为德性。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1] (P55)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自由论为指导,结合中外哲学史,阐发了人生论、价值论、真与人生理想、善与道德理想、美与审美理想等理论,提出了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新理想。他说:“智慧给予人类以自由,而且是最高的自由,当智慧化为人的德性,自由个性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4] (P347)他又说:“我们的理想是要使中国达到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的目标,也就是使中国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那样的社会。”[4] (P340)可以认为,智慧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新论,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新论。
智慧说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智慧说不同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宗旨,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有体现作者人格的鲜明个性,它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或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大突破
把冯契的智慧说放到20世纪中国哲学中考察,我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大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需要众多的哲学家共同努力的事业。李达、艾思奇、冯定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现实化、中国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肯定的。当然,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知识构成的局限,他们所建构和阐述的哲学体系,虽然尽力吸取毛泽东哲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但从总体上讲,还没有摆脱苏联20世纪30年代哲学体系框架,带有舶来品的特点,未能中国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哲学界在反思、总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时得出了一个普遍的共识:现行的从苏联20世纪30年代移植过来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亟待进行革命性变革。20多年来,从哲学观、哲学研究的方法到哲学的对象、内容和体系均有重大变化。有的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有的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有的主张实践唯物主义,有的主张超越唯物唯心的类哲学等等。现在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同2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加进了许多新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取得的新进展必须充分肯定。但统观近20年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专著,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即对中国传统哲学涉及甚少。编著者们着眼于对马克思著作的新读解(有的实质上是透过西方哲学的误读)、对西方哲学(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吸取、对科学技术革命新成果的概括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对吸取中国哲学的精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缺乏应有的关注。
可以说,直到冯契的智慧说发表之前,专门哲学家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尚未出现。冯契的智慧说是第一个这样的体系。如前所述,它有自己的宗旨、范畴、体系,有现有哲学体系中没有涉及或虽涉及而没有展开的新内容,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智慧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地地道道是中国的,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过程来看,冯契的智慧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新进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并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全盘否定与中断,而是意味着中国哲学要通过革命获得新的生命、新的形态。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哲学家在20世纪30—40年代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一家之言,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海内外的现代新儒家们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他们的哲学也都有明显的局限性。撇开时代、阶级这一点不论,就纯学术层面来说,他们只是对所各自偏爱的中国哲学中的某一派、某一家有所肯定与发挥,而对其他诸多的学派、哲学家,尤其是对其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少有肯定与弘扬。冯契的智慧说则不同,它没有宗派的狭隘性,没有门户的偏见。它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哲学,而不只是其中的一派、一家,它固然着重发掘、吸取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但也没有忽视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中有价值成果的改造、吸取。冯契着力发掘为一般研究者们所普遍忽视的辩证逻辑和自由思想。鉴于中国(不仅是古代而且包括近现代)哲学中逻辑思维和自由理论不够发达,他从50年代起就注意对这两者的研究。他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两篇正是为补中国哲学长期存在的这种不足而作的。
至于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智慧说更有开创的意义。在此之前,张申府(崧年)、张岱年兄弟俩曾作过尝试。张申府在上世纪20—30年代积极宣传唯物辩证法,提出马克思、罗素、孔子三者相结合的主张。遗憾的是他未能从事这一工作。(注:详见许全兴:《张申府哲学思想》,《毛泽东与中国20世纪哲学革命》一书第四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他胞弟张岱年则专注哲学研究。张岱年在研究中国哲学史(1937年完成《中国哲学大纲》)的同时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罗素分析哲学的结合,企图构造一个“三结合”的体系。他在40年AI写作作了天人五论,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他以简洁流畅的文字论述了哲学的性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思维方法、客现世界的实在性、事物与规律的关系、价值论与人生论、天人关系等。张岱年天人五论的主旨在求真、求善。它既不同于熊十力新唯识论、冯友兰新理学等体系,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由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别具一格的体系。天人五论的前两论主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后三论则基本上是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贯串天人五论的基本精神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天人五论是中国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初尝试,有其一定意义。当然天人五论的“三结合”的体系还很不成熟,带有明显的机械、折中的痕迹。天人五论在提出时未能发表,直到80年代才出版。此时张岱年虽继续大力提倡综合创新论,但他毕竟到了耄耋之年,已无力去完善、重构自己“三结合”的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议论甚多,但真正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方向从事这一研究并做出成果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除冯契的智慧说之外,本人迄今尚未见到贯串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精神的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体系。由此可见智慧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三、智慧说的几点启示
冯契的智慧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这里仅说本人感受最深的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有丰富的中国哲学史知识。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毛泽东本人博古通今,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有精深的了解,因此能提出中国化的问题,能在中国化上取得卓越成果。在毛泽东提出中国化之前,艾思奇已提出在继哲学大众化之后,要开展一个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当时,在延安、重庆等地,学术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国统区重庆叫“学术中国化”)展开了讨论,加深了对中国化的认识,并朝这一方向努力。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显著,以至毛泽东在晚年认为他们的哲学仍是“洋哲学”。究其原因,除受教条主义束缚外,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缺乏应有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养不足。“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5] (P391)一般地说,哲学家同时也应是哲学史家,至少要有较丰富的哲学史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对中国哲学做出总结和概括,继承和发展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困难之所在。冯契之所以能写出智慧说,这同他对中国哲学史有精深的研究分不开。他的四卷中国哲学史为写作智慧说三篇作了充分准备。没有四卷中国哲学史,就没有三卷智慧说,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如他自己所述,当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时,“哲学当然就有了一种新的面貌,不仅不同于一般哲学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且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1] (P2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发展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当代的中国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有具有丰富的中国哲学史知识,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贡献。倘若无中国哲学史的学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观愿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令人堪忧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自我革命,形成新的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外哲学相结合形成新的哲学的过程。在外国哲学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还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印度唯识论等等。哲学家们将各自偏爱的中国哲学流派和外国哲学流派相结合,形成诸多哲学体系。这诸多的哲学体系,虽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但从总体上看,都未能适应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需要,都被中国革命胜利大潮所淘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尔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了严重的曲折,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剧变,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思想文化中“古今中西”之争再次发生。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动摇,企图从现代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找出路。有的学者公开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一样应该终结,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人类哲学史之外。冯契经过系统的反思,继续坚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坚持对中国哲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结和概括,努力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他并不否认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中西哲学结合的体系,他主张对不同的哲学取宽容的态度。但他坚信,通过百家争鸣,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新阶段中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在相当一部分学者淡忘共产主义理想、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冯契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这显得尤其可贵、可敬。智慧说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同一过程,只有坚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中国传统哲学才能获得新的生命、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达到中国化,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吸取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要延续、发展、现代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作用,离不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
第三,哲学家要有独立自主人格,保持心灵自由思考。冯契认为:“哲学家如果不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1] (P18)他高扬自由,把培养知情意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统一的独立自由德性作为价值理想。他本人遵循“化理论为德性”的原则,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他说:他喜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对任何一种学说不能够迷信它,研究哲学不能依傍门户,不能人云亦云。对各派哲学都应持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如此”[1] (P17)。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不迷信;他尊重毛泽东,但不盲从。冯契在肯定毛泽东及其哲学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切肤之痛,他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独断论、权威主义、奴性等封建遗毒反复进行揭露批判。他指出: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把自己讲过的“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话丢到一边去了。“忽视了个性解放来谈社会主义,在一个小农国家里面那就必然成为以集权主义的方式来推行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就必然既无个性解放又无社会主义。”[4] (P341)他又指出:“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相结合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大祸害,是自由的大敌。”[4] (P342)针对奴性普遍存在、自主个性尚未普遍确立的情况,冯契认为,当代中国仍需强调个性解放,从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注:本人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本人在许多场合,大声疾呼当代中国需要开展一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参见《解放思想,解放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当代中国需要个性解放》,《现代哲学》2001年第1期;《为中国个性解放呐喊》,为阮青教授著的《中国个性解放之路》一书作的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他对流行的言行不一,缺乏操守的丑恶现象痛加抨击。智慧说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立自主的自由个性和求真、求善、求美的崇高人格。我们学习智慧说,首先要学习冯契的崇高人格和宝贵品德,保持独立自主人格,保持心灵自由思考。
本文高度评价智慧说,但并不认为它已很完善,无不足和质疑之点。智慧说作为一家之言,自然有许多可商榷之处。学者们对它的哲学观、体系和具体的论点等均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本人看来,人的智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还表现在(甚至是更重要表现在)改造世界上。因此,作为广义的认识论应包括如何改造世界的内容,即研究如何改造世界的规律,而这一点正是迄今为止的中外哲学少有研究的。(注: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之我见》有所论述,《理论前沿》1996年第6期。)在这方面,智慧说同样阙如。又如,智慧说十分重视自由的研究,提出中国社会仍需要个性解放,这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人的自由的获得,主要不是在个人德性的培养,个人智情意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统一人格,而在于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改造,这方面智慧说虽然说到,但无有展开。再如,如何“转识成智”,智慧说提出了独到见解,但似乎还未说透,还不易为读者理解。哲学是智慧之学,它是以理论知识形态来表达、传授和延续的。现在许多人否认哲学是理论,是知识,我以为是不妥的。任何一种哲学若变成一种供人阅读的书面文字,那它就成了书本知识。因此,正确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知识,但它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有关智慧的知识。一个人即使熟读了智慧学(哲学)之书,在理论上懂得了知识如何转变为智慧,但他还是不能说已“转识成智”,有了哲学智慧。因为智慧是一种能力和德性,它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传授、读书而获得的,它只能在个人生活实践中获得和发展,即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将所学得的哲学理论逐渐内化为自己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德性。因此“转识成智”的过程是“化理论为方法”(不只是认识方法、思维方法,而且包括改造世界的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而非仅仅凭理性直觉的飞跃。智慧说的“转识成智”需要补充和完善。
智慧说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自然有它的不完善之处,自然可对它提出种种异议。尽管如此,智慧说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遗憾的是智慧说尚未引起我国哲学界的广泛重视,尤其尚未引起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应有重视。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冯契智慧说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冯契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哲学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