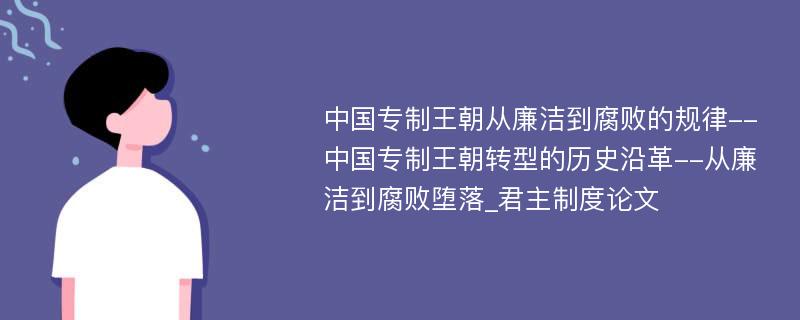
中国专制王朝由廉转贪的定律——THE INEVITABCLITY OF CHINESE DESPOTIC DYNASTY TRANSFORMING——FROM HONESTY TO CORRUPTION AND DEGENERATION,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定律论文,中国论文,INEVITABCLITY论文,CHINES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专制王朝由夏至清,历时四千载。它亡而复兴,兴而复亡,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探讨其由廉转贪的定律无疑是个大课题,为完成这课题,有必要利用前人的认识成果,抓住典型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华民族最可骄傲的王朝,它不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贞观年间,唐朝政治最为清明,唐太宗又是中国千百个帝王中最受推崇的一个。《贞观政要》就是以唐太宗为核心的中央群体智慧的结晶,廉政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它为基本史料,通过对唐太宗统治集团廉政思想及实践的评述,来认识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由廉转贪的必然性规律。
一、廉政建设的重心
学界在探讨历史上廉政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治吏惩贪上,似乎廉政建设只是针对官吏的。
确实,治吏惩贪贯穿中国自有国家以来的整个古代史。夏朝规定:“昏、墨、贼,杀”。[①a]其中的“墨”就是贪赃罪,主体是官员。官员一贪即染上“墨迹”,非但可耻,还要杀头。罪名恰当,用刑严厉。足见贪赃罪之猖獗,后果之严重,更说明中国治吏惩贪特别是官员行贪的历史是何等悠久!战国之际出现的《法经》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其中有“六禁”的规定,作为“六禁”之一的“金禁”也指官员贪赃。大汉王朝有“禁锢”之罪,规定“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②a]东汉禁锢更严,贪赃者非但本人终身不得为官,连子孙亲友也蒙受耻辱,不得为官。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对贪赃罪规定之严密至今令人叹服。如《职制》篇规定,监临官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也不得向被监临人借取财物,而且有责任约束其家人为上述行为;官吏出差,不得索取或强要财物,主动送上门来的礼物也不得接受。否则,即以坐赃或坐赃减等论处。尽管如此,立法者仍觉得不够全面,为此,《杂律》篇首就“坐赃致罪”设了专条,不仅对五花八门的贪赃罪作了分类,并对一切已经出现甚至可能出现而又难以明确的贪赃罪作了概括性规定,唯恐法外遗奸。在处罚上也不含糊。如官员受财枉法,以赃物折绢作价,计绢一尺即杖百,满十五匹处死刑,而盗窃五十匹仅处加役流,颇能体现严于治吏、宽于待民的精神。然而,贪赃之风仍愈演愈烈,故唐以后各王朝有关惩贪的法网越织越密,处刑越来越重,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明朝朱元璋。由于他出身贫寒,受过贪官污吏虐待之苦,更深知腐败是王朝毁灭的原因,所以惩贪手法令人胆战心寒,不堪目睹,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比如,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于官府门前,以示警戒。他还发动群众,允许民间青壮男子将赃官扭送到京陈告,创立了“民拿害民官”制度。但此类做法无法坚持下去,雷声一停,贪风骤起,明朝以严于惩贪而具特色,更以官场腐败而著称。逮至末代王朝,竟出现了“小小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奇观。
纵观中国专制王朝史,贪和惩贪朝着直线上升的态势发展,越贪越惩,越惩越贪,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常言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十官九贪,甚至无官不贪。王亚南总结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其论据是:“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是何等希罕!历代对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是如何的多!”[①b]其实,在数千年文明史上出现的几个清官廉吏也要经过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润色、修饰,卸装后,不外五十步笑百步耳;而百姓所以交口称赞,视虚为实,除去受愚弄外,并不乏期待和幻想的成分。
因此,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廉政问题的时候把治吏惩贪作为重心不无道理。但唐太宗集团认为,廉政建设的重心不是作为百姓之父母的官员,而是作为百官之主宰的君主。
君主最易于贪。狭义上的贪,与权力密不可分,没有权力就谈不上贪。但它又广泛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只要具备一定的外在条件,任何人都很难不贪,用唐太宗们的话说:“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②b]人人追求富贵,君主则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至尊至富,最具备贪的条件,最易于贪。不能以为只有官才会贪,贪不是官的专利。
君贪无厌。君主至尊至富只是相对于黎庶百官而言的,而相对于人的欲望来说,富贵没有止境。贞观四年,魏征警告唐太宗:“陛下若以为足,今之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③b]权是水,贪是船,水涨船高;君主权无限,贪亦无限。官不同,他们权有限,贪亦受限,与君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君贪无法治。唐太宗善于提出问题:“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可须苦谏?”深思远虑的大臣们善于解答问题,认为这是“首创奢淫,危亡之渐”,其结果是“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谏臣必谏其所谏,及其满盈,无所复谏。”[④b]廉难贪易,本性使然。君主一旦贪起来,尝到贪的甜头,就得寸进尺。此时,即使再动听的道理也无济于事,即使勇于上谏的大臣也必须保持沉默,任奢淫日进,待危亡来临,因为对他无人能治,无法可惩。官不同,对他们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奏效,毕竟有人治有法惩。
君贪必有贪政。各级官员不管怎样贪,也不管有多少人贪,往往是隐蔽的而非公开的,至多影响政策法律的贯彻落实,却难以将其上升为政策法律,得到普遍推行。君则不然,他“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⑤b]因此,势必将个人特殊之贪上升为一般,公开地强制性地要求所有官员去执行,使全国满足于他一个人的需要。夏桀、商纣如此,秦皇、汉武、隋炀帝也概莫能外。
君贪官必贪。当权者的道德人格力量无论何时都需要,在专制王朝、人治国家尤其需要,因为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限制规范权力。要减少权力的滥用,为使公共权力不致于完全为专制者的私情私欲所支配,成为纯粹的私权力,唯一的办法是自我觉悟,自我约束。所以孔子把“政”解释为“正”,并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⑥b]反之,“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⑦b]对此,唐太宗集团心领神会,他们认为,“上有所好,下必有甚。”[⑧b]“上好奢糜而望下之敦朴,未之有也。”[⑨b]君贪反要求官廉,那只能靠严刑峻罚才能一时起作用,结果不但降低君主的威信,还会使整个统治集团陷入紧张状态;如果放纵,则逐级对上负责的官员将立即效法,不教也要设法去学,不学也要冒险去干。因此,“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①c]只有上歪才下邪,君贪官必贪,君贪是官贪的前提,官贪是君贪的结果。
君贪则政权必倾。唐太宗集团认真总结了历史上的亡败教训,他们认为,秦所以二世而亡,不外乎“逞嗜奔欲”。[②c]汉之文景,厉行节俭,洁身自律,天下大治。然而,“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③c]任何帝王都不愿搞乱天下,甚至为维护稳定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隋朝也不例外,他们“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但它为什么短命夭折?原因是:“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④c]隋只考虑短期行为,用权力推行贪政,满足贪欲,却不知节欲廉政,细水长流。竭泽而渔,泽枯而鱼尽,统治者作茧自受,自取灭亡。无情的历史告诉人们,“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⑤c]
足见,一君贪甚于万官贪。唐太宗集团的认识触及到了专制王朝的核心。为维护这个核心,他们反复强调君主的决定性作用:“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⑥c]“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⑦c]那么,君主能否不贪?
二、由廉转贪的定律
学界在探讨历史上的廉政问题时,不仅把治吏惩贪作为主题,又侧重在具体的朝代、措施、经验或教训上。唐太宗集团不同,他们不仅把君主作为重心,又对历史进行了宏观动态的考察,发现了由廉转贪的定律。这个定律既是对唐以前各专制王朝廉政建设的客观总结,也对唐以后各专制王朝具有普遍意义。
(一)创业廉而守成贪
《三国演义》开卷便称:“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揭示了专制王朝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的过程。分裂是乱世,是帝王打天下、夺取政权时期;统一是治世,是帝王守天下、享受政权时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称前者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指帝王)一人之产业”;后者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⑧c]唐太宗集团早就注意到了这种重复的历史现象,并直截了当地称帝王夺取政权为“创业”、巩固政权为“守成”。为了家大业大、使家业永远兴旺发达,进而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创业与守成孰难?”
一般会认为,帝王创业之时,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历经千辛万苦,闯过千难万险,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难无以复加。待天下一统,政权在手,则往往居安忘危,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唐太宗集团正相反,他们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惟命,天授人与,乃为不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⑨c]原来,帝王创业之时正值旧政权败家之际,是利用百姓之不欲来反对旧统治者之贪暴,是散发他人所聚敛之财富给欲活不成、冒死反抗的百姓,以便将其推向战场,充当牺牲品,换取统治权。当此之时,最需要百姓,也最体贴百姓,当然是最清廉的时期,没有条件忙于侈务。甚至也最为慷慨,因为是慷他人之慨。确实,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无法不产生腐败,腐败到一定程度,不推而自倒。因此创业容易,清廉亦不难。创业是为了得天下,天下既得怎能不贪?贪又何以守成?帝王既拥有专制权力,又不滥用、享受权力,简直不可思议。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王朝容易,而取得政权后又不为权力所侵蚀则万难。
上述认识较之只知创业难而不知守成更难因而贪得无厌的人来说,要道高一筹。但创业廉而守成贪乃时代之产物、历史之必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二者虽形式迥异,而实质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在这点上,不宜厚彼薄此,有褒有贬。
当然,先民好怀古恶今也并非无因,它或许与帝王创业廉而守成贪有关,与现实处境一天天恶化而又找不到出路有关。然而,怀古,古已去;恶今,今更糟,专制王朝只能一天天腐败下去。不过,也不能苛求古人,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以从根本上长期有效地解决廉政问题,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那不是他们所应完成的任务。
(二)开朝帝王廉而后代子孙贪
唐太宗集团对历史上各王朝不同时期的帝王作比较说:“历观前代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后世守成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又说:“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味,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或设醴以求贤,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树至德于生前,留遗爱于身后。暨夫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荒无度”。[①d]这是从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环境等外在条件出发,阐明了开朝帝王廉而后代子孙贪的必然性。
乱世造英雄。大好江山一旦失去主宰,就使无数英雄为之倾倒,于是纷纷出世,斗智用武,争坐天下。在如此环境中取胜的一方,非但斗争经验丰富,又必是才能超群,是英雄中的英雄。既取天下,也难忘创业之艰,谨慎治国,清廉执政,以保护来之不易的江山。治世则完全不同。按专制王朝的世袭制,君位继承人不是在斗争中产生,而是在他出生前就命中注定了,并且一出生就与富贵、奢糜结缘,一继位就拥有无限权力,这怎能不昏贪?
历史无法试验。先帝可以把江山传给子孙,却无法将他所经历的历史给子孙们重演,使其在暴风雨中经受锻炼,再展雄风。子孙们离先帝越远,先帝的创业精神就越被遗忘,而且先帝所遗留的巨大家业足以使坐享其成的子孙们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更比一代贪,传代越多积病越深。乱世果真东临,这些深宫中养大的子孙们也势必败下阵来,为草野英雄所取代。
看来,古代盛行的先王观也事出有因,它与开朝帝王廉而后代子孙贪有关。然而,怀念先王,先王已逝;憎恶贪主,贪主又不由自主,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与先王有直系血缘关系,在行贪为恶方面更受制于先王所创造的条件。不应把全部罪责都归于后主,处于后主的条件下,恐怕任何人都很难不昏贪。但他们死于非命,留下骂名,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既不应过分迷信先王之伟大,也不应过分责怪子孙之不肖,起决定作用的是专制制度。
(三)初即位廉而在位时间越长就越贪
不仅从先帝到末代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就每个具体帝王来说,从即位到驾崩,也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对此,唐太宗集团也进行过总结:“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②d]“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一个人,即便是恶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帝王更不例外。恶人称帝自不必言,好人称帝也终将为恶。这里的关键是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定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③d]一般情况下,专制帝王的一生是不断为恶为贪的一生,掌权时间越长就越荒淫,他若功成身退,或许留下美名。然而,历史告诉人们,任何掌握专制权力的人都很难不为权力带来的无穷好处所迷惑,自动退出政治舞台。
因此,帝王不但终身,而且世袭,设法使其权力意志借助血统世代相传。为此,不惜在造就培养继承人上花大本钱、下大功夫:“其语道也必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从节俭,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轻奇物”。“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为什么对君父的宝贵经验、谆谆教诲只遵从于一时?“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①e]权力至高无上,情欲则千变万化,永无满足;权力助长情欲,情欲支配权力;而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情欲任何人也不能无。有这两条就足够了,什么经验教训、理性良知、法律制度都统统长不了,靠不住,一个专制权力掌握在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个人之手,却要他坚守死的规矩,终身清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已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情性领导一切。”[②e]因此,不应过多地责备专制者们晚年失节、昏贪,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专制主义是使人不成其人。这“人”既指百姓,也应包括帝王在内。在专制时代,百姓如牛马,重在维系生存本能的延续,有时甚至连生存要求也难以满足。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老百姓,好的时候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糟的时候想坐奴隶而不得。相反,统治者则不断丧失理性良知,其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无法控制,不断膨胀。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让一个人来统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③e]近代以来,西方更加坚信人的自利本性,对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采取怀疑态度,并创立分权制衡等制度设法限制权力,以防止权力自身的腐败,侵犯公民的权利。这条思路颇为耐人寻味。
三、唐太宗的廉政实践
唐太宗集团以君主作为廉政建设的重心,那么,唐太宗本人做得如何?唐太宗集团发现总结了专制王朝由廉转贪的一般规律,但目的并不是顺从规律,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么,事实上又怎样?
不能否认,唐太宗在一个时期确实做得出色,他节俭自律,为政清廉,垂范百官,从而出现了贞观之治那样千古传颂的好局面。他的名字直到今天还是妇孺尽知,有口皆碑。然而,魏征在贞观十三年列举了他十项“渐不克终”的实例,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由廉转贪的内容,兹择其要者录之于下:
(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俭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三)“贞观之初,损已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移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返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往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五)“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④e]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⑤e]这条经验出自西哲之口,同样适用于中国,唐太宗也不例外。他才称帝几年,就由清醒而昏迷,由无为而多为,由节欲而纵欲,由俭约而奢侈,由忧人而劳人。情欲与权力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丧失了非凡的理性,远离了美好的初衷,忘记了隋朝短命灭亡而血迹未干的教训。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简直判若两人,难以置信。因此,魏征当面批评他:“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善终之美”。[①f]此乃委婉之辞,其实,非但不善不美,且又恶又丑了,虽不可与桀纣之辈等而视之,亦相去不远。绝对权力终于导致绝对腐败,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没有把个人迷信推向顶峰,居然容忍大臣面对面的批评,并将劣迹记录史册,以致于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文明史中粗野的一面。
须知,乱世造就的英雄很少年迈老人,而唐太宗更为特殊。他十几岁帅兵起义,亲手推翻隋朝帝国,不到三十岁登基,主掌大唐天下。他不仅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就个人天赋而言,也足可谓圣明之主、仁受之君,不愧为“一代天骄”。但他同样未能超越由廉向贪的转变。他况且如此,其他出于乱世的鲁莽浅薄之主和治世坐享其成之君,自可想而知。
这里有必要重新审视唐太宗两项有重要影响并颇受后人称道的廉政措施。
关于纳谏。唐太宗并不认为做了皇帝就永远正确,所以不但以史为鉴,又以人为鉴,求谏、纳谏、赏谏,提倡奖励臣下的批评建议,试图集中央百官的群体智慧为一身,以预防个人独断、专横和昏贪。实践上,许多已有或将有的侈务、淫事、贪政,他因采纳臣下的上谏而或停止或取消,甚至将官中众多美女放还归俗。所有这些都早已成为史学界的佳话。
但好景不长,据《贞观政要·诚信》载,唐太宗初即位,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后,还能听人谏,悦而从之;八九年后,则渐恶直言,不喜人谏。人喜欢他人迎合、恭顺、歌颂、崇拜等弱点,在权力的作用下,随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占了上峰,越来越听不进去批评或反对意见,不可逆转地向专横走去。帝王是人而非神,他有情有欲,有衰老死亡,怎能期望他永不糊涂?即使象唐太宗那样的明主,最清醒时期也不过一两年,较清醒时期不过三四年,以后就不得不糊涂了。近现代以来,民主法治国家行政首脑的任期一般为四年,看来这也是基于人性弱点而设。
因此,以纳谏防君贪既非长久之计,又非根本办法。纳谏取决于君主,君主可纳、可求、可赏,也可拒、可禁、可刑,它不外一君一时之聪明,有谁能保证他不糊涂呢?又有谁能判断他何时清醒何时糊涂呢?他清醒时,任何明白话都会说;糊涂时,又什么事不能干?从总体上看,明白的帝王少,糊涂的多;即使明白者,也多时糊涂,少时明白,而且越活越糊涂。所以大臣上谏必须学会察颜观色,否则即有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历史事实表明,勇于直言大臣大多没有好下场。象唐太宗那样坚持在几年的时间里从谏如流,并且终生没有因持异议而制造大规模冤假错案,就足以青史永垂了。纳谏是专制者一种脆弱的理性表现,与近现近民主法治国家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存有质的区别。
以法治吏惩贪。在民主法治国家,以法治吏惩贪是一项长期而有效的措施,但在专制王朝,问题取决于君主。法由君主定,也由君主行;官由君主任,也由君主惩。君主不仅主持立法,同时是国家的行政首脑兼掌最高司法权。那么,君主能否对国家负全责?就唐太宗来说,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是唐以后各专制王朝立法的楷模,甚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他执法审慎而严明,维护法的尊严,大义灭亲。凡此,皆载入史册,传为佳话。
但好景同样不长。唐太宗只是即位初才“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后则“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②f]他个人的喜怒爱憎支配了权力,破坏了由他自己主持制定的法律。这看来奇怪,其实不怪,因为法不外是他用来治官治民的工具,是他个人权力意志的体现,而任何人意志都无法不变,他今天有今天的意志,不可能受制于昨天,而明天的意志又与今天不同。因此,他立法又势必坏法,坏法也同时是立法,君主的权力就是法,君主的喜怒爱憎也是法,甚至比法还大,说到底是无法。正始潘恩所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①g]在中国古代,象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毕竟没有完全置法律不顾,还要为他所爱之重大罪犯“强为之辞”,为他所憎之犯有小过者“深探其意”。其实,他完全能够不“强辞”、不“探意”。只要爱,不管犯何罪也可放可升;只要憎,不管有过无过也可刑可杀。
卢梭说,如果在国家管辖的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②g]“这个人”只能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在中国古代就是帝王。因为帝王专权,可以不遵守法律,所以最大的贪官不怕犯法而怕帝王。臣下若取得君上的信任和欢心,贪也能保官、升官;反之廉也会丢官、受刑。而在通常情况下,臣越贪越能取悦于上,因为他们专伺并满足帝王的私情私欲;臣越廉越难取得帝王的宠爱,因为他既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也不太留意帝王内心的变化,甚至往往触怒龙颜,遭到贪官的仇视和算计。最近与观众见面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虽然不是历史却以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历史,它充分说明了上述道理。帝王如此,朝臣如此,其也各级官员准此类推,均需以上司为榜样、为靠山,贪赃枉法,串通一气。他们若无视上司的眼色行事,秉公执法,过于认真,那可是最可怕的,简直是自断官路。因此,以法治吏惩贪,在专制社会里,不外一场恶作剧,只能越惩越贪,它与民主法治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专制王朝由廉转贪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专制王朝的历史是专制者的情欲与权力日益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升级的历史,是他们的良知、理性、法制等不断为其情欲和权力所征服、否定的历史,也就是走向腐败和自我毁灭的历史。只要专制制度存在,由廉转贪的规律就会重演,就无法走出王朝循环的迷魂阵。应该承认,唐太宗集团对于廉政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出色成就,为中国古代史写下了辉煌一页。但受时代局限,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旨在维护专制权力,而它正是产生腐败的总根源,所以无法改变由廉转贪的定律,避免规律的惩罚。今天看来,这是唐太宗乃至整个专制王朝廉政建设的最大教训,此外,哪怕有千万条经验,也无济于事。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大陆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它固然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有关,但今非昔比,性质不同,而且我们正在寻找古人所无法找到的克服它的有效途径,并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便是改革开放,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秩序,走民主法治之路,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几百年至今仍行之有效的做法,向先进看齐,与国际接轨。如果坚定信心,鼓足勇气,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不是走回头路或为沉重的历史重负所压倒,必将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性胜利,这正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还应指出,廉政自古以来就是大问题,将来,只要有政,只要由人执政,而人性弱点不改,就仍需为政之廉洁作不懈的努力,仍需限制权力,追求法治,不能幻想一劳永逸,放弃对权力的限制和法治的追求。莫说问题如此之大,即便小问题,亦见仁见智,人见人殊。不同时期,不同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对于所面临的同一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基于此,笔者才不揣谫陋,特著此文,以为繁荣学术贡献涓滴之劳,决非否认学界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可喜成果。
注释;
①a 《左传》昭公十四年。
②a 《汉书·禹贡传》。
①b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②b 《贞观政要·刑法》。
③b 《贞观政要·伶约》。
④b 《贞观政要·求谏》。
⑤b 《贞观政要·纳谏》。
⑥b 《论语·颜渊》。
⑦b 《论语·子路》。
⑧b 《贞观政要·伶约》。
⑨b 《贞观政要·君道》。
①c 《贞观政要·君道》。
②c 《贞观政要·纳谏》。
③c 《贞观政要·奢侈》。
④c 《贞观政要·君道》。
⑤c 《贞观政要·俭约》。
⑥c 《贞观政要·慎终》。
⑦c 《贞观政要·务农》。
⑧c 《明夷待访录·原君》。
⑨c 《贞观政要·君道》。
①d 《贞观政要·教戒太子》。
②d 《贞观政要·慎终》。
③d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①e 《贞观政要·慎覆盖》。
②e 《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③e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④e 《贞观政要·慎终》。
⑤e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5页。
①f 《贞观政要·诚信》。
②f 《贞观政要·公平》。
①g 《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②g 《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
